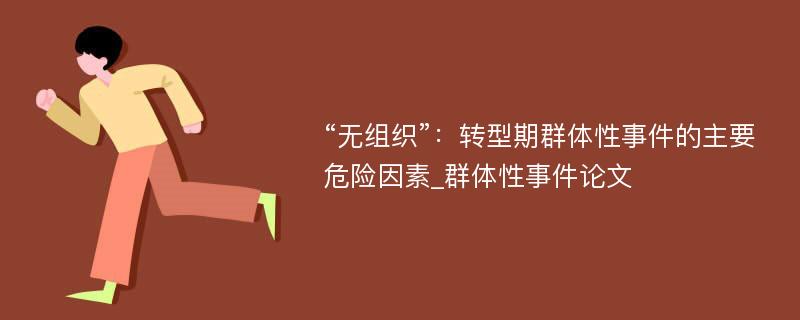
“无组织化”: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风险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因素论文,风险论文,组织论文,群体性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2)02-0038-11
目前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成为中国社会风险的信号。群体性事件一方面破坏性很大,对抗性很强,暴烈程度不断上升,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人身财产方面的重大损失,而且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产生极大的不良社会影响。但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目前处于“不可预测”、“防不胜防”、“乱哄哄”的状态①。很多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发生之后迅速升级,以至失控。在整个过程中,政府连协商、谈判的对手都找不到。为什么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如此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笔者认为,这些现象集中反映了目前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无组织化”。
一、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内在规定性
十余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5年,社会抗争的数量与规模进一步扩大,总共发生了8.7万起15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30%多,平均每天近250起②。而从2006年到现在,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又增加了1倍③。2009年至今,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有增无减,且参与人数、规模和对抗形式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在这些庞大的抗争事件当中,万人以上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社会抗争分布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等各行业;从地理分布上看,社会抗争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广泛性,不论是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农村还是城市,不同程度的抗争时有发生。与此相对应,社会抗争的参与主体呈多样化特点,涉及工人、农民、城市居民、个体业主、退伍军人、退休人员、教师、学生等各阶层人员。我国社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而且情况比较复杂。
“群体性事件”这一名词④,实际上是对目前发生在中国的这一系列新型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总称。因为群体性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的“新现象”⑤。“群体性事件”这一名词,一开始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出现在政府文件之中,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和分类,常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混用⑥。
为了克服这种不足,一些学者给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学术界定。但面对当前中国这类新型社会矛盾或冲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征或类型,学者们在阐述自己的概念时,往往坚持该概念在内涵或研究方法上的独特性,以至于对该概念的理解众说纷纭⑦。从目前国内的文献看,对群体性事件的内在规定性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1)有些研究者在界定其含义时,强调了该类事件的“违法性”特征⑧。而在现实中,违法性的界限是不清晰的,就某一集体行动而言,合法的行动和非法的行动往往交织在一起,行动者可能同时使用合法和违法的方式。而且如果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是非法的,那么很多“依法”或“以法”维权抗争事件就无法包含在内⑨。(2)有些学者强调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性”或“社会危害性”⑩。很多群体性事件的确具有危害性,但应清醒地看到,虽然有些群体性突发事件,表现非常激烈,社会影响也很大,但“它是一种带有对抗性色彩的人民内部矛盾”(11),“一味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违法性特征,甚至认为这类事件同一般的‘群体利益的表达行为’有本质区别,在经验上和学理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12)。而且也有些群体性事件基本在理性可控范围内,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如果一味强调其负面的“社会危害性”,就无法囊括这些事件。(3)有些学者强调群体性事件的“目的性”。比如,邱泽奇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聚集有一定数量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包括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的、有明确利益诉求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路线或公共场所等”(13)。但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为达成某种目的”之说又无法涵盖没有明确目的的事件,比如“社会泄愤事件”或说“非直接利益冲突”(14)。
作为对中国转型时期这类新矛盾的一种总体的、“统摄性”的提法,“群体性事件”一词应该能够涵盖转型时期所有这类新型的社会冲突。笔者认为,这些概念能够达成共识的、能够共享的内在规定性有三点(15):(1)“群体性”,这是指参与人数,这是形成群体性事件最基本的要素。(2)“官民冲突性”或“对抗性”,即“发起者是普通民众,行动诉诸对象是基层政府或其代理机构”(16)。“官民冲突”中的特定参与者使群体性事件能够区别于普通的“社会纠纷”,比如传统的“宗族冲突”、争夺资源的“民间械斗”、“医患纠纷”、“房产物业纠纷”等等,还区别于“球迷闹事”等文化群体现象。这些社会纠纷、文化群体现象与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不针对政府,不把政府或附属机构作为敌对对象(17)。(3)改变现状的政治性诉求程度很低,寻求或者反对的目标一般是具体的物质利益或者较低层次的抽象利益或抽象观念,很多事件只是为了发泄心中不满的泄愤行为(18)。这使群体性事件区别于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和革命。赵鼎新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没有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爆发的结构性条件,正在发生的是大量的只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并没有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的“集体行动”(19)。
二、转型期群体性事件考察的重要维度:“组织化与无组织化”
在获得关于这类事件的统摄性的内涵界定后,如果想进一步研究,就必须对这些外延现象进行适当的分类,才能有更细致的考量和更深入的理解。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群体性事件中,于建嵘认为可以根据“行动者的目的、行为是否具有暴力性、行为指向、组织性、理性程度、持续时间”等五个维度,把目前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为四大类,即“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社会泄愤事件”(20)。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于建嵘有根据新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将原有的四种分类扩展到五种,增加了一种新类型,即“社会骚乱”(21)。于建嵘认为社会骚乱与社会泄愤事件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攻击的目标不仅仅是政府还有不相关者。
赵鼎新从“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改变现状的诉求程度”三个维度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游说、常规政治等一组概念进行分类。在这三个纬度不同程度的组合中,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常规政治等都找到了自己的类型学意义上的空间。具体来说,赵鼎新把“集体行动”定义为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革命”是指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等等;“常规政治”是集体性的政治行为,高度组织化、高度体制性的,并且所追求的社会变革比较小(22)。我国很多被定义为经济利益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应该属于社会抗议活动或正常的常态政治。与社会运动、革命和常规政治相比,集体行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和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都很低,通常没有明确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目标,止于泄愤和闹事。赵鼎新对“集体行动”的表述类似于我国社会广泛使用的“群体性事件”范畴(23)。
单光鼐根据类似的标准,按照诉求、组织化程度、持续时间和对制度的扰乱程度四个维度,将群体性事件排列成一个谱系,那就是:“集体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尚表现为“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是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它既不是诉求明确、组织化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的“社会运动”;更不是带有鲜明政治诉求,有党派势力从中作祟的、社会危象频仍的“革命”前夜。现有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无诉求、无组织、多带有情绪宣泄的集体行为,如万州事件;其二是有明确诉求目的、组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集体行动,其中有的事件因其持续时间较长、组织化程度高一些,已见社会运动的端倪,如前些年的汉源事件(24)。
朱力从冲突指向的目标、冲突的原因、冲突的组织性、冲突的理性化四个维度将群体性事件分为“经济型直接冲突”和“社会型间接冲突”。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经济型直接冲突是指向强势群体或政府,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通过有一定组织的、较理性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冲突只是达成目的的工具。而社会型的间接冲突指向政府和公安机关,导火索具有任意性,行为方式无组织性、人员具有临时性,非理性化,冲突本身不是工具而是目的(25)。
通过对以上分类方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维度是他们共同分享的,就是“行为指向”和“组织化”。其中“行为指向”这一维度在当前中国,“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不成为直接诉求对象或诉求第三方的集体行动很少发生”(26)。而且若不指向政府,那也就不具有当下的迫切性了。其实其他维度比如“理性化”、冲突诱因的“不可预测性”、冲突诉求有无“目的性”、“可控性”则都是基于“组织性”的缺失,没有组织性,以上维度都不可能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组织化与无组织化”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有洞察力的维度。根据行动的是否具有组织性,可以将林林总总的群体性事件重新整合,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具有一定程度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比如“维权行为”、“依法抗争”(27)、“以法抗争”等等。对于这类群体性事件,由于通常基于某种权利或经济利益,有一个矛盾积累的过程,矛盾和事件的原因较为明显。而且冲突只是维权的手段,参与者具有组织性和理性化的目的,具有一定的自我约束能力,对于政府的冲击强度大而烈度小,较少出现严重的越轨行为和直接破坏政府设施的情况,是完全“可防可控”的。
另一种是基本没有任何组织化成分的群体性事件,比如目前愈来愈多的“社会泄愤性事件”、“社会骚乱”、“无直接利益冲突”(28)等等。对于这类群体性事件,由于没有任何组织性,事件的诱因具有偶发性和任意性,参与的人员也是临时聚集起来的,身份混杂,处于“匿名化”状态,不具有理性化的目的,没有明确的利益目标,对自我也不具有约束力,容易产生越轨行为和暴力行为,冲突的烈度更大,破坏性更强(29)。如何防控这类群体性事件是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三、群体性事件中“无组织化”问题的表现及其风险
近年来后一类群体性事件在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比例越来越高,比如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6年的浙江瑞安事件,2007年的四川大竹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等等。在起因、过程、后果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国内目前也把这些事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或“无直接利益冲突”(30)。这些事件除了具有“泄愤”、“无直接利益冲突”等特点外,更为根本的特征就是“无组织化”,所以笔者认为也可以称之为“谈判者缺席”的群体性事件(31)或“无组织化群体性事件”。
所谓组织,是旨在实现集体目标而建立起来的有一定结构的社会团体。组织为政治生活中有目的的集体活动提供了基础(32)。“组织化”是针对社会层面的有组织状态而言。“组织化”的社会和我们常说的公民社会的状态具有相似性。社会组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活跃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具有独立性、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各种社会组织或公民组织。怀特(Gordon White)认为:“从公民社会这一术语的大多数用法来看,其主要思想是,公民社会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33)康豪瑟(Kornhauser)认为,正常的社会在结构上应该有三个层次,即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所谓中层组织即“处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比如当地社区组织、志愿者组织和职业团体等等”(34)。由此可见,公民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介于国家与家庭、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其特点是“中间性”(35),是保证公民权利和理性参与的民间机构和组织。
在中国的语境下,“组织化”指的是在我国社会层面的自我组织化。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群体明显分化,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现实面前,分散的利益主体能够基于其利益的多样性,进行联合并以一定的组织结构约束这种分散状态,以实现分散利益的凝聚和理性表达。而“无组织化”指的是我国社会中间组织或说公民社会组织的“历史性缺失”(36)。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社会组织严重匮乏,没有比较成熟的居于国家与民众中间的社会组织,不能提供整合民众离散化利益表达诉求以及利益协商的平台和机制,社会利益群体的中间组织和协商机构处于缺位的状态(37)。“无论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还是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城市中产阶层,其社会自组织的机制都远远没有建立起来。”(38)
这种社会层面的“无组织化”,在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矛盾集中的社会转型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直接影响到转型期社会抗争的表现形式和社会冲突的冲突烈度,集中体现在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群体性事件中,表现为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问题。这种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危险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事件发生的难以预防性。这类群体性事件一般具有突发性,难以预防。由于协调机制的严重匮乏,不仅特定群体的代言人或代言机构缺位,而且也缺乏基层民众与上级政府的有效沟通渠道和利益表达渠道,缺乏基层民众与地方政府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机制,导致地方政府无法提前预判或及时发现、提前化解群体性事件(39)。在社会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偶然事件就可引起群体性事件(40),所以,这类事件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呈现出“不可预测”、“防不胜防”的特点,使政府对于预期的社会矛盾失去判断力。
第二,事态发展的难以控制性。由于群体性事件没有组织者,事态的发展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无法控制、一哄而上的自发状态。非组织化的情绪、传言、谣言和其他偶然因素在群体事件中起很大作用(41)。基本属于西方社会运动领域所定义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action),“相对自发的和无结构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方式”(42),“现场临时凑集起来的一群人,缺乏持久的结构,没有固定群体的可预料性”(43)。绝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的最初起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参与主体涉及工人、农民、城市居民、个体业主、退伍军人、退休人员、教师、学生等各种群体。这是其区别于维权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最主要特点(44)。这类事件一旦发生,便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地方政府往往难以正确研判事件发展的趋向,无法控制群体性事件的走向。
第三,难以协商解决,处理手段单一化。在群体性事件一哄而起之后,由于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国家面对的是原子化的个人,政府很难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一般来说,任何群体事件发生,都有不同程度的组织者和动员者,但在中国社会中,由于长期以来特殊的社会结构(45),加上政府对待群体事件的组织者态度较为强硬,所以在近年发生的群体事件中,当政府需要对话和需要沟通时,却发现这些事件参与者中,很难出现坦诚和负责任的谈判者(46)。政府往往不得不和众多分散的个体展开利益协商(47),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对政府而言,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几乎没有任何协商、斡旋手段,采取强硬手段往往比协商解决更为可行,而且往往是地方政府手中唯一的手段。
第四,直接面对政府。这类群体性事件最终往往会导致“直接面对政府的对抗性行为”。地方政府势必成为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当事方。分散的、无组织、不理性的民众,加上可供选择的处理方式的匮乏,最终导致对抗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这正是当下群体性事件发展的普遍内在逻辑,也是当下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风险因素。由于长期以来,基层群众没有自我组织机构,没有正常利益协商与表达机制,无法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所有问题都要依赖政府解决。政府是群众群体利益诉求的唯一直接诉求对象,是群众诉求的第一时间处理者。同时,基层地方政府直接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而没有任何中间组织作为“缓冲地带”来汇集、整理、协调、以理性方式表达民众的分散化诉求。当群众分散化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由于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调整和缓冲,最终导致民众与政府直接对话来解决问题,而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地方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直接对话的一种极端表现,最终导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摩擦碰撞,乃至激烈冲突。群体性事件因此呈现出“对抗性”的特点。
第五,无法制约公权力。在应对的过程中,由于基层民众没有有效的组织机构,“高度原子化的社会无法制衡政府”(48)。同时,政府面对原子化、分散的个人,没有任何有效的协商、谈判、斡旋手段。最终导致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从政府的角度往往倾向于使用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实际上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这种缺乏制衡又无其他选择的公权力,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往往会采取过分的强硬手段,甚至滥用而损害民众利益,最终导致了社会情绪的暴戾化,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第六,冲突的暴烈性。当政府与民众在群体性事件中一旦处于直接对话的摩擦状态,由于表达的无序化和无组织化,政府难以通过协商的渠道解决问题,一旦问题坐大,只能动用暴力压制,导致事态必然趋向暴戾化(49)。“对于民众而言,如果冲突是工具性的,并被视为是实现冲突群体清晰目标的手段,冲突的暴力性水平将会下降。”(50)但由于我国社会民众处于“相对自发的、无组织和不稳定的状态”(51),对于他们而言,冲突并不是理性的、工具性的、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对于政府而言,由于缺乏协商解决的必要机制,利益群体的代言机构缺位,没有谈判对象,政府面对的是群体性事件中原子化的个人,而且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制衡,在缺少其他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往往使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所以,相对其他类型群体性事件,无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冲突的烈度更大,破坏性更强,容易产生越轨行为和暴力行为,呈现出“暴烈性”、“破坏性”、“乱哄哄”的特点,“往往会产生大规模的社会骚乱”(52)。事件中的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四、结语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的表现形式,而“无组织化”是目前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社会抗争与社会冲突完全无组织化的表现形式,直接导致社会冲突与社会抗争行为的“不可预测”、“防不胜防”、“乱哄哄”的状态,以及“暴烈性”、“破坏性”的后果。尤其是在利益冲突比较集中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社会中间组织的缺失,分散的个体很容易被卷入群体化的行动之中。无组织的、原子化的大众社会是“一个可以被任何政治目的所利用的资源,唯独难实现的,恐怕就是有效的理性沟通、协商和妥协”(53)。
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这一问题是如何形成的?社会层面的无组织化是如何传导到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中来的?社会组织的缺失如何决定社会矛盾爆发的形式?这些问题深层次的结构根源是什么?如何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自发性”、“对抗性”,引入“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使群体性事件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有序”、“可控”?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单光鼐:《尽快开启越来越逼近的制度出口——2009年群体事件全解析》,载《南方周末》2010年2月4日。
②Jeff Riedinger(2006),Set China's Farmers Free,Journal of Wall Street,23 May.相关资料还可参见于建嵘《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2007年10月30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118361.赵鹏等《“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36期。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载《学海》2009年第1期。
③米艾尼:《专家称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稳定最大威胁》,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期。
④在对“无组织化”群体性事件进行界定时,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其属概念的“内在规定性”,然后根据其“种差”进行概念的细分。参见方雷《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章。
⑤柳建文:《“行动”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对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解释框架》,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⑥“群体性事件”这一用词较早出现于《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公安部2000年4月5日。其定义强调群体性事件的“违法性”和“危害性”。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定义淡化了“危害性”,却强调了“违法性”。参见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⑦对于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界定可参见: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王战军《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其多维分析》,载《政法学刊》2006年第5期;宋宝安、于天琪《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影响》,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笔者认为,对于群体性事件定义的多样性或说混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概念是对众多综合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总称,涵盖了多种维度和多种分类标准,没有抓住这类现象的独特属性,而且细分的标准在同一分类中前后不一致。
⑧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2页;王战军《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其多维分析》,载《政法学刊》2006年第5期,第12页。对于群体性事件违法性的讨论可参见: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笔者认为,从程度上很难区分应星所说的“个别的、轻微的”违法现象,而王战军所认为“群体性事件中所使用的方式都是未经合法许可的”也很难一概而论。“违法性”不应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总体的、“统摄性”的概念的内在规定性。
⑨Li Lianjiang and Kevin J.O'Brien,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Modern China ,1996(1),Volume 22; Kevin J.O'Brien and Li Lianjiang,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4.
⑩“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损害公私财产安全的社会事件。”见林维业、刘汉民著《公安机关应对群体性事件实务和策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公安部2000年4月5日),认为群体性事件是“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这一定义强调群体性事件的“违法性”和“危害性”。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中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淡化了“危害性”,却强调了“违法性”。参见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1)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载《学海》2009年第1期。周永康指出,深入分析这些群体事件,基本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问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谐社会首重稳定,群体性事件多发亟待关注》,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23842526232576/20050706/580196.shtml.
(12)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有些学者给出了较为中性的定义,比如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载《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3)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载《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4)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钟玉明、郭奔胜:《社会矛盾发新警号: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出现》,载《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0月17日。
(15)于建嵘认为群体性事件有四点共同的规定性:群体性、违法性、共同行为取向、社会影响。第二点现实中边界很模糊,第三点和第四点是不言自明的,已经包含在第一点中,所以只有群体性是所有定义都承认的,参见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王国勤认为有三点共享的基本特征:发起者是民众而诉诸对象是基层政府或其代理机构,群体性、行动方式是从有节制的到逾越界限的连续谱系。参见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王来华、陈月生认为有六点共同特征,见王来华、陈月生《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含义、特征和类型》,载《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5期。
(16)赞同这一点的学者如: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载《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宋宝安、于天琪《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影响》,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笔者赞同邱泽奇将针对政府及其代理机构的称为“群体性事件”。但他将不针对政府和其代理机构的事件称为“集体行动”,这一用法可以商榷。
(17)于建嵘认为“社会纠纷”也属于群体性事件的范围。参见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制困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笔者认为群体性事件不应包含社会纠纷,因为:一是社会纠纷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群体性事件却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所特有的现象;二是社会纠纷不具有官民冲突性;三是群体性事件的范围不应过大,否则就会失去这一概念的针对性和其所应有的学术意义。类似的观点见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载《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另外,如果不强调官民冲突性,那么按照于建嵘对群体性事件的四点界定:群体性、违法性、共同行为取向、社会影响,那么“球迷闹事”也可以算作群体性事件。
(18)认为群体性事件具有低政治诉求性的学者如: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覃爱玲《散步是为了避免暴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专访》,载《南方周末》2009年1月14日。
(1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301页。
(20)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21)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3)王赐江:《“集体暴力抗争”一种值得高度关注的极端维权方式——对2008年“贵州瓮安”等三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分析》,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
(24)覃爱玲:《散步是为了避免暴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专访》,载《南方周末》,2009年1月14日。
(25)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载《学海》2009年第1期。
(26)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27)相关文献可参考:Li Lianjiang and Kevin J.O'Brien,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J].Modern China,1996(1),Volume 22.Kevin J.O'Brien and Li Lianjiang,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G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4.Thomas P.Berstein and Xiaobo Lü,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17.
(28)钟玉明、郭奔胜:《社会矛盾发新警号: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出现》,载《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0月17日。
(29)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载《学海》2009年第l期。
(30)对于这类事件,有学者称之为社会泄愤事件,有的学者称为非利益相关冲突。罗干2006年11月27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政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着历史使命》中指出:“在一些地方,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这种社会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可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1)谢泳:《设法解决群体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载《南方周末》,2007年9月12日。
(32)[美]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
(33)Gordon White,"Civil Society,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Democratization,Vol.No.3,Autumn 1994.,pp.375—390.
(34)William Kornhauser,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The Free Press,1959,p.74.
(35)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治理的变迁》,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36)王锡锌:《利益组织化、公众参与与个体权利保障》,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4期。
(37)据资料统计,我国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NGO)的数量为2.7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一般超过50个,美国为51.79家,法国则高达110.45家),而且低于印度和巴西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般超过10个)。社会中间组织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0.73%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的水平,也低于4.6%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据调查表明,当前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学术交流团体,占总数的48%,其次是业务团体,占28%,利益代表和公益型的分别占约6%。当前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还较少。
(38)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研究报告:《走向社会重建之路》,2010年9月。
(39)张紧跟:《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看群体性事件》,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3期。
(40)比如,万州事件起因是重庆市万州区一名自称局长的男子与其妻当街暴打挑夫后,引发公愤致使出现群体性事件。瓮安事件是初中生跳河自杀引发的。石首事件是一名厨师暴死在其工作的饭店门口引发的。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越来越多的呈现出偶发性和不可预测性。
(41)单光鼐:《尽快开启越来越逼近的制度出口——2009年群体事件全解析》,载《南方周末》2010年2月3日。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159/0.
(42)[美]尹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赵明华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65页。转引自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载《学海》2009年第1期,第70页。
(43)[美]刘易斯·克赛等:《社会学导论》,杨心恒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页。
(44)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45)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1993年12月香港召开的“华人社会之社会阶层研究讨论会”参考论文。http://www.xschina.org/show.php? id=1441.
(46)谢泳:《设法解决群体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载《南方周末》,2007年9月12日。
(47)张紧跟:《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看群体性事件》,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3期。
(48)张紧跟:《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看群体性事件》,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3期。
(49)张紧跟:《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看群体性事件》,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3期。
(50)[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51)[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8页。
(52)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载《学海》2009年第1期。
(53)王锡锌:《利益组织化、公众参与与个体权利保障》,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