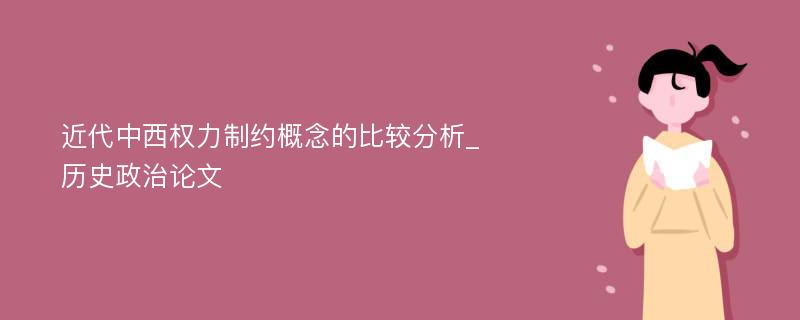
中西近代限权观念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近代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集中于权力和权利两个元话语维度,由此带来的是现代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革命性变化,在语义、语词、语法等诸多方面整体地实现了古今之间的超越。单就权力的维度来看,发展权力与限制权力构造了一个两难困境,它甚至超越了中西两分的语境,具备了一般的现代化意义。本文试图从中西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权力与限制权力的一般理论作一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基本命题。
一、权力宰制法治:近代中国法治的双重负累及其畸变
在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发展权力与限制权力、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双重诉求带来的是法治发展的双重负累。应该说,人们并非没有正确认识西方法治,然而,在双重负累的重压下,人们逐渐偏离了西语法治文本的内涵,走上了一条沉重的法治之路。
梁启超早年从限制权力、保障权利两个方面理解西方法治,可以说是抓住了西方法治精神的实质。然而,梁启超时而主张兴“民权”,以自由、平等为“救世之良药”;时而主张重“国权”,以君主立宪为“适时之美政”,① 表现出无所适从的政治心态。而后,梁启超由英美自由主义转向了德国的国家主主义,主动地离开法治价值,走向了独立与富强的目标。他指出:“我中国今日所最缺而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② 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独立与富强的压力使梁启超不但把自由与平等放到了次要位置,而且将团体自由视为自由的实质。他认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③及至最后,梁启超甚至“将任何有关个人自由的法规都看作是对他所怀抱的集体自由的潜在伤害”,④ 其基本的政治主张甚至从“君主立宪”退至“开明专制”。
严复的困境亦在于此。早年严复大量译介西方法学著作,深得西方法治观念的真谛。在严复看来,民主政治并不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根本,与自由相比,民主只不过是实现自由的工具而已。他明确指出:“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⑤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严复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⑥ 的政体原则,可谓开中国法治观念之先河,闪烁着真知灼见。然而,后期的严复则逐渐走向国家主义。在“国群自由”与“小己自由”之间,严复认识到,中国需要的并不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个人权利,而是所谓的“国群自由”。他指出,“故所急者,国群自由,而非小己自由也。”⑦
在强调个人自由与达成国家富强的两难困境中,严复、梁启超等早期的自由派试图以所谓的“调适”为手段将两者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其结果却是在富强与独立的诱惑下转向了国家主义。直到20世纪中叶,国家主义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直接影响了傅斯年、丁文江、钱端升、蒋廷黻、翁文灏、林同济、雷海宗等人。陷入误区的政党政治、多灾多难的议会政治、形而虚设的司法机构、腐败的行政系统,这一切让人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生下的畸形儿。身为芝加哥大学博士的蒋廷黻甚至认为,“我们愈多谈西洋的主义和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⑧
事实上,作为革命派的孙中山亦试图依靠军阀的力量完成革命,承认在中国实行“宪政”之前实行“军政”与“训政”的必要性。即使是胡适、罗隆基等“人权派”亦更多受英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一自由主义流派思想特质中“积极自由”的成分使他们对权力的戒备马马虎虎。在胡适的身上,人们仍然会发现这样的吊诡,“一边反现政府,一边又维护现政权。维护现政权,是出于反暴力;而反对现政府,则是为了搞宪政。”⑨
“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现世处境与“心向共和,身在君主”的马基雅维里情结成为百年中国法治主义者的真实写照。在衣食无足、仓廪不实的情况下,内外交困的中国人不但不会将宪政建设同权力的限制与权利的保护联系起来,反而会以富强与独立置换法治本身的价值,创造所谓的“中国式宪政语境”,⑩ 将国家的建构视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今天看来,中国的自由派蜷曲着期待伸展,其真正的价值更多的在于这样一种思考的开启:“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不仅自由、富裕,也是文明与道德的理想社会。”(11)
一方面,人们渴望强大的国家权力以实现法治,而另一方面,掌握了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却无所顾忌,在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中制造越来越危险的肥皂泡。这种膨胀迅速地推倒还停留于思想层面的法治围墙,畅通无阻地侵入了社会领域。在权力的宰制下,所谓的“法治”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民意强奸。梁启超不无讽刺地指出:“近来听见世界有个‘法治’的名词,也想捡来充个门面,至于法治精神,却分毫未曾领会。国会省议会,天天看见第几条第几项的在那里议,其实政府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民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议员自身更没有把他当一回事。”(12)
通观近代中国法治的发展,我们发现,限制权力的观念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宪法要么是缓和阶级矛盾的花言巧语;要么成为强权刺刀下的俘虏、军事独裁招摇过市的遮羞布。一方面是权力的缺失,无论是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国民立宪,均成无根游谈,宪法成为勾划乌托邦的废纸,在权力的宰制下成为麻木的玩偶。另一方面则是权力的专断,无论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还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均成专制、独裁的粉饰与伪装,在权力的膨胀中演绎了引火自焚的悲剧下场。
二、主权高于法律:从马基雅维里到卢梭
主权的一元论符合了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运动。然而,主权观念的甚嚣尘上并没有使对权力的制约问题销声匿迹。就理论形态来看,至高无上的主权观念同西方文化传统的法治观念存在着冲突,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进程充满了主权与理性自然法的痛苦挣扎,使得人们在坚持主权观念的同时亦陷入了混乱与分裂。在权力与法治之间,一元论者首鼠两端,既渴望强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又一厢情愿地希望这种权力接受法治,最终在权力与限制权力的两难选择中买椟还珠,使法治陷入困境。
民族国家的第一位代言人就是马基雅维里,然而,它同时又把这位虔诚的朝圣者分裂为第一个思想怪物。在这位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的思想奇才身上,深深地埋藏了一种“心向共和、身在君主”的“马基雅维里情结”。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主题是尖锐的,它集中反映在所有政治的核心问题上,即“权力和良心之间,力量和美德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他拒绝接受常规的答复并坚持认为总能找到答案”。(13) 马基雅维里情结的悖论性被外化在1513年写成的《论提图·李维的前十卷》以及《君主论》这两本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著作上。在第一本书中,作者盛赞罗马的共和政体,视其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而在后一本给作者带来极大声誉的书中,作者却转而赞成君主制,主张意大利采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狄克推多制”,从而完成意大利的统一大业。对前一本书,其中的大部分能让“十八世纪的自由派读了点首赞许”;(14) 而后一本,即使是专制君主读了也会感到害羞。对此,马基雅维里做出的解释是:“在腐败的城市维系或创新共和体制有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在那儿维系或创造一个共和体制,那么把它转向国王政体比转向平民政体更有必要,俾使由于傲慢而不可能被法律纠正的人可望因君主的权力而有所节制。”(15)
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马基雅维里的良苦用心。为了实现共和理想而通过君主政体求得秩序、实现法治正是马基雅维里的苦衷与尴尬,它是马基雅维里情结的最关键的一个结,但却是个“死结”。
如果说马基雅维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进退维谷是意大利长期分裂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布丹在主权问题上的混乱不堪则恰恰是法国内战的思想倒影。市民阶级的成长和国内的动荡使布丹在马基雅维里之后成为主权困境的殉道者,半推半就地做了君主专制的辩护人。
与马基雅维里一样,布丹亦是出于对秩序的考虑和强大主权的追求而离开民主共和,选择君主专制的。尽管布丹认为民主政体合乎自然,但他还是选择了君主政体,并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是实现真正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的惟一形式。在布丹看来,无论是贵族制,还是民主制,都容易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只有君主制才能充分地体现主权的力量,从而保障政治稳定。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仅仅作为自然过渡环节的家庭被布丹改造,用来对抗绝对权力。布丹区分了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国家与家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罗马法管辖权的观念,试图以不可剥夺的家庭权利来对抗至高无上的王权。这种区分使布丹的国家理论同时包含了两个绝对物:“家庭的不可取消的权利”和“主权者的无限立法权力”。然而,当布丹试图将“家庭不可转让的权利同国家的绝对权力联系在一起”时,他的理论“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逻辑困难”,在这一点上,布丹陷入了“彻头彻尾的矛盾。”(16)
另一方面,布丹试图以所谓的“高级法”(17) 弥合主权与法治之间的矛盾,即以高级法限制主权。这就又引入了布丹主权理论的第二对“绝对物”:即主权与“高级法”。在这一点上,布丹再一次陷入了混乱,这一混乱甚至成为“法理学上分析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长期争论的起点”。(18) 当人们审视布丹的主权理论体系时,他的混乱几乎是被贴在脸上的:一方面,他要求主权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作为最高主权者的君主遵守自然法的规范,宣称“君主没有权力反对自然法”。(19) 在这样的“双重权威”面前,布丹无法做出决断。(20)
布丹的混乱是近代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关节点。如果将布丹的混乱放到民族国家兴起的大背景下观察,人们就会发现,布丹的混乱只是一系列困境的一个环节,所有以主权为手段分析国家的理论都无法绕开它。它就像一个“连环套”,在布丹之后,不但套住了作为专制主义者的霍布斯,而且还将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卢梭绑在了一个更为困惑的结上。
阿伦特曾经指出:“一切运动的特点都是蔑视法律”。(21) 民族国家以主权为自己辩护,要求以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作为后盾来拓展空间,这就注定了主权理论蔑视法律的本性。对权力与稳定的渴求终于使本来就摇摆不定的一元论者否认对主权的法律约束,以强大的权力淹没了法治。马基雅维里完全将法律作为达到政治统治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22) 在马基雅维里的双重标准中,统治者不仅“置身于法律之外”,而且“不受道德的约束”。(23) 布丹亦明确地以法律为假想敌人,拒斥法律对主权的限制。他指出,主权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指挥的一种绝对的、永恒的权力,它是“超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24) 主权者则因此而超然于法律之外,法律的权威只及于除主权者之外的所有人。(25)
霍布斯继承并发展了布丹的主权理论,两人的主权理论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性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格兰,对强大权力的渴望是一致的。霍布斯赋予君主的“主权权利”几乎无所不包,而且,霍布斯断然否认任何对主权者的约束。他指出:“国家的主权者不论是个人还是会议,都不服从国法。因为主权者既有权立法废法,所以便可以在高兴时废除妨碍自己的法律并制订新法,使自己不受那种服从关系的约束;这样说来,他原先就是不受约束的。因为愿意不受约束就可以不受约束的人便是不受约束的。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自己负有义务,因为系铃者也可以解铃,所以只对自己负有义务的人便根本没有负担义务”。(26)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霍布斯认为,主权者的自我约束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市民法是全体市民的法律,所以全体市民不受市民法的约束。如果全体市民受市民法的束缚,那他就是自我约束”。(27) 为了强调主权者的不受约束,霍布斯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主权循环悖论为主权者的不受约束提供了最为经典的论证。在探讨国家致弱和解体的因素时,霍布斯指出:“主权者本身(也就是国家)所订立的法律,他自己却不会服从。因为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国家,服从国家就是服从主权代表者,也就是服从他自己;这就不是服从法律,而是不受法律拘束了。这种错误的看法由于将法律置于主权者之上,便同时也将一个法官和惩办他的权力当局置于他之上,这样便是造成了一个新的主权者;由于同一理由,又可将第三个人置于第二者之上来惩罚第二者,像这样一直继续下去,永无止境,使国家陷于混乱和解体。”(28)
霍布斯描述了以法律限制主权存在的困境:“主权之上的主权”使主权陷入了一个无休止的循环,即对主权的限制会造就一个新的主权,而新的主权又要接受限制,再造一个新主权……最终,人们变得无所适从,国家亦陷入混乱和解体之中。
事实上,霍布斯的这种主权循环悖论在洛克那里亦被以一种绝断式的陈述表达出来。在《政府论》一书中,他几乎是以相同的口吻说道:“在一切场合,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因为谁能够对另一个人订立法律就必须是在他之上。”(29) 在洛克那里,尽管论证的逻辑与霍布斯有着惊人的一致,但论证的主体还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使洛克议会主权的民主性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从而使洛克有资格成为霍布斯与卢梭之间的一条纽带。
在理性与意志、权力与约束之间,卢梭的一元论向前走了一大步,从而形成了人民主权的理论,但是,他也并没有解决权力约束的难题,反而沿着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的路线滑向了主权一元论的最深处。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卢梭的理论与霍布斯的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就一元论的主权逻辑来看,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就权力约束的问题,卢梭亦发出了“不得约束自身”的禁令:(30)“主权者若是以一种为他自己所不得违背的法律来约束自己,那便是违反政治共同体的本性了。既然只能就唯一的同一种关系来考虑自己,所以就每个个人而论也就是在与自身订约;由此可见,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根本法律是可以约束人民共同体的,哪怕是社会契约本身”。(31)
一元论的主权观强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的主权,这就使得主权的拥有者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按照这样的主权理论,有了主权者,就不会有自由;或者说,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就找不到主权者。无论是君主主权,还是人民主权,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是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还是卢梭,他们的困境在于过于张扬一元论的主权观念,结果却挤掉了法治的位置。
三、限权之限:政治思想的历史与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与逻辑是相统一的,历史的起点当然是逻辑的起点。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不难理解中西政治思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此不同的理论,却又如此近似的逻辑。对于这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列宁明确指出,“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和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32) 因此,权力限制的逻辑既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需要我们“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历史。(33)
权力的无限扩张无疑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通过对西方政治发展史的长期观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34) 这一权力定理被广泛地认可,揭示了权力运作的特征。
在权力造成的暴政面前,限制权力就成为人们良好的愿望。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是超越时间和地点的。如果说阿克顿的“权力定理”概括了权力运作的一般特征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限制权力的时机、对象以及方法等诸多方面。正像中西法治现代化过程中诸多政治思想家所遭遇到的那样,在这一系列问题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答案,而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均衡。正是发展权力与限制权力之间的动态均衡,完成了权力的分配与限制的一系列制度。它不但解决了种种利益冲突,而且为制度冲突提供了基本的评价标准。
西方社会对强大王权的要求体现在民族国家的兴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西欧社会希望从长时间的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发展民族经济、政治与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统一,代表着进步,发展王权成为时代的要求。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在事实上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35) 与这一历史相吻合的正是从“国家理性”到“主权”学说的近代西方国家理论发展的一般过程,反映了封建割据的欧洲各国要求统一的迫切愿望,成为“塑造现代化欧洲的决定性因素”。(36)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当中,我们发现了一整套绝对主义的理论脉络,从马基雅维里到霍布斯,甚至直到民主思想家卢梭那里。他们不仅主张主权的至上性,强烈反对限制权力,还强烈地反对分权、权力的制衡。然而,西方社会后来形成的宪政主义竟是从这些人的身上发现了法治、分权、限权等理论资源。这种看起来极为悖谬的政治思想史发展脉络的背后,有其清晰的逻辑建构,使我们再一次发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来看,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就国内的情况来看,清王朝的皇权已经崩溃,新的全国性的权力还没有产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列强却步步紧逼,形成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的民主派不但面临着建设民主的使命,同时还担负着民族独立与富强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王权,还是军阀的权力,都成为人们饥不择食的选择。
事实上,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存在着“内生”与“外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处境。然而,发展权力与限制权力的主题却是惊人地相似。同时,发展权力与限制权力亦并不是一个完全能够在时间上分清先后的序列。发展权力也限制权力并不要求权力作为一个体系而存在;部分权力的发展与部分权力的限制可能并行不悖。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超出约束与限制,权力解决了膨胀的饥渴,同时亦饮下了覆灭的毒酒。面对人民大众强烈的民主诉求,掌握实权的统治者一味地拖宕、回避,只能是错过良机,在进一步激化的矛盾面前走向毁灭。当清政府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欲开国会,行宪政时,其威信已经扫地,政权亦处于土崩瓦解的边缘;一党专政多年后,国民党政府才想起要实行所谓的宪政,然而,政权风雨飘摇,大势已去。没有权力,法治根本无从谈起;而过分膨胀的权力却必然走向毁灭,这正是权力失败的奥秘:没有法治的约束,权力往往难以跳出其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最终走向失败。
就近代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来看,强调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法治体系确实为权力的滥用提供了解毒剂,成为权力限制在制度层次的总要求。但是,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历史还告诉我们,限制权力、保障权利也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无须论证的普遍真理。
注释
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三,第69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③ 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四,第44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④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第14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严复:《严复集》,王栻主编,第1册,第3页、第11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⑥ 严复:《严复集》,王栻主编,第1册,第2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⑦ 严复:《严复集》,王栻主编,第4册,第98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⑧ 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蒋廷黻选集》,第45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国台湾),1979年版。
⑨ 邵建:《事出刘文典》,载《书屋》,2002年第8期。
⑩ 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1)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第30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就这一思想,本文还参考了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22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 梁启超:《组织能力及法治精神》,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167~168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13)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3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4) 罗素:《马基雅维利论》,载马基雅维里:《君王论》,第172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15) 马基雅维里:《李维罗马史疏议》,第55页,左岸文化(中国台湾),2003年版。
(16)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第467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7) 刘山等的译文原文为“《帝国法》”。参见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第466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据本文作者所知,布丹并没有这样一部著作。该词原文为拉丁文“leges imperii”,其中,imperii的英文解释有command; authority; rule,supreme power; the state,the empire等意,根据布丹的理论体系,“leges imperii”词意类似考文所称的“高级法”,而不应译为“《帝国法》”。参见George H.Sabine,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50,p.409.本文参照原文有所修改。
(18)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第467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麦克里兰亦认定布丹在这一点上容易陷入矛盾。但是,人们可能因为过于从现代立宪主义角度出发,从而夸张了这一矛盾。参见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第322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19) Jean Bodin,On Sovereignty:Four Chapters from The Six Books of a Commonwealth,trans,Julian H.Frankl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3.
(20) Julian H.Frankin,Jean Bodi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t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p.70~92.参见杨永明:《民主主权:政治理论中主权概念之演变与主权理论新取向》,载《台大政治科学论丛》(中国台湾),1996年第7期。
(21) 汉娜·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第352页,时报文化(中国台湾),1995年版。
(22)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3)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第40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4) Jean Bodin,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vail,translated by M.J.Tooley Oxford:Basil Blackwell,1955,p.25.Jean Bodin,On Sovereignty:Four Chapters from The Six Books of a Commonwealth,translated by Julian H.Frankl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3.另可参见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第462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5) Jean Bodin,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vol1,translated by M.J.Tooley Oxford:Basil Blackwell,1955,p.43.
(26) 霍布斯:《利维坦》,第20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7) Thomas Hobbes,Man and Citizen,edited by Bernard Gert,Gloucester,Mass:Peter Smith,1978,p.183.
(28) 霍布斯:《利维坦》,第25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9) 洛克:《政府论》,下卷,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0) 该用法参见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载埃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第2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31)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6~2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2)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4)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4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2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36) A.P.d'entreves,Natural Law :An Historical Survey,New York:Happer & Row Publishers,1965,p.66.另外可以参见Jack Lively and Andrew Reeve,The Emergence of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The Artificial Political Order and Natural Social Orders,Robert Fine and Shirin Rai,Civil Society:Democratic Perspectives,London,Portland,Or,1997,p.64.
标签:历史政治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政治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梁启超论文; 法律论文; 布丹论文; 商务印书馆论文; 君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