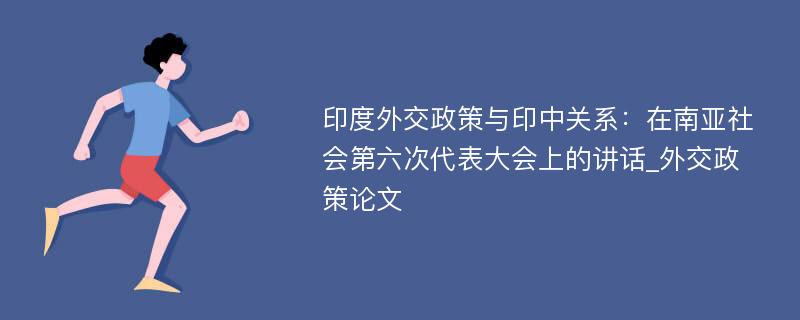
印度的外交政策与印中关系——在南亚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亚论文,外交政策论文,印度论文,第六次论文,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朋友们:
感谢你们在我来北京履新之际给我这次发言机会。很高兴今天能在在座诸君之中再次看到一些对印中关系怀着良好愿望的老朋友。
我应邀就印度外交政策与印中关系发表讲话。我非常愿意利用这次机会和你们交换意见。因此,我将先就印度的外交政策、形成这一政策的决定因素和印度对当今世界的观点,再就印中关系、这一关系的现状和展望简要发言。嗣后,我愿意以问答和评论的方式听取诸位的意见。
印度的外交政策
印度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自然与制约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目的相似。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人民寻求和平与繁荣。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印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保证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国内政治而言,我们相信,作为一个多元化、多宗教和多民族的国家,通过法治确立起来的世俗主义和民主,对我们国家的完整是必要的。就外交政策而言,我们承认并鼓励国际社会最终实现多元化。在印度,全国人民一贯认同不结盟政策;这是一项保证印度拥有决策自主权和根据有关问题对印度的影响程度来对其做出判断所需要的战略空间。我们始终远离各种缠结不清的联盟,也从不对外做出任何军事方面的承诺,并一直在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以满足印度人民与日俱增的发展社会经济的愿望。
印度在独立之时就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这一道路为印度政界的方方面面所一致认同,是不足为怪的。独立之时,印度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26岁,印度人口中只有不足14%的人识字,79%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饥荒司空见惯,疾病到处肆虐。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印度从一个世界上最富裕也最先进的国家沦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因此,印度自然要采取使其能够集中全力于发展这一压倒一切的国内任务的外交政策,同样自然的是,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一个主要作用是消除贫困和保证国内的统一。印度所采取的重大战略就是不结盟这一战略,其宗旨在于将地区发展和冲突与大规模的冷战及冷战中的对抗性政治隔离开来。不结盟也是一项积极的选择,即一项根据国家利益而不是盟国要求依照每一个问题的事实真相对其予以处理的决定。不结盟旨在保持一个免受大国纠缠的环境,从而使我们得以集中精力于自身的发展。
从结果看,印度在独立之时所选择的这一重大战略已经产生了良好而明显的效果。除了同中国以及在查谟克什米尔的部分地区同巴基斯坦之外,印度现在已经与其十一个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在地理上划定了界线。今天,印度的识字率约为62%,平均预期寿命接近65岁,印度实现了粮食自给,并可以向国外出口。正如你们之中许多人由亲身体验所了解到的那样,印度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多样化的经济体之一,拥有一体化的国内市场;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内经济一直在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令人难以接受的高额贫困数字得到了真正的削减,而如果印度经济继续如同九十年代那样增长,我们确实有望在2010年之前消除贫困。
回首过去,二十世纪这个历史上暴力极度横行的世纪,也是一个发展了至为惊人的变化和反差的世纪。它们是:旧式帝国主义的终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乃至被使用;世界范围内空前的技术发展和信息革命,最为邪恶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的滋长;世界上一些地区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发展,与之同时存在的其它地区的最有辱人格的贫困和匮乏。就在各种争取社会变革和权利的运动获得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一些过时的集团和原教旨主义集团以及跨国力量对公共秩序和国家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联合国之类国际组织的创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得到了空前的支持。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大国诉诸自行其是政策和施压政策的做法不断升级。我们将带着既往一个世纪遗留下来的不确定因素面对二十一世纪。
今天,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公开宣布以多极化为其目标,但尚未使之成为现实;强人利用这一点,持续试图重新界定并限制主权这一观念;科学和技术的机遇增加了许多倍。因此,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远比我们独立以来所目睹的一切复杂;各种威胁和机遇也相应增大。
就国内情况而言,印度自1991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及其它改革,是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回应。最初的改革,集中在解除对混合经济的管制、振兴公营企业以及通过降低关税、鼓励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来使印度对外开放这些方面。这些政策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尽管印度人民可能会对改革的速度持有不同的看法,但现在对改革的必要性或方向却几乎没有或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但是,伴随着成功也产生了一些难题。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第二轮的改革,发展我们的基础设施,进行金融部门和公共机构的改革,以及在诸如保险、银行和民航等服务行业进行改革。
就外交政策而言,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诸如强调主权和不干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是依然有效的。
与此同时,我们的安全政策必须不断发展以应对新形势。除了新的、危险的技术和武器的扩散之外,还出现了非军事性的威胁和非国家的危险人物。印度主张,所有国家均有平等的安全权利,而增进安全的最佳途径是以一视同仁的方式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诸位都熟悉印度就核裁军问题提出的许多倡议,并非所有这些倡议都取得了成功。1954年,印度率先主张禁止核试验;1965年,印度率先主张就核不扩散问题缔结非歧视性条约;1978年,印度率先倡议缔结不使用核武器的条约;1982年,印度率先提出核冻结的主张;1988年,印度率先提出了分阶段彻底消灭核武器的计划。然而,印度关于所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平等裁军的主张及其自我克制,却遭遇到其周边国家及世界持续不断的“核武器化”,以及国际上核武器在《核不扩散条约》体系内的合法化。根据我们对过去几年的评估和体会,我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业已恶化。
正如诸位所知,印度在核问题上尚未做出最后抉择,并且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核不扩散条约》在1995年的无限定延期及存在缺陷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随后缔结,均旨在强化“核隔离”局面,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不会对自己的核武器予以任何认真或重大的限制。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国家之一,甚至比中国的相应计划为时还早。而且,在1974年的一次地下和平核爆炸之后,我们有意识地放弃了核武器化,再度坚持核限制政策达24年之久。然而,由于面对日益不利的安全环境,同时由于需要确保能够行使我们的核选择权,我们在1998年5月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步骤以行使我们的核选择权,目的则在于维护我们的战略空间、国家安全和可贵的独立。
从那时起,印度长期坚持核限制政策和仅仅寻求最低限度的确实有效的威慑力量的基本态度,宣布自愿延缓将来的核武器试验。印度已经申明,其核计划是防御性的。我们并不寻求竞争或军备竞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我们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主权国家的决定。这属于我们的权利。我们已经反复重申了下述事实:我们的核武器并不针对具体的国家。印度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在普遍的、可核查的、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实行全球核裁军。与此同时,我们要确保印度的战略自主权得到维护。只有依照我们自己对不断演变的国际安全环境的评估来适当处理印度合理的安全事务,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核主张,是以最低限度的、灵活的、确实有效的核威慑力量为基础的。我们采取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并向那些没有核武器或不同核大国结盟的国家做出了无条件的保证。
如果要让我概括印度对自己的世界之交的外交政策的看法的话,我认为,今天的印度将自己视为具有独立判断和自主行动的国家,真正代表了自己人民的利益。我所以提及印度的自主决策,是因为有些学者低估了印度的这一方面,仅以印度同诸如前苏联或美国等其它国家的关系为借镜来衡量印度。那么,我们印度人怎样看待我们目前的战略环境呢?尽管我们都认为二十世纪的最后十五年是一个发生了空前而迅速变化的时期,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这一变化的特点抱有一致看法。在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看来,冷战的结束似乎导致了普遍的不结盟。两极局面的崩溃,造成了单极局面的出现和其它若干大国中心的崛起。国际体系的支点,正在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然而,冷战的终结尽管已经改变了国际问题出现的舞台,却没有改变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正如我在前面所要表明的那样,由于我们已经将我们的安全政策同联盟政治分离开来,我们关注的这些事务都是印度固有的,而非冷战的产物。
印中关系
我现在愿意在上述的大背景之下,进而谈谈印中关系。印中关系始终是印度对外政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是文明古国,有着友好接触和无可争议的在宗教和文化领域交流的悠久历史。我们在唐代的交流,可以作为不同文化既相互尊重对方的风俗又相互学习、交流技术及思想的历史典范。我们都是拥有广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我们两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加在一起占人类的三分之一。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我们都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外国征服的受害者。在那些困难的岁月中,两国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相互同情和支持对方争取自由的斗争。半个世纪之前,我们这两个古老的民族获得了新生,建立了新的国家。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稳步成长和发展。尽管我们依然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但我们在过去五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却是重大的。我们今天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都在根据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民族经验和我们对未来的展望,通过我们各自的对外政策,来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
印度是在1949年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众所周知,在五十年代初期,印中两国总理联合发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令人遗憾的是,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经历了起伏。然而,即使在我们的关系在六十年代遭受挫折之后,印度在诸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有关中国事务方面的立场却没有改变。印度也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1979年,随着时任印度外交部长的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先生对中国的访问,我们的双边关系恢复正常发展状态。访问期间,瓦杰帕伊先生会见了中国高级领导人邓小平阁下。1988年12月已故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成为我们两国关系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访问期间,印中两国领导人决定,在继续努力解决争端的同时,着手在所有领域建立双边关系。双方还就寻求相互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达成了共识。从那时以来的十二年间,双边关系取得了重大进步。1993年9月,那罗辛哈·拉奥总理访问中国期间,签署了关于维持双方实际控制线和平与稳定的协定。江泽民主席1996年11月对印度的非常重要的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访问期间,这一进程被进一步推动。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关于沿实际控制线在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已经倡议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一时期,我们两国在文化、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一直在稳步发展。
尽管印中之间在1998年5月之后出现某些误解,但目前双方已使印中关系复归正常。1999年6月我国外交部长的访华和今年7月中国外交部长唐家旋的访印都是意义重大的步骤。双方都声明不将对方视为威胁。我们已经开启安全对话,以解决双方关注的重要问题。两国都在通过适当的纪念活动庆祝建交50周年。最近,印度总统K.R.纳拉亚南先生对中国的成功访问,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今天,同此前一段时期相比,建立牢固而又良好的印中关系的前景更加明朗。我们双方应当利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伟大机遇。我这样讲是有若干理由的。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合作,我们目前也已经在这样做。即使事先并未协调,我们两国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反应常常是相似的或完全一致的。我们对所面临的国际问题的看法往往相互吻合。国际关系中的单方面政策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致力于在主权、人权和其它问题上寻求平衡。作为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社会,我们两国都面临着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极端主义的共同挑战和威胁,面临着往往源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强大的新现象。迄今为止,十余年来,印度一直是越境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一直在利用一个负责的民主国家所拥有的武器与这种反人道的罪行进行斗争。恐怖主义,特别是越境恐怖主义,同时威胁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将多民族和多宗教社会作为其攻击目标。我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是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同时也是对受其影响的不同社会的人民的基本人权的最为公然的侵犯之一。
此外,我们两国社会都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国内发展和变革,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印度外交部长去年访问香港期间明确指出,印度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贫困。将政治民主转为经济民主,是印度在新千纪里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要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印度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有十足的明确的理由来推进两国关系。我们两国社会都已经发生变化并发展到了拥有成熟的而且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制的阶段。我们是世界上两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且拥有巨大的市场,可以为两国公司携手合作、相互供应乃至供给世界提供大量的机会。有趣的是,印度经济的新的活力,是由生产率的提高和以增值的人力资源为本的产业驱动的。随着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在高等教育及科学技术(空间技术、制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实力的增强,我们现在拥有的经济合作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年仅二十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总额,与我们两国的经济是不相称的。
由于印中双方高层的积极行动,我们现在建立了在广泛领域进行对话和接触的恰当制度。诸如边界一类有争议的问题,正在由联合工作小组和专家组进行讨论。我们还在政府之间进行安全对话以交换意见,我们最近还同意将这一对话升级。我们建立了一个适当的名人论坛,不久之后就会开始工作,同时还设立了一个联合经济小组。随着纳拉亚南总统于2000年5-6月间的成功访华,两国高层领导之间的接触进程已经恢复。
如果存在一种使印中两国关系止步不前的因素的话,那也许就是我们缺乏对对方关注问题的敏感,相互理解不够。对印度的成见在这里似乎依然盛行,对中国的成见在印度似乎也一样。这在我们两国社会的变革速度极快的时期是很自然的。正因为如此,你们作为学者的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远远超出了学术交流本身的价值。我很高兴地获悉,若干新的双边学者接触活动,以及由于缺乏更好术语而被称为印中学者之间的第二轨道对话,正在进行之中。我坚信,通过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政策的要点和对方关注的问题,我们这两个古老的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关系将得到改善。
我将乐于听取你们的意见并回答你们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
2000年9月22日于北京
标签:外交政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