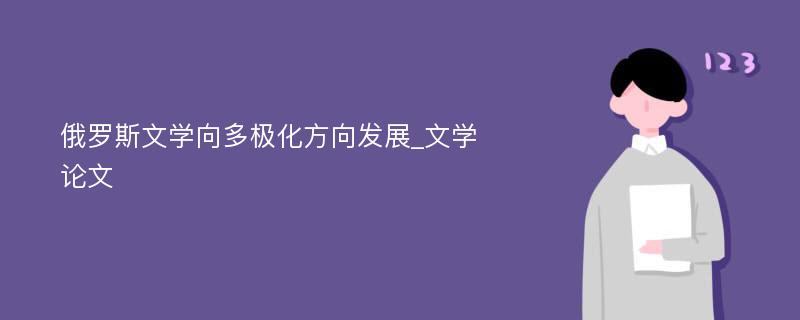
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俄罗斯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方向论文,多极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解体已5年有余。原来作为苏联文学主体的俄罗斯文学,在新建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也已熬过了5个年头。应该说,在这5年中,它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其中之一是某批评家所说的“文学与国家分离”(раз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这是苏联解体给文学带来的一个主要变化,文学的许多新特点都是随着这个变化而产生的。
我们知道,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如同列宁所说的那样,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者”。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文学事业一直受苏维埃国家的领导和扶植。到50年代下半期,文学界出现了一种企图摆脱国家领导的倾向。在“改革”年代,这种倾向得到恶性发展,而“文学与国家分离”的过程到苏联解体后才最后完成。
过去文学与国家的关系不仅仅只表现在国家对它实行领导和监督这一个方面。国家在这样做的同时,从各个方面支持文学事业,为它的发展创造包括物质条件在内的各种有利条件。苏联解体后,文学既然不再接受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不再承担对国家的义务,自然也就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和赞助,摆在它面前的,只有“自谋生路”这一条路。利哈乔夫院士曾把摆脱了国家领导的文学比做一只出了笼子的小鸟,说它“碰到了两个困难。首先它的翅膀软弱无力……其次它没有了饲料”。这只小鸟在苏联解体后被一下子抛到了尚未完全形成的、几乎不讲规矩的“野蛮的”市场上,由于一时适应不了新的生活环境,生命曾受到威胁。尤其是严肃文学(或称雅文学)日子更不好过。从19世纪以来一直在文学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并成文学状况晴雨表的大型文学杂志,陷入了困境,其中有的杂志曾一度面临停刊的危险。包括《旗》、《十月》、《民族友谊》、《涅瓦》等14家自由派刊物,至今仍靠美国“好心的大叔”索洛斯的资助才得以维持[①],而且印数仍在继续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图书出版业的私有化进程的加速完成,以商业利润为主要导向的各种私人出版社迎合读者不健康的趣味和要求,大量出版娱乐性和刺激性的通俗读物。原来的国家出版社为求得生存,也起而仿效。于是图书市场上刮起了一阵阵旋风,接连出现了各种“热”,例如侦探小说热、惊险小说热、言情小说热等等,出版物的格调愈来愈低,宣扬暴力、凶杀和色情的诲淫诲盗的作品大量上市。最近传统的大型文学杂志又碰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这就是所谓的“彩色杂志”(цветные或глянцевые журналы)。这些花里胡哨的刊物摆满了报刊亭和书摊,它们品种繁多,其中包括俄罗斯版的《花花公子》、《斗牛士》、《斯塔司》、《普丘奇》、《29》、《四海为家者》、《安德烈》、《熊》等等。俄罗斯《文学报》这样描述这种“新文化”的“盛况”:“这是各种名称和吸引人的彩色封面的汪洋大海,它在报刊亭和地下通道的书摊上简直淹没了由大型杂志构成的小岛,而在10年到15年前,大型杂志曾雄踞于像《星火画报》之类的孤零零的‘彩色’杂志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杂志熟悉市场行情,善于迎合读者的心理,刊登的主要是娱乐性的轻松读物,加上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正在夺走不少读者。同时它们的丰厚稿酬也吸引了一些名作家与之“合作”。著名小说家比托夫率先把新作交给《花花公子》连载;著名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常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诗作;女作家托卡列娃也开始为文学画报《29》撰稿。步他们的后尘者,恐怕大有人在。这些杂志的生意兴隆和奢华阔气与大型杂志的度日维艰和简朴寒酸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国家不再对文学创作实行直接领导和干预,不再鼓励和倡导某一流派和某种倾向,不再提出一些思想原则来规范创作,并且取消了审查制度,文学界的混乱无序状态有所加剧。各种文学思潮蜂起,具有不同思想政治倾向和采用不同艺术方法的作品杂然纷呈,文学创作朝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变得更为明显。
这种发展趋势并不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出现的。早在“改革”年代,原来统一的(至少表面上如此)文学界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分裂为拥护“改革”的自由派和对“改革”持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传统派,这两大派摆开阵势,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内战”。而从创作来看,两派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的差别愈来愈大。作家普罗哈诺夫早在1988年就指出“两种不同的文化”的存在,一种是以西方民主为准绳的“自由派文化”,另一种是希望保持独立自主性、走本民族道路的“保守文化”。他说的“保守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派文化。批评家佐洛托诺索夫也在苏联解体前夕说过,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文学正在“分解为一系列亚文学(сублитература),一系列‘独立的’部分,其中每一个部分有自己的审美观念和道德观念,同领导保持特有的相互关系,有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读者……实质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内部大量的亚文化”。不过根据当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分解为不同的“亚文学”的过程并未最后完成。
苏联的解体使得这个分解过程最后完成了。不久前女批评家娜塔莉娅·伊万诺娃又提出了俄罗斯文学分为几种“亚文学”的问题,并且指出:“每一种亚文学都有一批自己的小说家、诗人、批评家。有其习惯的体裁。每一种亚文学有自己的经典作家,自己的权威,自己的模仿者,自己的追随者和学生。每一种亚文学现在还有自己的杂志、丛刊甚至报纸,有自己的奖金,自己的代表大会(或‘聚会’)。”
在这些“亚文学”当中,影响最大的是自由派文学。它有一支庞大的、实力相当雄厚的创作队伍。中老年作家仍然是其中坚,这几年他们发表了不少新作。例如巴克拉诺夫发表了长篇小说《于是来了趁火打劫者》(1995)和一些中短篇;格拉宁推出了长篇《逃亡俄罗斯》(1994);叶夫图申科除了发表许多诗作外,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别在死亡前死去》(1994);扎雷金在编刊物之余写了两部长篇(《生态小说》,1993;《选择的自由》,1996)和一部中篇(《同姓者》,1995);雷巴科夫完成了描写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生活道路和命运的三部曲,发表了它的最后一部——《灰尘》(1994);继续用俄语写作并称俄罗斯为“共同的祖国”的艾特马托夫的新作《卡珊德拉印记》(1994)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奥库贾瓦的长篇《被取消的演出》(第1部,1993)和弗拉基莫夫的长篇《将军和他的部队》(1994)发表后受到批评界的重视,并分别于1994年和1995年获布克俄罗斯小说奖。还有那位在苏联解体后完全倒向自由派的阿斯塔菲耶夫创作力仍相当旺盛,他除了完成早已动笔的取材于战争的长篇《该诅咒的和该杀的》的第1、2部(《鬼坑》,1992;《登陆场》,1994;获1995年度俄罗斯国家奖)外,还陆续写了一些中短篇,其中包括中篇小说《真想活啊!》(1995)和《泛音》(1996)。在所谓的“四十岁作家”(现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年近花甲)当中,马卡宁在创作上进行了各种试验和探索,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铺着呢子、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1992;1993年获布克俄罗斯小说奖)和《高加索俘虏》(1995)。此外,基列耶夫、库尔恰特金、阿纳托利·金等人都正值创作的盛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过去的“地下文学”的代表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叶夫盖尼·波波夫等人,近年来比较活跃,先后推出了一批新作。“另一种文学”退潮后,留在国内的皮耶楚赫、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等仍坚持写作,陆续发表了不少引人注目的作品。
最近几年,自由派文坛上出现了大批新人,这些人并不属于同一年龄档次,其中有的人(例如哈里托诺夫、费多罗夫、奥加诺夫、多利尼亚克、安德烈·谢尔盖耶夫等)已经步入中年,他们早就开始写作,可是直到苏联解体前后才在国内得到发表作品的机会;有的人(例如加尔科夫斯基、希什金、叶尔马科夫、瓦尔拉莫夫、帕夫洛夫等)则比较年轻,他们一登上文坛就引起批评界的重视。现在这些文学新人已成为自由派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有人根据大批新人的涌现就断定“熟悉的作家已退居次要地位”,这样说有一定的根据,不过为时尚早。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是:现在正处于新老作家世代交替的过程之中。
如同在“改革”年代一样,自由派继续掌握着《新世界》、《旗》、《十月》、《民族友谊》、《星》、《涅瓦》、《青春》等大型杂志,《文学问题》、《文学评论》等理论刊物以及《文学报》、《文化报》等报纸,同时还创办了一些新的报刊,例如《文学新闻报》、《新文学评论》、《新青春》等。70年代由马克西莫夫在国外创办的《大陆》杂志于1992年搬回国内出版发行(由著名批评家维诺格拉多夫任主编)。这就使得自由派的文学园地有所扩大。
自由派也有他们的文学奖。由英国布克兄弟公司于1992年出资设立的“布克俄罗斯小说奖”虽然声称“将用来奖励用俄语写作的当代作家”,实际上只面向自由派,成为自由派的文学奖。历届的评委会主席和其他成员都是国内的自由派人士和国外的斯拉夫学者,每年进入“决赛”和最后得奖的小说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自由派作家的作品。现布克奖已评过5次,它已成为俄罗斯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奖之一。俄罗斯商界和金融界“七巨头”之一别列佐夫斯基于1992年出资设立的、被称为“俄罗斯诺贝尔奖”的凯旋文艺奖,也是面向自由派的。凯旋奖每年评出5名获奖者,其中包括一位文学家。此外,德国汉堡托普费基金会也为自由派作家和诗人设立了普希金奖。
在“改革”年代,尽管文学界两大派(即自由派和传统派)严重对立,论战非常激烈;尽管自由派作家于1989年成立了名为“四月”的派别组织,但是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还存在,组织上尚未完全分裂。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后,自由派夺取了全苏作协的领导权。与此同时,700余名自由派作家从一直由传统派领导的俄罗斯联邦作协(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或称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России)分裂出来,另行成立一个名叫“俄罗斯作家协会”(Союз российскиФ писателей)的团体。苏联解体后,自由派把他们已夺了领导权的原苏联作协改名为“作家协会联合体”(Содружество союзов писателей),并于1992年1月召开了“联合体”成立大会。传统派不承认这个组织,于是两派在组织上最后彻底分裂。
从自由派的创作来看,暴露和否定仍是主要倾向之一。许多作品继续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苏联的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竭力渲染这个制度下社会的黑暗以及生活的反常和痛苦。其中不少作品出自中老年作家之手,但也有一些作品是文学新人创作的,例如哈里托诺夫的长篇小说《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2,获首届布克奖)、彼列文的中篇小说《奥蒙·拉》(1992)和《黄箭列车》(1993)、扎洛图哈的《解放印度的远征》(1995)等。
“改革”开始后,某些自由派作家虽然竭力想把苏联的历史全部抹黑,但是在否定卫国战争方面还有所顾忌。苏联解体后,他们便肆无忌惮地亵渎这个“在人们记忆中留下的唯一没有受到损害的神圣的东西”(批评家库尔巴托夫语),而带头这样做的,却居然是当年参加过这场战争的阿斯塔菲耶夫、巴克拉诺夫、奥库贾瓦以及成为“邻近的外国作家”的贝科夫和艾特马托夫。他们在《该诅咒的和该杀的》、《于是来了趁火打劫者》、《严寒》(1993)、《卡珊德拉印记》等小说以及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把卫国战争描绘成和说成两个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争斗,完全否定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和它的胜利的伟大意义。自由派刊物《民族友谊》于1992年底和1993年初连载了叛逃到英国的前苏军情报总局军官列尊(化名苏沃罗夫)的《破冰船》,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把苏联说成侵略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有的写过去的作品打着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旗号,其实与“反思”无缘,只能说明它们的作者们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对过去的理想(如果有过理想的话)的背叛和精神支柱的崩溃。
我们记得,“改革”年代曾兴起过所谓的“另一种文学”,这种文学好景不长,很快就衰落了,但是喜欢描写生活中的污浊、展示人性的扭曲和行为的反常的倾向依然存在,这在博罗德尼亚、多利尼亚克、布依达、帕列依等人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色情描写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克利蒙托维奇的《通向罗马的大道》(1994)写一个混迹于莫斯科交际场所的“苏联的唐璜”的经历,其中有不少露骨地描写色情的场面。科罗廖夫的《埃隆》(1994)在描写勃列日涅夫时代特权阶层荒淫无耻的生活以及下层的愚昧和道德上的堕落的同时,不厌其详地写反常的性心理和性行为。把色情描写作为某种“添加剂”加到作品中去招徕读者的现象,相当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自由派作家虽然对过去的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和坚决的否定,但是对苏联解体后的现实也并不太满意,并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就连阿斯塔菲耶夫也在他的新作《真想活啊!》里通过主人公之口,批评了当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巴克拉诺夫也是如此,他在新作《于是来了趁火打劫者》里对目前社会的混乱现象表示了不满。扎雷金对现实感到深深的失望,他在《生态小说》里通过对一个生态学家的遭遇的叙述,写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悲剧。马卡宁的短篇《高加索俘虏》描写了目前民族间的流血冲突。切尔尼茨基的《朝见罗马教皇》(1993)揭露了某些人以朝见教皇为名进行的长途贩运活动。瓦尔拉莫夫的中篇《诞生》(1995)描写了一个婴儿出生后遭受的病痛的折磨,试图以此说明新俄罗斯诞生的艰难。
苏联解体前曾有人预言:果戈理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个具有资产阶级特点的乞乞科夫“将坐着鸟儿般的三驾马车回来,苏维埃国家将侧目而视,退避在一边”。此人还责备果戈理未能看出乞乞科夫是“民族英雄”。不久,大大小小的乞乞科夫果然回来了,俄罗斯报刊把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称为“新俄罗斯人”。[②]随着“新俄罗斯人”的回来,出现了一些着重描写这一类人的作品(例如罗戈任的《新俄罗斯人》、沃依诺维奇的同名小说、博古斯拉夫斯卡娅的《窗户朝南》等),但是看来多数作者都没有把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当作“民族英雄”来歌颂,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对他们采取批评的态度。女批评家拉蒂宁娜在谈到这种现象时说,文学拒绝发给新资产阶级“品德高尚证书”。
从艺术特点来看,自由派文学的某些作品表现出一定的自然主义的倾向。它们的作者在写日常生活时,喜欢“如实地”展示生活中的污秽和丑恶现象以及人们反常心理和行为,而不注意艺术上的提练和概括。有的人,例如阿斯塔菲耶夫,在写战争时,为了把它写得“无限的残酷”、“令人厌恶和可怕”,便有意加浓色彩,描绘各种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场面。近年来自由派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采用各种假定性的艺术手段(例如怪诞、变形、幻想、神话等),以表现生活的荒诞。彼列文的《奥蒙·拉》和《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1996)、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颅》(1992)、沙罗夫的《预演》(1992)、斯拉波夫斯基的《第一次基督二次降世》(1993)、伊万钦科的《花纹字》(1992)、捷列霍夫的《灭鼠》(1995)、扎洛图哈的《解放印度的远征》等,都或多或少地利用了怪诞、变形、传说等手法。阿纳托利·金的两部新作(《半人半马村》,1992;《昂利里亚》,1995)利用了神话。彼列文的《昆虫的生活》(1993)和彼得·阿列什科夫斯基的《黄鼠狼的生活经历》(1993)或假托和比附动物,或使人的命运与动物的命运相沟通。此外,还有一些完全借助于想象的所谓“反乌托邦小说”,例如马卡宁的《出入孔》(1991)、博罗德尼亚的《马列维奇画的礼服》(1992)就属于这一类。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对自由派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90年代初以来,出现了一批或多或少带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其中被戏称为“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的索罗金的作品最有代表性。这几年他陆续推出了《排队》(1992)、《四个人的心》(1993)、《达豪一月》(1994)、《定额》(1994)、《罗曼》(1994)、《玛琳娜的第三十次恋爱》(1995)等小说和剧本《土窑》(1995)。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和叶夫盖尼·波波夫也在创作中积极采用后现代主义技法。后者继那部带有某些后现代主义特点的《爱国者的心,或致费尔菲奇金的各种书信》(1989)后,又利用后现代主义常用的“复制”手法,仿照屠格涅夫的《前夜》写出了《前夜之前夜》(1993)。一些文学新人的某些作品也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其中特点比较突出的是上面提到过的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和加尔科夫斯基的《无尽头的死胡同》(写于80年代中期,1992年发表其中的片断,1993—1994年全文发表),前者被某些批评家称为像埃柯的《玫瑰的名字》那样的“后现代主义典范之作”,后者则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史诗”。后现代主义思潮还影响了像艾特马托夫这样的老作家。他在《卡珊德拉印记》里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常用的多文体手法,使得这部小说具有拼凑性,在这部小说里,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下子把几种文体、几种体裁结合在一起。这里既有幻想,又有现实主义,有时是新闻报导,有时带有电影的特点。总之,把脚本、小说、剧本、新闻报导这一切搅和在一起”。
现在“后现代主义热”正在成为过去。它的那种否定一切道德标准和审美标准、充满奇谈怪论、宣扬色情的“文本”,那种玩弄文字、追求诡异怪谲的作品,那种无连贯情节、无正常人物、断断续续、拼拼凑凑、杂乱无章的东西,似乎已引不起读者的兴趣。
从这几年的自由派文学来看,过去曾占主要地位的采用写实笔法的作品已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不过最近情况又有变化,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正在逐步恢复。自称为“顽固的现实主义者”的弗拉基莫夫的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部队》尽管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例如美化叛变投敌并成为伪军头目的弗拉索夫)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是它在艺术上的优点得到了不少批评家的肯定。在文学新人中也有一些人不追求时髦和新奇,他们主要运用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艺术方法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例如瓦尔拉莫夫的《诞生》、帕夫洛夫的《老一套的故事》(1994)、彼得·阿列什科夫斯基的《弗拉基米尔·奇格林采夫》(1995)、德米特里耶夫的《河流的转弯》(1995)、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1992)和《美狄亚和她的子女》(1996)等作品发表后,都受到了文学界的好评。
苏联解体后文学中的另一种重要的“亚文学”,是传统派文学。在“改革”年代,传统派由于与一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统派作家结盟,队伍有所扩大,成为一支能与自由派抗衡的力量。苏联解体后,他们对新政权采取反对派立场,因此除了在经济上受到的“野蛮的”市场的冲击外,政治上也受到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处境无疑要比自由派困难得多。但是他们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新的条件下争得了生存空间,保住了原有的文学阵地,文学活动没有间断,至今仍是整个文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传统派的创作队伍主要由中老年作家组成,主将仍是邦达列夫、拉斯普京、别洛夫、阿列克谢耶夫、普罗哈诺夫、克鲁平、利丘京、博罗金等人。苏联解体后,一些原来在两大派斗争中持中立态度的人(例如罗佐夫、叶辛、古谢夫等人)开始靠拢传统派。而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后,就连某些本来亲近自由派的前持不同政见者(例如季诺维耶夫、马克西莫夫、西尼亚夫斯基等人)也开始与传统派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这几年传统派中脱颖而出的新手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有尤里·科兹洛夫、焦格捷夫、谢根、帕拉马尔丘克、阿廖什金、克罗托夫等有数的几个人,而且创作成绩平平。这与自由派阵营新人大批涌现的热闹景象大不相同。
苏联解体前,传统派拥有3家大型杂志(即称为“三勇士”的《我们的同时代人》、《青年近卫军》、《莫斯科》)和两份文学报纸(即《文学俄罗斯报》和《莫斯科文学家报》)。这几份报刊克服了种种困难全都坚持办下来了。此外还有1991年初创刊、由普罗哈诺夫任总编和邦达连科任副总编的《白天报》,这份报纸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后遭到查封,后改名为《明天报》继续出版,现在它已成为反对派色彩最鲜明的报纸。
上面提到过,传统派自从“改革”开始以来,一直控制着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1992年6月,这个组织联合一些作家团体召开了第九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国际作家协会共同体”(Междув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писателъскиФ союзов),这样就使得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界形成了自由派“作家协会联合体”和传统派的“国际作家协会共同体”并存的局面。传统派也设立了自己的文学奖,其中最重要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奖和肖洛霍夫奖,前者由俄罗斯联邦作协与呼声出版社于1992年设立,已评了4届;后者由俄罗斯联邦作协与作家股份公司于1993年设立,已评了3届。
在传统派文学创作中挑大梁的依然是中老年作家。文坛耆宿列昂诺夫在1994年告别人世之前发表了他那部酝酿和写作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长篇小说《金字塔》(1993),这部巨著反映了作者对苏联的革命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深沉思考。邦达列夫发表了描写前线归来者战后的生活遭遇的《不抵抗》(1994—1995);阿列克谢耶夫在《我的斯大林格勒》第1部(1993)中颂扬了红军战士的英勇战斗精神;已故的斯塔德纽克在生前发表的自传性中篇《无悔的自白》(第2部改名为《一个斯大林分子的自白》,1991—1992)里回首往事,觉得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阿纳托利·伊万诺夫、普罗斯库林、奥列格·斯米尔诺夫等人都有新作发表。别洛夫的创作力相当旺盛,他在完成长篇《大转变的一年》(1989—1994)后,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剧本。很久没有发表小说的拉斯普京,最近两三年推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短篇。克鲁平、博罗金、利丘京、阿法纳西耶夫、叶基莫夫、克拉斯诺夫等人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创作上都有较多的收获。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普罗哈诺夫,他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办报纸和撰写各种文章的同时,还完成了3部长篇小说——《帝国的最后一个士兵》(1993)、《宫殿》(1994)和《方舟》(1996)。
农村题材本来是传统派文学的一个基本题材,可是近几年这方面的创作并无大的建树。别洛夫的《大转变的一年》的第3部与前两部一样,只限于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作全盘的否定,而未能对这一历史现象作进一步深入的揭示。他的那些反映农村生活和农民情绪的小说,例如《在锅炉旁》(1995)、《白血病》(1995),也缺乏新意。除别洛夫外,以写农村特写著称的伊万·瓦西里耶夫发表了中篇《农民的儿子》(1995);长期居住在农村的叶基莫夫也不时有农村特写和特写式小说发表,但是总的说来,未见有新的突破。现在文学界已有人在谈论农村题材文学的终结了。
在目前传统派的文学创作中,历史和宗教成为重要的主题,它贯穿在许多作品之中。这几年出现了一些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例如巴拉绍夫发表了写古代历史的《神圣的罗斯》的第5、6、7卷(1993—1995),利丘京完成了反映17世纪宗教界斗争的《分裂运动》的第2、3部(1992—1996);除此之外,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还有阿纳托利·伊万诺夫的《叶尔马克》(1992)、克拉斯诺夫的《弑君者》(1993)、博罗金的《乱世皇后》(1996)、谢根的《帖木儿》(1996)等。有的作品取材于离现在较近的历史,例如库兹明的《黄昏》(1995)写的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个短暂时间内错综复杂的斗争,突出描述了沙俄将军科尔尼洛夫这个人物。上述作品一方面反映了传统派作家对俄罗斯经历的历史道路的深沉思考以及他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要求和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其中也暴露出他们的历史观的偏颇。
批判和暴露也是传统派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传统派作家中相当多的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浓厚的宗教观念,不接受国际主义思想,也反对俄罗斯人民本世纪初所作的社会主义选择。有的人过去也曾受到过压制,有一肚子怒气和怨气。因此他们的刊物也发表了一些否定革命和批判苏维埃制度的作品。可是这些人与自由派作家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不赞成社会主义,虽然也有不满情绪,但是为昔日祖国的强大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自豪,因而不主张把苏联的历史全部抹黑。加上目前他们处于反对派地位,认为迫切要做的事是利用文学作为武器与现政权进行斗争,这就使得他们把暴露当前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揭露现政权的本质及其政策造成的后果作为首要任务。简言之,自由派文学把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过去,而传统派文学则着重批判现实。
就内容来说,传统派批判现实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所谓的“民主派”人士和政界上层人物为批判对象,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有叶辛的中篇《站在门口的女人》(1992)、奥列依尼克的《魔鬼》(1993)、克罗托夫的三部曲《平行世界纪事》(第1部《捕捉总统》,1993;第2部《交好运的时刻》,1994;第3部《结局》,1995),此外还有靠向传统派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季诺维耶夫的《乱世》(1993)。阿廖什金接连发表的两部中篇《我是杀人凶手》和《我是恐怖分子》(均1994)写了1993年的“十月事件”。拉斯普京的短篇《在医院里》(1995)通过一个主人公之口抨击了上层人物的叛卖行为。另一类作品则主要揭露和批判新的社会矛盾和各种消极现象,这样的作品有奥列格·斯米尔诺夫的《胜利者》(1993)、拉斯普京的《葬入同一块土地》(1995)、克鲁平的《谢天谢地》和《美国佬,滚回去》(均1995)、别洛夫的《怪话》(1996)等。阿法纳西耶夫的三部曲(《撒旦的首次造访》、《有罪的女人》和《莫斯科的杀人凶手》,1996)描写了莫斯科日益猖獗的黑手党的活动。年轻作家尤里·科兹洛夫的长篇小说《夜猎》(1995)采用了所谓的“反乌托邦小说”的体裁,描写了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世界,那里有任意杀人的自由。在环境被毒化的大地上,活动着大群吃不饱的、贫穷的、畸形的人,他们随时准备进行抢劫和咬断旁人的脖子。在这个地狱里,官僚和盗贼们为了获得政权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其实这就是对现实的比较夸张的描述。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传统派作品基本上采用通常的写实笔法,不过有时也运用夸张和怪诞的手法,但这主要是对果戈理和谢德林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一般说来,传统派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各种时髦的东西采取不屑一顾和抵制的态度。在语言的运用上,他们主张使用纯粹的俄语,因此他们的作品与某些自由派作家的那种充塞着外来的新词怪词和脏言秽语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不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有一种使用方言土语和古词语的癖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语言的表现力。
与自由派文学相比,传统派文学的阵地显得比较狭小,它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所占的分额和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及,但是它拥有自己的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体,仍能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上面提到过的女批评家伊万诺娃还提出目前俄罗斯文学中第三种比较有影响的“亚文学”,即“新潮文学”。对“新潮文学”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有时它被称为“新派文学”(нонконформ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或“不受检查的文学”(неподцензу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这种文学往往以独立不羁和反传统相标榜,其作者大多是年轻人,包括不少所谓的“八十年代人”。这一代人一般是在西方文艺思想的熏陶下以及在混乱的社会环境里开始从事创作和形成他们的创作个性的。批评家安宁斯基曾对这一代人进行过描述,说他们“从小就接受双重道德,‘白天’可以说这个,‘夜里’可以读那个,在社会上除了发现谎言和无耻外,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他们在音乐中追求西方时髦,在绘画中使先锋派得到蓬勃发展,在诗歌中使用超隐喻,而在散文中则大搞荒诞主义。在这一切之中,可以触摸到一个最奇怪的俄罗斯原则:越坏越好”。他还说,“这是一代这样的苏联人,对他们来说,文化是绝对独立的价值,既不需要外部的支持,也不需要鼓励。它‘不为任何目的’,是自在之物”。可见,这一代人无论就世界观还是就文艺观来说,都与他们的长辈有重大的区别。“新潮作家”开头依附于自由派,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至今仍在自由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后来自己陆续创办了一些杂志和丛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89年创刊的《新文学通报》(主编别尔格),80年代在纽约创办,1990年搬回俄罗斯的丛刊《射击兵》(主编格列泽尔),1991年创刊的丛刊《索洛》(“索洛”为并不存在的“个体文学家协会”的缩写,主编亚历山大·米哈依洛夫)和《世纪末》(负责人尼基申)等,此外还有《附记》、《开端》、《黄金时代》、《出版地点》、《此时此地》等等。这些刊物发表了不少后现代主义小说、概念派诗歌和各种“尖端的”作品。某些“新潮作家”兼营出版社(例如格列泽尔、库瓦尔金),这一方面使得他们的文学活动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开展得比较顺利,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的创作带有更浓的商业化色彩,进一步向低俗化发展。从总的实力和产生的影响来看,“新潮文学”似乎还没有成为与自由派文学和传统派文学旗鼓相当的“亚文学”,所以在目前的俄罗斯文学界基本上还是自由派和传统派这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
但是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这种格局可能会发生变化。两派的紧张关系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原来两派的刊物界线分明,互不刊登对方的文章和作品,现在有了少数“跨派”作家,例如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从1994年起陆续刊登传统派作家叶基莫夫的特写和小说,该刊主编扎雷金亲自写后记进行推荐;又如《新世界》专栏作者巴辛斯基参加了传统派杂志《莫斯科》编辑部组织的讨论。不久前两派的作家和批评家一起参加了一个叫做“莫斯科—彭内小说奖”的文学奖的评委会,坐到一起评选作品。另一方面,两派内部又都各自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而且日趋表面化。传统派的三大杂志由于观点上的分歧,相互关系中出现了裂痕。由诗人库尼亚耶夫任主编的《我们的同时代人》和先后由克鲁平、博罗金接任主编的《莫斯科》,民族主义和宗教的色彩不断加浓,而长期由阿纳托利·伊万诺夫任主编的《青年近卫军》(1995年9月起由克罗托夫接任主编)似乎对它的盟友的上述倾向和某些做法不大赞同,因而爆发了《我们的同时代人》与《青年近卫军》之间的一场公开的论战。此外,在传统派控制的俄罗斯联邦作协内部也发生了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争吵,最后使得主张对当局采取不妥协立场的邦达列夫被迫于1994年6月辞去俄联邦作协主席职务,由加尼切夫接替。在自由派内部,新老作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原来依附于自由派的“新潮作家”不再安于“寄人篱下”的地位,他们联合自由派中的年轻作家向目前居于中心地位并控制着大型杂志的中老年作家发起攻击,公开称他们为“保守派”,声称已到了“换班”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否定办好大型杂志对组织文学生活的重要性,宣布这种形式已经“过时”,另一方面又努力加强自己的刊物以扩大影响,并且建立了文学沙龙和俱乐部之类的设施来吸引更多的人。这场争夺战才刚刚拉开序幕。看来文学界的这种分裂和混乱状态将延续下去,文学创作将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 索洛斯为美国犹太富翁。索洛斯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性投资公司之一。它通过《旗》杂志前主编巴克拉诺夫资助了14家杂志。
② 据查,“新俄罗斯人”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1992年9月7日的《生意人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