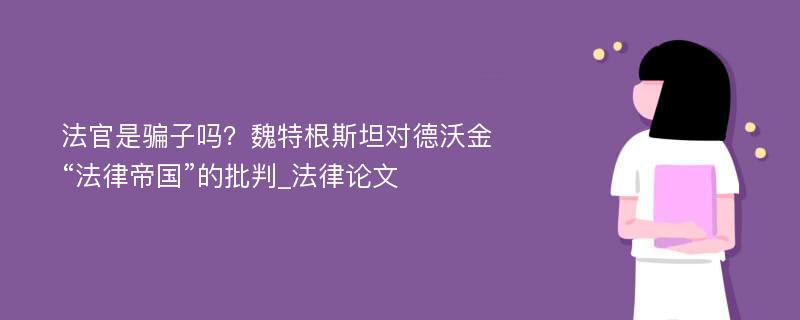
法官是说谎者吗?——对德沃金《法律帝国》的维特根斯坦式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说谎者论文,帝国论文,法官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法律现实主义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在美国法学思想界初露头角时,[1][2]它经常被误解为是对美国司法界的公正性和诚实性的攻击。毕竟,法律现实主义的中心教义不就是法官判案并不援引既定的、权威的法律规则,而仅仅依据他们认为是最好的方式进行吗?此类见解导致了对法律现实主义立场的贬抑性重述,譬如说认为法律取决于“法官早餐吃了些什么”。(注:德沃金引用了此种怀疑观的通行表述,Law's Empire,Harvard Univ.Press,1986 at 36.我查阅了德沃金的著作和其他资料,也不能确定这句话的具体出处。我猜想,它可能源自庞德的一篇比较一种法律体制与“卡迪”(Cadi)审判之任意性的文章。庞德谈到:“东方国家城门口由卡迪主持的审判率性而为,审判还受卡迪的消化状况的影响。”Pound,The Decade of Equity(1905),5 Col.L.Rev.20.21.二十五年之后,为驳斥那种认为不以规则为基础的决定必然含有任意性的观点,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援引了庞德的话说:“只是在法国、德国、英国或美国,人们才以为穆斯林国家的法官根据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自己的消化状况来判案。”Jerome Frank,Are Judges Human?(1931),80 U.of Pa.L.Rev.17,24.)
但这种对美国司法界吹毛求疵的描述,和大多数法律现实主义者实际所持的观点相去甚远。恰恰相反,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尊敬、甚至是崇拜那些伟大的普通法法官。他们赞颂马歇尔(Marshall)、斯托里(Story)和霍姆斯(Holmes)这样的法官,这些法官回应“对时代需要的感知”,(注:O.W.Holmes,The Common Law,Little,Brown,1881.此书(尤其是第一章)被现实主义者奉为近乎神圣的文本,其主题已浸润于许多著作当中,See e.g.Max Radin,Law as Logic and Experience,Yale L.J.,1940;F.s.Cohen,Transcendental Nonsense and the Functional Approach(1935),35 Col.L.Rev.809,825-829;John C.C.Wu,Realistic Analysis of Legal Concepts:A Study in the Legal Method of Mr.Justice Holmes(1923),5 China L.Rev.1,2.)将法律塑造、设计成符合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工具。[3][4](P23-40)为了确保实现这种塑造和设计,法官们不得不经常改变、扩充甚至放弃既有的硬性规则,而这正是法律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司法的过程通常并不仅仅指将既定的权威规则适用于具体的实际情况。相反,案子总是带着许多潜在的适用事实和硬性程式,让法官面临选择。这就使得——事实上是要求——司法判决不能仅仅依赖于对“正确的”法律规则的适用。
不过,司法部门——至少是其间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成员——所持的这种观点,虽然很有教益,但仍不能使法官完全免于被指责为含糊其辞。毕竟,法官直至今天仍然在书写他们的判决意见,其方式通常是先摆出唯一的裁决,作为适用既有规则的必然结果。如果现实主义者是正确的话,如果法律规则在大多数案件中的适用性的确是不可测定的话——因而那些决定几乎总是纯粹适用硬性条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结果,那么当法官们努力将其判决作为适用既有规则的必然结果摆出来时,他们是在说谎吗?(注:法律现实主义者并非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其中很多成员看起来接受了这一看法,即法官在判决意见的陈述方式上通常不够坦率。譬如吉尔摩就用欣赏的笔调,将斯托里法官在“斯威夫特诉塔尔森案”(Swift v.Tyson,1848,41 U.S.Pet.1)中的意见称为“狡猾的杰作”,G.Gilmore,The Ages of American Law at 33.杰罗姆·弗兰克的名著《法律与现代思想》(Law and the modern Mind,Coward-Mc-Cann,1930),在某种意义上尝试着用心理学的术语解释法官和律师的那种外在需要——用易误解的、严格而又限定的形式去描绘法律决定(依弗兰克的看法)。当然,自从法律现实主义者设想了可在其中清楚、如实地阐述司法行动的政策基础和社会科学凭据的法律论辩新形式后,就很难再指责他们在倡导司法虚饰,而只是默认其为向公开、如实地发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之法律的过渡阶段。)
随着罗纳德·德沃金的《法律帝国》的出版,司法虚饰问题又一次得到普遍的关注。[5]在这本引起广泛注意的书中,德沃金再次掀起了这种对法律现实主义的指责——法律现实主义要求将众多司法意见看作是谎言。随后,他比较了法律现实主义和自己的法学理论(为强调二者的差别,他称之为“整体性的法”)。德沃金认为这两种理论都为司法决断提供了形似合理的解释,似乎也非常符合司法活动的事实。不过德沃金争论道,他的理论比法律现实主义(及其桀骜不驯的后裔——批判法律研究运动)讲究实用的怀疑主义更可取,主要原因是它无须将司法意见看作是谎言、将法官看作是说谎者。
德沃金对法律现实主义的攻击性批驳,以及对其自身法学理论的捍卫,由此紧紧地依托于德沃金的一己之见,同时也附和了对法律现实主义的早期批评。在德沃金看来,接受现实主义者关于条文不确定性的观点,还使人认为那些将自己的决定摆作是对教义规则严格适用的法官,纯粹是在撒谎——或许是为了某一崇高目的而撒谎,但撒谎就是撒谎。
但德沃金对法律现实主义的批评有合理依据吗?我认为没有。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阐述为什么没有。德沃金的论断,所依据的是那种对司法决定中语言角色的极简单的看法。对德沃金来说,语言是一种镜子,反映了司法决定中司法推理的过程。它可能是对导出某一决定的推理过程的精确反映,而在这一决定中它是真实的;它也可能和导出决定的思维过程并无多少一致性,因而只提供了一个假象。
不过我们无须遵奉德沃金关于司法决定中语言角色的看法。我们可以运用一种远要详尽、精密的关于语言和实践之关系的见解,它见诸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后期著作中。如果我们并不把司法意见看作是法官思维过程的正确或错误的记述,而看作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德沃金对法律现实主义的批判会变得无力,相关的所有问题也会变得明朗。我们从探讨论证和解释在意见书写实践中的作用,以及赋予这种实践以一致性的制度性“生活形式”之角色入手,就会发现司法意见并不对应着任何特定个体的思维过程,它或许全然不是某一法官思考的描述或记述。但在同时,某个司法意见的确会起到些许作用——特别是联系制度性的背景对其进行考察时。
本文试图从这种维特根斯坦式的视角出发,考察司法决定的制作和司法意见的书写。以德沃金的论证为起点,本文尝试着将司法意见理解为维特根斯坦式语言游戏中的系列活动。这种进路避免了将司法意见的语言与其他事物——譬如法官决定时的思维过程——对应起来的种种企图。相反,它设法在形成司法意见语言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中,对这种语言进行检视,并考察其在审判实务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拟详细地考量《法律帝国》一书中德沃金针对法律现实主义的那些论断。第二部分尝试从维特根斯坦式的视角出发,驳斥这些论断,所运用的手段是探寻原因性陈述和解释性陈述之间的差异,法官在其中进行语言游戏(即意见书写)的制度性背景,以及论证在一般的语言游戏和特定的司法意见书写中的角色。
一、德沃金对法律实用主义的批驳
在《法律帝国》一书中,德沃金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考察了那些大致可归属于法律现实主义的见解。首先,法律现实主义表现为“内部怀疑主义”[5](P79)——一种关于一般意义上的解释策略的主张,而非关于法律。就德沃金看来,这种内部怀疑将一系列内部标准运用于解释实务中,以否认任何一致的、明显“最佳”的实务解释的可能性。人们也许会从某一单个文本来证实此种内部怀疑主义(譬如,“《哈姆雷特》过于含混曲折,压根不知其所欲云,是一出拼凑出来的大杂剧。”[5](P78)),也可就整个过程进行确证,德沃金称后一种情况为“总体的”内部怀疑主义。[5](P79)
德沃金就总体的内部怀疑主义所举的例子,是某个市民审视了邻居们所珍惜的礼貌习惯后,认为这些习惯“不但毫无用处,更糟的是它们还是有害的。因此他批评邻居们对礼貌所作出并予以维护的各种相异的解释都是不合情理的。”[5](P79)
德沃金承认在法律实务中也可能存在这种总体的内部怀疑主义立场,并且这种立场会“威胁我们自身的事业”。[5](P79)但他却将对这种立场的思考搁置到了此书的后半部分。
德沃金将讨论从一般性的解释和解释策略转移到了刘某一特定事务——法律的合理解释。德沃金在此书中以三章的篇幅分析了法律实务中三种解释方法也即三种法学理论的长处和弱点。德沃金称第一种为因袭主义——与奥斯丁式的实证主义大致相当,在此与我们无关。第二种被德沃金称为法律实用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大致相当。第三种是德沃金自己的理论——“整体性的法”。尽管这三种法学理论之间的斗争结果毫无悬念(“整体性的法”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优胜者),但就两个竞争者而言,法律实用主义的力量要强很多。
德沃金将法律现实主义描述为“内部怀疑主义”立场在法律方面的展开,并将一个潜在的“骇人”[5](P151)立场加诸于法律现实主义身上,即“否认一个社会通过要求用诉讼当事人的假想权利去检验法官的判决与过往的其他政治决定的一致性,可以获取任何真正的利益”。[5](P95)请注意,这恰恰是德沃金总体的内部怀疑主义对待礼貌事务所采取的立场,只有在这一事例中,尝试使决定与过往的先例相一致的努力被断言是毫无用处的。相应地,德沃金论及的法律实用主义者,“严格地说,排斥(德沃金)用来解释法律概念的法律见解和法律权利”。[5](P151)
但德沃金论及的法律实用主义者并未宣称司法决定没有适当的理由,而只是法官消化状况的表现。相反,法律现实主义拥有一个明确而又坚定的规范立场作为其司法决定的合理基础,即“法官的确并且应当使所有的判决看起来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不应该从延续性的形式着想,将任何与过往相延续的形式都视为圭臬”。[5](P151)
德沃金以这一表述方式承认,法律现实主义者的立场和法官及律师的真实陈述显得并不那么合拍。法官和律师每时每刻都在谈论过去的判决。律师的论证通常都是引用先前的案例作为一个依据、一项理由,并且在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决定案子时,这还常常是一个有约束力的理由。同样,法官在书写阐述判决理由的司法意见时,也紧密地以先例为基础。因此,当法律实用主义者将“法官断案并不‘从延续性着想而将与过往的延续视为圭臬’”作为事实真相予以宣称时,他们似乎没有说真话。
不过德沃金认识到,法律实用主义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击败。在《法律帝国》的第五章,德沃金展示了法律实用主义的一种更为“复杂”[5](P151)的形式,它使得法律实用主义能够描述关于实际法律商谈中先例的深入讨论,以及法官使其判决与过往的决定相一致的外在努力。法律实用主义这一修订版辩护的要诀,是认可依实用主义者的理论,与过往相延续的形式能根据如下理由而实现正当化,即“法官有时必须做出人们似乎享有法律权利的行为,因为从长计宜,这样做更有利于社会”。[5](P152)
运用“似乎策略”,德沃金展示了实用主义可能伴随着、甚至是被用来确认存在于法律商谈中的规则中心主义和延续性关怀。德沃金如此阐述实用主义者的立场:
除非被明确界定的某些人或团体所做出的决定,被所有的人承认为公共准则并在必要时能通过警察权力强制执行,文明才可能被实现。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建立税率、构建市场、制订交通法规和交通体系、制定可行的银行利率或者决定现代化进程中应保护哪些乔治时代的广场。如果法官被发现在法规中挑三拣四,只实施他们所赞同的那些法规,那么实用主义者的目的就会落空——因为这种情况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当一个自觉的实用主义法官佯装人们的确享有权利时,如果事实表明只有或主要由我们的法官宣称人们享有法律权利,那么实用主义或许是对我们的法律体系的一种合格解释。[5](P153)
上述所引最后一句中“佯装”一词,显然预示了德沃金的结论:对实用主义的维护需要求助于司法托词等假设,因此比较整体性的法而言,实用主义就逊色了不少。但从维特根斯坦式的观点来看,“佯装”一词还引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认识论问题。
德沃金刚才向我们指出,一个实用主义法官往往会断定:(一)法官应当以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断案;(二)如果法官前后一致地适用那些能够增进社会有序化的法规和其他权威规则,就能使社会得到最好的服务。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法官往往会感到从规范性角度出发,自己不得不做出有利于那些要求适用这些规则的诉讼当事人的裁决。同样,一位称职的律师,如果他通晓法官的法律哲学,而他的当事人又要求实现该规则的话,往往也会辩称法官有义务或有责任做出有利于自己当事人的裁决。因此,如果法官和律师在这种法律实用主义的假设下行事,就会一致认为当事人有权要求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裁决,那么从何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只是“佯装”当事人拥有权利呢?
当然,从维特根斯坦式的视角来看,这种叙述显得有点古怪。“佯装”当事人拥有权利和佯装某人有100万美元不就是一回事儿吗?在后一情形,当佯装的百万富翁不能如期清偿债务,甚至被拒绝延展信用度时,佯装有一百万美元和确实有一百万美元之间的差别就出来了(因为每个人都仅仅是“佯装”相信这个人是百万富翁)。不过,事情是会起变化的,假如一个银行家同意佯装这个可疑人物是一个百万富翁,那么相应地,这个人就可以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而不用担心银行会停止这种佯装(也许是因为他知道,银行家认为维持这种佯装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如果银行的佯装使他拥有价值一百万的资产用来花销,那么将他说成一位百万富翁是错误的吗?[6](P120-121)
显然,这一论证同样适用于德沃金笔下的法律实用主义法官。如果法官前后一致地做出有利于要求适用确定法规的当事人的裁决,并非仅仅出于心甘情愿,而是感到自己被迫这样做,那么从何种意义上来讲,说他承认法律权利是错误的呢?德沃金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为他注意到,实用主义在实践中并非像在理论中那么激进。[5](P153)然而,他好像仍然认为,在由一位实用主义法官所承认的权利(他的最佳选择就是称其为“似乎的权利”)和一位确实信奉权利的法官所承认的权利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实体差别。但是,他从未真正领悟到这种差异之所在。
不过,德沃金相当清楚,由于实用主义法官在决定是否支持这些权利时所运用的标准,和非实用主义法官所运用的标准是不同的。因此,实用主义法官所承认的权利的涉案类型和范围,也会不同于那些“确实”信奉使裁决和先前判决前后一致的法官们所承认的权利范围。这为德沃金检测法律实用主义之主张的妥当性,提供了一种实证检测方法——观察实际中的法官所支持的权利,是否只存在于这种权利支持能够依据法律实用主义取得正当性的场合。
德沃金断言法律实用主义非常适合于法官的实务。他通过一个个案思考来论证他的这一观点。在这一案件中,社会将直接从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裁决中受益(或许因为这方当事人会将重新获得的财物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不过这一裁决的条件,是法官必须拒绝适用一条有益于社会的规则(例如,不再坚持这一规则:谋杀者不能从受害人那里继承财产)。德沃金说道:“乍一看”,设想中的实用主义法官会倾向于径直适用谋杀者不可以继承预期的遗产这一规则,从而使这一为社会所期望的规则发生助益,也使慈善机构得到了捐赠。但是,德沃金论证道:当实用主义法官“通盘考虑整个事件”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将拒绝适用那些人们所期待的规则。主要是因为她认识到:适用溯及既往的司法规则,会促使大多数人在无须司法干预的情况下使自身行为符合社会所期待的规则。[5](P156-157)
尽管德沃金仍不会将这一过程完全视为是实现权利,但他认识到,一位决定适用溯及既往的法律规则,并且决定同既往的实践保持一致的法官,将会像一位现实中的法官那样去言说和行事,即便她的行动理由是实用主义的。她会讨论先例,并且向人们表明她的裁决是一次使自己的决定遵循既往实践的有意识尝试。那么,当法官这么做的时候,她是在撒谎吗?显然不是。德沃金刚刚告诉我们,这样的法官会有意识地试着去适用那些溯及既往的、最符合既往实践的规则,因为她相信自己是在做一件对社会最有助益的事情。因此,德沃金认为,在许多——或许是大部分——情况下,一位实用主义法官使判决在表面上符合先例,是“出于其他的理由——而非高贵的撒谎策略。”[5](P155)的确,在这种案件中,很难区分“表面上”的遵循先例和实质上的遵循先例。
但是,德沃金确实相信,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无法用实用主义理论来解释现实中的法官的某些做法,除非求助于“高贵的谎言”。他引证了这两种现象:(一)审案法官表示,要辨别立法原意,以解释、适用含糊的法规;(二)审案法官表示,要恰如其分地辨别含混或者有争议的先行判决的适用范围。
这两个例证都反映了一个潜在的事实——虽然德沃金能够理解一位实用主义法官为什么会前后一致地适用明确的成文法规和先例,以发扬有益于秩序和社会常态的习惯,但是,只有当潜在的权威规则相当明确并且能够为受之调整的人们清除理解时,德沃金的这一辩解才能成立。当问题不甚明了时,当潜在的权威规则不能够提供确定的指引时,德沃金应该考虑到,没有什么理由让一位实用主义法官去辩识这种规则中的原意或含义。相反,实用主义法官会直截了当地将最有益于社会的规则作为最好选择,并予以适用。
德沃金反对这一观念——通过努力适用那些更不明确的先例,也会增进那种有益的社会常态。如其所言,“如果法官以断章取义式的含糊意见拒绝遵循先例,那么,这些指引行为的先例的一般约束力,并不会遭受多少损害。”[5](P159)同样,德沃金认为,如果法官“拒绝考虑如何从过往或者是那些完全不同于当代立法者的意图中解读疑义丛生的规则,”[5](P158)也不会对立法的功能造成损害。从而,德沃金得出结论说,如果实用主义法官“有间接的、高贵谎言式的理由去佯装审判涉及立法原意”,[5](P158)那么就如我们所见,她只能遵从现实中的法官处理这些疑难案子(即表示事关辨识立法原意)的方式。
德沃金从未解释这种“高贵的谎言”是什么,不过,我们不难想象其中的原委。譬如,法官会认为:为了社会福利而确立这一规则——禁止国家不合理地使用电子窃听设备,使公民隐私受到侵犯——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规则产生实效,就必须约束行政和立法机关的行动,因而,法官宣称她是从在这个国家基本法中存续了两百年的古老规定——这些规定尽管古老但是为人民所尊崇——的模糊区域(而不是从他自己所认为的社会福利中)推导出了这一规则。这种声明就是一个谎言,因为法官实际上并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出该规则的,他也不认为国父们在制定这些规定时会考虑到禁止利用电子设备进行窃听。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高贵的谎言”,就像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结尾处关于金质、银质和铜质人的虚构那样,因为它所依托的是一种诚挚的信念,即从长计宜,这种谎言会强化规则,并给人们带来好处。
德沃金显然认为,同样的考虑是法律实用主义者能够解释和正当化其司法努力——将他们的判决当作是对含糊、不确定的先例所做的适用和阐明——的唯一途径。虽然德沃金没有完全否认法律实用主义是一种合格的法律观念,但他确实认为接受这种司法虚饰形式的差强人意之处,在于存在一个反对它的有力指责。他对此声称(我把它看作是德沃金反对法律现实主义的关键论据):
“因而,只有通过看上去极不合适的、强求一致的手段,才能帮助实用主义成为对我们典型的审判场景所作的上乘解释。只有当我们全然不是从其表面价值理解司法意见时,实用主义才能得获得拯救;我们必须认为,所有被有问题的法规和先例所困扰的法官,正在实施某些动机不明的欺骗。他们一定会被看作是在按照自身的确信——什么是最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为未来发明新的规则,并且不受制于任何源于一致性的假定权利,他们只是根据某些不为人知的理由,并以“从过往中发掘出来的规则”这一虚假的外衣提出了这些规则。作为一种对我们自身实践的合格解释的实用主义,如果想继续维系下去的话,就得提出某些相对确定的路线。而且,只有当实用主义在法律阐释的第二个层面变得很强大、就像为国家强制进行辩护的政治理由那样广受欢迎时——也就是说实用主义值得倾力支持时,人们才能容忍这些路线的存在。是这么回事吗?[5](P159-160)
《法律帝国》的答案当然是“不”。在接下来的两章里,德沃金倾力展示:一种更好的理论——“作为整体的法律”——提供了一种同样连贯的法律理由,而无需我们接受那种法律体系是以普遍性的司法搪塞为基础的看法。不过,请注意这一论证被认为是对法律现实主义的确定性胜利,因为德沃金相信他在我们刚刚分析过的论证中,早已将法律实用主义证立为一种毫无过人之处的法律理论,理由是法律实用主义要求我们接受这种看法——法官是在进行有组织的撒谎和欺骗。
二、对德沃金论点的一个维特根斯坦式批评
“撒谎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吗?嗯,我能对某人说‘我要对你撒谎’,并径直这样做吗?[7](P189)
我相信我极有可能去反驳德沃金对法律现实主义的攻击,虽然我赞同这种攻击中的那些本体论和心理学假定,简言之,即当法官声称他们的判决是以适用含糊的先例或费解的成文法原意为基础时,他们通常是在撒谎。事实上,现今许多法律学术——譬如尝试说明并论证司法判决“的确”是以微观经济政策考虑为依据的学说,似乎表述了些许这种假定。柏拉图本人就倡导将“高贵的谎言”作为对国家强制进行正当化的理由,并且人们很容易将各种政治理论——主张能够并且应当运用欺骗的方式来描述艰难的政治选择,从而使它们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想象成是对神圣文本的必然适用,而不是活着的法官所做的错误的、暂时性的结论。
然而,我不打算在本文中接受这一论点。相反,我将质疑德沃金的前提——如果接受了现实主义的信条,那么当法官说自己是依据含糊的先例或立法原意进行判决时,我们就必须认为他们一定是在撒谎。这种论证要求我们重新检视德沃金对司法语言、思想和行动之关系所做的假定,并且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维特根斯坦的后期理论——来重新审视这些关系。
在德沃金看来,法官的这一陈述——自己通过适用某个含混的先例得出了判决——是某种类型的经验陈述,当且仅当该陈述与真实事件相符合时,它才是真实的。因此,当且仅当我们所谈论的判决,确实得自对源于第四修正案中的不确定权利所做的考量时,“我的判决是以源于第四修正案中的不确定权利为基础的”这一陈述才可能是真实的。从这种角度来看,法官的陈述描述了自己得出裁决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某种内在事件或曰心理过程。
作为一种可供替代的选择,德沃金也许可以声称,自己用不着纠缠于任何的此类心理分析之中,相反,依据下面的逻辑性理由进行论辩就足够了:(一)现实主义法官们——德沃金所界定的那种——并不认为遵循先例为某种方式的案件裁判提供了一个理由;(二)然而,这些法官在他们的司法意见中,却将先前判决作为他们判决案件的理由;(三)因而,这些司法意见是法官对他们判决理由所作的虚假陈述,也就是谎言。
但是,德沃金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论证所包含的前提,从维特根斯坦式的视角来看都是十分成问题的。第一个前提假定,只有当个人的陈述能够准确地描述在决定行动时所感受到的某种内在心理状态时,其行动理由的陈述才是真实的。然而,反观日常语言用法的话,人们很容易发现许多完全一致的理由陈述,而这些陈述看上去不可能是当时心理状态的陈述。“我和他结婚是因为当时我天真,并被他的表面魅力所迷惑”,说这话的人在她结婚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想的。同样,“我逃避公司营业税是因为我不知道它那么苛严”这一陈述,也没有反映说话者在注册公司时的想法。然而,它们都是对决定理由所作的合情合理的陈述,并且很可能被当作是真的,即使这些陈述先前作决定时的想法并不一致。更确切地说,这些陈述是对先前决定的一种反思性分析和解释。我们稍后再来讨论原因性陈述和解释性陈述之间的区别。
从维特根斯坦式的视角来看,这个前提同样是有问题的,即这些陈述被等同、指涉为法官制作判决时所体验到的各种心理状态。维特根斯坦非常怀疑那种过于简单的假设,即语言和心理状态总是一致的。请考虑《褐皮书》中的如下节录:
12.如果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我告诉他火车将要在3:30分开走的时候,我是相信火车会在3:30分开走的,我只是说了这句话,别的什么也没做”,并且,如果有人表示异议,说“这肯定不是全部,因为你可能‘只是说了这句话’,而自己却不信”,我的回答是,“我并非是想说,在言说并相信自己所言,以及言说却不相信自己所言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中,‘相信’和‘不相信’这一对概念所指涉的差别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差别构成了一个系谱),而非仅指一种差别,即存在某种状态和不存在某种状态之间的差别。”[8](P152)
因此,德沃金论证中的问题在于:他以一种想当然的方式——相信或不相信火车会在3:30分开走——假定,法官要不“相信”自己列在司法意见中的理由,要不就不相信这些理由。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否认那种内在的心理状态或者感受的存在,不过,他提醒避免这一假定,即可以轻松地将某个词语(如“相信”)和某种具体心理状态对应起来。确切地说,法官可能“相信”自己列在司法意见中的理由是正确的,也可能“相信”这些理由促使自己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对案件进行裁决,但这两种“相信”方式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种形式的“相信”也许存在某种家族类似,但它们是不同语言游戏的组成部分。
至于另一个前提——德沃金论证中的“逻辑”公式——的缺陷,就是似乎将所有不真实的陈述,都等同为谎言。因为本节开头所引的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提醒我们,撒谎不仅仅关系到一个陈述的真实价值,而且事关做出陈述时所处的语境。如果我说,我将对你撒谎,也许我随后就能说出一件不真实的事情,但是,我不可能实施撒谎(说谎者悖论)。这类不真实的陈述——“我的嗓子里有只青蛙”,“我要死了,埃及,我要死了”(当《安东尼和埃及艳后(Antony and Cleopatra)》中的一位演员这样说时),“对不起,那晚我很忙”(当你提出约会请求时别人这样说)——一般并不认为就是谎言(尽管有些没有意识到表演习惯的人,当看见安东尼在戏剧结尾处拿起弓时,往往会指责他在撒谎)。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谈论的说话者不想撒谎。就像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一旦我告诉你我将撒谎,我就不能做到撒谎,不管我的意图是什么。将一个陈述描述成谎言,并不等于描述了这句话的真正价值,也不等于描述了做陈述时的心理状态,而是描述了发生在特定社会场景中的一个事件。我认为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下面这段话中所暗示的意思:
当我撒谎的时候,我能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已是在撒谎呢?只要我并非“是在事后才认识到自已是在撒谎”,那么随后我还是知道自己当时是在撒谎。知道某人正在撒谎是一种默会的技能。这和那些感知撒谎的特殊能力并不矛盾。【页边注:意念】[7](P190)
当我撒谎的时候,我可能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撒谎,但有些时候,也许直到事后我都没有意识到。有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压低嗓子讲话,但有时我压低嗓子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直到停止讲话时自己才意识到。但是,将我对自己压低嗓子的感知,和压低嗓子这一行为混为一谈是愚蠢的,正如将感知撒谎的特殊能力和撒谎本身混为一谈一样。确切地说,对撒谎和压低嗓子的自我感知,就是这样一种感知——知道如何去做那件自己正在做的、心知肚明的事情。
基于这些洞见,让我们重新检视那些被德沃金描绘成谎言的司法意见。首先,我们必须从维特根斯坦式的视角出发,来认识使那些陈述言之有物的社会语境。这些陈述是向谁做出的?听到或者读到这些陈述的人们,又是如何理解它们的?
法官是在为谁书写司法意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许多有可能的候选人,并且相互间也互不排斥。法官是在为其他法官、律师、当事人以及普通公众书写司法意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法官的判决会涉及到所有这些人。然而,还应予以指出的是,最有可能阅读大量的司法意见,以及花时间去分析法官的论证和推理过程的人,是那些参与实际法律交涉的法官和律师。这立刻使“高贵的谎言”的假设受到怀疑,因为看起来正是这些人(法官和律师)最不可能被高贵的谎言所蒙骗。
如果一位现实主义法官试图隐瞒这一事实——她所宣称的规则实际上是自行创设的,并宣称这些规则“得自”上级法院某些含混而古老的先例,那么当上诉法官在阅读这位下级法院法官的判决时,是不会被她所蒙骗的。上诉法官同样熟悉审判实践,知道根据法律推理的惯例,可以为对含混而古老的先例所作的许多种不同理解,找出同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此外,如果他们对那种理由心存疑问,就会去找来由败诉一方提交的论点摘要。摘要正好包括这样一种论证,它表明依据含混且古老的先例,同样可以做出对败诉方有利的判决。
当然,目前存在这种可能,即下级法院法官确实无法对先例作出合理的解读,除了她采纳的那种理解之外(很像某些人,当他们面对一帧视觉想象图——从中可以看到两幅完全不同的图象——时,却看不到其中的任何一幅)。但是,我们为何不将其视为是法官——负责权衡和评判双方论点之人——的缺陷和问题呢?
请注意,这种对司法意见所作的制度性考察,已经使我们陷入一种引人注目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依据“高贵的谎言”对司法判决所作的论证,看起来不可能说服其他法官和律师来阅读它,而这些法官和律师知道审判法官的意见是以含糊的先例为依据的。然而,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诚实的”法官——她“的确相信”含糊的先例促使自己得出了某一具体的结论——看上去顶多是一位天真的法官,甚至是一个傻瓜。
德沃金对这种困境作了回应。下面是德沃金笔下的海格力斯式(Herculean)法官所撰的司法意见,当时他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未在事故现场的家庭成员的精神损害,是否要予以赔偿。该司法意见权衡了两种相互对抗的一般规则,通过检测它们与先前判决的“一致性”,它发现每一种规则都相当符合先前的判决,但并不完全一致。最后它宣称:
根据我的分析,当无限责任可能带来危害时,整体性要求解决这两种一般性规则对事故案件所造成的相互对抗的影响,我们的实践尚未就此做出选择(作为一种后来的诠释性判断),但这种选择必将涌现。整体性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它要求我们续写整个故事,在其中两种原则都有一个确定的地位,而所有的问题都以最好的方式得以考虑。在我看来,最好的做法是使第二个原则(根据过错,对所有可以合理预见的损害都要承担责任)优先于第一个原则(国家应该使人们免于因意外事故而蒙受经济上的损害,即使事故是人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这种做法至少在机动车事故——以明智的条款规定了个人责任保险——中已经得到了实施。我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因为我相信:尽管每一条原则背后的推动力都值得关注,但在这些情形中,第二个原则更为有力。[5](P270-271)
这一“司法意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对于解决我们先前遇到的困境来说,它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虽然现实中的法官,也许不会像法律现实主义者那样书写司法意见,但是他们肯定也不会像海格力斯式的法官那样书写司法意见。实际上,我欲斗胆猜测法律书籍中存在许多坦然的现实主义观点:法官承认他们从先例中找不到指引,只能依据“政策”判决案件。上述情况远多于这些情况,即法官对两条可供适用的潜在规则(这两条规则和先前实践并不完全一致)进行权衡,根据具体情况来确立它们之间的优先权,并据此断案。德沃金在法官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上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法官表述自己正在做什么这一问题上,显然是错误的。
于是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法律常常是含糊和不确定的,然而在大多数时候,当法官写到法律时,似乎先前的司法实践为大多数案件提供了清楚、明确的指引。但是,当法官在他们的司法意见中写到法律时,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他们并没有在描述法律的状况,他们也没有在描述自己内心的思考过程,相反,他们是在制作论点。
从初审法官和上诉法院之间的制度性关系来看,法官在制作论点这一事实,很容易得到认可。从这一视角来看,初审法院的司法意见可以被看作是向上诉法院递交的一个论证、一个案情简介,它用来说服上诉法官支持初审判法院的判决。当然,上诉法院的司法意见也可看作是用来做同样的论证,以说服更高一级的法院赞同或者拒绝受理上诉。不过,论证的说服对象不仅仅只是其他的法官。律师、当事人以及公众,也是论证的说服对象,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并非是劝说他们对案件采取某种具体的行动(即支持),而是解释和证明法官判决的合理性。
解释完全不同于原因陈述。从科学的角度讲,某一事件的原因包括导致事件发生的所有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譬如,水沸腾的原因,就是在通常的气压下,被加热到了华氏212度以上)。在日常用语中,当我们说到原因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谈到了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原因(譬如,我摔倒了是因为我在冰上滑了一跤,并不是因为我在去上课的路上,或者是因为现在是冬天,尽管这些也是我摔倒的必要条件)。然而,当我们就某一事件给出一个解释时,我们也许只提到了使事件发生的众多必要条件中的某一个,而不是那时紧接着出现在事件之前的那个条件(譬如,我和他结婚是因为我太天真,并为他的表面魅力所迷惑)。但是,对同一事件的其他必要条件的陈述,也许根本就不能作为解释(譬如,我和他结婚,是因为在婚礼上的适当时刻,我说了“我愿意”)。
一个好的解释何以是好的,以及一个不充分的解释何以是不充分的?简要的回答就是:解释的相对人的期望,对于解释是否算得上充分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9](P17-20)[10](P285-372)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问“为什么乔治·布什当选为总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这一陈述——“因为他在1988年的大选中获得了最多票”——是一个充分的解释,尽管它的确是一个真实的原因陈述。但我期望的是一种有别于此的陈述,它或许是一种说明了全体选民的心态的陈述,或许是一种说明了布什竞选运动之状况的陈述,或许是一种说明了广义上之社会经济趋势的陈述。因而,我们可以参照解释的充足状况,将这些期待看作是特定语言游戏之语法的组成部分,而解释就是在这一语言游戏中做出的。
在法律方面,语言游戏的期待,毫无疑问就是法官的司法意见会包含某种法律论证,并且这种论证将努力依据先前的权威来解释和证立判决。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见,这种解释无须和法官裁决的直接原因相一致,也无须是这种原因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与法律论证有关的整个“真实”和“相信”问题,是相当复杂和烦人的。当我将自己看作一个说服法庭的律师时,会发现自己能够毫不费力地作出这样的陈述:“法律要求一个有利于本方当事人的判决”,或者“对方所引证的先例,和庭审的案子有着明显的区别”。简言之,我发现自己以同一种确定和清晰的语言进行论证,但当这种语言出现在司法意见中时,看上去却问题成堆。
我相信自己的论证吗?我真的相信法律要求作出一个有利于本方当事人的判决吗?当然是的。但是,其方式和我相信火车会在3∶30抵达是完全不同的。我相信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好的论证,我相信根据先例,做出有利于我的当事人的裁决是明智、公正的以及能够服众的。但是我也十分清楚,实际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要求法官按照我的方式来做出裁决,而我的对手也作了其他一些论证,并且法官的裁决有可能不利于我的当事人。
那么,为什么我在论证使用要求、强制以及确定性这种话语呢?部分的原因是,那仅仅是我的语言游戏的习惯而已。没有人会料想我会这样讲:“千真万确,在这个案件中先例会支持另一种裁决,但是我相信,做出有利于我的当事人的裁决会更可取、更合适”,实际上,假如我这样讲的话,别人会感到有点惊讶。法官非常清楚:当我说法律“要求”或者“强制”某一特定结果时,并没有否认法官在审理中的选择余地。法官以及其他参与司法过程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词语是制作一个有力论证的习惯之组成部分。这反过来使得我无法以更日常化的语言和更真实的想法来表述自己的论证,即一个有利于我的当事人的裁决是“可取的”或“合适的”,因为法律论证的习惯使那些措辞显得极其无力。
大量运用先例和权威,也常常是法律论辩之习惯的一部分。告诉一位美国法官“这种言论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和告诉他“这种言论不应该受到美国政府审查或压制”,也许没有什么差别。尽管一句是宣示性陈述,另一句是规范性陈述,但法官将它们都理解为法律论证中语言游戏的组成部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法条和先例是律师和法官用来辨别、对照自身实务的。当我们言及“米兰达忠告”、“规则11动议”、“501(b)社团”时,我们仅仅将它们看作是法律界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运用它们所提到的具体权威。
因而在法律论证中,大多数对先例的运用和争论,很有可能也是尝试去确定和表述法律结果,而不是陈述这些结果的理由或原因。当一名法官裁定:“有关欺诈的法条致使合同无效”,那么她是在说反欺诈法的适用促使或要求这般裁决吗?或者说她只是用一种能为其他律师所理解的形式,并以解释该结果与先前实践之关系这一方式来陈述她的结论?我料想是后一种情况,即法官是在运用先例来阐明结果,并解释和证明该结果和先前实践是一致的。因而,依据先例来阐明判决结果并不是在撒谎,不过,对法官判决结果的获得方式所作的真实的原因性陈述,也不是撒谎。
在《褐皮书》中,维特根斯坦深入讨论了假设性话语,其间他依据行动的可能性描述了了自然陈述(physical statement)。他说道:
一个部落在战争中,用它自己的语言来命令人们采取某些动作,譬如“射”、“跑!”、“趴下!”等等。这些动作可用来描述某人的体格,其描述形式有:“他可以跑得很快”,“他可以把矛投得很远”。我说这些句子是对此人体格之描述的依据,是他们对这种形式的句子的使用。因而,如果他们看到一个腿肉发达的人,他们会说他是一个可以跑得很快的人,虽然后者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法跑步。那种肌肉发达的人,被他们说成是“能把矛投得很远”的人。[8](P102)
我的意思是,在法律论证的语言游戏中,对行动可能性的陈述,经常是依据法律状况和法律地位来描述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说合同不应该生效,那么我们就说根据反欺诈法,该合同是无效的。如果我们想说,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被驳回,因为缺乏证据,并且他提出诉讼意在骚扰他人,那么,我们就说原告违反了规则11。因而,虽然这些陈述看起来是对实际法律状态的描述,但是在裁判之前,如果一个律师被问及“原告真的违反了规则11吗?”,他可能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他会认为,提这种问题的人根本不理解法律论辩和法律论证的性质。
我们从而看到,德沃金对法律现实主义所作的批驳之前提,就是凭着一种过于简单且很成问题的法律语言观,要求我们将法官视为搪塞者。司法语言有可能被看作是对某些理由的阐述,而这些理由完全不同于法官制作判决时飘浮在其脑海中的那些理由。确切地说,法律推理的惯例往往使法官依据法律规则所规定的确定结果,来阐述自己的判决,尽管司法过程的参与者,会将这些陈述理解为法官在裁决中选择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的解释和理由,而不是一种路径——法官据此发现待决案件之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描述。
当然,这些对法律论辩中的语言游戏所作的描述,仍然是尝试性的、不全面的。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在我们最习惯、最熟悉的日常语言形式中,常常隐含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惊奇。虽然大多数律师都知道如何讲好我们的法律语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接触到了法律语言之秘密的表层。
陈林林,浙江财经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杭州 310012);刘诚,中山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广州 43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