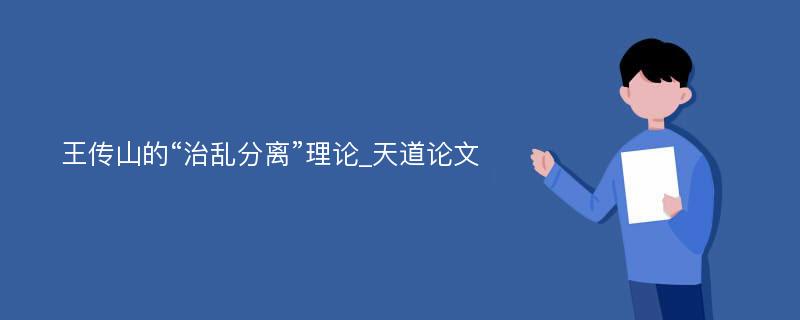
王船山的“治乱合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船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易·系辞下》云:“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乃天地固有之道,先秦以降,人所共识。王船山亦然,但他却不满于此,而是作了一番认真而细致的反思,进而系统地阐发出一套历史观来。在他看来,道之开展必产生出一个自然世界。自然世界无其心,于道不明。生于自然世界中的人,因天之化成人之能,为天地之心,故发明天人相续始终不二之理化成人道,尽物理通于天,因而于自然世界中创造出一个人文世界。人所创造的人文世界在时间中开展,便构成为历史。历史是人的历史,是“立人极”之人尽其道以通天的创造过程。历史因时因人而有,故亦因时因人而变。考之于现实历史,“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1],而治乱合离是历史变化的必有之理势。[2]于是,船山便以“治乱合离”来概括历史变化之形态,把它们作为历史变化的具体表现,故治乱与合离均为王船山历史观中的重要范畴。 一、“一治一乱,一合一离”本天道 王船山认为,治乱与合离之所以能反映历史变化之形态,首先从根源上讲,本身就是阴阳盈虚之天道。他明确指出: 治乱合离者,天也。[3] “天”,谓天之欲平治天下与否,有一治一乱自然之理数。[4] 一治一乱,自是天之条理错综处。[5] 世运之治乱,人事之顺逆,学术事功之得失,莫非一阴一阳之错综所就。[6] 一治一乱,其为上天消息盈虚之道。[7] 天命自成其一治一乱之恒数。[8] 天地之气,辅其自然而循其不得已,辅其自然故合,循其不得已故离。是故知天地之昼夜者,可与语离合之故矣。[9] 合极而乱,乱极而离,离极而又合……自然之节,不得已之数也。天且弗能违,而况于人乎![10]所谓治,因合而生;所谓乱,因离而成。[11]“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阴阳二气。”[12]天地有阴阳,辅其自然之几[13],就时位之正,则生“合”;循其不得已之几,时位有所不正,则生“离”。故合者,自然之理,有所辅正;离者,不得已之数,不正亦循。正而“无不正者以相干”,则治;反之,不正则乱。[14]故合而治,乱而离。船山指出,“一治一乱”,“一合一离”,无不是阴阳二气盈虚错综所致,为道之开展固有之理势。也就是说,治乱合离是天道阴阳之几所造成。道之开展,因时几之变,则有合而治,乱而离的变化。道之开展遵循的是“因时而万殊”的规律。其化生人物,虽然分一本之道为万殊之理,天地人物各得其理各有其命,因时位之不同,各有其变化;但万殊之理万有之化皆统于一本之大道一本之大化。故在船山看来,这些变化虽不息不滞,却非杂乱无章。“天乘乎时,而有治乱”[15],“时者,有序而不息之谓。”[16]合而治,乱而离,体现的就是时变之有序;而时变不息,则“一治一乱”、“一离一合”,循环不止。故治乱合离自是“天之条理错综处”,其反复相寻、循环不止则为“理之常”、“自然之节,不得已之数”即“自然之理数”或言“恒数”,“犹日之有昼夜,月之朔、弦、望、晦也。非其臣子以德之顺逆定天命之去留”[17],“不可以夫人之情识论之”[18]。由此,船山才说,“治乱合离者,天也”,“知天地之昼夜者,可与语离合之故”;治乱合离,反复相寻,“天且弗能违,而况于人乎!” 既然,治乱合离本天道之所然,为道之开展所固有,那么,历史之变化就可以由此而洞察知晓。由前述可知,人文历史世界是人造之于自然历史世界的。人文历史世界与自然历史世界的区别不在于时间本身,而在于人性因素的融入。前者是立人极正道术,践形尽性,以通天达化的人类实践创造的结果。人的创造并不是凭空而造,不过是对自然历史世界的改造。用船山的话来说,人道之大,作对于天而有功,只能是相天、参天,而必不能代天。因而,人所创造的人文历史世界,其变化形态首先应当遵循天道本然之性。这里,我们还可以根据前述船山对历史观念的诠释,做一逻辑证明来说明这一点。可以这么认为,“历史变化之可能”这个命题,取决于三个基本命题的结合,即在时间这个大前提下,以道之开展而有的自然世界为充分条件,以立人极正道术之人进行相天造命之实践活动为必要条件,三者合一,才得以成立。自然世界作为道之开展的显现,直接反映了道的本然特性。立人极之人创造人文世界,是在自然世界中本天道以尽物理而通天的实践行为之结果,即人生于世,道之在人,因我而行,相天造命,以人文化成天下。故道之本然特性必然通过立人极之人载道相天的活动反映出来。而时间因乎阴阳之几,与道合一。现代的逻辑哲学认为,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即是说,一切命题都可以用具有根本规律特征的真实命题所隐含的真值判断表现出来。[19]由于船山认为,组成“历史变化之可能”这个命题的三个基本命题都是真实命题,都隐含着对“一治一乱,一离一合”的天道之本然特性的真值判断,所以该命题必然也具有同一特性。即是说,立人极之人,能“充天地之化,皆我性也;试天地之化,皆我时也”,其所创造的人文世界于时间中开展而成之历史,必然表现为道之开展状态所固有之理势,即“一合一离,一治一乱”,反复相寻,循环不止。故船山曰:“一合而一离,一治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20]也就是说,通过“一合一离,一治一乱”,我们就能够明晓道之开展的状况,通达历史变化的形态。 二、“一治一乱,一合一离”亦人道 依船山看来,历史变化之形态具有“一治一乱,一离一合”的特征,固然是天道本然之反映,但历史之为历史乃在于人的创造,是人类有目的之行为的结果。历史变化之形态应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即为人所创造的历史,其治乱合离之变化形态是如何导致的,并如何与天道开展本然之性相通的。船山认为,这与作为历史变化动力的人本身密切相关。他说: “治乱合离者,天也;合而治之者,人也。”[21] “治至数百年而必乱,天道也。乱则必拨乱而反治,人事也。”[22]船山首先肯定历史变化“一治一乱,一合一离”的态势是天道所为,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亦有功于历史变化。具体而言,天无仁心,只因其自然不容已之几,成其治乱合离之势。人则有心,因天成能,“以至仁大义立千古之人极”[23],故其所行有仁义,离而乱之则思以合而治之,必拨乱而反治,以治相继;合而治之则戒以离而乱之,以图长治久安,“治者原不继乱”[24]。未有离而乱之而承其离乱,合而治之而继以离乱的。也就是说,人有功于历史,是在遵循由天道本然决定的历史变化基础上,唯有觉几审几,才能因而化之,循而治之,从而造之。而且船山认为,人可合其治之外,亦可成其乱,并且皆非一旦之功。他说:“天下之治也有渐,而乱也无余。乱无余,可以兴矣,而犹未遽兴也。未遽兴,则将流而复甚。无他,天道亏盈,而人心乐动。盈而动,一旦戢之,难矣。”[25]治乱本是天道开展的必然规律,无有商量。而且,治乱皆非一旦可成,不会“遽兴”。乱而图治,人事可为,但要有一个过程。治而生乱,人亦可为,然“犹未遽兴”,同样需要一个过程。若天已乱,人又为乱,人却不知,则人为乱之心流行天下必加剧天下之乱;待人已知,则不可挽回其为乱之心,因为人心乐动,一旦发动便难以收敛了。 此外,船山还强调“觉几”而行,不可不顾及仁义之道。他曾指出:“夫天下之合离与其治乱也,则固有几矣。几不可昧,昧之者逆;几不可觉,觉之者狂。昧而不逆,愚忠者也,志士仁人之所蹈也;觉而不狂,已乱者也,大人君子之所造也。夫郑则恶足语此哉!觉几之离,因而离之;觉几之合,因而合之。宗国可弗恤,寻盟可弗顾;仇雠可以亲,慝怨可以友。终春秋之世,日左顾右盼,以相天下之俯仰而合离。智益索,力益竭,乃辱人贱行在其君,辛苦垫隘在其民,乱其室以乱天下,而成乎乱门以终矣。悲夫!”[26]合离与治乱固有天之几,人除了必须正视它,觉察它,因循它之外,还必须时时兼顾人之为人应有的仁义之道,才能真正有所为。否则,背弃人之为人的仁义之道,“觉几之离,因而离之;觉几之合,因而合之”,就会“昧而逆”于几,“觉而狂”于几。这种人若为一国之君主,就会不顾宗室之国,胡乱结盟,亲仇雠友邪恶,辱人贱行,辛苦困顿其民,则乱其家乱其国而必乱天下,终究不得善终。因而,他强调“觉几”“必待其人”。他说:“人有人之道,皆可行者也,而非其人不能尽人之道,则必待其人焉。”[27]在船山看来,能否觉几审势且行仁义之道,因其治乱合离而有所作为,为功于历史,取决于人极立与不立之人。 人之创造人文历史世界,是立人极正道术,践行尽性以通天达化的实践结果。人极之立,人道之立,决定了人之为人的本真特性。若人极已立,则明于天人相续,继善成性,人为天地立心,故道自我行,与天同化。若不立,则天人不通,性命不明,人物相杂,而人同禽兽,故行禽之行,必乱天下。因此,立人极正人道关系到历史治乱兴衰的大事。然而,并不是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能知天尽性以立人道之大极的。船山说: 人与物皆生于天下,其并生而不相杂久矣,乃其俱生而易以相杂亦久矣。天下之生莫贵于人,人全其人而物不干之则治,物杂于人而害于人则乱。乃治矣,而流风易息,故治未久而乱乘焉。其乱也,必有人焉,因时致功,而后复治,自唐虞以来莫不然者,而今犹亟矣。[28] 人与禽兽皆生于天地之间,而欲全乎人者,必远禽兽之害。禽害人则乱,人远禽则治。[29]自有历史以来,人物与禽兽本有别不相杂。依船山看来,人物与禽兽虽同为二气五行所妙合而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但唯独人得形气之正,能全其性成其能,有择有持以立人道,于天地间创造出一个人文历史世界,而人成其为人。物之为物,只能因循天道本然之理以生,为天道所驱使,不能有所作为。禽兽之为禽兽,只能用其初命,有天明无己明,同物一样为天所驱使,无所作为。然人之生,虽有形气之正,若不全其性尽其能,则虽有人之名,而实际上无以异于物禽,听天由命,无所作为。故人与物禽容易相杂。人之全其性成为人,其要在于日受天命日成其性,有一日受命有一日成其性,则有一日为人;若有一日不成,则此一日便不成其为人,人同禽兽。故先人虽然已经创造了人文世界,人类皆生活于其中,但后人不尽其性成为人,没有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即便是享受着再高尚的人文生活,也于禽兽无异。因而,船山说,人与物禽“并生而不相杂久矣,乃其俱生而易相杂亦久矣”。天下之生以人为贵,就在于人能全其性尽其能,成为天地之心,统用乎物,于自然世界中创造出一个人文世界以协天地之化。由此,观之于历史变化,若“人全其人而物不相干”,“人远禽”,则成其治;若“物禽杂于人而害人”,则成其乱。天下已成其治,而人道相沿之风气不易长传,则“治未久而乱乘焉”;天下已成其乱,而必有人出以立人道,“因时致功,而后复治”。船山认为,中国历史自尧舜以来都是这样的。“其‘一治’者,人道治也。其‘一乱’者,禽兽之道乱乎人道也。”[30]“当其治也,则中国有共主”,故合;“当其乱也,中国无君”,故离。[31]历史就是如此治乱合离,循环不止。 由上所言,人之创造历史,以天道行人道,则道之在人,由人行之,故历史治乱合离之变化是天道本然之性通过人之创造表现出来。行人道远禽兽之道,则合治;禽兽之道杂于人而害于人,则离乱。而人道治于不治,禽兽之道乱与不乱,取决于人极之立与不立。故立人极便能行人道,则合治;反之,人极不立,禽兽之道杂害于人道,则离乱。历史变化之形态就由此形成。 三、“一治一乱,一合一离”,无定亦“无畛” 而且,船山还特别指出,治乱合离并没有固定的周期性,并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合治之后,就会出现同样时间的离乱,如此反复循环。他认为,治乱合离有其时几,“辅其自然而循其不得已”,故其治乱合离虽循环,却无定,亦“无畛”。船山说: “治乱循环,一阴阳动静之几也。今云乱极而治,犹可言也;借曰治极而乱,其可乎?乱若生于治极,则尧、舜、禹之相承,治已极矣,胡弗报以永嘉、靖康之祸乎?方乱而治人生,治法未亡,乃治。方治而乱人生,治法弛,乃乱。阴阳动静,固莫不然。阳含静德,故方动而静。阴储动能,故方静而动。故曰‘动静无端’。待其极至而后大反,则有端矣。”[32]所谓“治人”,立人极行人道之人;所谓“乱人”,人极不立,行禽兽之道之人;所谓“治法”,立人极行人道以平治天下之法。在船山看来,治乱合离是无定的。治乱循环的道理如同“阴阳动静之有几”一样。阴阳之几生动静,阳为动,阴为静,而阳又含静德,阴又储动能,方动即静,方静旋动,动静循环,只因几之发动而动,只因几之生静而静,而几之发生不可测,故“动静无端”。动静无端,无有其定。若说天下离乱至极后则一定有合治,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合治乃人事,人可为之谋;若说合治至极后则一定有离乱生,这怎么可以呢?如果离乱果真生于合治,那么尧舜禹这三位圣人以人道合治天下相承相继,各自都达到合治的极至了,为何在他们之间没有报以西晋怀帝永嘉或北宋钦宗靖康时期的离乱之祸呢?方乱之时,有治人生于世,而治法又未亡失,则天下终能由乱反治;方治之时,有乱人生于世,而治法又松懈不备,则治便转为乱了。[33]天下治乱循环的关键在于治人或乱人之生与治法之存。而治人或乱人与治法,取决于人极、人道之与立,其权全在人自身。人之立与不立,无有其定,如同阴阳之几生动静。故治乱合离亦无定。即言之,船山认为,历史的变化是因时几而偶然生成的,他的历史观不是决定论的。船山于此有言:“邪正无定从,离合无恒势,欲为伸其是、诎其非,画一是非以正人趋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断。”[34]然而,船山又指出,动与静“待其极至而后大反,则有端矣。”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动静相含相渗,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之中各有其静动之几,彼此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静中所含动之几必发展成其动之极,动中所含静之几必发展成其静之极。故动静亦有所定,于其无定之几中,见其理势之当然而定。当然,动极成端有其静几在,静极成端亦有其动几在。治乱合离之关系亦如此,彼此包含,彼此渗透。这无疑揭示了治乱合离的另一特性,治乱“无畛”。[35]船山曰: 何以谓之陵夷?陵之夷而原,渐迤而下也。故陵之于原,无畛者也。乱极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极而乱,非一旦之乱也。方乱之终,治之几动而响随之,为暄风之试于霜午,忧乱已亟者,莫之观焉耳;方治之盛,乱之几动而响随之,为凉飔之飏于暑昼,怙治而骄者,莫之觉焉耳。[36]如何看待丘陵夷为平原的现象呢?由丘陵夷为平原,其地势是逐渐斜着延长下去的。所以丘陵与平原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治乱的情况有同于此。离乱达到极点后出现合治,合治不是突然出现的;合治达到极点后出现离乱,离乱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当离乱快要完结时,合治之几已发动而一直跟随着离乱,好比暖风试探于寒午,忧虑离乱已经急迫的人是看不到的;当合治达到极盛时,离乱之几已经发动而一直跟随着合治,好比凉风吹扬于炎日,依仗合治而骄逸的人是察觉不到的。其实,离乱中已有合治的征兆,合治中亦已有离乱的预示。由离乱到合治,合治的因素一直存在着;由合治到离乱,离乱的因素也一直存在着。因此,历史之变化“离而合之,合者不继离也;乱而治之,治者不继乱也。”[37]难以确定何时合治、何时离乱,亦难以严格区分出治与乱、合与离之间的界限。“夫几亦易审矣,事后而反观之,粲然无可疑者。而迂疏之士,执一理以忘众理,则失之;狂狡之徒,见其几而别挟一机,则尤失之;无他,气焰之相取相轧,信乱而不信有乱之几也。”[38]故船山强调“明于治乱合离之各有时”[39],因治乱合离之几,审时度势,离乱不必忧,故能知合治之几动,辅其自然之几,则能成其治;合治不必骄,故能察离乱之几动,循其不得已之几,则能不继其乱,待合治之几发动,终能成其治。因而,治乱合离,无定亦有所定,于其无定之几中定;“无畛”亦有所见“端”,于其无畛之几中见。 四、“一治一乱,一合一离”,循环又发展 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和《四书训义》等有关部分针对孟子著名的“治乱”论阐发其微言大义,并将其精神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当然,船山并不是简单复述孟子的思想,而是深化完善了孟子的理论,探讨了治乱循环与阴阳之几的关系,从而为治乱循环找寻到了形上的依据,在天人两方面予以立论,深入发展了孟子有关治乱合离的思想。船山以为,治与乱、合与离,不是单纯的相接续,而是各有其时几,因时几而出现的。也就是说,船山的治乱合离论不是一种具有决定论性质的治乱合离首尾相衔的封闭循环历史观,恰恰相反,是一种既循环又发展的开放的偶合历史变化观。 就“治乱”而言,船山探讨了中国历史兴亡的原因。他发现“治乱”虽“形如一”,却是“质日代”[40]的。换言之,历史治乱的形式表面看似一样,其实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 上世之乱在天灾,而物乘天之灾以逼人;中古之乱在人事,而君率兽以害人之生;后世之乱在人心,而行禽之行、言禽之言以乱性。[41]依船山之见,历史治乱的原因因历史的先后变化而有三:其一,上古时代祸乱的原因在“天灾”。船山认为,尧舜时代,人道初立,人力衰微,天灾一起,物便乘灾威胁于人“以争人之处”,并不是物会害人,“水使之然也”。因而,只要治水就能远物之害。故禹之治水,“以人道为己任而治之也,乃一治矣”。[42]其二,中古社会的祸乱主要在于“人事”。若天安地平,物不害人,天下何以还乱呢?其乱在国之君主,不行人道而夺民以养兽,率兽食人,则乱。如殷周之际,商纣既已大乱天下,便有周公相武王,“以人道为己任,而除物害以安民生,又一治也”[43]在船山看来,随着人道渐立,社会取得长足地发展,人的力量逐渐强大,天下治乱兴衰便由人定。其三,后世社会祸乱出自“人心”。天虽不成灾,君主又无暴行,可是异端邪说兴盛而蛊惑人心,使人行禽兽之道,必导致天下大乱。如春秋战国之际,杨、墨之言充满天下,使人心之仁义塞,导致天下皆兽,而必有人相食之事,故圣人之道息,禽心猖獗,此为“一乱”,而且“乱至此,愈隐而愈极矣”。[44]船山认为,前述天灾与禽兽害人致乱这两种原因,还只是伤人之身体生命,人尚可以同天与禽兽“均敌于死生之际”[45];而异端邪说之害人,看似近理而实惑乱天下后世,使人言禽言,行禽行,入于心性[46],此“戕人之性,人且为禽兽驱遣,自相残食而不悟”[47]。这种危害最大,可谓为乱之极了。故要治其乱,唯有圣人复起,正人心息邪说,“尚可与治”。[48] 通过以上的分析,船山认为,历史变化的形式表面看似一致,体现为治乱循环;其实,却有着质的变化。若说历史之初,其变化由天而定;那么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自身力量的不断强大,其变化之因便由天而逐渐转为人,取决于人道。若人道不正,则禽兽之道兴,而人道必乱。乱而图治,必有治人出,因时致功以复其治。而且此种治乱合离不是一种简单重现,而是“日隐日深”[49]的。船山十分明锐地发现,乱之原因存在着由“天灾”到“人事”进而“人心”的发展变化,历史之治亦因之而发展变化的,并且是“乱日深”,其治必随之“日深”而有其不断的发展变化。因此,历史的治乱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表面上治乱交替循环,实际上却“乱的内容愈下愈厉害,于此相称,治的内容也愈来愈精致”。[50] 船山以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历了三次大的治乱变化。三代时期,“天下虽合而固未合”,“以义正名”而合万国,此为一变。春秋时代,诸侯雄起分裂天下;战国时期,更是七雄争霸天下,而“天下并无共主之号”。从此,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一合一离”的变化格局。“六国离,而秦苟合以及汉;三国离,而晋乍合之,非固合也。五胡起,南北离,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离,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离之局一变也。”此为二变。而宋以后,直至明末,“当其治,则中国有共主;当其乱也,中国无君,而并无一隅分据之土”,合而不离,绝而不续,形成统一国家内部的治乱更迭。此为三变。[51]总此三变,其格局不外乎“一合一离”的形态。但历史“一合一离”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不断进步发展的。在船山看来,唐虞以前,人类社会“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故“人之异于禽兽无几”。虽然三代及春秋时,犹可见人类如同物禽的种种陋行,如“当纣之世,朝歌沈酗,南国淫奔”,“春秋之世……父子相夷,兄弟相杀,姻党相灭,无国无岁而无之,蒸报无忌,黩货无厌,日盛于朝野”;但更可见尧、舜、禹等圣明之士明伦察物而远物禽以图人道在前,孔子撰《春秋》、裁《诗》《书》、定《礼》《乐》以立人道于后,故有“乱贼始惧”,而“道术始明”之说。[52]也就是说,尽管三代春秋时代人类有许多事情如同唐虞以前,但是在不断努力地开化文明之后,人类逐渐知晓“有天之性安”,终于能“立人极”明道术,其文明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以前了,“固非唐虞以前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者比也”。依此理,船山纵观历史“合离”交替循环之变故,明确了人类社会顺随历史不断发展,并开创出一个“世益降,物益备”[53]且“伦已明、礼已定、法已正”而日趋于昌盛的文明历史世界。由上可知,中国历史“一离一合”的变化同其“一治一乱”一样,形同而质异,是循环又发展的,并且是“质日代”的。[54]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王船山的“治乱合离”论虽以一种自古以来惯有的表现形式出现,却不满足于历史表象的阐述,而是深入其机理挖掘其内在依据,从天人两方面揭示了治乱合离的形上基础,进而通过理论与事实两方面的结合,极其睿智地抓住历史“形如一”却是“质日代”的本质,因而将历史的变化表述为既循环又发展的。 在船山看来,历史的变化看似无痕,实有其迹,皆因几而呈现,具体表现为“治乱合离”式的“日新之化”;而历史的治乱合离,因其自然之“几”而无定亦“无畛”,看似没有明确的分界,是一个有机地偶合构成过程,实则历史的变化是在偶然中展现出其多元性的,既可以是前进的,亦可以是循环的、停滞的,甚或是倒退的,任何一种可能性都存在。[55]由此可知,船山将历史描述成一个具有“时间之矢”的变化形态,并且是一个创化不已的、开放的、偶合的有机整体动态过程。若将该过程模型化,就可简化为一个几何图形,即所谓的螺旋式上升。但船山的历史形态观如同中国传统诸多学人一样,绝非几何式的。实际上,这是一些现代研究者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反观中国传统历史时所容易犯下的通病。即是说,源自西方欧几里德几何学而形成的,作为成就现代西方人科学理性的一种文化资源而出现的几何学式思维统治了我们的头脑,受此影响来反观中国传统思想,从而误读了中国历史。平心而论,对船山的历史变化观用现代语言来加以叙述的话,不妨解读为如下一句话:历史的变化是道在时间中因“几”而偶合的、因“几”而生成的开放的有机整体动态式的,即是历史性的,而绝非决定论的开展。具体来说,就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因“几”偶合而呈现出其治乱离合的形态并以治乱合离的样态不断转化。[56]此种转化,并非决定论式的固有之态,恰恰相反,有其偶合性与创造性,是一种“创化的历史观”。历史的治乱合离表现为“形如一而质日代”,就是这一创化历史观的直接反映。 应当指出的是,王船山认为,历史之所以表现为“治乱合离”的具体变化,皆因几而成。有在天之几,是天因之化生自然历史变化;有在人之几,是人因之化成人文历史变化;天人之几交相化,则是天人合同一致而成历史大同之化。所谓“几”,从根源上讲,是气之几。气有阴阳,必交感而有一阖一辟聚散屈伸往来消长之几,即所谓“轻者浮,重者沉,亲上者升,亲下者降,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皆阴阳和合之气所必有之几”[57]。故“几”指的是太和本真之义。如“盈天地之间,絪緼化醇,皆吾本来面目也。其几,气也。其神,理也。”[58]几只能是天道本然之真几,即太和元气固有的本真性。太和之本真性即絪緼相荡而化生天地人物之理势。即船山所言:“絪緼,太和未分之本然;相荡,其必然之理势。”[59]换言之,太和元气阴阳交感具有着“必然之理势”即为其真几。故太和阴阳之道因其几开展而有其历史,历史之变化就因其必然之理势所成就。船山“治乱合离”论的历史性特性主要是通过“理”与“势”来体现的。在他看来,历史的“治乱合离”是通过道之时几化成理势所偶合生成的,遵循的是因“贞一之理”与“相乘之几”而合理势所产生的“时亟变而道皆常”的历史规律。[60]合治成于理势,离乱亦然,皆因理势之自然所成。而理势因乎时几之偶发,故合治与离乱所组成的历史形态通过理势的偶合构成了历史变化的趋势,由此形成了历史这一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而这已超出本文所论范围,惟有留待于另文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