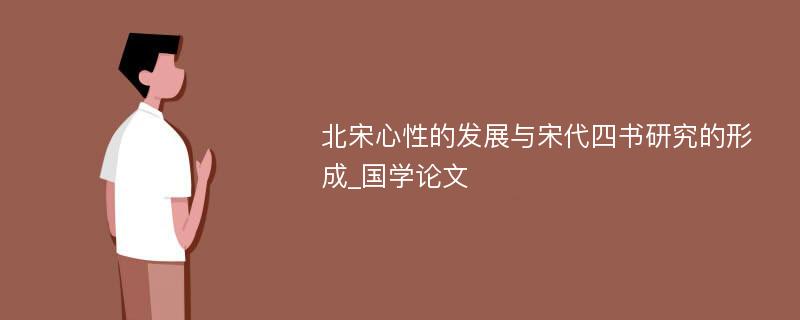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性论文,北宋论文,宋代论文,之学论文,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书》之名,起源甚晚。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首次将《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并为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终于出现①。此后,随着理学的兴盛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流传,《四书》之称遂被广泛接受、使用。《明史·艺文志》中立《四书》一门,《四库全书总目》亦在经部中立《四书》类,二者内容分别包括此前历代学者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注解之作。本来,从严格意义上说,《四书》之名确立之前的各种有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解说、注疏之作不应归入《四书》类中,如清朱彝尊《经义考》就于《四书》类之前,仍立《论》、《孟》两类,且凡《四书》之名出现之前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以存其古义。然而,正如四库馆臣所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流行于世后,前创后因,久则为律,《四书》之称已相沿成习。更何况“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因此,《明史》等将历代有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著作归入《四书》类,是“循其实”而“不复强析其名”(《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经部·四书类一》,《序论》,中华书局,1965年)。这一看法,虽为一家之言,却不无道理。本文所谓的《四书》学,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是指儒家学者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进行解说、阐释、注疏、发挥而形成的研究成果。
在《四书》学发展史上,宋代具有重要地位。而宋代《四书》学形成,又与北宋时期心性之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当时,儒家学者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试图以心性理论的探讨为核心,努力发掘传统儒家经典中的思想资源,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阐释、利用与发挥,宋代的《四书》学因此形成。
一、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
宋初,儒学发展已呈现出衰颓陵夷之势,面临着种种危机。从儒学自身看,汉唐以来,儒家学者在经典解释中多注重训诂考订,而对经典的精神实质与思想内容却缺少发掘。这种取椟还珠的治学方法导致了儒学的日益僵化,其内在活力受到扼制,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儒学不能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的精神生活起指导作用。这种状况,是当时儒家学者必须正视并着手加以解决的。事实上,为了挽救儒学的这一危机,宋初士人们也的确采取了种种措施。他们反思汉唐儒学的弊端,变革治学方法,希望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阐发其中义理以振兴儒学。为此,士人们力图摆脱汉唐经学拘囿于家法、师法,沉溺于考证训诂的治学学风,在经典训释中采取以心契心,自得于己的方式,最终自出议论,独标新义,以义理之学代替了章句训诂之学,为宋代儒学复兴开辟了道路。
但是,当时儒学的更大危机是来自佛道之学的外部挑战。魏晋以后,随着佛道势力的增长,佛道之学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亦不断扩大,其中佛教影响尤盛。到宋初,从皇帝朝臣到下层平民,都有不少人浸淫其中。儒家学者亦往往为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学所吸引,对佛教的本体、心性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一时士人相率谈禅,以高妙玄远相尚,出现了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五),“今人不学则已,如学焉,未有不归于禅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96页。以下引文出自《二程集》者均标注页码,《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河南程氏文集》、《河南程氏经说》、《河南程氏粹言》分别简称为《遗书》、《外书》、《文集》、《经说》、《粹言》)的情形。显然,异端之学的挑战空前严重,儒学的地位正在被削弱,已经到了必须对异端之学的挑战作出有效回应的时刻。
然而,佛道之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绝非偶然。佛道之学长于理论思维,在个人心灵安顿方面有一套颇为精致的说教。从东晋、南北朝开始,佛教思想家就非常注重心性理论的建构,将心性论作为其理论思考的重要内容。到隋唐时期,作为佛学核心的心性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各宗派都依据不同的佛教经典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心性理论。② 相对而言,传统儒学主要以现实生活中的日用伦常之事为其致思重点,虽然自思孟学派以后,探讨心性理论的儒家学者代有其人,也不乏精辟之见,但到汉唐时期,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现实政治运作的工具,儒学中强调外在礼仪制度、外在规范的内容被大大突出、凸显,而其中心性之学的内容则往往被忽视,心性主体的构置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因此,从理论思维上看,佛教心性论的精致细密,已非儒学所可比拟。一些佛教思想家对此也颇为自信。如唐华严宗五祖宗密(780—841)就声称:“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原,则佛教方为决了。”(宗密《原人论·序》)似乎佛教已经垄断了心性领域的话语权。后来北宋仁宗时高僧契嵩(1007—1072)亦谓:“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契嵩《镡津文集》卷八,《寂子解》)这种观点,反映了唐代及宋初一些佛教思想家普遍的自负心态。对这种观点,一些儒家士人也颇为认同,社会上广泛流传“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修身”之论。张载弟子范育曾谈到唐宋之际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张载集·正蒙·范育序》)一时间,对心性问题的探讨似乎成了佛学的专利,儒家在心性领域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
显然,对于宋初儒家士人而言,要真正战胜佛道之学,就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薄弱的缺陷,建立起能够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
宋初儒学学者在对佛道之学的长期批判与接触中,逐渐意识到必须“修其本以胜之”(《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本论》下),加强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从根本上战胜佛道之学。同时,他们对佛道之学理论上的长处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如李觏指出,“佛以大智慧,独见情性之本,将驱群迷,纳之正觉,其道深至,固非悠悠者可了。”(《李觏集》卷二十四,《修梓山寺殿记》)应该说,这种认识是颇为清醒、明确的。李觏甚至还肯定了性命之学的价值,并力图将讲性命之学的主动权归于儒家,认为儒家经典中已蕴含丰富的性命之理,不必求之于佛典。他批评一些儒者“欲闻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从释氏而求之。”(《李觏集》卷二十三,《邵武军置庄田记》)认为佛典中的性命之说,实际上并未超出儒家经典的范畴,“释之行固久,始吾闻之疑,及味其言,有可爱者,盖不出吾《易·系辞》、《乐记》、《中庸》数句间。”(《李觏集》卷二十三,《邵武军置庄田记》)从思想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既然已认识到“修其本”即加强自身理论建设是战胜佛道之学的关键,又已认识到佛道之学在理论上的长处及其吸引人们的原因在其精致的心性理论,甚至还力图把谈论心性的主动权抓到儒家手中,则进而建构儒家的心性之学已是势在必然了。
这样,随着对佛道之学认识的深化,儒家学者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开始了心性理论的探讨。如胡瑗在《论语口义》、《周易口义》中,对性、命及性情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把性归为天生之质,认为如果人性诱于外物,就会流于邪情:“性者,天生之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无不备具,故禀之为正性。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皆由物诱于外,则情见于内,故流之为邪情。”(《周易口义》卷一,《乾》)从中已依稀可见道德心性之学的影子。司马光亦突出“正心”、“治心”的修养论,把它作为学者为学进德的核心内容。他说:“大人之道正其心而已矣,治之养之,以至于精义入神则无违矣。”(《温公易说》卷三,《成》)“学者所以求治心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一,《中和论》)有关具体的“治心”的修养工夫,司马光也有详细的论述:“君子从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危则难安,微则难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执中而已。”(《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一,《中和论》)可以说,在司马光这里,宋代儒家的心性论已初具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初不少学者那里,对心性之学的探讨并非出于完全的自觉。如欧阳修就认为,“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七,《答李翊书二首》),司马光则一方面谈“正心”、“治心”,另一方面却对大谈心性道德的孟子颇为不满,专门作《疑孟》一书相诘问,且在熙宁元年(1068)上《论风俗剳子》,对当时举子好谈性命的学风提出批评:“性者,子贡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举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五,《论风俗剳子》)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然而,正如司马光在《论风俗剳子》中所描述的,到北宋中期,道德性命之学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当时同时并兴、相互鼎峙的荆公新学、苏氏蜀学与理学均以道德性命问题作为其理论思考的重心。
早期荆公新学注重对心性道德问题的探讨。这一特点,从王安石《性情》、《原性》、《性说》、《命解》等一系列杂著中可以看到。在《性情》一文中,王安石指出:“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王文公文集》卷一,《性情》)在这里,王安石从已发、未发角度讨论了性情问题,以体用内外合一的原则说明了性情一而不可分的关系。此外,王安石还探讨了人性问题,提出了“性不可以善恶言”等观点。对荆公新学道德性命之学的特点,历代学者都有较为一致的评论。新学学者蔡卞曾指出,以《淮南杂说》为代表的早期新学使天下士子“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王氏杂说十卷》条)金人赵秉文也以批判的口吻指出,“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赵秉文《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侯外庐先生等亦说:“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③
理学学者也对道德心性之学进行了着力探讨。程颐早年游太学时,便作《颜子所好何学论》,将道德心性之学确立为圣人之道的基本内涵,并以正心养性作为学者为学的方向。他认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文集》卷八,第577页)他批评一些儒家学者致力于为文章、治经术,却忽视了对道德心性之学的探讨,偏离了为学的方向。他明确指出:“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遗书》卷二十五,第319页)所谓“求于内”,指的就是对心性之学的探讨。清人黄百家曾以“穷极性命之根柢,发挥义理之精微”(《宋元学案》卷十六,《伊川学案下》)来评价程颐。事实上,其他理学学者也无不在心性道德之学的探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周敦颐“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周敦颐传》)张载“自立说以明性”(《张载集·经学理窟·义理》),其“气质之性”的理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朱子语类》卷四)。这些已经为历代许多学者所肯定。
苏氏蜀学学者虽然在早期对当时学者大谈心性之学颇为不满,认为“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苏轼文集》卷二十五,《议学校贡举状》)但后来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对性命之说也多有论述。如《东坡易传》就探讨了性情关系,认为性情合一,并无善恶之别:“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其它有关心性道德的探讨,在苏氏著述中也常常可以见到,甚至在蜀学中人自身看来,蜀学的主要成就不是其名闻天下后世的文章议论,而在于其对道德性命之学的探究。苏门弟子秦观曾谓:“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秦观《淮海集》卷三十,《答傅彬老简》)此说反映了蜀学中人对自身学术特点的基本估计。
陈植锷先生认为,以嘉祐之际王安石倡道德性命之学为标志,北宋学术可以分为具有不同特点的两个发展阶段:义理之学阶段与性理之学阶段,前者主要是指在治学方法上偏重于从整体上探究和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乃至整个儒家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与汉唐以来的训诂之学相区别;后者则主要指在内容上以探讨心性问题为核心④。这一划分,是符合北宋思想学术发展实际的。到北宋中期,随着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及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理学的兴起,对心性问题的探讨已成为儒学的重要主题。
二、宋代《四书》学的形成
在儒学理论重心向心性之学转移的过程中,宋代《四书》学得以形成。
对于宋初的儒家学者来说,要建立起与佛道之学抗衡的心性理论,除了对佛道之学进行吸收、融摄之外,无疑还需要对传统儒学自身所固有的心性之学的思想资源进行发掘、利用。汉唐以来,儒家学者所研习的经典主要是《五经》。宋庆历以后,儒家士人亦对《五经》进行了重新阐释、发挥,如胡瑗《洪范口义》、《周易口义》、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欧阳修《诗本义》等皆为阐释、发挥《五经》义理的著作。这些《五经》学著作虽然已有个别如胡瑗《周易口义》表现出探讨人性及性情问题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仍然没有关注心性问题的自觉。
然而,随着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及学风的变化,到北宋中期,儒家士人对《五经》的阐释已经颇为注重对其中心性资源的挖掘与阐发。如王安石就认为,“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虔州学记》)在作《洪范传》时,王安石着重阐发了其中的“性命之理”与“道德之意”,认为“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五,《洪范传》)这些阐释,已经具有以心性之理解经的特点。在《东坡易传》及《伊川易传》中,这一特点也同样体现得相当明显。
然而,通过对《五经》的阐释来建构心性义理之学是存在相当难度的。一方面,《五经》内容繁多、庞杂,涉及面非常之广,且大多文字佶屈聱牙,涵义晦涩难明,一般士人研习起来相当困难;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除《易经》中有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内容较为集中外,其它经典中适宜于从心性角度进行发挥的思想资源并不集中,在阐释中很难以之为基础吸收、融摄佛道之学有关心性的学说,从而凸显心性的主题。对于《五经》的这一特点,许多学者是有所认识的。如程颐说:“诸经之奥,多所难明。”(《文集》卷八,第580页)“《六经》浩渺,乍来难尽晓。”(《遗书》卷二十二,第296页)这些看法,确有其道理。显然,仅仅依靠阐发《五经》是不能满足建构儒家心性之学的现实需要的,在此之外,必须寻找、选择、发现新的思想学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与传统的《五经》相比,这几部著作更为直接地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后学的思想,文字明白晓畅,提纲挈领,对心性问题进行阐述的内容较多且相对集中。其中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已达到一定深度,所提出的许多概念、范畴、命题也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汉唐一些儒者特别是韩愈、李翱对它们进行推崇的影响,北宋中期时已有不少士人对这几部著作进行注解、阐释,并大量运用其中的概念、范畴、命题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宋代《四书》学逐渐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思想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宋代《四书》学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但其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却颇为曲折、复杂。
(一)《论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与《孟子》升格
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论语》从汉代起就取得了较高地位,历代许多士人对《论语》都相当重视,且多有注解之作。因而到宋代,士人们重视《论语》,并不显得突兀。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邢昺依照何晏《论语集解》改定皇侃旧疏,颁于学官。邢《疏》虽然是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刊定而成,但在《论语》学乃至整个学术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四库全书总目》将其视为汉学与宋学的转折点:“今观其书,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四库馆臣认为,虽然它详于章句、训诂、名物而未造精微,但“先有是《疏》,而后讲学诸儒得沿溯以窥其奥,”(《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经部·四书类一·论语正义二十卷》)其功绩不可淹没。
庆历前后,《论语》受到了更多关注。胡瑗作《论语说》,《宋元学案》中即辑有片断数则。到北宋中期及两宋之际,儒家学者注解《论语》的著作大量涌现。王安石有《论语解》十卷,王秀有《论语口义》十卷,吕惠卿有《论语义》十卷,龚原亦有《论语解》;苏轼有《论语解》十卷,苏辙有《论语拾遗》一卷;张载留下了《论语说》,程颐、杨时、谢显道、尹焞、吕大临都有注解《论语》的著作;此外,晁景迂、范祖禹、王令、汪革等也各有《论语》学著作。一时《论语》学呈现出繁盛局面。其中王安石《论语解》“绍圣后亦行于场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下,《王介甫论语解十卷》)影响很大。
《孟子》其人其书的“升格”是宋代思想学术发展过程中引人瞩目的事件。与《论语》不同,《孟子》从汉至唐一直属子书,孟子本人的地位也并不高。因此孟子其人其书在宋初地位的上升,就并非一帆风顺。在宋初儒家士人们推尊孟子、提高《孟子》地位的同时,也有一些士人对孟子其人其书提出了各种批评与辩难。徐洪兴、姚瀛艇先生等曾对唐宋之际“孟子的升格运动”及宋代的非孟思潮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考察,在此主要依据他们的研究,对宋初《孟子》学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
滥觞于中唐的“孟子”升格运动在经历了五代十国乱世的沉寂之后,到宋代又重新兴起。宋初最早推崇孟子的有柳开与孙奭。柳开认为,孟子辟杨墨而挽救圣人之道,是接续圣人之道的重要人物:“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故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柳开《河东集》卷六,《答臧丙第一书》)孙奭则曾在宋真宗大中祥符间受命校勘《孟子》,并撰成《孟子音义》二卷。庆历时,范仲淹、欧阳修等庆历思潮的领袖人物皆推尊孟子。如欧阳修即称“孔子之后,唯孟子最知道。”(《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十六,《与张秀才第二书》)孙复、石介师徒更盛称孟子辟杨墨、息邪说、辅圣道之功,强调孟子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地位。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尊孟”成为当时学者流行的学术取向。到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孟子升格运动达到高潮。王安石、二程、张载等不同学派的学者尽管政治、学术见解不同,但在尊孟这一点上却颇为一致。他们不仅极力抬高孟子的地位,还致力于《孟子》研究。这一时期的《孟子》学著作有:王安石《孟子解》十四卷,王雱《孟子解》十四卷,龚原《孟子解》十四卷,程颐《孟子解》十四卷,张载《孟子解》十四卷,苏辙《孟子解》一卷。不仅如此,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孟子》一书还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条)。宣和年间(1119~1125年),《孟子》一书又首次被刻成石经,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由子入经的历程最终完成。在北宋中后期,王安石、王雱、许允成所解的《孟子》流行于科场,“场屋举子宗之”(《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
与“尊孟”思潮相伴随的,是一些士人删孟、议孟、疑孟、辩孟、黜孟乃至诋孟的思想倾向。北宋初到中期,著名的非孟派人物有李觏与司马光。在《常语》等著述中,李觏从几个方面对孟子进行批判,历数其不续道统、背叛孔子、怀疑《六经》、不尊王之过,并对孟子性善论及义利观表示明确反对。司马光则作《疑孟》十一篇,对孟子进行了指斥与非难,认为孟子虽宣称愿学孔子,但其许多思想观点却并不符合孔子之意,有些甚至是违反君臣之义、人伦之理的;人性兼有善恶,孟子批评告子仅仅是“以辩胜人”,等等。非孟思潮虽然最终未能阻止孟子的升格,但从尊孟与非孟思潮的对立中,我们亦可以了解思想演进与学术发展过程的复杂性⑤。
(二)《大学》、《中庸》的重新认识与选择
与《论语》、《孟子》不同,《大学》、《中庸》在宋代所经历的是一个重新认识、选择的过程。作为《礼记》中的两篇,《大学》、《中庸》本身很早即已属经文的一部分。但二者之所以被从《礼记》中抽取出来,单独成篇,受到特别的重视与关注,则是由于当时人们对其价值的重新认识。在宋代以前,已有韩愈、李翱等学者关注《大学》、《中庸》,且《中庸》还有单独的注解之作。宋代初年,太宗雍熙中进士陈充曾以“中庸子”(《宋史》卷四百四十一,《陈充传》)自号,在其所作的《子思赞》中亦有“忧道失传,乃作《中庸》。力扶坠绪,述圣有功。”(《全宋文》卷一百○一,《子思赞》)这是宋代最早揭橥“中庸”之义者⑥。稍后,僧人智圆亦提倡中庸,自号“中庸子”。到庆历时,《中庸》已为当时士人所重视。范仲淹曾手书《中庸》以授张载,勉励他研读《中庸》,习儒家之学。胡瑗还撰有《中庸义》,讨论性情问题,胡瑗高足徐积曾谓“安定说《中庸》始于情性。”(《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司马光也撰有《中庸广义》。
《四库全书总目》称“《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经部·四书类一》,《大学章句一卷》),但饶宗颐先生称“《大学》篇早已出现于敦煌写经卷中”⑦,则其单独行世应在宋初以前。北宋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仁宗赐进士王拱辰《大学》一轴,这是现有的关于《大学》脱离《礼记》而单独行世的最早记载。对《大学》的独立研究,则最早由于司马光的提倡。司马光曾作《大学广义》及《致知在格物》。朱彝尊《经义考》谓:“取《大学》于《戴记》讲说而专行之,实自温公始。”(《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六,《司马氏大学广义》)司马光的《大学广义》、《中庸广义》二书已佚,无从知其具体内容。但从司马光整个思想体系看,其心性论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对《大学》、《中庸》“诚”、“中和”、“格物致知”等范畴的利用、发挥而进行的。在《致知在格物》一文中,司马光沿着李翱“去情复性”、“物格于外”的思路,将“格物”解为“捍御外物”,认为只要能摒弃物欲,捍御外物侵扰,就能从容把握至道。显然,在司马光这里,《大学》、《中庸》已成为其心性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
此后,对《大学》、《中庸》的阐释、发挥、利用进一步加强。北宋中期诸儒,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理学学者对《大学》、《中庸》非常推崇。二程认为《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外书》卷十一,第411页),《大学》乃“孔子之遗言”(《粹言》卷一,第1204页),“圣人之完书”(《遗书》卷二十四,第311页)。也就是说,《大学》、《中庸》都直接与圣人相联系,圣人之学的精髓、圣人之道的核心就蕴含其中。张载也说:“《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张载集·经学理窟·义理》)他还以其切身体会指出《四书》是为学进德的根本,涵泳其中,反复玩味,则能不断促人长进:“《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无不自此始,然后定止,于此发源立本。”(《张子语录·语录下》)“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张载集·经学理窟·义理》)
他们还对其思想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的阐释、发挥活动,使《大学》、《中庸》成为其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如周敦颐通过《易传》与《中庸》思想资料的沟通与互训,以“诚”范畴为中心环节沟通了天人,确立了其本体理论。源自《中庸》的“诚”也因此成为周敦颐之学的本质内容。明初学者薛瑄说:“《通书》一诚字括尽。”(《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上)黄宗羲亦谓:“周子之学,以诚为本。”(《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周敦颐还对《中庸》“中”、“和”等范畴进行了发挥与改造。其主要著作《通书》中的许多内容,都与《中庸》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明末学者刘宗周甚至认为,《通书》实际上就是对《中庸》的阐发与理论提升:“《通书》一编,将《中庸》道理,又翻新谱,直是勺水不漏。”(《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上)
二程对《大学》、《中庸》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发挥、利用,使之成为理学中的重要经典。他们对《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进行了训释,认为“格物”即“穷至事物之理”,赋予“格物”以“穷理”的意蕴,借此提出了其理学思想中重要的格物致知论。二程还以“理”解《中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八,第100页)“《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遗书》卷十四,第140页)他们对《中庸》的不少训解、论断,奠定了此后众多理学家训解《中庸》的基调。
张载融合了《易传》与《中庸》的思想资料,以《易传》释《中庸》,又以《中庸》释《易传》,使《易传》中“穷理尽性”及《中庸》中有关“明”、“诚”的思想得以沟通并在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上得以大大拓展,最终建构起其“因明而至诚,因诚而至明”的道德修养论。《宋史》张载传称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张载传》)
这样,从宋初到北宋中期,随着《论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孟子》的升格以及对《大学》、《中庸》的重新认识与选择,《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已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各派思想家在建构其理论体系时,都曾对这一学术资源进行了挖掘、利用。不同思想倾向的儒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所进行的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注释:
① 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第385页,第76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关于《四书》之名的确立,有不同说法。邱汉生先生认为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刻了《四书》,为之作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参见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第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② 有关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发展,见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第147—15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③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42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④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218—2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⑤ 参见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第92—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姚瀛艇《宋儒关于〈孟子〉的争议》一文,载于《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⑥ 参见饶宗颐:《宋学的渊源—后周复古与宋初学术》,载《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⑦ 同上。
标签: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四书论文; 四库全书总目论文; 孟子论文;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论文; 孔子论文; 宋元学案论文; 论语论文; 王安石论文; 经义考论文; 宋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