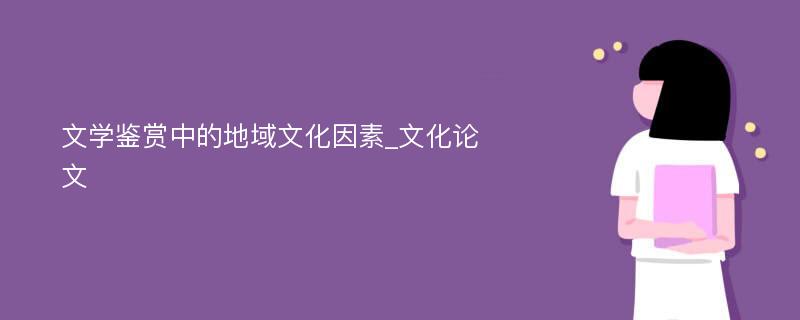
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论文,因素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域文化因素是影响文学鉴赏的外部诸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大体通过三个相关的方面反映出来:一是通过作为鉴赏对象的作品,二是通过作为鉴赏主体的读者,三是通过具体的鉴赏环境。作品、读者、环境,这是任何一个具体的鉴赏过程得以进行的必备条件,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鉴赏过程中,来自这三个不同方面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具体差异,可能是相当大的;即使处于同一个鉴赏过程之中,这三个方面所携带的或展现的地域文化因素也不可能完全一样。随着鉴赏过程的推移,这些来自三个方面的地域文化因素的信息,在以读者为中心、为主导的情况下,相互交流、渗透、震荡、会合,最终,以读者获得特殊的审美满足而使相关的鉴赏过程走向完成。
文学作品携带的地域文化信息
地域文化因素之所以会影响文学鉴赏活动,首先是由于作为鉴赏对象的文学作品所携带的或强或弱的地域文化信息。这方面的信息越强,则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就越浓郁,越鲜明,而它对鉴赏过程的影响也就越大。
由作品带进鉴赏过程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是作为一种可供鉴赏的内容、特色,乃至风格,而发挥作用的。它的被觉察,被辨识,被把握,是在读者的具体鉴赏实践中实现的。然而,多数读者对此都不十分自觉。倒是少数文学研究家、批评家,因为具有行家的眼光,具有较一般读者敏锐得多的文化分辨力和艺术洞察力,往往能够较快、较准确地捕捉到这方面的信息,并给以条分缕析的说明。他们的判断往往会影响广大的读者群,甚至影响久远。比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说过“徐干时有齐气”的话。“齐气”,概括的是一种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格。李善注解释说:“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干亦有斯累。”尽管此后在“齐气”的释义以及到底是“齐”还是“逸”的辨字上,很有一些争议与分歧,但多数论者还是接受了曹丕的概括和李善的注解。
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格,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描写对象;一是来自作家。从描写对象来说,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俗、方言、文化传统等。比如环境,在美学家泰纳那里是被当作与种族、时代并列的文学三要素之一来看待的。他认为环绕人的自然环境,乃至气候,都会对人产生影响。他是这样分析自然环境对阿利安人的影响的:“虽然我们只能模糊地追溯,阿利安人如何从他们共同的故乡到达他们最终分别定居的地方,但是我们却能断言,以日耳曼民族为一方面和以希腊民族与拉丁民族为一方面,二者之间所显出的深刻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有的住在寒冷潮湿的地带,深入崎岖卑湿的森林或濒临惊涛骇浪的海岸,为忧郁或过激的感觉所缠绕,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喜欢战斗流血的生活;其他的却住在可爱的风景区,站在光明愉快的海岸上,向往于航海或商业,并没有强大的胃欲,一开始就倾向于社会的事物,固定的国家组织,以及属于感情的气质方面的发展雄辩术、鉴赏力、科学发明、文学艺术等。”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点是在泰纳看来,自然的地域环境是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后影响文学艺术的;另一点是他明确提出了自然地域环境对鉴赏力的影响,而这正好直接关乎鉴赏主体文化心理的形成。
有人认为泰纳所讲的环境,只是自然环境,不包括其他社会文化因素。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他在分析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后,紧接着就谈到国家政策、军事干涉、教皇地位、城邦政权稳固等的影响,只不过理论的归纳不十分明晰罢了。
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小说中,它们主要起一种情调、氛围的烘托作用,让鉴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似真的审美效应。比如在鲁迅的小说里,《药》的开头华老栓出场时对于秋天的后半夜的描写,夏母上坟时对于柳树和乌鸦的描写,《故乡》中对于海滨月圆之夜、沙滩、瓜田的描写,《风波》起首对于夏日黄昏临河土场上的乌桕树和花脚蚊子的描写等,都属于自然景观。而《孔乙己》中对于包括咸亨酒店在内的鲁镇酒店格局的描写,《阿Q正传》里对于土谷祠的描写,《社戏》里对于水乡人坐在船上看戏的情景的描写等,又都属于人文景观。在鲁迅笔下,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因而能够把鉴赏者很容易地带进绍兴一带城镇、乡村的文化氛围中去。
在某些带有叙述性的诗歌作品中,也有类似于小说的情况。以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例,在最后部分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从去年辞帝京,
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
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
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
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
往往举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
呕哑嘲哳难为听。
这里住地的潮湿低洼,绕宅而生的黄芦苦竹,啼血的杜鹃,哀鸣的孤猿,春江花朝,秋江月夜等,都是自然景观,而粗犷得难以入耳的山歌村笛,以及终年听不到高雅音乐的荒僻与偏远等,则属于人文景观。两种景观相补充,适足以渲染出白居易谪贬地的地方特色和诗中所要营造的凄苦情调,这就为收尾处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做了最好的铺垫。
从鉴赏的角度看,地域文化特色的传达,环境描写与烘托固然不可或缺,但它在作品中毕竟是较为外在的东西,而真正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人物,在抒情性作品中则是抒情主人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的祖先常爱讲“钟灵毓秀”,这里的“钟”和“毓”都作聚集、聚拢讲,一方土地的山川灵秀之气丛聚于人,逐渐形成这一地域人群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文化性格。如“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等。至于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则更是直接以地域特点论定三秦故地的民风民气和性格特点的。文学作品只要写好了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人物性格,其他的地域文化因素如方言、风俗,乃至生活方式、想事方式、情感方式等等,都能够带起来。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地域文化色彩很浓的名著,作者对于他笔下的那些顿涅茨草原上的自然风物固然写得非常传神,使鉴赏者常常能够产生一种恍如置身其间的幻觉:冬日肆虐的暴风雪,春来冰泮雪融的春潮、泛浆的路面、耕地上蒸腾的水气,夏日暴风雨将至时,你甚至不难嗅出青草味和土腥味夹杂着的那种特殊气息。然而,最重要的却是肖洛霍夫写活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以麦列霍夫家族为主的那些顿河哥萨克的特殊命运和性格。这类人物,即使在俄国,也属相当特殊的群体。由于作家惟妙惟肖地写出了人物的文化心理、肖像、动作,以及从这些生动逼真的心理、肖像、动作中所传达出的深厚的地域文化传统,还有他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等,所以顿河草原浓郁的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也就几乎可以触摸得到。作家写得细致,读者看得投入,以致多年以后,闭上眼睛,不少人物和场景仍能从记忆的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这种情况当然不独《静静的顿河》才有,许多地域文化特点较浓的名作,在鉴赏者那里都会产生类似的效应。
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
然而,进入读者鉴赏视野的文学作品,毕竟都是由作家创造出来的,因此体现于其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以及其他因素,都无不是经过作家体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没有作家前创作的经验和通过创作在心灵中完成对这些经验的审美转化与升华,作品就不可能携带任何有关地域文化的信息供读者去欣赏。因此,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以及他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感受力等,就成为最关键的了。
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首先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长地,来自他的故乡、故园。那里的自然风物,乡俗人情,历史遗迹、文化传统等,从他刚刚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开始,便感染他,熏陶他,日积月累,遂形成他最初的、也是基本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表现为乡土依恋,表现为悠悠的乡情、乡思,它甚至可以伴人终生。柳宗元的“海上尖峰若剑芒,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传达的就是这种意绪。人们非常熟悉的李白的《静夜思》,更是如此。在现代小说创作中,鲁迅的《故乡》则对此表现得尤其深致感人。这可以称之为故乡情结,或乡土情结。它构成作家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的核心与基础。
正因为如此,大凡地域文化特色写得深致感人的作家,很少不是写故乡或从写故乡起步的。《楚辞》的地域文化色彩是很浓很浓的,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楚文化的重要资料,屈赋中那种生死不渝的执著与纠缠,那种烈火一样燃烧着向读者奔扑而来的情思,固然与诗人追求“美政”的理想,追求人格的完美有关,但无论是早年《桔颂》里“深固难徙,更一志兮”的坚定,还是后来《离骚》里“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难割难舍,都有诗人更深挚的乡土之思、之恋、之爱在。屈原终其一生都在为他的故园、故国而歌。这一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以现代作家而论,鲁迅自不必说,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取材于故乡的,其地域文化特色因乡土情结的作用而给鉴赏者留下极深的印象。鲁迅非常肯定的肖红和肖军,他们的名作《呼兰河传》和《八月的乡村》,其东北黑土地的文化特征是相当鲜明的,它们均取材于作者的故乡。此外,如老舍的写北京,沈从文的写湘西,沙汀的写四川等,都是在写着自己的故园,写着他们非常熟悉的那里的人和事。而在当代作家中,孙犁的写白洋淀、写冀中,赵树理的写晋中,陆文夫、范小青的写苏州,刘绍棠的写北运河,莫言、张炜、尤凤伟的写胶东,周大新的写豫西南等,在地域文化特色的表现上,也都各有招数,各见特色。他们都因为写了自己的故乡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以其笔下色调不同的地域文化风采而见重于当代广大读者。
简析陕西作家地域文化心理的细微差异
从全国地缘文化的分野来看,陕西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都具有秦文化的风貌,按其地域特色都可以划归秦文化圈。但细加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细微的差异。柳青的故乡在陕北,他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写的也是这里的生活,虽然未必着意于要表现乡土特色,但因其比较严格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故作品的地域文化信息还是不难被鉴赏者捕捉到的。到了写《创业史》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基地建立在长安县的皇甫村。虽说此地仍在陕西,但却属三秦故地的中心,与接近塞上的陕北相去颇远了。《创业史》升华了他在关中农村多年深入生活的体验,从外部环境的描绘,到人物内在性格的把握,到相关的社会风习的反映,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关中地域文化的风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的语言,除仍保留了柳青原来的部分风格特色外,又大量地提炼并吸收了长安一带的地方方言,最终形成了柳青自己的以厚重为特色的文学语言系统。这种语言对后来的路遥和陈忠实都有颇大的影响。所不同者在于,路遥更多地向陕北方言倾斜,而陈忠实则更多地向关中方言倾斜。
陈忠实是关中人,他的颇得好评的《白鹿原》在探索地域文化传统的表现上,无论与柳青比,还是与路遥比,都要自觉得多,甚至不妨说,这是他在这部作品中的一项重要的美学追求。白鹿原,又称霸陵原,雄踞于关中腹部,横亘于灞水与终南山之间,原体高平而谷岸耸立,显得浑厚而见气势,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但在陈忠实的笔下,它并非单纯的自然物象,而更多是一种文化的和历史的象征。陈忠实像他所描写的那些人物一样,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当他把自己半个世纪的人生体验对象化到白鹿原的巨大象征之中的时候,他也同时带进了对这一块土地的爱,带进了悠悠的乡心和乡情。他的语言比柳青更见三秦腹地地域文化的神髓与气韵,而整部作品也更多些历史的蕴积,独特的思索。特别是那位朱先生,通晓关学,道德学问俱佳,立身行事多古风,过世之后,精魂化作白灵,于雪后晴日的红妆素裹中,横空而过,飘然远逝。然而那形象,那气韵,却长留在鉴赏者的心里。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他的地域文化理想、人生理想和道德理想,有关这些理想的价值的评估,自然不妨见仁见智,比如我就认为很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但是朱先生之作为白鹿原及其所负载的历史文化的人格化的表现,则是确定无疑的。
贾平凹的家乡在商洛,他也是从写自己的故乡,写那里山川风物、人情世态而步入文坛,确立风格,赢得才名的。在地域文化特色上,他的作品不仅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高手们,而且也与秦地的比如路遥、陈忠实,包括老一辈的柳青、王汶石等互见差异,尽管同属秦文化系统。在文学史上,他应该算是第一个全面地向世人展示了商州故地之美的作家,也是那一块土地上迄今为止哺育出来的最重要的文人。商州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南、北方的结合部,交会部,战国时期是秦楚交兵之地,其东界,秦强则属秦,楚强则归楚,拉锯、易手,屡见不鲜。秦孝公时改革家卫鞅的封地就在这一带;秦楚交恶,楚师败绩,其所丢失的商於之地六百里,也在这一带。贾平凹作品中透出的某些南国气韵,如秀逸、柔婉、空灵等,其地缘文化上的根源,很可能与商洛故地的这种虽秦而近楚的传统地位有关。
读者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
作品中形态各异,浓淡不同的地域文化因素,都是作家把自己的体验自觉不自觉地注入的结果。读者在鉴赏活动中通过阅读接触到这些因素,进行欣赏和玩味,以实现其与作家的交流。然而,进入鉴赏过程的读者的心灵并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空无一物的单纯容器,故鉴赏过程决不是消极的容受,而是在相互的交流中进行选择,彼此发生影响。一方面是作家对象化在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被辨识、被评价,另一方面读者也就同时在拓展着自己地域文化知识的视野,当然还会获得鉴赏的快感。
进入鉴赏过程的读者,也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和地域文化知识积累。这种素质和积累,是他理解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出发点和参照系。读者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与作家并无大的区别,也首先是由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熏陶出来的。作为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乡情乡思,有对故园的依恋,有摆不脱、驱不走的故乡情结。由故土的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传统而来的这种素质和情结,是每一个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对于具体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采取何种态度的根据,也是他进行比较与选择的尺度。当然,也还要看他在进入鉴赏过程之前有关地域文化知识的积累丰厚到何种程度等等。
一般来说,作家赋予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越鲜明、越动情,就越能够吸引读者。读者被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所吸引,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读者在作品中看到了与自己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相近,或在某些重要点上相通的东西,这时往往会唤起他的有关记忆,可能是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也可能是早已淡去了的某个场景,某段意绪;另一种情况是作品中与地域文化因素交融在一起的作家的乡情,深深地感动了读者,勾起了读者不尽的乡思,这是一种乡心的共鸣,一种乡愁的慰藉,一种人情的泄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对于读者来说,是异质的、陌生的,然而却写得很成功、很见特色,这时吸引读者的就是作家营造出来的异域情调,使读者的猎奇心理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有助于他的地域文化知识的积累。
不能忽视鉴赏时的外部地域环境
在具体的鉴赏活动中,读者所处的特定地域文化环境对其鉴赏的进程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必须予以注意的。比如读者恰好是在远离乡关的地方,并且处于如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所说的那种“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境况之下,阅读一部带有浓厚的家乡地域文化色彩的作品,他就会感到异常亲切、异常温馨。相反,如果这位读者不是身在异乡,没有羁旅之感,读同样的作品,那效果则会相当不同。
命运无常驻,人生无定所。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生存的地域文化环境的变迁,是经常发生的。由于命运的播迁和生存地域的变换,人们的文化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就是说会在原本形成于故土故园的文化心理素质中注进新的因素。对于作家来说,这种随迁徙而来的地域文化心理的变化,自然会在创作中反映出来。庾信曾有从南朝到北朝的命运播迁和仕宦经历,其间外部地域文化环境的变动是很大的。这给他的心理与创作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杜甫评价他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显然考虑到了庾信文章自南而北之后的变化。庾信早年身居被后人以“六朝金粉”形容的建康,出入宫禁,诗文轻纤绮艳;中经变故,滞留北朝,又做了鲜卑人的官。屈身两朝,名节有亏,心中是异常痛苦的,加上北国地域文化的熏染,遂使他的诗文风格之中很增加了些沉郁苍劲的气韵。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里是从两个方面谈及庾信的:一方面说由于他和江总“身旅北方”,在他们的影响下,“南方轻绮之文,渐为北人所崇尚”;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了身仕北朝之后庾信诗文风格的趋于深沉,所以又说:“子山(按:庾信字子山)继作,掩抑沉怨,出以哀艳之词,由曹植而上师宋玉,此又南文之一派也。”在这里,刘师培“掩抑沉怨,出以哀艳之词”的评价,主要是指庾信晚年在北方的作品,应该说是准确的。掩抑沉怨,已非南音,而哀艳之词,遗响犹存。故刘师培虽说仍把庾信晚年的作品归之于“南文”,却又别为一派,这也是不错的。
杜甫是很欣赏庾信的,入川以后的诗作受其影响较深。如果我们把杜甫作为鉴赏者,把庾信晚年的诗赋作为鉴赏对象,来进行分析,则不难看出由于外部地域文化环境的变换而对鉴赏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杜甫名作《咏怀古迹五首》的第一首,可以说是用诗体形式形象地记录了他对庾信晚年诗赋的鉴赏体验:
支离东北风尘际,
飘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
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
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
暮年诗赋动江关。
清人沈德潜对这首诗的分析是:“此章以庾信自况,非专咏庾也。五、六语已与庾信双关。以上少陵自叙。”诗的首联是说,杜甫自己从因安史之乱而风尘滚滚的北中国的地域空间,携家小飘泊到地处西南的蜀中。颔联的三峡楼台,五溪衣服,还有云山等,俱为蜀中风物。此联与首联一起,非常具体地勾勒出了播迁中杜甫所处的特定鉴赏地域文化环境。颈联沈德潜说是双关,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杜甫在鉴赏庾信的诗赋时找到了二人命运的某些契合点、相通处,比如同是不尽的飘泊和淹留,都有深沉的乡思和乡愁等。尾联看似评庾信,实际上杜甫也把自己对象化到他所鉴赏的客体中去了。
地域文化环境影响的复杂性
庾信和杜甫都是在中年以后出现了生存的地域文化环境的远距离转移。转移之前,他们各自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均已基本定型,因而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对于新的地域环境的不能完全认同,这就更加强化了他们对于故国故园的思念。他们谁也不会“错认他乡作故乡”,“错把杭州作汴州”。但如果是从小离开故乡,而且不是因为如庾信和杜甫所遭逢的那样的战乱,则情况又会大为不同。以当代小说家刘心武为例,他的故乡在四川,但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迁居北京,其地域空间转移的距离,远大于庾、杜。后来北京地域文化环境对他的熏陶,也远大于他的家乡四川,可以说他的地域文化心理的形成主要是在北京。他的小说创作,无论从题材上看,还是从人物性格的创造上看,抑或是从总体的气韵上看,都透着京味儿。如果按地域文化来进行划分,则只能把他划归当代的京派作家群,而不能划归川派作家群。对他来说,第二故乡才是真正的故乡。
笔者本系秦人,自弱冠初度之年负笈京华,屈指算来盖四十年矣。称北京为第二故乡,应该说不算过分。然而至今仍有客居之感,总觉“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并且常有一抹淡淡的乡愁袭上心头。这就与刘心武在地域文化归属上的“反客为主”,“假故乡作真故乡”颇不相同。倒是很像贾平凹从商州老家来到西安,至今无法完全认同都会生活,即使化身为《废都》里的哲学家“牛”,做梦也往终南山里跑。笔者读刘心武的作品,觉得在地域文化的渊源上,他距老舍远比距沙汀近得多。而无论是读他的作品,还是读老舍的作品,笔者都颇为欣赏其中地道的京味儿,并常常为之击节,然而却从来没有产生过如读柳青、读陈忠实时的那种“君自故乡来”的体验。这也足以说明,地域文化环境对创作主体和鉴赏主体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
地域文化的研究,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而从地域文化出发的文学研究,也是“其来尚矣”,但近几十年有断裂。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文化热的出现,也由于研究角度从单一的阶级斗争模式和泛政治模式下的解脱,地域文化与文学活动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研究工作也开始向这个方向拓展,并且伴以作家的比较自觉的实践。其中,由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丛书》,在这方面是一项值得注意的开拓性学术工程,目前已出专著十种,虽以撰写者功力不齐而稍见参差,但颇能开人眼界。笔者受到启发,选了鉴赏的角度,把往日一些零碎的想法稍加梳理,谈了以上的意见,不当之处,恳望专家和读者指迷。
标签: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鉴赏论文; 艺术论文; 环境描写论文; 庾信论文; 读书论文; 杜甫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