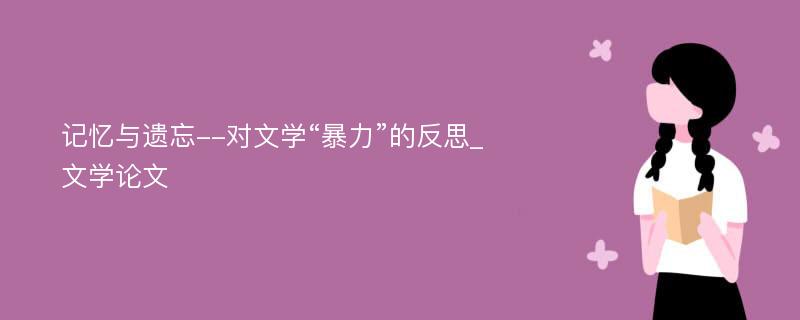
记忆与遗忘——对文学中的“暴力”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暴力论文,记忆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功利主义的写作立场: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营造形象化的历史图景
罗岗: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重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小说中的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熟悉《金光大道》的人都知道,它描写的是芳草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在小说正文之前,有一段长长的“引子”,是从1932年开始写起的。这段“引子”的用意,除了按照一般成长小说的模式,叙述主人公高大泉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更重要的是起到了缝合“历史”的作用。从“红军到了陕北”到“小轮车推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引子”几乎囊括了一部30年代以后的中国革命史,并且巧妙地将重大历史事件转述为具体的生活图景。这种叙述方式不仅为人物性格的发展注入了“革命”的因子,而且为现实的变动提供了充足的历史依据。两者的结合恰恰显露出当代中国文学想象“革命”的基本方式,即通常所谓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
事实上,建国后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始终应和着主导意识形态的询唤,与历史科学提供的理性交相运作,成功地构建了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历史意识相辅相成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理性的,观念化的历史意识和感性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共同作为权威历史话语,完满地解释了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得出了合乎主导意识形态的历史结论,从而构筑出一道完满整齐的权威历史话语链。离开了权威历史话语的阐释,我们得不出关于这段历史的其它结论。
摩罗: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实际上就是“战争文学”,所以写这一段历史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把注意力投到了枪杆子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正如你所说,这种战争文学,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提供解释性的感性图景,这就意味着它一开始就突出观念的立场。这就决定了它往往只能按照观念的制约对战争作处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战争的最基本认识是把它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并判定正义战争是革命的神圣的善的从而是红色暴力,非正义战争是反动的残酷的恶的从而是白色暴力。
刚刚过去的时代没有给文学创作留下多少可以施展手脚的空间,更不可能给直接为一代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提供形象论证的战争文学留下什么空间,所以,作家们往往不写战争对日常生活、对文化、对生命的摧毁,或者只是出于写作技术的需要,安排白军火烧民宅、强奸妇女,由此过渡到红军对白军的正义而又辉煌的打击、惩罚和消灭。——这里不能用“屠杀”或“杀戮”,而只能用“打击”、“惩罚”、“消灭”,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战争的诗意正是从这打击、惩罚、消灭中生长起来。至于对战争的人文反思、人道批判、人性悲悯,则完全找不到。
历史记忆的错位:暴力因涂上红色而神圣化,被遗忘的是对人、人性、生命和死亡的关怀
罗岗:任何对往事的关注都与对现实环境的认知紧紧相连,而对历史经验的诠释,也必然要受到当时价值观的笼罩。当代中国文学对“革命”形象的建构,正是为了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它直面看历史进程中的现实,同时又巧妙地绕过了历史与现实本身。这类作品往往具有激昂的基调、质朴的风格和鲜明的思想性,基本主题是歌颂革命战士的豪迈气概和英雄人们的无私品质。它们常常把革命年代中最能考验人意志的时刻当作衬托背景,把塑造革命者的英雄精神品格作为艺术功利目的,通过英雄史话的构筑来激发人们的斗争意志。在五、六十年代大批制作的过程中,这类作品已经建立了情节演进的基本模式,人物形象的固定特征,即已经具有了可资遵循的创作轨迹。模式化创作的目的在于塑造人民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记忆,启发他们对当代现实的线性理解。这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想象“革命”的起点,成为了革命历史题材本身参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缺席”的在场者。
摩罗:历史只是我们按照线性时间观念对过去时态的人文事件的总和的一种称呼,实际上历史并不意味着过时或消逝,它永远与所谓现在构成共时性存在,并且与现在一起,决定着未来的走向和面貌。然而,与现在构成共时性存在的,不是历史的全部,主要是为我们所记忆(包括潜意识中的记忆)的那一部分。我们根据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记忆方式,不但可以推断出这个民族当下的价值眼光和人文状态,而且可以推断出它的未来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应该特别关注对民族历史的记忆问题。鲁迅在思想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完全改变了对五千年中国史的描述方式和记忆方式,这么伟大的工作竟是用“吃人”两字完成的。这个判断使得历史的性质和意义有了全新的呈现,而且暗含了中国应该努力走向一个“不吃人”的未来的指示。可以说鲁迅是仅用“吃人”两字就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方向和历史方向的人。
有点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战争文学对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战争的记忆说明了什么吧。战争的本质是暴力。它是人类的征服欲暴力欲反抗欲在无可疏导和转移的压抑中的爆发性喷放。战争的基本形式是杀戮。在战争中,人们的暴力欲转换成胜利欲,而胜利的唯一保证是将敌军和支持同情敌军的人悉数消灭。当胜利成了战争的直接目的和最高目的,别的一切都成了手段和工具。两军相遇时,首先要取消对方的人性因素,把他们看作非精神的存在,这样才能无比勇敢地冲锋陷阵。战争对于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性的否定,是如此残酷如此彻底。它是人类苦难中最深重的苦难。它是全面地破坏人类的人文存在的一种反人文的人文现象。它给人类造成的精神创伤构成人类最惨重的记忆。
罗岗: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历史基本上是由一系列的战争构成的。但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战争文学中,对一部分杀戮与死亡的文学描写,不是为了激发人们对血腥暴力的恐惧,也不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生命毁灭的震惊。死亡经过阶级意识的再定义之后,成为了充满道德色彩的牺牲或惩罚。一方面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悲壮英勇,正如由《红岩》改编的电影所显示的:在烈火中永生,生和死的关系在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中得到确认;另一方面是“阶级仇、民族恨”喷出的怒火,战争成了末日审判式的仪式,敌酋往往在最后的垂死挣扎中被击毙,这种行为超出了战场厮杀的意义,而更像一场正义的宣判。五十年代初,文艺界开展了对小说《关连长》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批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从根本上规范了文学对“革命”与“战争”的想象方式和表述途径。
“文革”结束后,权威历史话语得到修正。有一批作家就依据修正了的权威历史话语重塑历史。譬如黎汝清,写了《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等以党史、军史上重大事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依然把为权威历史话语营造感性化的历史图影奉为写作的最高法则。而另一些作家,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的冲击,使他们获得了对历史的个人性的新认识和新体验,他们要将这种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体验写入作品中,就不可能再沿用旧的想象方式和表述方式,而必须找到新方式来重新想象和表述历史。“重新”想象和表述的过程当然包含用新的认识和体验对权威历史话语的质疑,以及对新的历史话语的确认,更重要的是,重新“想象”和“表述”意味着用新的文学话语重构历史价值和审美秩序。
摩罗:记忆的对面是遗忘,描述的对面是遮蔽。我们既然记忆了暴力的诗意,当然就遗忘了战争对人的摧残和凌辱,遗忘了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
就这样,通过革命英雄主义的文学描述,把暴力倾向凸突出来,让它的神圣性和功用性同时烙进民族的记忆深处。与此相关的另一面是,暴力所加给人们的人格凌辱和精神创伤却被遗忘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也被遗忘了。漫长的战争对于民族的生机和国民的精神的影响渐渐侵入到文化领域。
暴力主义的深渊:暴力刺激与暴力反应的循环
罗岗: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专门讨论过“法国革命式写作”。这种写作的特点是语言运动与鲜血横流直接联系,以戏剧夸张的形式说明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流血代价,从而使写作成为革命传统的实体,使人们震慑并强制推行公民的“流血祭礼”。他说:“法国的革命式写作永远以流血的权利或道德辩护为基础。”中国的革命式写作与法国的革命式写作尽管有许多差异,但流血的冲动与道德的寄寓同样潜藏在文本的深处。莫言的《红高粱》写的是土匪抗日的故事,当年很多人赞扬它蕴含着质朴的乡民在倭寇侵凌下所凝聚而生的威武不屈的民族尊严,由乡土之爱中升腾的抗暴精神。说莫言将文学创作的生命原则推向极致,让原始生命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高扬。今天看来,这都是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莫言小说的“暴力”倾向,特别是他的《红高粱》系列,不仅将性、革命、暴力和生命力不加择别地在故事层面纠结在一起,而且由此成就了一种所谓“爆炸”式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形态,其实是多年来的“革命”记忆的变态释放。这一点在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影片的结尾,“我爷爷”在大仰拍镜头中,一身泥泞,遍体夕阳,如同一尊铁铸的雕像。在一次象喻性的曰蚀之后,只有血红、近于黑色的高粱在狂舞。细心的观众或许会想起二、三十年前,同样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是《红日》,或是《烈火中永生》,同样是阳光照耀下的战争场景,同样是钢浇铁铸般的英雄雕像,可是,烫人的红色却有了迥然不同的意义。
摩罗:莫言的暴力描写,曾使我震惊。一个作家能让读者产生生命的震惊,这应该说是一种成功。可当我从中国作家的文字里读出了一种普遍的暴力描写瘾时,我的震惊中的审美意识就立即消失,而变成了文化发现式的震惊。有趣的是,促使我反思这一点的是一部古代小说。去年暑假,我为了辅导侄子们读《水浒传》,随手翻弄过几次。有一次翻到了武松在什么楼杀仇人。武松不但杀了仇人,还把在场的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地杀了,一个也不放过。又一次翻到法场劫宋江那场戏。李逵在杀败官军后,沿着浔阳城(今九江市)临长江的街道逃跑,他抡着板斧一路逃一路杀,见一个杀一个,那么一种沉溺其中乐而不返的陶醉相。最可奇怪的是作者。作者描述这些时,表现出比武松和李逵更加入迷的精神状态。他那份发泄,那份如痴如醉的享受感,那种“天人合一”的自我消融感,给了我强烈刺激,叫我无法忘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为什么竟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呢?这或许构成了一脉相承的精神链。他们的心理结构暴露了中国文化的某种秘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有极其冷酷无情,极乏人文气息的一面。无论是就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而言,还是就日常生活形态而言,内中深藏着对于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于人性的敌意。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普遍的暴力倾向,就在这种敌意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最后与这种敌意形成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恶性循环。我们跳开这种力不从心的文化分析,把注意力投到经验生活中来,可以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例如我们到图书馆去借一次书,或者到医院去看一次病,在这么简单的两件日常活动中,也许就会遇上十次粗鲁无礼、问而不答、冷脸、怒目、喝斥、谩骂等等各种各样的刺激,每一次这样的充满暴力色彩的刺激都会在受辱者内心种下一颗暴力的种子,我们的生活又十分缺乏发泄郁愤抚慰创伤的机制,只能任这暴力的种子在人们的心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悄悄积蓄。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这种暴力积蓄就以爆发的方式喷涌而出,造成巨大的毁灭和灾害。作家们在写作过程中无可遏止地表现出的暴力倾向,既可看作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也可以看作是对暴力刺激所作的心理反应——只不过按照作家的固有方式,他们是用文字而不是用枪炮来实现这种反应。说到这里,我已经消解了刚才对暴力倾向的批评,我对中国作家的发泄欲达到了完全的理解和同情,因为造就中国作家的这种文化,也以同样的方式造就着我。谁能抗拒得了文化的塑造和现实的刺激呢?
人文主义的超越:超越暴力压迫与暴力反抗的轮回,超越暴力刺激与暴力反应的循环
罗岗:在我的印象中,将革命“暴力”以苦难的形式彻底呈示出来的,是张炜的《古船》。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开始读《古船》时,觉得作者如一匹受伤的狼在低低嗥叫,同时有一种血色的浓稠液体向你涌来。由此可以想见“暴力”场景的触目惊心。抱朴沉湎于对后母之死的惨痛记忆中,同时不断地忏悔:我是老隋家有罪的人,正体现出张炜内心的惶惑。一方面是个体的毁灭,轮回的苦难,循环的仇恨,集聚着让人把握不定的宿命感;另一方面又分明昭示着历史演进的艰难,个体的悲剧正是历史前进必将付出的代价。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无法控制住文本中的“暴力”,反而可能使它泛滥成灾。细读《古船》,不难发现行文中语句的凝滞,段落间象征的混乱,以及通篇的神秘晦暗,这些似乎都暗示着作者由书写“暴力”情不自禁地滑向“暴力”书写,他好像在这里难于自拔了。
摩罗:要从这种暴力书写中搌拔起来,需要非同一般的精神力量。中国社会暴力压迫与暴力反抗构成的历史轮回,使我们要么处于压迫者的征服快感和对复仇者的恐惧中,要么处于反抗者的战斗激情和复仇快感中,反抗者与压迫者在精神意识上的同构决定了我们难于实现对暴力的批判与超越。如果像文革中那样一种暴力仅仅因为被命名为“红色”就获得了合法性,那么它的血腥和惨无人道必定也要同时获得合法性,这就只能走上压迫者的老路,造成轮流做庄的轮回格局,而没有任何进步可言。作家以什么姿态面对这样的文化现实,几乎成了一种考验。
罗岗:“暴力”以及由“暴力”造成的精神创伤,是当代中国作家极为惨痛的记忆,同时又是最可宝贵的经验。如何在文学中整合经验、重启记忆、治愈创伤、祛除暴力,至今仍然悬而未决。譬如余华,他的小说一开始便着迷于死亡,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唯一可以确认的被叙事件就是死亡与关于死亡的记忆。不需要在此复述他那些在劫难逃、令人发指的死亡描写,光看他在《一九八六》中重现似乎早已沉没、不复可考的古刑罚,他的叙述充满着令人毛骨耸然的身体性语词,似乎在能指的弥散与碎裂中传递着肉碎骨裂的语音形象,就可以想象余华是如何借重于“暴力”经验的。可惜在晚近的创作中,余华用轻飘飘的“活着”将自己从无边的“黑色暴力”中拯救出来。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或许可以借此卸下心灵的重荷,但他却要付出丧失作品份量的代价。与此相反,让我想到诗人穆旦,二十三岁时他便在败走野人山的战役中,亲身感受到死亡的滋味。可他只说过自己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骷髅,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王佐良说穆旦的叙述“没有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战争与死亡的阴影反而使穆旦体验到“丰富的痛苦”,不是简单地拒斥,或是一味地逃避,而是钻得更深,看得更远,身体的毁灭变成了心灵的死亡:“然而这不值得挂念,我知道/一个更紧的死亡追在后头,/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 /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吞蚀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 ”战争所带来的“暴力”,不会因诗人的歌咏而消失,但我希望,人们面对暴力的时候,能像诗人那样从容咏吟:“对着漆黑的枪口,你们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摩罗:余华的变化令人遗憾。在目前引人注目的小说家中,他是对暴力最为敏感的一人,而且他的暴力描写中能见出一点人文气息。看他目前的变化好像有点坚持不下去。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外国同行,从那里多吸取一些滋养。雨果《九三年》是写政治暴力的,可他始终伴有对暴力的思考,我把这称为知识分子立场。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是写战争暴力的,可作者的着眼点是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是生命对于战争的恐惧和控诉,我把这称为艺术家的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是写谋杀暴力的,可主人公拉斯科尔尼柯夫在施暴以后深陷在惶恐和反思中,最后走向血淋淋的忏悔,表现出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我把这称为上帝的立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展示暴力的非人性质,着力于对暴力的批判与超越,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他们已经做得足够了。二十世纪的欧美国家也像中国一样出现了那么多的暴行,单是六百万无辜的犹太死难者就足够叫我们世世代代难于安眠。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说,大屠杀使以往大约三十个世纪通过知识获得的一切都产生了疑问,一切都须重新审视。
应该早一天出现反省。作家应该首先做到这一点。因为文学的立场永远是肯定生命。作家作为精神生产者,不应该沦为环境的被动产物,而应表现出强大的精神主体性,从而最有力量从刺激——反应模式中挣脱出来。因为作家不只是现实生活的描述者,而永远是理想生活的创造者。
一九九五年六月 上海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死亡方式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战争论文; 古船论文; 革命论文; 历史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