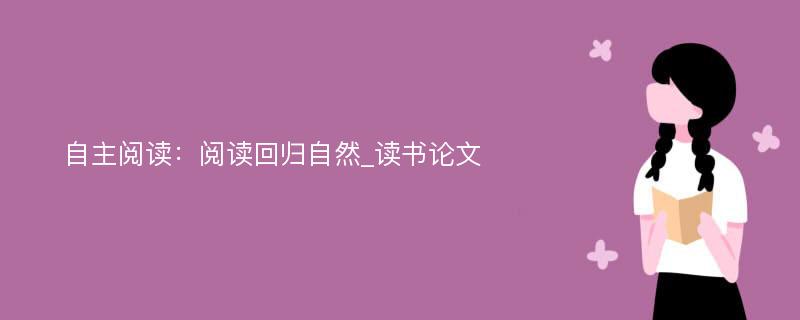
自主式阅读:阅读的返璞归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返璞归真论文,自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主式阅读,也可称之“自然阅读”或“感受式阅读”。其基本理念是:读者(学生)凭兴趣,主动、独立地阅读,而非被动强迫、较多先入之见外部干预地阅读;阅读的材料是读者不知道而又想知道的;阅读动机是以关注文章内容、获取信息或娱乐审美等满足实际需求为中心的,而非仅是章法、辞句、技巧、结构等形式化、技术性操练;阅读方式是重整体感悟、内在体验,而轻条分缕析、外来注入的,并且尊重感悟的个性,不求统解、甚解;阅读范围是开放丰富、大语文的,而非封闭狭窄、小语文的:阅读过程是放松惬意的,而非紧张负担的。因此,自主式阅读要求把说明文当说明文来读——获取新知,把议论文当议论文来读——了解新思想,把文学作品当文学作品来读——娱乐熏陶、审美体验。从“语言学”角度看,自主式阅读不属“语言学习”而属“语言习得”,是母语的第二次习得——书面语习得,阅读过程便是语言习得过程。“语言习得论”认为,学生的阅读能力,主要是学生在阅读活动中自然习得的,而不是靠老师对阅读材料的分析讲解和对阅读方法的介绍提高的。从本质上讲,语文是学生自己学会的,而不是老师教会的。
著名学者郭启宏先生曾介绍读书四法,可看作对“自主式阅读”的一种倡导:一曰“信马由缰法”,抓到什么读什么,有兴趣就读,没兴趣就歇,可行可止,思想无负担,放松近乎惬意。二曰“蜻蜓点水法”,只在书上款款飞,如打水漂,不求甚解,无意饱餐,王粲《英雄记钞》中说到诸葛亮的读书方法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不同,“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鲁迅在《随便翻翻》一文中也专门介绍此法。三曰“改弦易辙法”,一册书读来无味,绝不强读,马上换书。再无味,再换,至三番乃止。四曰“囫囵吞枣法”,即宋代学者陆象山所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也如林语堂所说“只是一路地读过去,不必在某些问题上过于拘泥,慢慢反刍消化。”
国外也有类似的理论。美国著名语言教学理论家克拉申在谈到如何提高美国人母语识字读写能力时,特别推荐了一种阅读方法——随意自愿阅读(free voluntary reading简称FVR)。FVR是自愿进行的一种阅读。读自己喜爱的书,不用写读书报告,不要求在每章阅读后做思考题,也不要求查阅生词,碰到不爱读的书就放下,去找另一本。他认为,如果能坚持这样做,“阅读和写作水平就会得到提高”《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1期)。显然,FVR就是一种自主式阅读。
中外都不乏这种现象:尽管许多学生对语文课不感兴趣,但对课外阅读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吕叔湘先生曾在《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的问题》中谈到:“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地说得益于课外看书。”国外阅读学研究中有一种有趣的“杰克现象”一名叫杰克的学生常常抱怨课文太没味道,不精彩。老师们都认为他缺乏阅读兴趣。然而在家中父母却埋怨他过分迷恋阅读,以至一份杂志,一张旧报纸,甚至一页广告他都百看不厌。“杰克现象”,并非国外特有和偶然发生,而是课内非自主式阅读教学的必然结果——纵有好的阅读材料,经落后的教育思想、不当的教学方法“加工”后,已变得面目全非,味同嚼蜡,却还要长期强人“吞食”,这正是造成学生厌恶语文课(并非厌恶语文)、产生“杰克现象”的重要原因。有人发现,即使同一作者的同一作品,课外,学生可能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一人选教材,到了课堂上,就精彩非昔了。一位叫卡罗的阅读学家把这种现象形象地概括为“课内的海明威没有课外的海明威精彩”。为什么课外阅读会更精彩呢?因为它是一种自主式阅读:是自愿主动的,是开放独立的,是以关注内容满足实际需求为中心的,是整体感悟内在体验的,是放松惬意无负担的。“真正的阅读,是与文本作者心灵的沟通与对话”,是由一个生命进入另一个生命的融合重建过程。海明威在教导他的儿子读写时说:“阅读名著,你只需要去感受它,而不需要去解释它。”此话深得阅读三昧。《红楼梦》中宝、黛二人都不爱读当时的“课本”——《四书》《五经》,但并非不爱“读书”,两人都有着浓厚的自主阅读的兴趣:《楚辞》、《庄子》、佛学、古风、唐诗、宋词、杂剧、传奇……凡怡情悦性的“闲书”,无不涉猎。(《四书》《五经》若作为可供选读的书籍之一,而非必读的课本“惟一”,更不要遇上像《牡丹亭》里陈最良那样的只会“以注解书”陈腐古板的庸师,宝玉也许会自己找来读一读)在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里,两人并坐桃花下,共赏《西厢记》,“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心内还默默记诵。”那自主阅读的情景,是何等美丽动人。黛玉的诗才、博学自不待说,是“大观园”中第一才女、诗人。那宝玉虽被时人讥为“愚顽怕读文章”,但“腹内”并非“草莽”。由于丰富的自主式阅读,他有着较深厚的语文修养,颇具“才情”。在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每到一处,宝玉都能根据景致特色、环境要求,拟出得体、新雅、灵气的匾额或对联,连一向嫌恶他“不读书”的贾政,也不得不颔首默许,一再命其“作来!”而那些皓首穷经的腐儒清客们,要么抓耳挠腮,要么拟出些陈俗浅陋、迂腐古板的对额。自许“自幼酷爱读书”的贾政,更是自始至终难题一辞。
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无论是学有所成的作家、学者甚至政治家、科学家,还是中学生中语文尖子,其在青少年时期,大都有过大量自主阅读的经历,可以说,是自主式阅读铺就了他们的成才之路。叶圣陶,由小学教师,靠自主阅读成为作家、教育家;钱钟书,学生时期即因“读书破万卷”而闻名;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自修;华罗庚,靠自主阅读成为数学泰斗,且文学功底颇深,诗文俱佳……从本质上讲,自主式阅读才是一个人读书生涯的真正开始。对此,笔者有深切的体验。上初中时(正是文革后期,文化萧条),我无意中从家中尘封的书箱中翻出几本叫《文学》的东西,残破的页面已发黄变脆。闲暇时随手翻阅,里面的一些篇章深深吸引了我:民间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唐传奇《柳毅传》,宋平话《碾玉观音》,名著节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岳飞枪挑小梁王》,都德的《最后一课》,契诃夫的《万卡》,鲁迅的《社戏》,赵树理的《三里湾》,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以及唐诗、宋词……我如获至宝,欣赏玩味,那情形,至今回想起来,心中每每荡漾起难言的甜美温馨,令人陶醉。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别人曾用来“学习”的课本(现在知道,那是建国后50年代,我国仿照苏联《汉语》《文学》分编,由人教社出版的一套初、高中语文教材)。设若当时我知道那就是用来“上课学习”的课本,是需要严肃对待、认真思考和考试的,带着众多任务、负担去“被动学习”,而非“自主阅读”,我一定会望而生畏、退避三舍的。即使看,也不会产生如此美妙的感受和深刻的印象。
而时下的语文教学,给学生自主阅读的空间甚为狭小。课外作业繁重,学生无暇阅读;课内又用纯“理科化”的形式,把一篇篇文章从字、词、句、篇到语、修、逻、文、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进行非常“科学”细致的“拆解”、深入的“鉴赏”、精心的“把玩”、反复的“历练”,醉心于枝节末叶的零碎知识,讲解不厌其多,不厌其深,甚至牵强附会,而很少舍得拿出时间指导学生自主阅读,体悟整体美感,品味文意语言。吴伯萧先生早就说过:“现在的教学把课文都讲‘肿了’。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阅读原文上。”更荒唐的是,还要硬性规定在特定时间内必须完成种种“阅读要求”,完成那些将一篇活生生的文章肢解而成的死气沉沉的匪夷所思的练习题;使学生在阅读时,总是带着“任务”的心态,吃力地被动阅读,总想微言大义,分析提炼出什么主题、词句寓义及章法技巧等,难以沉浸其中,拨动心弦,体悟文章情感内蕴,享受读书乐趣;使阅读变成了训练,训练就是做题,而且答案是惟一的,标准的;把读书的乐趣和美感,把启迪心智、提高感悟世界、认识世界、表述世界的能力等读书本意全都扫荡殆尽。林语堂早年就把这种“恶性读书,恶性教学,恶性出题,恶性考试”,斥为大煞风景的“烹金鱼煮白鹤”。这样的阅读必然是乏味、苦恼、令人疲倦的,必然使学生对阅读产生厌恶和畏惧,学生的阅读兴趣焉能不被破坏!而破坏了学生的读书趣味,就等于扼杀了他语文才智进步发展的机制。看似让他懂了些原来不懂的东西,实则得不偿失。一个人学生时期能否养成读书兴趣和习惯是件人生大事,将影响学生一生的走势和发展。国学大师梁启超认为:一个人不管是做什么的,工作之余,随时可以得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而读书的愉快能否得到,大概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决定了,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到读书趣味,形成读书能力。在梁启超看来,一个人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主读书的习惯,这个人简直就等于自己剥夺了自己终身的幸福,而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浓厚的读书兴趣。林语堂说:“所谓学习,就是喜爱。学生应该对读书发生狂喜。”(《论学问与知趣》)又说:“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读书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这才是不失读书之本意。”(《读书的艺术》)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也说:“一切语文从实践去学习比用规则学习来得容易。”(《大教育论》)有一种理论叫“阅读转注说”,认为阅读过程是个全息性辗转相注的过程,学生在阅读一篇篇文章的时候,字与字、词与词、句与句、篇与篇之间自动互相参注,互相补充,互相发明,使学生对语言文字和各种理法的认识由模糊到清晰,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不断积累,不断升华,语文能力便由此而得(《山东教育》2002年3、4期合刊)。这一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发现了语文学习的内在机制——自动转注、自然习得。而这种“机制”只有在“自主式阅读”中才能真正启动和运转,使各种知识信息、文化因子在头脑里聚集、碰撞、渗透、积淀,其语文能力、文化品位、人文素养乃至整个精神世界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课内教育是基础教育和共性教育,不可能保障学生兴趣爱好和个性的充分发展。课外阅读中的自我选择、自主阅读,就为其提供了一片寻找自我、发展自我的人类“文化原野”,学生在其中广采博收,尽情吸取各种文化滋养,移情化性,培本丰源,保证其个性和创造性的成长发展。
虽然课外阅读更多地体现了自主式阅读,但两者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自主式阅读的外延更宽泛。倡导自主式阅读也并非不要课内阅读和学“课本”,并非要弱化教师的指导作用,形成“大撒把”。相反,自主式阅读对教师的指导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在重视课外阅读的同时,通过教学改革增强课内阅读的自主性,变课内阅读为自主式阅读。
首先,课内阅读应让负载信息量的自主式、感受式阅读占主导地位。多给学生独立读书、体悟、品味、背诵的时间。最好在阅读篇目和篇目顺序上发扬民主,尊重学生的意愿和选择:对学生喜爱的篇目,可先学多学;适时将课外的美文佳作引入课内,作源头活水,或干脆定期在语文课时间将学生带入图书馆或阅览室,拓展学生自主阅读的时间和空间。发挥教师组织、引导、激励、点拨作用,点到为止,留有余地。注重感悟,注重阅读的整体性和文气文脉,少微言大意,少教条式拆解和技术性操练。组织学生畅谈读书体会,珍视学生体悟的个性化、差异性、创造性,使“课内的海明威”,变得比“课外的海明威”更“精彩”。
其次,重视课外阅读。新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及《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要求初中生每年课外阅读量(各类图书报刊)不少于80万字,高中生每年不少于100万字。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课本”加“读本”。《读本》成为课本的延伸、补充和扩展,意在扩大阅读量,着眼于学生的学而非教。由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等主编的《新语文读本》,更是以新理念、新面目展示在人们面前。每篇文章之后,只有启人深思的阅读建议,没有一个训练思考题,更没有标准答案,全是用平等商量的语气与读者对话、交流。人们会惊喜地发现,“教科书”之外竟还有如此广阔的语言艺术天地和“精神家园”。教师加强课外阅读指导,使之更科学、有序、高效。让学生多读一些有较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作品,特别是中外名家名著(国家要求高中生课外自读文学名著10部以上),使学生成为一个“好读书、乐读书”且品位情趣高雅的人。
第三,课内外结合,开设“佳作欣赏课”。让学生在课外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寻找“佳作”,文体不限,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在课上朗读,“奇文共欣赏”,再谈谈为什么将这篇文章推荐给大家,“佳”在何处,最后师生对这篇文章展开讨论,鼓励有个性、有新意的见解,以此引导学生大量阅读,精心选择,而且做到读、思、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