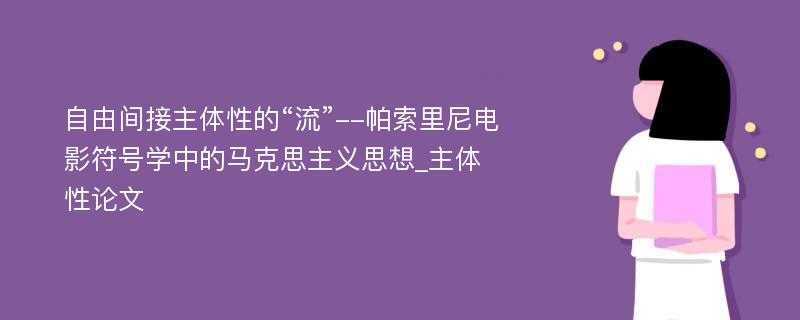
自由间接主体性的“流述”——帕索里尼电影符号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符号论文,学中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6-0086-06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6.011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被国人所知,多是由于他那“惊世骇俗”或“臭名昭著”的影片《萨罗,或索多玛120天》(Salo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人们只知帕索里尼是一位异端的意大利导演,并不了解他还是一位电影理论家,虽然他的电影理论名文《诗的电影》早在1984年就被译介入我国。事实上,帕索里尼是个多产多元的作者,无论是才华横溢的诗歌、小说,还是独辟蹊径的电影、剧作,都足以使他跻身当时欧洲一流作家之列。其重要的论文集《激情与意识形态》(Passione e ideologia)、《异端的经验主义》(Empirismo eretico),还有著名的文艺理论文章《现实的书写语言》(La lingua scritta della realtà)、《新戏剧宣言》(Manifesto per un nuovo teatro)等,亦证明他是一位理论与实践兼修的学者型作家、导演。尤其是《诗的电影》一文,奠定了电影符号学学科建立的先期基础,成为电影符号学乃至电影美学的经典文献,以此确立了他在西方电影理论史上的地位。 帕索里尼的电影理论以1965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60年代初,初执导筒的他就一直为杂志《新闻记者》(Il repovtev)的电影专栏撰稿,从自己文学创作和拍摄影片的实践经验出发,尝试用文学、美学、意识形态等工具对电影进行研究,此时期的文章基本属于“前-符号学”的电影评论之类。1965年6月,作为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的帕索里尼在皮萨罗第一届新电影节上发布了《诗的电影》。此文是他第一篇关于电影符号学的论文,开启了意大利电影符号学理论的研究,也是欧洲电影符号学的开山作之一。一些学者只知道克里斯蒂安·麦茨为电影符号学鼻祖。实际情况是,帕索里尼与艾柯、巴特、麦茨等著名符号学学者均参加了第一届皮萨罗电影节。在第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帕氏宣读了这篇论文。麦茨提出了一些关于电影符号学的构想,并与帕索里尼、艾柯等学者一起探讨了相关理论问题,最后结果是作为电影研究的主要法则“电影符号学”的建立。尼克·布朗说电影符号学始于三篇文章:1964年麦茨发表的《电影:语言还是言语?》,1965年帕索里尼发表的《诗的电影》,1967年艾柯发表的《电影符码的分节》。三篇文章奠基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模式的电影第一符号学。 一、实践唯物主义的“流述” 对比麦茨的《电影:语言还是言语?》所受到的赞许,《诗的电影》当时就被与会的艾柯等人批评为肤浅。在文中帕氏提出“电影梦的、原始的、不规律的好斗的视觉的特性通过它的技术手段被发现”。可后来,他又采用了不同的观点:在1967年的《活的符号和死的诗人》(I segni viventi e i poeti morti)一文中,帕氏声称一部诗的电影不能由前台操作的技术组成。于是,前后矛盾、立论玄奥,遣词粗俗,言语晦涩,对该文这样的评价甚至至今存留在学人们的认识印象中。[1](P.99)当时的其他专家攻击他的电影—现实符号学为异端邪说,艾柯说他的观点否定了符号学基本原则,把自然事实变成文化现象,是一种泛符号学的形而上学。[2](PP.95-96) 确实,作为语言学家、教育家、政治评论家,帕索里尼所有的理论文章,都不太注重自我立论的合学理性,不太在意过程化的详细阐说。为了追求一个理念,他往往忘记结束一个句子,或一整段话。他急切地需要抓住一个突现的思想火花时,常常牺牲文本的连贯性,遣词排句有着那么一种为了强调而重复的混乱性。因此阅读他的理论作品,会面临重重障碍。在其电影符号学的主要论文中伴随着调节现实中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他者间交流系统的普遍符号学思路,他还通过语言学和现象学来同步定位自我,并略带一点马克思—维科主义的观点,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和宗教神秘主义。这些均是其电影理论的组成部分。[3](P.23)泛化、多维、晦涩、矛盾……种种障碍遮蔽了深入解读帕氏电影符号学的道路。缺乏理论体系,是帕氏电影符号学的重大缺陷,使得其无法被系统阐发;又不如麦茨的“组合段”与“精神分析”可直接用于影片文本的解读,使得其不具备实践意义。但是帕氏学说的真正价值——只能在宏观地把握整体脉络后拣选出其理论的精妙要义,在于它前瞻性的语言哲学层次上。 作为学者,帕氏的电影理论及思想并不是建立在大量影片拍摄的基础之上,而是从文学实践开始,逐渐深入语言学领地,再从语言学扩展至符号学,以语言、符号的角度来论述。其语言学的思想渗入到他所有的文化政治理论及文艺诗学当中,帕索里尼声明,“(语言学)是我用来看见现实的方法的基本要素之一”,“所有作品的真实结构是它的语言学的结构”。[4](P.xxxi)他比其他符号学家更愿意把电影当做一种语言来研究。索绪尔语言学的标准术语时时出现在他的电影诗学里,帕索里尼发明的电影术语im-sign,kineme是想用来使电影和语言学保持整体的一致性。最后,帕索里尼甚至声称所有的生活都是语言——一个现实的泛符号学的表现形式。在该形式内每一种事物都是它自身的图像符号。[4](PP.276-283)如此宏大的命题,使艾柯的批评显得无力。 站在视现实本身为一种语言的高度,帕氏得出他对电影本体论的思考——电影是“书写”现实语言的符号体系。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当然也认同电影是一种语言,所以他寻找到了“大组合段”为电影共有的内在语言结构。帕氏“生活即语言”的高度,使得他所看到的不是固化的结构,而是电影符号书写的流动性,如生活随时而变的状态一样。他从查尔斯·皮尔斯那里借用了根据希腊语里表示“流淌”这个意义的词创造了一个新词“流述”(rhème)来表达自己这一观点。[5](P.32)流述这一概念,指出了电影存在的意义:发挥“书写语言”的作用,不是被动的记录,而是主动地赋予流动的、但可能缺失意义的生活一定的意义。电影不是现实语言的再现,而是对现实的符号化解析。那么,导演所做的工作就是创造和使用形象符号(im-signes)来记述流动的现实,赋予其意义。“电影导演没有词典,他只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他不是从某个柜子里或某个提包里取来他的形象符号,他要从混沌的世界中选取形象符号……并把它们编入一本形象符号词典。”[6](P.12)但“他对形象符号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无非是一个寿命极端的形象符号而已”,因为“它的文法符号来自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世界”。[6](P.12)这正是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对电影艺术发展史的表述。“流”表达了现实意义的流动感,“述”表达了电影表现的实践性,并隐含有主体性色彩。那么主体如何记述意义?这就是帕索里尼电影符号学的另一个核心观念——自由间接主体性。 二、自由间接双重主体 在以现实符号学为基础对电影的符号特性所进行的思考中,帕索里尼创造了许多理论术语,“流述”是其一,“自由间接主体性”(soggettività libera indiretta)亦是。从文字跨入影像,基于共同的符号哲学基础,这个在《诗的电影》中首次提出的概念,是他借用叙述学的“自由间接引语”概念来表述电影符号的实施技巧。 《诗的电影》一文使同时代的学者难以接受、不以为然。某些原因是帕氏自己疏于逻辑缜密地论证。他对“自由间接主体性”这一充满了思想火花的术语也是泛泛而谈:“‘自由间接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不是一个语言的,而是风格的要素。……这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自由间接主体性’的这种特性在电影中有很明显的风格可能性。”[6](P.21)在其后的论述中帕氏快捷地把自由间接引语等同于他倡导的电影中“诗的语言”:“自由间接主体性使电影有可能建立起一种诗的技巧语言的传统”,[6](P.22)最后总结出来“让人们感觉得到摄影机存在”成为制造“自由间接主体性”风格的保证。 人们在帕氏这些缠绕不清的术语中艰难推论的结果是,“自由间接主体性”等值于“感觉到摄影机的存在”。前者是帕氏定义的一种影片风格,后者是拍摄影片时场面调度的一种技法,把技法等同于风格,这是当时许多理论家对帕氏“自由间接主体性”理论的诟病。麦茨说帕索里尼对“自由间接主体性”的发现是“一种真正适宜的直觉”,但“帕索里尼没有能力把他理论的严格性赠与他的诗学的洞察力”。[3](P.93)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从相反的一面恰恰肯定了帕索里尼的洞察力给其诗学带来的前瞻性、预见性的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换一种工具来打磨这一蒙尘的理论,使其再度发亮,那就是“旁出侧见”法。以往对自由间接主体性的认识,只是局限于《诗的电影》这一篇文章的一个观点“电影诗性论”上,理解自然局促而狭隘。而帕索里尼的诗学,有着电影、文学、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呈现,弥漫着多变增值的意识形态。他所有实践创作或理论阐述的文本,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张互文性大网,彼此可以做最好的证明和注解。帕氏在语言学论文《自由间接引语的介入》(Interven-to sul Discorso Libero Indiretto)中,为再次发掘“自由间接主体性”的价值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论据。 在该文中,帕氏继承了从语言学、文体学到叙述学,再到后经典叙述学各家对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成果:自由间接引语的语义特点在于人物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两个主体双重意识的平分秋色、势均力敌,这种双重性表述了叙述对象与作者主体意识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构造隐含的作者对于有关人物的态度。……与人物泾渭分明的叙述者的出现可能造成一种含有讽刺意味的疏远效果。……叙述者说的话中也染有人物的语言或经验方式的色彩,这就可能引起读者的移情作用。”[7](PP.204-206)但同时,帕索里尼受到奥地利语言学家洛·斯皮策和其他德国语言学家的影响,不再把语言仅仅界定为一种抽象切分的索绪尔化了的纯形式,而是看到了语言的形式内涵与社会意蕴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特质,于是他肯定地宣称“每当某人用自由间接引语时,在作者那里,这意味着一种社会学的意识,无论清晰或否,对我来说是自由间接的基础和固定的特性”。[4](P.82)对帕氏而言,言谈的社会本质层面之一,即包含了“自由间接引语”,加上他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社会”观,因而在文中他给予了一个之前所有关注到自由间接引语的语言学家都不曾给予的政治性量度,提出了自由间接引语的阶级双重性问题。这种思考角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瓦伦丁·沃洛希诺夫/巴赫金不谋而合。这两位前苏联语言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中称“自由间接引语”为“类似直接话语”,指出在此话语中两个不同的主体言语同时发声,同时具有“元文学”以及社会性的特质:一份文本无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方式表达了其他(主体或文本)的言谈或话语——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总是包含了关于话语的话语,关于表达的表达。当叙述者和说话人之间的社会身份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在话语中体现的距离,均有明显的阶级意义。[8](P.198) 三、双重主体的阶级性 在帕氏的诗学观念里,自由间接引语是作者主体渗入人物的意识,人物口中所说还是自己的言语,“简单点说,那就是作者完全深入其人物的内心,他不仅采纳人物的心理,而且也采纳其语言”。[6](P.18)即文本中人物的思想是作者的思想,人物的语言却是自身的语言。而“人物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语言(专用语言、俚语、行话、方言等)”,[6](P.18)于是: 作者在纸页上复活他的主人公纯粹而简单的思想,以某种方式使他们生动,在语法和风格上,他制造了一种“内心独白”。但如果角色的言语和他的思想不一致,就有两种可能性:作者把角色当成一种机械装置使用,把其变形为自己的客观化的形式,如此组织起来的内心独白就成为一个径直的忠实的“主观”,或者是作者完成一个惊人的故弄玄虚,把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道德归因于在自己社会水平上不同于自己的角色身上,甚至归因于属于另一个社会阶级的角色身上。[4](P.88) 言语是主体的存在方式,通过主体的言语可以体认个人的生存状态。自由间接引语可以体认出其双重主体的不同阶级状态。作为小说家的帕索里尼,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坚持,及对布尔乔亚社会的反感与揭露,在目睹当时意大利社会的剧烈蜕变在语言上的反映后,结合自己大量的文学实践基础,察见到作者在自由间接引语语境中,尤其是隶属于中产阶级的作者,对角色的描写是和自我的地位身份、阶级等级、意识形态等主体性表达息息相关的。他分析自由间接引语现象的本质源于有着阶级差别的作者和角色之间神秘的相互渗透: 对于自由间接我必须含蓄地接受一个本体论现象,即一体感,或渗透作用。不管怎样称呼,(就是)在作者和角色之间的交感和睦关系,就似乎他们的生活经验是相同的。但是对我来说,断言使思想“复活”和“复活特别的引语来表达那些思想”是同一种现象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最无辜的布尔乔亚中,最讨厌的和不能容忍的事,是不知道如何认出除了自己之外的生活经验;是把其他人的生活经验带回到和自己经验的一个真实类比中。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给别人(一种经验)真是一种冒犯。即使一位高贵的、严肃的布尔乔亚作家,他不知晓如何认出一个生活经验不同于他的人的心理学上的极端特性曲线。[4](P.87) 在帕索里尼看来,即使是最无辜的、高贵的、严肃的布尔乔亚作者,也无法知道一个次无产阶级的角色真正的经验和感觉。所以作者只好“被迫复活”角色的那种不属于布尔乔亚世界的语言,通过低层阶级的言语来理解那个阶级。不过,有的作者在复活角色语言时暗示了自己的同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天主教徒的意识形态;而有的作者模仿低级阶层的话语则为了居高临下地讽刺他的角色。对于自由间接引语形式所蕴含的阶级意识形态上的观点,帕氏例举了自己的小说来证明。他在创作两部著名的罗马贫民窟小说《生活的年轻人》和《暴力人生》时,模仿了罗马郊区无业游民那肮脏淫秽的俚语,声称自己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乔亚的身份去认识角色的。 除强调自由间接引语的阶级意识外,帕索里尼还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有必要记住这一点:有的书完全由自由间接话语构成。即非常频繁地使用未完成式,意味着一位作家—叙述者,在某一刻,因为一种神秘的和他的角色互通的需要,一种至少是表达上的神秘需要,去创造必须使自己(叙述者)通过他的角色的体裁:特别是在对过去的复兴中,及在对现时或痛苦或喜悦的反映当中。”[4](P.90)如同把所有现实看成一种泛符号化的语言一样,帕氏察觉到自由间接引语不只是小说中人物所说的几句话语或更大的意识流段落,还可以是整部叙述文本。如此,把整个文本当做一个承载复杂讯息的符号体系,最外围的作者在编制该符号体系时通过人物的言行把自我主体性渗入其中,当接收者在解码时就会感受到“自由间接引语”的双重主体发声,察觉到作者之魂在人物言行的关键处发光,从而辨识出作者的主体意识所在。评论家不正是从《生活的年轻人》中那些生活在罗马底层的小偷、妓女、皮条客等人物的言语里揣摩出帕索里尼对现实中真正的次无产阶级抱有的同情悲悯甚或崇敬的心态么? 四、电影中的双重阶级 自由间接引语的阶级双重性以及它的宏阔适用性,是帕索里尼对文学文本中该语体形式的一种社会哲学、语言哲学的洞见。同时,帕氏也把该形式的哲学性申述运用到了他的电影符号学中。 在《诗的电影》中论述电影能否运用自由间接引语(即电影中“诗的语言”)技巧时,帕氏套用了自己对小说中自由间接引语的论说:“如同作家在运用自由间接引语时并不总是有强烈的技巧意识一样,电影导演直到今天也是完全无意识地或者仅仅以非常朦胧的意识创造了电影语言的各种风格元素。自由间接引语在电影中无疑是可行的,我们可以称它为‘自由间接主体性’(和相应的文学手法相比,它可能要呆板和幼稚得多)。”[6](P.20)在电影创作中,对应于小说人物的是演员,演员的一切表演行为相当于被转述者的语言,导演用摄影机模仿(再现)这些言语相当于转述者对被转述者语言的模仿,看似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其人的言辞特性,实则是那个最外围的叙述者(导演)的自我表达。“在导演工作的最初阶段,主观动机就存在了,因为对可能有用的形象所做的初次选择必然是以导演在这一刻对现实的看法为依据的。所以形象符号语言从一开始就是有倾向性的和主观的。”[6](P.16)可惜的是,帕氏太在意自己的“电影诗性论”,把影片文本中显露的导演主体性论证为一种造就电影“诗的语言”的技巧,把“感觉到摄影机的存在”这一技巧视为“自由间接引语”风格,犯了一个马马虎虎地把基本技术性和根本实质性等同起来的不严谨的错误。从而也使对帕氏电影理论的解读与评论者误解了“主体性”的含义,把它和主观镜头相提并论(原来意大利文的“主体性”一词就被有的英文译者译成了“主观镜头”)。 后来对帕索里尼电影理论有着再次精辟阐发的德勒兹,尝试着把相关镜头视角和自由间接主体性的区别与联系说清楚,他指出“自由间接主体性”蕴含了一个人物主观想象视野与镜头间的模拟关系:“摄影机不仅仅给我们角色的(视野)和他的世界的视野,它还强加另一种视野。在这种视野中,首先的(视野)是变形和反映。这样的双重性就是帕索里尼所说的‘自由间接主体性’。”[9](P.106)一种视野之外的另一种视野,即帕索里尼声称的一部影片外的“另一部影片”,[6](P.24)第一种视野/第一部影片是演员所扮演的人物的现实,另一种视野/另一部影片就是导演的视野和他所“记述”的现实——所有镜头都皈依于导演的主体观照下,都是他的“主观镜头”。为了强调导演的主观注视,帕索里尼在理论中提出了一种“感觉到摄影机存在”的技法,可以让观众强烈感觉到导演的主体在场。 影片文本的主体双重性也关涉影片双重主体的阶级性。《诗的电影》中帕氏实践性地用它衡量了三位大师安东尼奥尼、贝尔托鲁奇和戈达尔的影片,得出了三种不同的“自由间接主体性”,隐约地指出了角色和导演的阶级属性:安东尼奥尼在《红色沙漠》中“通过他的神经质的女主人公来观看世界,经由她的‘眼光’来再现世界……他以自己的沉醉于唯美主义的视象,完全取代了一个女病人对世界的看法”;贝尔托鲁奇在《革命前夜》中“让病人对世界的看法和作者本人的交替出现”;戈达尔“以一种冷漠的、几乎只是为了追求自我满足的迷狂心情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重新结合成一种含糊不清、不知所云的语言”。[6](PP.23-26)三位导演的主人公都是“作为假托来使用的人物,只能从作者自己的文化圈中选择,这些人物必须具有和作者相近的文化、语言和心理,必须是‘资产阶级的精华人物’。如果他们是属于另外一社会阶级的,那就要把他们纳入精神失常、神经质或精神过敏的框框,予以同化”。[6](P.30)帕索里尼这段不带褒贬之情的陈述,实则暗讽了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非理性病态存在——精神失常、神经质、精神过敏。要注意到他的“资产阶级精华人物”是带引号的,这就富含了帕氏的嘲讽之意,对影片中人物的嘲讽,亦是对作为资产阶级的导演的嘲讽,因为两者的心理是相近的。所以,影片主人公的病态呈现,实则是导演自我主体性的“自由间接引语”。而且,当主人公若属于另一阶级(无产阶级),那么这些无法深刻理解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导演,只有尽可能在摄影机下呈现符合无产阶级的言行,但表述的还是作为资产阶级导演的精神状态——“所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文化企图夺回它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失去的领地并尽可能予以彻底变革的运动的一部分。”[6](P.31)这是帕索里尼最后发出的警告。 通过互见法和去粗取精,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信奉葛兰西“民族—民众”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帕索里尼在其电影符号学中渗入了其他电影符号学家罕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实生活即语言,一条不间断地流动的符号之河。电影不仅再现自然现实的征象,而且是导演制造出“形象符号”来把流动现实中的某些意义与象征固定下来,是导演对“现实实在的符号体系”的书写,即“流述”。在这个术语中蕴藏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能量。进而,摄影机在“流述”现实符号时,导演依据自己的主体意识来选择与制造“形象符号”,以便在角色与人物身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自由间接主体性”的声音是具有阶级性的。在帕索里尼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导演们通过影片人物角色来表达自我存在的迷茫与虚无。他们无法理解与深入到无产阶级的内心,因此他们的影片中无产阶级并不是真正无产阶级,也和那些“资产阶级精华人物”一样病态,为资产阶级导演代言而已。如何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地?帕索里尼没有回答。但他曾说过,他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去认识自己小说中的次无产阶级角色的。以此观之,电影是自由间接主体性的流述,那么必须是真正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体的导演,才能用电影来表达真正的民族、民众的文化。标签:主体性论文; 帕索里尼论文; 符号学论文; 间接引语论文; 角色理论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语言学论文; 布尔乔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