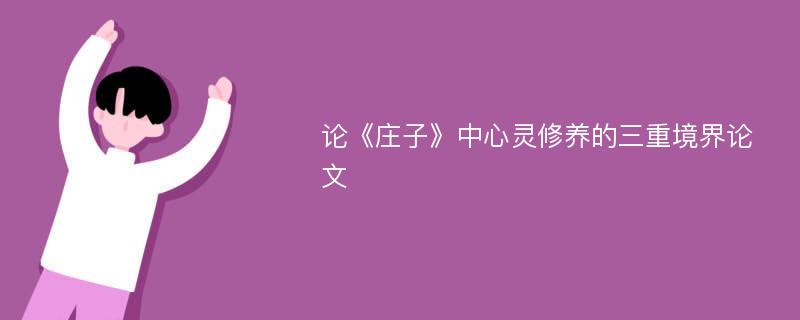
论《庄子》中心灵修养的三重境界
朱松苗
(运城学院 人文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0)
摘要 :《庄子》的智慧是“无”的智慧,“无”规定了道并成为生活世界的本源。然而世界却以“有”的形态呈现,因此人需要通过心灵之“无”复返于道。心灵之“无”蕴含三重意蕴,由低到高显现了心灵修养的三重境界:一是心灵的否定,即对人为之“有”的否定;二是心灵之“忘”,即对自然之“有”的超越;三是心灵之“化”,即心灵的转化、升华、提升和拓展。心灵所领悟的不是其他,正是“无”,唯有“无心”,人才能真正拥有“有”。
关键词 :《庄子》;无心;忘;化;心灵
“如果说西方的智慧为神性的智慧,儒家的智慧为仁爱的智慧,佛教和禅宗的智慧为空性智慧的话,那么道家的智慧则为‘无’的智慧”[1]。这种“无”的智慧突出地表现在《庄子》中,因为《庄子》所强调的不是儒家的积极有为、奋发进取,而是“无待”“无为”;不是儒家的立功、立名,而是“无功”“无名”;不是儒家的多识、多知,而是“无知”“无思”“无虑”;不是儒家的有心、有用,而是“无心”“无用”……因此《庄子》所强调的不是“有”之美,而是“无”之美;不是实之美,而是虚之美;不是物之美,而是道之美。“无”成了《庄子》的主题,它的存在、思想和言说是被“无”所规定的,它的理想世界是“无何有之乡”,它的理想之人是“叔山无趾”“伯昏无人”,它的理想之物是“空骷髅”……
然而,对于《庄子》而言,虽然“无”规定了生活世界,现实却并不以“无”的形态呈现,相反它所呈现的是一个琳琅满目、活色生香的“有”的世界,以至于人们沉溺其中、乐此不疲。在《庄子》看来,这种对“有”的“乐此不疲”本身就意味着人背离了其本源与本性,同时也意味着“有”自身越过了自身的边界。因此对于人及其所沉溺的对象“有”而言,他们的任务就是复返于“无”。那么他们如何复返于“无”呢?
这个问题又可具体化为:一,“无”的主语是什么?二,“无”的宾语是什么?三,“无”是如何实现和完成的?在此基础上,我们甚至还可以追问,这种“无”是人的主观意愿,还是一种客观存在? 其中,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无”的宾语就是生活世界中包括人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有”,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回归于“无”,就需要无“有”。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无”的主语是什么?一般认为就是人,但是这种不证自明的回答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是想当然的,即便不是如此的话,这种不证自明也会掩盖很多不可逾越的问题,如“无”的主语为什么是人,而不是动物?即便是人的话,它究竟是指人的身体,还是指人的心灵?如果是人的心灵的话,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灵?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200个缔约方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鼓励使用低碳能源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长远目标是确保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付出努力。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提供的信息,目前全球约70%的电力来自化石燃料,如果想在2050年实现上述目标,80%的电力需要来自低碳能源。
一般而言,就人的身体和心灵来讲,身体是不能否定自身的,能够否定身体的只有心灵。心灵不仅会否定身体,而且会否定自身。从这个角度来讲,否定的主语就不能是动物,因为动物只有身体,没有心灵,只有人才拥有心灵。基于此,否定的主语应该是人,但是人也只是具有了拥有心灵的可能性,因为还有一些行尸走肉的人其实与动物并无二致,他们只有身体,并没有心灵,所以否定的主语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具有丰富心灵的人。
最后,“无心”如何否定?既然它所否定的对象是心灵的区分和执着,那么这种否定也只能通过心灵来进行,这在《庄子》中被描述为“心斋”的过程。“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一、心灵的否定
如果说“有”可分为自然之“有”和人为之“有”的话,那么心灵要“无”之的话,就要具体区分两种情况。 对于人为之“有”,《庄子》认为回归的途径就是否定,即通过“无情”“无欲”“无知”“无言”等回归其本来的状态。在此“无”就不再是与“有”相对的存在性之“无”,而只是作为否定的动词性之“无”。或者说人正是通过否定性之“无”而通达存在性之“无”。质言之,否定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它符合“无”的本性[2]。
问题在于,首先,谁在否定?如上所述,它就是人的心灵,而且不能是作为“有”的心灵。既然“有心”不能成为否定的主语,那么否定的主语就只能为“无心”,所以《庄子》强调了“无心”的重要性——“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天地》[3]),正是基于此,《庄子》认为得道之人也应该是“无心”的,即像啮缺一样是“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的人。不仅如此,郭象甚至认为“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4]。也正是因为如此,刘笑敢认为不是“有心”而是“无心”,才是“庄子对待社会、人生的根本态度”[5]。
式中:ω1,ω2是定义的权重参数,gimax-1表示满足覆盖条件的子集数目,Pgimax表示不能满足覆盖条件的子集的网络覆盖率。显然,算法寻找最大适应度函数的过程就是不断增加覆盖子集的过程。
对于《庄子》而言,不是所有有心的人都能成为否定的主语,因为心灵自身也可以分为很多种,比如“成心”“机心”“惼心”“忮心”“蓬之心”等,很显然它们并不能成为否定的主语,因为它们带有自己的欲望或意见,其本身就是一种“有”心,所以这样的心灵不可能通达“无”的本性——在此意义上,“无”并不是心灵的意愿,而是事情本真的存在形态。
而就失去本性而言,“刻意而高”与不“高”、“仁义而修”与不“修”、“功名而治”与不“治”、“江海而闲”与不“闲”、“道引而寿”与不“寿”并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只有忘“高”才能“高”,忘“修”才能“修”,忘“治”才能“治”,忘“闲”才能“闲”,忘“寿”才能“寿”,故而“无不忘也,无不有也”。 进而《庄子》认为“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让王》),得道的关键在于忘心,忘心的前提在于忘形,忘形的基础又在于忘利。正是基于此,牟宗三认为“道家的智慧是‘忘’的智慧”[13],爱莲心则更明确地提出“心忘是得道的关键”[14]。“忘”就是心灵的超越,它是人的心灵从物的世界向道的世界、从“有”的世界向“无”的世界超越的过程,也即人超越自身之“有”而回归于“无”、复返于道的过程。
所谓“斋”,《说文解字》解释为“戒洁也”[7],而“戒”是一个会意字,上面为“戈”,下面的“廾”像两只手,双手持戈,意味着警戒或戒备,故而所谓“祭祀之斋”就是让我们的感官和身体保持在自身的纯洁、纯净之中,不让酒精和荤腥刺激人的欲望,这是通过感官和身体的戒备来实现的。但是人的感官和身体自身是无法戒备感官的欲望和身体的刺激的,因为从本质上讲,人的感官和身体本身就是欲望性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它们与动物的感官和身体并无二致。如果人无法依靠身体自身来戒备身体欲望的话,那么他就唯有依靠心灵来戒备身体的欲望,让感官和身体保持在自身的纯洁、纯净之中。正是基于此,人与动物的本质性区分就不在于身体和感官,而在于心灵。由此可见,人的最本质的斋戒就不是“祭祀之斋”,而是心灵之斋——“心斋”。 “心斋”就是让心灵保持在自身的纯净之中,这又是通过心灵的戒备来完成的,而所谓心灵保持在纯净之中,也就是通过心灵的否定,让心灵保持在“虚”或“无”之中,所以刘笑敢认为,“‘心斋’的实质即一个虚字,要达到心灵的虚静,必须……抛弃耳目心思,纯由神秘之直觉”[5]。
无独有偶,《庄子》认为“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知北游》)。所谓“齐”,郭庆藩在《庄子集释》中曾指出“赵谏议本作斋”[8],后曹础基[9]和陈鼓应[3]都将齐解释为“斋”之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斋戒心灵,就要疏通、纯净它,为此人需要否定或“去除”[3](“掊击”)心灵的“知”。人不仅要否定人为之“知”,而且要否定人的贪欲。“梓庆削木为鐻……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达生》)要让心灵保持在“静”(“无”)的状态之中,就需要对“庆赏爵禄”“非誉巧拙”“四枝形体”怀有戒备之心。
混合型鸡痘指的是皮肤型鸡痘与黏膜型鸡痘同时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染病鸡会同时出现两种类型的鸡痘病征,病情发展迅速,而且死亡率较高。
以护理前后ADL评分、FMA评分为评比项进行对比。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分,总分100分,>61分表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轻度的功能损害,41~60分表示中度损害,<40分表示重度损害。简式Fugl-Meyer评测法(FMA)评分,进行上肢、下肢运动功能的评定,运动功能程度与分数呈正相关。
对此,王博认为,“庄子这里提到了耳、心和气,并将其看作是三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前两个层次也许不同,但在要被否定这一点上却没分别。庄子要求无听之以耳和无听之以心,而要听之以气。因为气是虚而待物的,它没有任何的欲望、坚持和偏见,因此……可以在这个世界中游,而不和它发生冲突……耳和心则不同,只有某些声音或者事物是顺耳和顺心的,另一些则不是。这就有了分别,有了执着,有了冲突。这正是它们要被否定的理由……听之以气则不同,心此时如气一般的虚无恬淡。这就是心斋,就是使心变得像气一样的虚而不实”[10]。
二、心灵之“忘”
如果说对于人为之“有”,我们要进行否定的话,那么对于自然之“有”,则不能否定他们。因为人为之“有”原本并不存在,所以否定它可以让人和物各自返回自身;而自然之“有”则是天生而成、本然存在着的,否定它会让其远离自身,所以对于自然之“有”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摆脱”。但是对于某些自然之“有”,如人的动物性本能,它们虽然与生俱来,不能被完全否定,但是我们却不能被它所束缚,否则人将无法和动物相区分开来。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既不能否定这种“有”,又不想被这种“有”所拘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有”呢?《庄子》认为人应该“忘”自然之“有”,即超越自然之“有”。
问题在于,“忘”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如果“忘”仅仅表现为不记得的话,一个大脑有缺陷的人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真正的“忘”不仅仅只是不记得,更是一种心灵的转化和升华,是一种境界的提升和拓展——“不记得”只不过是它的外在表现,心灵的转化和升华才是它的真正内涵。所以“忘”的关键还在于“化”。
那么,“忘”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忘”意味着其对象是存在的,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所谓忘与不忘的。既然其对象原本存在,我们就不能“否定”它,而是要超越它,不被它所束缚、所限制。 其次,“忘”的主语也是心灵。因为从字形上看,“忘”即心无,所以许慎解释“不识也,从心从无”[7]。“有”是存在的,只是心不识这个“有”,这就是“忘”。那么如何才能不识呢?一是不知,根本上就不知道这个“有”;二是超越所识之“有”。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前者有可能从不识到识,后者则是从识到不识,它是对所识的远离。所以“忘”的实质是一种超越。因为“忘”只是心灵之“忘”,所以这种超越也只是心灵的超越。
“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达生》)人如果忘记了脚的存在,这不仅表明了鞋子的合适,而且表明了脚的舒适;如果忘记了腰的存在,就不仅表明了腰带的合适,而且表明了腰的舒适;如果忘记了是非的存在,则表明了心灵的安适;如果人内外不移不从,则表明了人的处境的安适。这意味着人一旦忘记“有”,而处于一种“无”之中,人也就超越了“有”,使自己处于一种“舒适”之中,即得道的状态之中。也即是说,只有在“无”中,人才能真正地“有”;只有忘记“有”,人才能真正拥有“有”。
因此,我们如果要真正拥有“足”“要”“心”“事会”,就要忘记它们,超越它们,让它们在心灵中成为一个“无”,唯有这样,它们才能成为自身,成为真正的“有”,否则事情就会适得其反。“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刻意》)高尚、修身、治世、闲游、高寿本来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当成一种“有”去追求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然”,也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本性。
其次,“无心”在否定什么?一方面,“无心”所否定的是人为之“有”。这种“人为”就表现为一种分别和执着,它将原本统一、完整的世界进行区分和切割,并执着于其中某一方面的“有”,甚至是一种贪“有”。另一方面,“无心”也否定有可能成为新的“有”的“无”,这既包括对形而下之“无”的执着,如执着于“有”的隐藏,“有”的缺失,或者与“有”共生的“无”;也包括对形而上之“无”的执着[6]。
《庄子》首先区分了两种“斋”:“祭祀之斋”和“心斋”,所谓“祭祀之斋”实际上就是感官之斋,在这里主要是味觉之斋,事实上不仅是味觉,包括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都应该是“斋”的对象,因为它们容易诱发人的贪欲,扰乱人的自然本性,损害人的感官和身体自身,所以我们要“斋”之。
三、心灵之“化”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这里的“堕”“黜”“离”“去”就不能被理解为否定之义,因为对于人而言,其“肢体”和“形”是原本就存在的,有些“知”也是生而具有的,对于这些自然之“有”,我们就不能完全否定它们,而是应该“忘”(“堕肢体,言忘形也……言身知俱泯,物我两忘”[11])或者“超脱”它们(“不着意自己的肢体,不摆弄自己的聪明,超脱形体的拘执、免于智巧的束缚,和大道融通为一,这就是坐忘”[3]),所以徐复观认为“庄子的‘离形’……并不是根本否定欲望,而是不让欲望得到知识的推波助澜,以至于溢出于各自性分之外。在性分之内的欲望,庄子即视为性分之自身,同样加以承认的”[12]。因此,《庄子》所要否定的并不是所有的欲和知,而只是“性分之外”的贪欲和巧智,对于“性分之内”的欲和知则是“忘”。
对《庄子》而言,“化”是宇宙间最普遍的一种现象,因为“万物皆化”(《至乐》),“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天地》),也正是因为此,“化”字本身在《庄子》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多达近百次,有“物化”“造化”“变化”“一化”“万化”“自化”“风化”“化育”等,但是爱莲心认为这些“化”都还只是“世间事物的转化”,而不是“这个术语的主要所指”,真正的“化”应该是“事物在我们对它们的恰当的理解中发生转化”,因此她把这种“化”归之于“个人觉悟水平的改变”[14]。这与冯友兰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人可以通过“理解”来洞见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从而超越“相对的快乐”而达到“至乐”[15],这种洞见也被称之为“觉解”[16]。这个过程被吴光明称之为被“唤醒”,“他要唤醒我们,使我们悟察而自动地从社会老习惯脱出而回到我们天然的真己,真正地与现实的天地世界有直接的交涉接触”[17]。
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只是通过感官去倾听,这实际上是其他动物也能完成的行为,如果我们只是执着于用“耳”去听,那么人就会像动物一样“止于耳”。人之所以贵于动物就在于他有心灵,但是如上所述,人们的心灵往往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之中——即“成心”“机心”之中,一个有“成心”“机心”的人所关注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事情是否符合自己的成心(“心止于符”),所以我们要戒备这种“成心”和“机心”,即“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而之所以要“听之以气”,成玄英认为“心有知觉,犹起攀缘;气无情虑,虚柔任物”[4],即“气”的本性为“虚”,因此它不会有“成心”和“机心”。这意味着我们的心灵要像“气”一样,保持在“虚”和“无”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即是得道的状态,所以“唯道集虚”,郭象认为“虚其心则至道集于怀也”[4],而这又是通过心灵的否定来完成的,既否定对于“有”的执着,也否定对于自身的执着。
沿着这样的思路,《庄子》中的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如《逍遥游》中鲲鹏之化,一般认为此“化”是世间事物之间的转化,但这样一来,鱼如何能变成鸟的问题将会变得纷繁复杂而超越《庄子》的旨趣。吴怡认为此“化”实际指向的并不是物与物之间的转化,而是通过寓言暗喻的人的“精神的升华”,最终达到“能够与物同化,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及通达这种境界的修养工夫[18]。这种解释不仅与《逍遥游》的主旨——心灵境界的提升相符合,而且与《庄子》更加重视如何达道的思想特质相符合。如果说《老子》思想重视的是道本身,那么《庄子》所重视的则是人与道的关系,即人如何达道,如何开阔视野、充实心胸、提升境界的问题。鲲与鹏、鹏与斥鴳、大知与小知、大年与小年之别表面所突显是“小大之辩”,实质上它们所通向的则是人的视野的远近和境界的高低,即知德之人、宋荣子、列子与至人、神人、圣人的分别。
在此意义上,心灵的转化是重要的,它所依靠的是人的心灵境界的提升,即人的心灵领悟的能力。只有当心灵领悟之时,人的真正“转化”才会发生,而不至于心随物转;同时,对于自然之“有”,人才能真正有意识地“忘”,而不至于在“忘”后又重新记起;对于人为之“有”,人才能真正有意识地“否定”,而不至于在“否定”后又重新肯定。心灵所领悟的不是其他,正是“无”——无己、无功、无名、无穷、无何有之乡;心灵之所以能够领悟,则是因为心之“无”,即“无心”,而心之“无”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道之“无”。
(1)适应度值好的一类采用本地生存策略,即当前的生存区域已经有较好的生存条件,草莓植株可在当前区域进行生长。本地生存策略在使用2-opt交换方法的基础上融入遗传算法的交叉算子,采用双链单点交叉,pc为交叉概率,如果pc>rand,则将原个体与最优个体进行交叉,如图6所示。
因此,对于《庄子》而言,真正的心灵之化不是一般观念的变化,而是超越了所有观点的转化;它是以道的视域、以得道的心灵即整体性的、无限性的、动态性的视角和观点来观照世界,而不是从某一个片面、有限、静止的视角和观点来看世界——在此意义上,心灵才能返回“无心”的状态,达到其最高的境界;人才能复返混沌一体的源初,消除物我的界限,从而与万物融为一体,因此“融化”“化育”才有可能。“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从现实的角度,庄周和蝴蝶显然是有区别的,但是在道的视域中却是一个整体,他们不仅相互依存、互为显现,且可以相互转化。但是要从现实物的世界复返道的世界,人需要心灵的转化,唯有如此,“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才能真正实现。
相比大江大河和骨干河道,县乡河道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河道治理需兼顾的内容较多,主要包括水安全(防洪排涝为主)、水资源(灌溉供水为主)、水健康(水质改善为主)、水景观(营造局部休闲空间为主)、水文化(彰显当地文化为主)等,相应的治理措施有清淤疏浚、清障、水系沟通、岸坡整治、堤防加固等。
四、结语
概言之,人因为有了“有”之心而远离了“道”,所以人要返回原初之“道”,就需要否定、遗忘(超越)和转化人的心灵——即否定人为之心、超越自然本能之心,而其关键又在于心灵的转化,也就是心灵境界的提升,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决定了他所能“否定”和“超越”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崔大华认为“庄子的‘闻道’过程实际上并不是认识内容的丰富过程,而是精神境界的提高过程”[19],吴光明也认为“庄书不传递信息而是在激发共鸣,传达的结果不在知识的增加,乃在新激起的境界”[17]。而心灵最高的境界无疑是得道的境界,在《庄子》中它又被具体化为“无己”“无功”“无名”“无古今”“不死不生”的境界,也即“无”的境界——这既是心灵的原初境界,也是心灵的至高境界。因此人的心灵修养就是让心灵还乡,让心灵返还到“无”心的原初状态。对于《庄子》而言,这种状态也就是得道的状态,因此也是至美的状态,在其中,人才能“逍遥游”,才能获得“至乐”。基于此,“人”才是美的人, “心”才是美的心,这个地方才是美的境界。因此“人”通过心灵之“无”通达“道”,也就是通达“美”。
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格外重视对学生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且高职院校中学生参与学习的时间基本都在三年左右,在有限的时间内学生若要高效掌握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专业内的教学人员就必然要具有极强的专业能力,这样才能通过高质量的教育培养出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而当前国内多数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却呈现配置及质量不均衡等现象。师资力量的匮乏会令院校的教育实力随之下降,故本着提升校内教育实力的根本原则,本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核心思路对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建设策略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朱松苗.论《庄子》之“无”的美学意义[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0(2):90-97.
[2] 叶秀山.世间为何会“有”“无”[J].中国社会科学,1998(3):64-65.
[3]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568,573,242.
[4] 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M].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124,80,81.
[5]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59,175.
[6] 朱松苗.论《庄子》之“无”的三重意蕴[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131-137.
[7]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8,220.
[8]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741.
[9] 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324.
[10] 王博.庄子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8.
[11] 释德清.庄子内篇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7.
[1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4.
[13]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4.
[14] 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M].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60,导言.
[15] 冯友兰,赵复三.中国哲学简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19-122.
[16] 冯友兰.新原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19.
[17] 吴光明.庄子[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68,83.
[18] 吴怡.逍遥的庄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6.
[19] 崔大华.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99.
On the Threefold Levels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in The Chuang -Tzu
ZHU Song-miao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Shanxi 044000,China )
Abstract :The wisdom of The Chuang -Tzu is “non-being”, which defines Tao and becomes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living world. However, the living world is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being”. For this one needs to return to the “Tao ” through the “non-being ” of the mind. The “non-being ”of the mind contains three connotations, which reveals the threefold levels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One is the negation of the mind, that is, the negation of artificial beings. The second is the forgetting of the mind, that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natural beings. The third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that is, th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being”. It i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the mind,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state of mind. The mind understands nothing but “non-being”, and only in the state of “non-being of the mind”, can people really have “being”.
Key words :The Chuang -Tzu ; non-being of the mind; forgetting; transformation; mind
*收稿日期 :2019-05-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庄子》之‘无’的美学精神研究”(17YJC720044);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庄子》之‘无’的美学精神及其当代意义研究”(2017265);运城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理想缺失背景下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国化研究”(YQ-2017012)
作者简介 :朱松苗(1980- ),男,湖北宜昌人,博士,运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37(2019)05-0084-05
(编辑:张文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