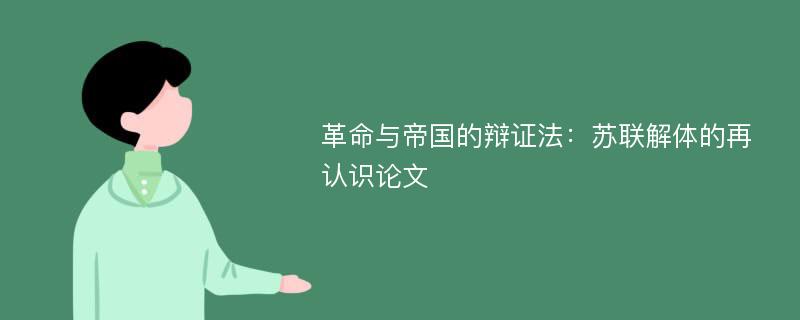
革命与帝国的辩证法:苏联解体的再认识
吴蔽余
[内容摘要] 美国学者祖博克的《失败的帝国》、浦洛基的《大国的崩溃》采用了一种理解苏联及其解体的新视角:“革命与帝国”。在他们看来,苏联的本质首先是帝国,包含了地缘政治扩张和多民族疆域维持两个维度;其次是革命,也即意识形态,包含了特殊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普世主义的“世界革命”两个方面。“革命与帝国”体现为具有内在矛盾的话语与实践,并贯穿了整个苏联历史。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历史可以视为革命衰退、帝国增强的历史。失去革命的帝国失去了合法性和吸引力,最终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抛弃。苏联解体的本质是帝国解体为民族国家,解体的根源已经埋藏在革命的宪法中。
[关键词] 苏联解体;革命;帝国;意识形态;民族国家
一
1991 年12 月25 日,残阳如血。戈尔巴乔夫发表了辞职演讲后,不到半小时,苏维埃的旗帜就从克里姆林宫降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传统的白蓝红三色旗。戈尔巴乔夫希望收藏那面苏联国旗的愿望被叶利钦拒绝了。① 〔美〕沙希利•浦洛基:《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宋虹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46 页。 这不是一次政权的轮替,而是俄国革命与苏联帝国最后的晚景。
从200名消费者中筛选招募57名年龄为20~55周岁的汉族女性,平均年龄为32周岁,其中干性肌肤和中性肌肤消费者29名,混合性和油性肌肤消费者28名。主要排除条件为:有严重系统疾病或近2年内发生过化妆品过敏现象;正处于孕期、哺乳期或者备孕期;正在参与其他临床研究项目;日晒时间较长的户外工作者;近3个月内接受过其他美容护理或其他影响测试的因素。
苏联解体之后,苏联问题专家就解体原因给出了大量的解释,这些解释要么采取内部视角,要么采取外部视角。内部视角将解体根源归结为苏联体制本身,也即高度依赖领导者个人意志的政治体制和高度依赖自然资源、高度计划性的经济体制。在此体制下,党国精英沦落为僵化保守的官僚,底层人民积累了苦难和不满,少数民族反抗不公的命运,这些都导向了苏联最后的解体。② 内部视角的代表性作品包括波兰记者卡普钦斯基的《帝国:俄罗斯五十年》、原苏联财政部长盖达尔的《帝国的消亡》等。〔波〕卡普钦斯基:《帝国:俄罗斯五十年》,乌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俄〕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 与此相反,外部视角强调外部因素对苏联解体的根源性影响。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动摇了苏联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军备竞赛给苏联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负担。在外部压力下,意识形态上亲近西方的苏联精英主动“自毁长城”,发起了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苏联解体本质上是改革初期获益的党国精英主动放弃社会主义,转而拥抱资本权力的革命。③ 外部视角的代表性作品包括美国学者科兹和威尔的《来自上层的革命》、霍夫的《苏联的民主化与革命:1985—1991》等。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Jerry F.Hough,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1985-1991 ,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
2014 年和2017 年,两部讲述苏联解体的作品被相继迻译到中文学界,分别是祖博克的《失败的帝国》(A Failed Empire ,2009)和浦洛基的《大国的崩溃》(The Last Empire ,2014)。两位作者出生于苏联并在苏联接受高等教育,苏联解体后相继移民美国。现在,祖博克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冷战史和俄国史,浦洛基在哈佛大学教授乌克兰史。两部作品虽然以英文出版并以西方读者为主要受众,但是无疑告别了同主题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大国的崩溃》不再将苏联解体视为西方冷战的胜利,而是指出:苏联解体根本是一件违背美国最初意愿的事。① 〔美〕沙希利•浦洛基:《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第370 页。 《失败的帝国》也认为,美国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充满误判。② 〔美〕弗拉基米尔•祖博克:《失败的帝国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475 页。 两部作品都自称表达了一种苏联视角的历史叙事,可视为延续了内部视角的解释。新颖之处在于,两部作品不再深陷于苏联的体制泥潭,而是用更具理论性的角度对苏联及其解体提供新的解读。这一角度可以概括为“革命与帝国”。
二
《失败的帝国》作者祖博克明确指出他多年以来一直采用“革命与帝国”的范式来理解苏联问题。③ 同上,英文版序(二),第19 页。 基于对关键人物个人因素的关注,他提供的范式是一种观察和评价决策者思想和行为的基本框架。通过这一框架,可以从帝国和革命两个角度,也即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角度,去观察和评价苏联决策者的思想和行为,并借此理解苏联命运的走向。
具体而言,苏联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祖博克认为,斯大林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建立与西方对抗的帝国,是受到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理论的影响。① 〔美〕弗拉基米尔• 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第26 页。 世界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论断。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世界革命,不会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② 〔德〕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21 页。 但祖博克又指出,斯大林并非世界革命理论的忠实信徒,而是将意识形态发展为“一个不断演变的混合物”,融合了国内斗争经验和国际政治需要。③ 〔美〕弗拉基米尔• 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第27 页。 如何理解祖博克看似矛盾的表述呢?祖博克没有讨论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理论的决裂,也没有讨论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对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从经典的世界革命论,到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再到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存在明显的理论变迁。④ 关于这一理论变迁,国内学者有详细的研究综述。参见王久高:《近十年来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综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 年第3 期。 列宁将社会主义革命划分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两个部分:政治革命的部分,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可以在一国实现胜利;但是社会革命的部分,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必须在全世界完成。斯大林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也可以在一国完成,无需等待无产阶级普遍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夺取政权。祖博克论述中的矛盾可以如此化解,即斯大林事实上发展了构成苏联意识形态的两套革命理论:对内的革命,以帝国认同为目标的特殊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对外的革命,以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为目标的普世主义的“世界革命”。
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记录在《失败的帝国》中只占了一章,这无疑让关心苏联解体具体过程的读者意犹未尽。祖博克显然试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中揭示苏联一步步走向失败的前因后果,并呈现为一部恢宏史诗,一部《罗马盛衰原因论》那样的作品。这是祖博克的不足所在,为了展现一个宏阔视野下的历史必然性,忽视了较短的时间片段中人物互动和偶发事件的影响。这些影响伴随着混沌性和偶然性,构成了对宏阔的历史必然性的挑战或调整。幸运的是,浦洛基《大国的崩溃》恰恰可以视为对《失败的帝国》的补充。如果说《失败的帝国》是一部跨越四十余年的史诗,那么《大国的崩溃》就是一部跨度只有五个月的纪实文学作品。在苏联解体的最后五个月里,复杂的人物交互和层叠的突发事件不断推动着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左右摇摆。高密度的叙事很容易让不熟悉这段历史和相关人物的读者产生疏远感。但是正如蕾切尔•波隆斯基评论的:这是一部“大戏”,表现了“主要演员的选择、忧惧、个人冲突和地缘政治的虚妄”。② 〔美〕沙希利• 浦洛基著:《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封面。 只有一口气欣赏完这部“大戏”,才会发现《大国的崩溃》分享了《失败的帝国》提出的理解苏联的基本视角——“革命与帝国”。带着这一视角回顾整部“大戏”,我们将从不可捉摸的混沌性和偶然性中走出,重新接纳那宏阔必然性中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虽然两部作品在形式上极为不同,但是从论述角度的共通性出发,我们可以将《大国的崩溃》和《失败的帝国》视为相互补充的作品,甚至将前者视为后者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细描。也可以说,《大国的崩溃》以一种更精细的论证,补足了《失败的帝国》中提出的抛弃“革命与帝国”与苏联最后解体之间的逻辑关联。
为了提高立体车库的运行效率,用户停车时间和停放车辆的位置到出入口的距离应具有如下关系:停车时间长的车辆,应存放到远离出入口的位置,周转时间短的车辆存放到离出入口近的地方。如此便能得出模糊规则,如表1所示。
在对厦门市实施可持续发展策略的过程中,首先应通过资源调查确定厦门市旅游资源的承载力以及资源的自身优势,进而保障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实施。[1]
《大国的崩溃》首先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苏联?浦洛基提醒我们,苏联和俄罗斯不能画等号,俄罗斯只是苏联的15 个形式上平等的加盟共和国之一,这些加盟共和国是以自治和独立的民族性为特征的。换言之,苏联并不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古典色彩的帝国。浦洛基将苏联视为沙皇俄国的直接延续,并视为“最后一个在现代实行古典欧洲和欧亚帝国制度的国家”。③ 同上,序言版,第5 页。 按照这一逻辑,苏联的解体就不是十月革命后那个新兴社会主义政体的倾覆,而是推迟近一个世纪的沙皇俄国的最后瓦解。浦洛基无疑提醒我们,祖博克对“帝国”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非只有谋求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苏联才是帝国,苏联本身就是帝国。从历史上帝国形成的角度看,沙皇俄国恰恰是15 世纪蒙古人的金帐汗国溃败之后,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俄罗斯民族不断扩张、征服和吸纳周边民族的结果。① 〔美〕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78 年版,第25 页。 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疆域和民族构成,也继承了帝国的属性。因此,作为扩张继承者的苏联和继续扩张势力范围的苏联,无疑表达了同样的帝国基因。多民族疆域的维持,地缘政治的扩张,都是帝国的应有之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可以放弃苏联的全球扩张,可以在军备竞赛上和美国取得彻底和解,但依然没有办法改变苏联是帝国的事实。浦洛基于是调侃道:“戈尔巴乔夫没有想过他生在一个帝国,并能统治这个帝国。”② 〔美〕沙希利• 浦洛基著:《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第363 页。
“革命与帝国”构成了贯穿《失败的帝国》全书的线索,这一线索在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等主要领导者身上的不同呈现暗示了苏联命运不可避免的走向。斯大林无疑是“革命与帝国”的创造者,面对西方发起的冷战攻势,斯大林带领苏联走向了一条兼重地缘扩张和革命输出的道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被祖博克称为“老近卫兵”:他们是斯大林“帝国与革命”的继承者,尽管未必忠实。在意识形态上,赫鲁晓夫继任后立即全盘否定斯大林主义,并实施文化解冻政策,引入西方的思想和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正如祖博克指出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依然被作为对美式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在全球推销。基于快速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赫鲁晓夫在帝国扩张上比斯大林迈得更远,他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支持建立起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政权。继任者勃涅日列夫接手了更为强大的帝国,却不得不面临更为衰落的革命。苏联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更为薄弱了,在更为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眼里苏联无疑堕落为修正主义国家,革命意识形态已经不足以为苏联扩张提供合法性基础。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大规模地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试图以军事上的优势扭转意识形态上的劣势。此时我们已经看到了革命与帝国的分离:失去革命话语的帝国陷入了赤裸裸的利益和权力的陷阱。随着“老近卫兵”的谢幕,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作为“革命与帝国”的背叛者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如果说勃涅日列夫是逐渐放弃了“革命”,那么戈尔巴乔夫则是连“帝国”也一并丢弃了,并以“新思维”取而代之。在祖博克看来,“新思维”无疑是一个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梦想。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每一步都在远离“革命与帝国”,都在抛弃苏联赖以存在的基础。祖博克不无黑色幽默地调侃道:“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也许是现代历史上最奇怪的帝国——并没有奋起还击,而是选择了自尽。”① 〔美〕弗拉基米尔• 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第476 页。
三
何谓帝国?祖博克眼中的帝国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扩张。对苏联而言,帝国存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意味着在区域内满足自身安全和生存需要。通过占领德国、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二战后的苏联首先建立了一个隔离西方对手的战略缓冲区。第二个阶段则意味着地缘支配由区域扩展到全球。④ 同上,第84 页,第466—467 页。 20 世纪70 年代后的苏联在中东、非洲、南美急剧扩展势力范围,并同美国展开全球范围的军备竞赛和霸权竞争。帝国的两个阶段虽然具有范围的差异,但扩张的本质并无区别。祖博克提醒我们注意,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苏联正处于千疮百孔和百业凋敝的时期,很难想象决策者会不顾国内恢复和发展的需要而谋求建立与西方对抗的帝国。为此,要理解二战后苏联的行动还必须引入革命的视角。
完整地理解“革命与帝国”,我们还应该避免这样的认识:革命是“虚”的,是话语,帝国是“实”的,是实践。革命或意识形态有其“实”的一面,意识形态不仅解释世界,还要求人们“采取明确的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也即“改造世界”。⑤ 〔美〕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张慧芝、张露璐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 年版,第6 页。 同时,帝国或扩张也有其“虚”的一面,帝国意味着对西方强硬的态度,是政治上取得强势地位和获得精英阶层支持的条件。如果谁在帝国问题上态度软弱,“那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⑥ 〔美〕弗拉基米尔• 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第133 页。 在此意义上,革命和帝国都分别有话语、实践两种含义,“革命与帝国”也必然包含着话语与实践。
既然苏联是一个帝国,那什么是苏联解体?浦洛基认为“八一九”政变后的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是两回事,民主运动、经济下滑、军备竞赛并非苏联解体的根源,“帝国的根基、多民族构成以及苏联的伪同盟结构才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③ 同上,序言,第4 页。 在浦洛基看来,苏联解体的命运是最后4 个月决定的。占苏联71%的人口、提供苏联主要税收来源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放弃了联合,才导致苏联的解体。在此叙事中,乌克兰议长克拉夫丘克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才是决定苏联命运的关键人物。1991 年6 月12 日,叶利钦赢得俄罗斯总统竞选,当即承诺加强俄罗斯主权,他被称为“民族构建者”,在与“帝国拯救者”的斗争中获得胜利。④ 同上,第37 页。 1991 年8 月24 日,克拉夫丘克迎合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诉求,代表乌克兰议会宣读了《乌克兰独立宣言》。⑤ 同上,第157 页。 这两起事件对苏联的最终命运具有转折点的意味。当两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斩断与帝国的关联,苏联剩下的部分已经难以维系。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治理一个帝国,叶利钦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放弃了帝国,克拉夫丘克在民族主义的鼓动下脱离了帝国。他们共同埋葬了苏联。或许索尔仁尼琴道出了部分真相:“我们无力承担一个帝国!——而且也没有必要,我们应该将其抛弃,因为它使我们不堪重负、民穷财尽、加速毁灭。”⑥ 〔俄〕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1 页。
何谓革命?祖博克是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理解革命的。对苏联而言,革命就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在“革命和帝国”的视角下,苏联呈现出“社会主义帝国”的复合特征。⑤ 在中苏关系破裂时期,国内曾将苏联视为“社会帝国主义”;祖博克所谓的“社会主义帝国”是一种不带明显意识形态偏见的概括,应该予以区别。 相应地,冷战则呈现出了两种维度的交锋:武力和资源的竞争,以及意识形态的竞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在冷战中加入苏联一方还是美国一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所能提供的意识形态与本国需要的契合程度。苏联和美国提供的两种意识形态绝非代表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毋宁说,二者都是现代性的产物。正如浦洛基的精辟概括:美国和苏联或许根本就是两个“现代性”的“远房表兄弟”,它们只是在争夺谁能更好地代表现代化和全球化道路而已。⑥ 〔美〕弗拉基米尔• 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第475 页。
浦洛基同样揭示了革命对苏联命运的影响。他提示我们,苏联解体的根源已经蕴含在苏联宪法之中,这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革命意识形态鲜明地体现在激进的民族政策上。在沙皇俄国,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之间并不平等,非俄罗斯各民族之间也不平等,比如波罗的海日耳曼人、波兰人和芬兰人享受了极高的自治,而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以农民为主的斯拉夫民族则受到歧视。俄国革命在民族平等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4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联盟,并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同时还规定,各民族公民一律平等。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平等和“自由退出权”无疑具有激进性。这种激进来自对沙皇俄国不平等民族政策的矫正,更来自世界革命的平等观念,和以阶级性取代民族性的革命浪漫主义。在实践中,为了遏制俄罗斯民族的沙文主义,列宁甚至采取“逆向歧视”的政策,给予非俄罗斯民族许多特权并推进少数民族的“本土化”。① 〔俄〕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56 页。 在浦洛基看来,西方决策者普遍忽视了一个事实:“苏联领导人无法在宪法上对各加盟共和国作出区别。”② 〔美〕沙希利•浦洛基:《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第369 页。 这些加盟共和国无论是大如俄罗斯还是小如摩尔多瓦,它们在宪法上都是平等的,并且有权自由退出苏联。虽然在60 年的时间里,激进的“退出条款”从未被“激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条款“无效”。在浦洛基看来,正是苏联宪法中的“退出条款”给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在苏共有效统治之下,这一隐患并不明显。但当戈尔巴乔夫将民主选举引入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一种新的民主合法性便被激活并拥抱民族主义,与旧的党国体制的合法性产生了竞争。民族主义者重新发现苏联宪法,并启动了“退出条款”中潜藏的“革命”。1991 年9 月6 日,苏联议会在西方压力下被迫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独立。从法理上说,这等于激活了宪法中的“退出条款”,并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既然15 个加盟共和国的主权都是平等的,那么其他12个加盟共和国自然有平等的脱离联盟的权利。普京眼中“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由此发生,苏联帝国以让人目眩的速度解体为15 个民族国家。12 月8 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在白俄罗斯签订了《别洛韦日协议》,并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虽然此时距离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演说还有17 天,距离苏联形式上的解体还有23 天。
苏联的悲剧性命运提醒我们,革命与帝国是具有内在矛盾性的。革命的普世性和平等性不断挑战着帝国的特殊性和不平等性。但是帝国的维系和扩张又离不开革命,因为革命代表着一种整合帝国的精神力量,给帝国的精英和人民提供了集体认同的核心价值,给帝国的内外行动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在上述矛盾之下,帝国或者被革命消解,或者因为抛弃了革命而瓦解。也许冥冥中的命运就是:帝国终将逝去,而革命永存。
虽然颈部推拿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推拿手法集中在旋转过伸和颈部扳法,提示发生不良事件多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推拿治疗相关,且尚未对一些相对轻柔的微调手法(牵拉和按揉等)做出安全性研究,是否会影响颈部斑块稳定性、斑块大小等尚不明确。
最后要指出,“革命与帝国”既放弃对“帝国”常见的意识形态抨击,也打破对“革命”通常的浪漫美化。当我们将苏联纳入“帝国”概念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语词背后的古典含义或冷战语境。西方冷战语境中的“帝国”是一个明显带有贬义的指称,与社会主义阵营经常援引自列宁的“帝国主义”犹如针尖对麦芒。如果能从较少意识形态的角度,而是从政体实际构成与运作方式的角度看待“帝国”,我们或许能接近一种更为公允的认识。③ 冷战以后,西方的历史研究者开始注重从古典帝国的研究中为当代困境寻求经验,并尝试着给帝国下新的更具普遍性的定义,关于苏联帝国的代表性研究如多米尼克•利芬的《帝国》,see Dominic Lieven,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对于“革命”,也是一样。
The Dialectics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The Soviet Dissolution Revisited
Wu Biyu
Abstract: Two books by American intellectuals-Vladislav Zubok’s A Failed Empire and Serhii Plokhy’s The Last Empire-offer a new perspective in understand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demise:revolution and empire.These authors see the USSR first and foremost as an empire,due to its geopolitical expansion and multiethnic territories.They also see it as a revolution or an ideology that included both exceptionalist and universalist dimensions such as“socialism in one country”and“world revolution”.The dialectics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 run through the lifespan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set of narratives and practices with inherent contradictions.The period from Stalin to Brezhnev can be understood as a history of receding revolution and expanding empire.Having lost its legitimacy and appeal,the empire without revolution was eventually forsaken by Gorbachev,Yeltsin,and Kravchuk.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s essentially the falling of an empire into nation-states.The seeds of destruction had long been plan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constitution of the USSR.
Keywords: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revolution,empire,ideology,nation-state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