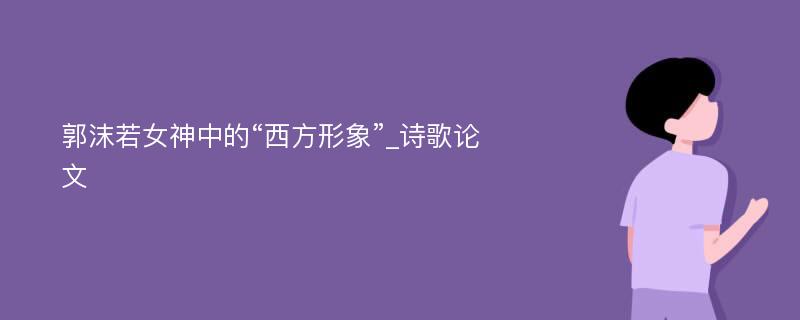
郭沫若《女神》中的“西方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女神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1)06-0110-05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有一个长期以来不为研究者所置重的现象,即它以大量的“西方意象”,有意无意间“塑造”出一个异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过程,是诗人发抒胸中郁积、反思中国古旧文化、想象民族未来的过程,是觉醒的个体言说西方文化的过程,是一种宣泄,一种呐喊,一种建构。经由“西方形象”,《女神》与民族古典诗歌及同时代诗歌区别开来,别具风骨。
一
意象是诗歌形象构成的基本元素,《女神》中的“西方形象”由大量的“西方意象”组构融合而成。本文所谓的“西方意象”主要是指作品中所使用的体现西方文化的意象,它们是西方社会历史与现实、此岸与彼岸、经验与超验世界的存在物,是意与象相融合的西方文明的承载者。从所指层面看,《女神》中的“西方意象”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各有特色,相互融通,形成新的文本意蕴与情感空间。
一是西方拼音文字意象。对于习惯于汉字的中国读者来说,西方拼音字母、单词、语句等,不仅陌生,而且奇异,它们不只是意味着一种书写文字的差异,不只是犹如衣着、服饰代表着外在装扮的不同,而且体现为一种由表及里的陌生文化形象。《女神》中许多诗歌夹杂着西方拼音文字,构成一种特殊的意象群。
第一辑的第一首诗即《女神之再生》一开篇就引录了德国诗人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结尾的诗句:“Alles Vergaengliche/ist nur ein Gleichnis;/das Unzulaengliche,/hier wird's Ereignis;/das Unbeschreibliche/hier ist's getan;/das Ewigweibliche/zieht uns hinan.——Goethe”诗人将最后两句译为“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① 它是这些诗句的灵魂,是诗人旨意所在,也是巧妙连接《浮士德》与中国上古女娲神话的纽带;换言之,诗人找到了中西文化深处女性崇拜意识交互融汇的契合点,而那些西文诗句给人以视觉冲力,一种别样的文字画面扑面而来。
《胜利的死》是一首并不为多数研究者所关注的诗歌,然而诗人却很看重,专门为它写了“引言”和“附白”,《女神》中享受这种待遇的作品少之又少。该诗共四节,每节均以苏格兰诗人康沫尔《哀波兰》中的原文诗句开篇,第一节前的英文诗是“Oh! once again to Freedom's cause return,/The patriot Tell-the Bruce of Bannockburn”;第二节前的是“Hope,for a season,bade the world farewell,/And Freedom shrieked——as Kosciuszko fell”;第三节前的是“Oh! sacred Truth! thy triumph ceased a while,/And Hope,thy sister,ceased with thee to smile”;第四节前的是“Truth shall restore the light bv Nature given,/And,like Prometheus,bring the fire of Heaven!”诗人不仅借以铺排、歌颂了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党员马克司威尼“胜利的死”,而且作为一种整体的“英文诗句意象”,以一种新的诗境空间承载、认同与赞美了现代西方不死的“自由”精神。
《无烟煤》第一节诗句,是司汤达(Stendhal)1834年“被任为驻罗马教廷辖区契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现属意大利)领事时致狄·费奥尔(di Fiore)信中的话”②,即:“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虽为中文译文,但与别的诗歌中的西文语句构成互动生成关系,丰富了作为整体的“西文”意象。
《女神》中还有很多作品里出现了西方拼音意象,如“Enengy”、“X”、“Pioneer”、“Pantheon”、“symphony”、“Open-secret”、“Hero-poet”、“Proletarian poet”、“soprano”、“Disillusion”、“unschoeh”等等,它们展示的是一种西方文化存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取向。这些单个的西方拼音意象与前述西文诗句在诗集中交相辉映,形成西方拼音文字意象群,使《女神》在文字视觉层面具有一种西方性。
二是西方文化先驱者意象。《女神》诗集中,西方不同领域的名人成为抒情言志的重要意象。例如:“政治革命的匪徒们”——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等,“社会革命的匪徒们”——罗素、哥尔栋、列宁等③,“宗教革命的匪徒们”——释迦牟尼、马丁路德、耶稣等,“学说革命的匪徒们”——哥白尼、达尔文、尼采、Spinoza等,“文艺革命的匪徒们”——罗丹、惠特曼、托尔斯泰、歌德、拜伦、Thomas Campbell、Stendhal、贝多芬、Carlyle、Millet、Mendelssohn、Brahms等,“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卢梭、丕时大罗启等。他们是欧美历史上反叛、变革与创新的先驱,是西方天际闪烁的星星,是人类文明的推进者,构成诗歌中特别的意象群。
三是文化先驱者之外其他文化标签性意象。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存在物象,它们相当程度上构成欧美文化的重要标签,看到或听到它们,西方历史与现实场景就会立刻浮现眼前。《女神》中的这类意象,有的属于神话传说,如亚坡罗(Apollo)、Cupid、司健康的女神、司春的女神、普罗美修士、Venus、Bacchus、Poseidon等;有的属于宗教范畴,如圣母、耶稣、礼拜堂等;有的是近现代文明产物,如摩托车、Energy、X光线、电气、电灯、轮船、半工半读团、太阳系等;有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如图书馆、法庭、Violin、Piano、哈牟尼笳等;有的是历史现象,如新芬党、爱尔兰独立军、黑奴、俄罗斯的巨炮、交响乐等;有的则是抽象的思想概念,如德谟克拉西、泛神论、“大宇宙意志”、“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社会改造”、“返自然”、密桑索罗普等;有的属于艺术品如“沉思者”、抱破瓶的少女、《牧羊少女》、《The Hero as Poet》、《仲夏夜的梦》、《永远的爱》、《哀波兰》、《哀希腊》等等。它们凭依诗人的想象力,穿越时空,闪烁在《女神》那浩瀚而繁复的天际,蕴涵情感,彰显文明,创造诗意。
四是西方民族国家、地域名称意象。在《女神》中,诗人还有意识地反复书写欧美民族国家、城市乃至更小的地方名称,如英格兰、爱尔兰、比利时、荷兰、俄罗斯、大西洋、加里弗尼亚州、伦敦、可尔克市、剥里克士通监狱等等。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意象群落,营造出一种世界性抒情场景;不仅如此,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与人文地理符码,一种世界意识的体现,经由它们诗人将读者视线由东方引向西方,拉近了国人与欧美世界的距离,或者说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将中国纳入世界知识文化体系,以逐渐改变国人的宇宙观念,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不同类型的西方性意象群,经由诗人的艺术组结、融汇,生成出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意境,这是《女神》的重要特征。
二
“写什么”固然重要,但“如何写”对于意义生成则更为关键。郭沫若留学日本,他曾说那时“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④ 西洋书籍为他提供了关于欧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诸种知识,扩展了他思考、书写的地理场景与人文背景,影响了他的文化价值取向,丰富了其想象空间,使他逐渐形成新的思想逻辑与言说方式。那么,在《女神》中,他究竟是以怎样的情感和文化立场观察、取舍“西方”?以怎样的语态与方式言说“西方”呢?
一、以比较的方式取舍、言说“西方”。《胜利的死》最初刊登于1920年11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诗中言说了两个“西方”,一个是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党员马克司威尼和苏格兰诗人康沫尔以及拜伦等为代表的“西方”。新芬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于1905年,主张爱尔兰独立,马克司威尼(1879-1920)作为新芬党员积极从事爱尔兰独立运动,曾多次被英国政府逮捕,1920年他在监狱中与英政府进行不屈的斗争,绝食73天后逝世。在郭沫若看来,马克司威尼虽肉体寂灭了,但精神不死,如诗所言“‘自由’从此不死了”。康沫尔(1777-1844)是苏格兰诗人,惠助波兰,22岁时创作《哀波兰》,《胜利的死》不仅每节开头引用该诗诗句,而且“附白”中认为它“可与拜伦的《哀希腊》一诗并读”。拜伦援助希腊独立,其精神早已化为西方民族独立自由的传统。《胜利的死》还写到为马克司威尼祈祷的爱尔兰儿童等等。在诗中,马克司威尼、康沫尔、拜伦等“是自由神的化身”,他们共同构建出一个以自由为价值诉求的西方形象。另一个则是将马克司威尼投向监狱的英政府所代表的“西方”。在诗人看来,英政府导演了“有史以来罕曾有的哀烈的惨死呀!”奸污了自由之神。面对如此的情景,诗人不禁吟道:“冷酷如铁的英人们呀!你们的血管之中早没有拜伦、康沫尔的血液循环了吗?”“汪洋的大海正在唱着他悲壮的哀歌,/穹窿无际的青天已经哭红了他的脸面,/远远的西方,太阳沉没了!”这是一个太阳沉没了的“西方”,一个戕害自由精神的专制的“西方”,一个如同诗人在《凤凰涅槃》中所言的“西方同是一座屠场”的“阴秽的世界”。该诗以对比的方式取舍、言说出两个对立的“西方”,在诅咒冷酷如铁的英政府所代表的专制主义“西方”的同时,赞美了张扬自由精神的“西方”:“自由的战士,马克司威尼,你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的权威如此伟大!/我感谢你呀!赞美你呀!‘自由’从此不死了!/夜幕闭了后的月轮哟!何等光明呀……”这是该诗的诗思逻辑。
《西湖纪游·沪杭车中》初刊于1921年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以抒情主人公“我”的视角,在对比中表现了沪杭车中的“西人”、“同胞们”和“东人”。“西人”“肃静”,且“一心在勘校原稿”,认真地工作;自己的同胞则是另一番情景,“你们有的只拼命赌钱,/有的只拼命吸烟,/有的连倾啤酒几杯,/有的连翻番菜几盘,/有的只顾酣笑,/有的只顾乱谈”;再看“东人”,也就是日本人,他们“骄慢”地在“一旁嗤笑”中国人。诗人作为清醒的观察者,看到如此反差的情形,眼睛要被“泪泉涨破了”,几乎撕心裂肺地哀叹:“我怪可怜的同胞们哟!”这是又一种“对比”书写方式,它已经不是简单的言说修辞,而是体现了诗人忧患的民族情感和对“西人”生存方式和价值理念的认同。
二、将赞美“西方”与挖掘民族文化精义融为一体。在郭沫若看来,《胜利的死》中的马克司威尼代表了“人类意志”,而这种“人类意志”在古代中国早已有之:“爱尔兰独立军的领袖马克司威尼,/投在英格兰,剥里克士通监狱中已经五十余日了,/入狱以来耻不食英粟”。这里的“耻不食英粟”就是化用中国古代伯夷、叔齐耻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典故。马克司威尼在监狱绝食而死后,诗歌再一次歌吟道:“——啊!有史以来罕曾有的哀烈的惨死呀!/爱尔兰的首阳山!爱尔兰的伯夷,叔齐哟!”显然,此时的诗人并没有因为赞美崇尚自由的“西方”而贬抑中国文化,而是相反,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独立自由的精神,或者说对马克司威尼所代表的“西方”的歌吟,就是对中国文化精髓的发掘与赞美。
《女神之再生》表现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女娲的再生。她曾补天以匡正世界,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人类景仰的女神;然而在“浩劫要再”的今天,她却不愿再在壁龛中做偶像,而是毅然决定去创造“新的光明”、“新的温热”,去创造“新鲜的太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为歌颂女娲,一开篇即引用了西方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结尾处的原文诗歌,并将中文译文并置于右边,推入读者眼帘,而该诗的诗心是“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郭沫若在有意无意间接通了中国古代女娲神话与西方长篇诗剧,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关于女娲神话的叙述习惯,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表述西方文化的一种方式,即以西方文化精髓印证、支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发掘,以西方文化思想作为开掘中国故旧文化的话语依据,“西方意象”也由此在中国话语场景中获得了意义,其中潜隐着作者那时不仅看重西方思想而且尊重中国古人智慧的文化心理。
1920年初所作的《晨安》一诗,展示了一种超越性的宇宙视野与世界胸襟。诗人不仅向大海、白云、山峰、旷野、晨风道一声“晨安”,不仅向祖国、同胞、扬子江、黄河问好,不仅向印度洋、红海、苏彝士运河、金字塔道一声“晨安”,而且将视线转向西方,向俄罗斯、爱尔兰、比利时、大西洋畔的新大陆问好,向达芬奇、“沉思者”、华盛顿、林肯、惠特曼道一声“晨安”,“我所畏敬的Pioneer呀!”一句表现了诗人的“畏敬”心境。他将西方文化先驱者视为永恒的江河海洋、高山大川,向他们由衷地表达“畏敬”之情。在诗中,“西方”与“东方”融为一体,没有高下之分,而诗人则作为更有力量者,向他们发抒情感,体现了那时诗人的文化观、自我观,也是《女神》言说“西方”的一种方式。
三、以认同的立场、赞美的口吻和张扬的语气言说“西方”。在《无烟煤》中,诗人以一种钦慕语态引用司汤达的话语——“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之所以将之译为母语,显然意在表达对司汤达“新思潮”的认同;“Stendhal哟!/Henri Beyle哟!/你这句警策的名言,/便是我今天装进了脑的无烟煤了!”这种不自禁的感叹沟通了西语意象与自我心绪。钦慕、感叹与认同是该诗言说“西方意象”的特点。在《天狗》中,诗人写道:“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借西方现代文明意象的力量,张扬自我精神。亚波罗(Apollo)乃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诗人在《日出》中写道:“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你二十世纪底亚坡罗!/你也改乘了摩托车吗?/我想做个你的助手,你肯同意吗?”以“亚波罗”比喻“摩托车”,表现了诗人对西方文化源头之神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崇仰,崇仰即是一种书写立场与心态。
《匪徒颂》中,西方文化意象繁复,但诗人不是冷静地排列、并置它们,也主要不是如同中国古诗那样让意象在自呈中显现意义,而是以激越的情感颂赞它们。在诗歌正文前面的“引子”里,抒情主人公曰:“小区区非圣非神,一介‘学匪’,只好将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来赞美一番吧。”面对古今中外的“匪徒们”,他的态度相当谦恭,这在《女神》中少见,而那些古今中外的“匪徒”,除了菲律宾的黎塞尔、印度的释迦牟尼、泰戈尔和中国的墨子之外,全都是西方文化巨子,是西方文化史上的标签性人物,如克伦威尔、华盛顿、罗素、列宁、马丁路德、哥白尼、达尔文、尼采、罗丹、惠特曼、托尔斯泰、卢梭和丕时大罗启等,这些标签性人物大都以自己的学说、理论、思想、艺术或革命行为助推了西方历史的转型,在人类社会由黑暗向光明、由愚昧向文明、由专制向民主的演变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文化史上,选取所谓的“匪徒”而不是帝王将相加以赞美,在“匪徒”中又主要选取西方那些推进历史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离经叛道者,对他们谦恭地表达敬意,发出由衷的赞美,这就是一种文化取舍,一种价值立场,一种言说方式。换言之,诗人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认同,致使其作品不可能如同中国传统诗歌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那样铺陈意象,而只能以一种“赞美”的方式,一种极度张扬的语态,疾风暴雨式地宣泄认同之情。
三
郭沫若留学日本,对西方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与体验,他对西方的了解主要来自课堂,来自西方书籍,这一经历限制规约了他对西方的言说,致使《女神》中的“西方形象”具有书本性,是诗人关于西方的间接知识的表现。
那些生成“西方形象”的意象来自书本。如前所述,它们要么是西方拼音文字,一种不同于中国象形文字的书写符号,其本身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是记忆的书面化表现形式;要么是西方文化源头神话所记载的诸神,如亚坡罗、Cupid、司健康的女神、司春的女神、普罗美修士、Venus等,它们是西方早期人类想象力的反映,被多少个世纪的人们所讲述、传承与再创造,寄托着西方社会共同的理想与情怀;要么是西方文明演进史上不同领域的变革者、发明者与创造者,诸如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马克司威尼、列宁、惠特曼、罗素、哥白尼、达尔文、尼采等,他们是与超验世界相对照的真实西方历史的创造者、体现者;要么是地名、国名,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它们陌生而神秘,曾经颠覆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世界观念,它们虽为自然地理存在,却为“非我族类”所居,意味着一种“他者”文化;要么是别的突出彰显欧美文化的标签性符号。所有这些西方性意象,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书本知识,一种文化符号,并非日常生活里客观存在的可以触摸的事物,不具备日常性、世俗性与鲜活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缺失文本意义。诗人几乎在诗集的每首诗中点缀甚或铺排这类单词语码,使西方文化气息在整个诗集里萦绕,那些意象随着读者的阅读接受汇为特别的“西方形象”,展示出西方文化的某些轮廓。可以说,《女神》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通过这些意象锻造出自己的形貌,从而与传统诗歌区别开来。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核心意象,要么是小桥流水、秋风茅舍,要么枯藤古树、凄风苦雨。要么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要么晨钟暮鼓、金戈铁马,要么芭蕉夜雨、寒江渔翁,要么梨花啼鸟、长天大雁,要么布谷杜鹃、荷花牧童,要么月夜空山、清泉溪流,等等,它们是半开放型大河民族封建文明的基本物象,承载着传统社会的经验,传达的是农耕社会读书人的情感,塑造的是古代中国文化的形象;而《女神》中那些“西方意象”,主要是西方社会进化的结晶,承载的是西方历史故事,传达的是西方智慧与经验,它们大量进入作品后丰富了中国诗歌的意象谱系,拓展了中国诗歌情感表达的空间,使《女神》所展示的画面相比于中国旧式诗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些画面所承载的思想意蕴、价值结构也随之不同,所包含的经验与情感变得别样而新鲜,也就是说,那些书本化的“西方意象”所构建的“西方形象”,使《女神》从外到内与中国旧诗区别开来,成为一种包含着西方近现代价值取向的作品,也就是传达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大量书本化的“西方意象”,在有意无意间所“塑造”出的异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形象”,是《女神》意义生成的重要途径。
对西方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与体验,不只是使诗人所运用的意象来自书本,使其“塑造”的“西方形象”具有书本性,而且影响了他对那些意象的“艺术安排”。如果说《女神》里的中国性意象多为诗人现实人生中的元素,诗人对它们有着深刻的理解与体认,不仅识其象,而且会其意,他们鲜活地跳荡在诗人的意识里,所以诗人让他们自己开口言说,自我呈现,如《女神之再生》中的女神,就自由地行走在文本世界里不断地声称“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即便是共工、颛顼、牧童等也具有自我行动的力量,也是以第一人称言说、张扬自我。与之相比,诗歌中那些西方神或人,尽管他们原本具有超凡的力量与智慧,但由于诗人对他们缺乏深刻的了解,更没有一种“相濡以沫”的体认,他们来自书本,是一种间接知识,一种概念化存在,所以诗人没有办法让他们真实地站立起来,没有赋予他们以真实的生命,没有让他们直接开口言说,他们只是充当了抒情主人公言说、倾诉与赞美的对象,例如在《晨安》中,诗人深情地向“爱尔兰的诗人”、“华盛顿”、“惠特曼”、“林肯”等送去真诚的问候,不断地发出感叹——“啊啊!我所敬畏的俄罗斯呀!”“晨安!爱尔兰呀!爱尔兰的诗人呀!”“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他们是诗人感叹、歌吟的对象;在《电火光中》,诗人如此赞美贝多芬:“哦,贝多芬!贝多芬!/你解除了我无名的愁苦!/你蓬蓬的乱发如象奔流的海涛,/你高张的白领如象戴雪的山椒。/你如狮的额,如虎的眼。”“贝多芬哟!你可在倾听什么?/我好象听着你的symphony了!”诗人在尽情发抒情感的同时,不仅控制了诗歌的内在情绪、节奏,也控制了惠特曼、贝多芬、林肯等,他们在诗歌中没有自己的生活逻辑与行为力量,只是被动地存在于诗人的话语逻辑中,无法表现出超凡的力量与智慧,他们完全为诗人所掌控,所安排,成为诗人书写自我情怀的单词、语码,具有被言说性,碎片化地存在着。中国女神以第一人称方式表达对于当时社会的看法,以主体性姿态发抒自我意愿,要去创造新的世界,自主地创造着;而西方神、人虽为诗人所景仰、所赞美,但却没有自我表达的权利,只能概念化地存在于诗人的话语中,这种差异深刻地体现了诗人对于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令人玩味。
对“西方意象”这种特别的“艺术安排”,使《女神》对“西方形象”的“塑造”过程,成为诗人充分张扬自我主体性的重要环节。宣泄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是诗人创作《女神》主要的心理需求与动力,在宣泄过程中竭力为民族涅槃、新生而歌唱,在宣泄与歌唱的过程中,他引入了大量的具有超凡力量的西方神和体现西方现代文明的人,这些意象的出现颇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些西域意象,那《女神》的言说、抒情空间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下”视域,所使用的语词仍来自旧的谱系,其言说气势难以获得超越性。换言之,对那些他所崇仰的西方神、人等意象的掌控、安排,让他们仅仅成为诗人表达自我与价值认同的话语元素,让他们成为被动的倾听者、被赞美者,其客观效果是诗人高高在上,诗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尽情宣泄,获得了空前的主体性。
在宣泄与歌唱中,诗人充分地掌控着西方的神或人,他们被诗人“断章取义”,被诗人删减或增补,形象被改造,于是文本中所生成的“西方形象”,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性格逻辑,而是一个被充分郭沫若化的“西方形象”。
注释:
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后文所引《女神》中的诗句、语词意象皆出自该版本,如没有特别情况不再一一注释。
②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所收《无烟煤》一诗后面的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后文这类注释均出自该版本,不再一一注释。
③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所收的《匪徒颂》与1921年初版的《女神》略有不同,此处依据初版本,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第116页注释。
④ 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5月版,见《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标签:诗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女神论文; 郭沫若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艺术论文; 女神之再生论文; 浮士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