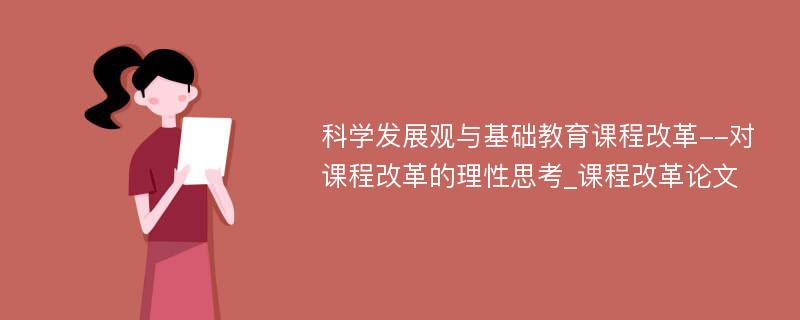
科学发展观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课程改革的理性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程改革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基础教育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关系全局的执政理念。被专家称为“第二代发展战略”[1]。是全局性战略方针,也是对当前各项工作的总体要求,而不单是一个经济方针。科学发展观要义在于:我们要用科学的头脑作指导,促使“发展”科学化。所谓科学化,第一,就是要承认发展的条件性、阶段性、客观制约性。不能搞只顾主观愿望,不顾客观条件的“拔苗助长”式的发展。第二,就是要承认发展的有序性、连续性、规律性。承认发展的历史背景,有来龙去脉,总是从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有序;从量变到质变,有规律的发展。新与旧总是相对的,生命总是从母体中孕育的,发展必然有继承,而继承必须发展。第三,就是要承认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发展总是互相关联的,互相协调的。平衡的打破总是暂时的,打破平衡是为了新的协调。不协调的发展,不可能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一是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二是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平衡。”[2] 第四,人是发展的根本。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是为了人,有了人才能发展。新课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所以发展必须以人为本。
二、以科学发展观反思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给了我们重要启迪,使我们发现近几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新课程改革忽视发展的客观制约性、理论准备不充分,观念不和谐,导致改革出现“强制性”,缺少“自觉性”[3]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教育“转变观念”。可是新课改只有教学论的简单解释,没有教育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论证。教学论只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只有教学论的解读是远远不够的。创新的课程改革,必须以创新的教育学,相应的心理学、哲学作先导,给予系统的、全面的阐释。即必须以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作为理论基础。新课程改革的教学理论本身的正确性都尚待论证,就开始了推广。因此,人们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人们无法把握改革的方向和要求。于是改革失去学术基础,靠用行政命令,靠自上而下发文件强制推行。缺乏理论基础,必然导致理念的冲突与不和谐。表现如:
“整体人发展”的新观念。这是新课改要求树立的核心观念,要求新课程的教学追求“个体、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4]。但是,这与“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观念相冲突。“全面发展观”是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论证的,是教育界普遍认可的,是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个体、自然、社会……整体人发展”观,则是需要说明的。
“以学生为主体”的新观念。新课改要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教师要当“催化剂”。这与“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观念相冲突。但是,学生主体论在当代是否合理则是需要说明的。“儿童中心主义”十九世纪就流行过了。那时有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经验自然主义哲学作基础,即使这样,到了20世纪60年代还遭到了抛弃。今天的学生主体论新在哪里呢?与“儿童中心主义”有无区别呢?
“新型知识观”。新课改提出的“新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探索的行动或创造的过程”,知识不仅有“显性”,知识还有不可言传的“缄默的知识”,认为学习即“建构”。这就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知识观相冲突。反映论者认为:知识是人的认识,是“人”这个认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反映”。知识分感性和理性两个层次。人的真知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亦即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统一。认识必须通过实践,从感性到理性,又从理性到感性,才能发展。获取直接经验和获取间接经验同样重要。新课程知识观不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混淆认识过程与认识结果的界线;取消理性知识,看轻间接知识。他们说:“传统课程体系信奉客观主义的知识观,视知识为普遍的、外在的、供人掌握的真理。”这意味着“个人见解在给定的课程知识前没有意义”。这就否定了人类积累的“普遍性”知识,剩下的就只有个人的“体验”。他们只承认“个人因素”。例如:“知识客观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必然以牺牲个人知识因素为代价。”“建构”知识观来源于现象学的教学论,是否合理,是需要证明的。
此外还有“活动的伦理原则”,“知识的生存方式”,“个性化”,“回归生活”……等等似是而非的“新”观念,也都需要作系统的理论说明的,不是凭引证几句罗素、胡塞尔、杜威或后现代主义的只言片语就能解决问题的。不作系统论证,广大教师如何实施教学?
(二)无成功的实践作先导,急于求成,导致改革推行边缘化
新课程改革方案只是一个假说,一个设定,推广前是没有人完整实践过的。包括整体计划、教材、教学过程都没有拉通的、完整的实践样板。只有零星的“示范”,就迅速的在全国推广。再好的课程方案,没有至少一届学生的成功验证,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由于没有成功的实践作先导,于是,教师培训“概念化”。照葫芦画瓢,层层照本宣科,“培训”成了“传达文件”。第一线的教师感到茫然、困惑。“素质教育失真,课程改革作秀”,一方面应付检查,一方面追加补课。这就成了“边缘化”。
各级领导采取二重标准进行评价。一方面要求贯彻新方案,另一方面又要求提高升学率。对升学率,党政领导“高压”,教育部门“暗压”,学校行政“卡压”,社会家长“重压”。对课程改革,教育部门“拖”,学校“皮”,教师“衍”,社会家长“迷惑不解”[5]。一方面,高等学校招生要从考试中选拔,另一方面,新课程改革的教学又要淡化“甄别与选拔功能”。你替教师想想,他们怎么办?研究表明“教学评价难以展开”[6]。有学者指出:“课改面临的困境,即是现行教育实践与教育评价错位。”[7] 为什么会错位?为什么新的评价行不通?因为现行的价值观形成,有其深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根源。问题根本不在教师,也不在教育。
边缘化新课程标准,有一部分不具有操作性。如其中的“体验性目标”和“表现性目标”。由于很难操作,教师上课求其形式,要体验吗,那好,就搞全班讨论式、记者采访式、双方辩论式。语文课如此,科学课如此,综合实践课也是如此。教师们一边上新课程,一边又为难以向校长、家长交代而愁眉苦脸。
(三)以“生活为中心”的新课程与“学科中心”的现课程之间缺乏衔接,产生断裂,教师无所适从
新课程教学内容“以生活为中心”,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式要求“活动式”,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方式,不论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都是以批判学科课程的知识性为基础的。竭力渲染新课程与学科课程的对立。“可以说,以事实性知识的呈现为中心,还是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成了新与旧教材的分水岭。”“新教材的设计和呈现须要进行根本转变,就是走向以学习为中心……”“课程标准不再规定教材基本篇目,也不再规定各类课文比例……”“必须从教材作为‘事实性知识’的呈现形式这一传统观念中走出来,重新审视教材的内涵。”这里的“分水岭”、“根本转变”、“不规定”、“重新审视”所指向的,即现行中、小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新课程体系否定系统知识的价值,把“生活”与“知识”割裂和对立。由此必然引发许多问题:
第一,“知识”与“能力”能够截然分开吗?
现行的基础教育阶段所学的“知识”,其性质到底怎么估价?是否能用“客观化”、“事实性材料”或“信息性知识”就可以否定的?例如,乘法九九表、元素周期表,到底是知识,还是能力?是“反映”还是“建构”?印度洋海啸中,有一个小孩救了一百多游客的命。因为去旅游之前,他刚上了关于海啸知识的讲座课,有了海啸的知识。而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却难逃灭顶之灾,他们没有知识。有趣的是,当他们有了“体验”时命都没有了。“体验”性的与“反映”性的知识能截然分出谁优谁劣?如果抛弃了知识,能力又如何发展呢?
第二,儿童的年龄特征需不需要尊重?
基础教育是处于6、7岁至14、15岁这一阶段的儿童,他们的自我意识、自制力等方面都还处于发展中。小学还主要处于“他律阶段”,初中处于“他律”向“自律”过渡。新课程要求“自主”学习,自主到什么程度?怎么个自主法?思维也有阶段性。小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初中生的思维只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建构”性知识,怎么建?“协同教学、讨论教学、创意教学、探索教学”,听起来倒是满不错的,但对于中小学生,能做到何种程度?
第三,以“生活为中心”的“生活”是什么?
把彩票中奖的概率计算写进教材、搬进课堂,这是生活。那么,在光速、高能条件下,探索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就不是生活吗?探究夏天酿酒变黄,这是生活。那么,分析醇的高分子结构就不是生活吗?在高科技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代社会,生活能仅仅局限于个人感受到的直观范畴?还有,“上山下乡”、“进城打工”、“网吧上网”、“学工、学农、学军”、“搓麻将”算不算是生活。
第四,“综合”能够脱离“分析”吗?
新课程强调“综合”、“整合”。可是人类的认识规律告诉我们,只有分析,才能综合;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如果没有对一个事物的细部有所了解,又怎么能认识它的整体?现在的新课改,是在低年级强调综合,高年级才强调分析,走的是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相反的道路。综合和分析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方面。
以上这些问题,新课程并没有很好解决,因而,使实践中的教师们感到新课“难整”。
(四)新课程设置着眼于城市,要求高,与1080多万中小学教师参差不齐的水平和能力不相协调
有调查表明:“现在新课程设置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农村推行比较困难。”[7] 新课程改革实施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是教师。可是我国现在的普通中学教师502万,小学教师577万《中国教育年鉴》。其中真正符合学历要求的一半也没有。据2002年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农村教师严重缺编,城市超编50万,农村缺编40万。农村还存在大量代课教师。据调查,四川某县目前就有代课教师200多人, 约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十[8]。“新课程强调开放式学习,教材提供的学习材料是非常有限的”,新课程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自主生成”,要求学生在学习中“探究”、“发现”、“创新”。过高的要求与实现的能力不协调,要求就会落空。以初一语文课《羚羊木雕》为例。这一篇课文许多学校选为新课程的示范。调查中发现,即使在重点中学,是优秀教师,也上不好这篇课文。对课文中的价值观吃不透,不能“自主生成”。学生辩论始终围绕该不该把羚羊木雕送人,“亲情重”还是“友情重”争论。但是,无论亲情还是友情都不是课文揭示的价值,正确的价值观在于主人公的“人格”,即儿童“做人”的权利被否定了;儿童“自生的需要”被否定了。学生达不到,教师达不到,进入不了这一层次,新课改的价值目标就落空了。这样,素质教育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五)新课改忽视社会大环境的制约性,脱离高考升学和社会就业的迫切需求,家长很难认同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竞争激烈,家长送孩子上学,最直接、最迫切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而考大学的背后,是拿文凭就业。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改变高考凭分数选拔、升学的现实;另一方面,新课程改革又要淡化“选拔与甄别功能”。现实与愿望严重脱节。于是我们看到,新课程改革愈彻底的地方,家长们愈是忙着找教师给孩子补课。补的是“知识”而不是“生活”。所以有人说:“新课改加大了教育的两级分化,做成了一锅夹生饭。”[8] 实际上使一部分人更加片面发展。
三、从课程改革的发展错位,再反思主观头脑的非科学性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首先头脑要有科学性,其二是发展要有科学性;用科学的头脑,指导实践,科学地发展。从新课改的五大问题,证明教育发展偏离科学性。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头脑思维也偏离了科学性。其表现如下:
(一)思维模式是陈旧的,是小生产的、二元化的、平面的、线性的思维模式;而非现代多元化的、立体的、系统化的思维模式
从一些倡导新课程的学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十分熟悉的,非此即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二元化的思维。新课改有句响亮的口号叫“先立后破”。这与“先破后立”一样,都是在对立中进行思考,在否定中进行选择,非此即彼,不能调和,只能转变。接受新观念,就得连缺点也一起接受;放弃旧观念,就得连优点也一起放弃。新课改提出的“整体人发展观”、“建构”知识观、“学生主体”观等等,与“德智体全面发展”观、“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知识观、“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观等等,其实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可是新课改却把它对立起来,一定要二者必居其一。一些倡导新课程的学者,对西方学者如杜威、胡塞尔、罗素、泰勒等,对他们的教育哲学观、教学论,不加分析,不作取舍,一概承认,一概搬用。对我国现行的理论,仍然不加分析,不作取舍,一概否认,一概取消,通通斥之为“传统课程体系”。这同样是陈旧的二元化思维。
(二)思维不讲逻辑,论述不顾“名”、“实”,理论使人难懂
一些倡导新课程的学者,随心所欲地提出一些新名词、新概念,多处不合逻辑,名、实不相符合,使人难以理解,让人望文生畏。例如:“‘整体的人’包括两层含意:人的完整性与生活的完整性。”就逻辑学的意义讲,在这一判断中,前一个“人”是被定义项,“整体的人”即“人的整体”。后面的定义项中,“人的完整性”的内涵和外延,与被定义项“人的整体”的内涵和外延已经相等。人的整体,即具有“完整性”的人。可是,论者却告诉我们,还有“生活的完整性”。显然后一个“人”,已经偷偷地改变了内涵和外延。违背了同一律。偷换了概念。实际上等于作者告诉我们:a=a+x,要么等式不能成立,要么“a”已经改变了内涵。“整体的人”不光有人的“完整性”,还有“超完整性”。就辩证逻辑的意义讲,“人”并非是单个的抽象物,人是“应然和实然的统一”。生活是“人”的内容,“人”是生活的本体,“人”与生活不能分割。离开了“生活”的“人”,与离开了“人”的所谓“生活”,同样是荒谬的。如果“整体人”仅仅指的是生活,那么,什么生活“有”完整性,什么生活“没有”完整性?所以,“整体人”的观念是含糊不清的,是不明白的,令人难以理解的。
新课改把教师称为“催化剂”。“在所有的教育方法中,教师的角色都是一个催化剂”。过去曾经有人把教师叫做“顾问”,也有人叫“促进者”的。但他们还是“人”的身份,“催化剂”却连人的身份也失去了,成了物化的“工具”。还有“整体主义”,“教学觉醒”,“活动的伦理原则”,“苏格拉底式探讨评定”,“素材性课程资源的生命与非生命形式”,“课程管理的均权化”等等说法,都值得商榷。综合上述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反思,我们看到新课改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发展观的偏离。这种偏离,难免不对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隐患和潜在性危机。由于教育的人文性、复杂性、长周期性、难测定性等特点,这种潜在性危机很难测定和判断,容易产生麻痹,搞不好,极有可能给教育造成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那样的损失。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反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问题,并不等于否定基础教育的改革。中国教育本身的问题需要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希望改革审慎一些,稳健一些,不要付出太高的代价。这恐怕是所有家长以及关心教育者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