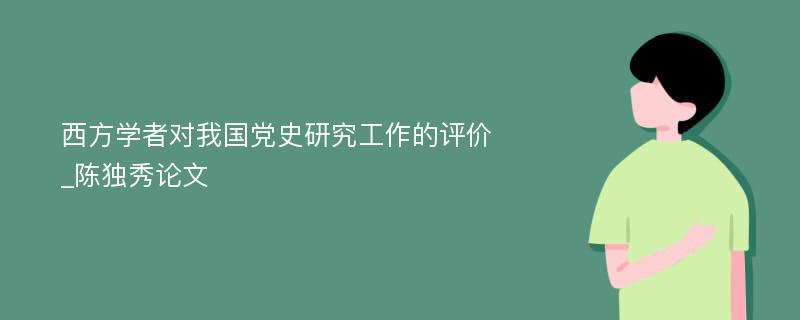
西方学者对我党史研究工作的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我论文,党史论文,研究工作论文,学者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祚康译
编者按:本文对我党史研究工作作出了评价,其中有些观点值得参考,一些方法值得借鉴,但有些观点,显然有失偏颇,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
80年代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写的党史书籍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千篇一律、带有宣传性质的。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这一负面印象很快有了改变。1979年以后,中国国内外读者都认为中国的党史著作是对现代史的重要贡献。
作者认为,虽然1976年以前中国的党史著作大部分是千篇一律的,但有些著作的价值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大。另一方面,虽然1979年关于党史的讨论要活跃得多,但这些讨论的论据与理由仍然遵循着1976年以前的模式,因而,仍然是千篇一律的。
作者称他的根据除去中国党的文件、教科书、报刊上的文章外,还有1980年作者访华时与13名住在北京的中国党史工作者的谈话。
作者在介绍了1945年以来中国党史学以及中国大学中党史系建立情况后,对中国党史研究工作者作了分类。作者认为在党内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能够决定如何解释和评价党的历史,如毛泽东和邓小平,但胡乔木是这一领域内最杰出的,他是1945年《决议》的定稿人、50年代《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主要作者,又是1981年《决议》的起草人。除此而外,党史工作者分三类。第一类是在社科院、中央党校和其他重要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他们的年纪大,革命经历长,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大部分参与了政策制定,因为他们不仅是史学工作者,在党内也有影响,他们在1949年前就参加了党史工作,许多人在延安或华北大学任过教。由于他们的经历和他们对党的忠诚,他们有双重任务,写党史方面的教科书和培养在大学任教的教员,同时又是中央委员会在党史方面的顾问。1980与1981年,党史研究室的人员参与了1981年《决议》的起草工作。他们还撰写了第一本官方党史的书,供内部使用。这些人的著作中有缪楚黄1959年出版的《中共简史》,廖盖隆1952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李新等1959至1962年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叶蠖生1951年出版的《现代中国革命史讲话》等。
第二类人是今天各大学的党史教授。他们是50年代培养的,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他们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编写教科书,有一人现是党史研究室成员或与该室有联系。这些人的著作有徐元冬等1962年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等。
第三类人是今天年青一代的教员,他们与第二代人一样受过正规训练,是近年来大学学报上的文章作者,他们在文章中急于表现出他们是能够“解放思想”与“打破党史禁区的”。同时,他们也奉命参与编写新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多以第二类党史工作者的名义发表,是严格按照官方的解释编写的。
作者进而评论这三类人的方法论。他认为,中国党史工作者的研究方法与他们在党史工作中的地位相适应。作者引用他采访过的一位党史工作者的话说:“我认为研究党史应特别注意党内外的报纸以及党领导下出版的报纸。但仅在这些材料上花功夫是不够的。我们的问题恐怕就在这里。回忆录是有些价值的,但由于离事件年代久远,一定是会有些错误的。事后的认识也影响到叙述事实,当时只是粗糙的事,后来被说成是成熟的事,但它仍然有价值。最重要的是原始材料。有宣传性质的原始材料,也有档案性质的原始材料,但我们很少能查阅档案材料。党史是史学的年轻学科,许多先决条件还不具备。我认为,严格地说,党史领域中的科学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编译者:作者未公开所采访的13名党史工作人员的姓名,并称如需要,可与他直接联系。这些人员的意见,作者综合在他们的1984年的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史:类型、方法、主题与著作》中)作者称第二、三类党史工作者只能依赖宣传材料,这与他们的地位、与读者有关。主要要求他们建立事件的官方编年史并将事件与官方的解释联系起来,因此,报纸是研究的“足够”资料来源了。只有第一类人员才能查阅档案材料,因为他们的读者是负责解释党史的中央委员。第一类党史工作者的力量主要来自档案。他们是为中央委员会解释党史的顾问,而第二、三类人员则负责传播官方批准的解释,将这些解释与官方批准的少数材料联系起来。
以上的分工说明党史工作的一个重要性质,这就是说,可以将党史分为史(事实)与论(评论、理论)两部分。这是和党的工作人员与党史工作者之间的组织分工相适应的。因此,我们能看到一些书主要是提出评价和理论,而另一些书是详细地“重构历史”。
1945年与1981年的两个《决议》就是党的工作人员所喜欢的那种党史的典型样板。它们的目的不是“重构历史”,而是“统一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内各派别之间的均势合法化并按照各领导人的“功过”排定地位次序。因此,它们主要是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与对有关人员的叙述,并不详细地讨论历史情况。这样,“论”就是根据实际的权力政治所作的评价,是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的政治哲学所作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以前所写的教科书,虽然是为了宣传、教育目的而写的,却是史论结合的。它们的任务是传播毛泽东思想,强调党的《决议》中的评价,并将这些评价与历史材料相联系,使读者更信服。在这些书中,“论”就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关于党史的《决议》的评价。其出发点不是“历史的实际”,而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过程的实质。
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历史杂志中的许多文章,特别是《教学与研究》和《历史教学》中的文章,主要是补充教科书的,因此是同一风格的,而1979年以后的文章则风格、内容各异。
基本上,文章有三类。第一类文章的作者对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实质”比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更感兴趣。历史本身并无价值,必须与现实和未来相联系,因此他们只谈论与现实有关系的历史事件。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专注于建立论据的逻辑链,提到过去只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因此,这些文章不是根据重构历史的证据,而是根据论据的内在逻辑写出的。
第二类文章具有作者称之为“探古”的意图。这些文章的作者认为他们的任务是重构历史,以作为直觉理解的根据。他们认为过去一定是不同于现在的,因此他们的目的是使人记得那些事实。这类文章极少,但是可以在新发行的学术杂志,如中国革命博物馆出版的供内部使用的《党史研究资料》中看到。
第三类文章是第一与第二类文章的混合物。作者们既解释过去,又谈事实,因此他们将“探古”与宣传目的结合起来了。有些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时均用官方的解释,但文章的大部分篇幅则是用于“探古”。另一些作者提供了比正规教科书更多的信息,但他们的材料仍是与事先已确定的解释和评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文章所提供的事实的数量和材料相对独立于官方的解释和评价,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具有“探古”的目的,而为使权力合理化和为达到宣传目的所写的文章则使事实从属于解释,传递的信息量相对来说就要少些。这类文章为数极多,中国各大学的学术期刊上均可以见到。
1979年与1980年进行的关于如何评价陈独秀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邓时代开始时的各类解释。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将陈独秀看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谁应该对1927年的失败负责?说陈独秀是奸细是否应该?关于第一个问题的文章主要是第三类党史工作者写的。虽然对这一问题有各种答案(如《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3期的《应当全面地历史地评价陈独秀》、《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的《对陈独秀评价的评价——简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的《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的《评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等),但读者的印象是,作者们不是在争论陈独秀,而是争论当前的政治与理论问题。他们对材料各取所需,只用有利于自己论点的材料,他们显然不是在重构历史,而是利用过去的事在理论上进行一场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很微妙的问题,它涉及对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作用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在第一类和第二类党史工作者内部进行的,因为当时中央委员会对如何解释这一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
第三个问题是在内部刊物上争论的(如《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5期的《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之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的《评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三封信》、《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6期的《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6期的《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言论》等),目标是针对六大的决定的。第二类党史工作者利用了1979年反康生的运动,小心翼翼地重新构建和解释了过去的事件。虽然如此,在有些文章中,“探古”的目的是主要的,其中传递“真正”信息是主要的,解释是次要的。
作者认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史是与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引用胡华1953年在《新建设》第1期上发表的《怎样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文中对党史所下的定义,认为,党史是付诸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在50年代末以前,毛泽东思想被宣传成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思想,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期间,它又被重新确定为代表党的左翼的正确思想。这时,制定1945年《决议》时组成的联合已破裂,因而,对《决议》的评价已失去其重要性。相反,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被确定为党史的内容。除毛泽东而外,其它人在理论上的贡献都被从教科书中删去。这种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史写作方法也反映在各领导人在著作中被提及的次数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否定了七大所推崇的各次会议,并标志着毛与刘联盟的崩溃。但1971至1976年间的党史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党史差别不大,只有少数著作将党史写成是10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党史所起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作用,如按韦伯关于魅力与常规化(Charisma and routinazation)的理论,有两个。一方面,它是完完全全的革命后的常规化,另一方面,它起到使毛泽东的有魅力的领导永恒化的作用。宣称党史是付诸实际的毛泽东思想,从而使对毛泽东著作的理解规程化,这起到了常规化的作用。宣称毛在党史中处于中心地位是为了使其魅力永恒化。因此,在1964与1965年教科书中的毛中心主义为70年代初的教科书开辟了道路,70年代的教科书将毛的理论与精选的历史事实相结合,将1945年《决议》丢在了一边。
1945至1976年间党史中的毛中心主义与今天党史的主要任务有密切关系。今天党史的任务是传递毛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有限的观点,把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义为共产党的集体智慧。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之一,就是写文章谈他在1949年以前的理论贡献。这些文章是政治运动的产物,但也起到了提供更全面信息的作用。
如1979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的文章《古田会议决议是怎样产生的?》详细叙述了《古田会议决议》形成过程,说这个决议是毛泽东综合了红军干部战士,包括朱德与陈毅的正确意见的产物。这篇文章详细谈到毛以外其他人的贡献,以至毛本人的作用反倒不明显了。另一篇文章也有这一特点,如黄少群在1981年《教学与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有关古田会议两个问题的研究》中,提供了大量细节,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对历史的贡献与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不相称的。
另一个例子是《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中《立三路线时期的一个问题——试论毛泽东同志对李立三的认识和抵制》。该文与教科书不一样,提出毛对李立三的认识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他感到路线不正确,但没有公开反对。在第二个阶段里,他认识到敌人比红军强大得多。在第三个阶段里,他开始说服战士离开长沙,因为如果守不住,那么,占领大城市是不起作用的。该文作者对第一、第二阶段提出了许多证据,但对第三阶段没有提出什么证据。给人们的印象是该文作者证明毛初期接受了李三立的路线,但对毛后来与该路线作斗争却未能提出证据。1980年《党史研究》第4期的《略论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批评上文作者接受了中央委员会苏区局的一个扩大全会的解释,提出该文受到“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批评的一个论点是有趣的:该文作者使用了机密文件,似乎毛选四卷对他说来是唯一可靠的信息来源。
1981年《决议》又重新恢复了1945年《决议》的论点,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贡献是极为重要的。该《决议》力图团结党内各派,因为各派多少都与毛泽东有关系,肯定毛的贡献也就肯定了他们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1981年《决议》仍然要求助于毛的有魅力的领导,同时,1981年《决议》还必须帮助稳定新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一个方法就是将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分开就能使新的领导将他们不赞成的毛泽东的观念删去,加上新的内容。
这样,毛在党内作用降低了,这使党史工作者能研究以前与毛无联系的事与人,如旅欧支部对建党所起的作用、其他领导人的传记等。但党中央仍不能或不愿对1949年以前的历史制订出一份文件来回答在党史研究中新提出的问题。
*本文编译自《古为今用》一书,德国1993年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