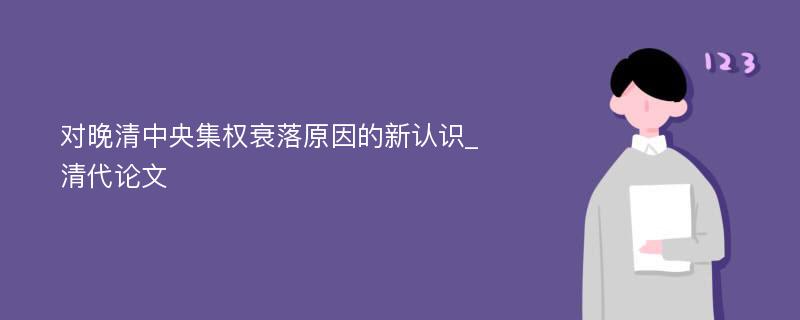
重新认识晚清中央权威衰落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原因论文,中央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学者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认为,对于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来说:“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有助于力量的协调和资源的征用以支持现代化进程”(注: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可是在中国,晚清高度完备化的中央集权君主体制并没有成为启动和推行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其实,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在已经迟到却又不能不到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清政府不仅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央集权权威资源,反而带来了中央权威的持续衰落,并直接阻碍着现代化的发展,这里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西方势力的持续侵入,在不平等条约护符下所形成的特权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分割和威胁,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政治腐败所造成的社会不信任感的加剧等等,均成为清政府中央权威衰落的重要因素。
然而,这一切似乎仍不足说明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观照历史,就会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危机和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过程中,清政府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而是为维护统治,被动地采取了一些早先极不愿意采取的改革措施:成立总理衙门,设置南北洋通商大臣,允许地方督抚兴办了一批军事和民用企业,训练新式海军;甲午战后,光绪颁发谕令,推行新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推动练兵、兴学、修铁路、发展工商等各项事业的开展;1901年,慈禧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从洋务运动开始,清政府的改革并没有中断过,这些改革都是由中央政府推动的,且具有从器物到制度逐步推进的渐进改革特点。
因此,一个鲜明的却又被人忽视的历史现象被凸现出来:一方面,是清政府利用中央权威逐步推进各项改革;另一方面,是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降低,中央各部职权的有效性不断丧失,地方权力扩大。二者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可见,这两者之间必有某种联系,换句话说,中央权威衰落与清政府的渐进改革方法、措施有密切关系。探讨晚清政府推行改革的方法和措施,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一问题。
1
在中央体制危机和社会新需求的矛盾面前,清政府采取了避免中央内部矛盾的做法,下放权力,把改革变成地方督抚的事权,由此带来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直接削弱了中央集权权威。
这一现象起源于19世纪50—60年代。当时清政府在绿营废弛、国库空虚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依靠地方,允许地方督抚自己组织军队,自行筹饷,镇压太平天国。正是通过这些督抚,清政府渡过了统治危机。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已发生变化,形势需要清政府采取措施,推行改革,以适应社会变化而带来的新需求。对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来说,推行改革可以有两种入手办法:一是从中央做起,首先进行体制调整,确立改革者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然后确定规划,一步一步推进改革。它的前提条件是,最高领导人要有现代化意识,并能利用一批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官僚和革新人士推进改革。但是它也会触动相当部分既得利益者,使改革遇到极大的阻力。另一种办法是从地方做起,把各项改革化解为地方事权。但这必须以下放权力为前提。它的好处是可以避开中央内部矛盾,可以在不需对中央体制进行大的调整的情况下进行,但也需要冒造就地方利益势力的风险。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高层领导中还没有形成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改革力量。总理衙门虽倾向于引进西器,但它只是临时应付对外交涉需要而设置的,大臣是兼职的,因此不是独立的职能部门,难以独立承担现代化领导机关的重任。而地方督抚则不同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所兴起的一部分汉族官僚,具有“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以宏济艰难为心”的品格(注: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3页。),较注重现实,又较早接触到西方文明,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奏折制度影响中央决策,所以,他们很容易地成为朝廷的依靠对象。当时,正是这一批地方督抚首先认识到“变局”、“自强”及引进西器、设局制造的必要性。1865年,李鸿章上折提出设置制造局,总理衙门复函“其一切章程及如何筹办经费之处,统由阁下通盘核计入告”(注:《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6页。)。次年1月,在批复御史陈廷经的上谕中,清廷命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整顿营伍、筹划海防、制造外洋船舰之法(注:参见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也就是把创办新式企业的一揽子事情,包括筹措经费、创办、管理、人事任用之权都交给了地方督抚。正是依靠这批地方督抚,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但也由此打开了一个缺口,使晚清改革具有从地方开始的明显特点。
甲午战后,光绪皇帝决计推行新政,包括兴工商、办学堂、修铁路、练新兵等。但就其中几条最关键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措施看,都具有首先在地方举办的特点。如裁兵,光绪21年6 月谕令:“各省挑留精壮三成,其余老弱一概裁撤”;经济方面,谕令各省办理制造船械,“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兴学方面,光绪22年11月谕令:“育才为当今急务”,要求“各直省添设学堂,实力举办”(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33、3637、3910页。)。
1901年,清政府推行的改革进入到“变通政治”的新政时期。当时虽成立了督办政务处,但这个机构“以军机大臣领督办事”,对新政诸项措施详议后又需“次第奏闻”(注:《清史稿》卷114,职官志, 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270页;《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55页。 ),所以只能是参议和督察新政实施的机构,很难独立担当起新政领导中心的职责。当时对新政的推行,慈禧只是笼统地要求“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注:《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71页。 ),从而使新政诸措施仍是延续甲午以来的做法在各省推进。
清政府从地方开始推进改革的做法,确实避开了高层领导集团中的矛盾,它是晚清现代化得以启动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权力扩大,地方利益逐步形成。
早在19世纪50—60年代,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清廷就下放给地方督抚财权、军权,以及相应的人事权、司法权等等,但当时这些权力都具有临时性质,所以60年代以后,清廷就以军兴已过为名,借整顿收权。但这些收权措施大多没有效果,重要原因就是随着洋务活动的开展,清政府又把兴办企业的一系列权力交给了督抚,致使督抚权力出现了再扩展:对兴办企业所需经费,户部无力拨款,只得变相允许督抚就地筹款,这样,厘金、洋税的一部分就被截留下来;随着各个洋务局的开办,所需人员增多,督抚的用人权也延续下来;从60年代开始,在整顿绿营的过程中,督抚掌握的勇营得以保留,并借挑练练军、训练海军的机会,扩大了军事实力。
甲午战后,清政府欲把新政向全国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财政需求更为扩大, 清廷遂将“就地筹款”作为基本政策加以推行。 光绪21年6月,光绪皇帝在批准户部奏请盐斤加价, 重抽烟酒税厘等扩大财政收入的办法时谕令:“着该督抚一体实力举行”;光绪23年闰3月, 户部奏折又称:“迭经钦奉谕旨,饬令各省考核钱粮,稽核荒田,开办蚕桑,振兴商务,并行令各省督抚就地筹款”(注:《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35页;《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080页。)。就地筹款名正言顺地成为地方扩大收入的途径,遂使晚清财政分成中央和地方两个部分。据研究,晚清的地方收入包括10项:常例征收上解京饷后的剩余部分、厘金、捐纳款项、杂捐、部分海关关税、田赋附加和盐斤加价、官业官股收入、发行纸币铜元余利、举借外债内债、他省协款(注: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各省在扩大地方财政的过程中,还建立了厘金局、筹饷局、捐输局等税收机构,建立了铜元局、官银局、官钱局等金融机构。地方财税体系开始形成。
甲午战后,清政府推行军事改革的政策是“就饷练兵”,让各省就已有之饷改练洋操。它实际是把湘军之制沿续下来。督抚可以自筹军饷,自行练兵,从而改变了军队的所属关系,使国家军队——绿营在改练洋操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改变了隶属关系,成为督抚直接控制的军队,兵部对军队数额已无从掌握。地方军事体系也在形成。
19世纪6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地方洋务、财税和军事体系均已超出了中央行政所管辖的范围,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事业,它是地方利益形成的基础,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1)它不仅提高了地方实力和督抚的地位, 而且带来了中央与地方改革不平衡的矛盾。这突出表现在:省一级机构改革走到了中央改革的前面。在原有的清代中央集权体制中,省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督抚虽然统辖地方行政,但都是承中央指命而行,所以省没有庞大的行政机构,只有藩臬两司,分别向中央负责。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省级事权的扩张,省的行政职能大大扩展,行政管理机构也随之出现。在19世纪后半期,省一级行政机构主要是应事而设,名目繁多,但大致分财政、军事、司法、洋务等几类,如洋务局、厘金局、支应局、筹防局、筹款局等。到20世纪初,随着新政的深入,各种工商和新政事务的管理机构先后建立,如工商局、商政局、矿务局、农务局、商务农工局等。在一些省份,还将原来分散的税务机构合并,设立财政局。它们的出现,大大增强了省的适应性和独立性,并由此带来省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正如户部在一份奏折中所说的:“臣部总揽天下财赋,凡有大军大役,用款向由部拨…近年库款支拙,(各省)知臣部筹措之难,动辄自行电檄各省,求为协济…各省亦不尽能另筹的款,遂将例支正项,及报部候拨者,挪移擅动以应之。迨臣部查知,而款已动用,往返驳诘,迄难就绪。”(注:《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474页。 )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削弱了。
(2)省之独立意识的兴起。在清代的原有体制中, 省只是代表中央承担管理地方府厅州县的职责,没有自己具体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所以,省更多只表现为一级行政单位。晚清以来,随着新政的推行,督抚有了自己的财权、军权,省有了自己的经济、教育事业,以省为单位的财税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逐步形成,从而使“省”的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尤其经过甲午新政和1901——1905年新政的推行,到20世纪初,一种立足于一定地域经济文化认同意识和自身利益的新的“省”观念出现了。江西、福建等省成立铁路公司时,其章程皆以“本省”自称。他们声称办铁路公司就是为“维持地方,自保利权”;他们强调自己一省在全国的地位和重要性,福建报纸说:“铁道之于福建,又全省安危得失之所寄也。我闽人宜保勿失,非特为一省计,不啻为全国计。”(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966、985页。)这种利权观念,本质上就是省的利益所在。
从地方改革做起,是晚清政府改革的一大特点。而这一改革方法实施的结果,是使地方迅速形成了地方利益,出现了弱中央、强地方的矛盾。从总体上看,晚清的改革在逐步推进,但却是以中央集权的衰弱和权威流失为代价的。
2
晚清社会变化对改革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但清政府的改革始终只是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原有体制滞后与政策变化过快的矛盾,也削弱了中央权威。
体制、制度、政策,是政治改革中三个互相关联而又区别的范畴。体制是一种权力组合的框架,是一定的统治和治理方法的根本意图的集中体现;制度在体制的框架内建立,表现为一种维持体制的规范;政策则是一定体制和制度的具体执行。三者之中,政策是最易变化的,制度其次,而体制变化则相对缓慢,因为它更集中地体现为一种统治利益所在。
纵观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日本是首先从体制入手推进改革的成功范例:1868年确立天皇体制,建立太政官为政府的中枢机构,组成了以维新派为核心的新政领导核心。在它的领导下,逐步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制度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确立中央集权;成立通商司,成为掌管政府经济政策的机关(注: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明治维新的成功表明,从中央体制改革入手,是建立和充分利用中央集权权威资源的最好途径。
清代的政治体制,在中央形成了皇权——军机——六部的格局,其中皇帝和军机是决策中心。但其决策依据主要是各部和地方大吏的奏折;来源单一,不了解下情,是清代中央决策的主要弊端。六部的行政职能,主要是实现和维持对地方的控驭,致使行政功能萎缩。如户部的主要机构,是按地区设置的十四个清吏司,分别掌核各省钱粮收支数目。兵部掌天下兵籍和武职任免,目的是以大制小,制约地方督抚。这种中央集权体制,难以承担和实现对社会的管理这一最主要的政府职能。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实现中央体制的创新与改革,成为能否利用原有中央集权资源并为启动现代化服务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晚清并不缺乏中央体制创新的时机。第一次是19世纪60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平定太平天国,清政府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国内经济结构有所变化,引进和制造西器,逐渐成为一部分官僚士大夫的话题。历史到了需要清政府出面启动现代化的时期。但由于当时最高领导人不了解世界大势并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只从应付对外交涉需要出发设置了总理衙门,并把总理衙门置于皇权——军机体制之下,从而使总理衙门难以成为推进现代化的中枢领导机构。
第二次是90年代甲午战后,当时举国上下朝廷内外,自强之议纷起。1895年光绪谕令推行新政,并命内外臣僚就新政条陈意见。四品京堂官盛宣怀上折提出设立银行、开办学校等建议,其中也提到要学习外国,在京城设立专管兵事之大臣,设参谋部;还要设置商务、学务大臣,以推进工商和教育的发展(注:《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 第3877 —3882页。)。这些主张并不完整,也没有触及到皇权专制这一根本问题,但它却把新政需要中央行政机构创新和职能转换问题提了出来。当时光绪令总理衙门户部复议,总理衙门的复议只肯定了设银行等具体措施,对行政体制改革却不置可否(注:《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 第3907页。)。1898年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更是明确提出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之法,吸纳维新人士,设制度局作为新政的总领导机关,但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这一建议也就烟消云散,未能实现。
第三次是20世纪初年,慈禧宣布要“变通政治”以后,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提出整顿中法以行新法的各项建议,其中也提到改革中央行政体制,设专管筹划兵事和矿路商务大臣。当时慈禧只是笼统地说:“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注:《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71页。)这样, 在“变通政治”的初期,清廷并没有抓住时机建立有力的新政领导机构。
不主动从体制和制度上进行改革,使晚清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具体政策的调整。它虽然也使改革能维持下来,但也带来了三方面的深刻影响:
(1)体制滞后,使中央无法形成具有现代化意识的领导核心, 从而使改革缺乏通盘计划和理论指导。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最初五年,清政府的改革都是在没有明确目标和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自强”成为支撑各项改革的主要动机。但是,“自强”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在统治集团内部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1864年奕炘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甲午战后清廷的谕令指出:“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1901年清廷的上谕又说要“变通政治,力图自强”(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3页;《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631页、4655页。)。在这里,自强始终只是引进西器和练兵的手段,立足点仍是内治,即维持原有体制的运作。在这一模糊观念的支配下,改革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只就具体做法进行调整,从而缺乏计划和步骤。
(2)体制滞后,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可避免地带上人治色彩。 从决策程序看,清廷的决策权在皇帝和军机,所以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受决策人的主观因素制约;另一方面,政策的推行主要在地方督抚,所以政策执行的怎样又要受地方督抚的制约,这就使政策极易受不同利益者的左右, 带来了中央政策的不稳定和执行中的走过场现象。 如1895年光绪谕令各地裁兵练军,最初确定的比例是“裁七留三”,用节省的军费练新军。但各地发不出遣饷,同时又担心裁兵过多会影响社会治安,所以多持谨慎态度,只有山东省计划分五年裁五成,其余各省“或请将兵额酌减,尚无成数,或仅裁绿营二三成,所裁营勇更属寥寥无几。”实际上,山东省1898年裁至三成时,巡抚张汝梅就以“地方紧要”为由,奏请免裁其余二成。各省的拖延塞责,迫使朝廷实行变通,让各省“就现有兵饷精练陆军”;实际是允许各省就便行事,自行练兵(注:《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633、3946、4043页; 罗尔纲《绿营兵制》,第101页。)。仔细考察其他工商政策、 办学政策的实施情况都是如此。
(3)体制滞后,使许多政策的推行超出了中央政府的职能范围, 使中央政府无法实行有效领导。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各项经济、教育、军事改革政策都是通过朝廷谕令的方式下达的。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和管理部门,所以很快出现各地执行不一和发展不平衡现象:在军事方面,各省练新军,一切营制饷章军服操法,“不仅此省与彼省不同,且同省同军,此营与彼营又不同”;发展工商方面,“各省开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牵制抑勒等弊,以至群情疑阻”;财政方面,各省争相鼓铸铜元,不仅成色分两不一,而且出现“鼓铸日增,此省竞运出口,彼省严禁入口,则是铜元充斥,民用足敷”的情况;各省官银号发行钞票,形成“行号林立,票纸日多,官视为筹款之方,商倚为谋利之具”,中央“无从知其底蕴”的状况(注:《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05、5073页;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51、1075页。)。
在发展政治学中,把体制和制度很少变化,而政策却迅速发生变化的现象称为“政治停滞”(注: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政治停滞”反映了这种政治变革方法的本质。在政策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与体制和制度的矛盾必然尖锐化,不仅使政策在执行中会偏离原有轨道,而且只要政策在执行中各行其是的情况能够实现,那就必然会壮大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并使这种既得利益很快成为一种压力,抵触和消耗原有的中央集权权威。清政府只是在各项政策推行并与中央体制发生矛盾以后,才意识到中央行政制度调整的必要性,1903年成立商部、财政处、练兵处;1905年成立学部、巡警部,作为新政的管理和执行机关。但这种制度变革已落到政策变革的后面,是建立在各省改革极不平衡的基础上,所以已难以确立起应有的权威了。
3
长达半个世纪的晚清改革,只是在它最后五年才认识到了体制变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确立的目标是学习日本,建立二元君主立宪政体。还颁布了宪法大纲,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并为建立新的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的中心,是通过体制和制度改革恢复中央集权的权威。然而事实上,由于19世纪60年代以来改革措施的不当,中央权威衰落,从而使这一时期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不能不受到已经形成的统治集团内中央和地方两方面既得利益者的牵制,造成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失误,大大抵消了改革目标的实现,终而无法挽救中央权威衰落的状况。试举几例:
(1)在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中,编纂官制大臣曾提出裁军机处、 成立责任内阁的草案,而相当部分部院大臣和亲贵指责此举是“实阴以夺朝廷之权”,极力反对。清廷迁就反对势力,宣布军机处照旧,只将中央行政部门作了改组。这一斗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的权势之争,也表明清廷并不愿意从根本上触动以君权专制为中心的中央决策体制。因此,招致社会人士尤其是立宪派人士的失望,“伪立宪”之名由此而起,中央权威进一步受挫。
(2)在地方官制改革中,朝廷最初所确定的原则, 是将督抚之财权、军权收归中央,但相当一部分地方督抚则明显表现出希望在维持晚清以来督抚制度的既定局面下,进一步扩大权力的倾向。如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划分中央和地方行政权限,“其属于地方行政事务,则由督抚监督下级官厅执行,凡在范围以内之事,皆得自为规划,直行具奏,各部亦不得侵越”,同时又提出:“今日之弊,各省对于中央,病在情形壅隔,必使督抚预闻阁议”。两江总督张人骏则明确提出地方官制“自督抚以至州县,皆以旧制为主而酌量变通”,要求督抚有“奏事之权”、“军政之权”、“外交之权”、“操监察督率府厅州县地方自治”之权。朝廷迁就地方势力,1907年颁布的地方官制改革章程规定中央与地方督抚的关系是:“总督巡抚于各部咨行筹办事件,均有奉行之责,但督抚认为于地方情形窒碍难行者,得咨商各部酌量变通,或奏明请旨办理”(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7 、545—546、591—595、506页。)。这就是说, 督抚可对各部核议之事提出不同意见,并可越过各部,自行请旨取得事权。所以地方官制改革并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旧制。这样,督抚权力并没有在地方体制改革中削弱,反而得到确认。
(3)在财税体制改革中,1908 年御史赵炳麟提出将一切租税分为国税和地方税两种,国税专备中央政府之用,听部指拨,地方税专备地方之用,各省留支的意见(注:《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920页。)。1909年,御史王履康上折提出:“今值国税未定之时,断不能先从地方税为入手办法”(注:《宣统政纪》卷38,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637页。),提出了程序上的先中央后地方问题。然而, 由于中央自19世纪中叶以后就难以明了地方财政情况,所以在实际运作中度支部拿不出如何划分的具体方案,只好又一次迁就地方,上奏请饬下各省督抚将“何项应入国税,何项应入地方税,详拟办法,咨明度支部分别核定”(注:《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956页。)。这样, 各省自行为是,河南所列地方税有56项之多,甘肃所列国税及税外收入有66项之多,且各省税种划分方式极不一致(注: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载《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5册,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35页。)。这项通过制度调整以达财政统一的办法最终无法完成,使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因地方利益的牵制而打了折扣。
(4)在立法体制建立的问题上, 当时社会上尤其是立宪派人士主张先立国会、制定宪法,但清政府始终害怕社会新兴力量进入国会,因此借口国民程度不足要先设资政院作为过渡。在设立程序上,清廷又一次依靠地方,一再督促地方筹办地方自治,1907年又谕令各省速设谘议局,“为资政院储材之阶”。1909年全国除新疆外,各省谘议局均宣告成立。谘议局的职责是“凡地方应兴应率事宜,议员公同集议,候本省大吏裁夺施行。遇有重大事件,由该省督抚奏明办理。”(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67页。)这样, 在中央和地方权限并未划定的情况下,首先出现了地方性立法活动。正是借助于这种立法活动,使省迅速成为一种团体力量,省的独立性大大增强,进而扩大了督抚的权力来源。其后成立的资政院的民选代表则由各省谘议局代表组成,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地方利益,使资政院对各省的监督无法实现。
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期间所犯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失误,实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改革措施失当的继续。正是这一系列措施的失当,造成了中央权威的不断削弱。伴随着这一过程,各种既得利益势力乘机起来或成为左右改革的力量,或直接瓜分改革的果实。这是清末改革失败的内在原因,也是一条深刻的历史教训。
收稿日期:1998—02—21
标签:清代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晚清论文; 中央集权制度论文; 光绪朝东华录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地方领导论文; 光绪论文; 经济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