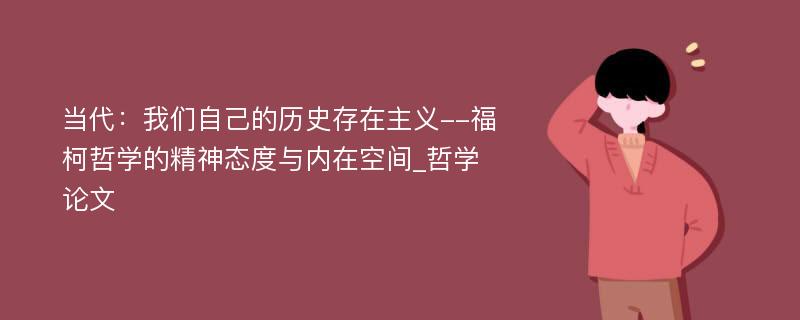
现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福柯哲学的精神态度与内在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态度论文,精神论文,历史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福柯的名字无疑意味着一种独特的思想与生存风格,就如他那颗铮亮的光头与莫名的身体令人眩目又充满蛊惑,如何谈论这颗光头与身体的哲学是一个问题。
英国的福柯研究专家阿兰·谢里登(Alan Sheridan)在《米歇尔·福柯:求真意志》中指出:“福柯的终生梦寻就是去理解现在。”[1] 的确,只有在与现在的关系中,我们才能把握福柯思想的命脉。
一、启蒙与现代性态度
在1977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说:“长期以来,哲学的问题是:‘在这个一切都会消亡的世界里,什么东西不会消失?’而在我看来,自19世纪以来的哲学则不停地在问:‘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我们作为也许只是这一刻所发生的东西是什么?’因此,哲学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自己是什么的问题。”[2]
在去世前不久的1983年,福柯发表了一个名为“何为启蒙?”的讲演,后收入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编的《福柯读本》。据拉比诺所称该读本的文章都是福柯亲自选送的[3],而《何为启蒙?》又是该读本的首篇,“可见,这是一篇重要的、甚至带有决定意义的文字”[4]。在这篇文章中,福柯通过论述康德的同名文章对自己多年来的思路和有关问题进行了总盘点。
康德的文章《回答这个问题:“何为启蒙?”》发表于18世纪末,相对于康德的其他著述,这篇文章似乎不太引人注目,然而它却令福柯着迷。早在1978年题为“何为批判?”的讲演中福柯就讲到康德这篇文章,在1983年它更是被频频提及,最后他干脆做了与康德文章同名的演讲。
康德这篇不起眼的文章何以令福柯着迷?我认为其根本的原因是这篇文章为福柯提供了一个有效而简明地阐释自己哲学观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利用福柯对康德这篇文章的阐释来进入福柯哲学的特殊殿堂。
在康德这篇文章中,福柯发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哲学,一种与他的哲学一拍即合并被他称之为现代哲学的哲学。
福柯问:康德的问题(“何为启蒙?”)是一个什么问题?(注:“何为启蒙?”是当时一家德国报纸提出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何为启蒙?”》是康德为回答这个问题所写的文章。从康德对此一问题的回答来看,康德是认可这个问题的。) 答曰:这是传统哲学所禁忌的问题。“启蒙”是一个历史事件,是提问者康德身在其中的特殊事件,是提问者自己的历史性现在与之有关的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和地点。我们知道,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最忌讳询问时间中的事情,它拒绝思考我们自己经验中的个别事件,它关注的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即时间之外的、超历史的、超验的普遍必然存在,它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现在毫不关心。
在福柯看来,哲学家康德对“启蒙”的询问与回答意义重大。
因为这是一个哲学家首次不仅将形而上学的体系或科学知识的基础作为哲学研究的任务,也将一个历史事件,一个最近的、甚至是当前的事件作为哲学研究的任务。
1784年的康德问:何为启蒙?他的意思是:刚刚发生并正在继续的是什么?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时期、这一刻是什么?
换言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作为启蒙者的存在者吗?我们是作为启蒙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吗?比较一下笛卡尔的问题:我是谁?作为一个独一的但又是普遍而非历史的主体,我是谁?对笛卡尔来说,这个我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刻的一切人吗?
康德问的是另一回事:在这个特定时刻的我们是谁?康德的问题仿佛是对我们和我们现在的分析。
我认为哲学的这一方面越来越重要了……
“普遍哲学”的一方面没有消失,但哲学的任务作为对我们当前世界的批判性分析却越来越重要了。也许,全部哲学难题中最确实的难题是有关现在的难题,是有关在这个特定时刻的我们是什么的难题。[5]
在福柯看来,自康德以后,西方哲学有了两条路线,一是继续延伸其传统的“普遍性哲学”,二是新辟一路的现代“历史性哲学”,他自己的哲学属于后者。
在与康德同名的文章中,福柯借阐释康德而阐述了自己对现代哲学的基本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现代性哲学态度的论说。
福柯认为“启蒙”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它至少已经部分地决定了今天的我们是什么,想什么和做什么”[6]。因此问“何为启蒙?”等于问“何为我们的现在?”在谈到康德对“何为启蒙”或“何为现在”的回答之前,福柯列举了曾经有过的三种回答:1.将“现在”看作一个特殊的时代;2.将“现在”看作一种未来事件的先兆;3.将“现在”看作走向新世界的转折点。康德与此不同,他将“启蒙”(他所在的“现在”)看作“出口”(exit)或“出路”(way out),或者说他将“现在”看作现在的出口或出路。福柯认为康德的回答十分重要,因为它开启了对启蒙和对现在的一种具有“现代性哲学态度”的思考,这一思考为我们反思现代哲学提供了线索。
康德明确指出,“启蒙”作为“出口”或“出路”是一个过程,它使我们从“不成熟”(immaturity)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走向“成熟”(maturity)。康德所谓的“不成熟”状态指的是在他人权威的控制下按他人意志去使用理性,或依赖外在权威并在外在权威的引导下去使用理性,比如当书本代替我们的思考、当某个精神领袖代替我们的意愿、当医生代替我们决断时,我们就处在不成熟状态。我们被替代,我们只是他人的替身,他人操纵了我们的理性,我们并没有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所谓“成熟”指的就是摆脱了权威的控制和支配,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性。故而康德说启蒙的口号就是不畏权威,摆脱迷信的“敢于认知”!“有(自己独立)认知的勇气和胆量。”
康德将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性区分为两种情况,即他所谓的“对理性的私下运用”(private use of reason)和“对理性的公共运用”(public use of reason)。“对理性的私下运用”指的是一个人意识到在特定的范围内,基于某特定的职责,为了某特定的目的应该按特定的规则去运用自己的理性,比如作为一个军人应该服从命令,作为公民应该按规定纳税,作为牧师应该按教会的章程传教。从表面上看,这里的服从和所谓“不成熟”状态的服从没有什么两样,但它们却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后者是未经自己思考的盲目服从或出于恐惧的被迫服从,而前者则是在无畏的状况下经过了自己的思考而自觉自愿地服从,因此前者是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一种方式,后者不是。所谓“对理性的公共运用”指的是无条件地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考虑特定的范围,特定的职责,特定的目的。换句话说,它指的是一个人作为纯粹的人可以超越任何特殊的限制,自由地“为理性而运用理性”(to reason for reasoning' s sake),比如一个军人在自觉自愿地服从命令的同时,也可以超越自己的军人身份,作为一个纯粹的人对该命令的正当性进行自由的思考,一个公民在自觉自愿地按规定纳税的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的人对相关的税收规定自由地提出质疑,一个牧师在自觉自愿地按教会的章程传教的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的人对教义自由地说三道四。为此,康德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说不成熟和成熟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服从,不思考”,后者是“服从,但思考”,因此,无论是有条件的思考(“对理性的私下使用”)还是无条件的思考(“对理性的公共使用”),都体现了理性运用的自主与自由。
在福柯的思路上,康德明谈“启蒙”暗论“现在”。在此,“启蒙”作为“出路”成了这样一个“现在”时刻,一个人们摆脱不成熟而走向成熟的时刻,一个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服从任何权威的时刻,一个发生差异的时刻,一个人们与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决裂(自杀)的时刻,一个人的理性获得自由而对自己的现在进行反思批判的时刻,也是人们意识到要对自己的不成熟负责并决定改变现在的时刻。福柯提醒说:“还必须指出,康德是以一种相当含糊的方式论说这一出路的。他不仅将这一出路描述为一种现象、一个正在展开的过程,他也将其描述为一种任务和义务。在文章的开头,康德就指出人必须对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负责,因此必须设想只有通过他自己在自己身上引发的改变才能摆脱这种状态。”[7]
“关注现在”、“自由”(摆脱、走出我们自己的现在)、“批判”(自由地反思批判我们自己的现在)、“责任”(自己改变我们自己的现在)是福柯在康德相当含糊的描述中所看到的一种对待我们自己之现在的全新态度,他称之为“现代性态度”(attitude of modernity)。
福柯对“现代性”(modernity)的解释十分特别,他说“现代性”不是用来描述一个历史的“时代”(era)或“新纪元”(epoch)之特性的概念,而是指一种特殊的对待“现在”的“态度”。“我说的‘态度’是指与当代现实的一种关系模式,指一些人所作出的自愿选择,归根到底,它指一种思想方式和感觉方式,也指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同时标志着一种归属关系并将自己显示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谓的ethos。因此,我想与其竭力将‘现代’(modern era)与‘前现代’或‘后现代’区分开来,不如尝试去发现现代性态度自形成以来是如何与‘反-现代性’(counter-modernity)态度对立起来的。”[8]
以福柯之见,现代性态度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启蒙中形成的,这种态度与传统的哲学态度完全相反,它不仅可以在哲学家康德《何为启蒙?》这篇文章中见出,还可以在诗人波德莱尔的意识中看到。
福柯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意识概述为四点:1.将“现在”“英雄化”,突出现在,关切现在,将瞬间即逝的“现在”放在与“永恒”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并将对现在的肯定与对流变和时尚的简单迷恋区别开来;2.反讽的英雄化,即不把被突出的“现在”永恒化而是对其采取一种反讽的态度,从而将其看作一个差异化的时刻,一个即将被超越的时刻,一个通过现实与自由创造的互动而使现实变形的时刻;3.精心制造和改变自己,将自己创造成艺术品;4.现代性的思想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今天的社会中只在艺术领域有其地位。
通过阐释康德和波德莱尔对“现代性态度”的论说,福柯得以揭示现代哲学和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以及现代哲学与启蒙的特殊关联。在福柯的思考中,“现代哲学”并不是指在自然时间的意义上产生于某个新近时代的哲学,而是指一种具有现代性态度的哲学,换言之,现代哲学的现代性并不是年代学意义上的,而是精神类型和态度类型上的。为此,福柯才如此富有深意地说:“使我们与‘启蒙’关联起来的纽带并不是对一些教义的忠诚,而是不断复活某种态度,即不断复活一种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进行持久批判的哲学的‘ethos(精神态度)’。”(注:Michel Foucault,What is Enlightment? in The Foucault Reader,ed.Paul Rabinow (New York,1984)。我认为福柯分析的“现代性态度”不仅是现代哲学最内在的精神态度(ethos),也是一切现代文化的精神态度。一种文化是不是“现代的”不是因为它位于年代学意义上的某个时代,而是因为它禀有一种“关注我们自己的现在”、“自由批判我们自己的现在”和“对改变我们自己的现在负有责任”的现代性态度。以此来区分文化上的“现代”与“非现代”十分重要,而在各文化领域维护和坚持现代性态度就更重要,因为它涉及到现代社会的命运。)
二、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
福柯将自己的哲学归于一种具有现代性态度的现代哲学,一种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现在负有自由批判之责任的哲学,他称之为“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the histor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
“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首先是反形而上学的。以福柯之见,传统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持有一种“反-现代性态度”,即它不关注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现在,不关注人类的经验和实践,害怕时间中的短暂、个别、偶然、差异和变化,迷恋时间之外的永恒、普遍、必然与不变,它与我们历史性现在的唯一关系就是用它所玄想到的超时空和“超历史的普遍存在”来规范和强制我们的“历史性现在”,从而在根本上遏止了我们创造自己之现在的可能。“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坚决拒绝思考时间和历史之外的普遍存在,坚决拒绝从超历史的普遍存在出发来理解历史并强制性地规范历史,坚持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思考一切问题和回答一切问题,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福柯与尼采思想的基本关联。
对尼采而言,大写的“上帝”(God)死了,他坚持在没有上帝的处境中重新思考一切,对福柯来说,大写的“人”(Man)死了,他坚持在没有人的历史中重新思考一切。大写的人和大写的上帝都是一种时间和历史之外的存在物,这种存在物不仅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也是它进行思考的逻辑前提,彻底抛弃这种思想的对象和依赖物就是彻底抛弃传统思想。
不过,在福柯看来,要真正与传统思想决裂是不容易的,因为历史和语言的原因,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之间的界线往往模糊不清,因此,现代哲学要真正确立自身就必须将自己从形形色色的混淆中剥离出来,福柯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细活。
比如作为现代性哲学态度核心之一的“批判”(critique)。
福柯说他所谓的“批判”“不是一种毁灭工作(a demolition job),不是否决(rejection)和拒绝(refusal),而是一种审查(examination)工作,这种审查工作尽可能悬置它检验和评估的那些价值系统”。[9] 更明确地说,福柯的“批判”绝不同于俗常那种根据某种价值系统进行指指点点的“评判”(judge),它要做的事恰恰是要“审查”(examination)人们现在是根据什么价值系统在进行评判?这些价值系统缘何而来?为什么人们会将这些价值系统当作真假是非评判的唯一标准?人们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此外,福柯的批判也不同于形而上学对价值系统本身之真假是非的批判,它不试图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唯一合法的价值系统,而只是调查形形色色价值系统的历史,查它们那并不光辉的谱系,从而抹掉这些价值系统身上由形而上学所赋予的超历史的圣光,解除它们对人们所思、所说、所做的禁锢与奴役,让人们有可能别有所思、别有所说、别有所做,让人们的现在成为走出过去的一个“出口”或“出路”,成为一个发生差异的时刻,这正是康德所说的启蒙的时刻。
福柯的批判意识与康德有关,但又不同于康德。福柯说哲学的态度首先是一种审查界限的态度,形形色色的价值系统就是形形色色的界限。这种“界限态度”(limit-attitude)或对界限的批判(审查)首创于康德。不过,康德对界限的批判性反思旨在划定一条普遍必然之界限,以防止理性的滥用和僭越,而“我认为,在今天,批判的问题应当转变为一个积极的问题:在被我们接受为普遍的、必然的、义务性的东西中,哪些地方被个别的、偶然的、专断的成分所占据?简言之,问题在于把以必然的界定形式所做的批判转变为以可能的越界形式所做的实践性批判。”[10] 换句话说,福柯的界限批判是要为理性的越界提供可能,而康德的界限批判则要为理性设置不可逾越的界限。
问题的关键在于,福柯根本就不认可有所谓康德式的、先验的、普遍的、必然的、超出历史之外的理性界限,任何被我们以为是普遍的、必然的、义务性的界限(规范系统、价值系统)中都有个别的、偶然的、专断的成分,没有超历史的界限,任何现实的界限都来自于历史,来自于历史中的偶然事件,据此,福柯将自己的批判态度确认为“历史批判的态度”(historico-critical attitude)以区别于康德式的“先验批判的态度”(transcendental-critical attitude)。
“历史批判的态度”是要对造就现在的“历史”进行批判,从而寻求摆脱过去的出路,使现在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时刻;“先验批判的态度”则是要对规范现在的“准则”进行批判,目的是找到一个不被历史污染的超历史的真正准则来防止现在脱离正轨而走上歧途。分歧的关键在于:“先验批判的态度”相信在事实性的历史之外有一种唯一正确的历史,一种规范经验性历史的先验历史,一种“元历史”,一种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只有找到这个历史,人类的经验性历史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而福柯不相信有这种历史,在他看来只存在经验性的历史,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不过,福柯认为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大写的历史,摧毁这个历史,摆脱这个历史,因为这个历史现在仍以真理之名并借权力之威取消我们可能的多元小历史,使我们的现在成为一个与过去和未来同在一个轨道上的时刻。
要摆脱大写的历史,首先就要将形形色色有关这一历史的大写还原为小写。在福柯看来,那在历史上自诩为由上帝或绝对精神等超历史的存在者书写的历史(有关的规划、规范、规则与真理)都不过是由一些人在小历史中小写的历史,比如尼采所揭露的被宣称为由上帝注定的道德史,不过是某个历史时期的一些“教士”在“阴暗的作坊”中制造出来的。任何一种大写的“历史”事实上都是对人类可能之小历史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本身就是在小历史之中进行的,因此,它没有权利宣称自己超越在全部小历史之上而规范全部的小历史。
然而在事实上,我们的今天仍被形形色色的大历史所规范,因此,我们要调查这些大历史本身的小历史,将其还原为小历史,从而走出这个小历史而进入另外的小历史。这就是福柯对现在的批判,或者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对“现在的历史”的调查。
福柯区分了“过去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past)和“现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所谓“过去的历史”主要指一种学科式的或出于嗜古癖而对过去的研究,它旨在建立一种“关于过去”的历史,而不关心现在;所谓“现在的历史”则是出于对现在的关切而对构成现在的那些过去事件的调查与研究,其目的是建立“有关现在”的历史,以便理解现在。此外,这种“现在的历史”也不是什么从现在的视角去书写过去的历史,把过去整合到现在的视野中,以证明现在视野的普遍正当性,而恰恰是调查那仍然支配着现在的过去的视野,从而破除某种现在视野天然正当永恒不变的神话。
那在今天仍支配着我们的视野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所形成的有关历史的大写,有关真理和普遍规范的大写,那是我们今天的地平线。调查“今天的历史”就是要查明:这条地平线在哪里?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今天的历史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历史?那别样的历史是什么?哪里有不同的地平线?一句话,破除单数地平线的神话呈现复数地平线的历史事实。
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批判就不是先验的,其目的不是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从其规划上看,它是谱系学的,从其方法上看,它是考古学的。所谓考古学的(而非先验的)是说这种批判并不想确定全部知识或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力图将那些使我们的所思、所说、所做得以表达的话语实例作为大量的历史事件来探讨。说这种批判是谱系学的,指的是它不会由我们是什么的形式中推断出我们不可能做什么或不可能认识什么,而是从已经使我们是什么的那种偶然因素中区分出不再是我们所是的什么、不再做我们所做的什么和不再想我们所想的什么的那种可能性。
这种批判并不力图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而是力图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给自由之不确定的运作以新的动力。[11]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批判的态度,福柯将他的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哲学区别开来,并认为这是近年来哲学话语和理论批评领域中发生的最有意义的变化。“大多数哲学话语和理论批评不再指点人们应该成为什么、做什么、相信什么和思考什么,而是让他们弄明白迄今为止的社会机制何以能运转,那些压抑和束缚的形式如何运作,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己决断,自己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12] 福柯式的哲学家不再效法希腊智者、犹太先知和罗马立法者,不再迷恋立法和预言,不再梦想确立一种超历史的普遍规范或普遍真理,因而也就不再梦想有唯一正确的哲学和唯一合法的哲学。哲学作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不再是唯一的和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哲学活动”(philosophical activities),这种新型的哲学活动不再试图去规范人们的思想,而是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或促使人们的思想转型。
福柯认为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非常重要,因为“思想是一种具有独立的系统和话语结构的存在。它常常是隐匿的但又总是给日常行为以活力。即使在最愚蠢的体制中也总有些许思想,即使在不经意的习惯中也总有思想”[13]。简单地说,人们的思想方式制约着人们的行动,只有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才能在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动,否则,无论行为改革的规划如何,它也会被始终如一的思想模式和体制模式同化掉。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介入社会改革的方式就是要在他工作的特定领域中促进思想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福柯所谓的改变思想不是教导人们说:你们原来接受的真理是伪真理,我现在给你们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你们原来的真假是非判断不对,照我的来。如此这般地改变思想所改变的只是奴役人们思想的真理,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被真理奴役的思想方式。福柯认为改变人们的思想不是改变人们所信的真理,而是改变其被真理奴役的思想方式,改变那种真理常变而思想照常的思想宿命。为此,哲学就要坚决放弃自己的求真意志,更不能将这种意志强加在人们的头上,以建立自己的专制。哲学要做的事恰恰是打破真理的神话,把人们的思想从真理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还人们的思想以自由。
如果哲学不再是一种反思真假的方式,而是反思我们与真理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它会怎样呢?人们有时抱怨法国没有主流哲学,那可是太好了!没有统治性的哲学,的确如此,但有某种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哲学活动。哲学是这样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不是不费力,不是没有不确定性,不是没有梦想和幻象)人们摆脱以往所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去寻求别的规则。转换思想框架,改变既有的价值,用其他方式思考,做另外的事情,把自己变成不同于自己的东西——这也是哲学。由此观之,近三十年来是一个有着激烈的哲学活动的时期。在分析、研究、“学术的”或“理论的”批评与人们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之间存在着大量而经常的互动。[14]
福柯说他梦想这样一种哲学批判,“这种批判不想去评判(judge),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个观念以生命。它点燃火,看草的生长,听风的声音,抓住微风吹起的海沫并把它撒开。它增加有关存在的符号而不是有关存在的评判,它召唤这些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创造这些符号,那更好。评判式的批评令我昏昏入睡。我喜欢一种具有想象之闪烁跃动的批评。它不是至高无上的或红袍加身的君主,它是孕育具有可能之风暴的闪电。”[15]
从事这样一种非专制的、自由的哲学批判活动,在福柯看来,才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对此,福柯还提醒说,这样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普遍全能的知识分子”(the universal intellectual)了,而是出现在“特定领域的知识分子”(the specific intellectual)。这个在某个特定领域工作的人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去思考,因此,“当哲学话语想从外面对别的话语发号施令,指点它们的真理何在以及如何发现它时,或者当哲学努力以朴素的实证语言建立起一个背离这些话语的事实时,哲学话语中总有某种可笑的东西。”[16] 因此,总在某个特定领域中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创造出一种关于世界的普遍理论,也不可能制定出什么普遍有效的法规和作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预言,“知识分子的职责并不是告诉别人必须做什么。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想一想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在两个多世纪以来由知识分子所竭力给出的预言、许诺、指令、蓝图以及它们的后果吧。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铸造别人的政治意愿,而是通过在他自己的领域中做出的分析来不断地质疑那些被假定为自明的东西,来打乱人们的心性习惯(即他们思与行的方式),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东西不再感兴趣,重新测试法规风俗并在这种重新问题化的基础上(以这种方式履行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参与一种政治意愿的建构(以这种方式履行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17]
一句话,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和新型的哲学家,福柯的历史批判不再给现在之思想套上命定的枷锁,而是要打破既有的枷锁给思想以自由。不过,福柯说:“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对自由作单纯的肯定或对其抱空洞的幻想,这种历史批判的态度也必须是一种实验的态度(an experimental attitude)。”[18] 所谓“实验的态度”就是为了在寻求另一种现在之可能的时候不要落入空洞的幻想,即不能脱离当代现实系统去制定一个有关另一社会、另一思想方式、另一文化和另一世界观的总纲领,而是要立足于当代现实系统去细察在现实中已经发生的局部变化,并确定这些变化的准确形式。福柯说:“与20世纪一些最糟糕的政治体制所重复提出的新人方案相比,我宁愿选择在过去20年来在一些有关我们的存在和思想方式、与权力的关系、性关系以及我们看待精神病或疾病的方式的领域中被验证为可能的特定变化,甚至我宁愿选择在历史分析和实践态度的相互关系中已经发生的局部变化。”[19]
福柯从来就不信任一种超出特定现实之外所构想的普遍必然的全球总规划,这种总规划或普遍理想要么是天真与善意的空想,要么会变成与权力合谋的暴力(普遍强制),真正的变化一定要有现实的可验证的依据,因此它只能是实验性的(因为没有先验的保证)、局部的(因为没有普遍的现在,由不同的历史造就的现在是多元的)。
不过,福柯也指出这种历史的-实验的批判虽然要避免形而上学的种种诉求,但绝不意味着它只在无序和偶然中进行,它有自己的赌注、类别性、系统性和普遍性。
福柯说启蒙时代有一种伟大的希望或诺言:人支配物的技术能力的增长和人对人的自由的增长会同步而成比例地发展,但启蒙以来的事实却是:人对物的支配性技术能力增加了,而人对人的自由却减少了,因为随着技术能力的增长,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权力与现代技术越来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今天对现实所进行的历史的-实验的批判下了这样一个赌注:“如何可能将能力的增长与权力关系的强化分离开来?”[20] 这是一种赌注式的希望或理想,它来自于对现实的分析,但却没有未来的必然承诺。
福柯认为他的历史批判也有自己的类别性,只不过这种类别性源于他所研究的诸实践系统而不是凭空虚设。福柯认为诸实践系统由两个方面或两大类型所构成:1.决定人们做事之方式的合理化技术(所谓技术方面);2.对他人行为做出反应并在某种程度上修改游戏规则的自由(所谓策略方面)。因而对诸实践系统所进行的历史批判当以这两个方面为不同类型的参考领域,此即历史批判的“类别性”。
此外,诸实践系统源于三大领域:1.对物进行控制的关系领域;2.作用于他人的行为领域;3.与自己的关系领域。这三大领域既相对独立而自成系统,又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大的系统。对物的控制以与他人的关系为中介,而与他人的关系又总是依赖与自己的关系,反之亦然。福柯从这三大领域概括出三大轴线:知识轴线、权力轴线和伦理轴线以及相关的三大问题:我们如何被构成具有知识的主体?我们如何被构成行使或服从权力关系的主体?我们如何被构成有我们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这三大轴线和三大问题构成了福柯所谓的“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the histor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的对象领域和问题空间,它有自己特定的系统性,其他一切问题都隶属于该系统。
福柯还指出他所谓的历史的-批判的调查也具有某种有限度的普遍性,这种调查虽然不提供什么历史之外的无限度的普遍真理,但它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比如“神智健全与神智不健全”、“疾病与健康”、“犯罪与法律”以及“性关系的功能”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西方历史上反复出现,至少对西方来说它们是普遍的。除此之外,这些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化模式(modes of problematization)相对于这一时期也具有普遍意义。
到此为止,我描画了一张福柯思想的地图,并想以福柯所谓“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来给它命名。1983年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回忆了小时候一些历史事件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他说:“历史、个人经验与我们参与其间的那些事件的关系使我着迷。我认为这是我理论欲望的核心。”[21]“历史”让福柯着迷,不过,福柯之着迷历史乃是为了思考“现在”,历史只是作为“现在的历史”而让他着迷。福柯的现在是一个有生有死的历史性的现在,而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现在。与尼采一样,福柯彻底杜绝了在世界历史之外寻找另一种大写的存在(Being)来理解和规定世界历史中的小写的存在(beings)的形而上学思想,坚持在世界历史之中思考一切存在,尤其是我们自己的现在,因此,福柯的哲学是一种“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这种存在论的基本构件不是五花八门的与历史不相干的哲学术语,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与事件。这是一种让历史言说哲学的哲学,是一种从历史的血管中流出的多少有些血腥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是分解为具体的知识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哲学的尸体。这种对我们自己的现在进行自由批判并对我们自己的现在负有责任的存在论绝不是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一套正在积累中的恒常知识,而是一种态度、一种ethos、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所做的批判既是对那些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界限做历史的分析,也是对超越这一界限的可能性做一种实验”[22]。一种将自己从自己身上分离出来而朝向死亡的自杀实验。
让不死的形而上学永垂不朽吧,福柯却让我们面对“死亡”,因为在这里“死亡离开了它古老的悲剧天空,成了人类的抒情内核(the lyrical core of man):他那不可见的真相,他那可见的秘密”[23]。
标签:哲学论文; 康德论文; 现代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论文; 福柯论文; 存在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现代哲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