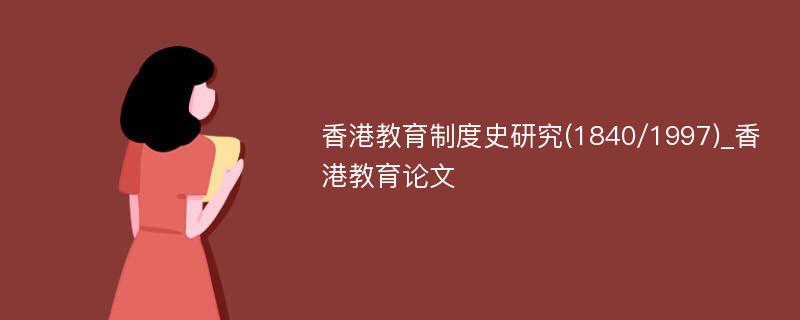
香港教育制度史研究(1840—199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史研究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香港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石器时代,香港地区就有中国先民在此居住与生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分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香港地区属于南海郡的番禺县,从此香港便正式纳入了中国的行政版图[①a]。近代以前,其文化教育与内地无异,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所习者不外乎子曰诗云,以致仕为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据了香港。香港教育从此走上了与内地迥然有别的发展道路,其教育制度也被打上了明显的殖民主义烙印。1984年,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如今,香港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教育史也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为了有利于“九七”以后香港教育的平稳过渡与顺利衔接,促进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回顾和总结英占时期香港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探讨并揭示其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因此,研究香港教育制度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由于多方面原因,香港教育制度史在以往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40年代末阮柔先生出版的一本《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1948年版)以及其后人们零星发表的若干论文外,多年来鲜见专门的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面世[②a]。即便是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也在观点、资料等方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从深化中国教育史研究(包括香港教育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研究香港教育制度史也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为指导思想,以香港教育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和整理为依据,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对英占时期香港教育制度的演变过程、性质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剖析,以揭示其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利于香港教育在“九七”之后继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在正文展开之前,需要说明三点:1.教育制度的定义。教育制度一般指各种教育机构的系统。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一是泛指有组织的教育和教学的机构体系,包括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制度;一是专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①b]。本文取第一种用法。考虑到港英当局一贯奉行行政主导,故本文在论述程序上是先教育行政后学制系统。2.日占时期的取舍。由于日军占领香港仅三年多时期(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在香港被外人占据的150多年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加之日军此时忙于战事,虽竭力推行殖民教育,但往往有心无力,绩效不彰。故本文未将日占时期的香港教育制度单列一节加以论述。3.英占时期的分期。本文依据国际和中国政情的变幻、港英当局教育政策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香港学校教育制度完善的程度,将英占时期香港教育制度史分为英占初期(1840—1900)、英占中期(1901—1941)和英占后期(1945—1997)三大段。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大致的。
一、英占初期的教育制度(1840—1900)
19世纪中叶,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泥沼,香港岛就是在这个时期被英国强占的。从此,香港教育被烙上了殖民主义的印痕。
(一) 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英国占领香港之初,并不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是将之交由英国圣公会、罗马天主教会和英国伦敦传道会分别办理。直到1847年12月6日,港府才在《香港政府宪报》上宣布以每月10元的标准资助三所中文学塾,并成立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
教育委员会是在香港出现的最早的专责教育管理事宜的机构,其组织方式来自英国,设置的目的无非在于逐步加强对香港教育的影响,其时以宗教教育的渗透为甚,1847年3月13日,戴维斯总督在给殖民地事务部的信中表达出这样一个愿望:“倘若这些学校将来能够完全由受过新教的传教士所薰陶的基督徒担任教员,那么教导香港当地居民,使其皈依基督教便大有希望了[②b]。”
1851年,接受政府资助的学塾增至5所,至1854年完全归由港府接管,时称“皇家书馆”。1857年5月,港府设立视学官,负责巡视及监管所有的皇家书馆,首任视学由德国传教士罗传列牧师担任。为使管理工作能达到控制学校的实质性效果,他订定了一套《皇家书馆则例》,规定对学生实行按班级管理,要求教师备有完整的学生名单、出席登记表及教学纪录,以便视学随时查阅。这是香港最早的一份学校教育管理条例,对健全学校行政制度多少有些意义,但用意更为明显的恐怕是规定学生要尊敬外国人,“遇有任何欧籍人士,特别是政府官员到校参观,进入教室时,教师要令学生起立致敬[③b]。”
事实表明,英国统治香港岛的初期,香港教育基本上处于教会势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教育行政机构操纵在教会人士手中,学校教育实际上已成为传教和巩固英国统治秩序的辅助工具。
19世纪60年代前后,英国政府开始改变以往对于教育的态度,加强对教育的控制,促其走向世俗化。英国国内教育状况的变化影响到了香港。其时,中国内地战乱频仍,大量人口辗转至港,造成学龄儿童人数大增。而港内中文学塾水平有限,教会学校又于50年代初陷入困境,更促使港英当局开始加强对教育的控制,与教会争夺香港教育的主导权。于是香港教育事业的重点从19世纪60年代起始由宗教教育转向世俗教育。
1860年,教育委员会被改组为教育局,成为专管官立学校的政府机构。推崇世俗教育的理雅各此时已成为该机构的实际操纵者。是年7月3日,理氏在教育局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教育革新计划”,后来又以书面形式刊登在《香港政府宪报》上,建议创办中央书院,重视英语教学。
1862年中央书院成立,首任校长由史钊活担任。史氏同时又兼教育局视学,负责监管全港所有官立学校。至此,香港教育事业始脱离英国国教会的控制,由政府官员管理,直接对总督负责。从本质上说,革新计划是一项脱离英国国教的计划,它主张对世俗管理取代会督统治,即将世俗主义引进圣公会的教义中去[①c]。
史钊活承袭了理雅各的世俗教育主张,并付之于实践。香港教育的世俗化基本上是在他的努力下逐步实现的。1865年,教育局扩大为教育司,他出任教育司的首长,继续引导官立学校脱离教会的影响。史氏在职近20年,1879年由欧德礼继任视学,而中央书院校长则另有黎德担当。由于两人意见相左,终导致中央书院脱离欧德礼控制,成为一独立机构,直至黎氏离任后方又重归教育司管理。
(二) 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中文学塾在英军登临港岛之前就早已产生并得到发展,它是英占之前香港唯一的初等教育机构。从整个中国教育史来看,它构成了近代新式学制正式建立以前中国教育的主体。
香港开埠以前,这些私塾规模不大,既没有严格的程度划分,也没有明确的教学年限的规定,私塾里所设课程以读书习字为主,同时重视道德、人伦的陶冶。常用教材为传统的“三、百、千、千”,这些学校在中国内地废除科举制度之前还是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②c]。
香港较早的西式学校是教会人士开办的。教学学校的出现,标志着香港现代教育制度的滥觞。在港岛最早创办教会学校的宗教组织是马礼逊教育会。1842年2月,英国驻华使臣兼商务监督璞鼎查接受该会理事会申请,拨地供他们修筑校舍。是年11月1日,马礼逊书院由澳门迁至香港,不久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声誉最隆的一所教会学校。继马礼逊书院迁港,美国浸信会、伦敦传道会、英国圣公会、美国公理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等俱纷至沓来,建校传教。
1873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补助书馆计划》,对教会办学极力鼓励和支持,激发了基督教学校的兴办,而1879年补助计划的修订,对宗教内容的认同则连天主教学校也踊跃加入受补助之列。到19世纪末,接受政府补助的教会学校数目已达101所[③c]。这些学校多为初等教育性质,常实行免费教学,课程除圣经、英文等西方科目外,也设有中国文学、写作、历史和地理等传统知识。
英军统治香港之初,当地居民出于对侵略者的憎恶和对一种外来制度的隔膜,很少有人愿意进西方传教士们设置的学校求学。这种情况促进了中文书塾的发展,1844年港府首次公布这类学校数字为7所,[④c]次年则增至9所,学生145人。[⑤c]1847年港府首次对3所学塾实行资助,1851年增至5所。据港府的中英文通告称,这些受资助的中文学塾可由政府提供教室以及教师薪金,学生只需每月给教师铜钱25文,“以作茶资之用”,而不必交纳学费。
1854年,该5所学塾完全免费,成为港岛最早的官立学校。它发展很快,至1859年,已由最初的5所增到19所,学生由102人上升到937人,每年由港府拨给的教育经费亦由125镑增到1,200镑[①d]。官校中开设初级中文、中国经典、地理及英语科目。
自19世纪60年代始,香港教育事业的重点转向了世俗教育。1860年7月,理雅各建议停办所有位于维多利亚城的皇家书馆,把全部学童集中于一所新的中央书院[②d]。后获港府支持。1862年2月,中央书院正式开学,其后,未并入该校的皇家书馆成为纯粹的中文小学,为中央书院提供生源,1864年,中央书院共有学生120名,该校起初只分为初级中文班和高级英文班,经过几年以后又增加了预备班。课程有中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等,1868、1869两年还陆续增设了代数、自然、化学和几何学,并启用了一间实验室。
该校创办之初以招收中国学生为主,后逐步重视英语教学。1878年2月轩尼诗总督召集了专门研究英文教学问题的教育会议,决定改中央书院每天学习中英文各4小时的制度为5小时英文教学和2小时半中文教学。英文定为必修课,中文则改为选修,所有官立学校都被要求讲授英语,正式确定“重英轻中”的教育政策。该政策对香港学制的发展影响深远,轩尼诗的继任者们对其奉行不违。1895年时规定新设学校若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便不能获得政府补助。港府甚至于还停办官立中文学校及学校之中文班,直到1902年才准予恢复[③d]。
19世纪时香港除西医书院外没有其他大专学校。该书院完全借鉴英国办学模式,课程设置也与英国各医科学校没有太大的差别,任教者多为居留香港的外籍医生,且以在英国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者居多。学制5年。1912年香港大学成立时,并入其中成为港大医科。
此一时期可视为香港教育制度发展的奠基阶段。
由于英国刚刚通过三项不平等条约占据了香港,主要精力始终放在建立统治秩序、维护局势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事项上,对教育的发展则基本上沿袭英国惯用的“不干预”政策,只是鼓励教会及私人团体去从事教育事业,政府则适当地给予资助,摆出“低限度承担”的姿态。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英人的这种“不干预”决非纯粹地放任教育发展。首先,港府于60年代初从教会手中夺回了对公共教育的管理权,并任命视学官专司其责;其次,多次成立有关委员会对香港教育进行检讨,并在《香港政府宪报》上逐年刊登香港教育的年度报告,制订有效的教育政策和方针;再次,许多港督也通过召集会议、签署法令、视察学校和发表讲演等形式,对香港学校各方面工作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另外,逐渐增加教育投入,实行经费资助,以影响学校发展。1853年教育经费在当年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仅为0.3%,以后则逐渐增长,1863年为1.07%,1873年为2.14%,1883年为3.08%,1893年为4%,[④d]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港英当局对教育的控制和影响的加强,其结果促使了香港教育行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发展是有相当限度的。
从学校设置方面来看,官立学校系统中有了初等教育机构和中等教育机构,后期甚至出现了接受政府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但各级各类学校之中,仍以小学程度者居绝大多数,各级教育机构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上下级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官立学校、资助学校和私立学校各成系统,缺乏一种统筹力量,彼此间的关系亦未理顺。显然,港英当局开办和资助这些学校的动机,是希望通过这些教育机构培养出对香港及中国内地产生影响的亲英势力。1868年史钊活在该年官立学校年度报告中,认为“部分中央书院的中国学生通过考试后进入由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就职”,具有“显而易见的间接的好处”,这些“好处”不在于获得与教育经费等价的短期效益,而在于帮助港英政府实现其“更高的目标。”[①e]1902年香港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对皇仁书院的这种作用表达得更为露骨:“从大英帝国的利益着眼,值得向所有愿意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的中国青年提供这方面的教育。……本殖民地的额外支出微不足道,而英语的传播,对我们大英帝国友好感情的传播,使英国在华得到的收益将会远远超过这笔费用[②e]。”
二、英占中期的教育制度(1901—1941)
随着外来侵略逐渐加深,民族灾难日益沉重,中国终于在1900年爆发了以反帝爱国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它声势浩大,沉重地打击了各国侵略者在中国内地的嚣张气焰。其强劲冲击波也扩散到香港,震慑着港英当局,迫使他们改变统治方式,加强买办阶级的培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香港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 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1901年,伊荣出任视学,初期皇仁书院不为所辖。1909年,黎德校长离任,香港的官立学校包括皇仁书院在内便完全由一位教育司统管。教育司成为香港最高的教育行政长官。是年4月8日,港府正式任命伊荣为香港第一位教育司。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种政治活动广泛渗透到香港学校中来,引起了港英政府的极大恐慌。为加强对香港所有学校的监督和管理,港府于1913年8月8日经立法局通过了《1913年教育条例》,这是香港有史以来首次经由立法程序通过的教育法规。《教育条例》公布以后,所有的公、私立学校,均须接受政府的监督。条例规定,所有学校(获得特别豁免者除外)一律要依法向教育司署注册,并要遵守《教育条例》的各项规定。未经正式注册的学校被认为是“非法学校”,其主持人可能被起诉罚款。该条例为后来香港教育行政提供了依据和法律保证。
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使接受教育司视察的学校由60余所猛增到1200余所。教育司署在扩大管理范围的同时,也增加大了管理的难度。为此港府于1920年成立一新的教育委员会,以辅助教育司改善与发展香港教育,当时规定委员名额除教育司、英、汉文高级视学官3人之外,再由政府委派9人,计12人(1923年后增至15人),教育委员会主席由教育司兼任。
英、汉文视学官负责香港、九龙、新界各学校的一切教育行政事宜。凡学校教科书的审定、学科课程的进度、校历的规定、假期的颁布、学费的征收、教授法的指导、学校图书的购置、仪器设备以及学生会的组织管理等等,皆归其监督和检查。其中首席英、汉文视学官分别管理在香港教育司署注册的英、汉文学校,其余的视学官分东、中、西、九龙、新界等区,各自负责巡视该区的英、汉文学校。同时设有体育、音乐、美术、手工、地理等专科视学官,轮回视察全港地区的学校,并负责指导各校专科教员的教学及各种教材、教具和设备。视学官之下,设有视学员,专门辅助视学官执行行政事务并视察各校[①f]。
中国内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度大力支持香港的私立中文学校,但由于两地在编制、设备、师资,尤其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使双边活动的开展存在着障碍。中国教育部乃于1931年在4月22日令广东教育厅通告香港各私立学校,要它们在港府注册的同时,也依照私校规程向广东教育厅立案。同年秋季,侨务委员会成立后,由该机构主管侨校的调查、立案和监督指导事宜,因而大部分的侨校,除了在香港注册,取得合法地位外,还在广东教育厅立案,后来,又向侨务委员会立案及教育部备案。
中国政府对香港侨校的积极领导与协助,使港府深感不安,它们担心中国势力在香港滋长壮大,1932年港督会同议政局,按照《1913年教育条例》第26条第12款,又订立了《规例25条》,其中对课室限额、卫生设备、消防设备、教育注册、课程时间、惩罚学生等均严加规定。次年6月20日,予以增修后再行通告。从此,香港教育条例的规定日形紧密,执行方面也较以前更为严格。
(二) 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1901年,港府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对香港教育的现状和未来进行研究,在其次年发表的报告书中,提出了指导其后教育发展的二项重要政策,一为加强英语教育;一为推行精英教育。1903年港府修正教育补助条例,大致上依照该报告书的建议,教育的主要对象是上层华人子弟;英文学校远较中文学校获得重视。一时间接受政府补助的教会学校纷纷开设中等学校课程,新办学校也以中学居多。接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上升率(60%)明显增加,远远超过接受中文教育学生的增长率(10%)[②f]。
香港大学的成立也是上述政策的集中反映。该校于1912年正式创办,仿英国大学模式,采英文为教学语言,是所不折不扣的以英式教育为蓝本的帝国大学。来此求学者绝大部分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毕业后几乎都跻身于香港的上层华人阶层。港大初设医学、工科两科,继设文科。文科和工科学制4年,医科学制5年,入学考试以医科要求最高。香港大学是香港第一所可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从此香港出现了由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较为完备的学校体系,它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学制系统化的开端。
据1938年香港教育司的统计数字,香港有各类学校1249所,学生总数104,134人。其中除了香港大学由香港总督直接管理和6所英文学校(圣士提反男书院和5所由驻军办理的英童小学)获豁免视察外,其余各中、小学都接受教育司署的监督、视察和管理。根据其办学经费来源的不同,可将它们大致分为官立学校、政府补助学校和私立学校三类。
1.官立学校
官立学校是指由港府拨款建校,由教育司署直接管理的学校。根据种族不同可将官校分为英童学校和非英童学校,共20所。其中官立英文小学一般有两种修业年限,一为5年制,即从第8班到第4班;一为3年制,从第8班到第6班,进入第8班的新生必须曾在中文私塾接受过4年教育。英文小学的最高班为第四班,毕业生可投考皇仁书院和英皇书院的第3班。汉文学校初沿用传统的4年制,1933年又根据中国内地学制,实行“6·3·3”制。
除师范学堂和汉文小学外,20所官校中竟有16所为英文学校,可见港府严格执行着重英政策,对中文教育则不屑于发展。1935年,英国教育家宾尼应邀来港,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对上述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后提交了《宾尼报告书》,建议港府要重视汉文小学教育,重新确定英语教育的目标,认为英语只具有应用及职业上的价值,水准无须太高,其他时间应努力发展中文教育,要港府将教育政策逐渐转变成为“第一,提供每学生足够的华语训练,使他们用于思考及表达;第二,进一步提供英语训练,以满足就业的需要[①g]。”但从日后的实施情况来看,港府根本未听取该报告书意见,中文小学教育只到战后才始获重视。
2.政府补助学校
政府补助学校是指由香港各教会及各团体筹捐款建校,由各教会、团体及私人管理呈请香港教育司署注册,并获政府经费资助的学校。根据其资助经费数额的多寡,又可分类,多者为补助学校,少者为津贴学校。其中各类补助学校计18所。津贴学校的数目远大于补助学校数,计281所,学生21,777人,其中既有英文学校,也有汉文学校,还有旧式私塾。
在1940年以前,大部分英文书院编制与官立英文学校相同,其课程设置也与官校相差不大,但对圣经科尤为注重,通常由教师或神父亲自讲授,考试时该科必须及格,否则不予升级,学生还被要求参加祈祷、做礼拜等仪式。女书院另外设有家政、音乐、钢琴、美术等科,任由学生选修,不过要收学费。汉文补助学校则采用“6·3·3”制,以中文教学为主,某些课程也用英文教学,由英国人教授。其毕业生可参加香港大学入学试;不过协恩中学是个例外,它的课程是准备学生入读中国内地大学而非香港大学的。另外由于它与圣保罗书院和英华女书院三校是汉文学校,故所得政府补助也远低于英文补助学校。
3.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是指完全由私人投资开设,在香港教育司署注册的学校。数目高达932所,注册学生数65,230人。根据程度可分为中学和小学;根据语言可分为英文学校和汉文学校;根据教育性质又可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具体地说,其中有145所英文学校(6所中学、133所小学、6所职校)和778所汉文学校(101所中学、675所小学、2所职校)。所修课程,具体编制,大多同前述学校没有太大的差别。
很显然,此期为香港教育制度的成型阶段。
就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而言,首先,港府设置了教育司署,任命了教育司,将整个香港教育置于统一管辖范围之内,解决了从前各类学校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为日后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确定了路向,构划了具体的功用特征。其次,制定了《教育条例》和《教育规例》,明确了教育行政必须依循的规则,使管理工作法规化、程序化。这些皆已具有典型的现代教育行政的特征。在学制发展方面,中等教育之上出现了与之衔接的高等教育,确立了由私塾而至英文中学,再至香港大学的上下一贯的体制。因此,无论是教育行政制度,还是学校教育制度在此期间皆迈出了发展的一大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制度的模式,是基本以此为蓝本,逐渐趋于完善的。
但是,客观地说,由于港英政府一贯地对教育采取消极保守态度,这种教育制度还很不成熟,挂一漏万之嫌实所难免。尤其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殖民因素充斥其中,如以英文学校为发展重点,漠视中文教育的存在;高级行政人员须由英人担任,从官学生中招取,[②g]未接受过英式教育的人至多成为助手,不能主事;香港大学建校目的是为港英当局培植亲信等,时时处处流露出阶级差别和等级歧视。甚而至于,还专门为英籍儿童开设学校,以别于华人子弟。根据港府制定的教育政策,“英国的儿童由政府另设学校来教育他们,不与种族不同、信仰不同的儿童混杂[①h]。”港府办有3所官立英童小学和1所英童中学,加上由驻军办理的5所英童小学,构成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系统,即由英童小学,至英童中学,最后以考升英国剑桥大学为目标。而为华人子弟办理的学校则构成另一系统,经由私塾,8年制英文中学和香港大学完成教育,从而形成鲜明的双轨制特征。
三、英占后期的教育制度 (1945—199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香港教育面临着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大量内地人口涌入香港,同时香港经济开始发展并逐渐转型,这些都向香港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港英政府迫于形势和压力,对旧的殖民地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因势利导,改革教育体制,修正低限度承担原则,以普及教育取代“精英教育”,逐步建立以智力投资为主导的、适应本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一) 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香港重光以后,港府重组教育司署来管理教育事宜。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也获得了较大的进步,推动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亦随之渐趋完善。1980年11月20日,教育司署的中文名称改为教育署,其首长称为教育署署长,并沿用下来。教育署署长下设副署长1人,高级助理署长2人,分别负责学校服务和策划与发展两大部门。助理署长7人,分管辅导视学、课程发展、策划研究、建校、学位分配、辅导服务、学校行政、专上教育及语文教育学院等工作。1981年教育及人力统筹科(简称教统科)成立,1983年改为现名,它直属布政司,下辖教育署、工业教育及职业训练署和劳工署等3个署,是香港最高教育行政机构。
由此可见,香港教育的领导与管理大致可分为3个层面。最高层面为教统科和教育统筹委员会(简称教统会),中间层面是教育署和教育委员会、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工业教育及职业训练署和劳工署;第三个层面是学校行政组织。
教统科在教育方面负责统筹、总管和决策工作,由一位司级官员掌管。教统会虽为港府教育方面的最高咨询组织,但带有制订政策、统筹规划教育的性质,它是1984年根据国际教育顾问团的建议设立的。主要职能是收集并研究教育委员会、职业训练局和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关于教育发展的建议,然后向港督和行政局提出综合意见。其委员会成员有16名,其中包括上述3个机构的主席。
中层机构大体分为行政执行机构和咨询参谋机构。行政机构里,教育署负责执行政府的教育政策,并按照《教育条例》监察香港的幼稚园、中小学及部分专上学院。教育署执行《教育条例》管理学校,主要是通过学校注册、校董注册和教师注册等去进行,并由署内辅导视学处负责提高教育质素,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在具体的教育管理过程中,教育署实行行政分区制度,以使监察学校的工作更形严密,与各校联系更为有效。工业教育及职业训练署是职业训练局的行政机构,1982年设立,署内大部分的职员直接为训练局工作。训练署的署长又是训练局的执行干事。该署为训练局开展各种训练业条提供服务。
咨询机构中,教育委员会是香港法定咨询组织,是由1920年成立的教育委员会发展而来,对制订或修改教育政策负责提出建议,并对各阶段的学校教育负责有总体监督的责任。教育署署长为其成员之一,出任副主席,教育署要为委员会提供一切所需服务。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是政府同各独立院校之间的联系组织,1965年成立,职责是对维持和发展高等教育所需经费提供专业性意见,策划大学及理工教育的发展和建议。职业训练局具有咨询和执行的双重任务,1982年成立,其职责是配合香港工业发展的需要,向总督提供全面的工业教育和训练的规划,开展和推行职业训练计划,设立和办理工业学院和工业训练中心[①i]。
上述咨询组织与政府行政机构各有分工,互相配合,并受相应法律条例的规范,构成一种比较严密的教育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在客观上会有利于教育行政工作快捷、有效地进行,但港英当局设置各机构的意图主要在加强对教育部门的控制,这一点始终未曾改变。
至于学校行政组织,官立中小学直接由教育署管理,委派校长负责一切校务。资助各私立中小学由校董会管理,校董会聘任校长和教师,并在校董中推出一人注册为校监,代表学校与教育署和政府其他部门进行接洽,校长为学校首长,主要负责对外校务,对内校务通常聘请副校长和若干教师协助处理。资助中学的组织中,校长属下还设有一个行政咨询委员会。在高等院校方面,经注册为认可专上学院者,均设有校董会、院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等组织,分管行政、产业和学术事宜,院长为其行政及学术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辖下的7所院校在行政上是自主机构,设有校董会、校务委员会、教务委员会和评议会等组织,各有分工,共同管理校务。校监由校董会主席担任,为大学的最高负责人,校(院)长由校董会聘任,为院校行政的具体负责人。
港府在健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同时,又制订并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在香港基本实现以法治校。1971年颁布的教育条例脱胎于《1913年教育条例》,后经数次修订而成一套完整法规。它详细规定了学校注册、校董会结构、教员招聘、学生编制、收费、卫生及安全设施等内容。各级各类学校均须遵循不同的条例和规例(如《幼儿中心条例》、《专上教育学院条例》、《学徒条例和规例》等),资助学校须受到《学校资助条例》的监管,独立的大学也制订有相应的法例。这些教育法例和规例的制订和执行,对保证学校的规范化和科学管理,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仍然保留着香港教育管理过度集权和带有旧式殖民地管治色彩的特征,如《教育条例》规定,禁止在校内进行政治活动;学校只能按教育署批准的课程纲要授课;如无港督的书面批准,学校不准举办教师训练课程等。
(二) 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现代香港教育依次分为连续的4级: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1.幼儿教育
香港教育当局长期不重视幼儿教育,对幼儿教育一贯采取放任政策,进入80年代后,这种状况才稍有改观。1980年《小学及学前教育》绿皮书发表;1982年实施幼稚园入学年龄和小学入学管制;1985年颁布了《幼稚园课程纲要及指引》;1995年正式推出幼稚园资助计划。这一系列政策规定,目的在于减轻幼儿的学习负担、改进教学方法,从而正确引导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香港幼儿教育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由教育署管辖的幼稚园,招收3—5岁儿童入学,多为半日制,师生比例规定为1∶20。另一个是由社会福利署管辖的幼儿中心,带有托儿所性质,招收2—5岁的儿童,多是全日制,师生比例是1∶14。迄今为止除一所官立幼稚园外,其余皆为私人团体主办。1993年,全港共有187,549名3—5名岁幼童在730所幼稚园就读。
2.初、中等教育
香港的中小学制度,在1963年前曾出现中文(“6·3·3”制)及英文(“6·3·2”制)两大系统,其后统一形成了当前的“6·3·2”制,即小学6年(6—11岁),初中3年(12—14岁),高中2年(15—16)。中六教育(又称预科教育)原分为2年制和1年制两类,到1992年统一为2年制。
(1) 小学教育
1935年的《宾尼报告书》及1951年的《菲沙报告书》都向港英当局提出了加强小学教育发展的建议,港府也对战前长期忽视小学教育的情况有所省悟,并开始以比较积极的态度对待教育事业。虽然港府于1950年和1951年分别制订的“十年建校计划”和“五年建校计划”未见实效,但1954年拟定的“小学扩展七年计划”,则成功地增加了大量小学学额。到1971年,港府终于实现了小学教育的普及。
按照1983年实施的小学一年级入学办法,凡年满5岁8个月的儿童,都可依照“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分配到附近的小学去接受免费教育。1994年,全港有小学生476,847名,小学884所[①j]。小学分为官立、资助和私立3类,大多数小学采用半日制,学生分上、下午班上学。小学的师生比例是1∶27,教学语言基本上是中文,只有少数几所例外。1978年以前,小学毕业生要参加“中学入学试”,甄选约30%的学生入读官立及资助中学,造成严重的升学压力。自1978年开始,以“中学学位分配法”代替了“中学入学试”。其方法是,把全港分成25个学校网,每个学生根据原校最后两年的学校评分、学能测验和家长对中学的选择为基础,然后作出电脑派位。这项措施舒缓了小学升中学的压力,不过仍有不少学校为求学生能入读区内名校,继续进行强化训练。
(2) 中学教育
小学教育普及后,港府将发展重点集中到初中教育方面,1974年发表了《香港未来十年的中学教育白皮书》,建议将普及教育扩展至初中。于是港府不断兴建新中学,改建部分小学为中学,实行浮动班制及向私校买位,以增加学额。1978年,9年制义务教育得以实现(包括3年初中)。接着,港府又发表《高中及专上教育发展白皮书》,将注意力转到高中及专上教育上去,并建议60%的15岁学龄儿童可获分配中四资助学位。除兴建新校外,港府又改建实用中学为工业中学,在职业先修学校开设中四、中五课程和重整某些学校的班级结构,以提供更多高中学额。
目前的中学学制是初中3年,高中2年,所有中学都从中一办到中五。中学大部分是全日制,师生比例平均为1∶21.8。1994年全港的中学生有458,199名,在484所中学就读[②j]。根据经费来源和管理机构的性质,香港中学可分为官立中学、资助中学和私立中学;按照中学课程的性质,又可分为文法中学、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还可根据教学语言将中学分为英文中学和中文中学。
(3) 中六教育(预科教育)
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文中学将6年改为“5.2”制,定预科为2年,其毕业生通过“高级程度会考”升入3年制的香港大学。1960年中文中学改制,将6年改为“5.1”制,定预科为1年,其毕业生可通过“高等程度会考”升入4年制的香港中文大学。有必要指出,“预科并非国际普遍的教育制度,除英联邦以外,其学科成绩并不完全获得认许”,可见,这种制度是否有存在必要尚有问题,许多人认为它不适合香港,应该废除[①k]。但港英当局很会随机应变,它承认预科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如课程艰深难懂,完全以考试为目的,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学制不统一等,并显出积极改善的架势。如今学制是统一了,课程也稍有变化,但实质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预科作为英国的特产继续保留着。1995—1996年度有中六学生5万人[②k]。
3.高等教育 (专上教育)
香港在向国际性的金融、贸易及工商业中心发展进程中,对高科技、高技术及其他专业知识的人才需要也日甚。除扩大香港大学外,1963年10月,在合并3所私立书院的基础上开办了香港第二所综合性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而香港的高等教育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却是80年代。这时,港府一改主要鼓励私营专上教育的政策,先后建立多所院校,如城市理工学院、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公开进修学院等。1990年7月,港英当局提出了一个大量扩展高等教育的计划,即计划到1994—1995年度,使适龄青年修读学士学位的比例达到18%。高等学校一年级学士学位的学额达到14,500个,再加上非学位的大专课程的学额,入读高等学校的适龄青年人数将占25%左右[③k]。企图把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延续到“九七”以后。
除了大中小学教育外,港府也非常重视职业训练,先后建起了2所科技学院、7所工业学院和19个工业训练中心,为生产和管理第一线培养从操作工到技师的各种技能等级的人才。同时,为失明、失聪、伤残、弱智、缺乏社会照顾、情绪问题及学习困难人士提供特殊教育。还大力发展成人教育,为在职人士提供工余进修,从而使社会各类型人士均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以贯彻普及教育的目标。另外,港英当局对师范教育也比较重视,其教师培训工作主要由两所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完成。其中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育学院开办全日制(1年)及兼读(2年)的教育证书课程。香港教育学院开办4年全日制课程。
这一时期可视为香港教育制度发展的成熟阶段。
经过近百年的探索,港英政府在教育发展上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改变了“不干预教育”的作法,这有利于香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更,更是形成香港教育有别于前期特色的深层诱因。英国国力的衰减、新中国的诞生与崛起、世界范围内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非殖民化”运动的广泛开展,以及香港“经济奇迹”的创造和人口的急剧增长,迫使港英政府对教育政策作出调整,“淡化”了其中的殖民因素,发挥出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某些积极作用。
在教育行政制度方面,香港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有效的教育决策与管理机制。运用教育咨询的方式,协调和发挥当地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加强教育法律法规建设,基本实现依法施教和以法治校;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决策部门和行政部门职能分离制度。从而在教育决策和教育行政的整个过程中增加了一定的透明度,利于政策获得社会认同,也便于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学校教育制度方面,香港比较迅速地实现了教育普及,到80年代末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并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改善办学条件等项措施,保证香港青少年受各级教育机会的均等。同时,鼓励社会各界重视教育,积极兴学,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据198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该年各类学校中政府办的点8%,圣公会占7.5%,天主教会占6.6%,中华基督教会占5.4%,东华三院占3.4%,佛教联会占2.9%,其他(包括同乡会、商会、福利会、慈善机构等)占66.2%[①l]。教会在办学上出力颇巨,1995年教会学校占全港幼稚园的1/4,小学的1/3,中学的1/2以上,另外还有2所专上学院[②l]。社会各界的大力推动以及政府当局的高度重视,为香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另外,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香港极其重视各级各类的工业技术教育,设立了19个工业训练中心、7所工业学院和2所科技学院,中学阶段里还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实用人才培养为宗旨的、多层次的、庞大的教育体系。
当然,香港教育制度的殖民性质仍然没有改变,教育行政制度上港督独裁,行政主导,学制上沿用英式的现象依旧存在,这将在下文里进一步指出。
四、香港教育制度的性质特征
教育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教育意向的具体化,或者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教育需求的具体化。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为英国的。所占据和统治这种所处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其教育制度的特殊性。通过对香港教育制度演变轨迹的回顾,结合对香港所处特殊环境的分析,不难发现,香港教育制度具有殖民性和资本主义性的双重性质。
受英国长期统治期间,港英政府在此强力推行的教育必为殖民教育,精心构建的教育制度必具鲜明的殖民性。香港教育制度的殖民性最显明地体现在以下数方面:
1.培植精英,养成买办。这个特点暴露了港英当局创办学校的宗旨。曾于1878—1897年担任香港视学官长达20年之久,对港英统治阶层内幕了如指掌的欧德礼就毫不掩饰地表示:“在这个时期(19世纪——引者注)几乎没有这种想法,即振兴中国人的社会,使之达到欧洲人的水平[③l]。”而是出于利己动机,企图通过推行英语教育,学习英国地理、历史等项措施,促使中国学生认同英国文化,成为“亲英的传教士”,甚至成为中国“未来官僚阶级的一部分[④l]。”1884年《孖刺报》对当时“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职员和雇员大部分皆是中央书院的学生”这一现象作的评论是“妙不可言”,认为“此事在一段时间内给本殖民地带来直接损失,但在未来却有巨大的间接收获”,即通过中央书院培养“中国官员苗子”,再由他们去扩大英国对华的影响[⑤l]。可见,注重精英阶层的培养是港英当局一贯的做法。1902年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明确提出,要“为少数社会华人提供一全面的教育”,认为这样的“较普及一般华人教育更见成效,因为前者能以其所学影响后者[⑥l]。香港大学也是这种教育政策的产物,港大的设立被认为是一项“帝国投资”,通过亲英份子、买办阶级的培养,可以巩固英国统治。长期来港大毕业生遍布香港各要害部门,成为香港的代言人。
2.港督集权,行政主导。如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前的印度的统治一样,香港也实行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港督独裁体制。港督为香港最高权力代表,行使最高军事、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就教育而言,港督也位于教育行政系统的最顶端,他会同其他行政部门具有最高的教育决策、立法和行政权。《教育条例》和各《大学(学院)条例》中都明文规定,须“服从总督的指导”,否则可能以“港督认为不受欢迎的人”之条款而被驱逐出境[①m]。香港总督由英皇任命,全权代表英国政府管治香港,这种主权在英,权力外来,港督独裁的体制无疑具有深刻的殖民性。与港督集权一脉相承,在政权架构中各种权力的互动关系上又必然是以行政为主导。教育上也不例外,港英当局无视教育规律,滥用行政手段压制民意强行统一预科和大学学制之举便是明证。由于香港的教育制度完全是英国教育制度的翻版,因此,通过行政手段维护香港当前的教育制度,其本质无非在于为香港教育设计一条符合港府意志的发展轨迹,维护既成的利于当局统治的各项制度、措施和政策,以加强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特殊关系的维系。
3.强制推行英式制度。萨得乐曾言:“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一个有机体,系历经长期的困难与奋斗的结果,其本身含有国民生活之隐而未显的作用[②m]。”这种“隐而未显的作用”,实指来自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可见,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制度,绝非移植或抄袭所能奏效,否则难免东施效颦,事倍功半。但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教育不仅在教育宗旨的制定,教育内容的甄选上体现对英国的认同,而且在管理和教学机构的组织形式上也深深地打上殖民主义烙印。其中尤以学制的翻版迹象最为明晰,得港现行的“6·3·2·2·3”制完全是搬用英格兰的模式,它与中国内地实行的、世界上普遍采用的“6··3·3·4”制不能兼容,根本不适应香港的实际需要。杜祖贻先生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1990年年会上提交的论文中指出,英国在香港推行这种学制,其忽视了两个使英国学制得以在英国本土实行的重要因素:年龄因素和语言因素,造成学业年限的“延迟”,再加上课程以考试为中心,结果使许多香港中学生学业与心理严重失调[③m]。在此无意于对不同学制的孰优孰劣作出判断(事实上早有定论),只希望以此说明香港学制已被英国化,并且这种“英国化”是港英当局强加的,其实质便是殖民化。
4.语文政策重英轻中。随着英军登陆,香港便逐步沦于英国统治之下,开始其150余年的殖民化历程,香港原本的单语制社会宣告解体,中英并存的双语制社会代之而起。但客观事实是,港英政府一开始便为中、英双语设制了不平等的发展际遇,使之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享受不一样的待遇,尤其是1878年,港督轩尼诗召开教育会议,定英文为官校的必修课程,中文为选修课程,并规定英文教学由每日4小时增至5小时,中文教学则由每日4小时减至2小时半,正式确定重英轻中的语文政策。自此以后,轩氏后继者们无不奉行强化英语教育的方针,政府政策明显地倾向扶植英文学校,接受英语教育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1912年香港大学正式成立,更标志着香港英文教育已形成系统,达到高峰,成为香港语文教育的主流,而中文则被贬为“二等语文”,不予重视。在英国统治香港的一个半世纪里,虽然中文教育在港人的积极争取下,时断时续地获得过暂时的重视,但重英轻中更是此时期香港语文政策的主要特色。这种以英文为重,并以之为官方主要语言,为教学主要媒介的不合理状况,正是殖民地教育最典型的特征。
因此可以说,从学校教育制度到教育行政制度的整个香港教育制度都渗透着殖民主义因素。
另一方面,香港教育制度又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伴随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在此落户生根。资本主义本身虽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与此前香港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相比,它无疑代表更高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们的更替昭示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进步首先表现在一向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所不齿的“奇技淫巧”在香港大量涌现,如现代的百货商店、洋房建筑、电灯、汽车、飞机、证券交易所、现代银行等,使香港不断受到来自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刺激了香港经济的起步和发展,为英占据后期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最终促使人们在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上发生变化,即促使那些从传统文化母体中成长的一代,去掉其对于新文化的无知和观念上的愚昧落后成份,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最大。因此在英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三种主要文化价值观念(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精神)[①n]也同样支配了香港的社会生活。在香港这种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环境下,人们无论在思想、语言文化、行为、道德和伦理的各个方面都融贯着较强烈的商业资本主义精神和准则,这种精神和准则也反映在香港教育制度上,并对其产生极大影响。如实行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就体现了注重个性培养、个人价值实现的“人人平等”原则;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联系,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批工商业劳动者等则反映出香港人讲求实用,不尚空谈的价值取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究其实质,无非在奉行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遍存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在香港,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实业投资”,受教者希望学得一技之长以在社会上赚钱谋生,施教者则以传授应变能力和实际技能为职志。目前,香港设有工业训练中心、工业中学、职业先修学校、工业学院、科技学院等主要培养实用人才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这固然能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取得一定成效,但所造成的消极面和隐患也不容忽视。因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实用主义则使香港教育仅着眼于眼前的、个人的、经济的需要,忽视了长远的、社会的、全面的发展需要。
殖民性与资本主义性的融为一体是香港教育制度的突出特征。
五、“九七”以后香港教育制度的发展趋势
《基本法》第136条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教育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政策。”如上所述,香港教育制度中既渗透有殖民因素,同时又具有一些较为合理、先进的资本主义成分。因此,“九七”以后香港教育制度如何发展也就成了本文结束前必须论及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九七”之后香港教育制度必定会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逐步的改革。
第一,改变殖民地教育制度为特区教育制度。以往香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英国统治香港和促进工商业发展培植人才。随着香港的回归,教育权的移交,香港教育制度的性质也必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今后的香港教育目标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和繁荣,为“港人治港”培养人才。因此,港英当局为使香港殖民地化而采取的忽视德育、轻视公民教育、漠视母语教学等反动措施必然要得到根除;而代之以加强国家观念和民族责任感的教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地理的教育、做一个好公民的教育,以及实行母语教学,推广普通话,提高中文水平,从而培养对祖国具认同感的香港人才。
第二,教育决策与管理要进一步民主化、科学化。香港目前的教育行政制度依然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如港督独裁,港督对香港教育的发展保持有巨大的影响力,教统会等咨询机构的成员由港府委任,而非民选,教育立法权实际控制在少数人手中,《教育条例》代表的仅是以港督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其内容“仍带有强烈的殖民地色彩,其中有不少不民主和反民主的内容”,[①o]如禁止师生参加政治活动等。学校行政管理层面也一直缺乏一个有效机制监察与评鉴校长的工作,问责制向来是自上而下,忽视教师们的参政议政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出人治的环境[②o]。随着今后香港政治制度民主化、自治化程度的加深,实行教育民主化,做到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充分发挥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也将是势在必行的。
第三,加强整体规划,建立合理的学制。香港学制的发展素来缺乏全盘计划,各个环节之间经常出现脱节现象,并且过分套用英国模式,如设立颇遭非议的预科阶段,且修业年限为1—2年不等,高等教育多为难与国际接轨的英式3年制,形成3年制与4年制并存的局面;与此一致,大学入学试制度也呈双轨制;另外,职业先修学校与实用中学日益文法化等。学制不统一使教育行政产生混乱,行政费用上涨,并且对学生造成不良的影响[③o]。而不加取舍、不经整合的生搬硬套又必然会脱离香港的实际。港英当局虽曾试作改善,如统一预科,迫使香港中文大学学制4改3,简化考试制度,划一招生制度等,但所有这些只是限于枝节上的修整,未作整体规划,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后随着殖民教育向特区教育的转变,香港学制会朝向国际接轨的“6·3·3·4”制演变,反映殖民关系维系的预科制度和大学3年制必将逐渐被淘汰。
第四,在教育普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教育质素。自1978年实施9年义务教育后,教育的功能已由筛选精英演化为满足基本教育权利,这显然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但由于重实用与功利等弊端积习日久,人们在广建学校,扩招生员的同时,忽略了对教育质素的要求。结果各种教育问题相继出现,如学生成绩参差,水平普遍下降,部分学生无心向学,违纪犯罪率、辍学率上升等,造成教育质素滑坡。针对这种状况,在稳定香港中小学教育发展规模的同时,必须将提高学生质素放到重要地位。逐步改变以往偏重教育经济功能,忽视其文化功能的倾向,向学生提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将他们培养成既具远大理想、又富实干精神和实干能力的一代新公民,将是未来香港教育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走向。
第五,协调发展,处理好高等教育急剧扩展带来的问题。港英当局过去一向对香港本地大学学额的增长控制得非常严格,直至80年代,大学学额的增长率每年不超过4%。港府趁机以满足家长的期望,香港未来经济发展需要和移民造成的人才短缺为由,采取“突进”的方式,无限扩大大学招生规模。到目前为止,香港有18%的适龄青年能够修读学位课程,若加上在港就读非学位课程及在外地求学的学生,其高等教育入学率已接近30%[④o]。在“九七”将届之时,港英当局一改初衷,作此惊人之举,显然是寄予更深远的政治企图的,即希望“以英式教育培养香港的接班人[①p]。”它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在教育制度本身,如影响到中小学经费的分配,打乱了分工配套的高等教育体系等,更在于替英国统治者在香港留下了殖民的后遗症。因此,香港未来的高等教育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既要稳定它的发展势头,使其与中小学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又要加强在校学生爱国主义方面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培养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第六,顺应时势,建立社会化、开放式的大教育体系。如今的世界瞬息万变,知识更新速度令人匪夷所思。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众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加强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结合,扩展了教育空间,延伸了教育时间,纷纷构建自己的大教育体系,香港也不例外。不过若从适应未来要求的角度来看,香港现行的教育体系还很不健全,不仅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之间配合得不够和谐,而且正规教育本身也没有完全开放,且欠缺灵活的沟通。从而限制了教育资源的充分发挥和利用。因此,鉴于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以及知识和信息量不断增长,本来的香港教育必然会进一步开放正规教育,使之与非正规教育以多种形式相互衔接、配合乃至交融,最终建立一种社会化、开放式的大教育体系。
注释:
①a 元邦建编著:《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6页。
②a 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只有黄仁华的《香港学校制度之研究》(1969年)、Lai.C.CHen的“Main Feature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Hong Kong,1946-66”(1969)和《香港教育制度全面检讨》(香港金陵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部分文章。除此之外,王齐乐的《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波文书局1982年版)、方美贤的《香港早期教育发展史》(香港中国学社1975年版)和香港博物馆编制的《百年树人——香港教育发展》(香港市政局1993年版)等书,也对香港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有所论及。
①b 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陈孝彬主编:《教育管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②b Hong Kong Educational System,Imperial Education Conference Papers,1914,P.2.
③b 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4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页。
①c E.J.Eitel:Europe in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392.
②c 子羽编者:《香港掌故》(二集),香港:上海书局1984年版,第17—18页。
③c 香港博物馆编:《百年树人——香港教育发展》,香港:香港市政局1993年版,第40页。
④c G.B.Endacott:A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42.
⑤c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4页。
①d G.B.Endacott:A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138.
②d 1889年,中央书院(Central College)更名为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又改称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并沿用至今。
③d 方美贤:《香港早期教育发展史》,香港:中国学社1975年版,第61页。
④d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15页。
①e 《香港政府宪报》,第15卷,第10号,1869年3月6日,第92—93页。
②e 《香港教育委员会报告(1902年)》第8页,载1902年《香港立法局会议文件汇编》。
①f 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二),《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②f 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波文书局1982年版,第278页。
①g 《宾尼报告书》,1935年。
②g 所谓官学生(Cadet)是指由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经过公务人员的预备考试,及格后被派往各殖民地接受各项训练的人。因此,香港的高级教育行政人员从本质上说是殖民官而非教育家。
①h 阮柔:《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1948年版,第45页。
①i 何辛:《亚洲“四小龙”教育纵横》,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8页。
①j 香港教育署统计组:《1994年学生人数调查(详细统计表)》,1995年1月印,第5页。
②j 香港教育署统计组:《1994年学生人数调查(详细统计表)》,1995年1月印,第5页。
①k 郭少棠:《大学预科学制改革的论争》,《信报财经月刊》(香港)1986年第9卷12期,第89—91页。
②k “95—96年度中小学生有明显下降趋势”,《文汇报》(香港)1995年2月25日。
③k 吴福光:《析香港教育从“挑选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当代港澳》(广州)1993年创刊号,第68页。
①l 杨奇主编:《英国撤退前的香港》,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
②l "The Schools with Faith in the Future~,In:South China Morning Paper,August 6,1995.
③l E.J.Eitel:Europe in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575.
④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1902,p.39.
⑤l Hong Kong Daily Press,March,4.1884.
⑥l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合编:《香港教育透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①m 陈谦:《香港旧事见闻录》,香港:中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②m 田培林主编:《教育学新论》,台湾:文景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③m 杜祖贻:《香港借用与改进外国理论以利教育实践》,《比较教育研究》(北京)1994年第5期,第43页。
①n 李玢:《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与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上海)1994年第3期,第44—47页。
①o 《快报》(香港)1989年7月10日。
②o 罗永华:《校工评鉴制度的再思》,《星岛日报》(香港)1995年5月15日,22日。
③o 李瑞全:《关于得港学制的一些原则性反省》,载:《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报》(香港)1989年第17卷第2期,第189页。
④o 程介明:《香港要怎样的大学毕业生》,《信报》(香港)1995年7月19日。
①p 梁锡华:《“九七”前后的香港文化》,《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冬之卷,第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