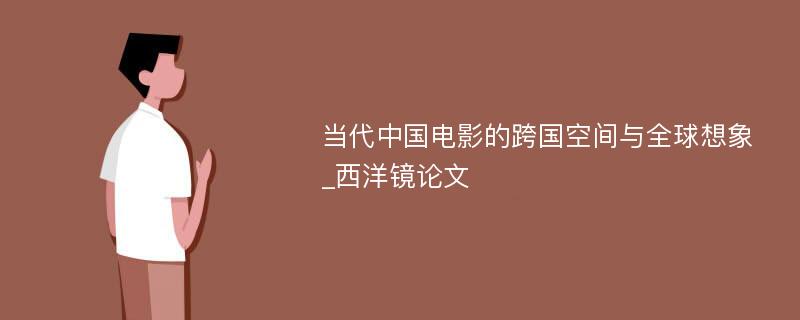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跨国空间与全球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当代论文,全球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8)06-0025-05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r)认为:“通过媒体形成的国际化空间在影片中无所不在。”[1] 在全球化时代,电影中的空间往往超越了原初意义上的空间所指,而形成全球想象,形成了麦克卢汉所谓的“环球村”(Global Village)。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跨国空间,不仅体现在电影文本的运作上,也体现在电影的制作方式上。在电影文本的意义上,一些影片开始在影像和叙事层面直接指涉具有跨地区、跨国界意义的多重城市/国家空间,视觉上的差异与语言上的交杂成为其突出的视听表征。这种空间的建构给观众提供了异国想象和全球想象。在空间想象的背后,想象的主体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尤为引人瞩目。而在电影制作上,进入异国拍摄,跨地区、跨国界的创作班底组合尤其是明星组合,也成为中国电影表达全球想象的重要方式。
一、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国想象与身份焦虑
《不见不散》(冯小刚导演,1998年)、《刮痧》(郑晓龙导演,2000年)不约而同将故事的背景置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导演/观众的“美国想象”,而事实上同时也表达了“中国想象”。
正如影片片名所显示的,《刮痧》的戏剧冲突/文化冲突是围绕着中国人和美国人/外国人对于“刮痧”这样一种行为的截然不同的理解(治疗/虐待)而展开的,并且试图显现中西文化对于父子关系的不同理解。这部间杂着汉语和英语对白的影片,在听觉元素的表象上就呈现出了两种文化的不同表征。而由梁家辉和蒋雯丽分别扮演男女主角,以大陆和香港演员联袂出演,不仅仅是出于商业目的,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不同地域/政治/文化倾向的视觉表征。
在影片的初始情境中,许大同获得电脑游戏设计奖与老霍扮演的兵马俑的并置,有意味地凸显了分别属于现代世界和古代中国的文化表象。如果说,兵马俑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是专属于中国而成为“世界遗产”的话,那么,电脑游戏则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而成为全世界共享的科技/文化产品。一位中国人获得电脑游戏设计奖,正是这种共享文化认同的标志。然而,富有意味的却是,这种成功被许大同(“大同”的名字作为一个符号表征也是很有意味的)看成是实现“美国梦”的标志,却提供了一个“美国=世界”的意识形态想象。“美国梦”事实上也再次被置换为“世界梦”,而这种置换在好莱坞大片中是非常普泛的。取名“丹尼斯”的儿子及其一口流利的英语,则从名字就可以看出父辈对于后辈这种梦想的寄托。
“刮痧”作为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治疗行为在丹尼斯背上留下的“伤痕”,被美国人读解为虐待。这种文化误读的依据,或许首先是因为丹尼斯背上因刮痧而形成的身体表征。这种视觉表征在美国医生和律师看来,足以构成虐待的证据。围绕着这一事件展开的,则是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误读。“西游记”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不但给许大同的电脑游戏设计提供了“中西结合”的灵感,同时也成为美国律师控诉许大同虐待儿子的佐证。尽管它有可能是一种社会现实,但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思维,却多少显得有些简单和牵强,从而在电影文本的意义上构成了对美国文化的简单化、概念化误读。创作逻辑与现实逻辑之间,并不总是构成一致的关系。
影片是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来想象性地解决叙事困境的,正如影片男主人公的名字。不过,“大同”的世界想象更像是一个乌托邦。许大同的美国朋友昆兰到一家摆满中国古董的中医诊所亲身体验刮痧疗法的场景,是影片中最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视觉表象,同时也成为推动叙事转折的“想象的能指”。然而,也恰恰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叙事的转折,影片呈现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峙,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伪命题。无论如何,这种文化认同显得过于简单和匆忙。因为,这样简单化的认同,跟那位美国律师对于《西游记》的刻意误读,其实是出于同样的思维模式。
无论是许大同,还是简宁,都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身份焦虑。这种身份焦虑一方面是来自自身对于身份认同的渴望,这种渴望是透过许大同的获奖来标示的,许大同对于实现“美国梦”的渴望,对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渴望,以获奖而完成了一个成人式,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指涉现实情境中“第五代导演”或者“第六代导演”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频频通过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而成就的艺术/文化加冕仪式。另一方面,也是影片更多企图表达的,是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比起许大同获得电脑游戏设计奖而获得身份认同要艰难得多。认同,或者误读,哪一种是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常态,确实是个很难厘清的问题。在影片中,这两个层面的身份认同是被纠结在一起加以表现的,因为对于《西游记》和孙悟空的误读,使得许大同第一层面的认同渴望产生了危机。许大同的电脑游戏设计之所以获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借助了中国文化中的经典形象,而这一点又恰恰成为被误读的目标所在。这种纠结不但使得文化认同产生危机,也使得许大同已经获得的身份认同产生危机。
相比较而言,直接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李安对于文化的命题表现出了更加宽容的姿态。在他的影片中,东西方文化并不是呈现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他的“父亲三部曲”《推手》(1991年)、《喜宴》(1992年)、《饮食男女》(1993年)都指涉家庭伦理关系、代际关系,并以此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问题。而兼有儒者和长者风范的郎雄,则是贯穿这三部影片的父亲形象。其中《推手》与《喜宴》都涉及了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相交织的文化命题。在《推手》这部交杂着中英文对白的影片中,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视觉表象之一,朱老舒缓沉着、神定气闲的太极拳与玛莎面对计算机的紧张、焦虑、烦躁形成了风格化的对比。朱晓生作为父亲与妻子关系中的一个调停者和中介角色,其实也成为文化交流、沟通,消弭差异、鸿沟的符号,导演借此表达了对于东西方文化未来走向的某种期许。与那种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念不同,在李安的影片中,东方/西方、传统/现代通常都以平等/共存的形式出现。而作为这种主题的承载者,父一代/子一代也不构成肯定/否定的简单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叙事态度同样体现在那部更直接地指涉某种文化禁忌的影片《喜宴》中。同样交杂着两种语言(对白),《喜宴》由于指涉了同性恋这样一个有关文化禁忌的命题,而使得文化冲突相对表面化。高伟同不仅没有真正的未婚妻,而且居然拥有一个同居多年的男朋友赛门,从而与父辈要求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形成了深刻的矛盾,并且触犯了文化禁忌。在一波三折的故事进程中,高伟同、赛门以及与高伟同假结婚的来自上海的年轻画家顾威威建构起一个特殊的家庭,而影片结尾走过机场安检处的高父慢慢举起双手的动作则超越现实所指,而显现为一个无奈/接受的象征姿态。高父宽容了儿子的性别取向,一意堕胎的顾威威决意留下孩子,赛门愿意成为孩子的另一个父亲——这种乌托邦式的宽容和想象,再度成为这部着意于东方/西方文化冲突影片的主体精神。李安的影片在异国的空间里,建构了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想象。
二、全球化想象与文化主体性
与《刮痧》相比,《不见不散》则更显示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有的学者认为:“《不见不散》提供了对于全球化新的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并不是那种彻底脱离中国的普遍性的故事,而是紧紧联系着北京的经验和回忆。一种王朔式的自来水般流利而机敏的对话异常奇特地置于洛杉矶的景观之中。男女主人公依赖‘北京’支撑起感情。这完全不像《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那样试图摆脱自己过去的身份,而是将过去的身份作为新生活不可动摇的基础和一种力量。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故事。它无论如何是一种通过移民经验对于本土力量进行发掘的叙事。”[2] 确实,尽管《不见不散》的故事背景设在美国,而在故事的本质上,在“北京的经验和回忆”的表达上,与冯小刚的另外两部贺岁片《甲方乙方》(1997年)、《没完没了》(1999年)却有着内在的互文性与相关性。与《刮痧》一样,《不见不散》同样在人物对话中夹杂着汉语和英语,只不过,许大同和简宁要求儿子丹尼斯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或是为了获得真正融入美国的身份,完成成为“美国人”的梦想,或是以英语为工具“屏蔽”其父亲对丹尼斯“刮痧”事件的介入,语言成为身份指向及其身份焦虑的一种主要表征。由葛优扮演的刘元间杂着汉语与英语的表达,以及初见由徐帆扮演的李清时的“美式汉语”,似乎其主要目的更是为了增强影片的喜剧效果。在语言表达的意义上,刘元这位在美国社会底层打工(摄制组、卖保险、卖墓地、住汽车)的中国人,比起那位成功获得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的许大同,保留着更多的文化主体性。语言是文化的标识,也是身份的标识。刘元教美国警察学汉语的段落,尤其是警察学说“同学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的喜剧式场景,以语言的戏仿效果唤起了中国观众对于“历史”的某种记忆。“作者这种多少有些自恋的错位手法,却会使中国观众产生一种奇怪的优越感。”[3] 而一个富有意味的对照则是,那些美国华裔孩子对于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汉语学习的消极抵触。
“在一个现代世界里,与地域、部落、家庭和宗教的‘前现代的’认同被粉碎了;这个现代世界的新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全球通讯)既瓦解了稳定的地方关系,也破坏了全球的宗教认同。民族主义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一个能与现代世界合拍的替代物。它要提供一种在新形势下有效的凝聚力,也提供了某种围绕着它人们可以建立起他们自己和别人的身份的东西。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方法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91)的把民族看做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观念。”[4] 在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表述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5] “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影片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很大程度是建构在“语言”上的。它使得文化认同可以超越地域(空间)和历史(时间),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力量。
与《刮痧》、《不见不散》不同,《大腕》(冯小刚导演,2001年)则在中国本土的背景中演绎了一个有着全球化想象的故事,并以此表达了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曾经是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奇观。这种奇观一方面通过陈凯歌、张艺谋等导演的影片呈现于西方观众的视野里,其更多的是以黄土、高粱、宅院、乡村、京剧舞台等空间意象为主体建构的;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导演镜头里的中国,诸如意大利导演贝尔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末代皇帝》、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中国》等。而《大腕》的起始情境正是美国“大腕”导演泰勒对于“紫禁城”与“末代皇帝”这一中国文化奇观的影像建构。在资本运作的意义上,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一声叹息》(2000年)主要面向本土市场而获得本土票房奇迹①,到《天下无贼》(2004年)、《夜宴》(2006年)等试图拓展海外市场的努力,《大腕》可以视为一种过渡。中国内地、港台、美国的跨越国界明星组合,正是这种努力的表征之一。而在影片叙事的意义上,《大腕》又可以看成《不见不散》的一种延续,同样由葛优扮演的男主角尤优是回国后的刘元。他们同样用夹杂着汉语和英语单词的方式与人交流。葛优式的英语、关之琳的港腔国语以及唐纳德·萨瑟兰间杂着个别汉语词汇的英语,汇成一种全球化时代北京古城背景中一道独特的声音奇观。语言交杂,正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之一,它建构了一个多元混杂的现代城市文化空间。
作为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化产品,《大腕》对于这种文化空间的建构是表象的、平面的,而并不是追求深度的。在为泰勒举办葬礼的广告招标中,这种平面化空间的建构得到了更为明白的表达。平面的广告形象,构成了这个时代典型的空间景观,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广告不仅用于广告对象的宣传与营销,广告本身又构造了一个新的城市空间。广告背后总是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它们试图让观众做或者相信符合广告商利益的一些事情。观众与广告商默契的地方是关于优裕的生活和美好的社会等笼统的观点或形象。”[6] 但《大腕》则试图解构广告,解构充斥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广告形象。在一个广告弥漫着社会空间的年代,《大腕》将葬礼也变成了广告发布的对象,而其解构的广告对象,尽管以“可笑可乐”、“爱岛VCD”、“乐哈哈”等等这样虚构的形式出现,但由于这些虚构广告背后的真实广告在中国几乎是耳熟能详,因此在观众一方很容易产生会心的效果。其中关于补钙的广告段落,不但由于傅彪的表演而产生喜剧性效果,更重要的是,它与社会空间构成了一种讽刺和想象关系,其讽刺矛头直接指向多位明星出演补钙广告而引发的争议,以直接指涉现实而构成了一种自嘲的效果。
三、另一种想象中国的方法
与上述影片相比,1999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美国子安制片公司联合摄制、胡安导演的《西洋镜》刚好走了一种相反的路径,即从准西方的视野来审视和想象一个发生在20世纪初北京古城的电影事件。所谓的准西方,其实更多指的是胡安作为旅美华裔女导演的文化身份。这部与中国电影诞生的史实有关的影片,其主要创作意图似乎并不在于再现这种史实,无论是它对于20世纪初老北京城市空间的建构,还是它对于中国电影诞生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正如影片片名所显示的,“西洋镜”构成了更多指涉文化而非指涉历史的一个特殊的视觉隐喻。
在世界电影诞生10年之后的1905年,中国也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与西方电影不同,中国电影诞生于一种古老的戏曲样式与新兴的科技手段的结盟。而正是有了这一次历史性的联姻,直接导致了从“西洋影戏”到“中国影戏”的转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此后中国电影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历史的叙述中,“西洋影戏”不但给中国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样式与消遣样式,同时也以一种相对“文明”的方式打开了中国人接触“西方”的大门。观众不仅可以透过“西洋镜”来观察“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反观“西洋镜”本身,并进而反观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西洋镜”正是中国电影诞生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及拍摄《西洋镜》的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中国电影诞生90多年之后,拍摄关于《定军山》的影片《西洋镜》,以影像的方式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电影史实,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文化事件。前后跨越将近一个世纪的两个电影事件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文化上的相关性。同属世纪之交,作为一位走出国门在美国接受电影教育的导演,与在进入中国的英国人雷门的影响之下完成第一部中国电影拍摄的历史/影片中的刘仲伦/刘京伦之间有着一种深刻的文化认同关系。
在《西洋镜》这部语言(对白)交杂的影片中,“西洋镜”不但构成了视觉表象,同时具备着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富有意味的文化符号。由雷门所带来的“巴黎影戏”,在刘京伦吃惊的目光中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那是对一个未知世界充满了饥渴探求的目光。在这种目光的指引下,以《工厂大门》、《水浇园丁》等早期影片为视觉表象,向观众呈现了通过“西洋镜”所看到的“西方”。这个“西方”的神奇一方面在于它与东方/中国文化的显著差异,另外一个方面则在于它的呈现方式只是一束光线。双重的诱惑吸引了观众吃惊的目光,其中包括老佛爷慈禧太后。
作为一部电影,《西洋镜》自然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不同于电影史的文字表述。在视觉表象上,影片多次呈现谭鑫培/谭林培的京剧演出片段,构成了奇观化的视觉效果。影片将叙事的重心偏移到了刘京伦/雷门、刘京伦/谭小凌、刘京伦/任景奉等几组人物关系上,而并非关于中国电影诞生的史实上。这种对历史的规避从表层上看好像是为了增强影片的观赏性,以吸引更多的东方/西方观众,而其深层,则隐含着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刘京伦与雷门从对立到沟通、从隔膜到理解的情感发展进程,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交流通过“影戏”这一媒介集中地表达出来。我们很难推测,谭小凌这一虚构人物的设置是纯粹出于观赏/商业的考虑,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是这一人物的设置以及她与刘京伦关系的变化无疑既带来了更强烈的观赏效果,同时又通过刘京伦/雷门的关系揭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在爱情观念上的差异。任景奉这位中国电影的创始人,在影片中被表述为与刘京伦相对立的不思进取的旧式商人,于是,任景奉与刘京伦的师徒冲突背后也就包含了一个意指着文化冲突的主题。这种看起来背离了中国电影史实的倾向其实也许只是为了叙事的需要。这样,就使得影片成为杂糅着多种文化因素的一个文本,它在20世纪末的出现是别具意味的。
事实上,关于中国电影起源本身,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段传奇。之所以说它是传奇,不仅因为百年以前的《定军山》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历史,还由于影片《定军山》以及相关资料的失传。而这恐怕也是《西洋镜》这样的影片在关于“历史”的问题上会遭遇争议的原因所在。
为“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而拍摄的《定军山》并没有类似的视角,而其对于中国电影发生史实的叙述也与《西洋镜》有着明显的差异。两部影片同样呈现了“西洋影戏”给北京观众所带来的视觉震惊。在《定军山》中,它在任景奉的视线里呈现为一种奇幻的“魔术”奇观。与《西洋镜》不同的是,任景奉和刘仲伦同时在推动着说服谭鑫培拍摄“中国影戏”的进程。在任景奉看来,拍摄“中国影戏”是“影戏和京戏两好合一好”。而在谭鑫培那里,拍摄“中国影戏”唯一的阻力,是京剧的唱念做打在“影戏”里仅仅留下了做和打,因为“影戏”归根结底是“哑巴片”。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任景泰对于电影声音的敏感以及“影配声”的创意,是属于电影史实,还是来自创作者的想象。相比较于《西洋镜》那样的“传奇”式表达,《定军山》在其表象上似乎是更加遵循“尊重历史”的创作原则的。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刘仲伦与雅琦格格的爱情就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全球想象,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中国想象,这种想象的交汇,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的产物,或者说是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充满张力的矛盾的产物。那些表象不一,并且看似相互矛盾的电影文本,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文化症候。在全球化时代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我们已经很难脱离“世界”来单纯地探讨“中国”,很难在讨论本土文化时能够不涉及全球化的命题。另一方面,世界日趋全球化的背后,往往会带来文化差异性的趋同乃至丧失,而文化存在的重要前提之一,恰恰在于其不可复制的差异性。这种巨大的文化矛盾,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呈现于各种电影文本之中。
收稿日期:2008-06-11.
注释:
①《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一声叹息》在“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分别名列1998年第二、1999年第一、2000年第二和第三,《大腕》名列2001年第一,《手机》名列2003年第一,《天下无贼》名列2004年第三。参见《电影艺术》1999年第3期(4-5页),2000年第3期(4-5页),2001年第3期(4-5页),2002年第3期(12-13页),2004年第3期(16-17页),2005年第3期(4-5页)。
标签:西洋镜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刮痧论文; 甲方乙方论文; 喜宴论文; 不见不散论文; 没完没了论文; 推手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喜剧片论文; 综艺节目论文; 家庭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