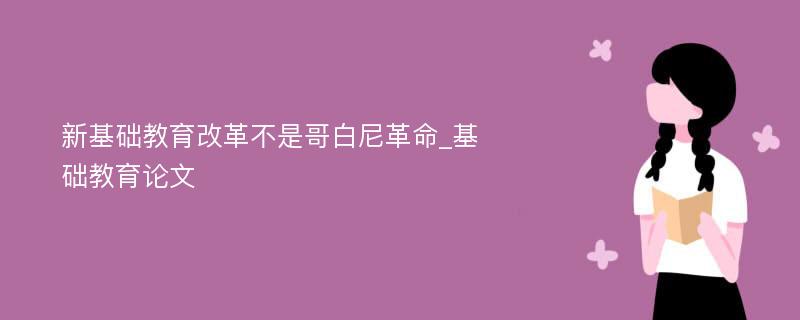
新基础教育改革不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白尼论文,教育改革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掀起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高潮,“为了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改革者的激情寄托了人们对新基础教育梦幻般的追求,21世纪理想的“爱弥儿”也许即将诞生在世纪之梦的寻逐中。
改革需要激情,改革更需要理性。当改革者的目光聚集大洋彼岸的西方文明,怦然心动的寻觅到与中国传统教育迥异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对欧美新教育的欣然向往,对传统教育的无比憎恨溢于言表。
于是“山姆大叔”的那套文化教育和肯德鸡、麦当劳一样诱惑国人的眼球,人们痛惜之余开始对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横加指责,对中国传统文化无原则的批评,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是扼杀孩子创造性的“凶手”,中国传统文化是淹没孩子个性的“祸首”,甚至把中国没有出现一流的科学大师,总是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都归罪于传统教育,主张完全用西方话语和制度取代中国传统教育者更不在少数。仿佛西方教育是孩子成材的摇篮,中国教育一切都不尽人意,一本很普通的《素质教育在美国》竟风行中国,成了众多家长和老师不离手的“圣经”。“从西方现代性的镜子照出我们一脸无奈”,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竟在国人的躁动和狂热面前,如此失落和卑贱。
传统果真是教育现代化的包袱而须予以彻底抛弃吗?为什么“五四”以来对传统棒追鞭打,传统仍然不识趣的存在呢?为什么素质教育、新课改迟迟不能在中小学扎根化为它们的自觉行为呢?一种异己的教育理论,失去传统的滋养,就无法化为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就会造成水土不服。
一、传统是什么
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1]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延续纽带,传统的本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法国人的浪漫情调、德国人的理性传统、美国人的实用态度、中国人的礼仪文化都是通过传统的潜移默化维系和延续着,并且活跃在当下的生活中。无论我们如何诅咒教育“传统”,它的影子仍然活跃在师生行为上,甚至说“传统”的某些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教育工作者实践理性,抑制了理论改革家的浪漫的冲动。
传统是反思现代、未来的参照系,“忘却历史的人,注定重犯历史的错误”,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钟摆现象”,对我们当今基础教育发展具有启迪意义。传统和现代作为教育发展的两个端点,为我们基础教育改革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支点提供了参照坐标。
基础教育改革不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彻底分离,而是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和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国教育知识基础扎实,数理训练要求严格这是我们的特色,不能轻易抛弃;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也不能忽略,但是这些经验是针对该国特定问题和情景而产生的,是否可以直接移植是需要仔细甄别和筛选的。西方后现代文化催育的浪漫色彩的课程理念与我国课程改革的实施环境有相当的距离。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孩子们想获得深造机会,就必须通过激烈的升学考试,尤其是在就业压力极其严峻的今天,无数家长对子女的理想和就业期待,寄托于高考的“鲤鱼跳龙门”。甚至可以说一个学校和教师应试教育搞得不好,就很难生存下去。在当前情形下,无论我们对新课改理念“爱”有多深,无论通身洋溢人性美好的教育话语有多诱人,也只能是隔靴搔痒。另外,现在国际教育主流回归基础质量,后现代那套理论在北美大陆也不受欢迎。所以,我们借鉴国际教育经验,必须考虑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及其与我国教育情景的差异。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土壤,都是其母体文化内涵的反映。由于文化具有不可通约性,我们移植的西方的教育理念也许只是其表层的“知识和观点”,而无法捕捉其特定的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优秀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是我们母体特质文化的长期积淀产物。因而,继承和延续传统教育文化基因,打通历史和现实的血脉联系,在民族生命和文化精神的舒展中重建基础教育改革的民族文化自觉性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过去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不正确的认识,简单把传统教育化约为儒家教育,又将儒家教育简约为专制教育,从而连根拔除。轻易的割断历史联系,不利于传承和发展,更不利于吸收外来文化。
20世纪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激励下的基础教育改革就表现出对传统儒家教育的彻底颠覆,认为“新旧之间,绝无两寸调和之余地”,彻底“打倒孔家店”、全盘清除封建教育,为欧美教育理念的纷至沓来提供适宜的氛围。事实上,以民主和科学相标榜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确实超越了清末传入我国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僵化和呆板,极大张扬了个性和自由,体现出尊重儿童和适应儿童心理发展的科学教育观,丰富了中国人的教育理念。但是,急风暴雨的新文化教育改革没有对传统进行和风细雨的梳理和扬弃,而是全面彻底的否定传统。外来的教育理论无法寻找与之相融合的生长点,所以欧美教育理论始终停留在长江沿岸几所发达城市的实验学校,没有与国情民性很好的结合化为民族血液一部分。
陶行知曾自述:“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主流。我从民国六年起陪着这个思潮来到中国。八年来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正是缘于实践中的碰壁,陶行知先生开始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民族传统教育中优良遗产,融会中西,创立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生活教育。
二、我们究竟在探求什么
在西方强势文化侵袭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代化诉求基本停留在抄袭、模仿和移植的水平,“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2]
50年代,受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制约,基础教育改革全面倒向苏联,尤其是1956年凯洛夫来华讲学,一时轰动中国教育界。当时宣传苏联教育思想特别是凯洛夫《教育学》的书籍印刷品达230多万册,而我国中小学教师只有200多万人。由此可见,我国中小学老师对苏联教育模式何其虔诚!
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惟恐学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50年代后期,则对凯洛夫《教育学》惟恐批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3]60年代破除苏联迷信,中国教育改革开始本土化之路,却滑向了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泥潭。中国教育改革之路可谓“红颜薄命”、命运多桀。
改革开放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迎来了春天,在“三个面向”方针指引下,基础教育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扎扎实实的开展改革实验,在学制、课程、教法和教材等方面的探索,均取得喜人的成绩。但从总体上来看,基础教育仍没摆脱传统的束缚。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考试要求,强调社会要求轻视个性差异等弊病仍然存在,所以我们不满意,对基础教育课程的“繁、难、偏、旧”和“六个过分”[4](过分注重知识传授,过分强调学科本位,过分强调接受学习,过分强调课程评价选拔功能,过分强调课程集中管理)深恶痛绝,抑或干脆彻底抛弃,另请神仙。然而建国后八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伤透了理论专家的脑筋,探求各种解决办法,始终没有逃出这些矛盾。课程文化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我们越是逃避它,越是牢牢地被粘住。
从国际上看,英美的教育是以现代派为主导,他们不满意基础差,下大力气强化基础教育质量,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国教育界为什么向美国学习。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在竞选中都向选民抛出“绣球”,立誓做一个教育总统,提升美国基础教育质量水平,主张向东方教育学习,学习东方教育考试制度,想通过借鉴东方严格的考试制度,恢复美国基础教育元气。[5]但美国是多元文化、自由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整齐划一的考试制度和教育模式在美国不过是总统的“一厢情愿”。
追溯基础教育现代化艰辛的探索历程,改革似乎总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纠缠间徘徊。简单地将一切打倒,另起炉灶,摆脱不了教育改革的左右摇摆现象。身经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风风雨雨的“活化石”吕型伟先生说:“出路何在?似乎在寻找结合点或者说在寻找中间地带。”[6]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都有各自优势,中国与西方都有各自民族文化特点,改革必须摈弃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完全对立的机械二元论思维方式,应该努力探寻它们之间的融合点。对待传统和民族的遗产,不应简单否定,而要贴近时代和文化发展的脉搏,创造性转换为现代化生长的基点。
总之,教育改革不是简单的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而是通过对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双重超越,建构一种立足中国国情的、符合时代要求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基础教育发展观。
三、寻觅课程改革的民族文化自觉性
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浪潮中,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放眼全球,中小学追求与国际接轨,但是本土行动略显迟缓,民族特色的优秀的教育话语略显不足,特别是伴随着国际教育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理念涌入国人视野,欧美的、日本的、加拿大的、前苏联的……中国教育学呈现多元化态势,可谓异彩纷呈,在众多流派中,欧美教育思想最为“抢手”。但是在名目繁多的译述和著作中,却缺少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话语,我们仿佛患了“民族文化失语”症。中国的教育研究与改革基本上成了外国教育思想的跑马场,即便“当今如火如荼的新课改,构成其主要的理论支柱的,无非是泊来的‘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西方文化教育流派。当急促的马蹄声渐渐衰歇、狂热的看客纷纷离场之后,空旷的赛场上只剩下默然的清洁工和孤寂的守门人。”[7]中国的知识人竟训练成为各种西方教育理念的代言人,充斥教育科研的各种西方的“后XX主义”话语,让读者无法使用现代汉语的思维准确把握。由于课程研究缺乏民族化的感性语言表达形式,致使许多研究成果无法为课程实施者——一线教师接受、理解、应用和创新。
美国学者希尔斯在其专著《论传统》一书中说,人类永远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历史中,而不是置身其外。事实上无论我们自己多么现代化,无论我们世界多么全球化,我们都不能忘却自己来自何方,都不能抛弃自己文化认同的根。否则,在全球多元文明对话中,我们拿什么与国际接轨?
中国近现代基础教育改革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教育救国”始终是教育家寻求教育改革和出路的突破口。由于教育的社会功能被无限的放大,教育改革的精神内涵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滋养,导致教育视野中人文精神的断层。
当代中国素质教育针对应试教育中无视学生的生命意识,摧残个性的弊病,提倡教育对人的精神自由、生命和尊严的终极性关怀,关注教育的超越性和人性化。基础教育的精神转向无疑切中痼疾,振聋发聩,但是素质教育的精神内涵不自觉的移植了西方人文主义或人学思想,忽略素质教育改革的文化合理性。“直接把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移植于素质教育之中,用这种方式反省和批判传统观念和应试教育,是一种过于偏激的文化拯救心态,这只会导致素质教育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性格。”[5]
从实践政策取向上看,素质教育在中国获得如此强大的社会回应,极大的得益于中央高层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应该说这种自上而下的过程,表现出中央对基础教育中愈演愈烈的升学竞争的忧思。但是,必须看到名目繁多的素质教育口号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将素质教育炒作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忽而成功教育,忽而挫折教育……将广大师生搞得无所适从。在一片喧闹声中,“几乎看不到从教育消费者的角度包括家长和学生的观点出发,来分析教育问题的论文”,表现出一种应景式的、“浮萍式”的研究。教育改革声势浩大,却在中国的土壤中找不到生长点,只能流于形式。
无论是对凯洛夫教育体系的留恋,抑或对欧美教育理念的向往,都不能脱离当下国情,抛弃我国教育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凯洛夫”这块发霉的奶酪,似乎应该连根拔除,然而在中小学课堂尤其是农村却经常活跃着“凯洛夫的影子”,“山姆大叔”那套新理念却迟迟未开花结果。事实上,传统教育不能彻底否定,即便凯洛夫教育体系,也不是百弊从生的渊蔽,至少它赋予了孩子们扎实知识基础和严谨的逻辑思维。完全用西方的话语、制度取代民族传统,不仅会使中国教育传统的薪火相传陷入困境,更重要的是会丧失我们基础教育中固有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