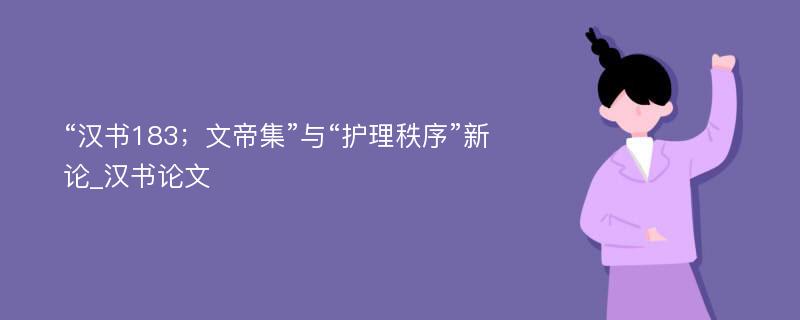
《汉书#183;文帝纪》“养老令”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书论文,文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1)06-0009-06
《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元年事: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1](《文帝纪》)
这段文献中“又曰”之后提到的养老内容,通常被称为“养老令”①。它以诏令的方式,申明国家对80岁以上老人提供养老福利,明确规定了不同年龄级别的老人享受的不同的福利待遇,并且对福利物品的发放程序也有严格要求,真实体现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和文帝“宾礼长老”的惠民政风。研究汉代敬老养老领域的问题,文帝“养老令”是最基本的史料之一,故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被反复征引,屡见不鲜。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文帝纪》此处的记载,似乎存在着叙述上的缺漏。《史记·孝文本纪》载: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2](《孝文帝纪》)
汉代但逢皇帝加元服、册皇后、立太子、祥瑞现等吉庆之事,往往会下诏赏赐臣民。此类诏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由“赐由”、“受赐对象”、“赐格”三部分组成。《史记》所载,便是其典型,即文帝元年三月诏赐的“赐由”是立皇后。“受赐对象”是“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赐格”是“布帛米肉各有数”②。两相对照,《汉书》的“赐由”亦是立皇后;“受赐对象”为“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及高年两个群体,与《史记》基本相同,唯孤儿一类,《史记》特列“九岁已下”,《汉书》则未作强调。“赐格”方面,二者差异较大,《史记》的表述较为含混,对于什么样的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赐物,没有明确说明;《汉书》对高年群体的赐物分配有明确说明,对“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却语焉不详,单从文本角度看,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群体是否属受赐之列③。由此看来,《汉书》传世文本在文帝元年三月诏的记述上,存在着一些值得推敲的问题④,而其中赐物价值即“赐格”之高,尤其令人生疑。学界已有成果多根据“养老令”之赐格来论述汉代养老福利政策的变化,如果这个赐格不实,那么对于相关问题就需要重新审视了。笔者不揣浅陋,试考述如下。
文帝“养老令”所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按照常规的释读,可以理解为:8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得米1石、肉20斤、酒5斗;90岁以上老人,每月除1石米、20斤肉、5斗酒外,还可得2匹帛、3斤絮⑤。细细研磨,这段史料中至少存在着三个令人费解的地方。
其一,80岁以上90岁以下的老人每月受米1石,意味着这一年龄段的老人事实上成为了“受鬻法”的实施对象,值得怀疑。“受鬻法”是西汉前期最重要、最基本的养老制度之一,其福利物件是90岁以上老人[3]。吕后时期,拥有大夫以上爵位者,年龄达到90岁,每月可受鬻米1石,公卒、士伍之类的无爵者95岁方可享受此项福利⑥。武帝时期,受米者的年限基准笼统规定为“九十以上”⑦。显然,文帝时期的80岁受米与其前其后的90岁受米规定存在着矛盾。有学者据此认为,文帝放宽了吕后时期的90岁受米限制,“八十岁以上者即可享受月赐廪米一石的待遇”[4]。对于“受鬻法”这样的重要制度,文帝为什么要“放宽”年限?如果文帝之“放宽”是事实,那么武帝为什么舍文帝之制而遵吕后之制?
其二,“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史料中将“赐”与“月”联系起来,意味着“赐物”的行为结束后,与之相应的“受物”的行为却在每月重复,有些不同寻常⑧。从道理上讲,这样的“赐”法不是不可以,帝王予物臣民的许多行为方式都可以称“赐”,天子愿意怎么赐就怎么赐;但是从《二年律令》专设《赐律》一门的事实来看,在汉代,“赐”也是有章甚至有法可循的,并非想赐什么就赐什么,想怎么赐就怎么赐。而且从文本的角度细究,汉代文献记载中但凡皇帝赐物于臣民,通常的格式基本上都是“赐某人(或某群体)某物若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中关于“赐”的条文,全部遵此格式。“赐某人某物每月若干”,就笔者阅史所及,这种表述方式尚无二见⑨。如果这种判断不误,那么在“赐”与“月”之间应该存在着一些我们尚未注意到的问题。
其三,赐物异常优厚,规格与价值过高。仅以90岁以上老人群体而言,他们每月得1石米、20斤肉、5斗酒、2匹帛、3斤絮。根据西北汉简所揭示的汉代物价水平⑩,猪肉价格约为每斤3钱至7钱,取其平均数5钱,则20斤肉约值100钱。酒价每斗为50钱,5斗则合250钱。帛价每匹约为325钱至800钱,以平均400钱计算,2匹帛则合800钱。絮有“阜绔橐絮”、“堵絮”、“络絮”、“襄絮”、“系絮”等品类,其中用来装棉衣之“堵絮”,价格大约是每斤150钱,3斤则合450钱。如此,90岁以上老人每月所受肉、酒、帛、絮四项合计为1600钱。又,居延汉简所见禀食名籍中,大男每月禀食量为三石,大女、使男为二石一斗六升,使女、未使男为一石六斗六升,未使女为一石一斗六升。90岁以上老人的食量,与使女、未使男较为接近,其每月所得米一石,基本上解决了月需口粮的一半以上。按照这样的统计,90岁以上老人的月度收入,已经超过了一些低级官吏的月俸(11)。虽然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优遇高年,但是国家对这一群体的福利支出超过特定官吏群体俸禄支出,这样的现象,实在罕见。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赐格的不合理性。文帝诏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12),所以赐米、肉、酒,帮助他们解决饮食问题;赐帛、絮,帮助他们解决穿衣问题。这里的“二匹帛、三斤絮”,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汉初的衣服用料有相对固定的尺寸数量,如《二年律令·赐律》规定:
赐衣者六丈四尺,缘五尺、絮三斤,襦二丈二尺、缘丈、絮二斤,绔(袴)二丈一尺、絮一斤半。
又《金布律》规定:
诸内作县官及徒隶,大男,冬稾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绔(袴)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绔(袴)丈八尺、絮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夏皆稾禅,各半其丈数而勿稾绔(袴)。夏以四月尽六月,冬以九月尽十一月稾之。布皆八稯、七稯。以裘皮绔(袴)当袍绔(袴),可。
汉制,布帛长四丈、幅宽二尺二寸为一匹。二匹即八丈,加上絮三斤,基本可以裁制“衣”或“袍”一件。90岁老人每月都可得二匹帛、三斤絮,那么每位老人每年可得九十六丈帛、三十六斤絮,至少可制成“衣”或“袍”12件,或冬夏衣至少各四套(“衣”、“襦”、“绔”俱全),如此多的帛絮,几乎足够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服饰之用(13),这是不是有些太“奢侈”了?这样的“养老”政策,不但能给当事人提供足够的生活所需,还能顺带解决当事人所在家庭的生活问题。所谓“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明确表示养老的主要承担者是老人所在家庭,国家只是起着辅助即“佐”的作用。“养老令”关于国家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这种功能定位,意味着此次赏赐高年的福利物品仍然有限,而不会是包吃包穿。显然,“养老令”中的赐物价值,已经高到与这个前提极不匹配的地步。
另外,从国家对“三老”和“高年”两个老年群体的政策待遇上看,也能发现一些问题。汉代县、乡皆设三老一名,由50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的男子担当[1]《高帝纪》。既为“众民之师”[1]《文帝纪》,又参与基层行政事务管理,三老之受重视程度,通常要高于高年群体。高祖二年初即设三老并“以十月赐酒肉”,而未顾及高年群体,或多或少已经反映了其不同之处。从史实记载来看,天子赐及三老及高年的时候,三老得到的赐物往往更为优厚,或者说至少不比高年薄少。如《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狩元年立皇太子,“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可以清楚地看到,90、80岁这样的高年,在待遇上逊于三老。文帝时期也有赐及三老的例子,如《文帝纪》载文帝十二年三月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与“养老令”90岁以上老人每月“帛二匹、絮三斤”的规格相比,却明显低了许多。文帝时期三老待遇不及高年,这又是令人生疑的地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养老令”赐格之高,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帝为人恭俭仁爱,在位期间多有善政,如废肉刑、减免税赋等等,在尊老政策上更为惠厚,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高规格的赐予,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当时的西汉政府能否承受得起?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在论证过程中通常是径直使用这一材料,甚至将之作为赞颂文帝尊老惠政的论据,却忽视了西汉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的问题。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养老令”赐格过高的问题,并由此对“养老受鬻令”是否成为制度提出质疑(14)。当然可以认为,执政者制定政策时脱离了现实,使所具之令沦为“具令”。诚然,一项制度,如果成本太高,得不到现实条件的支持,出发点再好,也难以贯彻实施下去。文帝时期推行的一些变革,也确实有迫于现实压力而未能入令者,甚至有最终流产者(15)。从赐格过高这个角度理解,“养老令”或许也是执政者考虑不周而出台的不切实际的政策。但是,从以上诸多令人费解之处综合考虑,“养老令”不单赐格过高,还存在着与立法精神背离、文本表述不合规制等问题,如果复以“立法不谨”视之,似乎未免有些过于简单化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翻检史书,西汉时期与文帝“养老令”赐例最为相近者,是武帝元狩元年四月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并存问致赐事。《汉书·武帝纪》载:
丁卯,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诏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
就关涉高年的内容而言,二者都将80岁以上、90岁以上老人分成两个群体分别行赐。就90岁以上群体而言,二者都有帛二匹、絮三斤的内容;就80以上群体而言,米三石与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相比,品类不同,价值大致相匹。二者也都对发放程序作出了规定。唯一不同的是,文帝“养老令”在发放数量前置一“月”字,使得二者的赐物规格形成巨大差别。文帝是因立皇后而赐,武帝是因立太子而赐,二者都是最重要的行赐事由,赐物规格却是如此悬殊。而导致这种匪夷所思情形出现的直接原因,唯在一“月”字之有无。那么,文帝“养老令”中的“月”字,会不会是衍字呢?
查《汉书》百衲本及其他后世校勘补注成果(16),均不见可征之据。但顺帝阳嘉三年五月戊戌诏提供了新的线索。《后汉书·顺帝纪》载:
昔我太宗,丕显之德,假于上下,俭以恤民,政致康乂。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5]。
“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这个赐格未见于东汉诸先帝,倒是与文帝“养老令”颇为相似。所不同者,一是米的数量由“一石”改为“一斛”;二是“米人月一石”改为“米人一斛”,少一“月”字。石与斛是同级的计量单位,在汉代经常互通使用,一斛即是一石(17)。如此,二诏之差异,只在“月”字之有无。如果文帝诏中剔除“月”字,那么两诏之赐格规定与语言表述几乎完全相同。这种高度相似,难道纯属偶然?
按太宗即汉文帝。顺帝诏书先述文帝之德政,复言自己“嘉与海内洗心更始”,不难看出,发布诏书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天灾人祸,手段便是按照文帝“故事”施行仁政,因此,诏令中赏赐高年的规格与“养老令”雷同,似乎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复制”行为。如果这种理解不误,那么就可以由此反推,文帝“养老令”中本无“月”字。如果“月”字确实为衍字,那么“养老令”的赐格内容相应变为:“年八十已上,赐米人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帛,絮三斤。”如此,前文提到的各种令人费解之处,也就自然冰释了。
顺帝阳嘉三年诏,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是对文帝“养老令”的“扬弃”——在继承其福利人群二重分类方式和福利品种、基准数量的同时,变更其月度发放方式为一次性发放方式,从而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但是从情理上推测,顺帝既然有意效法文帝,把“养老令”内容作为自己的施政模板,那么就不应该在福利标准上“大打折扣”。如果打了折扣,则是心不诚,心不诚则事不济,事不济则功不显,徒为人笑。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汉书》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讹误,“月”字之衍导致文献信息失真,使原本现实的政策变得不现实了。从《资治通鉴》对《汉书·文帝纪》相关内容的阐述来看,最晚到北宋,“月”字之衍就已出现。
日本学者大庭脩曾指出:“在汉代,作为天子的诏令,在具有长期必须遵行的重要诏令中,在文中或结尾附有定令、着令、着于令、着以为令等用语。”[6]从文帝元年三月诏书反复出现“令”字的情形来看,“养老令”应当属于那种“长期必须遵行的重要诏令”,故有学者据此推测,这条诏令“大约在整个汉代一直是必须遵行的”[7]。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养老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长期施行(18)。那么,“养老令”到底是在文帝之后即被废止了,还是作为法令而为后世所遵行了呢?
本文篇首已经指出,传世《汉书·文帝纪》所载文帝元年三月诏,内容斑杂,需要结合《史记》相关内容来仔细辨析。其中涉及养老的内容,可以大致划分为三部分。一是以立皇后故,对80岁以上、9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的高年赐物,即“年八十已上,赐米人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二是对赐物的发放环节予以强调,即“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其中提到的“禀鬻米者”,实际上是“受鬻法”的对象(按照本文“月”为衍字的推断,当指九十岁以上老人),由于基层官吏在发放鬻米的过程中存在着以次充好即“或以陈粟”的渎职行为,令文帝深为不满,所以诏令在细化赐物发放流程的同时,顺带对鬻米发放流程作出规定。三是对受赐人群的身份予以严格界定,即“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对“养老令”作如是解析,目的在于从其内容本身而不是从空泛的概念出发,来寻找其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轨迹。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养老令”中的部分内容,在文帝之后政治实践中确实有所体现。
其一,赐物发放环节方面。《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狩元年四月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并存问致赐:
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
这里的“县乡即赐,毋赘聚”,就是赐物发放时的注意事项。如淳曰:“赘,会也。令勿擅征召赘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师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赐之,勿会聚也。”可见武帝诏要求县乡基层官吏“送物上门”,不得将受赐者召集会聚在一起统一散发。之所以有这样的强调,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对受赐者特别是高年之人的优渥敬重,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愁扰百姓,或者影响他们的农作安排(19)。
又《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四年七月诏曰:
……《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
东汉的仲秋行糜粥制度,是西汉“受鬻法”的流变[3]。所谓“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意指按照规定,地方长吏应该亲自到场发送糜粥,这与“养老令”关于地方官吏亲自发放鬻米的规定,也是基本一致的。
武帝诏和安帝诏在发放物品环节的规定,表述不尽相同,但是似乎都是在遵循着一种既有制度。制度之源,应该就是文帝“养老令”中所谓“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虽然武、安二诏的表述远不如“养老令”细致,但是其内在关联不应被忽视。从这个角度上说,从文帝时期一直到东汉,“养老令”的部分规定似乎始终以制度的形式存在并被遵行。
其二,文帝“养老令”赐格方面的规定,在文帝之后似乎也是有迹可循的。前引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诏,赐“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90岁以上老人所得帛、絮的数量,与“养老令”完全相同。武帝此项赐格所援引的模式,或许就是文帝的“养老令”。东汉顺帝阳嘉三年五月诏在赐格上几乎完全“复制”文帝“养老令”,而其后的桓帝建和二年春正月的赐例(20),亦与“养老令”的赐格相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两汉时期的各个朝代,即使是在相同或相近的行赐背景下(比如皇帝加元服、册皇后、立太子),不同的君主对高年的赐格往往存在着差异,说明当时不大可能存在着整齐划一的相关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帝的模式和规格对后世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某个特定时期,先帝的模式和规格仍然可能以“故事”的方式对后世施加着影响。从顺帝阳嘉三年诏、桓帝建和二年诏的例子来看,文帝“养老令”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编入典册的律令制度,而是在政治法律生活中具有重大作用的先帝“故事”。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养老令”在文帝之后似乎既未被完全弃置,也未被严格遵行。
综合以上分析,传世《汉书·文帝纪》“养老令”中存在着若干经不起推敲的疑点,“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中的“月”可能为衍字。如果“月”字之衍属实,那么“受鬻法”的福利对象在文帝时期并未发生调整,“养老令”的赐格虚高问题不复存在。文帝“养老令”是否作为一个完整的“令”被纳入后世法典暂且不论,其个别规定演化成为后世遵行的常设制度,个别内容在东汉时期仍然以先帝“故事”的方式产生着影响,却是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格说来,如果不是把“养老令”之“令”理解为“诏令”之“令”,而是视为“律令”之“令”的话,那么所谓文帝“养老令”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为避免歧义,不如把文帝“养老令”改称为“养老诏”。
注释:
①明确将文帝元年三月诏中的养老内容冠以“养老令”之名,不知始于何时。沈家本《汉律摭遗》卷十九之《养老令》,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之《养老令》,都收录此诏,“养老令”一词沿用至今。
②史书经常用“各有数”或“各有差”这样的术语来表述,而忽略具体的数字。
③清代学者王鸣盛比较《史记》与《汉书》之异同,认为:“马意主行文,不主载事,故简,班主纪事,详赡。”(见《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这一论断之合理性,在此处有明显体现。又,文帝元年三月诏,亦见荀悦《汉纪·孝文皇帝纪上卷》:“诏曰:‘今方春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朕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于是出布帛米肉之赐,其肉刑耐罪已上不用此令。”《汉纪》只记录了鳏寡孤独穷困之人而忽略了高年,不知何故。
④王文涛先生即认为:“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三月所下赐物诏令,《史记》与《汉书》的记载不同,都有令人不解之处……《史记》所载当有所本,此系帝王诏令,非比录常之事,可率意而写。班固对《史记·文帝本纪》的这一修改令人难以理解,疑有脱漏。”参见氏著《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3-144页。
⑤《资治通鉴》卷十三《汉纪五》文帝前元元年:(三月)“诏振贷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赐帛、絮。赐物当稟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其表述保留了赐物的品类,略去了赐物的数量,又将“月”字置于赐物前,用以说明每月所赐物包括米、肉、酒(80岁以上)和米、肉、酒、帛、絮(90岁以上)。这样的理解,实际上与今人无异,说明我们对“养老令”的解读符合逻辑,代表了最常规的释读方法。
⑥《二年律令·傅律》:“大夫以上[年]九十,不更九十一,簪衺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士五(伍)九十五以上者,稟鬻米月一石。”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⑦《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夏四月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道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⑧有学者称之为“定期赐物”,以区别于史书中常见的“临时性赐物”。参见尹怡朋《秦汉养老政策研究》“汉代对老人的赐物活动”,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⑨《二年律令·傅律》的“稟鬻米月一石”,不能等同于皇帝的“赐”。对于政府向高年发放粥米这种行为,文帝“养老令”亦云“吏稟当受鬻者”、“当稟鬻米者”,用“稟”而不用“赐”,这种表述方法值得关注。汉代行政文书(如居延汉简集簿)中的“稟食”,往往是指官府供给粮食,而“赐”则突出强调恩惠来自皇帝。“受鬻法”用“稟”而不用“赐”,暗含着这种福利是国家义务而非皇帝恩赐的意思。君主专制国家,公共权利与皇权也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因此,严格地说,“受鬻法”的发放粥米行为不能用“赐”、“赐物”来概括或指代。山田胜芳认为,“吕后时代是赐物于90岁以上老人,而文帝则将其降低到80岁以上”(《鸠杖与徭役制度》,庄小霞译,《简帛研究》二○○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这种说法如果不是认可文帝将受粥米者年龄降至80岁,便是混淆了“赐”的临时性特征与“受鬻法”的常制特征。
⑩以下各类物品的价格,参见刘金华《汉代西北边地物价考——以汉简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1)据陈梦家先生考证,西汉后期,百石之吏俸钱七百二十钱,其下的斗石、佐史为六百钱。见《汉简所见俸例》,《文物》1963年第5期。又据《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待诏公车的东方朔,其月俸为“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又据居延汉简,西北边地烽燧之候长,月俸亦不过一千二百钱。
(12)典出《礼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汉人常引用,如《盐铁论·未通》文学曰:“饮酒之礼,耆老异馔,所以优耆耄而明养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饱,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徭役,非养老之意也。”《盐铁论·孝养》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饱,衣非帛不暖。”
(13)黄今言先生说,“假设汉代每人每年夏、冬二季各做一套衣裳,又不论大人小孩,平均每套用布2丈即半匹,则全家五口,一年做衣需要用去5匹布上下”,《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分析》,《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如杨振红将“养老令”与《二年律令·傅律》以及武帝元狩元年夏四月诏比较研究之后,推测认为“文帝所具养老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长期实行”,“养老受鬻令是否成为制度亦因此成了问题”。分见杨振红《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5)文帝时有“九十者一子不事”的优复政策(《汉书·贾山传》),武帝时又有“民年九十以上……为复子若孙”的诏令,沈家本据此即怀疑文帝此法“未著为令”(《汉律摭遗》卷十四《户律一》“年九十一子不事八十二算不事”条,《历代刑法考》1985年版,第1632页)。又文帝二年废除犯罪“相坐”之法,后来又恢复了这条酷法,以“夷三族”惩治了新垣平(《汉书·文帝纪》)。
(16)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汉书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张舜徽《二十五史三编·汉书之属》,岳麓书社1994年版;徐蜀《两汉书订补文献彙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17)陈梦家《汉简缀述》:“在通常计量之时,则可以石代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9页。
(18)杨振红先生即认为,“必须具有普适性和长期法律效力,并且符合后主的治国思想、仍然可以施之于当代的令”才能被编辑入律,“文帝元年颁布的养老令,由于无法永久施行,故在景帝修订律令时便未将其编辑入律”。她还指出,武帝建元元年四月诏所谓“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显然指的是《二年律令·傅律》的规定。武帝诏不提文帝元年所具养老令,反而提《二年律令·傅律》的律条,表明文、景修订法典时并未将文帝所具养老令编辑入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文帝所具养老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长期实行吧”。参见氏著《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9)《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永元五年二月诏曰:“去年秋麦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20)《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年八十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绵三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