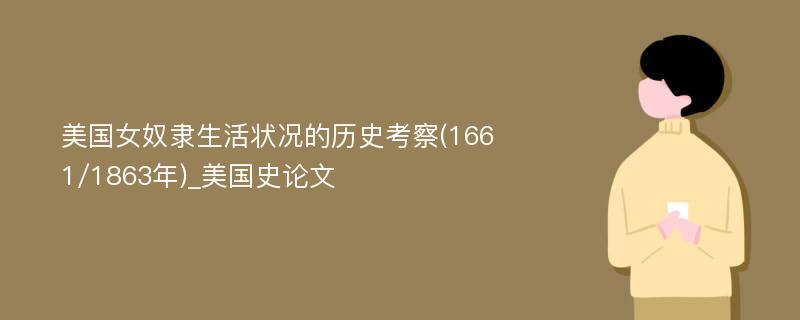
美国女黑奴生活状况的历史考察(1661~186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奴论文,状况论文,美国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619年首批到达北美殖民地的20个黑人中,一个叫安纳森的男子与伊莎贝拉的女子结婚,他们的儿子威廉·塔克成为第一位在北美殖民地出生的黑人,并于1624年在弗吉尼亚接受洗礼。
在1619~1661间, 北美殖民地出生的黑人皆为自由人或契约奴。 1661年首先从弗吉尼亚殖民地开始,奴隶制成为合法,奴隶的孩子永远是奴隶,奴隶的母亲自然是肯定的奴隶。这种状况维持到1863年奴隶解放为止。
从1661年到1863年的200年里, 美国的女黑奴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白人世界,在那里她是女奴,是主人的财产;另一个是黑人世界,在那里她是女人,是孩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
本文试图考察女黑奴在这两个世界的生活状况。作为女奴和女人,这双重角色是不可分割的,并为从女奴到成为自由的女人进行斗争,构成女黑奴的独特性。在美国妇女史上,她们自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和魅力。
一 在白人世界
美国奴隶制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正如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弗·道格拉斯揭露的那样:“美国的奴隶制就是授予一个人得以运用和强行把别人的肉体和灵魂作为财产的权利,奴隶的处境简直同野兽一样,他是一份财产……他自己的美德、良心、智慧和感情,完全被主人废弃不顾。”(注:杨生茂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20页。)因此,奴隶制下的黑人处境是极其悲惨的。通常说来,女黑奴在各个方面又比男黑奴更加艰辛、痛苦、受限制,她们除了跟男黑奴一样从事强制性劳动外,还要忍受生育痛苦,忍受无视她们女性特征的虐待。此外,成为白人男性的泄欲工具,更是女黑奴的家常便饭。
女黑奴的使用分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田间劳动,另一部分用于主人的家庭服务。前者从天亮到天黑都在地里干活,种植、管理和收获棉花、甘蔗、稻子、烟草等。她们耕地、扬场、砍树、拖木、锄地。在每年8月开始的摘棉季节里,黑奴们带上一只小袋和一只大篮子, 天蒙蒙亮就到棉花地里,除了有10到15分钟的时间吃一顿冷熏肉中餐外,其余时间必须马不停蹄地干活,直到天黑看不清为止。那些第一次来地里干活的新手,往往在监工暴风骤雨般的皮鞭驱使下,尽可能快地摘棉花;当天晚上过称时,他(她)摘来的棉花的重量将成为日后每天上交的标准。每天收工后,所有奴隶集合在仓库前将摘来的棉花过称,一旦超过重量10到20磅者,监工就要调整他(她)第二天的上交量,一旦不够重量,那便是一顿鞭打。如果被发现在仓库里小睡,或者早上睡过了头,将受到不少于20鞭的惩罚。因此,“黑奴们总要在祷告之后才敢沉沉睡去,他们祈祷第二天能一听到号子便迅速睁开眼, 站起来”(注:GerdaLerner ed.,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 A DocumentaryHistory,New York,1973,pp.16.)。
一般说来,正处生产期的女黑奴在小孩出生前3~4个星期内工作量相对减少,也较少受鞭打。小孩出生后,她能得到额外配给的衣服和口粮,但通常在小孩出生4个星期后,她即被赶入地里干活, 与平常无异了。未断奶的婴儿交由家里4~6岁的孩子照看,如果家里没有能够照看婴儿的孩子,婴儿就随带地里。这里是一个前黑奴的回忆:
早上四点钟铃声响了,他们有半个钟头的准备时间……女人必须干跟男人一样的活,完成一样的工作量,如果种植园离家远,未断奶的婴儿整天带在地头,如果离家近,那么妇女被允许一天回去两三次照看她们的婴儿。(注:Barbara Welter,The Women Question in AmericaHistory,New York,1971,p.48.)
相对于种植园里劳动的女黑奴,那些做家奴的境况要稍好些,至少不必受风吹日晒之苦。但她们照样得没日没夜地干活,并时刻处在神经紧张的状态,谈不上丝毫自由。她们在主人家做饭缝补,照料孩童,却从没有被主人放在眼里,甚至连马都不如。
奴隶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在中午12点,没有桌子,端着盆站着或蹲着吃,不给饭吃是常用的惩罚手段。奴隶没有灯火、柴火、毛巾、盆、肥皂、桌子、椅子和其他家具。担任裁缝的女奴在冬天的每一个夜晚都在寒冷的楼道入口处干活,因为只有那里有微弱的亮光可以加班完成庞大而沉重的规定工作量,她们被期望在这种冰冷黑暗的环境里做出的手工活能像坐在火炉边上干出的活一样细致完美,否则就要挨打。担任侍者的女奴是不准离开房间的,万一她们想出去方便,必须征得主人的同意,如果离开的时间超出了主人容忍的限度,那么就要受惩罚。
家奴有各种明确的分工。在白天她们之间是不允许交往和交谈的,甚至夫妻之间也不允许。即使在晚上,清理卧室的女仆和缝纫女奴经常得睡在女主人卧室的地上,随时为她效劳。“有一个女奴,她结婚十一年了,却还没有被允许睡在女主人卧室的外面。”(注:Gerda Lernered.,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New York,1973,pp.18.)
有些住在城里的种植园主经常将女奴的孩子一断奶即强行送往乡间的种植园,因为他们不想女奴为照顾自己的孩子而影响了照顾女主人。遇到主人高兴,女奴有一年一次去乡间看望孩子的机会。
漠视奴隶并对奴隶造成伤害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更改奴隶的姓名。每换一个主人或遇到奴隶重名,姓名即被改掉,也就意味着奴隶的母亲要伤心地失去同一个孩子的联系。
无论是种植园女黑奴,还是种植园主家里的女黑奴,她们除了被当做劳动力使用外,更被当作生育的工具。托马斯·索威尔在其《美国种族简史》中指出:“美国在1825年拥有的奴隶数目居西半球各国之冠,不过,其他国家实际进口的奴隶却要比美国多,巴西进口的奴隶就是美国的六倍。区别在于,美国是奴隶能够繁衍后代,并按自然规律保持人口增长的惟一国家。”(注:托马斯·索威尔著:《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其中“马里兰州就是一个繁殖奴隶的州,在那里,男人、妇女、孩子都是养着卖钱的”(注:杨生茂:前引书,第21页。)。贩卖奴隶比使用奴隶更有利可图。于是,奴隶主把女黑奴当作“母畜”,强迫生育。因此,女奴的价格是按乳房的形状来估价的,女黑奴中的“姑娘”是最值钱的。1773年巴尔的摩奴隶主威廉·奥特的财产状况表显示, 一个叫南妮的25 岁姑娘价值40美元,一个叫汉那的20岁姑娘价值45美元,而一个叫杰克的30岁男奴只值16.25美元(注:Mabel E.Deutrich and Virginia.C.Purdy ed.,Clio Was A Woma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Washington,1980,p.59.)。可见,姑娘的价格远远高于壮年男奴。因此,女黑奴往往十几岁就被迫生育,一辈子生十多个孩子是司空见惯的事,孩子生得越多,越被奴隶主看好,甚至被许诺给予自由。
由于劳动的艰辛和受到野蛮的毒打,在高出生率的同时伴随着高死亡率。
弗朗西丝·嘉宝是英国著名女演员,她嫁给皮尔·伯特。1838~1839年,她来到皮尔在佐治亚州的种植园,呆了5个月。其间, 她深深地被女黑奴的苦难震惊了。她写道:
“芳妮,有过6个孩子,只存活1个,她前来请求减轻地里的活。”
“南妮,有过3个孩子,死了2个。”
“丽,有过6个孩子,死了3个。”
“苏菲,前来讨些旧亚麻布,她生活凄惨,有过10个孩子, 死了5个。”
“莎丽,两次流产。生了3个孩子,其中1个死了。她哭诉后背持续发痛。”
“拉莎,流产4次,将7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却死了5个。 现在又怀孕了。她哭诉后背痛得厉害,由于在地里干活后背的一个肿瘤已经肿得很大。 我想, 她的后背痛可能是因为肿瘤破裂。 ”(注: GerdaLerner,OP.Cit.,pp.48-50.)
如果说永无止境的生育和超负荷劳动构成女黑奴生活的主要内容,那么自己的骨肉随时被拉走卖掉则成为女黑奴最撕心裂肺的痛苦。劳动和生育的苦永远不能跟失去孩子的苦相比。这里是一个叫乔赛亚·汉森的黑人神父对早年经历的回忆:
我的兄弟姐妹们被一个接一个买走,母亲被悲伤击倒了,只剩下我一个还牵在她手里。接着她被蒙特哥马罗郡的艾赛克·吕力买下,而我被购买者继续挑选着。这时,我的母亲意识到所有她的孩子将一个不剩地离她而去,于是,她不顾一切地推开人群,跪在吕力先生面前,恳求他同时将我买下,不要拆散我们母子。那位先生不仅将她的恳求当耳边风,而且凶残地打她,踢她,将她推开。当她被那个残暴的家伙带走时,她哭喊着:“天哪!天哪!我还要忍受多久!”那时我大概五六岁,现在我似乎还听到我可怜的妈妈在哭泣。(注: Mabel E. Deutrichand Virginia C.Purdy,OP.Cit.,p.65.)
奴隶主之所以可以随意拆散黑奴的家庭,是因为黑奴只是他们的财产而已。
既然是财产,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地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女黑奴的压力更大,处境更危险,“这是因为当时在所谓的真正的女性概念的影响下,中产阶级妇女节欲自禁,使白人男性更有理由以女奴习惯于男奴的性欲无度为借口,随心所欲地侵犯女奴”(注: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译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4页。)。同时,“倘若一个黑人妇女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操和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对其残暴的主人的野蛮袭击稍加抵抗,就可能当场被杀死”(注:杨生茂:前引书,第23页。)。
女黑奴成为白人男子的泄欲工具在奴隶制美国实在是太普遍了,这一现象对美国历史造成的影响也是极其复杂的。它打击了黑人家庭生活,也打击了男黑奴作为妻儿保护者的自尊,同时它创造了一个数量巨大的混血阶层。混血阶层的出现,一方面分散、削弱了黑人队伍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些混血儿由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往往成为黑人运动的领导者。
但是,这一现象最严重的直接后果是对女黑奴的身心摧残。大多数女黑奴怀孕后,仍遭抛弃,境遇稍好的,往往成为白人男子的情妇,但想成为合法妻子是很困难的。因为混血婚姻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不仅婚姻双方当事人面临惩罚,就是证婚人也要受到惩罚。1726年,一位叫乔·布兰克南的证婚人就因此受到50磅的罚款(注:Mabel E. Deutrichand Virginia C.Purdy,OP.Cit.,p.66.)。 若是碰到有良心的白人男子,他会较好地安排黑人情妇和混血孩子的生活,但女黑奴想因此子贵母荣是不可能的。奴隶永远是奴隶,一旦当可依赖的白人男子死去或破产时,作为主人的财产,她和孩子将随之被变卖或赠送。女黑奴被男主人当作性工具玩弄时,女主人不仅不予同情,往往因嫉妒而更加残酷地加以折磨。说实在的,南方白人妇女对于奴隶制度的感受也是极其复杂的。如果说,束缚女黑奴的是残暴的奴隶制度,那么束缚白人妇女的则是男尊女卑的淑女规范。因此,就连女权主义小说家切斯内特也承认,看到被自己轻视的黑人妇女用淫荡的、邋遢的、富于挑衅的方式生存时,她才痛恨奴隶制度。她在日记中写道:“在奴隶制度下,我们被妓女们包围着, 每一个体面的家庭里, 都有遭冷落的妻子。 ”(注:Gerda Lerner,OP.Cit.,p.51.)
从切斯内特过分偏激的言词中可以看出,女黑奴成了南方白人妇女抱怨自己困境的牺牲品。特别是那些漂亮的、天生高贵的女黑奴更是女主人的眼中钉。一个名叫派西的女孩,被称为“棉花地里的皇后”,然而她的后背留着上千道皮鞭的抽痕,因为她是放肆的男主人和嫉妒的女主人的奴隶(注:Gerda Lerner,OP.Cit.,pp.50.)。 一个名叫伊丽莎的女黑奴受男主人宠爱九年,并生有一女,当男主人不幸去世后,复仇的女主人将她们母女送到奴隶交易市场(注:Gerda Lerner,OP.Cit.,pp.10.)。
由此看来,在白人世界的女黑奴犹如生活在不见天日的漫漫长夜,被奴役、被污辱、被虐待便是她们的命运。
二 在黑人世界
在奴隶主眼里,黑奴同牛马一样,但毕竟黑奴不同于牛马。让黑奴维持家庭和婚姻的相对稳定,是防止黑奴懈怠和逃跑的有效途径。为此,奴隶主让奴隶们享受着随时都面临被拆散的家庭生活,在晚上、在星期六下午、在星期天。
种植园的奴隶住处,是一个并非经常不断地处在主人监视之下的黑人世界,那是奴隶们可以寻求感情满足和亲密关系的场所,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社区生活,也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他们扮演着不同于黑奴的角色,对于女黑奴来说,她们是女人,是母亲,是妻子。
作为黑人母亲,由于主人要求她时刻照顾白人孩子,将她与自己的孩子分离,表面上看来,那些黑人保姆与白人孩子的关系反倒更加亲密,这种对主人的孩子超过对自己孩子的母爱被赋予种种黑人母亲的传说。
富兰克林·弗雷泽在其经典著作《美国的黑人家庭》一书中说:“母亲不能随意对孩子有自发的感情上的流露,哺乳和抚爱孩子也受到限制,因此她常常对自己的孩子显得很冷淡,这成了很自然的事。”(注:丹尼尔·布尔斯廷著:《美国人:建国历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29页。)笔者认为,与其说冷淡, 不如说独特,独特如冰山下的火焰。
这种强烈的母爱有时表现为黑人父母宁愿杀死自己的孩子以使他们免遭奴役。
1856年,肯塔基州的奴隶西米奥·加纳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及两个孩子逃入辛辛那提,结果,武装追捕队发现他们的藏身处,破门而入。这时,玛格丽特宁可让她的孩子们死掉,也不肯让他们受到奴役,已经设法弄死了一个孩子。在遣返路上,绝望中的玛格丽特带着孩子跳入冰河,企图自杀。
一个叫西尔瓦的女黑奴为了不让孩子们遭奴役,亲手将13个孩子全都弄死在襁褓中(注: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郭瀛、伍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
不让孩子们长大遭受奴役而杀害自己的子女,这是一种被奴隶制度扭曲的母爱,一种非常的却是炽烈的母爱。
奴隶主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常常出售奴隶的孩子。为了阻止奴隶主拆散自己的家庭,黑人母亲进行了不屈的反抗。为此,母亲们将处于危险时刻的孩子藏在森林里,到山洞或小水潭给孩子们找水喝,到森林里采一些浆果、草莓等给孩子们充饥,待到主人答应不再出售她的孩子时,母亲才将他们接回家。遇到孩子们被无情地带走时,母亲会呼天抢地地反抗,结果往往招致一顿毒打。这时,奴隶主发现,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情绪低落,甚至郁郁而死。为了充分调动女黑奴的劳动积极性,一般说来,允许10岁以下的孩子跟母亲在一起。
这种骨肉分离的不幸未降临时,奴隶的小屋里充满了融融的亲情。
奴隶小屋用粗劈的圆木搭建,盖以木瓦顶,铺以松木地板,还附设烟囱,终年干燥、温暖,因为奴隶主知道奴隶的价值取决于奴隶的健康。奴隶主只发放极其不足的口粮,迫使奴隶在他们小屋附近开辟自留地。这样,由于父母子女就在自己的园子里为自己而共同劳动,因此促使其家庭关系更加亲密。
不过,奴隶的大多数时间在地里或主人家里干活,家人相聚的时间极其短暂。女黑奴在沉重劳动的闲暇抓紧时间与孩子、丈夫共享天伦之乐,尽一个母亲、妻子的责任。黑人运动领袖布克·T.华盛顿回忆:“我早年的记忆之一是母亲在深夜烧好一只鸡,叫醒孩子们起来吃。”(注:Barbara Welter,OP.Cit.,pp.47.)废奴主义者弗·道格拉斯关于母亲的回忆是这样的:“她住在离家12英里的地方,常常在一天的劳动结束后,匆匆步行回家,到家已是深夜。一大早又必须在监工规定的时间里赶到地里劳动。”(注:Barbara Welter,OP.Cit.,pp.51.)有很多黑人自小与母亲分离再没见面,但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来依然充满了深情。因此,南方重建时一位自由民事务署的官员说道,黑人当中:“每一位母亲的儿子好似都在寻找妈妈,而每一位母亲都在寻找其子女。”(注:托马斯·索威尔:前引书,第251页。)
作为黑人妻子,女黑奴享受到的关怀和地位比当时的白人妇女要高得多。
这是因为同在奴隶制度下挣扎的黑奴夫妻首要的是相互体恤和尊重,他们无暇追求当时白人社会流行的那套维多利亚式生活,共历苦难的黑人夫妻更体现了一种夫妻情深的平等关系。
奴隶制的美国,一个女奴和一个男奴的婚姻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尽管如此,这种婚姻通常都能保持几十年。1860年对某地前奴隶夫妇的调查表明,40几岁的人当中有半数以上已有20或20年以上的婚龄(注:托马斯·索威尔:前引书,第238页。)。 黑人世界自有一套风范和习俗,其中婚姻被看作十分严肃的事,不得轻易中止。即使被奴隶主强行拆散的鸳鸯也能保持好多年的夫妻关系,在黑人获得解放之后,许多分离的夫妻为团聚踏遍整个美国。当一对黑奴夫妇未经准许走出棉花种植园之外而被巡逻人员抓到时,丈夫准会除了自己挨一顿鞭打之外,还主动代妻受过,再挨一顿。看到自己相亲相爱的女人在拍卖台上被野蛮地展示,卖掉,带走,自己却无能为力,“他的心都碎了,这样的情景是美国奴隶制每日结出的果实”(注:杨生茂:前引书,第22页。)。
出于对妻子的关爱,同时也出于维护男人的尊严,男奴们往往冒死抗争。在奴隶制时代,夫妻分离后曾发生过自杀的事例,也有谋杀那些强奸奴隶妻子的白人的事例。这种谋杀,一经查出,死路一条。前奴隶汉森回忆父母为保护母亲遭惩罚最终被卖掉的情景,那时他三四岁左右,父亲因为殴打了那个对母亲施以兽行的白人监工,根据马里兰州的法律遭到了严惩。回到家时,父亲“血流满面,右耳打掉了,整个背部挨了一百皮鞭而皮开肉绽”(注:Barbara Welter,OP.Cit.,pp.57.)。
一则悬赏50美元的缉奴广告是这样写的:“一个名叫保罗的男奴从承购者处逃跑。我知道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被汉尼先生买走,并将她们安置在古斯——克罗克种植园,因此,毫无疑问,这家伙一定潜逃在该种植园附近。”另一个叫保尔的黑奴从佐治亚州逃出,为的是去马里兰州找那里的妻子和孩子们(注:Barbara Welter,OP.Cit.,pp.55—56.)。
如果说受到丈夫的关爱只能说明黑人妻子心酸的幸福,不足以说明黑人妻子的地位高,那么下面的材料则可说明。
根据1790年的户口调查材料,北美十三州的所有黑人家庭中, 有3894个男户主,513个女户主,女户主也占了总数的12%( 注:Mabel E.Deutrich and Virginia C.Purdy,OP.Cit.,p.61.)。
在黑人家庭中,如果母亲不幸被卖掉或死去,那么代替母亲执掌家务的不是父亲,也不是长子,而是长女。甚至有妻子为追求个人独立和自主向奴隶主请求与丈夫离婚。在对子女的婚姻上,母亲有绝对的发言权。
通常说来,女黑奴在家庭中居支配地位。美国社会学家古德在其《家庭》一书中也认为,黑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要超过白人妇女(注:古德:《家庭》,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第120页。)。
众所周知,奴隶制时期的白人妇女正处在被要求“贞洁、虚弱、温柔”的社会,她们在享受骑士“尊重、保护和帮助”的同时失去了自由和平等,从丈夫那里得到几个可怜的零花钱成为她们的主要话题。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奴隶制下的美国,黑人妇女总体上家庭地位比白人妇女高些。其根本原因在于女黑奴有独当一面的优势。她们是主人地里干活的能手,也是主人家里烧饭、做菜、制衣、带孩子的能手,甚至有的还成为男主人泄欲的对象。她们是主人家必不可少的部分。她们利用这种资源(如果可以称为资源的话)养家糊口,同时她们也因为拥有这些女性特长的“技能”,在自己家里成为丈夫和孩子们的生活依赖。这种家里家外的重要性无疑巩固和提高了她们的地位。
三 小结
综上所述,在白人世界过着非人生活的女黑奴,在自己的黑人世界总算过着作为女人的日子。然而,这种令人欣慰的事情是相对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她们是主人的财产,随时面临着苦难的深渊。
比较正常的家庭生活的甜味和奴隶生活的苦味,自由成了她们惟一的企盼。即便像菲力斯·惠特勒这样杰出的女黑奴诗人,她也强烈地渴望自由。虽然在主人家里,惠特勒因才华出众备受宠爱,比如她只分配很轻的活,可以随意去拜访波士顿的社会名流,可以在床边安放一盏灯、一支笔、一本信笺,有时她可以在房间里整夜用火炉取暖。总之,她可以享受到小姐般的待遇, 然而她还是要自由( 注: Paul Engle,Women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Follett Publishing
CompanyChicago,1976,p.97.)。
著名的女英雄哈丽特·塔布曼更是追求自由的典范。她自己从马里兰州只身一人逃到北方获得自由后,又19次返回南方,将她的家人、邻居和其他黑奴共300多人通过“地下铁路”解救出来。当时, 她的人头被悬赏4万美元。
尽管由于地理知识的缺乏、路途的艰难遥远、以及显而易见的肤色特征,奴隶逃亡的可能性很小,但广大女黑奴还是毅然踏上为自由而斗争的漫漫征途。
标签:美国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