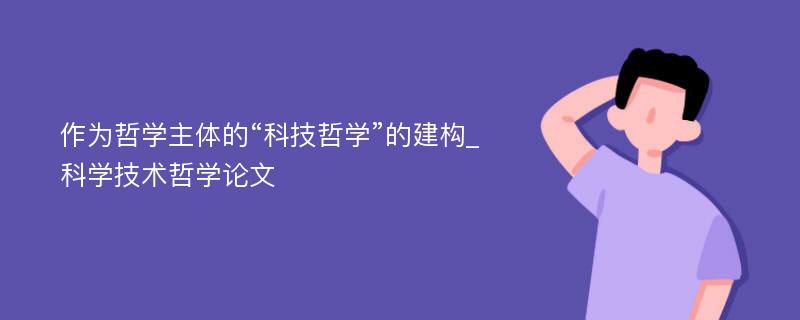
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科学技术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
这个题目包含两个意思:第一,把“科学技术哲学”当做学科来建设;第二,把这门学科建设成为哲学学科。这两个意思表面看起来很荒谬——“科学技术哲学”早已经被列为“哲学”的分支“学科”,其实不然。
为什么提“学科建设”?从大面上讲,由于历史的原因,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向来模糊,缺乏学术范式,这个学科通常只被当做一个交叉和边缘的研究领域,很少被当成一个学科来建设。但没有学科建设,就很难有学术意义上的进展。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必须尽快摆脱某种因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过渡状态”,尽快建立学术规范,向学科化方向发展。所谓学科化既有社会建制的方面,也有内在范式的方面。用“科学技术哲学”替代“自然辩证法”,标志着中国自然辩证法在学科化道路上朝建制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学术范式的方面迟迟没有突破性进展。我本人从1989年发表“自然辩证法辨”(《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年第2期), 到前不久发表“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为何稀缺”(《方法》1999年第3期), 呼吁“学科塑范”也十年有余了。今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调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任教,马上面临着本专业的教学和招生任务,更感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为什么提“哲学学科”?由于这个学科目前处在不确定状态,因此学科建设的方向很多。不过,正象我多次指出过的,20年来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已经大体分化为两个群体,一个是哲学群体,一个是社会学群体,两大人群渐行渐远,实际已经不再是同行了,因此应当各自构建自身的学科范式。这个学科可以建设成“哲学学科”,也可以建设成别样的学科。我本人一直自认是哲学群体中的一员,因此这里只讨论如何把“科学技术哲学”建设成为名符其实的“哲学学科”。
一个成熟的专业应该形成知识训练的梯级结构,这个结构中包括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高级知识四个部分。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入学之前应该掌握基础知识和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入学考试主要是检验这两方面掌握的情况;硕士研究生就读期间主要学习专业知识,并通过其学位论文显示其对专业知识某一个领域的熟悉程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主要检验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就读期间学习高级知识,并参与推进本学科的前沿发展,其学位论文应该是对学科前沿的一个推进。在本专业专职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至少应该具备本专业的硕士学位或相当的水平,通常应该具备博士学位或相当水平。
如何界定这个知识训练的梯级结构,是学科建设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个梯级结构不是特别明确,博士和硕士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以致有许多人报考本专业时持有考硕士不如考博士的想法,觉得你们这个专业也没有什么规矩。学科建设就是要立规矩,而且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是关键。
大家基本上都同意,本专业至少有两大基础,即自然科学基础和哲学基础。但过去很长时间来,大家比较强调自然科学基础,不怎么强调哲学基础。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我的看法,可能是人们都觉得搞自然科学比较难,而哲学则相对容易一些,所以往往强调比较难的那一部分。这显然是对哲学持有不正确的看法。实际上,对哲学的忽视是导致学科建设迟迟不能提上日程的根本原因,因为严格说来,要把“科学技术哲学”建设成“哲学”的分支学科,落实到最后是“哲学”,哲学基础应该是最重要的。
与重视科学基础不重视哲学基础相联系的,过去还有一种倾向,即重视前沿和现实问题,不重视历史。历史是用来自我确认的,是一个学科的identity之所在,学科建设无人问津与不重视历史是相适应的。没有强大的历史后盾,跟着五花八门的前沿和现实问题跑,这个学科就没有“根”,没有范式。
因此,“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首先可以确立两个原则,即重视哲学基础,重视历史。我建议,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可以有三门课,即自然科学基础课(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数理逻辑等的合取或析取)、哲学基础课(哲学通论、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合取或析取)、专业基础课(科学史、科学哲学的合取或析取)。对我个人而言,我特别强调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基础地位。
我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列为专业基础课,科学哲学自然好理解,为什么要把科学史也列为专业基础课呢?科学史本身是一门独立于哲学之外的学科(中国学位机构已将其列为理学一级学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也独立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但是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的关系很象数学与理论物理学的关系,它与科技哲学的缘源非常之深,在学科的每一层而中都相互渗透相互纠缠。因此,尽管科学史不是这个专业的专业方向,但列为本专业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就象数学不是理论物理学的专业方向,但却是理论物理学的基本功和必修课一样。就象历史上大物理学家对数学作出贡献(如牛顿发明微积分)一样,大科学哲学家也可对科学史做出贡献(如库恩)。
在大学本科阶段,学生所学习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课程只可能是概论性的、初步的。进入研究生之后怎么办?是否让他们把“科学通史”和“科学哲学概论”再学一遍?这是不行的。到了研究生阶段,学生应该读原著。“原著选读”是研究生阶段学习专业知识的主要形式。
专业课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之分,必修课规定了本专业的基本学术范式。有什么样的必修课,就形成了什么样的学术范式。继续贯彻我上面提出的重视历史和重视哲学的原则,我建议设立四大必修课,即“自然哲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原著选读”、“技术哲学原著选读”、“科学史名著选读”。
科学史不读“原著”而读“名著”,因为科学史的原著应该是科学史上的科学文献,对硕士生来讲太专深了。这个阶段需要了解的是不同科学史家的工作,了解不同编史纲领和编史方法所产生的优秀科学史著作,使学生了解科学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加强历史感,也训练驾驭科学史材料的能力。
自然哲学和技术哲学没有列在硕士入学考试之列,因为前者太老,后者太新,有点专深,况且它们的内容或多或少可以分别通过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反映出来。但它们应该做为必修“专业课”单独提出来,因为自然哲学反映了这个学科久远的历史,技术哲学反映了这个学科面临的新问题。“自然哲学原著选读”选取从柏拉图《蒂迈欧篇》到怀特海《过程与实在》的自然哲学经典著作(包括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使学生了解西方自然概念之流变的同时掌握哲学的思想方式,这本来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过去自然辩证法界因缺乏哲学背景而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
四大必修课并不排斥其他的选修课。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对某一较大的课题领域进行概括,充分掌握这个领域的文献资料,进入前沿。论文主要考查搜集资料掌握文献追踪前沿的能力和水平、独立的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
如果说硕士生阶段更强调本专业的通用范式的话,那么博士生阶段可以更具导师的个人色彩。(目前硕士生招生时不分导师,直到作论文时才分,这有它的道理。)博士生的入学考试除了检查考生四大基本功的掌握情况,也会考察考生在导师指定的专业方向上的既有程度。我觉得,博士生阶段可以看成是在本专业从事学术研究之能力和水平的一个见证,这个阶段的课程形式应该是讨论班,讨论那些前沿的进展。博士生的必修课实际上只有一门,即本研究方向的讨论班,而其他方向的讨论班均可作为选修课。讨论班亦可以作为硕士生的选修课。讨论班没有固定的教材,每次讨论都是新鲜的东西。博士生阶段应鼓励自学,要求一开始就主动寻找课题,一开始就动手试着搞研究。专题班的课程考试方式以写论文为主。最后的学位论文,要求课题较小,能有较大的创见和突破。“微言大义”是博士论文的理想境界。
我们现在每年都出版不少“自然辩证法原理”类的教材,大同小异。人们笑话说,一个县一个啤酒厂,一个地区一个卷烟厂,一个大学一本自然辩证法教材。这些教材都是为理科研究生开政治必修课准备的,有它的市场。但是,“自然辩证法原理”类的教材出得虽多,却不是为本专业的研究生准备的。“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自身的教材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我建议,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应当担当起这个任务,组织全国的专家,认真论证,尽快建立起一套本科、硕士、博士三层次的课程和教材体系。这将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的重大成果。
学科建设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应当是,培养中国的“学院派”队伍。从队伍建设方面讲,中国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队伍,现存的科学史家主要研究中国科学史,少有西方科学史方面的专家和权威;现存的科学哲学家主要是介绍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工作的科学哲学译介家,没有科学“哲学”方面的大思想家和权威。从知识水平上讲,我们对西方历史上的许多基本科学名词、概念、人物、思想、理论,尚缺乏一致认同的翻译和理解,亟待规范和整合。从思想深度上讲,我们根本还谈不上有什么学派和独立的思想体系。
抓紧建设核心课程
我想就学科建设坦率地谈四点:
第一,应当长期保留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帽子。这有很多好处,另外从学术上看也没有什么不恰当。即使有人想脱离一些过时的影响,也可以旧瓶装新酒,赋予其全新的含义。
辩证法一词目前西方学者也叫得很欢。“自然辩证法”确实有中国特色,也只有中国还在用这个词,过去它也的确为学术繁荣和国家建设做出了成就。“科学技术哲学”只能代表一部分内容,以此取代自然辩证法是不合适的,教育部的定名也可以改回来嘛!另一种办法是如最近上海交大的做法,成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只关注大口袋中的一部分内容,也与国际接轨。但是这样“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没有归属,划到社会学系也不恰当,虽然国外目前基本上是这样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二,学术规范确实要建立起来。首先要确定自然辩证法题下的最基本的“知识集”,用它来界定本领域的研究内核,以区别于其它学科。我认为此知识集包括三门课程: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这些学科在国内虽然名义上也存在,但各自包括什么基本内容,恐怕多数人包括教师也说不清楚,这就很危险了。所以当务之急是研究此三门学科的基本知识点,列出讨论提纲,使得以后教师上课基本上以此纲要为参照进行授课。据我观察,目前多数自然辩证法教师不具备此三门核心课程的较完整的知识背景,因此第一步是教师要提高业务素质。能搞研究不一定能教书,教书需要对整个学科有完整的认识。当然,教师可以另外多讲一些自己熟悉并作了一定研究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不讲纲要的内容。
第三,在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再确定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二级课程。前三门课程是“基础课”,现在要讨论的是“专业课”。这些应当适当灵活一些,如包括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专题,科学计量学,科技政策研究,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批判,科学文化等等。这方面的课程要依据本单位的实际能力和特长突出时代特征,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研究、讨论热点问题。
第四,本领域的研究论文要有头有尾。重视积累,不能天天创新,总是“填补空白”。几个大刊物应当完善审稿制度。
从韦伯关于《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谈起
1917年11月,马克斯·韦伯应邀到慕尼黑大学给一群学生做题为《作为职业的学术》(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讲。这篇演讲在韦伯众多引起轰动和争议的著作中也许不是十分起眼的,但它所表达出来的对一般学术的“理想类型”的期待,却是很值得我们,尤其是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们深思的。
按照韦伯的说法,不管是谁,如果他想作为一个教授在学术界工作,就应该遵守学术的原则。
第一:具有完全献身于学术的愿望,以及发现的能力。韦伯认为,一个能称得上学者的人,必须明白,他或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时节,或者说,他或她的整个命运(das Schicksal seiner Seele)就在于找出对某个特定的学术问题的解答。
为得到学术上的独到看法,既要求艰苦的工作,同时更需要直觉。两者不能相互代替。只是艰苦的工作,没有直觉,不可能导致学术上的成功;没有艰苦的工作,只有直觉,也是无用的。(P574)
第二:任何学术都有其局限性。一个学者必须要有足够的谦虚,承认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将会马上过时。无论一项发现在当时看来是多么有意义,它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也许会具有不朽的价值,但是任何一项学术成就都只是相对于产生它的时间和社会环境来说,才具有意义。“在科学工作上,每一次‘完满’,就意味着‘问题’的提出,科学工作要求被‘超越’,它要求过时。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被别人超越。这不仅是我们的共同命运,而且还是我们共同的目标。”(P582)
第三: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按照韦伯,一个好的政治家必须充满信心和决心,而一个好的学者必须是犹疑不决、充满怀疑的。好的政治家必须有勇气与他的对手发生冲突,而好的学者却必须假定,在他不同意的那些思想中可能还有一些真理存在(P585)。因此,韦伯认为一个教授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教导他的学生去接受那些哪怕是令人不快的事实。人性的弱点将会误导我们,把我们引向只去接受那些我们假定是真的见解,然而,这种弱点在大学里是不可接受的。只有把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也当成有可能(潜在可能)是正确的,学者们才能提出新的见解。(P587)。
韦伯的上述原则(或者说理想),对于素以严格自律闻世的德国学者而言,或许都太高,但它却绝不是不可以达到的。联想起当下学术界普遍的急功近利、自吹自擂以及邀功请赏,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学术标准究竟有多低。甚至我们有时不得不发问,我们还有没有标准?
拿第一个原则来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真心献身学术理想的?学术被普遍地变成了一种敲门砖。通过一本又一本地“著作”而得到了教授头衔的人,在学术界里还算是老实的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违背韦伯第三原则的人,他们套用政治的做法来做学术,以党同伐异的做法来掩饰其不学无术的真面目。学术界一日不摆脱这样混乱状态,一日就不得安宁。至于第二原则,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的迹象。然而,学者的自我膨胀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对那些怀抱“宏大的”理想,为“万世开太平”的学者来说,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似乎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就自然辩证法界而言,套用库恩的说法,还处于“前科学阶段”,甚至可能离这一阶段还有一定的距离,更不用说向前迈进了。一是学科范式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建立。另外,非学术的因素太多,也影响了学术范式的建立。
自然辩证法界的当务之急在于确定学科研究范围。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如果不算是伪的或假的,也至少是幼稚可笑的。正如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如果不是有意骗人和坑人的话,也至少是无效的一样。
吴国盛君在文中提出的一些具体设想,比如把“为理工科研究生开设的‘自然辩证法’单门必修课,改为对本专业多门课程(比如自然哲学、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的限制性选修课”等,若能被采纳,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最起码,我们会有一个较好的研究起点。最后,真切希望那些准备把工科院校办成综合性大学的设计者们,能有一个较宽的视野。我并不希望所有工科院校能马上变成综合性大学,因为这不但不现实,而且也没必要。从业人员的多寡并不是学术繁荣的唯一的因素,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有多少大师级的人物存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至今仍是一个以工科见长的学校,其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虽有 15个系、所和研究机构,150个全日制教授,50个全日制讲师,335个研究生,200个本科生及400个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辅修的本科生,但从教师和学生的规模上讲,都只占麻省理工学院的十分之一,可它却有3 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8个麦克阿瑟奖获得者,8个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30个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其主要目的是给学生提供创造性地表达人类想象力的机会;理解人类的过去;检查社会、经济、政治随着时间的变化;考察科学技术植根于其中的文化与社会建制环境。它的所有系、所,尤其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中心、 技术与法律研究中心、技术与政策研究中心都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许多新的见解正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的。
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尤其是自然辩证法界能早日进入这种状态。
也谈科学——人文资源的稀缺与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
自然辩证法学科在近20年里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包括吴国盛所说,完成了全国范围的体制建设,并成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但是,这一学科从来就没有明确提出自己要“担当起积累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的重任”,与所有其它学科一样,这一学科也存在着先天不足。事实上,理工科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与文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都是政治课。在理论上,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一切的指南,所以文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工科学自然辩证法,都是要获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本学科实践的能力。
目前许多理工科大学开始了人文学科的重建工作,也开展了跨学科教育,但如吴国盛所说,“这些轻微的调整和改革,并没有真正导向对学生‘科学-人文’素养的影响”。并非文科学生知道宇宙怎么大爆炸,理工科学生能背诵莎士比亚,就能算文理兼备了。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的培养,需要整个教育思想的转变,需要相当漫长和艰苦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自然辩证法学科能够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
作为自然辩证法专业支柱的是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三大学科,但目前理工科硕士生编写的自然辩证法的教材中,只包括科学哲学的一部分内容。从学科的发展和影响考虑,应该向包括文科在内的本科生开设一门课程,争取列入必选课。科学思想史应该是最佳选择。传统的科学史(主要是编年史)沉闷枯燥,并无多大意义。但科学思想史则可以跨越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大领域,即讲授科学史中闪光的部分,又可将科学哲学的最新观念融入其中(科学史是科学哲学的根基,科学哲学是科学史的方向);可深可浅,可生动活泼,可重建科学和科学家的形象,容易为文理科共同接受。同时,这门课程也可以为教师提供比较大的自由空间,这也是以此课为首选的重要理由。等时机成熟,再开设稍专一些的科学哲学及科学史本科课程,并为某些系科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科学社会学。
标签: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科学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自然辩证法论文; 学科建设论文; 研究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