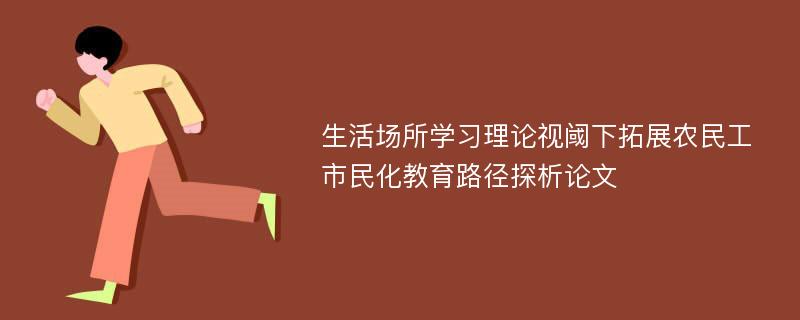
生活场所学习理论视阈下拓展农民工市民化教育路径探析
姜浩天,陈明昆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 要】 城镇化建设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实现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化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过程,在此期间,教育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生活场所学习作为理论依据,分析生活场所学习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价值意义,阐述当前开展农民工市民化教育面临的瓶颈问题,进而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协调教育供给主体、开展互联网教育以及促进非正式学习等方面构建并拓展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新路径。
【关键词】 生活场所学习;农民工;市民化教育
相较于以往将农民工教育简单等同于职业技能培训的传统观点,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内容不仅涵盖意识、知识与能力三个维度,教育场所也从学校和工作场所拓展到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更加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教育与学习活动。这一新概念的提出不但体现了从知识、能力到思想认识的全面性,更加凸显了学习场所的灵活性和学习者的主动性,给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设计与开展提供了新的启发。
一、生活场所学习理论及其对成人学习的实践意义
生活场所学习(Lifeplace learning)作为工作场所学习(Workplace learning)的替代性概念,由齐泽姆和伯恩斯(Chisholm&Burns)于21世纪初首次提出,其旨在重新审视被工作场所学习窄化了的校园外学习,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学习行为,从而将校园外的非正式学习界定为一种包含但并不仅限于工作场所学习的新模式。哈里斯(Harris)在2008年发表的观点指出:“生活场所学习是指人一生中获取或得到的包含知识、技能、行为与态度在内的一种学习,而无论何时、何地、为何以及如何获得的此类内容都应当包含在内。”[1]
一般以村集体干部(比如村支书)或村能人牵头,成立村民俗旅游合作社,有闲置宅出租但是又不便自己打理(或者没有能力自己打理)的村民自愿加入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了托管协议书,合作社对入社的房屋统一经营管理。托管期间,房屋卫生、旅游接待、日常看护等均由合作社负责,村民拿出游客住宿费用的一定百分比(比如20%)作为托管费,支付给合作社。这种形式既统筹利用了房屋资源,又增加了农民收入。这种模式在北京市密云区司马台村、穆家峪镇、陕西咸阳袁家村比较常见。
与传统意义上校园内、课堂上开展的教育和学习活动相比,生活场所学习发生于一个人在生活中身处的各种环境里,包括社区、家庭以及各类自愿学习的环境。[2]这不仅意味着学习形式的灵活性和学习媒介的多样化,而且指向“真实生活”的学习内容更易激发学习者的动机与兴趣,由此带来的良好学习效果必然会促进学习者对于日常情境中实际问题的良好解决,从而真正体现生活场所学习过程与结果的价值。面对工作场所学习关于“工作”“场所”与“学习”三个关键要素的原有定义,生活场所学习在此三个方面皆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将“工作”的内涵从有偿工作延伸至无偿的、玩耍性质的工作;“场所”的空间从固定地点扩展到虚拟的移动场所;“学习”的方式由受控制的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3]而这样的转变也正是生活场所学习概念的鲜明特征。
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已经不断走向成熟,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广播电视领域,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网络传输的基础上,运用了4k技术,与原来的视频传输效果相比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视频传输的质量以及效率。本篇文章主要讨论了基于4k网络的视频传输在电视台的应用,并结合实例进行分析,希望通过4k技术的应用,视频的传输效果更加安全可靠。综上所述,在4k技术电视时代背景下,4k技术电视播放实践一体化已经成为主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对电视制作和播出的各项内容进行整合,构建播放实践一体化网络系统,并制定统一的管理平台、设计合理的制作方式,如此才能促进4k技术电视的持续发展。
实现学习方式由“受控”向“自主”的转变是生活场所学习核心要义,学习者由迫于职业压力、功利化的学习转变为重视个人长远发展、主动进行的学习,背后体现出的是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内化。当学习的视野从校园和工厂移向日常生活场景时,我们可以看到为之众多的学习活动与学习者的兴趣与需求息息相关,因而更容易激发学习者的内部动机。如,摄影爱好者主动学习摄影相关的理论知识而不需要来自外部压力的逼迫;年轻妈妈花费大量时间和耐心学习育儿知识或烹饪技术却并不为获得任何奖励,等等。作为接受教育的主体,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受限于较低的收入水平、较少的闲暇时间和自身薄弱的文化基础,参加培训活动的积极性欠缺,也无法通过有效学习获得个人职业技能的提升与观念意识的改变。要扭转这一现状,激发农民工内部学习动机,基于农民工所处生活场所的宣传与引导自然成为了重要的助推力。以社区为单位组建、鼓励农民工参与的“快走队”“合唱团”等文体团队以及定期举办的生活技能大赛等活动可以通过兴趣与休闲的形式帮助农民工掌握运动保健、艺术欣赏等方面的知识,建立学习活动与兴趣爱好、社交需要之间的联系;而流动性的择业、就业和创业讲座可以促使农民工在切身利益层面真正意识到接受培训对于个人长远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生活场所学习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价值意义
与部分传统观念认为农民工教育主要是教育者讲授知识或传授技能、农民工被动接受不同,随着城市定居时日的增加和市民角色认知的提升,越来越多农民工出于职业发展或者美好生活的需要,常常从周遭的环境、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态度出发,通过外出、读书、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等日常生活行为,积累大量的隐性知识、技术,并获得态度和洞察力。[11]这正是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利用身处的生活场所,借助多样化媒介,在与周遭环境的互动中进行主动高效学习的体现。然而基于日常生活获得的个性化与自主化的知识与技能因其开放性、经验性甚至是跨学科性,往往难以设置明确而统一质量标准进行评估并予以认证,也很难被用人单位和社会所承认。当主动学习的成果不能转化为学历文凭或资格证书,并带来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正向的、显性的改变时,农民工继续学习的积极性自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挫伤。
1.生活场所学习强调立足生活,可以促进“生活市民化”教育的更好开展
生活场所学习的相关研究认为,成人日常生活学习是伴随着个体生命活动的开展并以形成新经验为目标导向的,[4]形成新经验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在生活中、通过生活和为了生活。这一立足生活的观点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生活市民化”教育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步骤,“生活市民化”不仅仅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稳定的工作和可靠的收入,还要求他们在观念意识、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生活质量、文化素质等方面全面转化,以实现与城市的有机融合。[5]而满足以上要求的教育也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的、通过与日常生活中人员与环境互动实现的,是指导农民工实现其更好生活愿望的教育。与单纯将农民工教育视作职业技能培训的传统观点不同,“生活市民化”教育应将视线聚焦于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由于城乡差异所带来的小到语言沟通、生活习惯、法律安全常识,大到社会公德意识、文化适应性与自我归属感等多个方面的困难与障碍,并通过家庭、社区以及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对农民工开展相应的知识普及与培训活动,促使农民工在掌握真正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增强与社会成员的良性互动,获得市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2.生活场所学习倡导拓展空间,可以使教育和培训的形式更加丰富
生活场所学习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对教育与学习活动空间上的拓展:无论是传统的教室集中上课,还是工作单位开展的培训学习都难以完全涵盖现代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的发生场所。耶克斯利(Yeaxlee)认为,只有真正具备洞察力的领导者和老师才会意识到成人教育将日趋于俱乐部、教堂、电影院、剧院、音乐厅、工会、政治社团中进行,在有书籍、报纸、音乐、无线设备、工作室、花园和参加朋友聚会的家中发生。[6]面对农民工市民化教育中存在的多样化需求,借鉴和应用生活场所学习拓展空间的理念,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形式。具体来看,一是重新审视目前仍占主导地位的课堂讲授形式,针对枯燥内容的讲解引入音频、录像等多媒体手段作为辅助,提高农民工基础文化知识学习的效率;二是继续以农民工所在的企业为重点进行以学徒制和工作指导培训为重点的在职培训,强化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中的操作性优势;三是重视包括社区在内的休闲娱乐场所中的学习活动,发挥社区环境的文化熏陶作用,通过休闲娱乐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四是利用互联网+时代下远程教育场所的虚拟性,将教育活动与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结合,方便农民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3.生活场所学习注重内化动机,可以更好激发农民工学习的积极性
该理论所指向的“生活场所”显然是一个“大生活场所”的概念,它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解决成人有效学习问题的一条崭新路径。生活场所学习理论进一步拓展了成人学习的空间和时间,使得处于工作世界的成人能够把工作、生活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通过新的学习手段和媒介,凭借自我学习的习惯或兴趣,有目的、有选择、有效率地进行学习,打破了传统成人教育课堂上的沉闷局面,激发了成人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为学习化社会的形成提供新的动能。
三、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教育面临的瓶颈问题
1.政府责任存在缺失,监管机制尚不健全
根据《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虽然中央每年都会下拨农民工培训专项资金,各级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也在逐年增加。然而面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政府的经费支出依然显得微薄。据统计,中央政府层面每年用于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达到100亿元(王小霞等,2009),[7]考虑到数以亿计的群体数量,平均到每一位农民工身上的培训经费杯水车薪。相较于政府,以企业投入为代表的社会资金的投入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多数用人单位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导下,过分关注雇员培训投资带来的企业运营成本增加,加之考虑企业与农民工关系的不稳定性,往往“重用轻教”,竭力压缩经费,选择成本较低的“速成式”培训,部分企业甚至省掉培训环节,要求农民工“直接上岗”。在政府与企业的培训经费投入皆难以满足需要的前提下,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成本自然水涨船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巡视员徐诺金在《2049:中国农民工转型问题研究》报告中的测算,全国农民工市民化年人均成本为6.93万元,[8]平均每月5 775元,而统计显示2017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 485元,[9]排除日常生活必要开销费用后所剩无几,自费参加培训也只是空想。
2.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大多数农民工难以接受培训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核心之一是通过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改变农民工群体文化素质整体偏低、职业技能相对匮乏的现状,帮助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其长期的就业竞争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本应发挥保障与监督的双重作用,然而当前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较为有限,缺乏长期目标规划的同时,政策与制度的落实也不容乐观,对于培训项目的实施亦缺乏有效监管。具体来看,近年来中央政府虽然日渐重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开展“阳光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等项目,但并未设置专门机构对农民工培训进行统筹管理,对于培训开展的计划和所应达到的目标也未有明确表述,进而导致地方政府具体执行中存在“敷衍完成”与“随意行事”的现象。除此之外,相关立法与保障性政策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到位也会导致包含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企业和一些社会组织在内的教育培训提供主体过分着眼于自身短期利益,逃避开展高质量培训的社会责任,从而使农民工培训的质量大打折扣。
3.学习形式与场所单一且受限,一些学习内容陈旧或脱离实际
农民工市民化教育是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的系统性工程,既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也需要在实际开展中面对计划、组织、宣传、监管以及保障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督促立法、经费保障、监督管理和宣传引导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一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教育中的定位和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针对农民工培训中的乱收费、乱办班的现象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规范各培训供给主体在农民工培训中的行为。二是发挥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作用,继续加大农民工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市民化教育专项基金和农民工教育定向补贴,根据条件设置免费培训项目,减轻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经济压力。三是建立合理、长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对各类培训进行从立项到实施过程的全面监管,严把职业技术证书的认证与发放工作,最大限度保证培训质量。四是加强对市民化教育政策的宣传,通过自上而下的机构传达、报纸和门户网站的媒体宣传以及发放传单、设置咨询点等形式帮助农民工了解国家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最新政策,引导其积极参与。
从内容来看,教育和培训内容在忽视农民工身份转变需要的同时,也与市场的需求存在脱节。一方面,受教育主体的认识以及时间、场地和师资力量所限,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教育开展中很少涉及法律安全意识、公共道德素养、社会人际交往和文化适应等文化与心理层面的教育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社会身份转变的关键。另一方面,当前的技能培训未能紧跟社会发展潮流,科目仍以传统的电气焊、汽修、烹饪、建筑为主,内容陈旧且单一,不能适应城市发展中紧俏行业的用工需求和农民工多元化的就业要求。调研显示,城市用人单位最希望得到的教育培训内容依次如下:快递、网店、家政、管理。这是产业转型升级给城市就业带来的影响,[10]却也正是农民工技能培训未能与时俱进的短板所在。
4.现代市民日常生活教育未受重视,教育供给主体责任感不强
选定滚转角az的模糊论域AZ={-2,-1,0,1,2};模糊集为{NB,NS,Z,PS,PB},分别对应“负大”、“负小”、“零”、“正小”、“正大”;隶属度函数种类选择为“trimf”,如示意图6所示。wz、anglelh1、anglerh1、anglelh2以及anglerh2的隶属度函数图像均与图6类似,后文仅给出隶属度函数对应的参数。
面对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在谋生就业与社会心理适应方面遭遇的困难,定时定点、以课堂讲授形式进行的培训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手段。农民工日常大部分时间身处工作场所与家庭社区中,无论是工作中暴露出的能力差还是与城市居民沟通交往中因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差异而产生的“格格不入”感,都亟待一种恰当且行之有效的全新教育形式出现。这一教育形式必将指向农民工作为现代市民身份所面对的日常生活,以满足农民工工作谋生与社会交往中知识技能与心理层面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在政府的支持下,由雇用单位、农民工所在社区以及社会公益组织协同实现。但当下从政府、企业到社区,提供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各个主体尚未意识到日常生活教育的重要性,在教育与培训供给过程中也存在责任感缺乏的现象。放眼工厂车间,“现代师徒”关系的结成常以农民工文化素质不高、能力低下为由将其排除在外;聚焦社区内外,针对农民工城市生活常识、心理健康和知法普法的宣讲活动至今仍没有得到普及;而社区居委会组织不定期开展的家庭走访也大都流于形式,很难对农民工家庭的学习与交往需求进行深入了解。
5.主动学习成果认证困难,农民工学习积极性受挫
生活场所学习对于日常生活情境的重视、学习与教育空间的拓展以及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引导和激发与农民工市民化教育多层次、多元化的教育目标要求不谋而合,对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有效性与针对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四、发挥生活场所学习优势拓展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路径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健全监管与保障机制
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形式与场所单一,仍以学校、培训机构的面授和现场教学为主,深入社区或是利用电脑、手机等互联网移动终端面向农民工开展的教育活动较少。这不仅难以满足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便捷性需求,也与农民工群体的心理特点相悖。农民工作为成人学习者,针对其开展的教育培训应当适应其学习心理,体现多样性与灵活性,将传统教育模式指导下的集中式课堂讲授作为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主要手段是不合适的。
2.协调教育供给主体,提高市民化教育服务能力
农民工市民化包含“职业市民化”和“生活市民化”两个主要方向,与此二者相应的教育应由不同供给主体分别或交叉提供。除政府在教育供给中的主导地位之外,包括企业、社区、高校等教育培训供给主体都在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民工日常生活学习发生的场所存在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各教育供给主体更应协调彼此间的定位,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切实提升农民工教育供给的适应性、多样性和有效性,进而体现出其在农民工市民化教育中的服务优势。具体来看,一是发挥企业的技能培训应用优势,借助农民工身处工作场所的便利,定期开展岗位培训,提升农民工实践操作技能并即时应用于日常工作,辅以薪酬增加和职位提升的激励政策,增强农民工的职业成就感和企业归属感。二是发挥社区的精神生活培育优势,针对农民工与社区居民情感联系不强、精神文化生活贫瘠、法律与公德意识薄弱以及心理适应障碍等现象,立足社区平台,组织社区运动会、演讲比赛、书法大赛等活动,举办普法立德讲座,为有需要的农民工提供心理义诊,推动农民工与社区居民友好交流,引导农民工融入社区,进而适应城市生活。三是发挥高校的学历提升优势,通过学校与学校、学校与培训机构以及学校与企业间的联合培养,满足正处青年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文化知识和职业能力更高层次的需求。
全省已建的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在防御2012年汛期的强降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防灾减灾作用,有效避免了群死群伤事件的发生。
3.利用虚拟场所学习优势,开展互联网和多媒体教育
柯林和玛格丽特(Colin&Margaret)认为,一个人在任何适宜的环境中进行的工作和学习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面对农民工工作强度大、空余时间难以集中的现实,农民工市民化教育应与时俱进,利用虚拟场所学习的灵活性优势,借助智能手机、电脑等移动互联网终端,随时随地开展互联网及多媒体教育,让教与学随时发生于上班途中和茶余饭后。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是要做好网络平台搭建工作。开放性院校可与企业联合提供网络平台,建立从内容输入到评价反馈完整一体的学习机制,做好平台日常的更新与维护工作,保证农民工参与学习的良好体验。二是要坚持互联网教育的需求导向。市民化教育产品的开发过程既要考虑到农民工群体较低的知识文化水平、有限的消费能力和碎片化的学习时间,又要联合政府相关机构对农民工身处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发展需求和日常生活中的城市融入状态进行动态分析,从而增强教育内容的适应性,提高使用者的学习效率。三是要保证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开放性院校、职业技术学校可与企业联合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教育网络资源库,整合各方的优势师资力量和丰富在线教育资源,为农民工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保驾护航。
4.发掘农民工日常生活需要,促进非正式学习成果的个性化认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12]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能否建立起个人生存发展需要与接受教育之间的联系,并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而这种联系的建立离不开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对于自身利益的现实诉求和长期发展的潜在需要。促进农民工自主个性化学习,不仅依赖农民工自身对于日常生活需要的发掘,更需要家庭、社区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社区居委会、妇联等组织可通过走访慰问了解本社区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生活上的困难与要求,进而认可农民工家庭成员的正当需求,鼓励他们通过自主学习解决困难。另一方面,面对农民工主动学习所不可避免出现的随意性以及学习成果非结构化的特点,教育体系应当借鉴部分欧美国家在生活场所学习实践中较为成功的质量保障标准与评估方法,对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学习成果予以认证。如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可借鉴芬兰、西班牙等国家开展的生活场所学习认证实验(LPL)项目,利用生活场所学习认证模型(Lifeplace Learning Model),由教师等专业人员与农民工协商订立个性化的学习协议,通过对协议目标完成情况的多样化评估对达成学习目标者给予认证,并依据知识、技能、素养等不同维度的认证内容分别将认证结果推广至雇用单位或所在社区。让农民工切实感受到目标达成与需求满足的成就感,从而实现其市民化过程中的自主个性化学习。
将后缀igs格式的文件导入Anycasting模拟软件中,同时对零件进行网格划分.网格的大小设置为1,所画出的体网格数在六万左右.将铸造工艺参数中铸件材料设置为AlSi9Cu3,模具材料设置为45号钢,浇铸温度选择640 ℃,注射速度设置为2 m/s,模具温度选择220 ℃.设置基本参数后,启动模拟过程[3].填充结果如图4所示.从图4可以发现,铸件充型过程平稳,未出现紊流等现象.
【参考文献】
[1]Harris M,Chisholm C,Allan M.Lifeplace learning for 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industry and business[J].Industry & Higher Education,2010,24(24):135—141.
[2]Colin u.Chisholm,Margaret S.G.Blair.Extending the Models for Work-based Learning into the Lifeplace[J].Word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2006.
[3]茹宁,吴梦林.超越“工作场”:生活场所学习模式的兴起[J].开放教育研究,2016,22(6):119—126.
[4]李娟.行动者网络理论:成人日常生活学习研究的新视角[J].成人教育,2017,37(11):6—10.
[5]刘文烈,魏学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思考[J].东岳论丛,2010,31(12):151—154.
[6]Dr Margaret Blair.Lifeplace Learning:What is it.[DB/OL].https://learningtousegimp.files.wordpress.com.2016-05-26.
[7]王小霞,江宜航,张娜.农民工再就业培训:“九龙治水”多头管理[N].中国经济时报,2009-10-19.
[8]申秀清,徐莎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教育的困境及对策[J].继续教育研究,2015(7):38—41.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N].中国信息报,2018-04-28(003).
[10]刘慧.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继续教育研究[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17(4):11—16+108.
[11]Coombs P H,Ahmed M,Israel B B.Attacking rural poverty;how nonformal education can help[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0,46(46):235.
[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00.
An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Exploring the Migrant Workers'Citizenizatio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place Learning
JIANG Hao-tian,CHEN Ming-kun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Abstract】 The core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s“urbanization of human beings”.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farmers to citizens is a long-term social process,during which education needs to play a greater role.Taking lifeplace learning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lue of lifeplace learning for the citizenize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expounds the bottlenecks faced by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migrant workers'citizenship education,play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coordinates the supply of education,and conducts Internet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ew path of migrant workers'urbanization education in the aspects of promoting the independent and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lifeplace learning;migrant workers;education of citize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794(2019)11-0046-05
doi: 10.3969/j.issn.1001-8794.2019.11.009
【收稿日期】 2019-01-10
【作者简介】 姜浩天(1993—),男,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农民工教育;陈明昆(1963—),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非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
(编辑/徐 枫)
标签:生活场所学习论文; 农民工论文; 市民化教育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