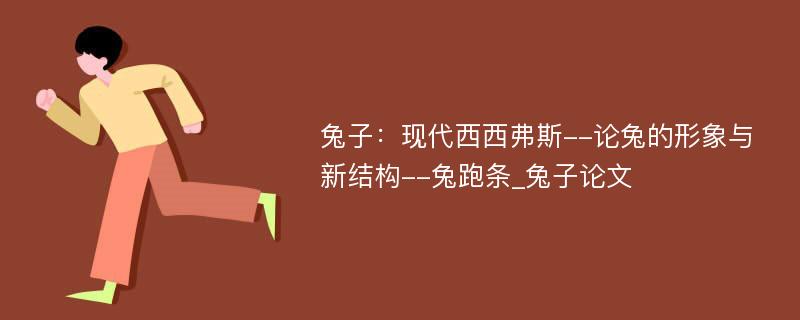
“兔子”:现代西西弗斯——--论《兔子,跑吧》中的“兔子”形象与小说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兔子论文,形象论文,结构论文,小说论文,跑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兔子,跑吧》(1960)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小说表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传统的主题:对“美国梦”的追求及其幻灭。关于文学创作,厄普代克一直坚信“有必要制造一种模糊性。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比生活清晰。”[①]在他看来,人的生活都是模棱两可、多面体的,人的性格自然也不例外,本着这样的创作信念,厄普代克在《兔子,跑吧》中将“兔子”哈里·安格斯特罗姆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再现在读者眼前。本文试对“兔子”的性格作一剖析,并且分析小说结构是如何表现、突出人物性格的。
一、摇摆不定的“兔子”
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西西弗斯是一个自私、狡滑、残酷的暴君。由于在世上犯下了种种劣迹和罪行,上帝在他死后将他判入地狱。地狱中的西西弗斯为得到上帝的宽恕,便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把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山底一直推到山顶。这一任务成了西西弗斯的终极目标。山顶代表了上帝对他的宽恕与慈悲,石头推上山顶,西西弗斯就可重新获得曾经属于他的自由。因而在这一意义上,山顶又是自由的象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西弗斯没日没夜地推动着巨石;然而每一次他几乎快要推到山顶时,石头却又毫不留情地滚回到山底。于是西西弗斯又不得不重新开始新的一轮“推石努力”,他不知何时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甚至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兔子应该说是一个现代社会中的西西弗斯。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和差异,但在最根本的一点上却是具有可比性的,即“两人都为令人精疲力竭的、单调枯燥的,而且显然是无穷无尽的任务所困”。[②]那么,兔子的任务又是什么呢?他像西西弗斯一样,也试图重新找回那曾经属于他的东西;像西西弗斯一样,他所经历的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像西西弗斯一样,他的行动也是摇摆不定的。在小说《兔子,跑吧》中,兔子年轻时曾是一个杰出的篮球运动员,对他来说,作为篮球明星的日子是他生命中最灿烂、最辉煌的顶峰,成年后,这顶峰上的感觉在他已是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了。为了重新达到这一顶峰,重现过去的辉煌,他仍然不停地、一次又一次地“跑”。兔子的“跑”这一行动在本质上类似于西西弗斯推石头的行动。他不断地跑着、不断地失败、不断地返回。在奔跑中,他实际上是在试图登上理想的顶峰,而在返回中,他又落入失望与绝望的深渊。一旦回到了起点,他又不得不重头再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兔子这一摇摆不定的性格呢?
兔子性格中这一摇摆不定的特征主要缘于他生活中一对对无法调和的冲突。其中最突出、最明显的是过去与现在的冲突。对他来说,过去是一个理想的完美世界,那时,他感觉自己无所不能,既有作为篮球明星的名气,又有这名气给他带来的一切:教练的赏识、队友的钦佩、漂亮姑娘的爱慕;然而过去毕竟已经过去了,他的现状,即现实世界则让他万分沮丧:平庸的生活、无聊的工作、中下层的地位,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与妻子之间的性爱已变得“死气沉沉,毫无新鲜感。”[③]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生命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兔子没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出于对枯燥无味生活的厌倦和失望,兔子一次一次地“逃跑”,他试图回到过去完美的日子。然而,那些日子毕竟属于过去了,不论他怎样努力,他的梦想总是与现实冲撞,兔子不时的“逃跑”和与现实不时的冲撞似乎将他固定在一条来回摆荡的直线之上--线的两端分别是过去和现在。
兔子无法调和过去和现在,也无法调和自身角色的两重性。26岁的他现在已为人夫、为人父了,这一社会角色要求他承担起家庭责任,按社会传统的标准循规蹈矩。然而,兔子偏偏又是一个自我意识极强的个体,这一角色又无时无刻不在催促他去寻找自我、拯救自我。两种角色总是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作为一个社会人,他的行为举止理应像一个成熟稳重的成年人,但他心中强烈的自我意识又决定了他总是像青少年一样反复无常而且捉摸不定。他宁愿有负于社会、工作、家庭“强加”给他的义务和期望,而不愿有悖自我的需求和念头,那怕这念头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时不时感觉自己“被家庭责任、被社会阶级、被工作所困。”[④]尽管他坚信责任、义务和规定阻碍他寻求自由和自我,然而可悲又可怜的是,生活中的兔子又不得不面对现实。这样,结果只能是一个:他的社会角色和自我角色不断地相撞,虽然后者偶尔也会向前者妥协,但最终导致的是剧烈的冲突。兔子无力调和这两种角色,因而在这两种角色之间不停地来回摆荡。
除了以上两对冲突之外,兔子还无法调和外部环境与他内心渴望之间的矛盾冲突。从外部世界来看,兔子生活的时代是艾森豪威尔任总统的五十年代,那是一个“举国上下毫无生气、循规蹈矩的时代”[⑤]。美国人民似乎怡然自乐、津津乐道于生活所赐与他们的一切,很少有抱怨、牢骚、不满和反抗;但兔子并不像周围环境一样安稳、平静,不像周围的人们一样自得、沉默。在他内心世界,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设法改变现状,重新寻得自由与完美。这一愿望缘于兔子对自身现状的深深不满,缘于他对“艾森豪威尔年代性爱及社会约束”[⑥]的反感。正因为如此,他不停地奔跑、出逃,而书中其他角色则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对兔子来说,运动成了对周围平静世界的一种反抗,只有在运动中他才能感到自己的活力,只有在运动中他才能感到自己在向梦想挺进。在小说中,兔子的情人露丝也说道,“尽管你干得愚蠢,可还在斗争。”[⑦]兔子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是因为别人无法接受和理解他的努力。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兔子是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人,他以自己的运动即奔跑来对抗外部世界,来实现、或者至少是憧憬内心的渴望。
《兔子,跑吧》创作于1959年,当时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狂热信仰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潮;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孤立无助、彷徨迷惘。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对世界、对人生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兔子正是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正一天天地失去意义,因而梦想拯救自我。要拯救自我,他首先必须从混沌状态中觉醒过来,要觉醒过来,他就必须反抗,必须反叛。兔子选择了“逃跑”,选择了世人所不齿的性放纵,然而正如存在主义作家贝克特所说,任何形式的反叛、拯救都不过是人生死刑的“缓刑”(respite)[⑧]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受苦受难,因而自救是永无出头之日的。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正是在这看似徒劳无功的绝境中的反抗与挣扎,兔子才感到作为个体的存在,才感到自己内心的希翼和憧憬,在这个意义上,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他能否最终自救,而是他在始终不停地寻求自救,寻求自身存在的价值。为了表现兔子的思想和性格,厄普代克在小说中精心安排材料、建构文本,他对全书结构的关注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下面再分别从小说的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来分析人物性格是如何通过结构得以展现的。
二、纵向结构
我们发现,从小说的纵向结构上来说,厄普代克描写了许多向上和向下的行动。兔子的脑海中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梦想,在这一梦想的驱动下,他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往高处跑的冲动和欲望。在他看来,只有往高处跑,他才能到达他的理想王国,才能让自己的美梦成真。因而他不仅是经常跑,而且是“向上跑呵”(第6页)、“爬上了山”(第406页)。他跑的方向基本上都是“往上”(uph-ill),但等待他的总是随即到来的、事与愿违的“向下的”(downhill)的突变,兔子被困于“跑上”-“跑下”的循环往复中。在高处,他似乎置身于精神的理想王国,而在低处,他又不得不面对物质的现实世界。
这种自“上”而“下”的变化也是一种“突降”(anticlimax)。作为修辞手法,“突降”指的是从重大、精彩的文本内容突然转入平淡、琐屑的内容。在《兔子,跑吧》中,厄普代克将这内容意义上的“突降”与文本结构紧密结合起来,指出兔子自上往下的循环运动其实也表明了他不断从希望、兴奋跌入失望、沮丧。全书的纵向结构正是在这样一个个的“突降”中建构起来的,这样的结构将兔子摇摆不定的性格特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小说一开篇,兔子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几个少年在打篮球,便兴趣盎然地加入了进去。打篮球使他很兴奋,让他感觉“从长期的忧郁中解脱出来了”(第5页),这“长期的忧郁”源于兔子心中由来已久的对工作、生活、婚姻、自我的不满。打完篮球后,兔子感觉到“万物复苏”(第5页),他甚至觉得“空气中充满了生机”(第5页)。对他来说,不仅周围事物焕然一新,连他自己也变成了全新的一个人。他不加思索地扔掉了香烟,毅然决然地对自己说要戒烟了。带着这一决定,带着一颗“解放了的心”,他开始向高处跑去。这一下意识的举动表明兔子决心翻开新的一页,生活在重新发现的自由与荣誉之中。
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一旦回到自己的家,现实中的一切又一股脑儿地向他涌来--房子的前面“墙面壁板色泽斑驳”(第6页),通往房间的木板台阶破烂不堪,“没有阳光的门厅”(第6页)里总有一股抹不去的怪味;进了屋子,他发现喝得醉醺醺的怀孕的妻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低级庸俗的电视节目,而家里则是乱糟糟的。一进家门,妻子就叫他去接儿子,去取车子。与刚刚发现的自由与完美相比,现实中的这一切是如此令人沮丧。兔子忽然感觉到家庭琐事和责任将他重重包围起来,自由与完美转瞬即逝,兔子被残酷地拉回到现实之中。现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由辉煌到琐屑的“突降”,最终促成了兔子从家中“出逃”。
兔子的离家出逃完全是一时的冲动,因此他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出逃,更不清楚应该往哪儿跑。一路上,他不停地幻想着太阳是他的目的地,而到达高高在上的太阳就意味着要往上走,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到达高悬在上的太阳,他又必须往南走,即在地图上往下走;地图上朝下的方向是接近太阳的正确方向,但是它与兔子脑中一直存有的向上的方向截然相反,这一矛盾暗示着兔子向上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开着车一往直前,最终发现自己陷入了绝路。逃往“天堂般的”太阳的努力失败了,兔子只能开车回去,他没有回家,而是去找以前的教练--一个“世俗气十足”的人。在兔子这平平常常的一来一回中,似乎存在着令人啼笑皆非的“自相矛盾”:要想到达高处他得往下走;而他往上跑的结果又总是往下跑。这“自相矛盾”似乎将兔子的行动限制在一个循环往复的框架中,正如书中所说,兔子“就是不愿意沿着自相矛盾的路子一直朝前走”(第328页),其实,即使他愿意,周身的“自相矛盾”也使他无路可循。
兔子结识了露丝,并随即与她同居。值得注意的是,在与露丝的交往、甚至做爱的过程中,兔子感兴趣的并不是性爱本身,而是一种“超验的启示”。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天启”可以将他带入一个神秘的空间,任他美梦成真,而只有“通过追求超验的目标,人才得以存在。”[⑨]于是他向露丝提议并坚持去爬山,他的提议和坚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内心“向上”的渴望。快近山顶时,兔子突然变异常兴奋,他莫名其妙地对露丝叫道,“我的女王”,“我的好马”(第155页),他此时似乎徜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似乎在神秘的“超验”中寻求到了自身的存在,外人自然无法体会他内心的感受,难怪露丝要问“你的什么?”(第155页)。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栖息的这个实实在在的空间在向上延伸”(第156页),与其说这是他的认识,倒不如说是他的希翼。他想证实自己的行动是“向上的”,他所追寻的是绝对真理。与露丝一同站在山顶,兔子眼中的一切都变得温馨、浪漫而有诗意。
但是兔子突然问露丝,“你以前真的是妓女吗?”(第157页),露丝的默认使得兔子很失望,起初他将露丝看成他的女王,甚至他的女神,但结果证明这个女神不过是个妓女。露丝真实的身分对兔子及其光辉的梦想简直是一种侮辱。爬山使他兴奋起来,而露丝的身分又使他的情绪一落千丈,这一“突降”令兔子领悟到性爱作为一种反叛方式亦是徒劳的。想在性爱中感受“超验”、发现自我的努力失败后,兔子紧接着“乘客车下了山”(第157页)。回到住处后,兔子再也不像刚开始一样赞美、欣赏露丝,相反,在做爱过程中,他将她当作一个真正的妓女;兔子这样做是要把自己降为一个好色之徒,他自身产生了“突降”,即从浪漫、虔诚变得卑鄙、猥袤,他更觉得世界无情、生活无序、而寻求自我更是无着。
类似以上各例,“突降”的情节贯穿全书,兔子正是在这样一个结构中上下奔跑。然而这还只是在纵向结构上,在横向结构上,兔子同样也是来回奔跑。这两者相辅相成,将兔子摇摆不定的性格特征展示出来。
三、横向结构
纵观全书,兔子的追求行为有一个规律:出逃-回归-出逃-回归-出逃-回归……这一规模又将兔子固定在一个线性的横向结构之上。虽然他每一次出逃的方向和目标各不相同,然而循环往复的行动又毫无例外地将“他和他的问题带回恒久不变的出发点。”在不停的出逃、回归中,在来来去去的摆荡中,兔子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梦想始终没有得以实现。如果说兔子摆荡不定的性格缘于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内在与外在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那么兔子在横向结构上来来去去的行为轨迹则从另一个向度上展示了这些矛盾。
兔子第一次离家出逃的原因其实是内心深处一种对理想世界的憧憬,抑或是幻觉。通过出逃,他想摆脱社会和家庭要求他承担的一切责任,想成为一个无拒无束的自我。第一次离家过程中,他与露丝同居,为一位老太太看管庭院,与牧师埃克利斯打高尔夫球,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确实享受到了片刻的自由。但这自由毕竟只是片刻的,当他妻子进了产房、生出他们第二个孩子时,兔子的自由感倏地消失了。听到妻子临产的消息,他强烈地感到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不可推诿的职责。此时,他的社会角色超过自我角色而占了上风,他回家了。一回家,他就“承担起一个改邪归正的丈夫的角色”[⑩]:照顾妻子时体贴入微,陪儿子玩时耐心卖力,干家务时兢兢业业。此时,他似乎与妻子、与现实达成了某种和解。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和解是暂时的,对兔子来说,要尽职地担当起社会角色意味着牺牲自由,为外界环境放弃内心需求,这是兔子怎么也不愿意做的。无论他与妻子、与现实作出什么样的让步,达成什么样的和解,最终的胜利者总是他的内心需求。回到家后有一天,兔子突然觉得异常兴奋,他迫切地想要和妻子做爱,而妻子刚生过孩子,身体还虚弱。她的拒绝让兔子很伤心,他觉得自我意识受挫。因而第二次出逃,他要逃出这个家庭的“牢笼”。
兔子任性地走了。他的自私和出逃将妻子詹尼斯彻底击垮了,一想到再次被丈夫抛弃,她悲痛欲绝,因而借酒浇愁,她的神态变得麻木,行动变得迟缓,竟在给刚出世的婴儿洗澡时不慎失手将孩子淹死了。出逃在外的兔子听到这一消息,也震惊万分,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孩子,嘴里不停地说“是我的错”(第382页,第384页)。内疚之下,他甚至希望自己被关进监狱。这表明兔子愿意承认错误,愿意为此承担所有的责任。然而,在孩子的葬礼上,他感到一股“令人窒息的委屈”(第406页),他当众大叫起来:“别盯着我!不是我杀的”(第405页),“是她(妻子)干的”(第406页)。他所说的话虽然句句属实,但不合时宜,所有在场的人都因他“突如其来的冷酷无情”(第405页)而目瞪口呆。但兔子觉得自己是清白的,不应承担太多的内疚,他想对众人喊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然而他的内心感受与葬礼是如此格格不入,无奈的兔子在众人震惊的表情之下,又一次“转过身,跑了”(第406页)。
他又跑回到露丝的住处。直觉告诉他,他在露丝那里至少可以享受到性的自由。然而出乎他的意料,露丝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以前兔子之所以愿意与露丝同居,是因为没有什么束缚、没有任何顾虑。但是现在,露丝怀孕的事实将不可推卸的责任摆到他眼前。他从自己的家庭中逃出来,却发现又逃入了另一个“家庭”。见到兔子,露丝也向他摊牌了,“你同她离婚,否则就忘掉我”(第421页)。从性爱中获得自由的想法此时破灭了,兔子忽然觉得自己“陷入了双重约束之中”(12]:无论选择詹尼斯或是露丝都等于选择责任与义务,现在谁都不能给他以充分的自由。兔子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他所知道的只是再一次跑,因为只有在跑的过程中,他才可以拥有一种获得自由、发现自我的渴望。就这样,整部小说在“啊,跑啊,跑啊”(第425页)中意味深长地结束了。读者自然不知道兔子往哪儿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是跑不出什么结果的,无论往哪儿跑,也无论跑多少次,他终究还是要回来的。
综上所述,兔子的“心路历程”也是沿着“出逃-回归-出逃-回归”的规律以时间为顺序展开的,这一线性运动构成了小说《兔子,跑吧》的横向结构。在这一结构上,兔子在本质上仍然和西西弗斯一样,不断地出逃,寻求自由、完美和自我,而结果却是不断地回来。兔子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又无法停止追寻,这正如西西弗斯无法将巨石推上山顶,却又无法放弃努力一样。兔子成了一个现代的西西弗斯。联系小说的创作年代,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兔子其实是一个“引申的比喻”,他象征着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他们面对的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异化的、甚至敌对的世界。作为个人,他们感到被孤零零地抛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活失去了意义,生存失去了价值,自我意识被忽略,他们苦闷、迷惘、挣扎,他们是一群苦苦寻找灵魂的现代畸零人。
注释:
①(11)Donald J.Greiner,John Updike's Novels,Ohio,Ohio Univers-ity Press,1984,p.48,p.59.
②David D.Galloway,The Absurd Hero in American Fictio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0,p.10.
③⑥Ralph C.Wood,The Comedy of Redemption:Christian Faith and Comic Vision in Four American Novelist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Dame Press,1988,p.210.
④⑩Josephne Hendin,Vulnerable People:A View of American FictionSince 194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88,p.113.
⑤Matthew Wilson,"The Rabbit Tetralogy:from Solitude to Society to Solitude Again",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37,No.1,Spring 1991,p.7.
⑦约翰·厄普代克《兔子,跑吧》,李力、李欣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25页。文中作品引文出处同此,不再注明。
⑧⑨转引自钟良明“论存在文学的人道主义内涵”,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第26、22页。
(12)Judie Newman,John Updike,Houndmills,Macmillan,1988,p.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