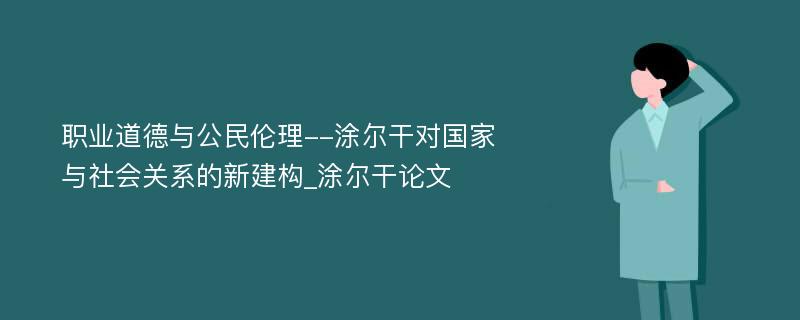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公民道德论文,关系论文,职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由来 在晚近的社会理论中,无论是帕森斯以降趋于中观和微观的社会研究,还是以福柯和布迪厄等为代表的广义上的权力分析,或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及哈贝马斯反其道行之而提出的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的概念,都似乎有意无意地表露出一种“去政治化”的思想倾向。这种“社会性”的偏好,往往喜欢预设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结构(Habermas,1992;Lockwood,1964),或者用一种弥散性的社会权力概念或激进或舒缓地来解释政治的构成和运作机制(Foucault,1979,1980;Giddens,1990,1991),或者干脆认为一切存在均为一种流变的过程(如Bauman,1987,2000)。无疑,社会理论的凡此种种努力,都旨在寻求一种超政治的解放,由此,生活政治成为了寻求新的自由和秩序的最终依据(斯科特,2004,2007),甚至社会学家也必须承担这样的一种主体性的角色(图海纳,2012)。 这种强烈的社会思潮,既与二战以后对于威权政治的普遍反思有关,也与批判遍及生活世界之各个角落的资本与资本的衍生物及其无所不在的隐形控制有关。而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说,也必会影响到观察和归纳、演绎与分析的基本范式。中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受此种思潮或范式影响颇深,长期形成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往往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为基准(邓正来、亚历山大编,2006;张静编,1998),或是直接切入底层社会生活之中来实施社会学的干预性实践(沈原,2006)。不过,面对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转型的时代,或对于那些曾经此类转型的经典社会学家来说,纯粹以预设性的社会为基点,是很难透视政治体制及其生活样态的全部的。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社会学家很难对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向上各层级的具体结构和运作机制做实地的经验调查,容易产生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意见式的抽象判断,因而在经验认识上国家与社会的两端往往是不对等的。二是基于这样的情况,社会学家更倾向于从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机制的社会效果出发,来判断后者的形态和性质,因而往往采用社会分析的概念来探讨政治领域的问题。三是产生一种研究策略上的悖论,即将政治与行政体制及其派生而成的制度视为正式制度,而在社会具体生活中运行的其他逻辑则皆不具有正式性。这样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似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基于对正式制度的变通、析解或对抗而形成的,社会生活“非正式的”运行,恰恰成为了对“正式的”制度标准的“偏离状态”,从而消解了其自身的逻辑(刘世定,2006/1996;渠敬东,2013);而另一方面,则很容易形成对政治生活的制度主义解释,仿佛政治体制的运行仅遵循一种刚性结构,其间没有任何非制度化的空间,没有任何情感、道德和价值的社会成分。对于这种简单的认识,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政治分析(马克思,1972)和韦伯有关三种支配类型的政治学说(韦伯,2010)中找到反例。 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政府的作用逐步加强,社会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家治理的研究,一是向理论与历史的纵深领域推展(周雪光,2011,2013),二是逐步将经验观察深入到地方政府行为的过程中,进而揭示社会、经济与政治层面合力而形成的结构效应(折晓叶,2014)。不过,国家治理与政府行为的研究,还不能等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社会理论关于国家构成及其作用机制的一般原理的研究。社会学的思考若要拓展到这一领域,还必须追溯到现代社会得以酝酿和形成的那个大转型时代,追溯到现代性问题得以全面产生,进而矛盾化甚至危机化的历史大格局之中,从那个时代构成的总体思考中寻找更丰富的想象力,来获得对于当前社会和政治的新的理解。 本文的一个主要用意,是尝试回到经典社会理论家涂尔干那里,去寻找思考现代社会及政治问题的思想资源。这位甚至被后人称为“社会学主义者”的思想家,其一生的学术思考遍及几乎所有的实质问题领域,我们今天实在不该把他强行划入学科化的门类。他的时代,正值法国大革命后危机重重、疑影重重的时代。大革命既首次全面践行了现代政治的最高构想,也让民主带来了“暴政”,旧制度再次复辟(托克维尔,1992)。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处于危难之中,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怀疑情绪高涨,到处都是抽象的观念和成见;家庭纽带解体,经济竞争激烈而残酷,赤贫阶层大面积出现;在政治上,民众充满着暴戾之气,而上层政权因派系林立,合法性丧失,经常瞬间性地倾覆和更迭,而紧接着全社会又再次掀起要求革命的浪潮。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普遍陷入的“失范状态”(即anomie,见涂尔干,2000;渠敬东,1999)。 面对这种情势,涂尔干所做的工作,首先是从人心、制度和政治构想上全面清算大革命的遗产,《自杀论》这样的带有实证意味的研究即是这方面的成果。接着,涂尔干拓展了现代社会之形成的历史资源,从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历史研究中拓展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解释链条。与此同时,他也开启了社会自成一类的神圣性研究向原始宗教加以引申的问题线索,显露出从整体上回应和重建卢梭和康德等人奠定的现代问题的理论志向,从而最终从道德个人主义、群体组织和国家政体的总体面向上提出了重建社会和政治的完整方案。 二、民情与政治 以往涂尔干的研究者,常常愿意从“社会作为实在”或“社会作为本体”的角度来理解他的社会理论。前一个角度喜欢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把握方法论上的意涵,着重强调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考察是依据社会分布状态来区分正常现象和反常现象,以此来确立社会规范的基础的(Lukes,1972)。不过,后一种角度却对此不以为然。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指出,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所提出的集体表象的理论已超越了实证论的角度,而将社会的构成看作是一种神圣存在的象征表现过程(Parsons,1949)。 简言之,两种理解的差别,一个是着眼于社会的现实存在,即对社会性事实做出科学归纳的判断,用来当作提供社会整合的规范依据(Nisbet,1974),人们常把《自杀论》作为这一研究路径的范本。一个则是将一种超越性的宗教存在作为社会本体,而所有用以再现这一存在的神圣仪式及其实践过程(即仪轨,practices)将社会存在内化在每个成员的行为和意识之中,由此才构成了社会规范的最终根据(参见Pickering,1984;Mestrovic,1985)。尽管两方各执己见,似乎反映了涂尔干社会思想早晚期的差别,但事实上都不过是呈现了涂尔干总体问题的不同侧面而已。实证论对经验实在的强调,说明涂尔干已将带有形而上学气质的圣西门和孔德学说真正注入了现实的经验世界中,指出规范并非仅来自于观念的层面,而必须植根于现实之中。而本体论所强调的是,涂尔干绝不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社会规范得以构成的基础,在于所有存在都内在于一种神圣与凡俗的二分结构中,与契约论所诉诸的个体意志之合意原理不同,社会乃是一种自成一类(suigeneris)的存在,只有通过社会本体构成的分类图式及其神圣生活的仪式活动,道德和政治秩序才能获得最终依据。 很显然,理解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一个困难在于如何调和其内在的实证主义和康德主义的两种倾向,如何在社会实在和社会本体之间找到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不过,即便解决了这一难题,还依然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无法克服:以往对于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大多数解释,包括上述两种看法,都带有一种唯社会论的色彩,或是人们常说的“社会学主义”之倾向。大多学者认为,涂尔干的道德学说带有强烈的“去政治化”的倾向,并未给国家政治问题留出多大的理论空间:即将革命时期的公意政治消解为职业群体内部的义务结构,将国家问题转换为公共性问题,将意识形态问题转化为集体意识的主体性问题(Lehmann,1993:167-173)。于是,集体的逻辑就置于国家的逻辑之上,似乎解决现代政治危机的方式,只在于用具有团结效应的群体社会生活取代政治生活,将道德确立在集体意识的基础上。 事实上,这种唯社会论的解释是相当片面的,既没有看到涂尔干社会思想中针对国家政治的特别的论述,更没有看到涂尔干与那些政治哲学先贤们之间微妙的思想传承关系。涂尔干曾经把“社会学先驱”的美誉送给孟德斯鸠和卢梭,这充分说明他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教益并不仅仅是批判意义上的。这意味着,以“社会”为逻各斯(logos)所奠定的一门科学并不单纯是对于政治的替换,而毋宁说是一种转换。涂尔干曾指出:“对卢梭来说,社会生活并非与自然秩序相反……卢梭在某些地方说,遵从立法者权威的前提是某种社会精神”(涂尔干,2003a:121-122)。他在评述孟德斯鸠的时候也曾说:“法律规范并不必然源自社会的自然,它们深藏于现实之中,除非某些立法者能够识别它们,阐明它们”(涂尔干,2003a:39)。这说明,孟德斯鸠和卢梭似乎早已明晓,在立法者之外确有一种特别的社会存在影响着法律的确立和运行效果,甚至决定着应选择什么样的政体类型。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提出,如果我们从“法”,即“来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出发,来探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秩序,就不仅要考察政体中权力分配的制度结构,还要考察那些能够让政体运动起来的人们的情感结构,即“民情”(mores)。换言之,国家的构成并不是单由政体形式决定的,其政体性质与民情基础是否匹配,才是“法的精神”的内在要求(Montesquieu,1989:21-30)。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治法的构成所依据的是自然原则,而民情却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有着现实的多样性特征。这是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最初论断。涂尔干充分肯定了孟德斯鸠这一论述的社会科学意义:“孟德斯鸠并不相信法律是被随意制造出来的;他坚持认为习俗和宗教都超越于立法者的权力,甚至认为与其他事物有关的法律不得不符合习俗和宗教的规定”(涂尔干,2003a:37)。但同时他批评说:“孟德斯鸠尽管观点新颖,但依然迷恋于原有的概念”(涂尔干,2003a:20-21),孟德斯鸠虽然看到了民情的精神意涵,却依然采用自然法的理性原则来做推理式的考察,或将法或政体的形式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相似地,卢梭虽然也系统论述了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之构成的整体机制,却依然坚信“完美只有在孤立的状态中才是可能的”,只有自然才能提供“神圣的纯一性”(sancta simplicitas)(涂尔干,2003a:80)。 涂尔干对自然及自然状态学说的批判,在后来的著述中得到了更确切的表述。他认为,将法理解为自然或将政体视为自然的表达,都没有看到一个更高存在的本质。事实上,构成人类生活的不是政体的自然与民情的情感这种二重关系,而是人性的二重性及其现实条件的关系。不仅法与国家政体的构成夹杂着情感和信仰的因素,而且民情中也蕴含着人的自然性质,因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如果仅靠一种理性的政治体制设计是无法持续维持的,必须依赖于带有宗教性的神圣事物才能确立起来。同样,民情的存在也不意味着纯粹的现实性,因为集体意识和道德秩序亦需要一种更高的灵魂表现才能形成(涂尔干,2003b:231-245)。于是,涂尔干将孟德斯鸠的论题倒转过来,将国家与社会群体理解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实体组织,而其存在的最终依据,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终极基础,则诉诸人性中的那个更高的存在本质来规定。这样,现实的个体感觉和意志活动,成为了凡俗的日常生活的身体感受性反应,而那种自成一类的更高存在,即本体论所说的那种神圣存在,具有灵魂的本质,并通过概念和范畴、思维和理性、语言和宗教等形式,借助公共节日、庆典和各种仪式等集体表象来确定人们的社会规范(Miller,2012)。 涂尔干对人性二重性(homo duplex)的论断,印证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对于“社会”存在之证明的理论努力。不过,这一康德式的证明也常常引来误解。人们往往将其与他较早时期的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相对应,将这样带有本体色彩的“社会”理解为社会事实意义上的物的形态,或者理解为区别于所有政治体的一种社会体形式,并将社会与国家人为地对立起来。殊不知,在涂尔干看来,所有超越于个体存在而为个体所信仰、依恋和服膺的集体形态,无论其表现为社会还是政治的形式,都具有道德力,具有神圣的集体表象而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呈现。因而,研究规范形成的根源,既不在于观念与物质的分立,也不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立,而在于在日常的凡俗生活之上必须有一种神圣存在,只有靠此人们才能在思维、语言和仪式活动中获得规范化的道德秩序。而且,正因为一个社会的神圣存在是不会凭空创造出来的,所以若将它与它的传统彻底割裂开来,一切道德规范皆不可能存留,一切秩序也必会瓦解(Miller,1996:43-44)。 可以说,涂尔干在诸领域所提出的各种学说,皆本于上述社会的证明,他的国家理论亦是基于这种原初的设定提出的。他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Durkheim,1958)一书,可以说是将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论述得最为充分的集大成式的作品。此书原名《社会学教程》,由题为“民情和权利的物理学”的手稿整理而成。①从原书的副标题和英文版给出的新标题中可以看出,涂尔干着意从民情和权利的概念与历史出发,探讨政治上的权利结构与社会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而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从而为大革命后的法国提供社会和政治建设的思想路向。 三、职业伦理与法团组织 在涂尔干的整个道德学说中,职业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早在《社会分工论》中,他对分工的讨论便有别于功利主义的看法,将分工看作是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化过程,而非纯粹的资本竞争的结果。此外,他接续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奠定的分析传统,亦将分工视为民情产生社会性作用的机制;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民情状态,与社会分工带来的交换、流动、传染和社会密度化密切相关。由是,涂尔干的权利科学,便不再完全落实在由霍布斯和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和康德以降的意识哲学发展出的理性基础上,而是在个体存在之外,确立了一种基于社会实体的自成一类的存在,而这种更高存在的活动才具有更为本质的理性意涵。相对于自我意识的学说,涂尔干明确提出了一种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的学说。即人的存在,或人性、人的权利的本质,乃为其存在其中的群体或集体(即社会体)的本质,个体间虽然有其自然性的差别,有其感性带来的个性的差别,有其职业确定的社会性机能的差别,而真正构成其道德生活之神圣性基础的,必来自他所依恋的社会。社会是其理性的来源、信仰的来源和道德团结的来源(涂尔干,2003b)。 不过,《社会分工论》提出的只是一种预设和一些历史片段式的说明,②还未做出充分论证。同样,有关社会作为自然原理的证明,则要等到更晚的时候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得到确证。这里有一条线索很有意思,即涂尔干于1902年为《社会分工论》所写的“第二版序言”,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均来自他1890年到1900年间在波尔多大学开设的“社会科学公共课”的讲稿,而这恰是《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前三章的主体部分。由此可见,涂尔干显然已表露出,这里有关职业伦理的论述,完全是对于《社会分工论》之论述的拓展和深化。 在有关职业群体的历史研究中,涂尔干强调了古朗治、瓦尔沁和拉瓦瑟尔等人对他的影响。他借助《古代城邦》等著作的思路,指出《社会分工论》所提及的法团组织可一直追溯到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古朗治等历史学家对于希腊和罗马的认识,已然突破了此前仅在家庭与城邦框架下的分析角度,而将群体性的职业生活及其神圣信仰作为理解古典时代的第三条线索。沿着这条线索,涂尔干特别考察了法团的历史形态。而这一考察的基本出发点则是为了探讨道德和权利科学的基础。 涂尔干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的开篇即指出:“任何人要想生存,就必须成为国家的公民。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有一类规范却是多样化的;它们共同组成了职业伦理”(涂尔干,2001:7)。这意味着,规范本质上具有两种形式,一是均一的政治性规范,即卢梭所说的公意共同体下的每个公民个体,其权利在人民的形式上作为主权者,同时也作为国家的臣民,而必有其被规定的义务。涂尔干说:“无论何时何地,这些义务在基本特征上都有相似之处,如忠诚和服务的义务”(涂尔干,2001:6-7)。第二类规范则有所不同,对于职业生活来说,不同职业组织所规定的义务往往差别很大,教授与商人、士兵与牧师都各自履行自己的职业,其规范性的要求不仅殊有不同,甚至有些竟是对立的。这即是说,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不同,它既不同于家庭的逻辑,亦不同于国家的逻辑,而必须有群体组织的保护。它必须诉诸一种集体的权威,而这种权威也不可归为个人的特殊意志,只能来自于功能性的职业规范的要求,以及共同生活的集体情感和价值基础。 显然,一个国家的义务要求,不能因个体的差异而放弃政治原理的共同规定;而职业群体的义务要求,既有其差异化的组织纪律的不同约束,同时彼此必然存在一种互为开放的功能空间,这两种规范颇与《社会分工论》提出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机理相一致,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共同构成了每个历史时代的公共的规范生活。而且,如何从个体上升为群体,从群体上升为国家,如何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进阶式地有效结合起来,便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的最大要务。 在涂尔干看来,对于规范的科学之确立,必须要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状态来加以考察。涂尔干追溯罗马“百人团”(Centuries)的制度体系,指出这种带有手工业行会特点的职业组织,虽然处于萌芽时期,却已经呈现出法团制度(régime corporative)的基本特征。 在罗马,法团带有宗教社团的特点,每个组织都有各自特有的神灵和仪式。同每家都有一个家神(lar familiaris),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公共神(genius publicus)一样,每个社团也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即社神(genius collegii)。正因为有着自身的神圣崇拜,所以在这样的法团活动中,神圣的共同生活便成为了纽带:无论是节日中的祭祀仪式,还是宴会、庆典,无论是在生活上能够给予成员定期帮助的公共基金,还是成员死后葬于一处的公共墓地,乃至最后他们的墓碑上都刻着的“敬社”(pius in collegio)字样。这足以说明,职业社团中的工匠们过着一种集体生活,彼此称呼为“弟兄”(sodales),虽像是同族兄弟(gentiles),却不像家族制度的约束那样范围狭窄,其亲密虽可比拟为亲属关系一般,却已超出血缘的纽带。这些职业社团依据职业生活及其专有范围内的社团信仰,结合成为更大范围内的行业组织,将家庭与政治上的纵向等级结构拉平,最初呈现出一种社会性的维度(涂尔干,2001:23-25)。 在涂尔干看来,基督教社会所属的框架与城邦社会的模式不同。法团在中世纪的发育与罗马社会相比表现出不同的样态。无疑,基督教的影响,不仅在宗教维度上培育了人们的“作业”观,而且这种职业群体在公共政治上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涂尔干引证拉瓦瑟尔的研究指出,法团往往是在一个专门的教堂中成立的,成员们在举行庄严堂皇的弥撒后,便开始一场宴会,将具有同样职业的人们集合在一起,通过业绩来做出信仰的证明。在这样的组织中,既有收支平衡的预算制度,也有带有慈善性质的公共基金,雇主之间、雇主与雇工之间皆有明确的义务规定;同业公会对于本行业的用工办法、技术标准、买卖规矩、信用制度等都有严格的规则。通过这样的组织化方式,人们彼此联系、彼此依赖,分享着共同的观念、利益、情感和职业,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共同的事务与共同的生活结合起来,在日常状态中构成了道德规范的整体。 法团在中世纪的复苏,非但不是一种旧有传统的遗续,反而变成了“由一部分人口组成的常规结构”。而这部分人口,恰恰就是第三等级、平民阶层或资产阶级的起源,亦即现代世界的起源。从社会形态学的角度看,最初作为工商业者的资产阶级,通过作坊生产和买卖活动,逐渐将贵族在自己领地开辟的市场转化为工商业人口的聚集地,城镇化过程也由此展开。一旦城镇成为制造和交易活动的中心,工匠和商人成为了主要的城镇居民,城镇便脱离了贵族的监护,具有了自由市的特点。涂尔干指出:“商人(mercatores)和居民(forenses)这两个词与公民(cives)是同义的:都同样适用于公民权(jus civilis)和居民权(jus fori)。这样,手工业的架构就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最早的结构形式”(涂尔干,2001:37)。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权的获得,意味着近代公民权的最初确立。 资产阶级的双重权利结构的确立,说明法团这样一种群体组织在中世纪中后期的发展不仅强化了其本来的职业特征,而且也显露出其城市自由化过程中的公共政治的性质。若说居民权的获得与法团的职业性有关,那么公民权的获得,至少在自由城镇的范围内也源自于此。因而,中世纪法团制度的确立,事实上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密切联系在一起,法团的职业组织化过程,与近代国家之公民政治的构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讨论也再次呼应了现代社会早期的民情与权利之间的微妙关联,即职业群体的道德性的传染机制,与现代政治之基本权利结构的形成和规定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发展过程。 因法团的发育而导致的城镇独立使得当时欧洲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上都产生了“去贵族化”的趋势。而顺应这一趋势,法团也不断得到扩充,逐渐形成行会的集合体,进而结成了新形式的公社(commune)组织。在几乎所有的公社中,政治体系与行政官的选举都是以公民分化为各种手工业行会为基础的。人们往往通过手工业行会进行选举,而法团和公社的首领也往往是同时选出来的(涂尔干,2001:37)。法团最终为整个政治体系奠定了基础,而政治体系也恰恰是从公社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 可是,大工业社会的来临对于曾经存在的法团制度极具摧毁作用,面对资本化的强制,传统上的职业群体抱残守缺,很难适应新的竞争需求而分崩离析。“所有这些事实都解释了大革命前夜的法团状态:它俨然变成了行尸走肉,变成了惟有在社会有机体中苟且偷生的陌路人”(涂尔干,2001:40)。现代经济竞争会将文明中以往存在的所有传统要素连根拔起,现代性的根本动力,就在于扫除一切过往的群体形态,而将一切社会关系纳入到大工业的经济结构中,在政治上也体现为全面革命的态势。 然而,对于大革命后的社会危机,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及《自杀论》中做了清晰的判断:整个社会所处的失范状态,其原因恰恰在于社会政治的运行革除了一切传统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每个人不再受到传统的家庭、共同体和职业群体的保护,因社会疏离而产生的极端自我主义的原子性个体,沉浸在抽象意识的妄想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政治体也因缺乏社会中间团体的保护带,而沦入不断革命的怪圈之中。因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切实的中介环节,让孤独的个体重新获得群体的依恋感和道德上的自足,同时让现代民主政治落实在一种既能够有效地组织经济生活,也能够充分地代表公共政治诉求的环节上,便成为了重建社会的基本路径。 四、从合意契约到公平契约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大革命的所谓公意政治的思想基础是契约论。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等,都是契约论的奠基者。因此,若要对这些学说进行总体的清算,就必须在理论和历史上为人们重新构建对社会契约的认识,破除从个体意志直接构成普遍意志的政治共同体的观念,这也是重新将社会与国家相结合的一项重要任务。 涂尔干指出,“对大多数人来说,契约的观念是一种操作非常简单的观念,可以认为是所有其他社会事实都源此而成的首要事实”(涂尔干,2001:181)。近代的契约观念似乎有一种逻辑上的自明性,即基于自由意志达成的合意状态,权利和义务关系就获得了明确的确定,现实中的所有社会约束关系也得以形成。涂尔干在他的文章《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中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基础是所谓“绝对可靠的”普遍意志,“它构成了一种非个人的平均标准,而将所有个人的考虑排除在外”;同样,根据康德的看法,“只有影响我的动机与我置身于其中的特殊环境无关,而与我作为抽象的人的品格有关,我才能确定终极的行为是正当的”(参见涂尔干,2003c:202)。对这两位思想家来说,道德义务的惟一形式即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形式,因此,也必然会预设一种“普遍的人”的观念形式。 可是,这样的契约要件虽是基于一种自然状态的判定,或是一种基本的道德预设,但其要求之高,绝不可能是人类早期起源的一种制度,必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会出现。无论从政治制度史还是民情史的角度看,契约论的标准都是在用观念的设计来去除社会的实在,既难以包容多样化的职业群体所具有的不同伦理样态,同时也漠视了契约的神圣性基础。所以说,“再也没有比这种表面上的明晰性更带有欺骗色彩的东西了”(涂尔干,2001:181)。既然有关契约的上述理解只是一种出于假设的理解,不是基于社会实在的理解,既然契约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上的约束关系,它的起源不可能很早,因而我们就应该考察这种带有法律或道德之性质的约束关系的历史渊源。 事实上,契约的这种约束关系有两个不同的来源:或是“来源于关系中物或人存在的一种状态或条件,在这种状态或条件中,这些物或人(暂时地或永久地)在特定环境中具有某种性质,并借助公共意识拥有某些已经获得的特性”;或是“来源于另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是物或人存在的状态,只是双方希望或渴望达成的状态”(涂尔干,2001:182)。显然,后一种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契约状态,但前一种状态的形成史却有助于揭示这种约束关系的本质,即权利的起源是某种普遍的物或人的神圣性基础;即便说是个人的意愿使然,也不过是这种神圣性传递而成的结果。 涂尔干援引了人类学家罗布森·史密斯(Robertson Smith)有关血缘契约或盟约(blood-covenant)的研究,指出在早期社会,群体所依赖的纽带是人们所属的自然群体的纽带。“食物制造血液,血液创造生命”(涂尔干,2001:186),人们吃同样的食物,意味着共享生命的同样资源,分享共同的神灵。无论是歃血为盟,还是基督教圣餐中的酒和面包,都通过分享圣物来约束自己,或只有通过血液的融合来获取群体的成员资格。在这种情况下,那种物或人的存在状态是神圣的,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成为权利的自成一类的本源,其他存在均为派生来的产物。与此相似,在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中的要物契约(contrat réel),即某人对某物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也“取决于该物的状态和条件,以及它的法律地位”(涂尔干,2001:187)。一般而言,要物契约中的主体是世袭财产,因交易物是对方世袭财产的一部分,故接受物的一方就成为了债务人。因此,他有义务恢复它或者交出相应的等价物,以示尊重。支付定金(arles)的习俗即来源于此。③不过,人们也常以象征的方式采用“某种没有价值的物”,如象征神圣性的稻草或日耳曼法中使用的手套,来代表对于世袭财产交换中的神圣等价物。罗马人的圣誓(Sacramentum)习俗,则将上述的象征性发展到了极致。在所谓的庄严契约中,人们为言辞和仪式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力量,言辞一旦说出就不再属于言说者,也不能撤销。通过誓言和乞灵,神圣存在会变成交换诺言的保护人,约束关系通过神圣的庄严仪式而最终得以确立。 只有当孟德斯鸠所说的贸易不断发展,使得社会密度骤然增加,人们因市场中交易主体的陌生化,才会淡化仪式性的特点,而使语言仅用来表达意志。于是,合意契约(contrat consensual)才会出现。意志共识的结果似乎是双方根据共同的意愿即可产生契约性的约束关系,就像经典契约论所设定的那样,单纯的意志宣称,就是契约达成的最终依据。但涂尔干认为,这种所谓的合意契约依然是不充分的。因为交互的意志既然可以随意达成,也就可以随意反悔和撤销,仅从意志中我们无法得到任何确定的东西,权利也不能从中派生出来。事实上,现代经济生活的迅速扩张,将原来契约达成的各种仪式“去神秘化”了,使缔结契约的纽带更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就像涂尔干所刻画的那种失范状态一样,人们在残酷的经济竞争中,“几乎以武断的形式把这些界限挪来挪去”,契约论所诉诸的平等意志,在现实中却沦为只有最强势力独占上风的意志,“自由也只不过是一种虚名”(涂尔干,2000:14-15)。 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契约得以存在的另一个事实:契约若要避免自由意志的随意性,依然需要担保和保护,契约的庄严性并未彻底消除。换言之,在现代社会中,罗马社会中的那种需要巫术和神圣过程才能得到保护的契约,即要式契约(contrat solennel)的形态,虽因世俗化的过程驱逐了神灵的位置,却依然需要确立双重的约束关系。任何合意契约的达成,单靠交互的意志共识都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依靠一种超个体意志的存在作为最终的根据。涂尔干指出:“如果神也曾是契约的当事人,它也用神来约束他们;如果社会也介入到代表社会的人之中,社会也对他们具有约束作用”(涂尔干,2001:202)。即使古老的神灵退了场,也必须有一种更高的自成一类的存在作为契约的终极担保人出场,合意契约才能具有要式契约的条件,从而得以持续有效地存在。 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新的公平契约(contrat juste)。公平契约的出现,将使整个财产制度发生转变。它彻底驳斥了所谓财产依继承作为其主要来源的看法,从而直接对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以及人的权利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平要求我们不能以低于其价值的方式去估价人们所提供或交换的服务”。这意味着“人们所得到的任何价值都必须等于他所提供的服务”(涂尔干,2001:223)。一旦出现不等同的情况,即意味着特权所享有的超额价值必来自于他人的劳动,而非其自己的劳动,这恰是他人被其非法剥夺的部分。因此,只有当人们之间物的分配相应于每个人的社会应得时,这种分配才会是公平的分配;只有当每个人的财产对应于他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时,他才真正明确了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个人才会超越自身的个别意志而成为社会的存在,也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和善意,因为他通过社会分配来确认自身为主体,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体。 公平契约的实质涵义是:契约所规定的人的权利和义务,并非单纯是由契约当事人双方合意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就保持和维护全体利益和价值而形成的分配机制来决定的。契约中意志的自由,必须先分有社会存在的内容,获得道德属性,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涂尔干指出,在人类行为的道德中,往往存在着两种义务:一种是公平决定的义务,一种是仁爱决定的义务。虽说公平是一种依照法律或制度之规定而产生的社会效应,同时也必须植根于“同情”这一情感法则之中。契约的同情基础,一是对那些付出大于所得、服务没有得到补偿的人提供社会情感的支持,二是对于所有先在不平等的状态给予一种情感的平衡,确保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社会的情感结构(Lukes & Scull,1984:235-237)。对于那些因个人禀赋和功德的差异而形成的现实的不平等,必须依靠仁爱这种人类的情感本原加以超越。这是一种基于人之社会性本身发育而成的大同情感(cosmopolitanism),可克服“一切从遗传获得的天赋和心力”所造成的差别(Durkheim,1970:294-295)。大同观中的仁爱是一种神圣性的同情,是基于人类的普遍性而形成的对于现存世界的情感超越。涂尔干一再强调,只有用人性的宗教维度来约束意志的自由活动,才能为契约确立公平的最终根据。“只有社会才能对自然实行全面的支配,为自然立法,将这种道德的平等凌驾于事物所固有的物质不平等之上”(涂尔干,2001:228)。 涂尔干对于传统契约论的超越,旨在证明:1、以社会的总体作为最终的根据,公平原则超出了契约权的范围,而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的基础;2、契约的达成不仅是个体意志的合意结果,也必须通过一种更高的社会存在作为衡平的约束;3、契约所规定的不只是一种法权关系,社会形成的规范既具有法律效应,也基于同情而具有情感效应;4、人性的二重性使得人们在共同的意识、理性、语言上确立一种大同的宗教情感,从而平衡着现实存在着的一切不平等。 五、民主制中的公民道德 从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对于契约权和财产权的讨论明显呼应了《社会分工论》有关两类社会团结的未完成的论述。在早期的著作中,涂尔干仅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古今差异中看到了现代分工的社会性基础,或是从压制型法律到恢复型法律的变迁中看到了整体上的社会平衡状态,却很少从公民政治的契约论基础来分析其得以构成的社会性根源。 而现在,有了对于契约论的进一步梳理和批判,社会存在的基础已经落实到了公民政治的领域,国家的理论问题也便映入眼帘了。很显然,涂尔干在这里对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问题做了一次翻转,即两者的关系并非仅呈现于古与今之前后对比的关系,而且是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双重性的关系:即人们既具体地处于职业生活中,也一般地处于公民政治中,两者都显露出“社会存在”这种最终的根据。在形态学的意义上,并非社会组织最终取消了国家,而是与国家一道构成了团结的双重纽带。相应地,涂尔干将法团这样的职业组织看作一种“次级群体”,而为一切人所属的国家则被称为“初级群体”。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其规模和范围显然比所有群体组织都大。但对于两类群体之关系的问题,涂尔干明显更侧重于孟德斯鸠的学说,而不是传统契约论者所建构的那种作为超级意志的国家。 涂尔干引证了《论法的精神》中的讨论,指出孟德斯鸠早已认识到“能够最充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形态就是君主政体”。这种形态包含着“中间的、附属的和依从的权力”。涂尔干认为,孟德斯鸠的这一讨论揭示了一种现代政治构成的秘密:即这些次级群体“不仅对引导特定的家庭或职业利益来说是必要的,也构成了更高级的组织的首要条件。这种社会群体不仅拥有统治权,也以更为特殊的方式被称为国家,它与国家本身并非是截然相对的,相反,它们的存在就是国家的前提:只有有了它们,才能有国家”(涂尔干,2001:49)。总而言之,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构成,并非仅仅是所有个体直接让渡权利所形成的合意状态,就像契约也不仅仅是两个个体意志达成的合意状态一样。相反,政治国家之所以形成,首先是奠基于职业组织这样的次级群体上的,而非所有个体通过让渡权利而构成的主权形态。 因此,如果说国家是统治权威的代理机构,那么政治社会所指的就应该是一种复合群体,国家乃是其最高机构。而国家与社会的真正关系是:“当国家进行思考并做出决议的时候,我们不能说社会通过国家进行思考并做出决议,而只能说国家为了社会才进行思考并做出决议。国家并不单单是一种引导和集中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次级群体本身组织化的核心”(涂尔干,2001:54;Mestrovic,1988:130-131)。事实上,现代分工的出现,既为多样化的职业群体之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又通过集体意识达成的有机团结确立了道德的基础。不过,虽然这种具体的道德意识克服了契约论中的单纯由个别意志推论而成公意的抽象状态,却依然无法形成一种更为广泛的认同基础。仅靠法团维系的道德依然存在着因分工和竞争的加剧而不断分化的危险。因此,如何能够将国家的理想与人类的理想融合起来,是奠定人类普遍道德义务的关键。④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亦是一种群体,是一种自成一类的最高群体,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情感认同。同时,国家也是现实功能意义上的公职群体,所谓公共服务即是国家的服务,法院、军队和教会都是国家的公职性的组织形态。国家与作为职业群体的法团不同,法团是社会中各种各样的集体情感和集体心态的载体,而国家只能听到这些情感和心态的“微弱的回声”。法团是一种通过构成集体情感而塑造社会道德基础的器官,而国家的功能则主要体现在社会思维上面:代议制中的代表们并不直接来自于公民个体,而是来自于代表个体的各职业群体,它们将来自不同群体内部的各种观念和情感结合起来,形成决议,再交由执行机构具体执行。国家突出体现为审议性的集体思维活动,通过次级组织的“代表”来使一般性的政治权利得到“表现”。⑤而各行政管理部门只是作为执行的代表,而不像法团代表那样是作为国家生命的代表来体现国家意志的。涂尔干比喻说,国家与其各行政部门的关系,仿佛是中枢神经系统与肌肉系统的关系。 涂尔干藉由法团系统为中介而构筑的政治结构颇有深意:个体只有通过职业群体的功能化和道德化,才能真正构建一个更高的政治体,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政治权利。而这一政治理论的出发点,旨在克服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构建现代政治的两重路径,既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那样,将国家理解为社会生活的监督者,也不像早期社会主义者那样,将国家理解为一种经济运行的庞大机器。同样,就政治体制来说,虽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宣称应遵循民主制的原则,但一种仅强调直接基于个体意志自由的民主,另一种仅强调基于总体社会平等的民主;就其社会思维的功能来说,一种“来源于社会的集体大众,并散布于大众之中”,另一种则“来源于国家或政府这种专门的机构”。涂尔干认为,这两类政治学说虽然从各自的角度确立了现代政治的合法性依据,却都因偏于一隅而成为治乱的根源。 从实质问题出发,民主制的真正性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意识的辐射范围,即政府所能融合的个体意识的范围非常大;二是政府意识与众多个体意识之间应存在非常紧密的沟通。涂尔干鲜明地指出:“实际上,国家的作用并不是表达和概括人民大众未经考虑过的思想,而是在这种想法上添加一种更深思熟虑的思想,两者截然不同。国家是而且必须是一种全新的、原创性的代议制核心,应该使社会更理智地运作自身,而不是单凭模糊的情感来支配”。他同时也强调:“所有这些审议,所有这些讨论,所有这些统计调查,所有这些行政管理信息,都由政府会议来支配,而且它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是全新的精神生活的起点”(涂尔干,2001:97)。这意味着,国家既不能脱离所有个体意识而成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也不等于直接顺从于公民,并归结为公民意志和大众舆论的单纯回应。事实上,“民主的暴政”既有可能来自于众多个体意志所造成的分散流变、犹疑破碎的混乱状态,也有可能来自于应对这种状态而产生的绝对权威,这两种形态虽形式上不同,但并无实质差别。⑥ 涂尔干指出,“我们的社会疾病与政治疾病同出一源”,即“缺少能够将个人与国家连接起来的次级组织”。为避免现代政治表现出来的一治一乱、左右摇摆的危机状态,就必须正视次级群体在政治构建中的重要意义。涂尔干对于大革命以来的社会失范和政治危机作出了明确判断,即在政治原理上,“倘若国家不压制个人,这些次级群体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国家想要充分地摆脱个人,这些群体也是必需的”(涂尔干,2001:101)。换言之,如果说国家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审议思维的形式对那些构成民情的大多数人的观念和情感作出反馈,那么它就不能仅依靠自己所做出的所谓权威判断来强行贯彻国家意志,也不能仅依靠代表的选举权来计算支持某种意见的人数,这样的做法等于“几乎完全摈弃了国家的理念”。若免于此,就必须在政治制度上全面构建个体与国家的公共纽带,因而在选举制和代议制的设计上,应将法团这样的职业群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单位。因为在现代分工社会中,能够建立此种政治关联的是职业生活中形成的道德纪律,而非传统上的地方忠诚关系。 涂尔干大胆构想了未来的国家政治架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按照我们所勾勒的计划来确立或复兴的法团究竟是什么样子:每个法团的上层都有一个委员会,负责指导法团,并管理内部事务……法团及其机构始终在发挥作用,所以,通过它们构成的政府会议决不会失去与社会的各种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它们决不会冒自身分裂的风险,而会迅速地、主动地感受人民在深层发生的变化。我们既可以保证它们的独立性,又不必打断其中的沟通关系”(涂尔干,2001:109)。惟有这样,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之间才可真正确立起相互依赖并彼此中介的道德政治的融合。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既不是一种遵循着各自逻辑并彼此构成限制的对立关系;也不是一种由个体经验性的功利生活,经职业群体而到政治国家的自然过渡的关系。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社会”扮演着多重意义的角色:首先,社会激活了历史传统的当下生命,法团所具有的共有制形式以及凝聚着集体公共性的仪式、意识和精神,都是构造现代道德不可或缺的基础。其次,职业群体构成了连接个体与国家的一个重要中介,既可作为个体所依恋的组织性载体,同时也为国家政治构成了富有弹性的保护带,从而避免了盲从性的个体因政治不满而形成不断革命和复辟的往复变迁(Müller,1993:104-106)。社会存在的另一个意义,是修正了对于民主制一人一票的简单理解,倘若仅“将民主理解为社会管理自身的政治形式……就等于说民主是一种没有国家的社会”(涂尔干,2001:87);代议制国家的民主主体,是职业群体作为代表来行使最高的国家权利,从而将具体的民情与一般的政体密切结合起来,这正是对孟德斯鸠提出的实质问题的回应。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涂尔干认识到,现代社会之政治构成始终面临着几重交困的局面。现代经济竞争的急速扩展,往往对旧有的社会文化传统构成摧枯拉朽之势。而从意志论和契约论出发所奠定的抽象政治设计也往往与此相配合,要么使抽象的自我主义发展到极端,让人们广泛地散布在各种各样的绝对意见之中,反而使他们的内心陷入更大的不安;要么将抽象的集权主义推展到极致,并用观念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以渲染,使政治时刻处在潜伏着的战争状态之中。⑦因此,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都需要一种新的方式加以规定、调节和润滑。 在人们的总体生活中,个体、家庭、职业组织和国家等是一种相互连带和构成的基本结构。不过,对于这一总体生活的构建,人们曾经尝试过不同的路径。自由主义者大多强调个体本位的权利,其中,契约论所推演出的政治也是基于个体意志的合意结果。相反,法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们多从现代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出发,要么将国家视为一种经济组织的扩大化,要么视为产业组织的体系化,故而发展出或是无政府主义或是国家主义的历史后果。 相比于上述两种路径,涂尔干的视角有着很大不同。他先是从民情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和政治构成的逻辑,并通过追溯传统社会的历史来厘清其组织化的形态,由此确立现代社会个体道德和伦理构成的社会基础。同时,他也通过细致追察契约的历史结构,全面批判了契约论视野下的现代国家观。涂尔干指出,民主制政治的形成,既不是个体意志权利让渡的结果,也不是纯粹国家权威的体现,而是经由法团这样的职业群体作为政治的基本单位并由此形成的中介作用,将国家政治最终落实在了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相结合的基础上。 今天,在中国远未完成的现代变迁过程之中来反观涂尔干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富有教益的。正因为经历了连续革命的历史和现实,涂尔干意识到,仅仅依靠政治的一般原理来构建抽象的国家意识,必会无视社会最基本的民情,损毁传统的价值,吞噬一切现实的合理成分。同样,仅仅依靠观念化的社会意识来抵抗国家政治,则会让人们淹没在意见的海洋中,反而使政治秩序和公民道德迅速解体。因而,大革命后的社会重建,绝不是一种“去政治化”的社会重建,而是要通过在现实中重新寻找并恢复传统的生命,全面确立据以保护个体权利、培育职业伦理和维护社会团结的中间组织群体,并以此作为代表性主体来构建国家的政治体制,从而避免个体和国家两种层面上的抽象性。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作为一切人所属的初级群体,其得以确立的基础并非仅仅是其自身的利益以及在实施公共服务中所享有的权力,它必须依据更为普遍的人类理想而为公民提供最值得依恋的情感和最值得履行的义务。总之,只有植根于民情及其传统中的国家理由,才具有其神圣的基础,才是公民权利和道德的最可靠的保证。 ①实际上,涂尔干1890-1891学年开设的是一门叫作“权利和民情的生理学”课程,中间停了5年,直到1896年才首次以“民情和权利的普通物理学”(Physique générale des moeurs et du droit)为题来讲授(Lukes,1972:617-618)。涂尔干离开波尔多后,又分别于1904年和1912年在索邦大学讲授过此课,在他临终前几年还讲过这些内容(参见Fournier,2007:528-529)。 ②见第一章对于原始部落、希腊和罗马、犹太教以及早期基督教教义的讨论(参见涂尔干,2000)。 ③对此问题的详尽考察,可参见莫斯对于总体呈现体系(système des prestations totales)的研究(莫斯,2005:120-124)。 ④参见米勒对涂尔干关于人类的爱国主义(human patrie)与大同论(cosmopolitanism)之关系的讨论(Miller,1996:245-246)。 ⑤在涂尔干的理论中,政治学说中的“代表”和宗教学说中的“表现”(或“表象”)为représentation这一个概念,这恰恰说明了政治领域的代议制就像宗教活动中的表现过程一样,是一种神圣存在的表达和社会情感的呈现(参见Durkheim,1965)。 ⑥参见魏文一对法国大革命后抽象个人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并行出现之现象的分析(魏文一,2010;亦参见Llobera,1994:145-157)。 ⑦参见涂尔干在《德意志高于一切》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病态意志活动的分析(涂尔干,2013)。标签:涂尔干论文; 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学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