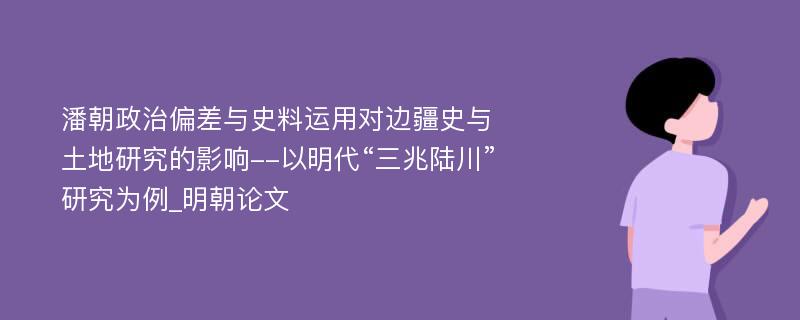
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影响——以明代“三征麓川”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政论文,边疆论文,为例论文,史料论文,偏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明朝解决西南边疆危机的重大战事“三征麓川”的得失利弊的争论,如以事件发生的正统年间①到仍有相关文章不断发表的今天来计算,②已经延续了六百余年。六百年来当事者奏疏、诏令和满朝文武的廷议以及后来明清史家的评述、当代学者的研究,可谓连篇累牍。然而,至今人们对麓川问题的了解仍置身庐山;对明朝解决麓川问题的是非曲直,众说纷纭。这让笔者困惑,是什么导致了该问题认识上的差异而使研究难以走出泥沼呢?为此笔者试图将六百年来相关争议做一番梳理,希望找出问题的症结。
一、正统“三征麓川”决策始末
明朝西南边疆的麓川问题起于洪武年间。元末明初,在元代云南行省的范围内发展起三大割据势力:滇中、滇东被元宗室梁王控制,滇西为大理段氏盘踞,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成为麓川的势力范围。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平定云南不久,即面临着麓川势力扩张侵扰和西南边疆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洪武十八年(1385)明朝发动了“景东之役”,击退内侵的麓川军队。尔后为防范麓川,明朝连续三年向云南增兵,总计达17万,通过重兵集结、屯种听征、坚壁固垒、设驿置堡等措施,③将麓川势力遏制于其老巢麓川、平缅一带(今云南省陇川县、瑞丽市),暂时缓解了边疆危机。永乐、宣德年间相对平静。到英宗正统初年,麓川势力经过多年的蛰伏和养精蓄锐,再次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正统元年(1436)十一月,麓川思任发“称兵扰边”,侵扰云南的孟定府(今云南省耿马县、沧源县)、大侯州(今云南省云县)地区,“掠杀人民,焚毁甸寨”。④正统二年(1437),思任发侵夺南甸(今云南省梁河县)罗卜思庄等278村寨。⑤正统三年(1438)六月,麓川在云南西部“侵占地方,虐掳百姓,抢象马,害官吏,掠官船”,“势愈猖獗”,⑥边地土司不堪麓川侵扰和胁迫,纷纷投靠麓川势力,“助其凶暴,亲率蛮寇来侵金齿(今云南省保山市)”,⑦西南边境全线岌岌可危。麓川势力侵扰愈演愈烈,扩张企图昭然,引起了明朝统治集团的严重关切。明朝虽然“遣署都指挥佥事李友发、大理等卫所马步官军守备金齿”边防重地,但仍难阻麓川“侵夺城池”,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晟上奏朝廷“乞调大军剿之”。⑧从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是否用兵征讨麓川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最初表现为云南方面的边事危机奏报不绝于道,兵部方略频出,英宗敕令累下。据《明实录》正统三年(1438)六月至正统五年(1440)十二月间的记载统计,云南边将和地方官员所上关于麓川侵扰的奏报、兵部与云南边将的对策商议以及英宗关于麓川问题的敕令等的记录达45次之多。⑨如正统三年七月庚子兵部奏:“麓川宣慰思任发先遣陶孟刀派本以金银器皿象马来贡,又遣其部万余夺占潞将等处地方,杀死官军,其实假以进贡为由,阳为顺服,意在延缓我师。” ⑩正统三年十一月壬寅英宗敕曰:“览卿奏送麓川宣慰司绎书,益知反寇思任发诘诈多端,可不怀服。即今清凉之时,卿等共顺兵进讨。仍量调附近土官,各领精兵,协力剿除,以靖边境。”(11)正统四年(1439)二月,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晟奉敕“累遣指挥车琳等往潞江招抚”。(12)二月辛未,沐晟又奏“贼势益众,乞增调官军,以殄此寇”,英宗令下廷议,朝臣英国公张辅认为“必用兵剿灭”,以彻底解决西南边疆的危机。(13)正统五年七月丁未,云南总兵官都督同知沐昂奏:“麓川贼思任发纠百夷数万众屯孟罗,杀掳人民,抢掠象马,据者章硬寨,与官军抗衡。”(14)可以看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边疆与中央有45次之多的奏报与诏令互动,这是一个细致的了解与筹谋过程,明朝上下逐步清楚了麓川的扩张威胁和西南边疆的严峻形势。边疆危机的升级也使明朝对麓川的政策不断发生变化,初为对麓川招抚,(15)进而“抚捕思任发”,(16)再到正统三年六月乙亥敕令“都督方政、佥事张荣同征南将军黔国公沐晟、右都督沐昂,讨麓川叛蛮思任发”,(17)反映了在麓川威胁加剧的情况下,明朝政策从“招抚”到“抚捕”再到“讨叛”的演进,即从和平解决到武力“讨剿”的重大转变。然而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奏效,导致正统三年云南官军大规模“讨剿”麓川的军事行动以都督“(方)政中伏死,官军败绩”,(18)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晟因军事失利而暴病身亡的惨痛失败。(19)麓川更加嚣张,边疆日益加剧。
此时明朝对麓川可谓“抚”、“剿”皆失,束手无策。麓川仍在大规模“称兵扰边,侵孟定府及湾甸等州,杀掠人民”;“思任发连年累侵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任发兵愈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孟琏长官司诸处皆降之”;“时任发遣贼将刀令道等十二人,率众三万余,象八十只,抵大侯州,欲夺景东、威远”;“任发乃遣众万余夺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云龙”,“麓川、木邦争界”。(20)仅以上述史料提到的麓川势力侵犯地区作今地对照:孟定府包有今云南省耿马县、沧源县;湾甸州为今云南省镇康县和施甸县部分地区;南甸宣抚司即今云南省梁河县;干崖宣抚司即今云南省盈江县;腾冲州为今云南省腾冲县;潞江长官司在今云南省保山市西南;金齿指明代中期云南西部的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地理范围包括今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永平县、昌宁县等地区;景东府即今云南省景东县;大侯州即今云南省云县;孟琏长官司包有今云南省孟连县、西盟县、澜沧县等地区;威远州为今云南省景谷县;云龙州为今云南省云龙县;潞江指今怒江及其流域地区。麓川势力曾南侵车里宣慰司,达到今云南省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的北界。麓川的中心区域即明代正统年间“麓川平缅宣慰司”,在今云南省陇川县和瑞丽市等地区。由此可见正统年间麓川势力不仅占据了明代云南布政使司所辖而今已属境外的大部分地区,内侵之地北起今云龙,南及车里(今西双版纳),东至景东,也就是说今天云南省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饱受其侵扰之害。加之麓川对“木邦、车里、八百、缅甸等处觇视窥觎”,(21)在麓川势力扩张和胁迫下,西南边地土司纷纷投靠之,明朝面临着西南边疆完全失控的局面。
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明朝内部力主以武力讨伐麓川之声高涨。(22)正统五年十一月丁卯,云南镇抚官员首先向朝廷提出调大军征伐的建议,“沐昂等言麓川地方险远,夷情诘诈,必欲攻取,非十二万人不可”,英宗下兵部等覆议。(23)为此,明朝在正统六年(1441)正月甲寅至戊午连续五天集中廷议,为解决麓川威胁进行决策。对这次关键性的廷议,《明实录》做了以下记载。
第一天,“正统六年正月甲寅,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言:‘唐虞之时,有苗勿率,帝舜命禹徂征,苗民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舞于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然……今麓川叛寇思任发逞凶造祸,反道败德,朝臣合辞请兵征讨。臣窃以为麓川之在南陲,一弹丸之地而已,疆里不过数百,人民不满万余,以大军临之,固往不克。然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王骥等会同公侯伯、都督、尚书、侍郎、御史等官,太师英国公张辅等议:‘文渊所言与今日事势,似有不同……思任发自父祖以来荷国厚恩,授职宣慰,殆今六十余年,乃敢纠集丑类,屡抗王师。虽蒙贷罪恩,彼却怙终稔恶,释此不诛,诚恐木邦、车里、八百、缅甸等处觇视窥觎,不惟示弱外帮,抑且贻患边境。’”(24)由此看来,第一天廷议争论激烈,结果以兵部尚书大理寺卿王骥为首,包括“公侯伯、都督、尚书、侍郎、御史等官,太师英国公张辅”等大部分官员一致认为麓川所侵扰地区决非何文渊所说的“一弹丸之地而已”,麓川的侵扰已经“贻患边境”,导致西南边疆失控,危害国家安全,所以“廷臣多主用兵”,(25)决定大军“刻期并进,直捣贼巢,擒其魁酋,献俘阙下,诛其党首,枭其藁街,以震天威,以靖边境”。(26)
第二天,正统六年正月乙卯,英宗开始派兵命将,“各以制敕授之”。(27)
第三天,正统正月丙辰,“行在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王骥奏陈征剿麓川事宜”,提出了具体的军需粮饷的筹集方案。(28)
第四天,正统六年正月戊午,廷议集中讨论军队调配和战略部署,征讨方略基本制定。(29)
第五天,刘球上《谏伐麓川疏》,廷议再掀波澜。刘球认为当用“周伐崇不克即退,修德教以待其降”之策,麓川残寇“僻居南徼,灭之不为武,释之不为怯,特降玺书原其罪恶,使得自新,是即周汉修教赐书之意也,奈何边将不能宣达圣意,复议大举,欲屯十二万兵于云南,以急其降,不降则攻之,而不虑王师不可轻出,夷行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是该兵法所忌也”。英宗刊章下兵部覆议,兵部朝臣同奏“麓川之征已有成命,难允所言”,当立即“整搠训练,毋致怠忽,失误事机。上从之”。(30)至此,明朝内部对麓川征与不征之议暂告一段落,“正统六年二月甲戌,以征麓川叛寇思任发,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31)大军征讨麓川的军事行动正式展开。
笔者依据《明实录》不厌其烦地罗列征讨麓川之前的西南边疆形势和相关争议,是想还原明朝征讨麓川决策的全过程,梳理这场争议的是非曲直。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指出:
其一,明朝面临麓川称兵扰边、扩张分裂之势昭然、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从中央到西南边疆、从皇帝到朝廷众臣乃至边疆将领通过总结洪武到正统年间长达半个世纪处理麓川问题经验,汲取对麓川“抚”、“剿”无功的惨痛教训,经过旷日持久的筹谋与严肃讨论,形成了共识,做出了武力征讨麓川的明智决策。整个决策过程包括正统元年(1436)至六年(1441)长达五年的云南边疆抚臣与明朝中央之间四十余次关于麓川的筹谋,也包括正统六年正月的五天激烈廷议。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宦官王振的干预。《明史·刑法志》说:“正统初,三杨当国,犹恪守祖法。”“是时,太皇太后贤,方委政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惮之未敢逞。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荣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论死不出,溥老病,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振遂跋扈不可制。”(32)说明王振预政是在正统七年(1442)以后。因此,正统六年正月明朝制定举大军征讨麓川的方略充分体现了明朝上下护国捍边的决心,其决策的严肃性是不容置疑的。
其二,这场争议的主战派由三方面人物构成:一是长期镇守云南边疆的云南总兵官沐晟、沐昂等边将,他们深切地感受到麓川势力“势愈猖獗”,对云南侵扰日益加剧和西南边疆危机加深。在与麓川势力的长期较量中,云南边将逐渐意识到麓川势力日益强大,云南自身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剿灭之,故“沐昂等言麓川地方险远,夷情诘诈,必欲攻取,非十二万人不可”,(33)首倡举全国之力征讨麓川。二是负责全国边防军事的兵部官员,他们了解西南边疆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具有全局的意识,认为麓川势力不除,将“贻患边境”、“示弱外邦”,后患无穷,因而“廷臣多主用兵”,力挺大军征讨,“以靖边境”。(34)三是英宗本人,英宗面对北有瓦剌威逼,南有麓川侵扰,边疆形势异常严峻的局面,而且多年来对麓川势力“招抚”无效,“剿捕”无功,不得不痛下决心大军征讨。因此,征讨麓川决策中,主战派既有身处云南边疆前线的边将重臣,又有以兵部尚书王骥为代表的“公侯伯、都督、尚书、侍郎、御史等官,太师英国公张辅等”众多朝臣,还有深为边疆严峻形势忧虑的英宗本人。他们在征讨麓川问题上达成共识,并非因为政治集团利益驱使,而是对西南边疆局势的深刻了解,对国家安危负责任。
其三,反对征伐麓川的著名人物是刑部右侍郎何文渊、行在翰林院侍读刘球等人,均是身居朝廷内院的文臣,既不直接负责边防军务,又不了解边防全局和麓川问题的要害。何文渊的生平,据《明史·何乔新传》记载:“(何乔新)父文渊,永乐十六年进士。授御史,历按山东、四川……宣德五年用顾佐荐,赐敕知温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赐玺书。以胡濙荐,擢刑部右侍郎,督两淮盐课。”可见何文渊主要任职于内地,是一个从未到过西南边疆,也不曾管理边防军务的文臣,然而在“朝议征麓川”时,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征讨麓川,说什么“麓川徼外弹丸地,不足烦大兵”,(35)可见其对西南边疆毫无了解和迂腐。另一位极力反对征讨麓川的大臣刘球,“字廷振,安福人。永乐十九年进士。家居读书十年,从学者甚众。授礼部主事。胡濙荐侍经筵,与修《宣宗实录》,改翰林侍讲”。(36)刘球居官经历表明他对西南边疆的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和边防形势也毫无认知。因此,何文渊、刘球等文臣所上谏阻征讨麓川的奏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开篇均举唐虞远古圣贤为楷模,动辄主张崇古效祖,(37)通篇透露着对西南边疆缺乏认识,充斥着对云南边疆民族的无知与偏见,竟把遭受麓川侵犯的占云南布政司管辖疆域三分之一强的广大地域轻率地说成“弹丸之地”,“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38)这种缺乏国家疆域主权意识,仅从狭隘的朝廷中心观出发,无视国家利益和轻视边疆的空洞朝议,自然不会被深为边疆忧虑的英宗采纳。
综上所述,正统六年以前明朝内部关于麓川问题的争议和“三征麓川”的决策,并非宦官与朝臣之间的政治斗争,也非好大喜功之议,而是形势所迫。主战与反战的分歧,源于对西南边境形势认识的差异及国家疆域主权观的分歧。主战者为肩负护国捍边重任的边将、朝臣和英宗皇帝,出于对国家安危负责,从边防全局考虑而决策;反战者则深居庙堂,难窥全局之貌,缺乏边疆与朝廷利益攸关的意识。因此说到底,在武力征讨麓川问题上主战与反战之争是明朝内部在边疆与国家利益关系上的认识差异而引发的,是维护边疆、反对分裂,还是放任麓川侵扰、放弃边疆对国家的藩篱护卫作用等的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绝不是所谓的朝政之争。
二、明清以来麓川问题研讨中的泛朝政化倾向
征讨麓川决策后,争论并没有结束,随后演变为不明就里的文人对明中叶以后腐败政治的追究;明末以后,特别是清代的史家更是忽略事件过程的探究,疏离对引发战争的边疆形势的考察,仅就朝政进行评述。
正统八年(1443)六月,刘球“应诏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包括整肃朝政、理顺职官、严肃法律、问民疾苦、戒劳民力、减免赋税等九条建议,仅第八条是就麓川用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大军征伐麓川“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也”,但没有具体的边疆形势分析。(39)刘球所陈十事虽然涉及反对麓川用兵,但主要内容是对当时朝政纲纪弛坏提出了严厉指责,因而触怒了英宗,得罪了王振,故《明史·刑法志二》记载:“侍讲刘球条上十事,中言:‘天降灾谴,多感于刑罚之不中。宜一任法司,视其徇私不当者而加以罪。虽有触忤,如汉犯跸盗环之事,犹当听张释之之执奏而从之。’帝不能用。而球即以是疏触振怒,死于狱。”(40)足见刘球之死的原因主要是揭露了明朝纲纪败坏,并非“谏伐麓川”而获罪。刘球上疏后不久即被下狱而死,后来史家仅以时间的相关性,武断地认为刘球因反对征讨麓川和得罪当权宦官而获罪。从此,麓川问题的评论参杂了政治斗争的色彩,人们越来越以朝廷政治斗争的眼光来看待麓川问题,把明朝宦官专权与麓川问题混杂在一起讨论,淡化了对麓川问题实质和边疆形势的探究。
更有甚者,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王骥第三次征麓川战事刚结束,时任会川卫(在今四川省会理县)学训的詹英向朝廷上《陈言征麓川状略》,(41)参劾王骥和总兵官宫聚等征麓川时“不体朝廷之心,苟安贪利,行李二三百杆,用夫五六百人,声势喧烘,沿途劳扰”;“大军一十五万,俱从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难为士卒”;“盖因主将无谋,致有此患,损中国生灵”,(42)等等。詹英虽措词激烈地批评征讨麓川的明朝官军军纪败坏,但并没有明确指斥明朝武力征讨麓川的决策。詹英其人,《明史》无传,生平难考。据乾隆《贵州通志》记载詹英从来没有参加过征讨麓川的军事行动,他对“三征麓川”的了解完全来自其好友王训的述说。王训,字继善,生于永乐年间,祖籍昌黎,明初迁徙贵阳。王训长期在贵州任儒学教授,三征麓川时曾从军征讨,其后写就《程番客夜》等五首反映征麓川战事的感时诗。王训与詹英交情笃深,詹英去世后,王训曾为其写墓志铭。(43)由此可见,詹英对麓川之役明军腐败、扰攘地方、贪利谋私、指挥失当等的控诉和揭露并非亲身体验,而是来自王训一人的一面之词,可以断言詹英对麓川问题和边疆形势是缺乏了解的。詹英上疏后,“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问。而命英从骥军自效。英知往且获罪,匿不去”。(44)詹英没有亲自参加征讨麓川的战役,故其奏疏有文谏扬名之嫌。于是英宗命詹英到王骥军中效力,亲身体验军伍生涯。詹英心虚,从此匿去,不复见。
无论詹英《陈言征麓川状略》中反映的明朝三征麓川的问题是否真实,但是他上疏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然而,可悲的是从明朝中叶至今,大凡讨论和研究“三征麓川”问题的政治家和学者必引詹英奏疏,却无人深究詹英上疏的目的和所反映史实的真实性。大多数学者都把詹英奏疏作为“三征麓川”亲历者的第一手史料来引用,认为詹英观时政、察边情并有参加征麓川的亲身体验,甚至以此作为评判明朝征讨麓川决策失误的重要依据,也成为后世史家批评明朝政治的证据。詹英的奏疏就这样被以讹传讹,反复征引,影响越来越大。
明朝后期,关于“三征麓川”的讨论还在继续,但已由当事人的争论转变史学家的评论。争论的核心已非边疆问题,而是朝政的功过是非。嘉靖年间郑晓在《今言》中承袭詹英观点,严词斥责“麓川之役,大费财力,骚动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复虚耗”。(45)嘉靖年间田汝成说“麓川之役,举朝皆以为非,谓王振专权呈忿”。(46)浙江会稽人诸葛元声,万历九年(1581)到云南临元道贺幼殊处做幕僚,居滇35年,撰著《滇史》14卷,完全把明朝护国捍边的征讨麓川战争看作宦官专权与权臣弄权的朝政事端,说正统征麓川乃“太监王振方宠幸用事,欲示威远夷,乃与兵部尚书王骥谋”,其所撰《滇史》仅片面地收录刘球《谏伐麓川疏》,进而认为“三征麓川”的决策失误“以致土木之祸”。(47)天启年间刘文征所撰《滇志》卷1《大事考》略记征麓川事后,按曰“权阉王振专权,遣都御史王骥统东南兵十五万征麓川思任发”,“玩其语意,似归咎于权珰”,(48)并在该书《艺文志》中全文转载詹英《陈言征麓川状略》。(49)从此,云南地方志乘连加转引。高岱《麓川之役》更直接记载为:“王振方幸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请大发兵讨之。”(50)
可以看到,从明代后期开始关于“三征麓川”问题的所有讨论都以何文渊、刘球和詹英奏疏为依据,不再引述正统年间数十次边疆抚臣的奏疏和君臣之间面对严峻边疆局势商议、畴谋的原始记载,已将麓川问题完全演变成对明代宦官专权黑暗政治的声讨。
明末,一些有不同于上述论点的评论则不被人们重视。明万历时史学家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3《史乘考误四》对英宗复辟后曾任内阁大学士的李贤所撰《天顺日录》诋毁征麓川之事进行纠谬,说:“文达(李贤字)又云:‘麓川不如中国一大县。纵得其地,于人何利益,而军需所费万万不可计,兵连祸结,以有今日。’此又大谬也。”进而认为若“败于麓川而竟不诛”,“则中国之西南者亦非我有矣”。(51)这是明清时期史家站在国家整体高度,对正统征麓川对明朝全局安危的重要意义的肯定。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的《麓川之役》得出了与王世贞相同的看法,认为放任麓川肆意妄为,将导致中国西南边疆“忧患长老,甚者屠掠郡国,吞并诸部,再复数年,蒟酱不见于番禺,邛杖不来于大夏”。(52)王世贞、谷应泰对麓川问题的论述是具有国家疆域主权意识和全局观念的评论,高远深刻,可惜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清代对麓川问题的探讨又回到朝政体系的轨道上,出现严重的偏差。张廷玉等撰《明史》对麓川问题记载失误和歪曲达到了顶点,影响很坏。首先,在《明史·云南土司二·麓川传》的第一句话“麓川、平缅,元时皆属缅甸”,(53)极端错误地记述了麓川地区的主权属性,把自汉代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部分的麓川地区(其中心在今云南瑞丽、陇川一带)轻率地看作缅甸的一部分,不仅毫无事实依据,而且严重误导了人们对麓川问题和西南边疆的认识。(54)其二,《明史》认为正统三征麓川是“中官王振方用事,喜功名”(55)的贸然动议,并在相关重要人物的传记中强化这一观点,如“(刘)球言麓川事,振固已衔之”,“时麓川酋思任发子思机发遁孟养,(陈鉴)屡上书求宥罪通贡。不许,复大举远征,兵连不解,云、贵军民疲敝。苗乘机煽动,闽、浙间盗贼大起。举朝皆知其不可,惩刘球祸,无敢谏者”;(56)“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陈得失,语刺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57)“大兴师征麓川,帑藏耗费,士马物故者数万。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势益盛,大作威福”,(58)等等。总之,《明史》编撰者认为征麓川有三失:一失在于宦官弄权,决策失当。二失在于大肆兴兵,“帑藏耗费”,将官贪暴,扰攘地方。三失在于征麓川而弛西北之防,招致土木之祸。《明史》代表了晚明至清代史家的主流观点。由于《明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被封建史家奉为正统,因此《明史》的错误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更没有人通过严肃的边疆形势研讨和地理考证对其纠谬,“三征麓川”的研究就这样被严重误导了。《明史》的一系列错误反映了清朝史家带有浓重的朝政中心论特征,反映了明清史家缺乏应有的边疆观和疆域主权意识,对西南边疆认识上的模糊含混和错误,更为“三征麓川”研究的泛朝政化推波助澜,“三征麓川”几乎成了明代宦官专权的典型反面教材。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清史家是如何反复征引刘球、詹英奏疏,将麓川侵扰引发的边疆问题刻意曲解为一场宦官与朝臣斗争,他们囿于朝廷政治斗争,用朝廷为中心的视角,以朝政为出发点,对西南边疆历史上的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带有偏见的歪曲和诠释;部分明清史家甚至不顾历史的真实和国家利益,刻意选择或篡改史料来支撑自己观点,以朝廷政治替代了对边疆形势实质探讨,逐渐疏离麓川问题的实质,无视麓川问题缘由的原始记载,用政治情感代替理性的史实分析和史料选择,这一边疆问题的研究完全被异化了。这就是明清至今在“三征麓川”研究中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的根本原因。
三、资料运用的偏差与历史真实的回归
当代学者对明代麓川问题的研究虽然有较大进展,但是观点差异较大。在对正统“三征麓川”具体事件的评价上,缺乏对西南边疆民族问题复杂性认识的部分学者仍然受明清史家观点的左右,其对资料的选取运用上出现严重偏差。
如,《论“麓川之役”》一文就基本依据何文渊、刘球和詹英三人反对三征麓川奏疏和明清史家的主流观点写成,论文中全文收录了何文渊和刘球反对征讨麓川的奏疏全文,赞同郑晓《今言》“麓川之役,大费财力”说法,斥责王世贞从国家安危的角度分析麓川形势的看法。该文片面运用史料否定了明朝征讨麓川,认为“明朝征剿麓川有三错:其始用剿不用抚,决策之错;其继也,大举兴师不纳乞降,战术之错;其终也,谕木邦、缅甸参与征剿。许裂地以酬,战略之错”。而且由于英宗“刚愎好胜”,主张用兵麓川,导致“专权干政的司礼太监王振,为固位邀宠,力赞其议”。(59)
《试论明英宗时期的三征麓川之役》一文对明朝三征麓川也持否定态度,强调西南边疆的麓川侵扰对明朝是小患,西北边防为大虞,征麓川是没有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考察其文所运用的史料,也主要是何文渊、刘球、詹英等反战派史料,没有深入发掘真正反映明代西南边疆局势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论文不约而同地将宦官专权、英宗刚愎、朝政败坏作为否定麓川之役的依据,认为“三征麓川之役是王振打着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号,其实是为巩固权势,示威边境少数民族而发动的一场战争”。(60)这种不对史料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和辨析,而以明清史家的片面议论代替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显然受到封建史家泛朝政化议论的影响,不过是对明清史家在麓川问题研讨上朝政中心论的现代版诠释。
当代云南一批从事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对明代麓川问题的缘起在边疆视角下进行了新探讨,为回归历史的真实做出了重要的努力。著名民族史学家方国瑜1936年至1946年期间连续十年从事云南傣族历史的原始资料搜集、整体和研究,重要的成果有《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61)和《〈麓川思氏谱牒〉笺证》,(62)连同江应樑的《百夷传校注》(63)共同构成了元明时期麓川内部社会状况、历史发展及元明两朝对麓川经略的基础资料。方国瑜发现了《麓川思氏谱牒》并对此谱牒进行了缜密严谨的考证,指出这是麓川思氏1256至1404年间崛起、兴盛与衰败历史的原始资料。《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是将散见于《元史》等十几种文献史籍的相关资料一一收集汇编、考辨梳理,以元代为重点,推及元代以前,将傣族源流及历史发展状况的资料条分缕析,编年疏证系统清晰,是迄今为止汇集考证元代云南傣族的最完整资料,其中大量涉及麓川傣族部落所属的大傣区域部落分布、部落名称、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该编年史料虽非专论麓川,但涉及麓川在元代的崛起、发展及其与元朝、缅国的关系。江应樑的《百夷传校注》可视为对明初西南边疆史料一次系统整理。正是在资料整理过程中,方国瑜全面考述了元代至明初麓川崛起的历程、特性和内部结构,得出麓川是元代后期在云南行省范围内从大傣族部落区兴起的带有割据政权特征和扩展性质势力的客观认识。(64)
在研究方面,西南边疆史著名学者尤中《明朝“三征麓川”叙论》、(65)刘亚朝《试评麓川的兴衰》(66)和百川《明代麓川之役述评》(67)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从元末开始直到明正统年间的近一百年时间里,傣族首领思氏势力在这里发展起来,据有以麓川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形成与明王朝对抗的地方性政权,明朝从洪武年间至正统年间解决麓川问题的努力和征战,是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的统一战争。当代云南学者对麓川问题研究的这些新见解和新突破,说到底是元代至明初关于傣族社会历史、边疆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资料在发掘整理方面有了突破,以发现新的重要资料为突破口,摒弃封建史家的朝政中心观,用边疆视角重新审视历史,部分揭示了麓川问题缘起的复杂性和边疆地缘政治的特殊性。
通过对“三征麓川”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从正统年间的何文渊、刘球反对征讨麓川的奏疏到明清正统史家对麓川问题的评述存在着严重的认识扭曲,而部分当代学者的研究则受明清史学家泛朝政化的干扰,出现了考察视角错误和史料运用偏差,导致这一边疆问题的研究多以朝廷政治斗争代替边疆形势的分析。明清史家常常将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所谓清正朝官引经据典、崇古颂祖的空泛议论作为这一边疆问题的原始史料加以运用,形成了泛朝政化的评价特征,导致边疆问题研究流为无视边疆实际而以一时朝廷是非为基准的主观评判。当代某些边疆史研究者既疏于边疆问题原始史料的发掘,无视大量当时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和实录的真实记载,不对相关论述的史料真实性进行考辨,特别是对传统史学家经常犯的泛朝政化倾向缺乏基本的警惕,误将某些明清史家居于某种政治需要而进行的高谈阔论或道听途说当成真知灼见和第一手史料,不自觉地对明清史学家盲目追随,终使边疆历史混沌不清,真假难辨。
当然,边疆问题和边疆史地的资料零散而有限,常常混杂于历代王朝的实录、各级官吏的奏疏文档和正史类文献中。传统史家在编辑史书的过程中,对边疆问题的记述已经受到他们固有的王朝中心观影响而有失公允,因此我们今天在研究边疆问题的时候,应当对这些受王朝中心观影响的资料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进行严肃细致的辨析。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边疆的视角和国家疆域意识,充分认识边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跳出王朝中心观的窠臼,注重边疆地理环境、地缘政治、民族关系的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整体性客观研究,才能使边疆复杂问题的研究逐渐回归历史的真实。
同时,我们还需要对边疆民族问题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对涉及边疆地区的史料进行新的发掘,对已为人们熟知的资料进行全面地收集、认真地整理、客观地解读,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研究更为客观和接近历史的真实。如对发生在六百年前西南边疆的麓川问题的研究,就应当对实录等第一手文献中保存的麓川问题当事者数以百计的奏疏、论辩和战争历史记载等资料进行客观收集整理,而不是随意采用明清史家的评论作为史料,更不应该不加辨析地将那些狭隘的朝政泛论作为原始资料运用。
注释:
①《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5记载,正统六年正月甲寅、乙卯、丙辰、戊午连续五天举行了关于麓川问题廷议,可看作这场争议的高潮。本文所引《明实录》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下同。
②较近的研究论文有毕奥南:《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③参见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版,第13—25页。
④《明英宗正统实录》卷24,正统元年十一月甲辰。
⑤参见《明英宗正统实录》卷35,正统二年十月辛未。
⑥《明英宗正统实录》卷43,正统二年六月己未。
⑦⑧《明英宗正统实录》卷43,正统三年六月乙亥。
⑨由于相关史料太多,不便一一引述,此列史料出处,仅供参考。《明英宗正统实录》卷43,正统三年六月己未、六月乙丑、六月乙亥、六月庚辰;卷44,正统三年七月庚子、七月丁未,正统三年八月乙丑;卷46,正统三年丙戌、九月戊子、九月癸卯;卷48,正统三年十一月壬寅;卷51,正统四年二月癸亥、二月辛未、闰二月壬午、闰二月壬辰;卷53,正统四年三月戊午、三月丁卯、三月己巳、三月壬申;卷54,正统四年四月辛卯、四月戊戌、四月丙午;卷55,正统四年五月庚戌;卷56,正统四年六月癸未;卷57,正统四年七月壬戌;卷59,正统四年九月丙午;卷61,正统四年十一月辛亥;卷64,正统五年二月己丑;卷65,正统五年二月丁巳;卷67,正统五年五月癸丑、五月丙辰、五月戊戌、五月己巳;卷68,正统五年六月壬申、六月庚子;卷69,正统五年七月丙午、七月丁未、七月己酉;卷71,正统五年九月壬寅;卷72,正统五年十月癸未、十月丙戌、十月辛卯;卷73,正统五年十一月己丑、十一月丁未;卷74,正统五年十二月己巳,等等。
⑩《明英宗正统实录》卷43,正统三年七月庚子。
(11)《明英宗正统实录》卷48,正统三年十一月壬寅。
(12)《明英宗正统实录》卷51,正统四年二月。
(13)《明英宗正统实录》卷51,正统四年二月辛未。
(14)《明英宗正统实录》卷69,正统五年七月丁未。
(15)《明英宗正统实录》卷51,正统四年二月条载,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晟奉敕“累遣指挥车琳等往潞江招抚,贼沿江拒守”。
(16)《明英宗正统实录》卷43,正统三年六月乙丑。
(17)《明史》卷10《英宗纪》。
(18)《明史》卷126《沐英列传附子晟列传》。
(19)参见《明英宗正统实录》卷53,正统四年三月丁卯。
(20)均见《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二·麓川列传》。
(21)《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甲寅。
(22)参见《明英宗正统实录》卷53,正统四年三月己巳。
(23)《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3,正统五年十一月丁卯。
(24)(26)《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甲寅。
(25)《明史》卷183《何乔新传》。
(27)《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乙卯。
(28)《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丙辰。
(29)参见《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戊午。
(30)《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戊午。
(31)《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6,正统六年二月甲戌。
(32)《明史》卷304《宦官一·王振传》。
(33)《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3,正统五年十一月丁卯。
(34)(35)《明史》卷183《何乔新传》。
(36)《明史》卷162《刘球传》。
(37)参见《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戊午。
(38)《明英宗正统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甲寅。
(39)《明史》卷162《刘球传》。
(40)《明史》卷94《刑法志二》。
(41)全文在天启《滇志》卷22《艺文志·疏类》,古永继校注本,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2)(明)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天启《滇志》卷22《艺文志·疏类》,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3)参见《贵州通志》卷28《乡贤》,乾隆六年木刻本。
(44)《明史》卷171《王骥传》。
(45)(明)郑晓著、李致中点校:《今言》卷4,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4页。
(46)(明)田汝成:《行边纪闻》,嘉靖三十六年刊本,北京图书馆影印《善本丛书》。
(47)(明)诸葛元声撰、刘亚朝点校:《滇史》卷11,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314页。
(48)(明)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天启《滇志》卷1《大事考》。
(49)(明)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天启《滇志》卷22《艺文志》
(50)(明)高岱撰:《鸿猷录》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389册。
(51)(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23《史乘考误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
(52)(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30《麓川之役》,中华书局1977年版。
(53)《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二·麓川传》。
(54)参见拙文:《元代的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
(55)《明史》卷171《王骥传》。
(56)《明史》卷162《刘球传》、《陈鉴传》。
(57)《明史》卷304《王振传》。
(58)《明史》卷148《杨士奇传》。
(59)赵毅:《论“麓川之役”》,《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
(60)刘祥学:《试论明英宗时期的三征麓川之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61)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方国瑜文集》第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44页。
(62)《麓川思氏谱牒》为傣文写本,原名Meng-Mao Tse-nan Si Pitsa,意即孟卯者澜思家官谱,为孟定土府收藏。方国瑜1935至1936年间在云南滇西考察时得此写本,后由孟定土司罕中兴族叔罕定国携此本在孟琏募乃厂为方国瑜口译讲解。方国瑜遂于1953年作笺证,内部刻印流行。《民族学报》1981年第1期转载,今收入《方国瑜文集》第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2—558页。
(63)(明)钱古训撰、江应樑校注:《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4)参见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方国瑜文集》第三集;江应樑:《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国家》、《部落时代的傣族史》,《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65)尤中:《明朝“三征麓川”叙论》,《思想战线》1986年第2期。
(66)刘亚朝:《试评麓川的兴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67)百川:《明代麓川之役述评》,《思想战线》1986年第2期。
标签:明朝论文; 明史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边疆论文; 历史论文; 云南发展论文; 明实录论文; 明清论文; 刘球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宋史论文; 元史论文; 专门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