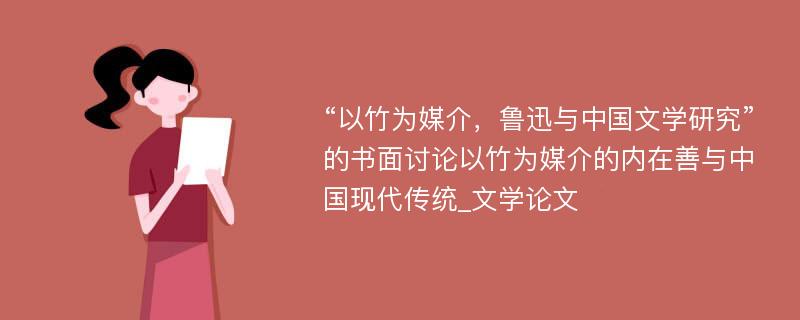
“作为媒介的竹内好与鲁迅及中国文学研究”笔谈——1.作为媒介的竹内好与中国现代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鲁迅论文,笔谈论文,中国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6-0016-11
竹内好(1910-1977)是日本现代思想家和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日本有“竹内鲁迅”之称。随着他的文集《近代的超克》于2005年3月出版,国内学界悄然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竹内好热”。据日本一桥大学坂井洋史教授在该年5月的一次中国学术会议上观察,“很多年轻的研究者在没有任何必然性的情况下也动不动提到竹内的名字”。[1]这看上去很像近20多年来我国引入各种西方思潮时的那种情形,自然也不排除同样的“接受”结构掺杂在其中的可能;但一个明显的不同是,《近代的超克》的出版,并不是竹内好第一次出现在汉语语境,早在1985年,他的《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便已经被译成中文发表,翌年,竹内的重要著作《鲁迅》也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竹内好著作在那时的出版显然被中国学界忽略了。那么,事隔20年后,同样一个外国学者和思想家为什么会在汉语语境里遭遇如此不同的命运,尤其是考虑到1985年这一特殊的年份。
回想起来,正是从被文艺界称为“方法年”的1985年开始,各种西方文学和哲学思潮被频频地引入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理论热点。这些热点或热潮,反过来又参与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文学观念乃至其他各种观念。推动这些热点或热潮的,就历史观而言,是一种告别昨天、走向明天的热情——其中的明天,自然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现代化的明天,并有发达国家现成地在那里做出了榜样。就文学界内部而言,则表现为急于告别传统的文学意识形态,创造出一种能够跻身于世界文学大家庭的纯粹的文学。表现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鲁迅研究的,则是在“祛左翼化”的框架中重新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秩序和以“启蒙”话语的绝对优势重新确立鲁迅的价值——而这一系列重新确立的背景则是:一、原本被压抑的对象,即一切非左翼文学,则逐渐演变成新的压抑性力量;二、在一部分学者那里,作为“启蒙者”而得以重新确立价值的(前期)鲁迅,在另一部分学者那里又作为“左翼文学家”(后期鲁迅)而被等而下之。新的现代观是以颠倒了的同一法则即新的二元对立法则构成的,它在20世纪80年代发挥出巨大的解放能量之际,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使自身僵化的伏笔。所以,当意想不到的新的历史条件出现时,作为这种新的“现代观”的对立物,又出现了在一定范围内再颠倒回去的明显的或潜在的趋势。
因而,竹内好的学术思想作为亚洲知识而不是西方知识,其在20世纪80年代新的“现代观”蓬勃兴起之际被视而不见,而在本世纪初各种观念冲突的复杂历史情境中又被重新发现,也就不是一件奇怪而费解的事了。换言之,也就是当下既存在着把竹内思想作为一种西方权威知识加以膜拜的那种历史惯性,也存在着以竹内好为媒介,并借助亚洲视野反思我们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观、文学观以及在诸观念影响下的当代学术状况的契机。
在日本,竹内好有时候被认为是一个近代主义者,有时候又被认为是一个反近代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相互矛盾的概括说明他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被贴标签的人物。在他所描述的“欧洲一步步地前进,东洋则一步步地后退”[2](P181-224)的近代世界史图景中,东亚(东洋)理应在“抵抗”(即保存“自我”)中更新“自我”,但遗憾的是,他在日本的“近代”中竟没有发现这样的代表人物,反而在被视为“落后”的中国发现了鲁迅。因此,他称日本的“近代”为“转向”型的(“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而中国的“近代”为“回心”型的(“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3](P3-164)并对日本“无抵抗”的近代文化展开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尽管在一个时代结束后,竹内的同道也批评他对于两国“近代”的概括多半是基于“憧憬”,而不是真实历史,[4](P1-21)但这种“转向/回心”说在原理上仍然是有效的,也即在被卷入“现代”的后发展国家里,不存在一条仅仅通过外部学习就能抵达“欧洲”的直通道。“现代”的标志不是对应“欧洲”所具有的各项外在指标,而是通过“保存”自我而又“否定”自我的“挣扎/抵抗”,在自己内部形成一种新的主体性。这就吊销了进化的线性“现代观”,将一个时间坐标上的“现代”,转换成一个内部空间上的“现代”。
“主体性”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并不陌生。那场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因为遭遇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而带上某种悲剧色彩。但80年代所言的“主体性”,是要确立与“整体”相对的“个体”价值,和竹内好从鲁迅那里发现的带有自我否定契机的主体性并不是一码事。因而,这种以强调“个性”、“个人”为指归的主体性,在完成反拨一个泯灭个人价值之时代的任务后,便渐渐消融于随后所兴起的市场意识形态,从而使被张扬的“个人”成为一种丧失了“主体性”的个人。被竹内好所发现的具有自我否定契机的鲁迅的主体性,似乎很难以这样一种样态进入中国研究者的视野,更没有被80年代以来知识者的主导思想所吸收。“立人”命题虽然在“新时期”刚开始时便被提出,并在当时起到了“反封建”和承续五四“个性解放”的应有作用,但这个命题本应发展起来的更丰富的内涵,却始终停留在它被提出时的那种历史限定中,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一些优秀的知识者当作鲁迅思想贫乏、鲁迅时代可以结束的根据。而鲁迅研究也因为那种平面的现代观,而被置于两种看似对立的情形中:鲁迅价值的肯定者通过把鲁迅放置在“启蒙”框架中,以期从左翼中“抢救”出鲁迅;而鲁迅价值的贬低者,则继续把鲁迅放在“左翼文化”框架里,并通过“胡适还是鲁迅”的二项选择模式而把鲁迅等而下之。在这种历史情境下,“竹内鲁迅”之于我们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个日本思想家始终以中国的鲁迅为思想元点这么一种楷模性的启示,而是借助竹内的鲁迅论,把握被我们以往所忽略的鲁迅之根本,并通过鲁迅而重建中国现代传统。
那么,这个被我们所忽略的鲁迅之根本是什么呢?竹内好并没有用逻辑性语言去界定它,而是用诸如“文学者”、“回心之轴”、“孕育……的根源”、“原初的混沌”、“根本的自觉”、“以死相抵的唯一的东西”这类隐喻性词语加以指认。这种流动的界定自然会招致“拒绝同样拥有追究‘本源’倾向以外的人的理解”[5]的批评,但这却并非仅仅是竹内好的癖好,而多半是由研究对象本身带来的,即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原本就存在着某种难以言传的东西,它不是中国古代就已经有的,也不是近代欧洲现成地放在那里可以加以对应的,而是某种在东方的现代之一刻重新生成的。对此,竹内好最常用的指称词是“文学者”,但这个“文学者”中的“文学”,却不是一般意义上可与“音乐”、“美术”或“哲学”、“史学”平行的某种艺术门类或学科门类,而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一种在本质上是“无”的东西,一种“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3](P142)鲁迅固然也是“启蒙者”、“左翼文艺家”或中国语境中的“革命者”等等,但这些身份由于依赖于某个特定时刻的现实,因而都是第二位的。于是,处于第一位的“文学者”,便帮助我们标出了这个独特的东方现代者的信仰的位置:不是任何确定的宗教信仰,也不是历史目的论,甚至不是认同绝望的虚无主义,而是把绝望和希望、虚无与实有同时引入自身的那种悖论性状态。竹内曾用鲁迅爱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同”来加以指认,并指出被“鲁迅在精神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3](P8)
这种在信仰位置上被标出的鲁迅形象,使我们无法再固执于自己的鲁迅观,也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在面对鲁迅思想遗产时,为什么在最需要重建主体性之际,我们却仅仅抓住了“反封建”、“启蒙”这些并非鲁迅精神的根本之物,而错过了鲁迅的主体意识这一更为深邃的内容?由于错失这一更为深邃的内容,在同一个平面上,又导致人们以基督教神学来批评鲁迅虽然堕入了绝望的深渊却未能顺势走向“上帝”,导致人们把自己有过的挫折性经验错置在鲁迅身上而抱怨鲁迅“向左转”,导致人们基于自身幻觉的对鲁迅的各色批评。饶有意味的对比是,正是在鲁迅以“中间物”或“相对者”意识对“自我”加以限定的地方,当代言说者那未加清理的“自我”却悄然膨胀起来。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是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20世纪80年代重建当代文学观念时曾特别加以处理的问题,而在竹内的鲁迅论中,这个问题也被特别地谈及。《鲁迅》一书写于1943年,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本国内实行着严厉的法西斯高压政策,文学也被笼罩在意识形态的铁幕之中,被迫成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只有“文学主义”成为曲折对抗意识形态高压性的唯一出口。竹内的“文学/政治”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学主义”的影响,尽管如此,竹内好仍然拒绝倡导文学与政治“脱离”论。他在鲁迅那里看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奇特关系:“鲁迅的文学,就其体现的内容来讲,显然是很政治化的……然而,其政治性却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3](P19)那么,文学和政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竹内好的正面回答至少包含这么几个层面:一、“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不是相克关系……(而)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二、“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三、“文学是无力的”。“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才成为文学”。四、但文学并非不是行动,和政治一样,“文学是行动,不是观念。但这种行动,是通过对行动的异化才能成立的行动。文学不在行动之外,而在行动之中”。“没有行动,便没有文学的产生”。五、“产生文学的是政治”,“文学诞生的根元(源)之场,应常被政治所包围”,“然而,文学却从政治中择选出了自己”。[3](P134-135)
竹内好就以这种类似绕口令的方式论述了文学和政治的悖论关系。但破除绕口令的外壳,我们看到的便是一种被重新界定了的文学和政治,以及完全被刷新了的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所有这一切,并非出自论述者的某种抽象理念,而是来自“现代—东方”的具体时空中。竹内好说:“这是为使文学能开花的苛烈的自然条件。虽长不出娇艳的花朵,却能使劲秀之花获得长久的生命。我在现代中国文学那里,在鲁迅身上看到了它。”而相比之下,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确立当代文学观念之际,却正好处于40年前竹内好就批评过的格局之中。我们把在极左政治中形成的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天然地看作文学一旦与政治相关就必然产生的关系,因而决绝地让文学与政治告别,以“纯文学”或抽象的“文学自律”论为核心来构筑新的文学观念。这在当时虽然起到了瓦解传统文学意识形态的策略性的功效,但却战略性地将之作为文学应有的永恒样态,以致使其在完成了有限的时代任务后,便逐渐消融于新时代以交换为法则的市场意识形态之中,至少,它不再具有生机勃勃的批判和生长功能。需要反思的恰恰在于,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性使我们拒绝把文学定义在(非凝固的)政治之中,同时也拒绝把政治定义在(凝固的)政治之外?竹内好40年前在鲁迅那里发现的“文学与政治”的有机关系,为什么在40年后仍然拒绝进入我们的视野?
在“现代—东方”的具体时空中,对于一些挫折性历史,竹内好倾向于将此看作“现代性”在东方的曲折展开,这与我们倾向于看作是一种不应发生的历史错误,又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对于二战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的超克”命题,竹内好并没有仅仅以法西斯意识形态而加以简单否定,而是甘冒“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以火中取栗的方式,在缠绕不清的历史麻团中区分哪些是“作为事实的思想”,哪些是尚未成为意识形态的思想要素,哪些又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竹内好做得是否成功我们先不作探究,但这种方法却启示我们,面对后来被推向极端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究竟是采取一种整体肯定或否定的方式,还是采取“分层”的方法,区分作为“价值”的左翼和作为“社会运动”的左翼,区分通向荒谬历史结果的逻辑和至今仍然活着的逻辑,区分所有需要我们加以区分的内容。这,恐怕仍然是对我们“知性”和“心性”的考验。
竹内好一生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业,但始终秉有超出自身专业之外的社会关怀心;他以中国的鲁迅为自己思想的元点,致力于日本国民主体性的构建。他之于我们的价值,显然不仅仅在于某种学术的交流和思想的移植,而是借助他这样一种媒介,重返乃至重建我们的现代传统,以确立我们脚下的位置,并把握我们的“现代”时刻。
收稿日期:2005-0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