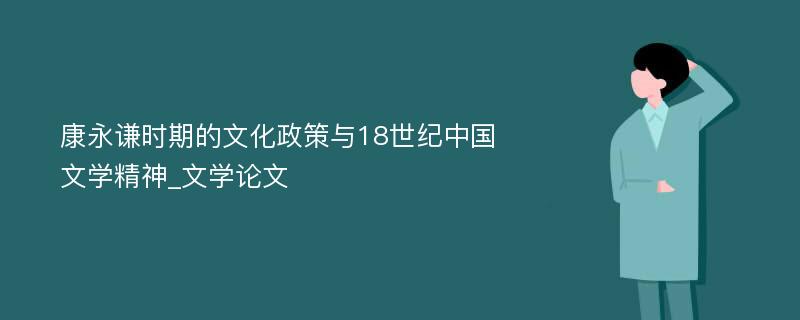
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与18世纪中国的文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时期论文,精神论文,政策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07)04—0118—06
每个作家都有鲜明的个性,但一定范围内的作家和作品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通之处,我们谈论18世纪中国的文学精神,就是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中国18世纪大体是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到嘉庆五年(1800年),包括康熙朝二十二年、雍正朝十三年、乾隆朝六十年和嘉庆朝五年。这一时期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上获得了大发展,文化事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康雍乾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对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一些文化政策和举措对文学发展演变的直接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一、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文人的现实境遇
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后不久,清王朝开始了大规模平定边疆的战争。这些征战绝大多数发生在遥远、偏僻的边疆地带,而中原地区除了几次小规模的动乱,则是和平安定。这就使得统治者们有余裕的时间和精力来着手巩固和调整政权。康熙帝执政伊始即着手清除威胁皇权的因素[1]。随着八旗制的调整,南书房的设置,军机处的成立,亲王对朝廷要事的发言权一步步被削弱,宦官、外戚只能在政权的边缘观望。这一时期统治政策的起伏变化,与统治者个人性格的不同有一定的关系。如雍正帝在谕旨中对党派作了严厉的谴责,朝廷中的帮派受到严酷的惩罚。而乾隆帝则一方面利用帮派牵制平衡朝廷内的各股力量,另一方面又对任何一方力量的消长小心警戒,在适当的时候实施铲除。作为在野士人议政核心场所的书院被明令禁止,在后来的官设书院中,士人只能讲解经书,温习八股课业,言政被视为非法,普通百姓叩阍更受惩罚[2]。皇帝的权威在士人的心目中得到确认,一些有名的学者、诗人以跪献诗书、受皇帝一顾为莫大的荣耀,而这在明代和清初是为士林所不齿的。
满族的统治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得以确立,要归功于他们的满汉政策。满族统治者对儒教的尊重让汉族士人看到了一线光明。除了博学鸿词科的开设外,清廷给士人提供了多种接近朝廷的机会。晚明残余力量被消灭后,康熙帝努力弥和满汉间的民族鸿沟,如划一满汉官员的等级,废除“各省督抚尽用满人”的不成文规定[3]。但直至乾隆末年,满汉问题仍被一次次地提出,这说明满族对汉族士人的戒备和歧视一直存在。
虽然科举制度很早就受到了文人的怀疑和批判,但清代科举却让汉族士人爱恨交加。清初的统治者一方面指责八股文的空疏无用,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承续了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他们很清楚科举对稳定社会、收拢汉族士人之心的重要作用。与明代和清初相比,18世纪中国的士子队伍更加庞大。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朝廷取消了对童试名额的限制,让无数士子满怀希望埋头苦读,而有限的乡试、会试录取名额又使绝大多数士子徘徊于科场大门之外,成为社会上的浮游一群。再加上种种捐纳,除去满族人占据的职位,汉族士人即使中举,真正进入仕途的机会也是了了[4]。因此,这一时期的文人小说一方面充满了对科举的企羡,另一方面又对八股科举的弊端作了最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满族统治者对付汉族士人的强硬手段就是文字狱。18世纪中国几次大的文字狱,其残酷程度令几百年后的文人仍心有余悸[5]。许多现代学者认为《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中对朝政的嘲讽批判的含蓄隐晦,民族感情表现的婉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文字狱的影响[6]。其实这一时期文字狱对汉族士人的影响被有的学者夸大了。到康熙晚期,晚明遗民相继故去,在满族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汉族士人已经开始将精力投向考举,以期在新的王朝中建功立业,因此对故明的怀念为科举不第的牢骚所代替,而这种牢骚正是满族统治者所希望看到的。
康乾时期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国库的金银和粮食储备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这是统治者一次次蠲免百姓赋税、不断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7]。18世纪中国的财政收入仍然主要来自土地,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耕地迅速增加,康熙帝、乾隆帝对培育、推广良种的热心在封建帝王中是极为少见的[8]。由于解除了工籍,手工业者可以自由地从事手工业活动;商人们从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捐献给朝廷,从而赢得更多的经营自由权。工商业的繁荣造就了一座座繁华的城市,被战乱破坏得面目全非的江南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并超过了以前的富庶,为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8世纪中国的通俗小说和传奇多以江南为背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南人文之盛。
连年征战、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以及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应付,虽然显示了国力的强盛,但也耗尽了国家的财力。特别是人口的急剧膨胀,抵消了经济的增长[9]。实际上在清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衰败的迹象已经隐隐显现,除了人口和土地的因素,朝廷的糜费所造成的高额租税,贪官污吏的盘剥,使广大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上。普通士子的生活境况与一般民众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他们可以获减一些赋税,但是土地的贫瘠,耕作技术的缺乏,使得许多士人抛弃土地,为最基本的生活而奔波。士人们生活的困窘,前途的渺茫,人生处境的浮游不定,加上才华难以施展、只能默默终老的悲凉,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文中充斥着浓重的感伤。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在士人的哀吟中迅速逝去。
二、三教合一背景下的文人精神世界
从学术文化上说,康雍乾时期是又一个黄金时代,学术集大成的气魄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经典的搜集与整理,成为朝野上下的风气。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对18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
考据学成为乾嘉学术的代称,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明代甚至宋代学术中零星的考据成分,但康熙年间阎若璩、毛奇龄等人的工作才可以称为考据学的真正开端。考据学者所致力者,多为书本上功夫,偏重于以往之陈迹而远离现实问题,只可称为“古学复兴”。但很大一部分考据学者却声称自己是有为而作,是为将来的经世致用作准备,坚信所从事之考据有益于世,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10]。实际上,至乾隆时,随着民族复兴情感的逐渐淡薄,强烈的用世热情深入士人之心。考据学剔除种种误读、歪曲,还儒家原典以其本来面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原始儒家精神的复兴。考据学者于著述中寄托用世抱负,枯寂外表下隐藏着活泼跳动的真正士人之心。
考据学的风靡程度,今天只能从现存资料中知其大概。但可以肯定的是,普通士人无意也无法进行繁杂而无直接收益的考据工作,大多数考据学者的工作是在官僚或富有的藏书家的资助下才得以开展。考据学者主讲于书院,科举试题中渗入了点滴的考据学因素,这些必然对那些积极向上的士人产生重要的影响[11]。许多士人把经学之外的诗文视为业余的消遣,这就对传统诗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考据学甚至影响到了通俗小说的写作。18世纪中国文人小说中文人英雄的才华,不再仅仅是诗文,他们精通天文、水利、医术或礼乐,处理具体的政务游刃有余,熟读兵书,深于谋略,能够随时率军出征等等。同时与考据学的兴盛相伴的游幕之风,为通俗小说提供了充足的故事素材,文人小说中文人主人公的漫游,无疑是现实中游幕之风的投影。困窘的生活,怀才不遇的悲慨,浮游不定的人生,使得文人小说家与考据学者有着相同的心灵伤痛,因而也有着相同的英雄梦幻。
相对于考据学的辉煌,理学则显得黯淡无光。虽然康熙、雍正和乾隆帝对理学大力扶持,但实际上是利用多于崇信,一方面尊之为国学,另一方面却又对理学名臣的言行表示怀疑。例如,乾隆在《御制程颐论经筵箚子》中称程朱理学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为大逆不道。而谢济世注《大学》获罪,尹嘉铨著《名臣言行录》被杀,追根究底,也是因为其中的理学精神或儒教理想主义精神引起了满族统治者的反感和恐惧。然而,尽管如此,从思想方面说,考据学仍逊色于理学。戴震是18世纪中国考据学者中惟一有系统思想的,他的关于理的客观性、普遍性的论述,性之一元论和对情欲的提倡,以及一些新的知识观念的提出等等,是通过对天理和人欲的新阐释向宋明理学提出了质疑。但是戴震的思想在18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引起反响,而理学中的一些东西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从思想上说,理学对18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超过了考据学,像李绿园、夏敬渠等都既是理学家又是通俗小说创作者。
实际上中国到18世纪已经没有纯粹的儒学了。所谓的“三教合一”到这一阶段已经完成。在18世纪中国儒学复兴的浪潮中,被强调的是济世的理想主义精神。佛教结束了它的古典时期,佛教信仰中的一些因素成为普通百姓生活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统佛教特别是其玄秘的理论趋于衰微。顺治帝和雍正帝都信仰佛教,雍正帝更自称为教主,将僧人引入宫廷谈禅,大量的佛经被译为满文,朝廷专门设置僧纲管理僧众。但是这一时期朝廷宣扬的主要是藏传佛教,而且是利用多,诚信少。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加上朝廷对佛教徒数量和僧纲权力的限制,对朝野上下的反佛行动起到了暗示作用,地方官府拆除寺庙、驱赶僧人的事件屡屡发生。这在这一时期文人小说中有所反映,如《野叟曝言》中的主人公文素臣就将灭佛作为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功业。但与此同时,居士佛教迅速兴起,不少士人信仰佛教特别是佛教的净土宗。净土宗以对所谓净土的追寻和凡人皆可成佛的理论为特征,表明了18世纪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文人所信仰的佛教,既不同于民间佛教,又与正统佛教有所区别,他们更多的是吸取佛教中的出世因素,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这一点与儒教的“处”有相通之处。因此,《儒林外史》在结尾处由对儒家理想的关注转为向佛教皈依的愿望就显得非常自然,在《红楼梦》中,现实被称为“色”,与本质上的“空”相对,贾宝玉最后身入空门,作为对纷扰尘世的解脱。
对于道教,清代统治者采取的是容忍态度。统治者一方面斥之虚伪,另一方面其对长生的信仰,对快乐的肯定,以及对儒教、佛教的开放式的吸收融合,又使得道教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道教的神仙谱系不仅为民间信仰提供了偶像,而且为叙事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捉鬼、降妖、法术、修仙等,是神魔小说、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及其他通俗故事的重要情节要素,甚至是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重要的情节点缀。例如,《绿野仙踪》对成仙修道的道路作了形象化的描述,赈灾、平叛、锄奸惩恶等尘世的功业被当作成仙得道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慧根、吐气和炼丹,这体现了近世道教世俗化的特征,也表达了文人对道教的独特理解。
据说当有的大臣对雍正帝佞佛表示怀疑时,雍正帝解释说,佛教与儒教一样,都讲求修身之道,都可以用来劝世。理学是儒学吸收佛教的思辨因素后的发展。道教取纳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等因素及其仪式,更有意识、成系统地吸收儒教的世俗因素。佛教则一方面从道教的诸神谱系中借鉴了等级观念,另一方面又通过世俗化努力向以儒教为思想支柱的国家政权接近。到18世纪中国这三种宗教所共有的一些因素已经很难分辨出真正的本原,民间宗教更是将这三者直接混杂在一起。出儒入佛或出儒入道在18世纪中国的文人小说中有很鲜明的体现。例如,《野叟曝言》中文素臣以儒家正士自居,以排灭佛教为己任,却有着道教所自诩的奇异;《红楼梦》中僧与道成双出入神话和世俗世界;《绿野仙踪》中冷于冰身为儒士而出家求道。
三、18世纪中国文学的个性表现和文学精神
“达我心曲”是18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就绘画和书法来说,个性的张扬到了极致。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江南文人画,无论是题材的选择,画面的构思,图形的安排,还是色彩的运用,都无视传统的规范,在随意的一涂一抹中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个人的主体人格受到尊重,高雅的趣味和道德价值的寄托常常被忽略,有的画家甚至将自己化为画中的人或物。这种倾向也渗透于18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正如清代学术是对前代学术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18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亦在短短一百年内重演了近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
清代诗歌创作从数量上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12]。明清之交的遗民诗被当作清诗的开端,曾经主宰明代诗坛近一个世纪的拟古诗风在清初受到批判,但向前人学习仍然被肯定。直至17世纪末,诗坛上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在唐诗和宋诗之间寻找平衡以达到表情达意目的的问题,一部分诗人仍学习唐诗,另一部分诗人则经历了由学唐到学宋的转变。如朱彝尊的诗歌由唐入宋,王士祯独尊初唐,晚年却渐入宋诗。向古典学习是当时诗人步入诗歌之门、立足诗坛的基本途径。18世纪是清诗的真正开端。所谓清诗是指摆脱明代复古诗风影响,有着时代气息的诗歌。如格调派的领军人物沈德潜将诗人之诗与学者之诗融合在一起,而肌理派的代表翁方纲则将考订训诂之事与辞章之事合而为一。格调派和肌理派受到后起之秀袁枚的批评。袁枚标榜性灵,他的诗歌创作摆脱依傍,独抒性灵,被有的研究者视为真正的清诗。袁枚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风气变动的信息,而适时地将明代公安派性灵说大力张扬[13]。性灵说在当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抒写性灵成为一代诗风的主流。与此同时,格调派和肌理派迅速地走向衰落,沈德潜之后几乎再也无人写作雍容雅正的格调诗。18世纪的三个诗歌流派很好地说明了文学创作和身份、地位的关系。沈德潜是朝廷侍臣,翁方纲是朝中官员和金石学者,而袁枚则是下层官吏并早早地离职家居。
归纳起来,18世纪中国的诗歌创作有几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创作的繁荣。诗人人数以及每个诗人创作的诗歌数量众多,虽然很大一部分诗歌遗失了,现存诗歌数量仍然惊人。一方面,科举考试中增加试帖诗,必然使越来越多对科举抱有希望的士人练习写作诗歌[14]。另一方面,诗歌在18世纪已经成为中国文人记事抒情的得心应手的媒介,诗人甚至可以用诗歌谈论学问,表达其社会人生见解。因此,诗人们的诗歌题材十分丰富。二是对自我表现的强调。向古典学习的目的是寻找能充分表现自己情感的形式,哪怕是最保守的诗人都很坚定地承认这一点,融化古典以突出表现自我的程度成为评价诗人创作水平的最重要的尺度[15]。被称为诗余的词的创作表现了相似的倾向,对创作个性的追求,主体性的张扬,对性情和本色的强调,在18世纪中国的词论中非常突出。以醇雅为最高规范的浙派词人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以适应自我表现的需要[16]。18世纪的中国诗人更多地着力于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感受,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称为盛世衰音的诗歌[17]。这些诗歌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或描写普通士人的贫困,表达寒士的无奈与悲凉。实际上这两者常常交融在一起,因为沦落不遇的士人常一方面考虑生计,另一方面还惦念着济苍生的儒家理想,伟大理想与残酷现实和卑微人生的矛盾,使士人们慷慨悲歌,徘徊中夜。在生活面前,归隐田园、寄情山水、吟风弄月、消磨心志是几乎不可能的,道教、佛教的世俗化、功利化也使文人最后的心灵憩园失去了超尘脱俗性[18]。还有一部分士人,步入仕途后不久就无奈地退隐。所谓的盛世衰音,不仅仅是指对个人身世的感叹,更主要是对文人末路深沉的感慨。
18世纪中国的古文理论也体现了古文家集大成的雄心,从对文章源流的探讨,文与道、文与器关系的辨析,到具体写作技巧的分析,都有精深的见解。在被称为桐城派开创者的方苞看来,文章体现了一种辩证法,不欲以文章名,才能写出流传千古的好文章。其中的关键在于他所说的“义法”中的“义”,“义”被称为文章的灵魂甚至文章存在的惟一价值。他所说的“义”,虽也指“事”即客观现实,但主要是指理学的“理”[19]。而在经学家那里,“道”被视为气化流行的世界万物的规律,理义则指客观事物的条理,脱离“道”而深究理义如同流为艺的文章一样[20]。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将文章之道归纳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要素,显然受了经学文章家的影响,经学家有“理义”、“制数”、“文章”的说法。这种对“道”、“义”、“义理”的强调,显现了他们向古典靠拢、以文经世的意图。在这两家的文论中,作为艺的文章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个性因素也并非被完全摈弃。在方苞那里,德、志、才、学等主观的精神品质被认为是组成“义蕴”的重要因素[21],方苞的后继者不断修正他的理论,情感、个性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到了阳湖派,道统、文统和义法一起被搁置,文章的丰富多样性得到承认,心、神、气、知等个性因素被称为为文之本,文章被视为发难显之情的工具[22]。
虽然文论家们如此强调道与义,但实际上技法才是他们最讲究的,因为“法”才是具体实在。方苞将“法”概括为“言有序”,虽然“法以义存”、“法随义迁”,但对材料详略虚实的处理直接关系到义理的表现,因此“法”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方苞的后继者将“法”概括为神、气、音节、字句等为文之“能事”[23]。阳湖派的恽敬将遣词、用字等称为文法的“小处”,将结构、布局的艺术性称为文法的“大处”[24],归纳起来,古文家所说的文法,包括精和粗两个方面,精指那些玄妙的形而上的不可言说的东西,要靠长期的修养、反复的体味才能达到;粗则指具体的技法,从细处的音节、炼字造句,到大处的材料繁简详略虚实的处理、篇章结构的安排、伏笔与照应等等。在时文中,这些被古文家视为粗的文法得到了强调,由于士子队伍的庞大,时文选本的风行,像起、承、转、合等文章结构概念十分深入人心。
在18世纪,中国传统诗文的抒情言志因素被引入通俗小说,大批文人以前所未有的严肃和热情参与通俗小说创作,通过小说世界的虚拟来抒写自己的抱负、感慨,将通俗小说的创作视为传世不朽的事业,将通俗小说与儒家的三不朽联系到一起。与抒情言志小说相关的是通俗小说传播方式的新变化。有些作者原本无意于将自己的通俗小说刊刻行世,如《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生前坚决反对刊刻自己的小说[25],《水石缘》作者李春荣在书成之后秘之行笥,不想付梓[26]。不急于刊刻行世,不是由于不够重视,恰恰是由于将小说创作当作个人的事业,当作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著述[27]。文人小说家们认为自己在小说中表现的情志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只能藏之名山以待来世。与16、17世纪的通俗小说相比,18世纪文人小说突出了自我表现因素,更多地把抒写个人感受作为主要目的,无论是才学的显现、往事的追忆,还是对理想人生的憧憬,个性因素都很突出。比如《儒林外史》、《红楼梦》就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抒情小说。几乎每一部文人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主角的文人,他们在小说世界中的悲欢离合、得失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小说作者心灵的投影。文人小说家大多与诗人有着相似的境遇,他们利用小说的虚拟性将人生的无奈和壮志难酬的感慨转化为小说世界中的英雄伟业,在虚拟的语境中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反观自身的结果,文人小说家又不得不满怀忧伤地让他们的英雄黯然退场。虽然不能将18世纪中国文人小说中的感伤因素过分夸大,但与此前相比,其感伤色彩仍然很明显。文人小说家将人生的感伤、对命运的感喟和对现实世界的绝望,通过小说情节的安排、直接抒情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使得通俗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品格,从而与传统诗文取得了精神上的一致,使通俗小说走向独立、走向成熟,更使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达到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也就在18世纪,中国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在17世纪繁荣一时的通俗故事和话本小说走向衰落。文人将热情更多地投入白话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因为显示才学、表现自我等只有在中长篇小说营造的虚拟小说世界中才能真正做到。18世纪中国成书的几部话本小说集,如《五色石》、《八洞天》、《娱目醒心编》等,仍孜孜于道德劝戒,生机和活力已经趋于枯竭。至于文言小说,17世纪的《聊斋志异》虽然为18世纪中国的文言小说提供了典范,但也成为新突破的障碍,多数文言小说是学习或模仿《聊斋志异》,只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略开生面,有的研究者就将18世纪中国的文言小说归为“聊斋”和“阅微”两派[28]。但文言小说创作在18世纪也有发展,有意为文的色彩大大加重,如《谐铎》对篇目对称的刻意安排、篇章结构的整齐划一及其所表现的思想情感,都体现出鲜明的文人化倾向。从叙事艺术方面说,文言小说特别是其中的传奇小说有许多值得文人小说家借鉴的地方,比如第三人称的客观叙事,对视角的统一控制,主观化、诗意化的景物描写,都是文人小说的长篇巨作很难做到的。但18世纪中国最成功的几部小说在某些片段中较成功地采用了这些叙事手段,这些片段也是这些小说中的精彩部分。
在18世纪,中国戏剧的文人化进一步加强。剧本的案头化至清代中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8世纪中国戏剧的故事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特别是短篇杂剧成为作家表达人生感受的载体。传奇的书面化色彩更为浓重,剧本离实际演出更加遥远,剧本创作成为一种书斋化的创作。剧作家努力向正统文学靠拢以提高戏剧的地位。一是加强道德训诫。二是把传奇与史传联系在一起,羽翼正史被当作对传奇的最高评价,剧作的本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三是以文为曲,传奇作家和评论家将古文律法作为传奇创作的基本法则,“案头文章”常常被用来赞扬传奇剧作,优伶俳语、市人之谈受到鄙视,雅正的风格、浓艳典丽而显豁明畅的语言被大力提倡。这些文人化的传奇剧作被研究者称为文人传奇[29]。文人小说和文人传奇在题材上相互影响,但两者结构艺术上的相通也不容忽视[30]。文人小说的片段组合式结构与传奇分合自如的组合式布局十分相似。文人小说常常在由主人公游历形成的主线上挂上相关的人物和故事,这成为丰富小说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有许多小说中穿插的故事明显游离于主线之外,却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传奇剧作家对人物语言个性化的强调必然影响到文人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儒林外史》对人物动作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就颇似于戏剧中言简意赅的科介。
18世纪中国文学创作所发生的变化,是文学观念新变的体现。在康雍乾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上,这种变化突出了18世纪文学的整体精神特征,即文人中心主义。18世纪是文人的时代,同时也是如吴敬梓所说的文人走向末路的时代,没有一个时代的文人对自身有如此明确的体认。
收稿日期:2006—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