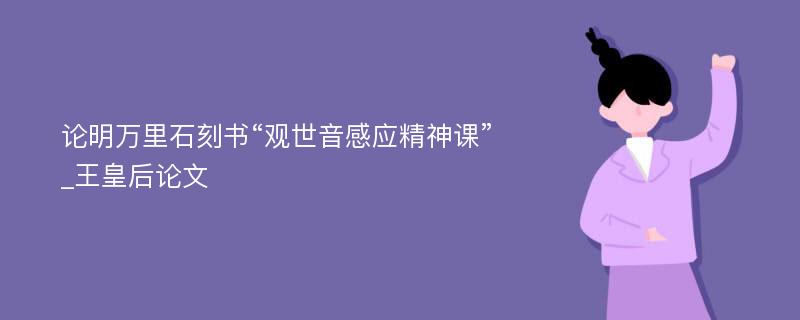
述石印明万历刻本《观世音感应灵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刻本论文,观世音论文,感应论文,明万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藏书家》第8辑载王涛《长安残书见精神》一文,谈到作者收藏的两张灵签残片,王涛先生自己认为是明初或者比这更早的刻本。文中附有这两张残页的照片。看到后使我想起多年前买到的一部同类读物的石印复制本。捡出敝藏相互比勘后发现,王涛先生的灵签残片,与寒斋所藏石印本灵签的底本,应属同一版本。在此谨借用《中国典籍与文化》一块版面,叙述有关版刻事项及相关历史问题,与王涛先生交流。
我得到的这部石印本灵签,是由民国时的大藏书家徐乃昌印行于世的。其法式是以五枚卜钱占卜。卜钱正面分别铸有金、木、水、火、土字样,统称“字”,背面则空白无文,统称“幕”,卜时或字或幕,字者又有金、木、水、火、土之别,相互排列组合,共得三十二种样式,每种样式各为一种卦象。此石印本灵签书前较原刻本增印有“印光法师法语”,说明占卜方法云:“欲决疑者,若原供有菩萨像,则于像前焚香礼拜;若无,则即向此课本焚香礼拜。取五净钱,在香炉上熏过,心中默祷所问之事,按下所列之偈,并念菩萨若干声,将钱掷于桌上,按次查是几字几幕,照刻本查是何卦,即得其所示之兆。”据此则似乎也允许使用普通商用制钱,只不过按照它掷出后的排列次序一一对应为金、木、水、火、土即可。
卦签中每一种卦的版面构成形式完全一致:首为一帧象征卦义的图,次序号,次卦名,次卦象,次等第,次五言四句偈语并西江月一阕,释卦义,相当于“象辞”。如第一卦,卦名“升进卦”,卦象为金、木、水、火、土五钱皆字,等第属“上上”,其“象辞”释曰:
彩凤临丹阙,灵龟降吉祥。
祸除福禄至,喜气自洋洋。
此卦求财大吉,正宜出入欢娱。官词口舌并消除,病人起离床席。
求官目下成就,行人早晚还归。祸除灾散福盈余,最喜高明富贵。
如此三十二卦有版画三十二幅,加上卷首、卷尾各另有观音、韦陀像一帧,全书共有版画三十四幅。画面线条镌刻流畅,不工不拙,适得其宜,以雕版技艺而言,自是上乘佳作。除此之外,在“象辞”的上方或末尾,还点缀刻有类似今日书报刊题花、尾花之类的装饰小图画,这至迟是明代以来佛经刻本中常见的装饰,据云均为佛家法器或者圣物。
前面提到的“印光法师”,是民国时上海、苏州一带的著名净土宗僧人,这个石印本在书前还缀加有印光法师所撰《观音感应灵课石印流通序》一篇,交待印行缘起,系“因徐积馀居士与其夫人,得前明古本,石印千卷,以结净缘”。“积馀”为徐乃昌字,是民国时居住在上海的大藏书家,其夫人马氏,名韵芬,乃昌有藏书印,并刻夫妇姓名,这些都是喜好藏书的人熟知的事情。但是徐乃昌夫妇在这部灵签末尾题记中的署名,恐怕没有多少人见过:
佛弟子徐长庆同妻马契圆,喜舍净财,发心印造《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一千卷。以斯功德,上愿四恩总报,三障顿消。扬教诲之波澜,遍周沙界;作人天之眼目,广度含灵者。岁次元黓涒滩观世音菩萨成道日谨识。
这长庆、契圆,估计是徐乃昌夫妇在家修行的法名。“元黓涒滩”为壬申年,即公元1932年。徐氏生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卒于1936年,印行此书时已六十多岁。人到暮年,容易找寻外在的精神寄托,取个法名,居家修行,是很自然的事情。此石印本内封面系倩沪上著名书画家海云楼主王震题写。王氏与徐乃昌行年相若,当时也已年过花甲,笃信佛法,有法名曰“觉器”。这在当时,是闲散文化人士的一种风尚。
海云楼主王震题写的内封面,与徐乃昌夫妇题记中的叙述一致,将书名题作“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原本正文卷首没有篇名,仅篇末题有“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终”字样,徐乃昌等都应当是依据它来确定书名的。但这是否为原书正名,还不能完全确定。这是因为古书卷尾所题书名,时常有用简称的情况。《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两种明抄彩绘本观音灵签,题作“南无大慈悲灵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课”,与此本三十二种灵课的情况正相契合,二者很可能为存有源流关系的同一种书籍,而书名之孰是孰非现在还不宜遽然确定。日后暇时,取以比勘,方可明晰。
王涛先生推断他获得的灵签残页为明初或比这更早的刻本,意即可能为元代刻本,这很大程度上应是受到其版刻“字体类赵孟頫体”的引导。其实明初或元浙本的所谓赵体字,一般比这要更为硬劲,只有明永乐北藏的佛经,字体与其相类。据石印本卷末原书题记,知此本刊刻于明万历年间:
大明中宫皇后,每斋沐焚香,捧诵《观音灵课》,时为社稷卜岁丰,祈太平,屡屡感应。遂命锓梓,印施百卷,以便臣民决疑,令预趋吉避凶,阐明法宝,慈泽后人。愿宫闱清吉,海宇万安,雨露均调,仁凤休作。愿我佛灵课,惟诚信以来格,佑为善以先知,苟渎慢不敬者占之,反至尤焉,尔其钦哉!
明万历壬辰春王正月十五日吉,刊于大乘禅寺,计板二十二块,竟请京都衍法寺,便流行天下也。
其刊印年代虽较王涛先生的判断要晚很多年,但是却并不因此而减损这两张残页的价值。这是因为检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见著录此书;徐乃昌当年所得全本,今下落不明,其已毁失不存,亦未可知。所以不惟王涛先生手中的残页,作为万历原版,具有无以替代的文物价值;就是敝人箧存之石印本,也因完整保存此书内容和面貌而差近于原本,值得珍重收藏。当年徐乃昌虽印行多达千册,但是这种书不受读书人的重视,一般求神问卦的人也不会特别留意护持,加之印书纸张脆软,容易破碎,护持保存直到今天的估计已经非常稀少。
这部书之所以值得珍重,是因为它除了研究占卜史和版画史的资料价值之外,还与万历年间的一大政治事件具有密切关系。
了解一点明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万历年间,围绕着“争国本”问题,宫闱内外,朝廷上下,展开过一场激烈而又持久的争执。对此,清初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列有专节详细叙述,感兴趣的人自可取来阅读。
所谓“国本”,是指册立太子。明神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万历帝朱翊钧,其皇后王氏身体多病,终生未能生育子女。另有恭妃王氏,生子常洛,为万历帝长子,后来袭位为光宗,年号泰昌,做了不到一个月的短命皇帝,便一命归西;贵妃郑氏,生子常洵,为万历帝第三子,后来封为福王,明末在开封被李白成统领的陕北农民军抓住,杀掉煮成汤喝了“福禄”酒。王恭妃虽生子在先,却不讨万历帝喜欢,而郑贵妃则深受宠幸,且与万历帝相亲相爱,终生不渝。由于宠爱郑贵妃,万历帝就想册立她生的儿子朱常洵为皇太子,可朝廷中一帮重规矩讲法度的大臣却不答应,他们认死理说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大事,含糊不得,必须长幼有序,遵依从前惯行的程序优先册立长子。于是自万历十四年二月朱常洛降生一个月时起,即大致以万历帝和郑贵妃为一方,以朝廷中很大一部分自以为护持国家根本秩序的大臣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坚韧拉锯战。万历帝想立常洵,大臣们不答应;大臣们认为应及早册立常洛,万历帝就挖空心思找出各种托辞来搪塞拖延。双方一来一往,僵持对立长达十五年之久。
在这期间,万历帝虽采用各种手段来压制上书进言的臣僚,或降或削,或杖或戍,威势不可谓不强,无奈这班人竟前仆后继,毫不退缩,《明史·后妃传》谓“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底,实在无法继续拖延下去时,万历帝才不得不屈从于臣下,于是朱常洛得以成为东宫皇储。对此,清代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不由得感慨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以帝王之尊而屈服于臣子,不能不心怀深怨大恨。按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看法,万历帝之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不补中外缺官等种种荒怠朝政的乖异举动,都是他对臣僚的报复行为。
在这场争执当中,皇后王氏表面看起来置身局外,不论立长立幼,都不关她什么事情。可是实际上却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甚至性命。王恭妃与郑贵妃虽同为妃嫔,但王氏之得幸生子仅缘于万历帝一时寻欢作乐,皇帝对她并没有多少感情,立恭妃子常洛,不会马上对王皇后的地位构成太大威胁,而且恭妃的儿子常洛一直由她带在身边养育,她对常洛“调护备至”(《明史·后妃传》),即使常洛登基,也不至于对她构成损害;而郑氏不惟深受皇帝宠爱,且已晋封“贵妃”,依明朝制度,“内廷嫔御,尊称至贵妃而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列朝贵妃姓氏”条),位距皇后,仅一步之遥,若其子常洵被立为太子,郑氏很可能随后就取代皇后的位置。
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揣测。明代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过废除皇后的先例,就是先废皇后,后立太子,也不是不能实行,而且施行起来似乎更为容易。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今上笃厚中宫”条记载说,万历二十八年即册立常洛为太子之前一年,京师盛传皇帝故意裁减皇后食用服侍,致使皇后久病濒危。若王皇后身故,郑贵妃继承后位,常洵便可依据朱元璋定下的立嫡不立长的原则,取代常洛,成为太子。万历帝闻流言大怒,内阁次辅沈一贯在劝慰他时讲到,“今日之谤,十年前已鼎沸”,说明万历帝因立储一事欲加害于王皇后的流言,早在万历十八年时,就已广为传播。纵使万历帝圣德仁厚,绝无加害之意,也说明客观上这是解决这场政治争执的一种自然选择。
万历帝是否真的要害死皇后?宫闱秘事,几百年后的今天,真相已难以确知。不过万历十八年时要废掉皇后的传言,却是事出有因。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正月和十月间,先是有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也就是明朝事实上的宰相,后又有吏部尚书朱纁率领群臣以及礼部尚书于慎行,先后几次上疏,请求马上册立东宫,确定皇长子常洛的太子身份。这几次表态,非常严重,从地位上看,出动了几乎所有最高文职长官;从规模上看,是朝廷官员的集体性示威。因此,万历皇帝不能等闲视之。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迫不得已,万历皇帝答复说,他讨厌臣僚们不停地上疏激扰,离间他和常洵父子,假如明年谁也不再拿这件事来烦扰他,他就一定会按照大家的请求,在后年亦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册立典礼。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采用了《明史》申时行、许国、王家屏、罗大纮传的说法。万历帝允诺的册立时间,其他史籍如《明史纪事本末》中另有记载是在万历十九年。申时行、许国、王家屏当时均位居内阁大学士,是最主要的当事人和最近密的知情人。《王家屏传》记述说万历帝先是允诺在万历十九年冬确立储位,王家屏担心口说无凭,万历帝随时可能变卦,于是起草诏谕请皇帝颁布,以留下公开的字据,造成既成事实。万历帝不答应,并改口说改在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册立典礼。这一变化,应当就是史籍中万历十九年和二十年两种不同记载的来由。
尽管王家屏当时没有如他所希冀的那样拿到皇帝允诺册立的诏谕,但他还是施展政治智慧,成功地把这一约定透露出去,由礼部尚书于慎行“通行南北诸司”(《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八年十月辛卯条),使之成为万历皇帝向所有臣民作出的正式保证。
早在万历十四年大臣们最初提出册立常洛为太子的时候,万历皇帝就明确表述过没有不立常洛的意思,后来又再三申明在皇后无子,诸子均为庶出的情况下,他完全认可“长幼自有定序”的皇位继承原则(《明史·王如坚传》、《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八年十月丁亥条),所以对举行册立典礼,他就应该早有考虑,可是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拖到两年以后去办呢?这实在耐人寻味。
后来万历二十一年的时候,在群臣连续不断的催促下,万历帝才亲口透露出一丝端倪。他说:“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王皇后若果然能够生育皇子,自然皆大欢喜,不过查继佐《罪惟录·皇后列传》称王氏因体弱多病而不能生育,况且纵使身体允许,生不生孩子,也由不得她自己做主,刑科给事中王如坚就直截了当地拆穿说:“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后嗣之繁难矣!”(《明史·王如坚传》)
既不指望也根本就不想让王皇后生育,那么万历皇帝打的到底是什么主意呢?请注意《罪惟录》记载说皇后王氏体质很差。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讲道:“后贤而多病。国本之论起,上坚操立嫡不立长之语。群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贵妃即可为国母。”(见卷七五《争国本》)原来万历皇帝是在等待王氏病死。王氏身体本来就相当孱弱,按照《万历野获编》记述的传言,在这时再通过撤减食用服侍等方式施加虐待,促其速死,大概万历帝估计,她怎么也拖不过一两年的寿数,这便给郑贵妃入主后宫正位预留出了必要的时间,所以才会答应在万历二十年为常洛举行册立典礼。
不过万历皇帝对待王皇后毕竟还是宅心仁厚的。他不愿向臣僚们承诺一个确定的立储时间,实际上是因为没法确定王氏的身体能够支撑多久。他清楚地知道只有王氏病故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却无意采用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加害于她。一定程度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条件的虐待容或有之,但终其一生,万历帝对王皇后始终未动杀机,这一点也应该可以肯定。不然,想让她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何不爽爽快快地定个虚假的册立典礼的日子去糊弄大臣们呢?
不过这些都是几百年后我们作为事后旁观者所作的判断,身当其事的王皇后可不敢这样乐观。自古天意高难测,生杀予夺都不过是万历帝一念之间的事情。她需要做好准备来应对最坏的局面。册立太子的时间既已公布,极度的危险也就向她直面扑来,生命的倒计时马上随之启动。可以想见,处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皇后王氏的心绪该是何等惊惶,何等恐惧?
那么,面对这一生死攸关的重大威胁,皇后王氏对待周围的环境又是怎样一种心态以及她又做了怎样的应对呢?
史籍中对于神宗王皇后其人没有留下多少记载。《明史·后妃传》只记述说她“性端谨”,也就是老实规矩,深得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的欢心,不与郑贵妃计较争宠;傅维鳞在《明书·宫闱纪》中除了“端谨”之外,则又增加了“聪颖”二字评语。作为她“聪颖”的具体表现,傅维鳞列举了两桩事情。一是暗自留心收下皇帝留中不发的奏章,以后遇到皇帝处理相关问题时,“则随取所奏上之,毫无错谬”;二是善于处理后宫内部的问题,“调剂之不使乖”。由此看来,她并不是一个完全老实巴交、遇事束手无策的女人。万历皇帝如此怜爱郑贵妃而又始终未能让她取代王氏的皇后位置,恐怕与王氏善于自处要有很大关系。只是以前我们在史籍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她如何应对废位危机的直接的记载,而这部万历刻本《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恰恰透露出一些相关的迹象。
了解到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一下子清楚地看到,王皇后出面刻成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万历壬辰春正月十五日”,正是万历帝与臣下约定的册立东宫的期限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这部书无论字迹还是插图,都镌刻得相当精致,这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所以其动工开版的日期需要向前推溯到万历十九年底。对于王皇后,这可以说是“大限”即将降临的时候。
虽然在这之前,由于工部主事张有德在万历十九年八月莽撞呈请皇帝准备翌年的典礼仪式物品,致使万历帝找到借口,降旨毁约,将“册立之事,改于二十一年举行”(《明史·王如坚传》,又《明史·申时行传》),但群臣并没有放弃先前已经争取到的目标。第二天,告假在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就密疏“请申前谕明春册立之旨”;工部尚书曾同亨也在同日“请明春册立,毋改期”。因申时行告假而在朝主持政事的次辅许国,与位居第四的内阁大学士王家屏,看到情况紧急,“虑事中变”,于次日“仓卒具疏”,“引前旨力请”“明春册立”(《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九年八月癸丑、甲寅条,《明史·许国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九月,内阁次辅许国上书引退,同时敦请皇帝,册立太子事要“仍明春如期勿改”(《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九年九月己巳条)。到年底十二月初,先前努力争取到万历皇帝建储允诺的大学士王家屏,因次辅许国、首辅申时行先后引退,三辅王锡爵省亲回家,这时已经成为内阁首辅,他又一次就此上疏,“力请践大信”,遵依前约,在“明春建储”。当时因“册立期数更,中外议论纷然”,王家屏劝慰皇帝说,只有如约册立常洛为太子,方能够“塞道路揣摩之口”,反映出人言汹汹,朝廷内外俱已进入焦点时刻(《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九年十二月甲午条,《明史·王家屏传》)。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刊印这样的灵签,其题记中所说的“以便臣民决疑,令预趋吉避凶”的刻书动机,毫无疑问,完全是讲给她自己听的,即她想通过施财刊印《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来为自己祈求神灵的佑护。
看破这一动机,我们就可以明白,皇后王氏正是利用这篇刻书题记,向神明也向世人,清楚袒露了自己的急迫心愿。揣摩题记中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有特定的指向,耐人寻味。特别是“愿宫闱清吉”一句话,直接针对她所面对的紧迫威胁。“诚信以来格,佑为善以先知”,是在为自己祈福,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能够预先佑护自己这样“为善”的人平安如意;而“苟渎慢不敬者占之,反至尤焉。尔其钦哉”这两句话,已经是破口大骂,是在赤裸裸地诅咒和警告郑贵妃,让她小心点儿:像她这种为人行事渎慢神灵的人,用观世灵签占卜,只会招来灾难!——如此生动的心态记录,能不珍视?
前文谈到,傅维鳞在《明书》中描绘王皇后是一个“聪颖”的人,很善于处理事务。粗看上述题记的内容,她刊印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除了直接为自己祈福之外,似乎只是想借机发泄一下愤恨,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王氏的家族没有显达的背景可以倚重。在这种情形下,她惟一可以借重来保护自己的力量,就是朝廷里那些一心反对郑贵妃专宠的臣僚。可是作为皇后,她深居后宫,无法直接与外界沟通联系。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她需要向外界发出一定的声音,表明自己的存在、处境和心迹,以进一步唤起官员们对她的关注和同情。祈福泄愤,都会直接招致或强化人们对她个人存废安危的关注;而她在题记中讲自己过去“为社稷卜岁丰,祈太平”,“屡屡感应”;愿今后“宫闱清吉,海宇万安,雨露均调,仁凤休作”,则是有意提醒大家,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社稷联系到一起。
王皇后选择以印施《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愿望,这种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了明朝皇后编刻书籍先例的影响。《明史·后妃传》载成祖永乐皇帝皇后徐氏,“尝采《女宪》、《女戒》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又《明史·睿宗兴献皇帝传》载世宗嘉靖皇帝的母亲章圣皇太后蒋氏,也作有《女训》,颁行天下;更近一些,有《万历野获编》卷三“母后圣制”条载万历帝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撰有《女鉴》一书。这些都应当是后宫的必读教养书籍,《明史·后妃传》就提到世宗嘉靖皇帝,令皇后张氏“日率六宫听讲章圣《女训》于宫中”。所以,万历帝的皇后王氏很容易想到要利用刻书来发表言论。
有意思的是王皇后的政敌郑贵妃,在后来步其后尘,也采用刻书这种方式,搞起了政治宣传。其事件缘起是万历十八年时山西按察使吕坤编纂了一部《闺范图说》,万历帝看到后赐给郑贵妃一部。大致在万历二十六年或稍前,郑贵妃唆使其兄郑国泰,重刻此书,增刻后妃一门,首列汉明德皇后,终以郑贵妃本人,郑贵妃且亲自出面作序,将其与先朝皇后撰著的《内训》、《女训》诸书相并比。这不管从哪一角度来看,都明显带有为郑氏篡夺后位而鼓噪张目的嫌疑。于是引发朝臣著书攻讦,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已经是与本文无关的后话,我在这里只是想通过这两件事的相互联系对比,来说明万历帝王皇后刊刻《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绝对是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宣传行为,而不会是无为而发。
王皇后刊印这部灵签是否产生过什么效用,史阙有间,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万历二十年正月壬午日,就在她印施《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六天之后,大臣们由礼部给事中李献可发端,以请求皇长子朱常洛“豫教”(即出阁请老师教授读书,这是培养皇太子所必经的途径)为名,发起了在漫漫前后十五年的“国本”争执过程中,声势最为浩大也是最为强劲的一场攻势,史称“九臣面讦政府,十四官同时降削”(《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尽管未能实现在万历二十年立储的既定目标,但万历皇帝也不能不越来越有所顾忌。
万历二十年前后各方面围绕着“争国本”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对于最终确保常洛的皇储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其中,也有王皇后的积极参与,而由她施财刊印的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则可能是她留存下来的惟一文字记录。
最后让我们回到版本学的问题上来,看看本书的刊刻地点。王皇后题记所云“大乘禅寺”,并不是具体的佛寺,只是一般泛指寺院。具体刊刻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衍法寺,位置在北京阜成门外大街路北,距阜成门约一里。寺院始建年代久远,据明杨一清正德七年撰《衍法寺碑》,系正德年间由一个名叫张雄的太监捐赀重建(见《日下旧闻考》卷九六《郊坰》)。寺院与明朝后宫的这种密切联系,可能是王皇后选择在这里刊刻灵签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据《明代版刻综录》卷三著录,在正德、隆庆至万历十四年间,衍法寺刻印过多种书籍,说明衍法寺本来就有很好的刻书基础,这应是在这里刻印《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最重要的原因。此石印万历刻本《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在版本学上另一重要的资料价值,就是丰富了北京衍法寺的刻书历史,除了可以为《明代版刻综录》增补一个版刻品种之外,还可以借此把有具体实物证据的衍法寺版刻活动,由《明代版刻综录》著录的万历十四年,下延到本书付梓的万历二十年。
标签:王皇后论文; 女训论文; 观音论文; 万历野获编论文; 历史论文; 郑贵妃论文; 国榷论文; 明史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宋史论文; 元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