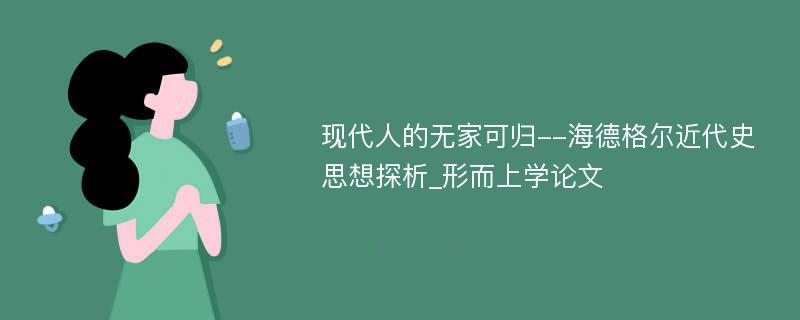
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析海德格尔对现代人类历史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无家可归论文,现代人论文,人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者、人的生存究竟由何而定的思考,是海德格尔历史之思的出发点。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认为,人具有现成的固定的本质,这个本质即是理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人有理性。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种对人的思考,是在问“人是什么”或“人是谁”,这种思路在方向上就是不正确的,因而它关于人的“本质”在于有理性的观点并未抓住人的根本。
海德格尔提出,人并没有现成的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在生存中形成的。这一关于人是一种生存着的存在者的观点,海德格尔早在1927年发表的开山性著作《存在与时间》中就已明确提出来了。他指出,人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的去存在(Zu-sein)——生存(Existenz),如果人这种存在者谈得上“是什么”的话,那么这种“是什么”也必须从他的生存来理解。“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所以,可以在这个存在者身上清理出来的各种性质都不是‘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现成‘属性’,而是对它说来总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并且仅此而已。”[①]海德格尔指出,只有人具有生存这种方式,这是人和其他存在者的根本区别。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人的“本质”的生成性、选择性,把去存在——生存作为人这种特殊存在者的根本规定。
在1946年写的《关于人本主义的信》中,海德格尔对现代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西方人类历史进行了第一次集中性的说明。他明确指出,人的身体在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机体,这种根本上的不同即在于人的“去生存”(Ek-sistenz),去生存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传统形而上学所说的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并不在于人有理性,而在于人的去生存;人的“本质”既不是由潜能规定的,也不是由现实规定的,而是由人的去生存规定的。在这里他把“生存”(Existenz)变成了“去生存”(Ek-sistenz)[②]。海德格尔在这里认为,人的这种去生存也即出窍状态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人自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存在本身”所决定的,因为人的去生存即是进入“存在本身的真”。“人是这样活动的,即,人是那个此,这就是说,人是存在的澄明。这个此的‘在’,而且只有这个此的在,才有出窍地去生存的基本性质。”[③]也就是说,人的去生存归根到底是被存在所决定的:“处于其活动中的人只是由于被存在所要求而活动,人只有从这个要求中才‘已经’发现他的活动居于何处。”[④]
问题在于什么是存在或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在1946年所写的这封信中所给予的规定是:存在是支配着人的生存、支配着一切存在者的活动过程的既澄明又遮蔽着的到来。应该明确指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这一规定与他在1935年写的《形而上学导论》(1953年出版)中对存在的涵义的论述是不同的。在那里,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自身涌现着的持续性在场。这也是海德格尔在50年代以后所坚持的关于存在的看法。根据这一看法,存在就是涌现、在场,而没有支配一切的内涵。相反,在1946年所写的信中,存在则是支配一切、决定一切的过程。如果存在是指自身涌现着的持续性在场,那么再用存在来指称支配一切、决定一切的意义就是不恰当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海德格尔在1949年版的《关于人本主义的信》的多个脚注中明确指出,这封信中的存在或存在本身,所表达的是“大行”(Ereignis)的意义,要用大行代替这封信中的存在或存在本身,他在多个脚注中已经这样做了[⑤]。而对于大行,海德格尔指出:“大行是源始的历史本身。”[⑥]大行是使一切发生成为可能的自行(Eignen)[⑦]。因此,海德格尔所说的支配一切的存在或存在本身,实际所指的就是大行。
如果人的去生存是被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即大行)所决定的,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存在与人的去生存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存在与人的去生存之间的关系是抛与被抛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抛者是存在,被抛者是人的去生存。人的去生存是作为被抛而成其本质的。这就是说,人的去生存本身虽然直接是人自己去生存,但从根本上并不是由人自己所决定的,而是由存在的抛所决定的。
其次,一切存在者的活动都是由存在所决定的,人无法决定其他存在者的活动。“存在者是否显现以及如何显现,上帝与诸神、历史与自然是否进入以及怎样进入存在的澄明,是否以及怎样在场与不在场,都是人所不能决定的。存在者的到来在于存在的命运。”[⑧]也就是说,人不仅不是自己的主人,而且也不是其他存在者的主人。
最后,海德格尔提出,人在对存在的关系中的生存地位是:人是存在的看护者。他说,存在在本质上比一切存在者更深远,因为存在就是澄明本身,存在是作为澄明而存在的;存在的澄明保持着通往存在的近处,人作为去生存着的人就居住在这近处之中;人不是存在的主人,而是存在的看护者,人必须按照存在的命运来看护存在的真,人作为去生存着的人的尊严就在于被存在本身召唤到存在的真中去。
这就是海德格尔关于人的生存究竟由何而定的思想。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与近代西方人学强调人对世界的主体性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突出强调人对世界(自然与社会)乃至人对人自己的主体性,是近代人学的主导精神。相反,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生存是被存在所支配的,人的主体性是在被决定这一前提下的主体性,因而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是人的活动的被制约性、被限制性,甚至夸大了人的活动的被制约性、被限制性。实际上,海德格尔关于人的生存被存在所决定的思想正是对近代主体性人学的消解或历史性反向。这既是西方人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主体性人学发展到极端必然走向非主体性人学,更是当时西方社会时代状况的反映。
二
“人的去生存作为去生存是历史的”[⑨]。由于海德格尔具有深刻的历史感,所以,他对人的生存的分析就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人的生存是被存在所抛投这样一种一般性的理论上,而是必定深入到人类特别是现代人类的生存的历史中去。他对现代人类的历史性生存进行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是:现代人已经处于无家可归状态(die Heimatlosigkeit)。
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现代人(或现代人类),主要是指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对于现代人无家可归状态的涵义,海德格尔所提供的是一些一般的提示而没有比较具体的说明,而目前的国内外海德格尔的研究者对此也还未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认为,海德格尔关于现代人处于无家可归状态的思想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
第一,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人无家可归状态的实质内涵是现代西方人处于(对)存在的遗忘之中。如前所述,存在是作为澄明而在的,人作为去生存着的人本来就居在存在的近处,居在存在的澄明之中。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今天,人已经不能够特别地体会并承担这种居了”[⑩]。海德格尔说,对于这个存在的近处,他在关于荷尔德林的挽歌《还乡》的演说中(1943)已从对存在遗忘的经验出发称之为“家乡”了。他对“家乡”这个词既不是在爱国主义的意义上来思考的,也不是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来思考的,而是在一种本质的意义上即在存在的历史这一意义上来思考的;同时,他用“家乡的本质”这个名称就是从存在的历史来思考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的。海德格尔认为,当荷尔德林吟咏《还乡》的时候,他关心的是他的“同胞们”在还乡中找到他们的本质,但他绝不意味着从他的民族的利己主义出发来寻找这本质,相反,他是从归属到西方的命运中来看待这本质的,他是要他的德国同胞与各民族一道成为世界历史性的。“这个历史性地居的家乡就是通向存在的那个近处”(11),“还乡”就是要回到在存在的近处的自觉地居。现代西方人早已遗忘了存在,遗忘了在存在的近处的居就是在他们家中的居,所以现代西方人处于无家可归状态,即找不到家的状态。因此,“无家可归状态是存在遗忘的标志”(12)。
第二,现代西方人无家可归状态的直接表现之一是对地球自然根基的破坏。海德格尔40年代末在分析技术时认为,技术的“框—架”本质对现代人类是一种极大的危险(13),在70年代答联邦德国《明镜》杂志记者问时说现代技术已经把人类从地球上连根拔起,所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这表明了海德格尔在现代西方人无家可归状态问题上的思想的一贯性,也表明了海德格尔直到晚年也总是深深地思考着现代西方人的历史,思考着现代人类的命运。
第三,现代西方人无家可归状态的又一表现是,欧洲思想已经落后于世界命运的本质进程。世界历史已经发展到何处?现代世界的命运究竟怎样?它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与要求?人类怎样才能够把握世界的命运并根据它的要求自觉地行动?在海德格尔看来,欧洲的思想对于这些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并没有获得清楚的认识,它已经落后于世界命运所展开的进程。“迄今为止的欧洲越来越清楚地被迫进入的危险也许就在于,首先它的思想——曾经是它的伟大之处——落到了不断展开着的世界命运的本质进程的后面,尽管这一本质进程在它的本质来源的各根本点上仍然规定为欧洲的。没有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不管它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还是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还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在其本质上而不只是在其追求展开自身的各种努力上还能够赶上这个命运,这意味着:能够思着赶上并聚集起现在在存在的完整的意义上还在着的东西。”(14)这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欧洲思想落后于世界命运,从根本上就是落后于存在本身的进程,就是没有认识到存在的真究竟为何。
第四,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西方人的无家可归状态还在于他认为现代西方人的信仰价值观发生了动摇。西方社会人们的信仰主要是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核心是认为,上帝是神圣万能的,人生来就有罪,人通过忏悔赎罪可以走向上帝而得救。这是西方社会人们的信仰价值观的基石,是他们生活的精神支柱。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残酷战争和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却无情地向他们表明,他们并没有因信仰基督教而得救,上帝并没有把他们从黑暗带向光明。这就尖锐地提出了是否有一个至上万能的上帝、基督教信仰是否靠得住的问题。也就是说,基督教在人们心目中的绝对神圣的价值地位发生了动摇,人们在精神上处于徘徊彷徨状态之中。海德格尔对现代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并没有明确进行这样的分析,但他所说的一段话却证明他把基督教信仰的动摇也看作是现代西方人无家可归状态的重要表现。他说,要做到在存在的近处历史性地居的话,就要断定:“上帝和诸神是否以及如何对人拒斥自身,黑夜是否以及如何停留,神圣的东西的白天是否以及如何破晓,在神圣东西的开端中上帝与诸神的显现是否以及如何能从新开始。只有神圣的东西才是神性的本质范围,而反过来,神性本身又只为上帝与诸神保持这个维度;但只有当存在本身事先并在长期的准备中已经澄明自身并在它的真中已经被认识的时候,神圣的东西才能出现。只有这样才能从存在来开始克服无家可归状态——在这个无家可归状态中,不仅人们而且连人们的本质都迷失了方向。”(15)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对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精神氛围的深刻写照,他的这些思考是深深地植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状况、精神状况之中的。
总之,在海德格尔看来,无家可归已成了现代西方世界的命运,是现代西方人的严峻现实。对此,必须进行追根问底的思考:现代西方人无家可归状态的根源何在?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人无家可归状态的根源就在于存在的遗忘。“无家可归状态是存在遗忘的标志。由于存在遗忘,存在的真未被思考。”(16)如前所述,存在遗忘的一个表现就是现代西方人乃至从柏拉图时代以来的西方人总是只研究和处理存在者。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也不可能不表象存在,所以,他们或者把存在看作是存在者的“最一般的东西”,或者把存在看作是那个无限的存在者(上帝)的创造,或者把存在看作是有限主体(人)的制造品,这样,他们就只是从存在者看存在,甚至把存在就看作是存在者,因而没有思考存在本身,没有就存在而思存在。
既然如此,他们也就没有思考“存在的真”。什么是“存在的真”?从海德格尔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来看,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存在的真”的意思是:存在的无蔽与遮蔽状态,存在的既澄明又遮蔽的运行状况。(17)西方人从柏拉图以来就由于遗忘了存在而没有思考存在的真,而到现代西方人几乎完全执著于存在者时,这一问题就突出出来了。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西方人没有思考存在的真,因而也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处在历史的何处,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究竟向什么方向前进,不知道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命运究竟怎样。当现代西方人突然处于不期而来的战争恐怖、经济动荡、社会制度的变革之中时,他们对自己未来命运捉摸不定、处于到处找不到自己的家的状态之中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存在的遗忘仅仅是现代西方人自身的缘故吗?仅仅是现代西方人自身没有记住存在的缘故吗?决不是。海德格尔认为,从根本上说,现代西方人对存在的遗忘并不是由他们自身的记忆力造成的,而是由存在本身的运行造成的,即,存在本身运行到了以遮蔽自身为主导状态的阶段,由此才有西方人、现代西方人对存在的遗忘。“存在作为发送真的命运,是遮蔽的。世界命运在诗中透露出来,但它作为存在的历史还未成为明显的。”(18)正是由于存在的历史还是隐蔽的,现代西方人才不可能深入思考存在的真,因此,西方人对存在的遗忘、现代西方人的无家可归,说到底是存在本身运行的命运。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从根本上并不是人类自己决定的,而是存在的历史、存在的真所决定的。
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现代西方人无家可归状态的思考旨在表明,现代西方人的历史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被存在所决定的,人类从根本上并不能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在历史中的能动性是有限的,人类在历史中的作用仅仅在于思考、服从那个支配一切的东西——存在本身。这就说明,海德格尔的现代人无家可归的思想是一种从根本上消解了人类的主体性的历史观,这与他的历史之思的理论出发点(人的生存被存在所抛投)是完全一致的。
三
对现代人无家可归状态的思考,是海德格尔的最重要的历史之思。无疑,海德格尔的这一历史之思无论在时代根源方面还是在理论本身方面,都既具有合理意义又具有局限性。
首先,海德格尔的这一历史之思的实质精神——人的生存及其历史是被决定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特定状况的反映,因此,必然既有其产生的时代必然性,又有其时代的局限性。20世纪上半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发生了多次大的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震荡,而且爆发了两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残酷的世界大战,无情地毁灭了亿万个体的生命,给人们的精神和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及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矛盾,又带来了复杂的新的历史情况。这些动荡、矛盾、残酷、复杂的时代内容,一方面,尖锐地突出了个体生存的严峻性,个体生存的命运、价值、意义成了个体必须思考的问题,忧虑、恐惧、烦恼、死亡成了个体生存经常面对的情绪体验,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凸现了人类历史的必然性问题,人类能否支配自己的历史,人类历史的发展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成了迫切要求回答的时代问题。因此,海德格尔的人的生存及其历史被存在(大行)所决定这一实质精神的时代合理性在于,他认识到了历史必然性对人类生活的制约作用,反映了人类在那个时代(以至在今天)还无法自由地支配自己历史的状况,只不过是把历史必然性命名为存在或大行罢了。
但是同时,正是由于海德格尔的历史之思的实质精神是对特定的时代状况的反映,他的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本身所造成的局限。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以及今天的人类还不能够充分认识和自由驾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而处于其盲目的支配之中的话,那么人类是否永远处于这样的必然王国之中?显然不是。当人类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制度高度合理、认识能力高度发展时,人类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社会和自然的必然性,能够比较容易地驾驭它们,从而不再是受必然性盲目支配的奴隶,而是成为自由利用和驾驭必然性的主人。在这样的时代,海德格尔所说的那个支配人类、支配一切的存在本身(大行),就不再是决定性地支配人类历史的力量。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本身(大行)却是人类永远无法征服、无法驾驭的力量,这实际上是把人类在特定时代受必然性盲目支配的状况看作是永恒的。这正是海德格尔历史之思之实质精神的局限所在。这一局限说到底又是海德格尔所处的那个时代本身的局限:人类还处于自己历史的必然王国之中。
其次,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本质”在于去生存的理论,克服了旧的形而上学而又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观点,认为这是把人看成了具有固定本质的现成存在物,指出,人没有固定的现成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在去生存中形成的。海德格尔的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生成论,的确打破了西方从柏拉图哲学以来一直延续发展的人的本质在于理性这样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形而上学人学观点,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的重要进展。然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海德格尔又认为人的去生存本身就是存在的澄明,是被存在所抛投的,人的去生存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由存在运行的命运所决定的。海德格尔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又把人看成具有固定本质的存在者:人的去生存被存在所先验地决定,人类的历史被存在所先验地支配。这样,海德格尔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就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试图破除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本质”的静止理解,提出人是一种生成着的存在者,另一方面,他又把人的“本质”的生成看作是被存在所先验决定的。海德格尔所陷入的这种矛盾,是他的思想的超越性和时代状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即,海德格尔力图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但时代的状况却是人的生存处于历史规律性必然性的盲目支配之中。因此,如果说,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本质”在于去生存的观点是对旧的形而上学关于人的静止理解的克服的话,那么,他关于人的去生存被存在所决定的观点则又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人学观,一种既强调人的本质的动态性又强调人的本质的先验性的形而上学人学观。正是由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包含着这样的矛盾,所以,后现代主义的德里达等人认为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并不彻底,批判海德格尔的思想还存在着支配一切的中心(存在、大行),就的确抓住了海德格尔思想(包括历史之思)的要害所在。
最后,海德格尔对现代人无家可归状态的分析,确实触及到了现代西方人生存状况的本质内容,但又具有把现代西方人无家可归状态的根源仅仅归结为存在本身的抽象性。本世纪40年代中叶,西方社会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大自然的破坏问题已经初露端倪,刚刚从残酷战争的动荡不安中解放出来的西方人也还没有从信仰观价值观的彷徨动摇中完全恢复过来,当时西方人的思想也的确没有具体地把握住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进程。海德格尔对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分析,抓住了那个时代西方人社会历史生活的这些深层内容,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西方人的精神状况,表明了海德格尔作为思想家所具有的敏锐性和独到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海德格尔把现代西方人这种无家可归状态的根源仅仅归结为存在本身,而并未去揭示存在本身的运行过程、具体机制,即,并未去揭示现代人无家可归得以发生的必然性,并未去揭示当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他就不能够具体深入地说现代人无家可归状态的根源,不能够具体深入地说明当时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这就是说,海德格尔的历史之思还停留在存在本身这种一般性的层次上。这也正是海德格尔的历史之思具有抽象性、“神秘性”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2~53页。
② ek—是希腊语前缀,与ex前缀意思相同,都有“从……中出来、到外面去”的含义。
③ ④ ⑧ ⑨ ⑩ (11) (12) (14) (15) (16) (18) Heidegger,Gesamtausgabe,Band 9,Wegmarken,Vittorio Klostermann,Frankfurt,1978,S.325、323、330—331、336、337、338、339、341、338—339、339、339,重点号为引者加。
⑤ 见同上书,第315、316、330、331、332、342、360等页的脚注。
⑥ Heidegger,Gesamtausgabe,Band 65,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Vittorio Klostermann,Frankfurt,1989,S.32
⑦ Heidegger,Zur Sache des Denkens,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 1976,S.20-25
(13) 关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框——架”本质的分析,参见拙文:“自然为人立法与人为自然立法”,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第94~100页。
(17) Heidegger,Holzwege,Frankfurt,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1980,S.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