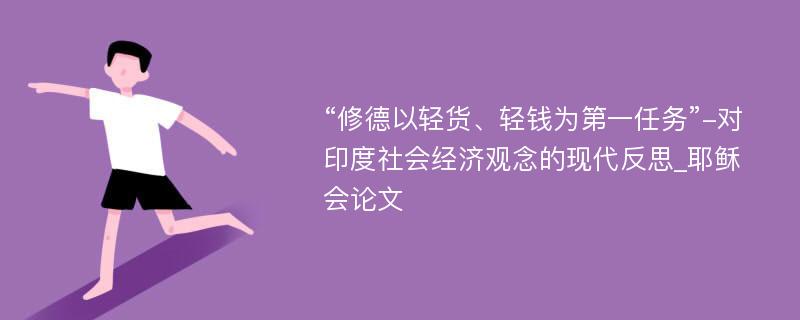
“修德以轻货财为首务”——对依纳爵社会和经济观念的现代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念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轻货财论文,依纳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50088-14 国内学界对16、17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甚至对当下社会经济问题的审视,现在很难绕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集出版于1920年),因为其中亲资本的观点和“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恶俗话语已然被不少人接受。这部著作将经济发展与精神的因素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但是韦伯政治上的右倾立场使得他的结论变成一种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歌颂,并假借新教伦理赋予其合法性,对资本主义的贪婪加以美化和圣化。英国经济史研究的大师托尼在1926出版有《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这部名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韦伯谬误的回应,但是更多的是阐释托尼本人的资本主义批判,认为基督宗教社会价值观的退让和边缘化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伴生现象。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评价这两位学者的上述观点?如果我们不美化贪婪,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基督宗教的伦理道德是否包含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工商业发展有利的因素?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究竟是基督教精神退却的结果还是因为受到传统基督教伦理演进的推动? 我们在这里试图追溯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1491-1556)的经济伦理思想,希望由此个案的考察,探索基督教传统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影响,以及对当下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具有的意义。 一、耶稣会经济伦理的思想史研究 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侧重对16、17世纪英国情况进行研究,但是也将问题的考察扩展到18、19世纪,其理论上的概括也不完全局限于英国的宗教状况与经济发展。他不赞成韦伯强调新教伦理特殊性的思路,认为整个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冲击下都有放弃道德监督责任的退缩,而且他还指出宗教之外其他思想和社会政治领域的动向也促成了资本主义贪婪的肆虐。他承认近代西方市场经济在技术进步和物质财富创造上的巨大成就,而他的核心观点是,如果基督宗教传统的伦理道德得到人们足够的尊重,近代西方社会就会更及时地意识到,经济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人的幸福,财富是为人服务的,人不应该被财富和对财富的贪婪所奴役。他清醒地指出,对贪婪的批评不能无视经济效益,但是经济效益如果成为压倒一切的目的,而不被正确地看作是服务人类的手段,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就会被破坏,而现代工业的效益本来就是离不开和谐与合作的。① 作为近代早期出现的最重要的、曾经引发多次争议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有何独到的见解、是否有过特殊的贡献?韦伯提出新教伦理推动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教徒中间一些人将工商业者的贪婪神圣化,所以新教学者对此有比较多的批评,但是其中有一种批评的观点是以反天主教的方式提出的,即指责耶稣会人士支持高利贷,认为他们才是近代基督宗教迎合利润、利息、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代表。②其实,诚如托尼所言,纠正资本贪婪的正确路径不是反对现代经济体制的全部,而是批判和改造资本活动的目的,让市场和工商业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私利。晚近学术研究的动态之一,就是注意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天主教会在这方面的贡献,而不再强调教会对高利贷的批评压制了市场和金融业的发展。譬如托代斯基尼就指出,方济各会在倡导清贫理想的同时,认同成功的有利可图的工商和金融活动,前提是商人不吝啬藏富,愿意投资于地方社团,创造更多财富,而且他们的慈善事业能起到刺激消费和资本流通的作用,达到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的目的。③与这一天主教传统相呼应,正如耶稣会社会思想的晚近研究者所注意到的,耶稣会的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以及其他耶稣会人士并不敌视工商业,而是积极争取工商业者的支持,积极借助新兴的商贸和金融手段来运作他们的宗教和慈善工作,同时对日益放纵的贪婪和资本的力量进行批判,强调财富本身并非是目的,而仅仅是服务的手段。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玛窦在其中文著作《天主实义》里面说,“修德以轻货财为首务”。⑤ 《自传》和《灵性修炼》的史料意义 依纳爵出生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吉普斯夸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少年时期就被其父亲送往国王斐迪南的财政大臣贝拉斯克斯那里,目的是接受廷臣的训练。在贝拉斯克斯于1517年去世后,依纳爵投效了守卫西班牙北部边区的纳赫拉公爵,并在1521年法国人进攻潘普洛纳时被炮弹炸伤双腿。决定依纳爵后半生虔敬宗教生活的精神转变,即他追求完美信仰的皈依,发生在他此次战败之后的疗伤期间。1524年以后,他先后在巴塞罗那、阿尔卡拉、萨拉曼卡和法国巴黎求学。1534年,他与自己在巴黎的几位同学和朋友发誓奉献自己给教会的传教事业,其中有后来在东亚因为传福音著名的沙勿略。这些人构成1540年正式成立的耶稣会的核心创始成员,依纳爵则被众人推举为第一任总会长,并担任此职务直到1556年去世。⑥ 在疗伤和求学期间,依纳爵的个人生活是严格的清贫实践。1522年,也就是他负伤后的第二年,依纳爵拜访和告别了纳赫拉公爵,从此结束了他的廷臣生活。他随着骡子的漫步,在3月份的时候到了加泰罗尼亚的蒙特塞拉特,在那里的一座本尼狄克修院忏悔三天。然后他把骡子送给修院,把佩剑挂在圣母塑像下,把脱下的贵族衣袍赠送给了一位乞丐。他在尚未破晓的时刻就踏上了旅程,手里只有一支朝圣者的手杖,身上只有一件粗布的袍子,脚上是系带子的简陋便鞋。当他走出一段路程的时候,后面追来一位市民,询问他是否把衣服送给了一个乞丐。依纳爵回答说“是”,眼泪禁不住就流了下来,因为他想到那位乞丐此时正被人们当作小偷在审问着。⑦当他决定离开曼雷萨,由巴塞罗那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携带任何钱财。船长愿意让他免费搭乘,但是无法提供给他食物,因而就连他带到航船上的干粮都是上船前乞讨来的。在巴塞罗那上船前,依纳爵已经是一个摆脱了焦虑和骄傲的信徒。临行时,他把讨干粮时好人们赠给的几个钱币也放在海边的一条长凳上,希望路过的穷人能拿去使用。⑧ 在离蒙特塞拉特不远的曼雷萨小镇,依纳爵停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即1522年的3月到1523年的2月。他在这里的宗教体验和写作的《灵性修炼》对他后来建立的耶稣会传统以及对整个天主教思想文化意义非凡。他在这个时期开始产生为教会和人类服务的炽热愿望,但是当时他的内心世界还仍然是“简单和粗糙的”。而在这一时期的磨炼之后,他不仅对自己的灵修有了把握,甚至也能够指导别人的信仰生活。⑨问题是,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一次在前往在曼雷萨附近一座教堂的路上,依纳爵在路旁卡多内尔河的岸边坐了下来,此刻自己这段时间以来苦苦思忖的许多灵修问题豁然开朗。他没有看见什么幻象,但是这一刹那的醒悟,依纳爵在《自传》里回忆说,比他一生六十多年里得到的收获还要大。吉贝尔把依纳爵在曼雷萨的心路历程概括为,由注重外在的苦修发展到深刻的内在灵修生活和强烈的宗徒使命感,并成长为具备训练和辅导他人能力的宗教生活导师。由《自传》来认识依纳爵灵修境界的成熟过程,读者会注意到他所强调的是天主恩典的协助。用依纳爵自己的话说,他在卡多内尔河畔的顿悟使他能够用“心灵的眼睛”(internis oculis)去理解天主。吉贝尔认为,拥有这种直接来自神恩的“灌注默观”(infused contemplation),是依纳爵自曼雷萨时期就开始进入的境界。⑩在胡戈·拉纳看来,河畔的顿悟是依纳爵在曼雷萨灵修经历的转折点,将他之前的许多体会总结成一个整体,组成《灵性修炼》的主体内容。拉纳在此引用了最早记载耶稣会历史的波朗科对这一经历的记载:依纳爵的灵魂豁然开朗,圣灵的启示与他对圣经的理解得以汇聚。他于是开始写下如何通过忏悔净化灵魂,思考和模仿基督的生活,指导他人在内心燃烧起对天主的爱。这就是《灵性修炼》这部小书。(11)耶稣会对近代西方文化和教会传教活动有重大影响,并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成为天主教社会思想和实践的新锐力量,在解放神学和社会正义等领域有突出的贡献。胡戈·拉纳在1953年就指出,这一宗教团体的历史成就无法简单地用社会和政治的眼光去审视和解读,必须深入到依纳爵和他的追随者的内心世界。然而在耶稣会丰富的历史文献里,我们还能找到这些宗教人士内心活动的痕迹吗?拉纳希望能够“穿透文献的文字”,进入“单纯的历史”之外的精神历史。他认为《灵性修炼》以及《自传》和依纳爵为耶稣会神父们制定的规章等基础性文件,在本质上出自他默观天主的心得体会,但是以文本的形式留存于世。书写依纳爵的传记和研究耶稣会的历史无法离开对这些著述的阅读和理解。不独如此,整个耶稣会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灵性修炼》内在的精神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更新。(12) 也就是说,理解依纳爵的内心活动,我们才能够理解他在尘世的活动,也能够理解和展示众多耶稣会神父为贯彻依纳爵的精神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的传教活动和实践天主教社会思想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书就不仅仅是一本灵修手册,而且也是研究耶稣会历史的基础性史料。 解读《灵性修炼》的社会思想 依纳爵的一些核心思想以及早期耶稣会的核心文献都隐含着对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和现代社会竞争的深刻批判。这一思想基础在20世纪拉丁美洲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成为解放神学的重要渊源之一,并构成当代天主教社会思想和社会正义学说里面最具活力的内容。由依纳爵和耶稣会人士的社会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活动来观察,近代以来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主要还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拒绝基督宗教社会思想的约束。我们经常公式化地把基督宗教笼统地看作是资产阶级文化,进而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真相:非基督教运动是近代西方历史上持久和广泛的社会现象,是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的思潮之一,至今还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基督宗教对经济秩序和社会正义的探讨,天主教社会思想所包含的经济观点,都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道德因素,也是经常被资产阶级忽略和蔑视的观点,并在有些情况下嬗变为激进的反文化。(13)埃弗里·杜勒斯在谈到依纳爵宗教思想的时候曾经分析说,耶稣会的传统强调信仰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依纳爵对基督人性的重视使他和早期耶稣会神父珍视人的价值和人世间的生活,对人类的文化遗产采取一种积极的正面肯定的态度。有学者甚至将这一态度归结到文艺复兴与耶稣会神学的相遇。这一态度也解释了耶稣会传统上为何重视教育和科学,积极进行与非基督教文化的对话和交流。(14) 但是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类文化的依纳爵神学深刻地塑造了耶稣会神父的社会使命感和他们以基督宗教价值观干预社会生活的决心。这里引发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显然是过度强调了耶稣会在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他们的科学教育成就,另一是他们对非基督教文化的研究和包容。在这两个领域,耶稣会神父固然颇有建树,但是他们在传教和圣化工作中对贫弱者关怀,他们对社会不公正的抗议,他们对社会改革的推动,他们以批评资本主义贪婪为核心的社会使命,过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晚近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15)如果我们回到依纳爵的《自传》《灵性修炼》以及他的其他著述,我们就会发现这位16世纪天主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与新教改革的主要人物一样,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在《灵性修炼》中这样写道: 你要注意到,那个巴比伦的原野上首要的敌人,坐在烟火弥漫中的王位上,模样是那样的可怕可怖。想一下他是如何找来无数的妖魔,并把他们四处派遣,有些派到一个城市,另一些派到别个城市,让他们布满世界;没有一个行省,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种生活,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他们。(16) 在撒旦的旗帜下,大小妖魔给人们布下陷阱,而他们引诱的手段首先是人们对财富的贪婪,由财富产生的荣耀,由荣耀产生的傲慢,一切其他邪恶都可以由这里续发。(17)而在基督的旗帜下,基督徒被派往世界各地去帮助所有的人。他们追求的是在基督的旗帜下认可天主的、模仿基督的生活,甚至不惜陷入物质的贫穷,甚至期望被欺凌和被蔑视,并由此学会谦卑。这就是所谓的“两旗默想”。(18) 包括一些耶稣会学者在内的天主教神学传统曾经长时期地以强化灵修的思路弱化依纳爵思想和活动的社会实践意义。在对《灵性修炼》的解读上,譬如对这里提到的撒旦和基督“两面旗帜”所代表的两个阵营,以往的解读往往偏重于理解为:信徒让自己准备好选择符合基督教信仰的生活,但是却避而不谈这一选择具有的社会意义,好像灵修的意义只是在个人品德的修炼。(19)屈松在他1968年出版的《圣经神学与灵性修炼》中仍然保留了这一倾向。这部著作通常被认为是对《灵性修炼》最好的也是最系统的评注之一。他注意到依纳爵刻意引导信徒思考和仿效基督的生活:我们的主诞生于极度贫穷之中,在备受艰辛之后,在遭受饥渴、暑热严寒、羞辱和暴行折磨之后,他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20)依纳爵所提示的基督的榜样,他对以财富和地位诱惑人们的撒旦的揭露,以及信徒们相应的祈祷和思考,在屈松的解读里,都不过是信徒内省和灵修的构成环节。屈松的确简略提及,这样的灵修为信徒接受圣灵指引做好了准备,为他们的牧灵和社会服务做好了准备,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走上十字架受难之路。他拒绝由信徒个人的灵修阐发到依纳爵和耶稣会的社会使命。(21) 在1973年出版的另一部关于《灵性修炼》的著作里,屈松解读的基础还是他前述的著作,但是他的侧重就有了微妙变化,主要是更加明确地承认依纳爵以基督为中心的灵修思想可能具备激进的社会意义。他注意到,思考撒旦和基督这两面旗帜下的生活方式不应该是抽象的,必须联系到信徒个人具体的生活情况。基督邀请信徒排除杂念,让他们忘却自我,进入心境的清空状态。即便被他人忽视,甚至被他人误解和蔑视,他们也能因为谦卑而保持心灵和平,能够在自己的内心给他人和天主留下重要的位置。而撒旦以财富和地位引诱人,让人在对物质和荣耀的追逐中排斥他人和天主。其实,由依纳爵的文本来看,正如解读者有时会注意到的,撒旦引诱人的“财富”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财富,还有在人世间被人们看作是具有吸引力的事物,譬如聪慧、健康、美貌、友情、工作成就、他人的尊敬、得到他人赞赏的见解和观点等等。这些事物本身并不是问题,错的是人们对它们的态度通常是以占有这些事物作为首要目的,以占有作为人生。依纳爵并不要求所有基督徒都放弃自己在人世间的财富和地位,但是显然希望他们懂得对财富和名利要有正确的态度,即按照基督教的律法和道德生活,甚至能够对名利有一个超脱淡漠的立场。在最高的境界,基督徒应该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天主的荣耀仿效基督的榜样,选择像基督那样贫穷,像他那样承受屈辱,像他那样遭人轻蔑和嘲弄。(22)屈松认为,这最后一种境界是圣徒的境界,是奉献自己于传福音事业的人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也是依纳爵对耶稣会神父的要求。“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跟从我来”(《路加福音》第18章第22节)。(23) 屈松的解读与卡尔·拉纳对《灵性修炼》的经典诠释接近,但是后者其实更清楚地把灵修与实际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虽然拉纳不会也不应该把依纳爵的灵修指导简单理解为资本主义批判,但是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和世界,干扰信徒接近天主的最强大阻力难道不是来自于市场经济相连的价值观念吗?在撒旦与基督的对峙中,如果信徒拒绝贪婪,他的思想境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现代商业社会,贪婪对人的深度腐化作用采纳一种浸润和弥漫的方式,有时甚至是难以察觉的:“如果我拥有这辆豪华汽车,购买这架私人飞机,每年夏天都在夏威夷度假,难道我会伤害任何人吗?”拉纳的回答是,这样的奢华生活固然不会直接伤害什么人,但是却会让那些丰富占有物质的人迷失在物质的炫耀中,很快就欣喜地接受“万国的荣华”(《马太福音》第4章第8节),而且不能自拔了。然后人就开始陷入深深的担忧,害怕失去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害怕失去自己的成功、优雅和名誉,害怕失去自己能够蔑视他人的崇高社会地位,最终不惜以一切代价来捍卫自己的财富,甚至不惜伤害他人和冒犯天主。我们也可以说,拉纳在这里描写的过程,不仅是物质的贪婪最终会败坏人的道德,甚至会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思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概念,即人们开始把本来为人服务的物质财富,提升和颠倒为人的存在本身。(24) “神贫”与社会现实有关联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和合本的这段中文翻译很关键。“虚心的人”其实就是很多天主教文献所翻译的“神贫的人”(pauperes spiritu)。(25)依纳爵在《灵性修炼》里谈到两种贫穷,一种就是“神贫”(ad summam spiritus paupertatem),另一种是实际的“贫困”(ad paupertatem actualem)。神贫通常被理解为灵修生活中的虚心状态,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但是依纳爵却把神贫和实际生活的贫困联系起来,而且注意到接受神贫的人往往会遭遇实际的贫困,包括人世间事业的失败、名誉的受损、地位的卑贱。(26)拉纳对此的如下评论,其实可以看作是对现代商业社会贪婪和竞争的尖锐批评: 一个人如果完全以天主为中心来生活,而不愿意把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世俗事物,那么在世人的眼里,他就是愚蠢、落后、怯懦和无用的。在人世间的战场上,与那些全身心拥有人间利器的人在一起,如果一个人与名利保持距离,不愿意把自己完美地与名利联系在一起,那么他就会永远处在一个失败的地位。好人和虔诚的人往往是要显得更加愚蠢一些,显得更加笨拙和无能一些。追随基督的生活方式有一个普遍和必要的特征,即那些认真对待自己的基督信仰的人不可能在追逐人间名利的赛跑中跑到前面去。 而且,人的物欲可以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竞争和追逐成功的强烈冲动甚至可以存在于恪守清贫原则的宗教人士当中,甚至他们也会把社会上流行的竞争和向上流动的理想带到教会里面来。如果一个人不这样适应现代的竞争心理,他就会被看低,遭受“凌辱和蔑视”。(27)在拉纳的解读中,依纳爵的灵修观很贴切地变成了对资本主义贪婪和竞争的批判。 由占有财富和社会地位而获得安全感,由这种其实虚假的安全感产生自我满足和傲慢,最终漠视和忘却天主,这条道路是依纳爵希望信徒们避免的。在这里,解读者一般没有分歧。他们的根本分歧是,是否应该灵修化依纳爵的《灵性修炼》,其中的内容是否具有社会实践的意义。屈松和卡尔·拉纳等神学家对依纳爵传统的社会意义持温和肯定的观点,而彼得斯在1967年出版的评注中直接驳斥和特意否定了这种思路,认为不应该把关于撒旦和基督两面旗帜的思考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观点联系起来,不应该把撒旦和基督两个阵营的对峙看作是要信徒选择自己具体和特定的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不应该把依纳爵的意图理解为支持或者反对某一种社会经济观点。也就是说,彼得斯不赞成把依纳爵对贪婪的批评看作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他特意提出,16世纪的教会和整个社会对财富的渴望是普遍的现象,但是依纳爵的意图是让信徒接近和喜悦天主,而不是进行经济道德的说教。(28)这当然是典型的以强调内心信仰生活来否定宗教社会意义的做法,即以灵修化宗教思想的方式去除其实质的社会训导内涵,捍卫既得利益集团。 作为解放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塞贡多《灵性修炼》的阐释恰恰与彼得斯相反,甚至可以说是对他的直接反驳。(29)“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和合本的汉译固然表达了信徒服从天主的寓意,但是却遮掩了文本的社会训导意义。在《新约》里面,耶稣所提到的“穷人”同时也是指实际生活中处境贫困的弱小民众。如果把这个“穷人”概念完全灵修化,完全理解为一种精神状态,人们恐怕是在曲解和阉割基督的福音了。这正是塞贡多最担忧的,而且他认为依纳爵为耶稣会设计的使命非常积极和贴近社会生活,但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神学使得他很难将这一使命恰当和充分地表达出来。《灵性修炼》里面,依纳爵曾经这样界定所谓的“第一原则”:“人被创造出来赞美、敬仰和侍奉上帝我们的主,并以此获得灵魂的拯救。人世间的其他事物都是创造出来帮助人在世间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如果这些事物能够帮助人达到这一目的,人将使用它们;如果这些事物妨害人达到这一目的,人将舍弃它们。”(30)塞贡多指出,在人与天主的关系中,爱是需要通过人的生活来体验和体现的,不能将天主和某一个人之间的整个世界和所有其他人都排除在外。天主创造的人是社会的人,因此天主对人的要求是一个社会的要求,即人们要照应社会中的弱小者,给他们吃喝,留他们住宿,给他们衣服穿,到监狱里去探望他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因此天主的爱不是设定某一个律法要人们去遵守,也不是设定一个终极目的要人们去达到,而是要人们在自己现世的生活中互相去爱。塞贡多特别提出,福音书里面提及“虚心的人有福了”,其旨意是呼吁人们去爱在生活中真实陷入贫困的弱小者,而不是在谈论“虚心”或者“神贫”的人。依纳爵也谈“神贫”,但是他被当时的神学和解经学所限制,还不能由此发展出清晰和系统的天主教社会训导。由《新约》的启示来看,天主已经有一种特惠穷人的爱,而耶稣在人世间的活动就是给穷人带来福音,呼吁改善他们的命运。也就是说,主的国不仅在天上,也会通过信徒的活动反映在人世间。塞贡多认为,依纳爵希望信徒思考如何侍奉天主,如果这样来理解,说的就是如何让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31) 与依纳爵和耶稣会十分活跃的传教、布道和慈善活动形成对比的是,《灵性修炼》把中世纪修道传统里的“舍弃”置放在重要的位置。塞贡多觉得这正是依纳爵被旧传统约束的结果,而非他的本意。(32)所以依纳爵的基督教社会思想更多展现在反映他实际牧灵活动的书信里面。(33)也就是说,他与基督的对话是在具体和现实的语境中进行的,而不是彼得斯理解的那种具有浓厚隐修色彩的个人的、抽象的人神交往。在纠正了这类过度灵修化的倾向之后,解放神学重视社会实践的优点也并非不需要有“舍弃”的关照,即在推动社会改革的同时与世俗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实际上,晚近的天主教徒在遵照《灵性修炼》做退省的时候就面临如何处理解放神学影响的问题,譬如有些热衷于社会正义的年轻神父在退省时思考了依纳爵设计的撒旦和基督两个阵营,意识到自己在关注贫弱者命运的时候不仅时常担心失败,而且没有充分注意到,所使用的手段也应该是基督的榜样所昭示的,即便是正义事业也要时刻注意手段本身的正义性。(34) “两旗默想”应该是《灵性修炼》里面社会训导色彩最浓厚的部分了。在摆脱了彼得斯所代表的灵修化倾向之后,学者对“两旗默想”的理解才能深入到依纳爵所处的社会环境。 二、依纳爵书信里的社会基督教 就依纳爵本人而言,他所经历的皈依主要是舍弃宫廷贵族生涯,而不是放弃经商和财富,但是当时的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尤其是他所途经和居留的巴塞罗那、热那亚、威尼斯、罗马、安特卫普和巴黎等一系列欧洲城市,都是当时商业活动最发达、新兴资产阶级最活跃的地区。他意识到,一个信徒追随基督的生活必定是与资本主义贪婪逆反的,但是信徒接近天主的路径不是逃离现实社会,而是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传播福音,接济贫弱者,教导其他的信徒们也来这样实践自己的信仰,并坦然面对因此遭受的贫困、羞辱和蔑视。他对工商业并不排斥。依纳爵的这一牧灵思路在他的书信中尤其明显,也反映在很多耶稣会传教士的书信和著述里。 伊莎贝尔和玛丽亚 依纳爵活动的时期是西班牙和整个西欧工商业勃然兴起的时代,他的生活和工作不可能避免周围浓厚的经商务实氛围。他个人与贵族和富商交往密切,努力引导他们离开贪婪和自私。巴塞罗有一位贵族妇女,伊莎贝尔·罗萨,是最早资助依纳爵和接受他精神指导的。她对依纳爵及其同伴长期的经济资助,尤其是对他们在巴黎求学期间的支持,并非是一项轻易的事业,与巴塞罗那浓厚的商业气氛是不协调的,而伊莎贝拉个人如果希望深化她的虔敬和灵修,也需要克服她习惯的贵族生活方式。(35) 在给伊莎贝尔的一封著名书信里,依纳爵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两旗默想”对他并非是抽象的内省,而是直接对实际生活有指导意义的。当伊莎贝拉遭遇经济困难和种种流言困扰的时候,依纳爵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期望完全生活在我们邻人眼里的地位和荣誉里,我们就不再可能与上帝我们的主紧密相连,我们也难以在凌辱面前无动于衷。”依纳爵鼓励她说,为了侍奉天主和为了天主的荣耀,信徒需要做的是树立起天主的旗帜,抗击人世间的荣耀,拥抱被人们看作是低下的东西,卑贱、贫困、被人仇恨或者排斥都不能打击我们,就像尊贵、富有、被人喜爱或者欢迎也不能收买我们一样。事实上,作为耶稣会早期的赞助人,伊萨贝拉花了很大气力和时间才克服了她的优越感。她曾经试图在罗马借助教宗的力量影响依纳爵在管理上的决定,要求耶稣会建立修女团体。当她抵达罗马时,整艘船上装满了她的衣柜和细软。(36) 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当时的工商业发达地区,即早期耶稣会主要的活动区域,很多贵族都卷入当时的工商业活动。伊萨贝拉和其他许多人对耶稣会的赞助往往涉及复杂的契约、借贷和不动产交易。财富和经营的成功是人们看重的地位标志,即便是耶稣会的传教、办学和济贫工作也不能脱离资源的管理和经营。问题是,在这个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阶段,依纳爵在这些事务上给神父和平信徒提出的建议,反映了什么样的经济伦理思想?他不仅在天主教的立场上谈及了对财富和名利一般的看法,如他给伊萨贝拉的书信所展现的,他也有一些更加具体的对工商业活动的见解。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鼓励信徒将财富由资本的流通中拿出来,投入到耶稣会的教育和其他慈善事业上去。而很多从事工商业活动和富有的信徒不仅反感耶稣会神父在布道中对贪婪的批评,也担心和极力反对自己的亲属把财富捐献给公共教育和济贫事业。在这个意义上,依纳爵的榜样和言论具有反文化的意义,构成一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批评。 1524年,依纳爵由耶路撒冷朝圣返回途中经过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费拉拉。(37)在这一年,费拉拉公爵手下的首相正好与玛丽亚·弗拉索尼结婚。后来公爵和首相都与耶稣会建立了友好的关系。1550年首相去世后,遗孀玛丽亚成为耶稣会在当地最积极的赞助人,热情地支持他们建立一所学院,而她的亲属们则散布流言说她早就计划把所有财产都奉送给耶稣会。当学院成立的时候,费拉拉公爵只赞助了费用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经费出自玛丽亚,而且她为了促成耶稣会和公爵之间融洽的关系,还默默地把赞助人的名义让给了公爵。(38)耶稣会神父得到许多贵夫人的支持,部分的原因是他们的社会工作十分重视贫困儿童和沦落的妇女。沙勿略等人在波伦亚救助妓女的事业就十分成功,最后由一批贵夫人接手这项工作。玛格丽塔·吉利和她的兄弟是耶稣会在波伦亚的重要赞助者,帮助建立了那里的学院,并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这所学校。波伦亚学院狭小拥挤,但是神父们觉得,“虽然我们总是处在贫困之中,我们得到的接济却总是足够让我们完成我们在这里的使命”(39)。如果赞助人的亲属反对捐赠财产,并不愿意接受调解,依纳爵和耶稣会总是委婉谢绝好意,并努力调解当事人的家庭关系,譬如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40) 他从来都相信,经济只是手段,宗教工作和社会服务才是目的。即便在家庭和个人友谊的层面,人们也万万不可以让金钱和财富成为伤害和睦感情的祸害。1528年,他来到巴黎求学,身上带着在西班牙筹措的学费和生活费,并在银行把汇票换成金币。然而现金刚刚到手,各项费用还没有支付,就被一位在法国的西班牙朋友借走花掉,然后这位朋友就失踪了。过了一段时间,依纳爵听说他在试图返回西班牙的途中病倒在港口城市鲁昂,于是徒步从巴黎走到那里。他整整走了三天,沿途靠乞讨的食物充饥,在抵达鲁昂后照顾和安慰自己这位贪财的朋友,帮助他找到去西班牙的船只,甚至为他写好到那里使用的推荐信。(41)在处理耶稣会收取捐赠的事务时,依纳爵总是留心,不让捐赠人有哪怕一点压力,尊重其个人意见,同时尽可能避免让捐赠人的家属有不满和不同意见。即便在耶稣会神父去世以后,在处理他留给修会的财产时,依纳爵也会把财产返还给其家庭,以便照应他亲属的生活。1544年,兰迪尼神父在科西嘉传教时去世,依纳爵把他的财产转到他姐妹的名下,后者的丈夫们就财产的分配发生激烈的争执。依纳爵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说:耶稣会可以依照法律拥有兰迪尼神父的财产,为了照顾你们生活才把它转给你们,希望你们的家庭生活更加和美,却没有想到财产反而成为你们家庭不和的原因。他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能接受调解者的仲裁,把家庭和睦放在钱财之上,这笔财产将会被收回到耶稣会。(42) “尽力就请满意” 依纳爵在耶稣会成立和担任其总会长之后,处理大量行政事务,深知各地纷纷建立的学院和日渐扩展至全球的传教使命需要大量资金。(43)但是他始终认为,真正能够帮助牧灵工作的支撑来自天主,而不是来自为谋取物质财富而滋生的急切和焦虑,更不必为财富操劳伤神和伤身体。这与韦伯所描写的新教伦理形成对照,后者尽管不一定符合近代早期新教伦理的历史真实,但是韦伯借引用富兰克林所刻画的发财致富的猴急心态,的确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绝好描写。(44)1555年,依纳爵在给科隆卡尔特修会的修院院长写信时感谢他对当地耶稣会学院的慷慨支持。他谈到各地耶稣会人数有很快的增长,他完全不知道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提供给他们食物和衣服,但他不会拒绝任何合格的申请人,因为“我们把希望的锚牢固维系在天主的善意上,无论人多人少,他都会让大家吃饱,无论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足”(45)。这种对待财富的态度并不局限于耶稣会的事务。在依纳爵1532年写给他哥哥的信中,他就引用圣保罗的话来规劝他的哥哥对家族的财富和经营有一个超然的态度,“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30-32节)。他鼓励他哥哥,作为一个富有财产的人,他应该挂虑的是用自己的财富来教育和支持自己的孩子、仆人和亲属,用于帮助孤儿和穷人,以此来获得自己在天上的荣耀;他不应该因为担忧如何扩大自己的财产和收入而彻夜不眠,不应该为了让自己在俗人眼里有个成功的好名声而成天焦虑不安。(46) 清贫是耶稣会的核心理想,不过在涉及神父健康和其他正当需求的时候,依纳爵从来不吝啬。他认为钱财是身外之物。当负责意大利北部耶稣会的维奥拉神父重病的时候,他非常担心自己花费过多的治疗费用,会拖累修会的财政。依纳爵写信给他说:“不要以为我们有很多债务,所以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无法提供必要的资金。在这些事务上,天主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他告诉维奥拉,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生,他可以先以修会的名义借钱,修会将及时归还欠款。吉罗拉莫·维涅斯有两个兄弟均为耶稣会神父,他本人一直协助处理耶稣会的经济事务。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商人,他总是很为耶稣会的财政焦虑。依纳爵写信给他,劝告他对商业和金钱有一个超然的态度。在处理这些事务的时候,“您应该平静和温和地做出决定,并尽力去执行就可以,不要再去担心和挂虑了,让天主去处理你自己不能把握的事情”。之后,依纳爵用一大段话说明了他对工商业活动的看法: 我们需要用心去做和适度关注与我们的服务有关的事务,天主会因此喜悦,但是他不会喜欢我们为做这些事滋生的焦虑和精神磨难,因为他希望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有限和脆弱的,我们应该懂得依靠他的力量和他的无所不能,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善意将弥补我们的缺陷和弱点。即便是一个要做大量生意的人,即便他做生意的时候有着神圣和良好的动机,也需要明确无误地知道,他只能做他个人力量范围之内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他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他实在不必为此而烦躁不安。他应该听从自己良知的声音,做好自己能做和应该做的一切。即便他没有能够做其他一些事情,也应该有耐心,而不要以为上帝我们的主会要求我们去做我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或者希望我们烦恼沮丧。让天主满意了比让他人满意要更加重要,如果我们已经做到让天主满意了,我们没有必要太劳累我们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尽力就可以了,其余就留给无所不能的天主吧。 当维湟斯担忧如何支付耶稣会的一笔大数额的债务时,依纳爵劝告他说:“您的担忧需要节制,可以促成您的勤勉,但是不要造成您的焦虑”。在另一封信里,依纳爵再次劝告他不要让财经事务过度影响心情和身体健康,劝他为这些生意的事情不要太劳累,也不要挂虑太多,有些细节甚至就不必太计较了。在这里,依纳爵总结了他对做生意和买卖的态度:认真勤勉也要适度,不要变成焦虑。对于这些事情的结果,人永远要坦然准备接受两种可能性,即成功或者失败。人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有限的力量尽自己的努力,其余就托付给天主。人很难明白天主的计划,有时候会因为事务的失败而沮丧,但是其实也许应该高兴呢。依纳爵于1556年7月31日因病去世,他在5月17日给维涅斯的信中再次希望他不要在为耶稣会操办财务时抱有一种焦虑的心情:“工作时请注意适度,尽力就请满意;无论结果或者成绩如何,平静地接受它们,因为你应该相信所匮乏的东西,上帝我们的主会提供给我们。”(47) 耶稣会的清贫理想 在耶稣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清贫理想始终是最突出的纲领之一。与中世纪许多修会的情况不同,在清贫理想和需要充分财政支持的服务工作之间,依纳爵始终有一个清楚的设计,注意不让二者互相干扰。在担任耶稣会总会长期间,他的工作有大量涉及在各地创办学院的事务,而办学校就需要经费。维涅斯所操劳过虑的财经事务大多也和办学有关,因此耶稣会并不避讳教育资金和办学房舍的筹措。但是就耶稣会神父自己的生活而言,清贫是严格的要求。依纳爵对清贫理想的理解和阐释可以分析到两个层面:一是清贫作为基督教道德对耶稣会成员和其他信徒的重要性,另一是清贫对耶稣会展开传福音和其他服务工作的意义。1552年,依纳爵派遣兰迪尼神父和戈梅斯神父到科西嘉考察和布道,并研究有无可能在那里建立学校。在依纳爵给他们的指示里,他特意提及,在吃住等生活条件上他们应该随遇而安,但是即使为学校和慈善事业募捐也要注意避免给人留下贪财的印象,不能为自己的服务收取任何费用,别人赞助的钱物不能由神父自己经手,要委托给耶稣会的代理人管理,只用于办学校和救助穷人的工作。(48) 清贫和勤勉的服务对树立耶稣会良好形象固然十分关键,但是依纳爵更加注重的是,清贫本身是模仿基督生活方式所必需的。1547年,当帕多瓦的耶稣会学院遭遇严重经济困难、神父们生活十分窘迫的时候,依纳爵给他们的书信实际上是一篇阐释清贫理想的文章,而且实际上明确地把我们前面提到的“神贫”与切实的清苦生活切联系起来。事实上,在这封书信里,依纳爵在这里借助引用经文表达了天主教社会思想的两个核心观点,即天主是特别惠顾穷困者的,而信徒有义务去救助贫弱者。依纳爵在这里抵制了把基督宗教社会思想灵修化的倾向。他指出,《新约》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天主启示出的形象是穷人的朋友,不仅圣母和使徒们是穷人,他派遣耶稣来到人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诗篇》第12篇第6节)。贫穷的人有福,他们能够进入天国,但是天主的这一承诺,在依纳爵看来在现世也有重大的意义:如果人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人世间这些贫困者,“贫穷者的友情让我们也成为天主的朋友”。清贫作为一种高贵的品德,在依纳爵的理解中,有两层含义:它鄙视在人世间为个人堆积成山的财富而操劳的富有者,因为这只会增加他们的傲慢和与天国的距离;它敦促富有者用财富去救助贫穷者,以此去“购买”教会所富有的天上的财宝,这些才是真正的他们永远不会失去的财宝。(49)按照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来看依纳爵,他已然很有力度地提出,基督宗教的教义是具有具体和现实的社会意义的,基督徒必须在自己的实际生活方式上体现自己的信仰,努力在人世间救助贫弱者。这里是否包含了直接对近代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呢?不管对此的回答是什么,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依纳爵的社会思想与当时正在恶性膨胀的贪婪和金钱拜物教是格格不入的。 其实在《灵性修炼》的最后一部分(第四周)里,依纳爵就提出,思考对上帝的爱需要注意两点:要通过实际行动而不是仅仅是话语来显示爱,要通过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来显示爱,无论所拥有的是知识、荣誉还是财富。(50)在给帕多瓦神父的那封信里面,依纳爵谈到“两旗默想”对贪婪及其道德腐蚀作用的批评,进一步论及实际救助贫弱者的意义,但是在给兰迪尼神父和戈梅斯神父的前述信里,他清楚地说明了耶稣会的社会服务并不是发动剧烈的社会变革,更不是要在贫富阶级之间激发冲突和斗争。他要求他们在访问科西嘉时请示当地的政府、贵族和主教,争取他们对耶稣会工作的支持。依纳爵提醒他们,如果看到当地的官吏有不良行为,在劝告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应该报告他们的上级。耶稣会宪章在界定该团体使命的时候,将神父们在贵族和统治阶级当中的传教和牧灵工作看作是具有特殊性的,即通过改善他们的信仰和道德来影响更多民众,“善功越普及,就越让天主喜悦”。(51)耶稣会重视与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交往,因为这些人的影响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协助或者阻碍牧灵工作”。依纳爵和耶稣会神父把社会服务看作是基督教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就耶稣会神父本身的时间和精力分配而言,宗教工作比具体的救助工作更加重要,因为后者可以“托付给其他人去做”。但是就耶稣会的整个使命而言,布道和祈祷是不能与直接救助贫弱者的慈善割裂的,因为后者同样是一种布道,即以行动而非言辞进行的布道。(52) 三、余论:由利玛窦到埃亚库里阿 与传统的耶稣会历史研究不同,杜勒斯和奥马利这两位有代表性的美国天主教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极力强调依纳爵和耶稣会的社会服务使命,认为救助贫弱者的社会服务始终构成耶稣会圣化工作不可剥离、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53)譬如奥马利就提出早期耶稣会的慈善活动与他们的“公益”观念有关。耶稣会规程所讨论的“公益”(commune bonum)与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中的同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语境,但是其渊源和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中世纪西欧神学和教会法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这种与近代西方个人主义对立的“公益”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现代天主教会的社会思想则会进一步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54) 问题是,依纳爵和耶稣会批评贪婪、倡导公益的思想传统对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是妨害市场经济还是像托代斯基尼所说的有着积极推动的作用?耶稣会神父利玛窦在17世纪初写有中文的《天主实义》,向中国人讲授天主教教理,包括说明为什么修士和教士有独身制度。他以财色二欲为例解释道,清贫和守贞有益于教士避免索求“无义之财”、沉迷“邪色之欲”。他强调说,他并不是蔑视家庭和日常生活需要的工商活动,“为人之父不免有货殖之心”,不过教士和他自己的职责是教化他人,不可陷入“不能超脱无溺”的境地,“修德以轻货财为首务”,以免贪求“非义之富”。在《畸人十篇》里面,利玛窦议论了“富而贪吝,苦于贫窭”的状况。他着力批评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贪得而吝于用”,指出“财之美,在乎用耳”。他并不诟病财富本身,而是嘲弄了一个富人卖出所有家产,得数万金,“成一巨铤,埋土中”,最后被盗贼偷去。那么在利玛窦看来,财富应该如何使用呢?他在《天主实义》里这样写道:“所谓‘仁者爱人’,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上帝欤?爱人非虚爱,必将渠饥则食之,渴则饮之,无衣则衣之,无屋则舍之”。(55)与依纳爵和其他早期耶稣会人士一样,利玛窦的财富观是兼容工商业活动的,而且以财富的社会效用为中心。“富而贪吝”在他看来不仅自私,也不是正常有益的商业活动。 依纳爵的社会经济观念到了20世纪仍然是耶稣会神父的重要精神遗产。教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而不是游离在社会关系之外。上个世纪80年代活跃于萨尔瓦多的耶稣会神父、解放神学家埃亚库里亚曾经就此写过很多文章。他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拉美国家的极度贫富分化和军人独裁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成为神学家乐于采纳的分析方法,尽管这并不是解放神学的主要推动力。拉美解放神学思潮和运动的真正背景是人们意识到,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在本质上是反基督的,是依纳爵所描述的撒旦旗帜下的人间地狱。因此,为了社会正义,教会一定要站在贫穷者和弱小者的一边,这才是教会真正应该站的位置。当然,与依纳爵的社会经济观念相比,解放神学以及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并非没有突破。在埃亚库里亚看来,在萨尔瓦多等贫困的拉美国家,社会制度的改良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才是教会应该努力的方向,教会不应该满足于教导穷人捡拾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56)这样激进的主张和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导致了埃亚库里亚和他的7位同僚在1989年11月16日被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军政权枪杀。而他们所批评的“拉美化”不良社会现象,早已成为公认的现代社会发展陷阱,是市场经济成长的最坏形态之一。 在商业社会批评贪婪永远是惹人厌烦的事情。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结尾,托尼曾经提醒当时西方的知识分子说,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具有压倒性影响、成为众人认可之常规的社会氛围里,批评贪婪不仅显得尖刻,也往往被指责为迂腐和莽撞。然而他坚信,真正可怕的是在压迫和非正义面前的懦弱:“当抗议不受大众欢迎的时候,说得太多的人应该得到宽容谅解,而不是保持沉默的人。”(57) ①R.H.Tawney,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New York:Mentor Books,1954,pp.227-234.关于托尼社会思想的研究,参见彭小瑜《“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 ②J.Brodrick,The Economic Morals of the Jesuits:An Answer to Dr.H.M.Roberts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pp.1-21; John W.O'Malley,The First Jesuit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96,150.布罗德里克这部著作对相关争议有系统的介绍。奥马利的著作吸收了晚近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强调在传教与自然科学工作之外,耶稣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对贫弱者的救济和扶助,有整整一章专述他们的这方面的工作,而耶稣会与教宗曾经被渲染的密切关系则被恰当地淡化。 ③Robert P.Maloney,"The Teaching of the Fathers on Usury",Vigiliae Christianae 27(1973),pp.241.-264; Raymond de Roover,"The Scholastic,Usury,and Foreign Exchange",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1(1967),pp.257-271; Giacomo Todeschini,Franciscan Wealth:From Voluntary Poverty to Market Economy,Saint Bonaventure:The Franciscan Institute,2009,pp.151-196. ④Dominique Bertrand,La politique de S.Ignace de Loyola,Paris:Cerf,1985,pp.275-291. ⑤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⑥John Patrick Donnelly,"Religious Orders of Men,Especially the Society of Jesus",in John W.O'Malley,ed.,Catholicism in Early Modern History:A Guideto Research,St.Louis:Center for Reformation Research,1988,pp.147-162;Ludwig Pastor,History of the Popes,vols.1-2,London:John Hodges,1891.帕斯托尔的《教宗史》第1卷的第1和第2章其实是一部早期耶稣会的简明历史。由这样的布局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心目中,耶稣会对16和17世纪教宗以及天主教改革的重要性。这种强调耶稣会与教宗依存关系的观察角度被其他许多学者长期沿用。中文著作参见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依纳爵《自传》最方便的英文版本为:St.Ignatius' Own Story,translated by William J.Yang,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6。这个版本的段落编号与耶稣会历史文献社所出版的西班牙—拉丁文版本是一致的,后者见D.F.Zapico et C.de Dalmases,ed.,Fontes narrativi de S.Ignatio de Loyola et de Societatis Iesu initiis,vol.1(Rome: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1943),pp.323-507.此后文中的引用简写为Fontes narrativi de S.Ignatio de Loyola,其后数字为段落号。 ⑦Fontes narrativi de S.Ignatio de Loyola,17-18. ⑧Fontes narrativi de S.Ignatio de Loyola,35-37. ⑨Joseph de Guibert,The Jesuits,Their Spiritual Doctrine and Practice:A Historical Study,translated by William J.Young,St.Louis: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1972,p.27.吉贝尔在这部1953年出版的著作里还是使用了“这个皈依的士兵”来描写依纳爵。部分天主教人士的这一习惯也是对耶稣会“军事化”这一误解难以消除的原因之一吧。《灵性修炼》比较好的英文版本为: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Ignatius,translated by Louis J.Puhl(Westminster,Maryland,1951)。这个版本的段落编号与耶稣会历史文献社所出版的西班牙—拉丁文版本是一致的,后者见J.Calveras et C.de Dalmases,ed.,Exercitia spiritualia,Rome: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1969,pp.140-417.此后的引文简写为Exercitia spiritualia,后面的数字为段落号。 ⑩Fontes narrativi de S.Ignatio de Loyola,28-35; Joseph de Guibert,The Jesuits,Their Spiritual Doctrine and Practice,pp.29-32. (11)Hugo Rhaner,The Spirituality of St.Ignatius Loyola,Westminster,Maryland:The Newman Press,1953,pp.88-96. (12)Hugo Rahner,The Spirituality of St.Ignatius Loyola,pp.ix-xv,96-112. (13)Avery Dulles,"Catholicism and American Culture:The Uneasy Dialogue",America,27 January 1990,pp.54-59,此处p.57. (14)Avery Dulles,"Saint Ignatius and the Jesuit Theological Tradition",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14:2,March 1982,pp.1-21. (15)Dean Brackley,"Downward Mobility:Social Implications of St.Ignatius's Two Standards",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20:1(1988),pp.1-50; John W.O'Malley,"Early Jesuit Spirituality:Spain and Italy",in Louis Dupré and Don E.Sliers,Christian Spirituality:Post-Reformation and Modern,New York:Crossroad,1989,pp.3-27; (16)Exercitia spiritualia,140-141. (17)Exercitia spiritualia,152. (18)Exercitia spiritualia,145-146. (19)Joseph de Guibert,The Jesuits,Their Spiritual Doctrine and Practice,pp.110-112.奥马利在评价吉贝尔的这部著作时曾经指出,作者没有充分阐释依纳爵以及耶稣会将灵修与传教和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的特点,也忽略了沙勿略和利玛窦等人重大传教活动所实践和发展的依纳爵灵修思想。John W.O'Malley,"De Guibert and Jesuit Authenticity",Woodstock Letters 95(1966),pp.103-110. (20)Exercitia spiritualia,116. (21)Giles Cusson,Biblical Theology and the Spiritual Theology,St.Louis: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1988,pp.253-258,276-277,351-352.法文原版出版于1968年。 (22)Exercitia spiritualia,165-167. (23)Giles Cusson,The Spiritual Exercises Made in Everyday Life,St.Louis: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1989,pp.84-90.法文原版出版于1973年。 (24)Karl Rahner,Spiritual Exercises,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65,pp.169-175. (25)我个人觉得“神贫”这样的直译并没有很好地传达词语内在的含义,而且也不是很通顺优雅的现代汉语表达,但是“虚心”这样的意译,一旦脱离具体文本的语境又容易失去其特定的含义。这里的确有一个基督宗教词语汉化的难题。 (26)Exercitia spiritualia,146. (27)Karl Rahner,Spiritual Exercises,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65,pp.176-178. (28)William A.M.Peters,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Ignatius:Ex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3rd edition,Rome:Centrum Ignatianum Spiritualitatis,1978,p.93.第一版出版于1968年。 (29)Juan Luis Segundo,The Christ of the Ignatian Exercises,New York:Orbis Books,1987. (30)Exercitia spiritualia,23. (31)Juan Luis Segundo,The Christ of the Ignatian Exercises,pp.90-93. (32)Juan Luis Segundo,The Christ of the Ignatian Exercises,pp.104-114. (33)Juan Luis Segundo,The Christ of the Ignatian Exercises,pp.114-124. (34)Brian Grogan,"The Two Standards",in Philip Sheldrake,ed.,The Way of Ignatius Loyola,St.Louis: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1991,pp.96-102. (35)Hugo Rahner,Saint Ignatius Loyola:Letters to Women,Freiburg:Herder,1960,pp.262-293.这部依纳爵书信集包括了胡戈·拉纳的评点和他对这些书信背景详尽的介绍。 (36)Hugo Rahner,Saint Ignatius Loyola:Letters to Women,pp.264-267,282-290. (37)Fontes narrativi de S.Ignatio de Loyola,50.在费拉拉,他口袋里有朋友施舍给他的一些大小钱币。遇见一个乞丐走过来向他伸手,他把一个零钱给他了,接着第二个乞丐过来,他把另一个稍大的钱币给他,当第三个乞丐伸出手来的时候,他口袋里面只有十几个银币了,于是他拿出一个来给他。众多的流浪汉看见了,都走过来,依纳爵最后给出了身上所有的钱。 (38)Hugo Rahner,Saint Ignatius Loyola:Letters to Women,pp.189-202. (39)Hugo Rahner,Saint Ignatius Loyola:Letters to Women,pp.210-219. (40)Hugo Rahner,Saint Ignatius Loyola:Letters to Women,p.244. (41)Fontes narrativi de S.Ignatio de Loyola,79. (42)Ignatius of Loyola,Letters and Instruction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artin E.Palmer,John W.Padberg and John L.McCarthy,St.Louis: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2006,pp.595-596. (43)Ignatius of Loyola,Letters and Instructions,pp.183-188.依纳爵大部书信的原文为西班牙文,少量是用拉丁文或者意大利文等其他欧洲文字写成。部分书信是由他的秘书波朗科根据他的意思起草的。在1547年写给耶稣会全体神父的这封信里,他呼吁大家像世界各地的商人一样频繁写信沟通,记录各地的情况,并汇报给罗马修会总部。 (4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9页。 (45)Ignatius of Loyola,Letters and Instructions,pp.556-558. (46)Ignatius of Loyola,Letters and Instructions,pp.3-7. (47)Ignatius of Loyola,Letters and Instructions,pp.605-608,627-629,665-667. (48)Ignatius of Loyola,Letters and Instructions,pp.387-392; Exercitia spiritualia,343-344. (49)Ignatius of Loyola,Letters and Instructions,pp.203-207.在这里我们应该再次注意到和合本在《马太福音》第5章把“饥渴”处理为“饥渴慕义”,把“贫穷”处理为“虚心”。但是和合本《路加福音》第6章第20节写道:“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经文的社会意义是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依纳爵在这里引用这些经文都旨在突出其社会训导的意义。 (50)Exercitia spiritualia,pp.230-231. (51)Constitutiones Societatis Iesu Latinae et Hispanicae cum Earum Declarationibus,Rome:Apud Curiam Praepositi Generalis,1937,pp.212-214.这个版本为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对照本,但是没有《耶稣会历史文献》版本附带的大量考订说明(因为绝版,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耶稣会历史文献》恰好缺分别收录宪章西班牙文本和拉丁文本的第2和第3卷,目前正在设法补全)。 (52)Constitutiones Societatis Iesu Latinae et Hispanicae,pp.220-224. (53)John W.O'Malley,The First Jesuit,pp.165-168; Avery Dulles,“Saint Ignatius and the Jesuit Theological Tradition”,pp.12-13. (54)Michael P.Hornsby-Smith,An Introduction to Catholic Soci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05; John W.O'Malley,The First Jesuit,p.167; Constitutiones Societatis Iesu Latinae et Hispanicae,Formulae,p.xxiv. (55)《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79-80、88、497-500页。 (56)Ignacio Ellacuría,"Utopia and Prophecy in Latin America",and "The True Social Place of the Church",in John Hassett and Hugh Lacey,ed.,Towards A Society That Serves Its People:The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of El Salvador's Murdered Jesuits,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1,pp.44-88,283-292. (57)R.H.Tawney,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p.235.标签:耶稣会论文; 基督教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耶稣论文; 灵修论文; 马太福音论文; 经济学论文; 天主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