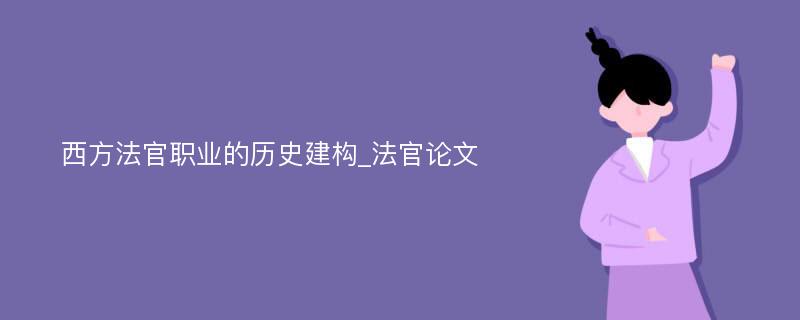
西方法官职业的历史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官论文,职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8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14(2008)02-0003-(10)
法官自被设置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能将法律从文字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主体。法官对纠纷的理性认识关系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社会对法治的态度。法官职业是一种必须具备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profession)。“这种品质植根于一代代法律人的努力而积淀的职业传统,并经由长期的法律学习、法律训练和法律实践而悟得。”[1]362关于法官职业的历史构建是一个富有理论内涵的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研究,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领悟“法官”是什么,并加深对法官职业的发展历程、基本概念以及正当化等问题的感知与理解。
一、法官设立的理性基础与初始的正当化过程
(一)法官的概念基础
当我们把法官设为研究对象后,那么对法官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就需要有明确的界定。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常识性话语中,法官常称之为裁判官、审判官。在英语中,法官称为Judge或Justice,法语中称为Juge,德语中称为Richter,日语中则称为はぅかん或“判事”。在我国古代,法官被称之为廷尉、大理、推事、判官、司法理、司法、法曹等。《牛津法律大词典》将法官解释为:“对其职责是裁决纠纷和其它提交给法院决定的事情的人的总称。法官可能是在高级法院的法官,总是那些在法律和司法上精通业务、富有经验的人。”[2]482按《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法官的解释:法官是“经任命或选举而在法院审理和裁决法律事务的公共官员”。[3]844日本《新法律学辞典》对法官的解释为:“广义是指从法律上解决调整纠纷或利害对立而且有下判断权限的人。其权限,除根据公的权力的公的审判权外,还有根据当事人的仲裁契约的私的仲裁人。狭义的在日本法律上是指具有审判官员的公务员,属于最高法院及下级法院,担任裁判事务者。”[3]365
由于概念是经验事实的结晶,是人们在对事实的了解中形成的,它表现为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些事实之间组成了一个整体。由此,尽管各种词典对法官概念的表述是基于不同的背景与视角,并且对“法官”含义的解释与定义略有差异,但其最终形式或最明确的形式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从其身份、职责方面为基本路径而进行界定的;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借助于公正、公平与正义等的理念来了解法官,使得法官这一概念具有意义。笔者认为,法官是一种被人类赋予公正信念的历史性存在物,以实现人类社会公平、公正与正义为最高理念,调整着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用一种强制性的方式引导着人与社会的发展。说他是历史性存在物,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形态的不同转换,法官的作用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不断地渗进历史的内容。
法官自设立之时起,就与正义联系在一起。比如西方语言中,法官Judge或Justice的直译就是裁判或正义,法官工作的地方叫Court,直译就是院子,是裁判或实现正义的地方。在西方法学中,正义的象征是正义女神,她来自三千年前的古希腊。她蒙着眼,看不见出现在她目前的东西。她不知道人们是富是穷,是达官显贵抑或无名小卒。她只听人们的陈述,并根据最有道理的言辞来判断案情。她手里有一把长剑,因为她必须不停地惩恶扬善。在西方国家的法院大门前,都伫立着这正义的女神,她体现着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期望。法官始终必须牢记的是:“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那种坚定而持久的愿望。”[4]5
法官作为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职业,它最初是怎样的?他是怎么形成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根据人类知识起源的一般特征,人类对法官的认知无非是源于经验、主体性感悟抑或现实的对象。“所有这些论说的基点,都是由近代社会确立了支配地位的认识论所提供的。这种认识论把最终的认识要素推托于主体与客体,它预设了现实对象中存在着真理或者主体内部先验地具备真理的条件。”[5]2而我们对法官概念的预设,是纯粹地根据他作为一种拟制人格的人性(人的本性)来表述。这样就使得法官成为一个独立于受身体条件限制的人(人的现象)。在哲学的论证中,任何先验的知识体系都包含着一些纯粹的概念。因此,以法哲学论证法官主要不是从法官的性格着眼,而是把法官具有意志的自由作为研究的对象。无论我们是以早期日耳曼的部落抑或古希腊早期农村公社为研究蓝本,都是在这一主体/客体模式的共同基础上展开的,从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关于法官的起源认知,从而趋向于获得一个普遍的认同。
在原始社会时期,“法律意义上的法律(law in the lawyer's sense),还没有与其他的社会控制力量明确区别开来”。[6]27人们相互之间只是以集体生活的发生聚集在一起。对于这段历史,留下的说法很多,最著名的有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述。而在这些著述中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原始社会通过传统习俗和由全体氏族或部落成员共同协商解决争端和纠纷的方法是被大家确认的,具有正当化的含义。可见,“正当化问题所要解决的,是论证和确认该历史阶段和该社会中所实行和维持的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正义和公平的性质”。[7]84
(二)法官的正当化与原始法律或习惯法的关系
当我们以西方法治主义之源——古希腊、古罗马为蓝本研究“法官”时,我们可以追溯到的比较典型的研究样本便是古希腊社会的“城邦”和日耳曼早期的部落时期。
如果我们追溯到古希腊早期农村公社之状况:古希腊早期历史分为两个基本时期,从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为克里特、迈锡尼时代;从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00年为黑暗时代(也称为荷马时代)。在这两个时期内,古希腊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原始公社阶段,每一个农村公社(建立在部落或氏族基础之上)都各自独立,不受外部控制,大部分部落首领的职责仅在军事与祭祀方面。几乎没有例外,习俗就是法律,司法行政只是民间私人的(甚至蓄谋杀人者也仅仅受被害者家属的处罚)。[8]211当然,在极少数情况下,也会由部落首领(亦为军事首长,音译为巴赛勒斯)主持审判重大刑事案件及少数民事案件。[9]20根据荷马的记载,古希腊早期的部落审判通常包括如下内容:当事人双方在自由民大会上控辩;部落酋长主持审判;然后由精通法律的智者提出多种判决意见;最后由自由民投票采纳其中最好的一个并由此结案①。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古希腊的法律纠纷比较简单、具体、琐碎,远远没有复杂到需要抽象和概括的地步。也正是由于古希腊体系化法典的稀少,法律在古希腊早期农村公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突出,反而是人民大会制定的或社会直接生成的习惯,其效力高于法律。这也导致古希腊早期农村公社大量的法律纠纷不是在民众集会中或依靠这些长官解决的,而是以政治形式被讨论和解决。当然,能够有资格参与政治讨论的人乃是拥有权威的人,他们通常都是村中或部落中受人尊重的长老。依此观点,在古希腊早期农村公社中,最初的法官似乎应该是由农村公社中的长老来兼任的。
如果我们追溯到日耳曼早期的部落时期,如同其它氏族一样,日耳曼王国时期并不存在专门解决诉讼的所谓法院,也没有专门审理诉讼的所谓法官。当作为王国居民的日耳曼人遇到诸如盗窃、伤害等经常发生的事情时,一部分人会选择传统习俗,寻求家族的援助,或者交纳和解金,或通过血亲复仇,私下了结。原始社会中,人们认为正义的实现并不靠法庭,处死犯罪、绞死窃贼、家族之间的血亲复仇都是解决争端的好办法。而另一部分人会选择通过集会,依靠长官来解决纠纷,从而实现正义。久而久之,随着通过集会依靠长官来解决纠纷的事例增多,于是人们便称呼这种传统的集会为法院,而对主持、参与集会的人称之为法官。[10]379法官出现了,“尽管最初并没有力量强制把争端交由其处理。早期的法官更像仲裁员,他们只有在当事人自愿选择其解决争端时,才有权审案。在后来的司法体系中尚能找到该遗风。”[11]126依此而言,在日耳曼民族中,法院是从传统的集会,法官则从传统的主持、参与集会者演变而来。
无论是军队的领袖抑或农村公社、氏族部落中的长老这样的人来充当“法官”,他们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缺乏组织性与固定性。然而,这种不同现象特征却反映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他们都选择了习惯和惯例作为规范社会的秩序规则。
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时期,人们在面对各类社会冲突与纷争的解决中,总结出了多种解决纠纷的机制与方法。而这种机制与方法目的总是围绕着对当事人纠纷的协调与部落首领的调解展开的。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中,承担秩序协调职能的人最初都是集体中那些身强体壮或者德高望重的长官或长老,他们凭借着其威望将氏族部落中久存的公序良俗上升为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久而久之一些群体生活的准则就形成了以氏族或部落为基础的原始法律,也有人称之为习惯法(customary Law)。不同的人类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发展出不同的习惯法,这些原始法律的相同特征体现在其中都蕴涵着不同的地方性。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原始的神明裁判、决斗、贤人裁判等野蛮无序方式逐渐被文明社会所抛弃。依“习惯法”裁判,无论这种裁判反映的是什么人的意志,但它在形式上仍然是体现着公力的救济性,强调的是人们对裁判正义与正当的要求,并继而排斥私力救济的不公平性。
公共权力的正当化问题最早是由古希腊人开始讨论的,“从根本上说,它可能源于一种对人的高度重视和由此衍生的对正义政治秩序的极致追求”。[12]326原始社会,人们对原始法律或习惯法的尊重,体现了氏族首领维系部落秩序,以及团结社群成员力量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反映了超越所有个体之上的公共权力需要正当化的要求。从权力的本源上看,公共权力是个人权力让渡的结果,“倘若人人都在涉己的纠纷中充当法官,实施强行正义,则可能陷于普遍暴力而无法生存。人的理性使他们认识到谁也无法从过分和不受限制的相互侵害中得到任何最终的好处,于是公众自愿让渡部分权力,通过立约的形式建立起‘公共权力’。”[12]196既然公共权力是全体氏族、部落成员共同契约的产物,任何加入这个契约的人,都必须遵守这个共同的契约,这是公共权力设立的一个根本理念。原初社会“公共”权力的正当化过程的代价是低廉的,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言:“习惯是最基本的社会知识,它存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散布在社会关系网络的每一个点上。”[13]62它体现的是氏族成员的认同,而不必靠暴力来支撑。
而在原始社会后期,习惯已发展为一种相对集中和相对形式化的知识,可以用语言加以表达,也可以由社会上的“绅士”来加以解释,其内涵已包含有权威性与政治性的特质。说到解释,它与“创造”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西方语言的主要分支(拉丁语、法语、英语、德语等)中“权威”一词的词根都是author,即“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性认同是权威认同的真正原型。[14]204“权威一词的寓意,是一些人有能力责求别人服从,不论对方是否认为这种加诸他们的命令或规则可以接受或者切合所需。”[15]15所以,权威即标志着人们对某一对象的服从关系。控制与解释惯例的“绅士”,通常都是村中或部落的长老——人们认为他们特别有资格运用社会行为的传统规则,之中体现的是原初民众的“主体”意识。
所谓主体(subject)“最早起源于部落的家长权,是一种主管权。其中治理、管理、主宰的涵义较为明显。”[16]4主体概念首先有权利的意义,而“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和权限,”[17]42只有具备资格,其权利才能受到法律和主权者的保护。为了在群体交往过程中能体现出基本的正义、秩序和安全,就需要设置基本的权利规则,以满足人类寻求安全感的天性。
在初民社会,制度化的权利规则作为组织社会秩序的秩序范式,体现了原初的正当性观念。正当性观念在原初状态体现的是有关部落长老如何能够为部落秩序或长老权力提供理据(justification)的问题,它是部落长老与部落民众双方关于管理权支配理由与根据的说明和解释,同时包括对这些理由的理解。通俗地讲,就是指部落长老依据什么理由说明他具有管理部落民众的资格;部落民众又是依据什么认为应当服从这种管理的道理。
“权力”一旦出现便具有了“不能把握和控制”的特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中,利益的量是有限的;但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其对利益的欲望是无限的。所以,权力天生便具有自利与行善的双重成份。也就是说人们对权力的使用既可能是破坏性使用,也可能是建设性使用。为了防止权力行使失去控制,于是,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产生了,“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8]170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分工的出现,公共权力也进行了相应的分化。当司法(Judicial)逐渐从公共事务中分离出来,便发展成为一种专门化的法律事务。此时,司法官吏所有的惩戒与定夺的理由、方式与发展程度,全都在于司法权力拥有者的自由裁量,因而根本没有“刑法”的存在。“适用强力的特权构成了法律中的‘官吏’因素。他们是一般地或特殊地被承认的正确执行物质强制的因素,是社会权力的构成部分。”[19]26此时,人类应该已经完成了从按血亲组织起来的社会向按国家组织起来的社会的过渡,于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官”便产生了。法官一旦出现,且进入制度文明的范畴,法官这一现象的复杂化也就开始了。
(三)法官的正当化与鬼神观念、与宗教崇拜的关系
在法官产生的初期,鬼神观念与宗教崇拜对法官的缘起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就中国古代法官的起源来看,在中国古代,虽然宗教始终没能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但鬼神崇拜观念对法官的缘起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相传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法官皋陶身边有一只神兽“獬豸”:它似鹿非鹿,似马非马,头上长着独角。相传獬豸生性忠直,能辨邪佞,当遇到疑难案件,只要将它牵出,它就能撞击真正的罪犯。正是由于獬豸象征着公正,所以,在中国古代,它就成了法律与正义的化身,御史等执法官员所戴的帽子被称为獬豸冠。
回顾人类早期的历史,诉诸神谕来解决诉讼的原始方法随处可见,例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及以色列的法的神谕都有这样的机能。早先“懂法的人通常多少是具有巫术性资质者,只因其卡理斯玛权威之故而在各案发生时被召唤前来;或者,他们是祭司,如爱尔兰的布雷宏(Brehons)、高卢人的德鲁伊(Druiden);或者,他们是经过选举而被承认为权威人士的法律名家(Rechtshonoratioren),例如北欧的宣法者,或法兰克人的判决发现人(Rachimburgen)。卡理斯玛的宣法者后来变成经由定期选举、最后经由事实上的任命而被正当化的官吏,而判决发现人则为国外所认证的法律名家——亦即审判人(Schoffen)所取代”。[20]169如同其它的文明发端一样,法官的正当化过程还与法官的形式化密不可分。梅因认为:每一种法律体系确立之初,总是与宗教典礼和仪式密切相关。[2]521博登海默也认为:“在古希腊的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在法律和立法问题中,人们经常援引的是特耳非(Delphi)的至理名言——他的名言被认为是阐明神意的一种权威性意见。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祀在司法中也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国王作为最高法官,其职责和权力也被认为是宙斯亲自赐予的。”[21]4
在西方,宗教神学对法官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初,法官是作为宗教的附属物而出现的。据记载,在对耶稣的审判时就经历了宗教裁判与世俗审判这两种程序。首先是犹太教公会(也被称为犹太教的最高法院)的审判。公元30年4月6日,犹太教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决定判决耶稣死刑,并将其交给罗马总督彼拉多。总督彼拉多在审问耶稣并审查案件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查出犯罪事实,并准备稍事惩戒(鞭打)即予释放,但在宗教势力的影响下,他就判了十字架刑将耶稣处死。[15]14这都表明,法官的世俗审判一开始就是宗教裁判的附属物。
由此可见,神的权威和价值影响着世界中所有人的生活细节和所有行为,“显示了人类对秩序的殷切需求,以及伴随这种需求的一种信念,认为上述的秩序,不论在地球上或宇宙间,必须具备两项极为重要的因素:权威与强制”。[16]4人们最初在设定和拟制法官时还含有自然属性特征和天然的权威角色,因为法官的权威只有与“神治”的权威合而为一,社会秩序的运行才能和谐一体。但不久,法官的权威便被置于一种更高实体权威控制之下。在法官权威与宗教信仰相互的融合过程中:一方面,宗教中的许多教义成为法官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进而指导司法实践;另一方面,宗教强化了人们对法官的尊重,当世俗的法官借神或上帝的名义颁布判决的时候,它就获得了终极意义上的合理性。此时,法官充分体现了人为化和神秘化双重特性。
宗教在赋予法律神圣性方面,确实居于关键地位。西方国家的审判程式更多的是从宗教中产生,至今一些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仍然渗透着这种意识。比如一些国家的诉讼程序中还保留着法院开庭前举行祷告、证人出庭作证手按《圣经》宣誓、法官在判决中仍可援引《圣经》内容的传统。同样,西方国家的法官的产生同样离不开宗教的影响,法官最初被人们的认可是缘自于宗教,如代表法官权威的假发、法袍、法锤等饰物,就缘起于宗教礼仪与象征的器饰,这里面就隐藏着法官职业的“正当性”问题。因为法官的形式特征也就是他的合理性依据,其目的在于使人们认知,他们的权威是天幸的,受到超自然的力的掌握和控制;法官代表着信仰、法律以及抚慰。
然而,当今的法官制度是建立在新的法文化(以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法文化)基础之上,它基本上不受任何宗教神学的影响;当今法官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也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对法官制度的改革中是否需要再人为的添置与中国传统、现实毫无关系的法袍、法锤等饰物,是有商榷余地的。西方是西方,中国是中国,即使要寻找历史的根基,也应该是从我们过去的历史中去寻找。
二、法官的产生及特征
(一)法官的产生基础
法官的产生完全是由统治者(国王)渡让权力的结果。在古代社会,并不存在分权之说,国家的一切权力都由国王所掌握。由于国王是唯一的立法者,也是唯一的最高法官(sole supreme judge)。国王在他的统治区域内、在所有的民事与教会案件中、是可对所有人作出裁断的最高法官。[22]21-22所谓的法官,是由国王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任命的;没有国王的任命,“不管他的理性效用是大是小,他也不会因此成为法官,他之成为法官,只因为国王任命了他”。[22]14这种依靠国王的喜好而任命的法官,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官。比如,在中国古代,皇权统摄一切,高度集中,没有独立的司法权,所以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官。所以,所谓法官,指的是由统治者(国王)依据理性设定并实际赐予某个团体的垄断处理与解决社会纷争的资格。
统治者(国王)将“司法权”渡让出去,究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还是非理性的冲动?这个问题从法律角度看可视为:法官究竟是属于一般社会利益的代表还是特定利益的代表;而从哲学视角看这可视为:人类最初的愿望是互相征服还是相互帮助。在远古时期,由于人类感觉自己是软弱的,于是互相依靠与帮助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第一需要;又由于人类的软弱本性,民主应该是他们当时首选的理性议事规则。理性行为象征性地被界定为某种性质的利益最大化,而霍布斯那种“人类最初的愿望是互相征服”的说法,一般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民主选举应该是人类社会产生初期的一项基本的规制,只有通过选举,人们才能最大限度地聚集全社会的共同意志与力量,克服人类的弱点,抵御困难。但民主的议事必须要有一个或几个人来主持,否则七嘴八舌,议而难决。于是,年纪大的、辈分高的人被推举出来,因为只有他们这些在村中或部落中拥有权威的人才特别有资格运用氏族社会的传统规则。所以,初民时期“法官”的产生显然是人类出自于解决问题——人类维护自身(集体)生活秩序的需要,他们应该是代表着社会一般利益的②。
(二)法官的产生路径
由于各民族的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因此法官的产生路径也是不同的:
1.由全社会直接选举产生法官。在这种场景下,司法权是属于全民的;也就是说,由于审判权是由全体社会成员直接行使的,所以,全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法官。在公民大会上遇有重大问题需要作出裁决时,全体公民都有表决权。比如:在古希腊,大部分审判权是公民直接行使的。公民大会开会时临时选举或抽签决定法庭组成人员。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众法庭判处死刑的。在雅典,享有初审权的500人的议事会的成员是抽签产生的。陪审法庭是希腊的最高审判机构,它的成员也是抽签产生的,直接来自民众③。又比如:在古罗马,重要的司法职能始终由民众大会所掌握。古日耳曼人的法院分为部族法院,每一法院都是由辖区内全体自由民组成,在成文法时代,法院的主席与裁判权全无关系,判决由自由民组成之会议作出。在大陆萨克森人中,判决则由邻接区域内或千户区内的全体人民作出④。此种社会对司法权之控制在中世纪仍然存在,只是出席裁判的人员的范围有所缩小而已。还比如:在法兰克人那里,“早期的法庭并不是由常驻法官组成的。因而法兰克的领主法官(rachimburgii)⑤都是针对某一特定案件从民众中选出的。……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些从民众中选出的人都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人士,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军事或是农业方面的事务,可是他们经常性地作为法官来断案。”[11]127
由此可见,由民众选举产生法官的前提是审判权由全社会所掌握;而民众选举产生法官的目的:一是为了使审判更加公正,因为民众知道谁是专家里手;二是为了防止腐败,因为民众“在选择一位将领的时候,是很有本事的。他们知道哪一个法官是辛勤的,知道很多从法院回来的人对他都感到满意,知道他不曾有受贿的嫌疑。人民知道这些,已足以选择一位裁判官了。”[23]9
2.从贵族群体中选举产生法官。当然,这是贵族政治的特征。在古罗马王政时期与共和时期,虽然具体做法有差别,但法官从贵族群体中选举产生是普遍存在的,具有审判职能的元老院的成员也是这样选举产生的。在古罗马,每年,大裁判官(任期1年)都会造一份名单和表册(Album Judicium),把他所选定在他任职年内担任法官职务的人员提出。每当遇到案件发生,人们就会从这个名单或表册中选派相当名额的法官去审理。
(三)早期法官的特征
与其他职业相比,早期法官还具有以下的特征:
1.法官并非“官”,其在社会地位排不上官僚序列。在古希腊,因其特殊的民主传统,致使其很早就有了法庭,并出现了“律师”的雏形;由于古希腊法庭充分允许“律师”的辩论,所以,律师在古希腊有着比较高的地位;而相反,由于古希腊社会对法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所以法官只是人们的一项兼职工作,由此法官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律师。在梭伦的眼中,法官的社会地位要远低于一般的政府官吏。众所周知,梭伦在他的民主精神指导下,曾按财产的多少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高的政治权利。比如:第一、二等级公民可以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而“人们要从四个等级的每一个等级里选举‘法官’,但只能从前三个等级里选择‘官吏’。这三个等级是富有的公民。”[23]10这似乎表明,古希腊社会法官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官职。各等级都有自己的法官,各等级的法官在管辖权里设定了范围,它们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交流的,第四等级的法官只能审判第四等级群体的案件。
2.法官并不由法律专家来担任。在古希腊,随着城邦民主制的发达,其法庭已初显现代法庭的模样,同时也产生了诉讼代理人,他们便相当于现在的律师。在希腊一种专门教人说话的人被称之为“智术师”。智术师教人诉讼的技巧,有时自己也参与诉讼。“可以说,智术师就是职业的论证师。双方辩论,最后由陪审团表决。有时候陪审团的规模非常大,有四五百人之多,大家最后投票表示自己站在哪一边。”[24]61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古希腊的“律师”是专业的,而“法官”却是业余的。同样,在欧洲大陆,最初的法官缘起于早期的“听证官”。在古罗马时期,法官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听证官’(iudex)即为法官体制的根源,但那时候该词的含义与今天大相径庭。在罗马法中,‘听证官’(iudex)是指其职业为在审判项目中按照地方法官(即司法执政官)的指令调查证据和听取证人陈述的个人。也就是说,司法执政官才是原审法官,具体执行法律。因此,罗马民事程序区分为两个阶段,即‘审判阶段’(in iure)与‘听证阶段’(apud iudicem),后者不负责处理任何法律问题,只负责调取审核证据。”[25]28在中世纪的德国,法官也不是由法律专家来担任,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经常要到法律博士那里去请教法律问题,而法律博士的话对审判结果常常起到重要作用。“从14世纪始,德国形成了一种制度,在将自由民组成的法院的案子送到新的职业性的法院的程序要求是,将案件提交到某一大学之法律系,由全体法学教授讨论后提供判决意见。此种方法一直沿用到16世纪。”[26]228
诚如伯尔曼所言:“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的,又是从社会中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27]665当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利没有分离,法律保护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即使法官由民主选举而产生,但仍然不能避免专制的非难。比如“在(古希腊的)拉栖代孟共和国,民选长官断案是武断的,没有任何法律作依据;这是一个弊端。罗马初期的执政官们的裁判方式也和拉栖代孟的民选长官一样。”[23]76由于法官的权力过大,就会有权力滥用与被腐败的可能。司法权发生了腐败,人民甚至不能容忍他们所委托给法官的权力,人民不再尊重法官。又比如,古罗马为了防止司法权的腐败,于是格拉古兄弟把这个司法特权转移给武士们,他认为武士比其他人更有品德;而杜鲁斯则把它给予了元老和武士,他认为,司法权放在元老们手中而不致被滥用;但苏拉却只给与元老们;哥塔给予武士和度支官;恺撒又把后者去掉;安东尼把元老、武士和百人长等编成“十人队”。但是,这些措施也并没有制止腐败。当罗马腐化了的时候,不管司法权转移给哪一个团体,给元老、武士和度支官也好,给这些团体中的两个团体也好,同时给三个团体也好,给其中的任何一个也好,事情总是弄不好的。武士并不比元老更有品德。度支官也不比武士们好,武士和百人长一样也缺少品德。[23]121司法腐败似乎是随司法权的产生而产生的,法官由选举产生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腐败,但面对选举也不能制止腐败的状况,于是采用任命的方式来防止法官腐败,最终也不行。法官从人民自由民主的选举到国王的擅自任命,这显示了社会在走向日益复杂的过程中,原始文明在现代专制面前的退缩;也表明以个人品德来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历史证明从来就是无效果的。
三、西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
职业,是一个源于拉丁语profession的古老词语,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讲,英语中的“职业”(profession)一词意味着声明或者宣誓(professing)的行为与事实。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语言里,对“职业”一词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德语里,用以描述职业的词语是akademischer Berufsstand,而德语Beruf(职业、天职)一词的含义与英语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相近似,蕴涵着一种宗教的概念——上帝的感召;与英语相比,德语中职业的概念更加强调基于宗教的伦理观念以及对特定工作领域的占有,但与英语中的职业概念类似,akademischer Berufsstand也强调了学术知识在职业生活中的意义。因此,“职业”的概念在各种不同社会语境下的意涵有着很大的区别。
(一)“权力分立”理论中法官与政体的关系
至16世纪的欧洲,法官的发展经历了从君主的臣仆到独立主体的职业转变,现代意义的法官独立与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思想影响分不开。洛克在其主要著作《契约论》(1689年出版)中指出,为保护公民的权利,必须对立法权和执法权做出明确的划分。在他的著述中,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司法权的划分,但是他的论述尤其是对权力划分的论述,却为后来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在其“权力分立”理论中,对法官与政体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专属道德论证的特征,用权利分立理论通过推测法官实际活动的趋势来解释政体性质。通过对不同政体的对照解释法官在不同政体下的特征。
由于政体的性质决定了法律的性质和法治的形式,从而也决定了法官的形式。孟德斯鸠在对三种政府形式(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与法官的关系所进行的分类的描述中指出,共和政体是古罗马的理想图景,专制政体是法国可能沦为的可怕图景,而君主政体则反映了孟德斯鸠对英国的看法。当然,这些纯粹都是学者一种理念上的假设。然而,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观,理念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学理的假设,因为它不能在事实中被查明。但只要这种假设能够说明事实,解决无法从事实上解决以及其它理论也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我们就可以接受。我们的学术研究必须以某种推想或假设开始,这里的要领是,须要为论证的建立打好基础。当然,我们对理论假设的论证必须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开始。
在民主政治里,法官应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因为在这种政治之下,投票选举的法律是一项基本法。在民主制度中的人民知道,应当选择那些人来接受他们赋予的委托。孟德斯鸠认为,人民看得见“哪一个法官是辛勤的,知道很多从法院回来的人对他感到满意,知道他不曾有受贿的嫌疑。人民知道这些,已足以限制一位裁判官了。”[23]9采取投票选举法官的方式,使得人们望而生畏的司法权,不归属于某个特定阶级或某一特定职业所专有。法官高高在上,不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样人们所畏惧的只是法官的官职,而不是法官这个人了。即使在控告重罪的场合,也应当允许罪犯依据法律选择法官,或者至少允许他要求许多法官回避,结果所剩余的审案法官就像都是由他选择的。[23]157而康德也认为,法官职务应当由人民自由选择来产生。因为,只有人民才可以审判他们自己,人民通过由他们在自由选择下选举出来的公民,代表他们去审判,甚至专门任命他们去处理每一个司法程序或案件。法官应该由低于国家首脑的人来充当,因为在审判工作中,法官说不定会掺杂自己的得失而作出不当的事情。如果这样,当事人就有机会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17]144
在专制国家中,法律本是无所谓的,因为王国内的最高法官就是国王自己,他有绝对的司法权力。当他使所有法官都成为其私人官员时,国王就成为司法本身的代表、等于法官。与此同时,国王有权任命、监督和惩罚各级法官;国王还可以亲自审判案件,这样国王、法官与法律就是同一的意思了。
在君主国家中,“法律是君主的眼睛,君主通过法律,可以看到没有法律时所不能看见的东西”。[23]81君主国的法官,“在法律明确时遵照法律;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则探求法律的精神”。[23]76君主国的君主是不可以审判案件的。如果君主国的君主像专制国的国王一样可以审判案件,那么“政制将被破坏,附庸的中间权力将被消灭,裁判上的一切程序将不再存在;恐怖将笼罩着一切人的心,每个人都将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信任、荣誉、友爱、安全和君主政体,全都不存在了”。[23]79在共和国里,政制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有关一个公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对法律作有害于该公民的解释了。[23]76
孟德斯鸠的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影响着康德以及德国政府限制改变或推翻仍然由国王代表法院来对犯罪作出有罪宣告的判决。因为当时的法官仍然没有实现人格的独立,由于法官在当时是市民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也便可以随时被罢免。西方学界一般认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司法独立始于19世纪中叶。“1848年,普鲁士宪法为司法独立制度奠定了一个现实的基础,它规定:司法权只能依法由有权行使的独立法官行使。法官非经法定理由与条件,并经法院合法宣告,不得被临时或永久地解职、调动及退休。”[25]29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法官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离职。该条款对以后欧洲法官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经过200多年的司法实践,司法权与立法权及行政权的分开观念已经被证明是稳固的。在法治社会中,“让司法机关享有独立的地位,并从政治压力中解放出来,显然非常重要。因为政治压力的产生,不是与行政部门就是与立法部门有关,他们通常都由政党政治中的部分人所把持。”[15]208虽然,期间曾有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是在这200多年的不断冲突与融和中,人们创制了不少的手段予以克服,虽然解决的方法未必都很有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在指派司法人员时,建立一种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坚定传统。”[15]208由此看来,司法与其他形式的宪法权力相互区分,可以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司法独立。
(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们选择了法律作为组织社会秩序的主要规则,由此发展出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的秩序范式。与其他约束个人行为的规则(比如中国的礼仪)不同,法律具有很强的‘外在化’特征,即它只能管束人的外部行为,而且只能靠外在于行动者的力量来维持。这样就需要有一些专门的人员来负责维持法律的正常运作。”[13]3正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民对法律的这种共识,使西方社会的法制发展从来就是在一种组织化誓约共同体形式①中实现的;人类法律的发展与制度的完善也是在依凭于一定的誓约共同体形式下而获得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根本上是在契约自由理念下形成的人群团体(Personengruppe);其本质上还是法律的统一化与理性化——连同近代机构化组织的政治团体的公开垄断法律创制——的产物。[20]81它是建立在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学专家等的自由协同上,而这些单位内部日后仍然保持其独立性。应该说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社会分工和自由协同思想的体现;正是法制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法律职业群体是随着近代司法独立制度的确立而产生的。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由执掌司法审判或以提供法律服务为业的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群体组成,这些法律职业群体是受过专业法学规范训练的职业化的专门人员,他们都来自同一个社会文化传统,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有着同样的法律语言、知识、思维、技能以及职业伦理。他们以相同的基本原理为出发点,遵守相同的科学实践规则和标准,这是常规科学的先决条件,是形成一个具体的、连续的研究传统的先决条件。[28]243在这个共同体中,有着领袖般人物的法律名家阶层(Rechtshonoratioren),法律名家阶层是将他们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内在因素。而所谓的Rechtshonoratioren一词,在拉丁文中意指“具较高名望者”;在德文里通常是在带点儿友善调侃的语意下用来称呼那些敬重的市民。在马克斯·韦伯的笔下,Rechtshonoratioren是称呼一些阶级人士,他们一来以某种方式使得法律问题的从业工作成为一种特殊的专门知识,二来在他们的圈子里享有这样一种声望:他们立足以将某些特殊的特征置入其各自社会的法律体系里。[20]15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法律家群体已经产生,其中有一些专门解答法律问题、传授法庭技巧、研究法律原则的人士,被称为法律顾问(jurisconsults)或法学家(jurist)。而他们对法律所作的阐释和研究就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的系统知识,他们把这套知识称为‘法律科学’(legitima Scientia)或‘法学’(jurisprudentia)。法律科学是罗马人对西方文明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它使法律传统成为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甚至在其中占据最核心的位子。”[13]4法律科学的形成,最终导致罗马法学著述的大量出版,后来它们成为中世纪罗马法知识的依据。这些著述以后被大批编撰整理,摘要抄录,并按主题分类,其中最著名、最完整并对中世纪资产阶级最有影响的一部汇编为《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
中世纪欧洲,法官职业化之风气正缓慢地在欧洲蔓延开来,在许多城镇,斯卡必尼(scabini)或是高级市政官都被任命或选举为终身任职的法官,这就使他们具有了某些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11]126受这种职业风气的影响,公众对司法的参与也就逐渐淡出,“公众不再拥有对心仪判决给予鉴赏的特权,相反,就是对城市法庭的宣判颇有微词,也会受到罚以重款的威胁——哪个才是最佳判决,全凭法官们自己决定”。[11]128由此,法官行业的职业自主性与司法从业者所享有的声望在社会中获得了合法性
欧洲法律职业阶层的起源各具特色。英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是与强大的中央王权支持分不开的。而欧洲大陆的民族国家,由于王权的力量始终没有达到英国相同的程度,因而其法律职业阶层的产生亦不能完全依靠王权力量的推动,需要借助其他因素的作用来完成这一进程。欧洲大陆法律职业阶层是在民族国家和法学的互动中产生的。[29]283然而,无论是英伦抑或欧陆,虽然法律职业阶层各有不同,但对其的描述是一致的,即:“法律的施行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训练背景,从而造就了共同的思维方式,而法律职业活动的关联性则使其具有了共同的利益范围。”[29]265
中世纪法律职业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对推动西方社会由中世纪神权、君权统治到近代民主政治社会的转型和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首先,法官,包括律师和法学家共同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为近代国家与法制的创建共同扮演着推动器的角色。他们使教会法体系成为一套以罗马法为蓝本的系统的、理性化的法律体系,剔除排他性力量的存在,为西方近代法律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法官成为国家对社会实施控制和管理的主要手段,最终导致近代“法治国”的出现。[13]11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西方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传统因素,法律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以及法学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已占据了核心位子。随着这种状况的发展,君主和市民阶层都竭尽全力争取在法学领域中的话语垄断权。于是,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在近代西方社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起初法律教育主要是在法律职业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或这些职业机构的‘行会’所开设的学校(比如英国的Inns)中进行的,而后来出现的大学法律院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这种职业培训的风格和方式。”[13]6
此外,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与教会办的大学相抗衡,他们创设了许多兼具教学与科研两种机构后来发展成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起初叫作studium generale,后来称为universitas)。“在1300年的时候,欧洲共有20所左右拥有较好的法学研究和教学力量的大学,到1500年时,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近80所。”[13]813世纪晚期,“法学也发展成了一门职业化的、规范性的诠释学(来自希腊语hermeneuein,意为‘诠释’);也就是说,一群职业人员被训练来根据普遍的、规范的法律和规则来决定具体案子。这样,教育不仅涉及有关成文法的知识(一个好的社会是如何建立的),而且涉及承认一个新案例为一特定种类的案例(它受一特定法律的支配)所必需的实践判断。”[30]111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一种向社会生活的不断“司法主宰化”(juridification)迈进的总体运动。通过并参与主宰这一过程,法官成为现代西方政治话语的代言人,他们把日常话语转化和重构成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作为法律这一元语言的诠释者,法官获得了把自身建构为一个独立的、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职业群体。[13]13
西方法官职业化的兴起与法官地位的提升是携手并进的;法官权力的增长与法官独立地位的巩固是相伴相随的。随着时光的流失,随着法官法律权威的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就越高。于是,法官的地位逐渐高出于其他公民,当法官作为优势民众的状况出现后,原始公正色彩已被阶级斗争的岁月洗尽。法官公正的信仰已不仅是一种抽象理念,它更多的是一种制度选择。统治者为了能适用法律对社会的控制,必须以一种与自己的统治理念相一致的法官制度来取代传统习俗的选举、任命或世袭规则。马克思·韦伯认为:“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只是这样的一种知识体系:它产生经验有效的可能性能够得到具体的保障。……所谓得到保障的法律,就是指存在一种‘强制机器’,也就是存在一些专职人员,他们随时准备适用专门的强制手段(法律强制)来实施法律规范。”[13]4可见,在西方法制发展史上,法官这样一个由专职人员构成的职业群体,其产生与发展是和西方社会的理性发展相契合的,他对近代西方社会的制度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政治法律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法官成为社会公认的有权力最终解决社会纷争的中间力量;二是法官能够满足社会为控制秩序需要而被设定为特定角色,如公平、公正、正义,等等。
在一个成熟的政治实体中,毫无疑问,法官是一种公权的参与资格。法官之为法治的支柱性载体,乃在于这种人为的设定和拟制足以让社会公众在同一法域之中占尽平等、公平、公正的利益,亦使得公众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共享民主、自由、参与、选举、被选举和执掌公权的好处。
收稿日期:2007-09-23
注释:
①See Homer's Description of the Shield:The Iliad,book ⅩⅧ.转引自〔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223页。
②而在阶级社会里,“法官并不是整个社会的代表,而是出身于数目有限的统治阶级,由他们带入法律的意识形态会强烈反映出那些阶级的看法”。参见〔英〕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③参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二编《雅典宪法》,转引自《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④见〔美〕Munroe Smith:《欧陆法律发达史》,姚梅镇译,商务印书馆民国32年版,第32页以下。
⑤指在特定案件中,在郡法院担任临时法官的领主,他们在伯爵的主持下进行审判,但又具有完全独立的地位。
⑥举凡同身份者、同职业者之间,或者城市市民相互间,或者在维护治安的目的下,根据自发性的誓约而协议成立的团体即称之为誓约共同体。〔美〕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