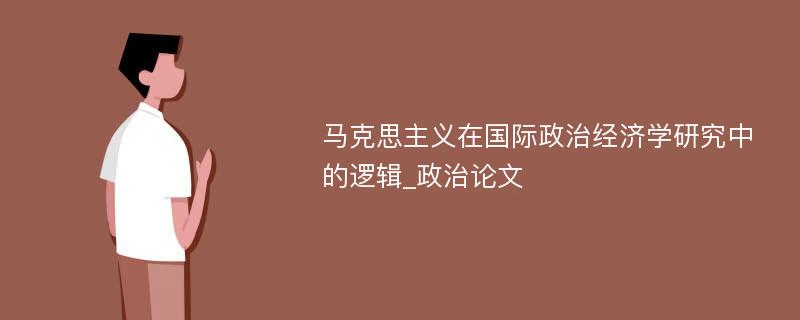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逻辑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国际或全球层面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从世界观来分类,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学派:自由主义、现实/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以怎样的逻辑来研究国际层面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呢?答案应该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但怎样从国际层面具体分析这种经济的决定作用和政治的反作用,马克思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只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简单提到:“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生产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更能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总体框架③的著作中,马克思以生产为起点④去发现具体生产中的生产关系以及阶级关系,从而发现生产中产生的权力关系、国家形态和意识形态;在国际层面,从国际分工中发现国际生产关系,最后去认识世界市场与危机。⑤马克思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从一般到具体,即把生产等抽象概念放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下去考察,考察在各种规定性或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是怎样进行的,从而去研究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⑥这种方法既强调了生产的基础作用,也重视生产之外既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反作用,从而避免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机械性。经济决定论否认既定的上层结构对生产的反作用,忽视历史的丰富内容与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基础决定论不是经济决定论,它强调既定的上层结构是过去生产的产物;但在某个历史截面,既定的上层结构对生产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由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是一个未完成的手稿,已经完成的部分内容体现在《资本论》中,而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直接有关的“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三个分册都没有完成。这让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缺少了许多直接借鉴的东西。虽然《导言》中零星地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但没有完整地分析阐述这一关系。比如,《导言》中谈到国际生产关系、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⑦但没有详细分析它们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导言》中谈及“第二等级的和第三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⑧但没有分析国际关系怎样影响。因此,还不能说马克思有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正如有人说,马克思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为后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方法和逻辑指南。虽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这些方法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些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但他们各自的观点都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思想渊源。如国际关系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是同一的(一元逻辑论)还是不同的(二元逻辑论),就是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存在的分歧之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亚历克斯·科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等人认为,国际政治体系具有自主性,与资本体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按不同的逻辑运行(二元逻辑论),前者表现为追求权力的相对优势、追求集体利益、固定于特定领土,后者是追求利润、追求个人利益、不受时空限制。⑨而威廉·罗宾逊(William I.Robinson)、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等人则认为,国际政治体系与资本的逻辑是一致的(一元逻辑论),国际政治体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⑩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同罗宾逊、哈特、内格里等人持大体一致的观点。(11) 因此,依据《导言》的提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是:以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生产组织方式为起点,分析由此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时,正因为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既定的世界秩序以及世界秩序影响下的国家对生产的反作用。简而言之,对国际层面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是围绕具体的生产方式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展开的。 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作品已经体现了这一逻辑,考克斯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就是典型著作之一。考克斯以生产为出发点,探讨了生产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由此探讨国家的形态和世界秩序;同时,他还探讨了世界秩序对国家、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国家在生产和世界秩序中发挥的作用。(12)另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也有类似的特征。“世界体系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建立在某种分工基础上的,即中心地区(通过工资劳动组织起来的生产)与外围(通过强迫劳动组织起来的生产)以及准外围(兼具两者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分工,通过世界市场交换来实现世界性生产过程。各种生产者的地位(即国家的地位)是由它们在这种分工体系内的地位决定的,由此形成了一种主宰与依附的关系;这一经济体系形成的国际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反过来维持与促进这种分工以及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模式,维系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13)在当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品(如《帝国》、《全球资本主义论》、《新帝国主义》)中,(14)都可以发现结合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核心来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逻辑。 下面结合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具体展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以及它们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应用,并且结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论述来演示这一逻辑如何运用在跨国生产、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发展这几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支领域。 二、生产:经济与政治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研究生产开始的。因为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其他经济活动的起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政治。在马克思的《导言》中,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的起点。马克思首先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15)这种物质生产不是“工艺学”上的特殊部门的生产,而是“生产一般”,(16)并且“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17)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生产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既不是特殊部门的生产,如工业、农业的生产,也不是超越历史时期抽象的社会生产。以这样的生产组织方式为研究起点,目的是研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是影响政治(政体和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同时,研究既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才能发现既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因素对生产的影响或反作用。所以,生产研究的逻辑必须建立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基础上,以此来研究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同时还要研究这一历史阶段特定的政治因素对生产的影响。这好比研究中国当今的生产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不能脱离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能不注重这一环境下的政治因素对生产的反作用。 按照这样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首先应从研究生产开始,以研究具体历史阶段的生产为起点来研究生产变革带来的政治影响。列宁在这一方面堪称典范。列宁在《帝国主义论》这本书中,首先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生产特点——民族疆域内以垄断为特征的生产,即生产与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资本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这一特点不同于马克思时代自由竞争的生产组织形式。列宁正是从他那个时代的生产特征出发,分析生产关系带来的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如金融寡头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殖民地争夺和大国的争霸直至战争。列宁曾批判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超帝国主义论”脱离生产历史阶段来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错误,批判他脱离了“20世纪初的历史的具体时代……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18)同时,列宁还十分注意政治因素的反作用。列宁从这种生产变革所带来的世界秩序的混乱和战争中看到了革命机遇,提出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开始革命的战略。这就是著名的“战争与革命”的命题。这个命题所体现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并不是缺乏经济基础的,而是建立在当时的生产特征基础之上。它所依赖的革命力量是当时社会生产方式下产生的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建立的新型生产方式是一种对旧垄断生产方式的扬弃。所以,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结合列宁的其他一些作品,这一著作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作品,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必须以生产全球化为起点,因为生产全球化是现在世界生产的主要特征。与过去生产过程国内化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组织方式不同,今天的生产全球化把各国生产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全球生产网络。(19)这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意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它所产生的全球性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政治影响都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问题。 从当代跨国生产出发,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提出了全球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新分析,强调了国家形态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时代的世界秩序观和新帝国主义观。(20)比如,考克斯提出:生产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已经形成了跨国管理阶级、中间阶层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全球性低层阶级;(21)国家的形态已经从福利国家转变为极端自由主义国家(hyperliberal state),(22)即目前人们通称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跨国的管理阶级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和新自由主义国家实行全球治理,并形成了一种帝国体系的世界秩序结构。这种帝国体系的结构“不等同于一些行为体,如国家或跨国公司,(虽然)这些行为体是这一体系的主导因素,但作为一种结构,这种体系超过它们的总和”。(23)简单地说,考克斯认为,今天的跨国生产已经产生了跨国的统治阶级和政体,使世界秩序和帝国主义发生了变化,不再表现为旧时代的帝国主义大国冲突,而是一种世界性的跨国垄断资本的集体统治,美国及其军事同盟是这种集体统治的最后军事强制力量。这种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并非个别,哈特和内格里也是从世界生产的变化出发,认为像一战和二战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失去了经济基础,当今世界秩序是一种全球资本的联合统治,从帝国主义向帝国转变。(24)威廉·罗宾逊也是这类观点的宣扬者。他认为,在“生产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的竞争与冲突呈现新的形式,不再以民族对抗来表现”,但“还存在着部分跨国资本与部分民族资本的冲突,还存在着跨国集团之间激烈的对抗与冲突,这种对抗与冲突更多地诉诸多种制度渠道(包括众多民族国家)来追求自己的利益”。(25)这种跨国垄断阶级的主要治理结构不同于传统的国家政体。它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制度形式,而是一个新兴的网络,包括西方大国以及一些超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论坛。经济论坛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等一些国际组织,政治论坛包括西方七国集团、经济合作组织、欧盟、欧安会等国际机构。这一新兴政体对全球的最后强制力依赖于美国的武力。跨国资本间的竞争主要是通过控制国家和跨国机构进行,而不是传统的帝国主义式的国家竞争与战争。(26) 这种一元逻辑论者的观点是:跨国生产产生了跨国统治阶级及其政治统治,今天的资本主义大国关系已经不具有对抗性,它们的利益关系在跨国资本的协调下已经融合,具有了考茨基所说的“超帝国主义”的特点(虽然所用的名称是“帝国体系”、“帝国”和“跨国国家机器”)。跨国资本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和美国这样的跨国资本的代理人国家来统治世界,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统治。应当承认,这样的观点仍然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与当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有区别的。因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建立在虚幻的设想基础上,当今的资本帝国论建立在生产全球化基础上,并没有脱离具体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生产方式。 持二元逻辑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政治结果有着不同的解释。比如科利尼科斯就坚持认为:虽然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一定的资本跨国融合,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对抗冲突仍不可避免。因为国家体系与经济体系是两个逻辑。前者需要资本为其权力竞争提供实力基础,后者需要国家为其提供保障。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三大经济中心的发展不平衡,阻碍着资本的世界统一进程,资本主义大国需要资本的积累为其提供权力竞争的实力,而资本需要国家为其提供积累的政治保障;各大中心的资本为了全球积累仍会利用国家为其积累服务,而国家需要资本的积累提升其竞争实力,两者的相互需要将会在21世纪导致资本主义大国间的冲突。虽然目前资本主义大国仍保持着合作状态,但这只是二战后美国世界霸权把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纳入其领导之下的历史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把这样的结果作为一个默认情景赋予优先性”。(27)在科利尼科斯的这一分析中,国际体系的自主性被认为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历史残余,对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仍然具有反作用;而且其观点所依据的基本理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规律理论——本身就含有阶级分析的成分以及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一般性描述。 三、贸易:作为生产的要素和实现的条件 从生产中考察交换,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对生产具有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反映的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在《导言》中马克思谈道:“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28)“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29)正是把交换作为生产的一个要素,才能发现贸易在维护怎样的生产和生产关系,才能发现贸易作为生产的一个要素和生产一起影响着政治;同时由于贸易的反作用,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权力关系对贸易的影响来发现政治对生产的反作用。马克思这种生产与交换关系的思想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框架。 国际贸易是国际交换,它是由具体的(国际)生产所决定的。从这一关系出发才能认识国际交换作为国际生产的一个要素的本质,也才能认识到国际交换对生产具有的反作用,或者说对生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这对于研究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等交换制度背后的权力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曾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对生产与贸易的关系做了精辟的分析,对政治关系的表述尤为透彻。自由贸易决不是自然秉赋形成的分工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的国际分工的产物。马克思批驳了“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的观点,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30)英国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巨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这要求有一个自由的贸易,废除谷物法;实现自由贸易不过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实现降低工人最低工资的目的,反映了英国的工业资本的要求和生产关系。同样,马克思认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31)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都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方式,都服从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关系,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内,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可以促进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所以在《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32)更进一步说,是由主导生产的阶级力量决定的。 在当今,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也要遵循上述逻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生产或分工的变化是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正是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和跨国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国际贸易出现了所谓的以产品周期、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为特点的新国际贸易形态。这些新型的国际贸易形态都是跨国生产的产物。这样,贸易作为跨国生产的一个要素前所未有地得到充分体现。而国际贸易制度发展恰恰在适应着这种生产的新变化,反映着跨国生产下的生产关系。在新一轮生产国际化浪潮中,国际分工呈现出分散化、复杂化的特点。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工序都通过国际外包和海外投资分散于世界各地,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生产链。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后工业化的状态,即主要从事研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主要的生产地点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原来关贸总协定(GATT)下的国际贸易制度已经不太适应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势,需要进一步修改国际贸易制度,以适应新的国际分工。(33)这就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所以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使新的国际贸易制度(WTO体制)扩展到投资、知识产权和服务业的根本原因。 乌拉圭回合谈判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准入门槛,大幅度地削减了关税,平均税率降低了40%,甚至有些产品的关税被彻底取消。这是自GATT成立以来第四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关税的大幅降低顺应了全球化生产要求,便于全球分布的生产进行顺利的交换,促进资本主义的积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订是对世界生产格局的重要促进。由于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所谓的“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在其国内经济中所占比例相对庞大,而且凭借技术和经验上的优势,跨国企业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服务业的开放有助于这些跨国企业扩大服务业出口,保证这种全球生产格局延续。《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签订也有助于促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的利益。生产全球化是在西方跨国公司主导下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把生产链分布于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进行资源配置,最大程度地利用各国的要素价格差异,实现利润最大化。《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有助于保障这种全球化的生产格局,减小各国对投资设置的各种限制,如出口比例、零配件本地化生产的比例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签订也是对跨国企业经济利益的重要保护。由于全球化生产的格局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的特点,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维护与全球生产相适应的贸易的开展,保障高额技术“租金”,从而保证全球化生产中跨国企业的利润和积累,控制全球生产链。另外,农产品贸易开放反映了跨国农业集团的利益。由于跨国农业集团在生物技术、育种技术、化肥生产等方面的优势,迫切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全球农业市场,这些集团成为WTO中农产品协议的积极促成者。所以,WTO新增加的一些主要内容(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协议和农产品协议)既反映了目前国际生产新格局的要求,也反映了主导全球生产的跨国资本的经济利益要求。 WTO反映的跨国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还可以通过观察不同的社会群体从新的贸易制度的受益程度体现出来。在WTO制度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益并不平衡。但在这不平衡背后是跨国生产的主导力量与非主导力量的收益不平衡以及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衰落。比如虽然发达国家大幅削减了关税,但残留的高关税产品仍然集中在纺织品和鞋类等对发展中国家比较重要的出口产品上,并且通常需要经过十年过渡期才完全取消。在货物贸易中,GATT/WTO倾向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自由化由来已久,有学者经过统计发现GATT/WTO虽然促进自由贸易,但促进的是西方企业占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在这一领域没有优势可言;而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鞋和一些初级加工制造业领域,发展中经济体总是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形或无形贸易壁垒的限制。(34)知识产权协议设置了较高的保护门槛,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的成本大大提高。在服务业上,WTO开放的服务贸易部门是金融、保险、电信等,但对另一些服务贸易部门如船运、建筑业等并没有开放。前者正是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后者是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服务业。这样,发展中国家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受益甚少。这一切体现着发展中国家及其相关群体在全球生产过程中处于待遇不公平的状态,因为它们不是跨国生产的主导力量。 如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次生产组织方式变革都会对旧的生产组织方式带来冲击一样,跨国生产对发达国家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带来了巨大冲击。WTO在促进跨国生产的同时,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工人失业率上升的现象,使过去受惠于传统生产组织方式的工人阶级经济利益受损。另外,WTO带来的跨国生产便利化还推动着原来以国家为基地的传统生产转向跨国生产,因为跨国生产带来的利润和竞争压力迫使原来立足于民族境界的企业也不得不转向跨国生产,否则将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如同历史上新生产方式冲击带来政治反弹一样,跨国生产必然带来政治反弹。反贸易自由化运动以及各种保护主义就是这种政治反弹的体现。它如同历史上手工生产的工人破坏机器生产一样,都是不满于资本主义带来的“创造性毁灭”。(35)不仅如此,建立在民族经济基础上的国家也受到了跨国生产的挑战。迎合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国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抑制贸易自由化意味着资本的“出走”和国家竞争力的衰落。所以,“两难”的国家不时在贸易自由化与保护主义之间迟疑摇摆,呈现出两面性。这都是既定的政治结构对跨国生产的政治反作用。 所以,只有把当今贸易放在全球生产方式中考察,才能看清全球生产过程中贸易制度作为中介的作用;从谁受益、谁受损、受益多少中,才能认识到当今全球生产关系的本质;从反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中,才能体会到政治的反作用。 四、金融:交换的中介和信用的工具 虽然与马克思时代的金融相比较,当代金融有了重大的发展,但如果仔细阅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我们仍可以发现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金融作为交换的中介和信用的工具与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生产方式的变化是金融制度发展的前提,同时金融也对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政治通过对金融的影响进而对生产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作为交换的中介,货币产生、发展与商品生产的发展相联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专门论述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货币的本质,即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产生在于解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货币的发展在于解决货币本身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内在矛盾。货币如果寄身于个别使用价值(黄金)之上,是用一种个别价值作为衡量社会价值的尺度;而价值是抽象的、社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36)但黄金的价值却是个别的和具体的,这就是货币的内在矛盾。正因如此,纸币可以作为货币(黄金)符号代替铸币行使职能。(37)当黄金无法满足商品生产发展带来的交易需要时,纸币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必然代替黄金发挥货币的职能。 当今的国际货币摆脱了个别使用价值(去黄金化)恰恰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是想象与观念性的,可以用纸币(货币符号)来替代的特点。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黄金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彻底地完成了货币虚拟化过程。这种货币的虚拟化除了政治原因外,经济上如果不是战后世界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巨大发展,造成的货币数量超出黄金供应,其完成过程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由此,这种虚拟化的货币价值在本质上只能由社会生产关系来赋予。因为价值本身就是社会的和抽象的,虚拟化的货币正好反映这一特性。这样,虚拟货币有利于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占主要地位的力量操纵货币发行以服务于其经济与政治利益。 如今美元行使着世界主要货币的职能。美元的发行主要由在世界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和“华尔街”——跨国金融资本集中的体现——来决定,因而是服务于它们的经济政治利益需要的。它们通过操纵货币发行权享受着重大的铸币税特权。美元的特殊地位使得美国不受外汇储备短缺的制约,可以避免巨额贸易逆差可能导致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同时,美国却能通过贸易逆差和发行国债,获得外部大量的实物资源和低息资金。而且,美国通过掌握着这种国际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38)——的政治权力,为其拉拢盟友、打击敌人、扩充武力、担当世界警察提供了重大的便利和资源。因此,虽然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美国不愿放弃美元带来的特权,仍要维护现存的金融权力结构。任何影响这种特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都会受到美国的阻扰。这充分体现了既定的权力结构的反作用,但带来的却是世界经济经常性的不稳定和不公平。 美元的变化不定给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是不确定性,影响着国际经济的稳定运行。美元升值带来的是世界性紧缩或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美元贬值则带来世界性通胀或经济泡沫。变化不定的美元还带来金融投机。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都与美元的币值变化有一定的关联。在这种动荡的国际金融局势下,许多经济能力较弱的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获得美元必须提高利率,必须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出口商品;否则,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就必须忍受经济紧缩和失业以及债权人对其经济主权甚至是政治主权的限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身受冲击最大。 相反,跨国金融资本则享受着巨大收益。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曾指出,“在这种不确定的条件下……唯一获益的群体是金融从业者,它们是鲜有破产的一小撮人……银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润。银行业务得到巨大扩张并且为内幕消息提供者、研究者、评论者和其他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信息和咨询需求的人创造了新的岗位和机会”。银行还“发明了各种新的工具……最初是应对通胀或政府税收与管理来减少自身的弱点,后来是针对不确定性进行套利”。(39)西方金融机构利用这种金融创新和衍生品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却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破坏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许多跨国金融机构管理者收入依然巨丰所引起的社会愤怒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可以体现出谁是现行国际货币体制的受益群体。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谁受益与谁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有着必然的联系。 因此,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当今国际货币价值的变动使谁受益、谁受损,其中的生产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它对世界性贫富分化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它在促进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上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当今国际金融的另一个方面——信用的研究也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启示。马克思对借贷资本作用的分析都是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在现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资本要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40)“银行和信用……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41)即它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和欺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对当时的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做过分析。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基础上的”。第二,流通费用的减少,它又包括:“A.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B.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了”。第三,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使个体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第四,为单个资本家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财产和劳动的权利。(42)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使货币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逐步平均化了;提高了货币资本的使用效率;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条件;为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提供了条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社会化或更新形式发展提供了条件;加剧了贫富分化。“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因此,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具有“骗子和预言家”的二重性。(43)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其信用制度的作用也在相应地发展。列宁曾经分析他那个时代银行的发展和新作用。随着银行的集中和与工业的融合,“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44)这种支配有助于形成由垄断金融资本控制的资本主义新型生产组织——卡特尔、托拉斯等。由于此时银行作用的变化,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分享的利润远大于过去的中介者角色。“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45)更重要的是,导致了“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46)由于这种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能力巨大,它更需要海外市场和原料,向海外输出资本、控制殖民地和取得势力范围成为保障国内再生产得以延续的基础。这一切是消除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缓解政治危机的重要表现。在国际关系上,这导致了资本主义大国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对他那个时代信用制度作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对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此时的金融资本没有导致利润的平均化,而是造成了垄断利润的产生。第二,导致金融资本对其他社会资本的优势和对社会的统治。第三,导致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和帝国主义战争。 当代的国际信用如何体现其“二重性”,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集中体现了当代国际金融的新特征。这一金融市场把世界性的资本相对集中起来,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成为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新、更社会化形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欧洲美元市场创造的各种信用手段和虚拟资本为跨国投资与并购、贸易扩大了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在真正意义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推动了全球生产发展。其次,它为消除以民族国家为基地的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创造了条件。比如,获得国际信贷的国家必须面向国际生产,否则它们会因无法获得偿还债务的外汇而陷入债务危机。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将面临国际债权人提供的调整方案。“华盛顿共识”可以说是这种调整方案最典型的代表,其核心就是拆除债务国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藩篱,使国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全面适应世界市场。再比如,原来西方国家以国内生产为主的企业,如果不加入全球生产的潮流,将在竞争中因成本较高被淘汰,而跨国生产离不开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这一切都在逐步消弭立足于民族国家的传统生产组织方式,也使得跨国金融资本成为控制跨国生产的最后主宰。 同时,当今的国际金融也是制造危机与欺诈的最有力工具,与马克思称之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47)高度契合,是一个最具赌场性的领域。(48)货币资本作为一种商品,由于增殖的目的性,其本身的生产过程开始与全球生产过程渐行渐远,且相当部分脱离了实体经济;各种金融衍生品和创新在扩大信用手段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欺诈方式。全球市场的赌博性特点已成为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成为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掠夺对象。这一切都说明,国际金融在促进经济的全球化、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积累工具的同时,也不断地为全球经济制造危机。 当今的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正复制着一百多年前民族垄断资本在国内经济所做的一切:资本的集中和对生产的控制。不同的是,当今跨国金融资本设计了一个更高级、更精巧、更复杂的虚拟市场,涉及的资本规模更庞大、范围更广泛,对应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跨国生产,体现的是资本的世界性统一趋势。这种跨国垄断资本的经济影响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什么意义?这就又回到前面所说的一元逻辑和二元逻辑的争论上。一元逻辑论认为,跨国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跨国生产将形成资本的世界联合,导致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全球政体,造成资本对世界的集体统治,而不再有资本主义大国为竞争市场与资源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冲突。二元逻辑论认为,各资本主义大国为了争夺资本全球统一和积累主导权,以壮大自己的竞争实力,仍会进行帝国主义式的冲突与战争。 五、发展:生产方式和分配的结果 从马克思到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有所变化的,但在本质上都与资本主义生产相联系。在不发达的原因上,马克思认为,不发达是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或社会结构造成的。而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在发展道路上,马克思认为,只要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国家也可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战后依附论者认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只有通过割断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独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引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实现发展。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依附论者认为,在不割断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也能出现依附性发展。 马克思对不发达民族落后的原因分析是从其传统的社会生产模式来认识的。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的结果》中谈到,“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9)马克思认为,虽然英国在印度发展资本主义既不会使印度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也不会使他们的社会状况得到改善,但可以发展生产力。(50)这里马克思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不发达民族在外部资本主义进入后,打破了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体制,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建设,最终会和发达国家一样(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把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描绘得与发达的英国一样)。马克思把印度的落后事实上归咎于印度的传统生产方式。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说得更明确。在谈到当时相对比较落后的德国时,马克思说,像德国这样比英国落后的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51)因此,马克思主要把不发达归因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 战后的依附论者更多是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角度,从这种生产结构的分配中来阐述不发达原因。他们认为,不发达是因为西方大国只想把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会在发展中国家中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附理论之父——保罗·巴兰(Paul Baran)就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因为它们向发达国家“提供大量的利润和投资出路”,是发达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必要腹地。因此,美国等西方统治者竭力反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52)在巴兰看来,西方资本主义需要不发达国家维持传统的生产方式,发展中国家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为本国依附于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积累,而后者则直接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提供经济盈余。因此,依附论者基本上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不发达国家不同层次的生产方式嫁接在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生产方式上,由此通过贸易、投资方式来榨取大量经济盈余,导致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充分化,只能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无法成为与发达国家比肩的国家。这一思想源自“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即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分,也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分。由于非资本主义成分为资本主义成分提供积累,资本主义成分为世界经济提供积累,因此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 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原因,依附论者往往认为,国际资本要控制发展中国家政治,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才能从发展中国家榨取经济盈余。这种政治结构从过去的殖民统治过渡到独裁专制体制。与此同时,国际资本还通过其政治代理人打击与孤立一切企图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另外,为了顺应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国际资本还向发展中国家传播一种“可口可乐”文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在思想上认同这种依附、政治上接受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消费上模仿发达国家的模式,从而在精神上麻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消除其反抗与革命的意识,通过追求西方的消费品来实现资本主义世界性再生产,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全面控制,阻扰发展中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 依附理论虽然在不发达原因的分析上与马克思的论述有一定的差异,但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看,仍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逻辑。依附理论主要以资本主义全球生产方式导致的分配结果来认识不发达原因。分配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是生产的一部分,“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53)因此,依附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或者说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结构产生的分配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在发展道路上,马克思的观点与依附理论也是有差距的。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的结果》中,马克思谈道:“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54)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5)“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56)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一种“阶段论”,只有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引入,发展资本主义才是实现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为今后的社会变革创造了物质条件。 战后早期依附理论者认为,由于西方大国需要保留发展中国家的混合经济结构为世界经济提供盈余,不可能让它们充分发展,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脱钩,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其他发展模式都有局限性。(57)简单地说,这是一种“跨越论”,就是不发达民族独立后首先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摆脱依附;之后不再经历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阶段,而是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以实现发展。这一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思维是一致的。 20世纪60~70年代,面对西方跨国公司投资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带来的发展,特别是东亚奇迹的出现,一些依附论学者提出了“与依附相联系的发展(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的理论。其提出者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认为,某些发展中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结构下,可以存在依附与发展共存的现象。这一历史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中威权政府、跨国资本与新兴中产阶级(即与跨国资本相联系的民族工业资本)形成相互配合的政治结构。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威权政府保证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执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投资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希望这些国家呈现一定的经济发展,以保证其产品的销售和生产得到延续与扩大;当地现代民族资本通过与跨国生产的联系,承接跨国公司的低端生产环节也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出现依附性发展的状态,即有所发展但却缺乏自主性,如缺乏自主技术和金融机制,受制于跨国资本和国际市场,并且分配上出现严重两极分化。(58)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他也强调,依附与发展可以共生,这种依附性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外围国家中本土资本、跨国资本和国家资本之间存在一种合伙的关系。(59)这时的依附理论已经不再完全排斥世界市场和跨国资本,而是承认跨国生产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依附性发展的观点影响着当今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认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孤立或脱离(于世界市场)的企图将只意味着全球体系的一种更加残酷支配,一种向羸弱和贫困的倒退”。(60)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改革开放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这一思想有类似性。 战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虽然与马克思的论述有一定差距,但他们都是结合具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结构来探索发展道路的,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即强调依据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具体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来探讨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逻辑探讨国际层面的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以具体生产(方式)作为探讨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的出发点,具体的生产决定着交换、金融与分配等生产(实现)的条件,体现着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着上层建筑。同时,注意既定的政治结构和因素对生产具有反作用。这样,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就是,以世界范围内具体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探讨各个历史阶段国际生产的不同特征,从这种特征中去分析国际贸易、金融和发展(分配)的本质,探讨国际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分析国家和世界政体的形态,研究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大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的特点等。同时,在具体环境下分析政治结构与因素对生产组织方式及其实现要素的影响。依据这些逻辑,我们可以判断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成分有多大。囿于篇幅,本文较少探讨具体环境下政治因素的反作用,也没有涉及与生产相关的其他因素如观念(意识形态)。观念的因素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重点之一。 ①这种分类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这里需要说明:《导言》中文版把“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译成“生产的国际关系”,但为了防止歧义和便于理解,笔者译为“国际生产关系”。《导言》与此有关的英文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ch01.htm#3,登录时间:2015年4月6日。 ③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资本论》(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马克思要写但没有完成的庞大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框架下。因此,《导言》更能反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总体框架。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1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7~2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7页。 ⑨有关论述参见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科利尼科斯的观点参见Alex Collinicos,"Does Capitalism Need the State System?" in Alexander Anievas,ed.,Marxism and World Politics,London:Routledge,2010,pp.19~21。国际体系的自主性被这些学者认为是历史遗留物,是历史上经济基础的产物。它来自封建时代,在资本主义初期得到加强,由于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得以遗留下来,对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仍然具有反作用。因此,二元逻辑论不能被认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虽然有人(如威廉·罗宾逊)认为它落入了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窠臼(William I.Robinson,"Beyond the Imperialism: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Transnational State," in Alexander Anievas,ed.,Marxism and World Politics,pp.64~68),但它与现实主义解释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 ⑩威廉·罗宾逊的观点详见William I.Robinson,"Beyond the Imperialism: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Transnational State," pp.64~68。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观点参见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21~239。 (11)考克斯的观点在《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一书主题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参见Robert W.Cox,Productions,Power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p.1~9。 (12)Robert W.Cox,Productions,Power and World Order,1987。其实,考克斯在这本书的主题中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表述得很清楚(见该书第1~9页),而且整书的章节都是按这一逻辑编排的。特别是考克斯在《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一文中所绘的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影响的图形已经把这个关系直观地表现出来。参见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and World Orders," 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221。 (13)参见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2000年版。 (14)参见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2000;威廉·罗宾逊著,高明秀译:《全球资本主义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2009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页。 (18)《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407页。原文中“现有”二字使用了黑体字,这说明列宁对考茨基不关注现有的经济状态来设想世界政治状态的批判。 (19)这种跨国生产的特征参见李滨、陈光:《跨国垄断资本与世界政治的新变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120~144页。 (20)战后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国际层面的阶级分析以中心—外围这样的结构来划分,这种划分依据的是国家在国际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全球生产的角度出发,以全球性社会力量来划分阶级,这与过去以国家为标准进行的阶级划分是不同的。 (21)这些阶级构成及其分析详见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pp.359~390; 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p.234~236。 (22)这是考克斯对撒切尔—里根模式的国家形态的表述,因为他按照传统的政治分类把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称为新自由主义国家。两者的区别参见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pp.285~289。 (23)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229. (24)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pp.3~21,pp.219~325. (25)威廉·罗宾逊的观点参见William I.Robinson,"Beyond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Transnational State," p.63。 (26)有关跨国国家的概念及分析详见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110~183页。 (27)Alex Collinicos,"Does Capitalism Need the State System?" pp.16~25.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7页。 (33)Jane Ford,"A Social Theory of Trade Regime Change:GATT to WTO," International Study Review,Vol.4,No.3,2002,pp.122~133. (34)有关分析参见Hans-Jurgen Engelbrecht and Christopher Pearce,"The GATT/WTO Has Promoted Trade,But Only in Capital-Intensive Commodities!" Applied Economics,Vol.10,No.39,2007,pp.1573~1581。 (35)参见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键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47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57~15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60页。 (39)Susan Strange,States and Markets,London:Pinter Publisher,1993,pp.109~110.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68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15~520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21页。 (44)《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46页。 (45)《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68页。 (46)《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6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21页。 (48)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的金融领域研究的西方学者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苏珊·斯特兰奇。虽然她的研究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特点,但却充分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赌博和欺诈性的定性。参见Susan Strange,Casino Capitalis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6; Susan Strange,Mad Money: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6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71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0页。 (52)保罗·巴兰著,蔡中兴、杨宇光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6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第1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73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0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1页。 (57)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0~488页。 (58)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Alfred Stepan,ed.,Authoritarian Brazil,Origins,Policies,and Fu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144~152. (59)Peter Evans,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State,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60)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p.284.标签:政治论文;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社会帝国主义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贸易金融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