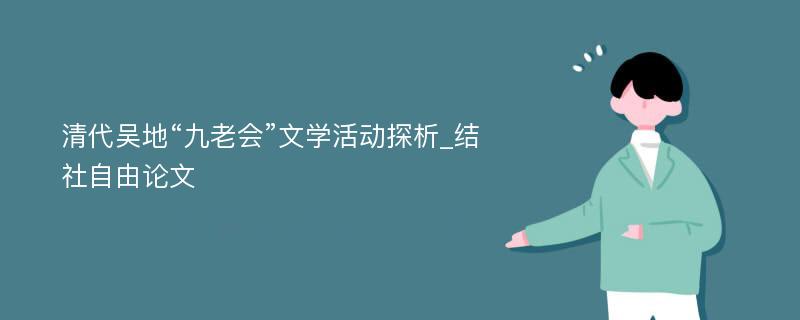
清代吴地“九老会”文学活动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文学论文,九老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09)01-0090-04
清代吴地出现了大量的结社活动,其中九老会作为耆老诗坛十分活跃,显示出吴地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人文气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历史学、社会学和地域文化学的问题,也是地域文学史上足可书写的一章。但对于清代吴地九老会的产生背景、活动形式、表现特征、诗歌价值等问题,至今尚缺少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探讨,一个极具认识价值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似乎没有能够进入研究领域。本文从吴地文献记载的相关资料出发,试图通过一定的考释,形成清代江南吴地九老会的基本镜像。
一、吴地九老会产生背景及在清代之繁兴
“九老会”是中唐以来文会的传统形式,“昔白太傅居香山,与胡杲诸人为九老会;李文正罢相,居京师,与张好问诸人亦为九老会;文潞公在洛下,与富郑公诸人为耆英会,史册艳称之”[1]卷三《尊德九老会序》。南宋以来,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原一带的文化家族也逐渐迁移到吴地,与环太湖一带原有的文化世家融合,使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而数百年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对科举的虔诚追求,对文化型社会的持久建设,使吴地崇文风气更加浓厚,这极大地促进了文人结社。除了一部分带有明显载道救世色彩的党社外,文化休闲类的文会也不断出现,九老会由此应运而生,如明成化年间常熟的虞山九老社、松江的莺湖九老会以及湖州乌墩九老会等。
清初朝廷为了维护新政权,实行了政治和文化的高压政策,屡申严禁讲学立盟结社之令,但事实上其时“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2]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至康乾时期,随着清王朝政治地位的巩固,文化上也兼施怀柔之策,甚至将“九老会”形式取为皇家所用。乾隆帝曾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十六年,两度邀请皇室及文武老臣年七十以上者,为皇家“九老会”。在此影响下,民间九老结社风气就更兴盛了。可以说,康乾盛世也是吴地九老会立盟最繁兴的时期。清康熙年间,昆山周庄屠彦征、郑任、徐汝璞等老诗人仿白居易香山九老会及文彦博、司马光洛阳耆英会故事,举耆英社;康熙三十四年(1695)顾汧自礼部致仕,归后“得读彭访濂、尤沧湄诗集,皆有悠然自得之致,招集小园,为九老会”[3]卷首《凤池园诗集自序》;乾隆十二年,沈德潜从京城回苏州,创二弃草堂九老会,其《二弃草堂燕集序》对此记载甚详:
丁卯正月,德潜值乞假归里,越五日,拜横山叶先生神位于二弃草堂,先生故栖息地也。时先生辞世四十五年,门下士存者九人,咸在列:叶太史长扬年八十一,顾处士嘉誉年七十九,张处士釴年七十六,德潜年七十五,谢徵士淞洲年七十一,并年六十九者沈徵士岩、李徵士果,年六十七者为薛徵士雪,周太学之奇年最少,亦六十五,而先生孙启祥年七十一,十人共七百二十有三,称盛事焉。昔白太傅居香山,结香山九老社,富郑公居洛,结洛下耆英社,彼与社者,多名臣硕德,既已功成不居,辞荣耽寂,颐养老寿,文酒燕游,后人披览图画,犹津津道其年命之多与邱园之乐。以今方古,乌敢较量,然太傅、郑公惟联一时友朋之乐,而今兹九人,皆向时请业于二弃草堂者,讨术业之渊源,合通门之情好。横山一脉,犹在人间,此又太傅、郑公所未闻,而今兹所独有者也。[4]卷九
乾隆十四年,常州有庄氏南华九老会;乾隆十六年,无锡举秦园九老会;乾隆二十四年京口张学林退居家乡后,仿洛中九老会,召集乡贤九老集会吟诗。其云:“洛中九老会,昉于香山,时唐会昌五年也……乾隆丁丑春,余自洛回里。越二年,病粗痊,年七十有一,里中戚友齿叙得九人,仿行之。名位远不古若而以品以年亦有足记者。去岁今冬,两会举行已三禩,间有推迁,今岁稍增一二人。春月,迎銮无暇,秋补行之,预赓八韵,以俟希属和焉。”[5]卷四《九老会诗(并序)》由此序不难看出结社的时间应在乾隆二十四年,参与人数最初为九人,后增加一二人,活动颇为频繁。
清代中期以后,吴地文会雅集仍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九老会也有繁衍之势。嘉庆九年(1804),上海便两次成立九老会。首次在嘉荫堂举行,由李廷敬倡导,廷敬时里居,同治《上海县志》载:“嘉庆九年元旦,松太道李味庄廷敬延邑中八十以上者七人饮于嘉荫堂,百有四岁者凌鹤辉,百岁者郑盈山,九十者全志南,八十四者陈熙,八十一者胡絅文、乔凤山,八十者桂心堂,而岷州知州乔鸥村钟吴年六十四,味庄年六十二亦与会,称九老。”是年花朝节时又于李氏吾园复举九老会,但成员有所变化。县志载:“鹤辉、盈山、心堂外,益以沈文炘,年百有三,陈叙东八十七,唐尔孝八十,桂海七十一,即心堂弟也,杨继东亦七十一,黄荣堃六十一,凡九老,绘图赋诗,传盛事焉。”[6]卷三十二《杂记》又唐尔孝亦有诗载其事,其诗题云:“甲子春花朝,笋香主人集沈光耀(一百三岁)、凌鹤辉(一百三岁)、郑盈山(一百岁)、陈叙东(八十七岁)、桂一枝绥寰昆仲(八十岁、七十一岁)、杨守愚(七十一岁)、黄绩葊(六十一岁)及余作九老会于吾园,笋香用洪北江太史留别韵纪盛,越四日,为余八十初度,以诗见贻,即次元韵奉酬。”道光二十年(1840),周萼芳偕诸友于松江举九老会。《华亭县志》载:“道光庚子,周贡生萼芳偕其友范少湖蕃、张远江鸿、吴韵亭墀、沈子耘履田、冯北垞东骥、曹次微垣、凌昂之若驹、张匏舟铭为九老会,而黄砚北仁、唐吟耕曦、姚敬修培柱、侯简亭法地先后与焉。诸人年皆六十以上,或逾七十,鬓发不脱,齿不危,手足皆健,精神不衰,又皆能诗。其会也,岁不恒举,举必作终日饮,饮必成诗。”道光年间,潘遵祁与苏州里中耆旧也结为九老会。
实际上,除以上明确标目的“九老会”外,吴地还有不少与之性质相似的怡老文会,如康、雍间吴江沈凤举、顾寿开、许硕辅、吴惠、吴然、孙元、赵文然等“十逸”创“岁寒吟社”。根据《江苏诗征》卷一百称许硕辅“晚年与同里沈餐琅、吴月轩、沈勉庭、顾玉洲诸前辈联岁寒吟社”和硕辅《岁寒初集即事》所云“屈指十数人,白首敦同气”,“首集恰九老,风流企前辈”,可以推定,该吟社也正是仿九老会的形式而建立的。另外,乾隆三十四年,松江李宗袁集里中老人举诗会,参与者共十九人,规模超过一般九老会,乾隆三十五年顾建元诸人在梁溪创立碧山十老会,道光年间潘奕隽为吴中耆旧之冠冕,常与苏州文士海内名公卿宴集,多会于沧浪亭。陶澍重修沧浪亭,创五百名贤祠,落成之日,举五老会,光绪十年顾文彬、潘遵祁等在苏州举七老会,遵祁有“甲申立夏后一日,松窗娑罗花开怡园,主人携尊花下举七老会,即席呈和”诗。凡此种种其怡老性质和活动方式俱与传统的九老会无异。从另一角度,它恰恰证明九老会在吴地影响之大,繁衍力之强。
二、清代吴地九老会结社活动的特征
吴地九老会作为一种结社活动,有继承和沿袭中唐以来香山文会传统的一面,同时也必然受到特定时空、特殊地域文化的影响,打上清乾嘉以后江南农商经济特别发达、学术艺文高度繁荣、自然环境清嘉幽美的印记。吴地“九老会”无疑是传统文化与吴文化交融胚育的产物,是一定历史时期某种特殊文学现象的指称,有其自身的一系列特征。这种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怡老娱情
与清初山河板荡之际出现大量遗民诗社的背景完全不同,九老会几乎可以说与承平时代共生。在前列的清代吴地九老会中,可考的最早立盟在康熙三十四年,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事实。此时干戈扰攘之气已歇,慷慨悲歌之声渐远,慎交、原社、云门、读书、雪苑、惊隐、东皋等具有遗民色彩和激情的社局都已退出三吴和两浙,朝廷文网渐开,逐步显现出重建文化的态势,期待着礼乐弦诵之声四起于大江南北。而一批江南士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新朝廷下的既得利益者,在致仕之后更放下经邦济世之累,乐于以一定的形式表现“闲”与“逸”的姿态,既要在政治上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安全空间,也要在生活上找到切实的消闲自适的路径,因此九老会就成为最好的形式和最佳的选择了。九老会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怡老娱情的需要,“诗酒流连”成为最重要的关键词,也是最基本的活动内容。康熙朝昆山九老之一陶唐谏的《文郁堂耆英社集诗》颇能表现觞咏怡性之状:“寻盟久矣属骚人,今日多君气谊真。社结香山诗一首,觞流曲水酒千巡。金茎露浥休夸寿,宝剑光韬漫说贫。唤我鸟声春正好,莫教寂寞负花晨。”这一九老会的活动地点后移至徐汝璞宅怡顺堂,屠彦徵作《怡顺堂社集诗》云:“文坛月夕逼中秋,风雅壶觞分外幽。长使清樽饶白发,直教北海逊南州。联吟思出高云迥,纵饮身忘冷露流。珍重主人休恋客,安心坐守药炉头。”管渊同题诗云:“筵开从日午,洗盏月初悬。露湛光如玉,觞飞酒似泉。分题愁险韵,接座逊高年。今夕知何夕,重逢洛下贤。”在这样的场合,分题限韵吟咏是作为文会诗社的必要活动内容,也是诗人抒发生命性情、展现个人才华的手段,而觞飞酒泉则既是现场氛围的创造,也是浪漫情趣的激发。这种一时诗酒、率真娱情的状态在清代吴地九老会中可谓是最普遍的情景。
2.家族聚合
九老会的参加者一般是具有诗歌创作才能的六十岁以上的致仕官员和当地耆宿,但由于清代吴地文化家族高度集中,高门族内往往英才耆宿孚望里闾者甚众,因此一门之中就可能出现诸老雅集的盛况,甚至产生家族性九老会。清代吴地最有影响的家族九老会是无锡秦氏九老会和常州庄氏九老会。秦氏九老会举事在乾隆十六年。该年乾隆帝南巡,驻跸无锡秦园(寄畅园)。秦氏乃江南最著名的科举家族、文化世家之一,影响甚巨。乾隆帝至时,秦孝然率族人六十以上者九人于园门迎驾,乾隆帝将其视为九老会,制诗褒奖,有“近族九人年六百,耆英高会胜香山”之句,孝然、实然、敬然、荣然、寿然、瑞熙、芝田、东田、莘田九老奉命和诗,成寄畅园九老会。关于常州南华九老会,阳湖张惠言《南华九老会倡和诗谱序》云:“庄氏于吾乡为故家,科第仍显,文章行谊,冠冕士类。”[7]62洪亮吉亦有《南华九老会倡和诗序》,其中俱载九老之名:“乾隆十四年,吾乡庄氏之致仕居里者凡九人:曰礼部郎中清度,年九十;曰福建按察使令翼,年八十四;曰临洮府知府祖诒,年八十二;曰黄梅县知县赠文选司主事枟,年六十九;曰密县知县封福建台湾兵备道歆,年六十六;曰开州知州学愈,年六十三;曰湖南石门县知县封甘肃宁州知州柏承,年六十三;曰射洪县知县赠顺天府南路同知大椿,年六十二;曰温处兵备道封礼部右侍郎柱,年六十。因为南华九老会,各系以诗。”[8]卷五《南华九老会倡和诗序》此次南华九老会后,另有同族年及六十以上耆德能诗者二十一人虽未能与会,但纷纷依韵唱和,使南华九老会成为乾隆江南诗坛一大盛事。常州庄氏集一族之耆老将传统结社形式发挥到了极致,显示出家族文化的特殊的聚合力和传播力。
3.园林雅集
文人群聚于幽静清嘉的场所吟诗作文之风由来已久,从魏晋七贤的竹林啸傲到王羲之兰亭集会,从白居易香山结社到顾阿瑛玉山雅聚,都以园林山水为活动空间。明清时期的文人结社延续了这一传统,有的集于山林,如常熟虞山的拂水山房,一直成为佛水社活动之所;有的集于水畔,环太湖一带有难以尽数的小筑可供诗人流连,青溪吟社、蓉湖吟社等由此得名;有的集于佛寺,如曹时中安耆会先后举于钟贾山之寿安寺、小横山之小山寺,十郡大社举于半塘寺,瞿源珠诸人结社于潮音寺等;但更能让文人结社增添诗酒风流色彩的则是吴地在在皆是的园林。在一定意义上,园林是隐逸文化的产物,是士大夫为求隐居乐趣而构筑的心灵绿洲,“士大夫解组之后,精神大半费于宅第园林,穷工极丽,不遗余力”[9]卷三。清代江南,几乎每一个结社活动都与园林有关,如几社常会集于松江南园,王晨、归庄结社于硕园,徐乾学耆年会举于遂园,吴门七子社集于鸥隐园,廖景文诸人社集于香蕙园,贾应璧诸人社集于栖隐园,听社会集于无锡辟疆园,顾建园诸人的续碧山吟社集于慧川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九老会同样多在园林举行社事活动,如秦氏九老会于秦园,南华九老会于漆园,耆英社九老会于兰芷轩,续碧山吟社诸老会于惠山之麓。嘉庆九年,松江九老会有三位百岁诗人与会,王应桂有《甲子花朝吾园中集百岁翁三人作九老会主人赋诗纪事用作长歌鸣盛》云:“甲子春,花朝日,花扑玉缸春酒热。吾园开,连翩九老相将来。”唐尔孝同题诗云:“争妍斗艳李桃荣,疏影高枝梅独瘦。初日丽光辉,新年甲子开。名园花放满春台,鹤发童颜三老来。”由此可见,诸老雅集于园林最能够进入现场情景,在与自然环境的交会中,既得到隐逸意味的满足,又得到山水物态的融摄,获取最大限度的审美享受。
4.绘图纪盛
明清时代江南社团在活动时,往往把社集状况以绘图方式纪事,并逐渐形成传统和特色。明代天顺时,昆山斯文会,曾“绘图纪盛”[10]卷四十三《斯文会觞咏图序》。成化年间,以秦旭为首的无锡十老创立碧山吟社,长洲沈周为之图,江左传为佳话。弘治年间瞿霆致仕归里,结七老会,“图画赋诗,时以为盛事”[6]卷三十二《杂记》。清康熙年间,徐乾学举遂园耆年会,有“遂园修禊图”[11]卷六。常熟吟梅诗会,“倩石谷子作《夏五吟梅图》,题咏者十数家,悉海内知名之士,至今传为韵事”[12]卷十三。道光年间,潘奕隽举五老会,好事者遂绘为《五老图》。太平盛事,贤达风流,一时传为佳话。光绪三十三年,陈去病诸人在上海举神交社,也绘有《神交社雅集图》,柳亚子先生又为之作《神交社雅集图记》。“绘图纪盛”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清江南的结社史,为结社活动雅中增雅。这一文化传统源于白居易香山九老会,曾绘图纪盛,成《九老图》,故清代吴地九老会几乎无不为之绘图,如康熙间昆山耆英社集兰芷轩,与会者用白香山诗为起句,各赋二绝,毛莹子锡年为之绘图。乾隆三十五年,碧山十老会绘十老图,以图系诗。道光二十年,松江周萼芳举九老会,画工为之各绘一图,萼芳乃集诸老所作诗与图一并梓之。嘉庆九年,松江李氏园林九老会,有赋诗绘图之雅事。而道光间潘奕隽、陶澍等结五老会,有《沧浪五老图》:“前内阁中书潘三松先生奕隽,己丑进士,年八十八,时方坐亭上,右手倚石床而弈;与之对局,前刑部尚书韩桂舲先生崶,丁酉拔贡,年七十有一;坐水窗,持竹竿而钓者,为前山东按察使石琢堂先生韫玉,庚戌进士,年七十有二;其一偃仰于笋石间,手书而观,为前山东道监察御史吴玉松先生云,癸丑进士,年八十一;最后一人,捻髭而行吟,蹙然若有所思,画手谓此老江苏巡抚,前壬戌进士云汀陶某也。”[13]卷四绘图纪盛,扬翊风雅,表现出江南文人特有的情趣,为地域文学史留下了永久的见证,为诗画艺术相彰提供了生动的范本,也为江南艺林增添了许多具有历史内涵的话题。
三、对清代吴地九老会诗歌创作的评价
九老会和形形色色的怡老会在清代吴地的繁兴,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学现象。虽然所有的九老会和其他诗社、文社一样,都是以一定的文学活动为支撑的,但与八股文社具有强烈的功利指向不同,与其他诗社具有较为鲜明的文学诉求也不同,九老会的诗会形式远远大于了内容,文学活动在这里表现出明显的工具性。也就是说,诗歌创作在九老会主要只是创造一种社会性活动现场气氛的方法和工具,具有鲜明的装饰作用。
九老会诗歌以抒发林泉之乐、雅集之欢、老至之情的作品为多。康熙三十三年,徐乾学在昆山遂园举办耆年会,有《遂园诗》云:“胜集群公共采兰,杏花烟雨系青翰。归田发渐惊全白,望阙心还抱寸丹。佳节啸吟行屐健,晚春禊祓袷衣寒。酒酣莫漫言辞去,指数东吴此会难。”无锡秦松龄参与了遂园耆年会,作《甲戌上已玉峰徐健庵司寇果亭中允盛诚斋侍御再举耆年会同诸公燕集遂园各赋二章拈兰亭为韵》云:“风光上已共追欢,况有名园傍翠峦。花底移舟闻笑语,雨中扶仗看檀栾。半生朋旧知心少,百里江乡会面难。何幸荷衣参末坐,一时投契比金兰。”参与遂园会的一批江南耆儒皆是昔日朝廷重臣,历经风波的生命终于在家乡的林亭盘栖,长期以来的政治生存焦虑已在日常性和审美化的江南生活中淡化,他们需要用一次次“朋旧知心”的耆年雅集,在杏花烟雨,名园翠峦中,在对香山之风的回忆和追攀中,使最后的时光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化境,实现自我的终极关怀。
与遂园耆年会的作者相比,一般九老会诗歌往往较少“归田发渐惊全白”的感慨和“望阙心还抱寸丹”的源于体制意识的表白,更多的是沉浸于聚会氛围的欢乐,如涂汝璞《花朝耆英社集漫赋》:“为欢无计待如何,月夕花朝莫放过。有酒不愁来日短,得闲便喜胜人多。堪夸白发三千丈,一醉衰颜顷刻酡。洛社风流虽已远,吾徒欣感渐余波。”王应桂《甲子花朝吾园中集百岁翁三人作九老会主人赋诗纪事用作长歌鸣盛》:“甲子春,花朝日,花扑玉缸春酒热,吾园开,连翩九老相将来。主人起敬介眉寿,金巵高捧绕筵走。筵间肆设枣与桃,满座人如香山叟。充耳头摇摇,眉长须白风乱飘。擎杯不放饮若吼,謦欬一声裂凤箫。凌老鹤辉颇清妙,婆娑之状鹤难有。”在这里,诗人们追求的是与他人之间的流畅的互动,在具有审美感的江南天造环境中,通过人际互动和环境感染实现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获得垂暮生命的最大的快乐感,甚至淋漓尽致的狂欢。其中有酒不愁来日,得闲便喜胜人的道白,也隐隐流露出对高门名族在精神优越之外对物质优裕的满足。
由于清代吴地耆年(英)会的参与者大多是诗才超迈的文坛名宿,故所创作的诗歌不乏艺术水平较高之作,有些整体作品或秀句吟咏性情,老成可取,颇能流传人口,成为江南地域文学史乃至清代文学史上永远的珍萃,但无庸讳言九老会诗歌的缺陷和不足也是显然的。
首先,远离社会现实,缺少富于时代感的洞察和思考,也就脱离了思想和意义的创造之源,使许多九老会诗歌内容显得平庸和苍白。持平而论,虽然我们偶尔能够在许硕辅《岁寒初集即事》这样的作品中听到“蒲柳向春荣,经秋辄衰替。松柏挺劲姿,岁寒葆根蒂。所以比君子,遇穷见节义。人生重伦常,朋友合真契”这样的人格象征意义厚重的吟唱,但毕竟曲高和寡,它的声音被沈德潜《九老会纪恩诗》“枕流漱石久归田,来祝兹宁典礼庆。文职武功同九老,分班计岁各千年。海疆画手须眉肖,天际殊恩锡予骈。人比会昌余两倍,熙朝盛事正连绵”这种肤庸的颂圣之声淹没。还有不少怡老诗,过于强调“须信人生总有涯”,“行乐及时良不负”[14]《二集》,“人生会有归,何苦日奔逐”[15]卷二,将放弃德行人格的休闲娱情故意标签化。
其次,典故使用一律,情景表现雷同,前唱后和,陈陈相因,艺术表现缺乏创新。香山风、洛下贤、履道坊、禊亭会、耆英旧盟、洛社风流……成为九老会作品中最常见的装点诗面的词汇,故实的意义并无贴近具体情境的新的生发,没有诗情凝聚,让人产生数典式的阅读疲劳。而平面的人物铺叙,环境描写,感情抒发,缺少意境的笼罩,不能构成完整的富于艺术感的心灵图像,难以产生审美愉悦。“筵开从日午,洗盏月初悬。露重光如玉,觞飞酒似泉”式的叠加直白,甲子、节序、年岁的恣意实录,往往使全篇难见含蓄之味,回环之致,既显出纪实性笔墨过重,也透露出雅集现场即景染翰时的仓促,表现出某种应景文学不可避免的缺憾。
然而无论九老会诗歌存在着多少粗糙的痕迹和艺术表现的缺憾,对这些江南诗老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中留下了许多记录雅集现场的作品,丰富了江南文学史料,使今人能够超越时空,去感知清代江南富庶繁华之地曾经有过的风雅,我们应该表示敬意;对其作品中的精神指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耆老的心灵活动,应该加以肯定;尤其对它所呈现的超越文学性之外的认识意义,更应给予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