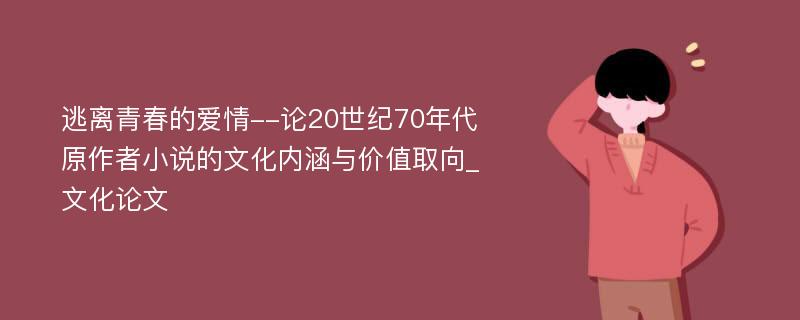
青春的逃之恋——论70年代生作家小说的文化内蕴和价值流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蕴论文,之恋论文,流向论文,作家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1)04-0049-04
一、青春的抗议
米兰·昆德拉曾经这样定义“青春”:“一阵愤怒涌过我的心头:我为我自己和我当时的年纪,那愚蠢的‘抒情的年纪’而感到愤怒……”[1](P157)。如果说米兰·昆德拉对青春的愤怒,是缘于被欺骗、被引诱、被凌辱的感觉,是抗议“诗人与刽子手联合统治”对人性的禁锢和对灵魂的腐蚀,那么70年代出生的作家则因前人的抗议与努力而受到庇护。当她们的前辈将“现代化”作为一种告别“历史悲剧”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发展方案付诸实践,当她们的前辈震惊于“现代化”的诸多负面效应而质疑过去那些神圣的历史神话时,享受着现代伊甸园丰硕果实的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以她们亲历的冷酷的生命体验,宣告了对“现代化”亲和性想象的灰飞烟灭。她们游荡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境遇中,以成长的烦恼和青春的空虚,遥祭那些遗留在历史记忆深处的青春的神话。那热血沸腾的、古典的、浪漫的、抒情的花季雨季,对她们来说都仿佛是虚构的诱饵,连眺望一眼的欲望都淡漠了。唯美的抒情诗般的青春,在她们的记忆和字典中,都仿佛是束缚心性的镣铐和枷锁。
《像卫慧一样疯狂》、《回忆做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香港情人》、《午夜场》……,当人们以异样的目光将她们定义为“另类”和“另类写作”时,我更愿意将她们视作以生命的迷狂向青春献祭者,更愿意将她们的写作视为青春的诔文。尽管这青春是那么不抒情、不浪漫、不古典、不唯美,相反是那么冷酷、那么阴郁、那么颓废、那么无聊和呆滞,仿佛是一片湿热的沼泽之上停泊的欲望船,仿佛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之中盛开的恶之花。然而,70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集体性的生命体验。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她们的小说“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悠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2]
当“现代化”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直面当下的生存体验得以充分地实践和展开时,卫慧们、棉棉们这些现代伊甸园果实的品尝者,在吸取了“现代化”丰富的营养之后,却将苦涩的果渣吐了出来。她们以毁灭性为表征的那种集体性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素质,作为写作的内驱力和小说的底蕴,仿佛在漆黑的夜色中潜入“城市”这个现代化符号的灵魂的私处,展现“城市”这个现代神话式的象征和寓言制造的存在之渊薮。残酷和阴冷的青春塑造了她们的叙事姿态和抒情欲望。她们是现代化大城市的产儿,以颓废和激进的生存方式与书写宣扬她们的“真情告白”。她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归类于本雅明意义上的“游手好闲者”的行列。她们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漫步,无须在任何异样的目光下惭颜与胆怯,“张望”决定了她们潜在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张望”构成了她们同城市和他人的关系中轴。她们在“张望”中鄙视着充满铜臭与权欲的生活。她们以另类的生活和前卫的姿态证明自己之于世界的存在。她们通过一种鲜明的酷性和特定的方式漫不经心却又持续不断地告诉人们:拯救不过是我个人的展现。
本雅明在《夏尔·波德莱尔》一文中说过:“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3](P6)70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仿佛阴冷夜色中的萤火虫,扇动着脆弱的翅子,引导我们潜入城市拥挤嘈杂的人群,穿过肉欲的光色和迷离的喧嚣,在星光暗淡的时刻扑入酒吧、咖啡馆、迪厅、夜总会……,让那些阴暗的、毫无顾忌的生命宣泄与放纵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人们在生命的萎顿和情欲的混乱中,顿悟生命的无聊与空虚。让人们在那些冷面无情、无动于衷的叙述语调中恍然悟之:人们为了创造充满城市角角落落的一切所谓文明的奇迹,却牺牲了人类本性的那些优良品质,城市的繁杂与绚丽中早已经孕含着丑恶的违反人性的萌芽。
卫慧在为《蝴蝶的尖叫》写的创作谈《我还想怎么呢》中侃侃而谈:“我的故事人物喜欢复杂的生活,男男女女之间存在着暧昧不明、神秘浪漫的关系,他们一次次地堕入陌生、欲望、绝望的情境中。最近我越来越喜欢用一种"cool"味写作。你可以说我在扮酷,没关系,因为我努力要成为真正通晓城市现代浪漫和冷酷的作家。”[4]棉棉在为《香港情人》写的创作谈《礼物》中强烈申明:“我残酷的青春使我热爱所有被蹂躏的灵魂,我为此而写作。我写作,直到有一天,没有任何一种感受可以再伤害我。”[4]卫慧、棉棉们为了热爱被蹂躏的灵魂,为了通晓城市现代浪漫和冷酷,在孤僻、逼仄的城市空间,在幽灵般灰色而冷漠的人群中,撷取青春的恶之花。仿佛“游手好闲者”僵冷地站在大城市和主流社会生活的边缘,以自以为成熟的“异化的人”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生存之域,以城市民谣和情人絮语般的方式诅咒它、狂恋它。她们用享乐主义的前卫姿态,践踏着那些庸常的生活秩序和行为准则。她们以激进的表演为城市人与日俱增的精神匮乏,洒上一抹反讽的冷艳的光彩。然而她们的书写从不为庸俗的“看客”们绽放内心的隐秘,正如周洁茹在小说《午夜场》中所写的:“这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了,他们都这样下去,只有我,前景未卜固执地走下去,没有节制,疲惫,错乱,忧郁烦恼,到最后,什么都有了,也什么都没有了。”[4]卫慧、棉棉这些忧郁的恶之花们,在脉脉温情掩盖的弱肉强食、秩序井然的城市黑色丛林中,在最原始意义上的存在体验中,发出了她们响亮的青春抗议之声。
二、酷性与时尚
经验往往是一种具有传统范畴色彩的心理规范性感受。无论是在集体存在还是私人生活的意义上,人们往往把记忆结构视为经验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与其说经验是牢固地扎根于记忆事实的产物,不如说它是记忆累积的通常是潜意识材料的汇聚。自从现代文明的因素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以来,人们就开始并且往往以哲学运思的方式进行“经验”的重新把握。人们希冀把握一种“真实”的经验,这种经验同现代文明标准化、非自然化所表明的经验是对立的和异质的。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规模工业化的不适合人们诗意栖居的时代,全球化与整体化的浪潮不断塑造着平面化的心理空间。经验往往沦为马克思所说的“思想狭隘的城市动物”本能反应的秩序化。于是,当人们的心灵体验和想象视野与所观照的现象愈来愈难以达成契合关系时,当人们的语汇流于经验的普泛化、庸俗化时,人们往往流连于词与物的裂隙地带,从中发掘激动人心的内涵,重新来塑造新颖的别样的语汇,传达异质化的心理体验,借以展现个体存在的独特风貌。
“酷”这一广泛出现于当下城市青少年口头的语汇,正是一种表征异质化心理体验的词语创新与换代。它逃离了传统素质的束缚,转向瞬间的震惊体验范畴的怀抱。正如保罗·瓦雷里谈到的:“人对印象与感觉的接受完全隶属于震惊的范畴;它们证明了人的一种不足……回忆是一种基本的现象;它旨在给我们时间来组织我们原本缺乏的刺激的接受。”[3](P132)所以,“酷”是心理震惊的瞬间体验不断累积和转化为记忆常规的一种经验的当下表达,传递了新奇、异样和震惊的效果。米兰·昆德拉说过:“如果一部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为止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1](P4)又说:“小说家则不制造种种观念的重大问题。他是一个探索者,致力于揭示存在的某些尚不为人知的方面。他不醉心于他的声音,而是醉心于他正在寻求的形式,只有那些和他梦想的要求相符的形式才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1](P147)由此来看,“酷”之于70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不仅是“有关生存的点滴”,而且传达的是被主流社群心理体验所排斥的自我沉醉的声音及其实现形式。
如果在寓言和隐喻的层面上,将70年代出生的作家和她们的小说及小说人物作一体化划界,把“她们”视为“酷”这种心灵体验的同一言说者,那么,隐喻式的思维将使我们看到:“她们”飞翔于纷乱的城市夜空,沉迷于“另类”体验,追求“酷”的自慰与不屑。正如《蝴蝶的尖叫》中朱迪对阿慧所说:“你是雅皮美女,意淫女皇,而我得保持穷孩子本色,这样我们之间会有一种张力,一种张力,知道吗?你能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4]她们带着青年亚文化群体普遍的生存焦虑,以“雅皮”与“嬉皮”的混成姿态,全身心投入到地下酒吧和迪厅,享受着劲舞、派对、爵士乐、性高潮、大麻、同性恋、酗酒……带来的疯狂的瞬间生命颠峰体验,在迷狂的生命醉舞之中宣泄着激动与悲欢。对种种欲望和生命狂喜的顶礼膜拜,使她们对奢华与刺激恋恋不舍,病态般的顾影自怜着自己,如同欣赏着“巨大草莓上的一块烂疮”。她们将狂热混乱的生活情调与厌世的颓废心绪拼接起来,表演着激进的、病态的、颓废的、青春碎片般的“酷”之舞,以更为本体的感性生活方式放逐着灵魂。她们的生命哲学以放纵和宣泄的形式,体现为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与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和内心底层的冲动。她们在鄙夷着市侩文化的同时,怀着复杂的矛盾心情抗拒着主流社群文化的压抑与规范。
因此,“酷性”的追求使她们以信仰缺席的方式表达着自身对世俗生活的迷恋与厌烦,使她们撕扯掉那些正统伦理色彩的循规蹈矩,企图剥离压抑自身潜意识和欲望的那些规范和准则,借以驱逐那些造就她们沮丧感、羞耻感、内疚感和恐惧感的外界力量,从而在想象中获得一种近乎梦幻状态的自然生命本真。于是,“酷性”的追求使她们以自恋狂般的方式展现生命能量的同时,也使她们成为“时尚”的制造者,从而获得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自我满足感与成就感。本雅明曾经说过:“时尚是与有生命力的东西相对立的。它将有生命的躯体出卖给无机世界。与有生命的躯体相关联,它代表着尸体的权利。屈服于无生命物的性诱惑的恋物欲是时髦的核心之所在。”[3](P186)但是,“时尚”却开启了一个幽幻的世界,使人们沉沦的同时也获得了解脱。“时尚”将那些从新意识中获得的最初刺激的幻想带回到最初的过去,同时又代表了突破过时了的东西的活跃的生命愿望。“时尚”带着鲜明的经验的色彩,充溢着体验的震荡,在一种逃避与回击的姿态中与时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寓言意义上,具体地呈现出时代与体验的某种内在的真实图景。
70年代生作家及其小说,以一种集体性的亚公众话语和生存体验,在寓言的意义上阐释着“酷性”与“时尚”致命的、诱人的、狂燥的魅力。而寓言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拥有的言说的特权。它意味着在这个“偶像的黄昏”的世界把握自身的体验并将它成型,意味着把握广阔的真实图景的可能,意味着持续不断地猜解存在的意义之谜,意味着冲破商品拜物教与意识形态规约的可能:在一个虚构的结构里重建人的自我形象,恢复异质的、被隔绝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时尚”与“酷性”暗示人们:把一个要将人的过去与现在碾得粉碎的时代作为思考的主题。
三、意义的可能
丹尼斯·贝尔曾喻称60年代欧美的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是一场孩子们发动的十字军远征,“其目的无非是要打破幻想与现实的界限,在解放的旗帜下发泄自己生命的冲动,它扬言要嘲弄资产阶级的假正经,其实仅仅抖露出自由派爹妈的私生活。它宣称代表着新潮与勇敢,实际上只会嘶哑着嗓子反复叫喊——由于使用电子共鸣器这种大众传播媒介,摇滚乐的音量陡然暴增——可怜的青年人,他们竟也要嘲笑半个世纪前在纽约格林威治村里放浪形骸的波希米亚们。”[5](P37)一本正经的老文化保守主义者丹尼斯·贝尔在嘲笑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负面效应时,却将他们在疯狂地破坏与解构之中显露的革命性的文化光芒给抹煞了。因为叛逆性的反文化潮流,至少刺激着主流文化的内审与自我矫正。在更可能的意义上,反文化潮流以其巨大的标新立异的势能,随时光流逝反而成为一种别样的经典。
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社会积累过程中,一种时尚的庸俗文化已经渐次成形。它表现为流行文化的人数倍增,中产阶层的享乐主义盛行,以及许多人对色情的追求与沉迷。加之低俗文化的腐蚀与败坏,使社会文化日趋粗鄙无聊。我们知道,人们的生存方式通常由一套价值观为之辩护,由社会机构规范予以控制,并在品格构造中体现出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只要有一定精神资质为基础,气味相投的一群人持有某种生存方式,就存在着社会学家所谓的“身份集团”的群体。当代中国尤其是城市社会,正在形成着诸多疏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身份集团”群体。人们往往将这些群体视为“另类”,将之与主流文化隔离开来,以异样的、警惕的目光审视这些“另类”和“另类生存”。但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的健全。”[6](P1)70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作为一种疏离主流文化情绪的文学展现,以色情、欲望、冲动、自由等,猛烈撞击着正常的价值观和行为动机模式,为酷性与时尚化,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心理武器。在70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中,疏离主流文化情绪体现着以下文本特色:童年情绪,欣赏荒诞,颠倒价值,讴歌冲动,关心幻觉,热衷冷酷与麻木,沉溺于性反常,渴望歇斯底里,反知性与理性,抹煞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融艺术与生活想象于一体,等等。这种情感释放和反抗,不仅是反规范的,还具有某种独立的美学倾向,甚至可以称之为小说化行为艺术。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艺术努力转向自律性,这是商品状态所迫,以便超越残酷的必然性。艺术是在使人厌烦而毫无社会功能的意义上,在一种更富于创造力的意义上被扭曲为自律性的:艺术故意转向自身,成为一种抵抗社会秩序的缄默的姿态,用阿多诺的话来说,这是用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7](P369)与西方现代主义相对照,正是由于精神潜质的同构性和反叛对象的差异性,我在将70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视为中国当代疏离主流文化情绪展现的同时,更愿意指出她们在反商品拜物教与文化规约中的价值与意义。
让我们严肃地体味她们的“真情告白”:
“可我那么喜欢文字,笔下的文字是我赖以在日益物质化的城市保持激情的温柔小点心。……我和那些模特、歌手、发型师、画家、经纪人、无所事事的PUNK、秃头的金融分析家一样,是吃着城市最物欲最前卫的秘密生存的一种小虫。”[4]
“身体不自由,连心也是不自由的,所写的东西就充满了自由、绮想和怪异。……如果说我身陷囹圄,写作就是我从栅栏里伸出来的一只手,我等待着它变成一把钥匙。”[4]
“我害怕所有人的昏倒。因为黑暗随时会来,在我灰色的时刻,在我灿烂的瞬间,我的人生是虚弱的。但我很幸运,写作带着医生的使命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因此可以期待自己不破碎,我蒙昧的身体因此而渐渐透明。……我坚信由于我的写作,爱会成为一种可能,生活的废墟将变成无限的财富。”[4]
正是在一种社会可能的意义上,我们看到,当70年代生作家的写作及其疏离主流文化情绪能够形成一种文化力量的时候,它将挑战传统的形式和意义,挑战建立在诸多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句法和语法规则。它将在现代舞台上跳舞,庆贺狂乱和谵妄,把所有社会性的联系都拆解成流动性的欲望。它的形式将成为它的内容——一种排斥所有社会既定语义的形式,并且提供一种可以想像为似乎实现了自由的微光。正如福柯所说:“凡是具有艺术作品的地方,就不会有疯癫。但是,疯癫又是与艺术作品共始终的,因为疯癫使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开始出现。艺术作品与疯癫同时诞生和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性质负有责任的时候。”[6](P269)面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写作,我们完全有理由具有同福柯一样的眼光与批判的勇气。尽管文学艺术生产本身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它能够潜在地影响社会秩序,是某种能够消除混乱的意识形态模式。但是,在我们对70年代出生作家的写作寄予某种希冀的时候,我们却不可避免地发现了它的一些致命的弱点:它往往会沉醉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庸俗的反历史主义而难以自拔,它往往回避批判的义务和承担意识,愤世嫉俗地取消所有真理、意义以及主体性,代之以具体的技术主义和姿态主义。或者,洗心革面,剥掉“另类”的油彩,以“成熟”的步伐摇身转变为主流文化的消费者和体现者。因此,当我们看到它胆怯的、可怜的、空虚的、无精打采的一面时,难免令人回忆起存在着秩序、真理以及现实性的怀旧化的想象空间。这不能不令人想起丹尼斯·贝尔的话:“我相信,我们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现代主义的衰竭,共产主义生活的单调,无拘束自我的令人厌倦,以及政治言论的枯燥无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漫长时代行将结束。现代主义的冲动原是想超越这些苦恼: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悲剧——去开拓无限,可惜它的动力仅仅出自激进自我的无穷发展精神。”[5](P40)
在“现代化”以一种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姿态影响当代中国人的心灵时,这可能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局面。当创造的冲动逐渐松懈下来、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逐渐消失,当它作为文化象征扮演激进时尚角色的功能沦为一种玩世不恭和流行格调时,当它的试验形式变为广告和流行时装一样的符号象征时,当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众”们日常化和制度化时,我们惋惜的同时也不便加以指责。我们更愿意说: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之所以在暮色中飞翔,正是因为生活的色调越变越灰暗。
70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崭露峥嵘,它的潜在的精神结构决定了它的价值与意义的多种可能性。我愿意转录卡夫卡的一段话奉送给她们: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是,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3](P14)
结语
事实上,70年代生作家及其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文坛的初绽异彩,在很大程度上是商品经济时代社会主流文化的衍生物和派生物,是社会主流文化夹缝中的寄生物。70年代生作家及其小说自身存在着先天的结构性精神矛盾和内在性精神缺陷,她们所具有的革命性文化资源极其有限。其充满欲望和破坏性的乌托邦冲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生青春期本性的躁动。因此,作为一种另类文化现象尽管可以风光一时,但是作为社会主流文化调味品的功能,势必最终淹没在主流文化的同化与包容中。
如今,70年代生作家及其小说在当代文坛掀起的波澜,已经日渐寂寥无声,“美女作家”的褒贬和明星般的热炒,也开始蜕变为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或者说已经进入历史记忆的行列。对于70年代生作家及其小说的褒贬不一,实际上反映了人们不同的文学史眼光,也反映着人们不同的价值态度和评判标准。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那样,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历史现象同某种价值或标准联系起来,只能参照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来书写历史现象。同样,这种价值系统来源于人们对时代整体精神的观照和判断,而且这种价值系统同时还必须是一个系统的知识整体。我们应当从这样一种视野出发,观照70年代生作家及其小说对当代文学的结构、规范和功能的解构与建构。或许多少年之后,它的价值取向和现实不再紧密关联时,它的意义与功能才会全面浮出历史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