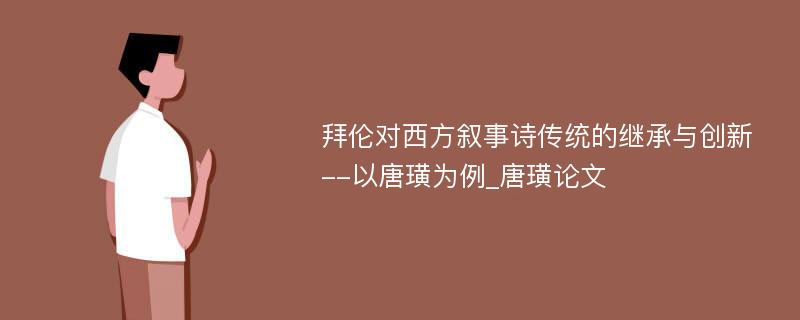
拜伦对西方叙事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以《唐璜》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伦论文,叙事诗论文,为例论文,传统论文,唐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6-0043-07
从《荷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神曲》到《失乐园》,西方叙事诗史见证了一座又一座的丰碑。在人们认为叙事诗日渐式微,小说日益兴起的18、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横空出世,他们的多部叙事诗作品如群星般璀璨,其中,拜伦又因其影响之大而尤为瞩目。拜伦的叙事诗不仅对普希金、巴尔扎克、奥斯丁、薇拉·凯瑟、奥登、库切、巴赫金等一大批作家和文论家,而且对尼采、德拉克洛瓦、罗伯特·舒曼等哲学家、画家、音乐家产生了实际的、深远的影响。拜伦诗歌中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技巧高,其诗歌中夹叙夹议的方式、写景加抒情的成分、明显的讽刺意味以及对口语化的伸缩性较大的意大利八行体的创造性运用等特点,均使诗人成为西方叙事诗史上当之无愧的大家,在西方叙事诗史乃至世界叙事诗史上拥有自己独特而崇高的地位。本文拟以拜伦的代表作《唐璜》为例,来说明诗人对西方叙事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一、从抒情到叙事的转向
拜伦的《想从前我们俩分手》、《雅典的少女》和《她走在美的光彩中》等抒情诗已广为传唱,他的抒情诗也分别被收录在《闲散的时光》(1802-1807)、《随感》(1807-1814)、《希伯来歌曲》(1814-1815)、《家室篇》(1816)以及《随感》(1815-1824)等诗集中,抒情诗的创作贯穿了诗人的整个创作生涯。即使在拜伦的讽刺诗和叙事诗等诗歌体裁的创作中,也不乏精彩的抒情片段,但抒情诗并非拜伦诗歌作品最精华的部分。在《简明剑桥英国文学简史》中,关于拜伦有如下一段评语:“只是在纯抒情诗方面,拜伦稍见逊色;所以读者不应从选本中去了解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审判的幻景》和《唐璜》这三部诗集就足以使任何有鉴赏力的读者深信:拜伦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世界永远需要这样一位诗人去嘲笑那卑鄙的事物,并且激励那高尚的事物。”[1](P17)这不仅是对拜伦叙事诗的高度评价,也是对诗人社会关怀的褒奖。
纵观拜伦的诗歌创作历程,其中经历了从抒情到叙事的转向,确切地说,是从抒情诗到融叙事、描写、议论、抒情、讽刺于一体的叙事诗的转向。这一转向应当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诗歌史方面的原因,西方诗歌的叙事传统由来已久,抒情诗总体来说为诗人们和文论家们所忽视。“在各种诗歌类型中,抒情诗一直被当作微不足道的一种而置于不顾,……人们认为抒情诗缺乏气势,也产生不了有益于人的效果,它的题材主要只是作者的自我感受,代替不了其它诗歌成分。”[2](P126-127)尽管气势宏大的抒情诗曾时来运转,但在地位上仍然没有超越过叙事诗。此外,通过对西方拜伦研究状况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对拜伦抒情诗的研究只占到其中很小的比重,也就是说,批评家们对拜伦的抒情诗给予的关注也远不如其叙事诗作品。
拜伦诗歌创作的叙事转向与诗人自身的生活阅历及其艺术技艺的成熟也是息息相关的。1807年,拜伦的第一本抒情诗集《闲散的时光》出版了,不久就遭到英国文坛权威杂志《爱丁堡评论》载文的猛烈攻击。对于此次失败的原因,拜伦的结论之一便是“情诗”最易招致反对。盛怒之下的拜伦开始刻苦研习德莱顿和蒲柏的讽刺诗,预备以撼世的长篇力作来取代抒情短诗,以还击《爱丁堡评论》对他的无情嘲讽。1809年出版的《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便是拜伦两年来卧薪尝胆的成果。自此,拜伦在英国诗坛上锋芒初露。1812年,《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二章的出版让拜伦一夜成名,很快他便享誉全欧;之后三年间,拜伦的《东方故事诗》相继问世,其重版之频、销量之大,令世人震惊;1819年至1824年间,《唐璜》各章节相继出版,这是一部兼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与讽刺为一体的叙事诗,作为拜伦诗歌的巅峰之作,全面展示了拜伦的思想感情和诗歌技艺。拜伦有意要在《唐璜》中“一反惯例”,创作出超越前人的史诗性叙事诗作,诚如诗中所说:“史诗的叙述法通常就是这样,但我却要从头说起,一反惯例;我的布局规定有严格的章法,若竟胡乱穿插,岂不坏了规矩?……”[3](P14)读过《唐璜》之后,我们不能不承认:拜伦的诗歌叙事艺术确定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当然,《唐璜》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它是拜伦人生经验和艺术修养都日臻成熟的结果。在人生经验方面,主要有两点:第一,《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让拜伦一夜成名,在英国社交界红极一时,后因叛逆激烈的言行和私生活上的问题受其政敌的攻击,拜伦愤然离国。从比利时到瑞士、从米兰到威尼斯再到拉文纳、从费拉拉到佛罗伦萨再到罗马……正是这样的亲身游历为拜伦叙事诗中的写景和游记成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外,生活的变故也让拜伦对于生活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第二,拜伦在意大利参加了烧炭党人的地下抗奥活动,因此,对英国上层社会的炎凉世态和欧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有了亲身的体会。正是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拜伦才能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守财奴嘴脸及其对他国政治的粗暴干预,才能对英国上流社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实面目,做出那样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也才能对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的命运给予那样深切的同情和关怀。拜伦在给穆尔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生活在社会的熔炉旁,就不可避免地受其热能与蒸汽的影响。我就曾受过这种影响,并且非常大,足以给我整个未来的生活打上印记。”[4](P251)社会对拜伦的人生,包括其写作生涯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在艺术修养方面,王佐良认为:拜伦写作《唐璜》时,已从初期的抒情诗、故事诗、记游诗、诗剧进到讽刺诗,风格也从绚烂归于平易,能够写得得心应手了。[3](前言)笔者以为,在《唐璜》创作期间,尽管拜伦也在尝试其他类型的诗歌,并完成了多部历史剧、诗剧和讽刺诗,但拜伦从未放弃他对叙事诗的偏好,而作为集拜伦诗艺之大成的叙事诗《唐璜》显然成为拜伦后期诗歌创作的重心,这一阶段的创作不是单纯的讽刺诗所能代表的。
此外,拜伦诗歌创作的转向也是单纯的抒情诗已无法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这一客观事实所致。对于抒情诗的这一缺陷,长期以来,批评家们达成了共识,包括挽歌、歌谣、十四行诗和颂诗在内的抒情诗体,“与叙述体和戏剧体不同,大多不具备人物、情节等成分,因为根据常见的模仿即镜子的观点,这些成分都是对作者心外的人和事的描摹。”[2](P126)而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用第一人称来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其抒发者最易沦为诗人本人,这种“为了迎合某种抒情需要而制作的东西”[2](P126)往往缺乏真情实感。因此,批评家多以为抒情诗“不过是想象的产物”[2](P127),它题材有限,难以再现客观事实。因此,要摹写重大历史时期的欧洲社会,单纯的抒情体必然要让位于融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与讽刺于一体的叙事诗,在拜伦诗歌叙事转向的实现过程中,诗人在各种诗歌体裁中游刃有余,最终创作出了《唐璜》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鸿篇巨制。
二、普通的英雄,不凡的诗歌技艺
叙事诗,尤其是史诗,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重大的题材必不可少。传统的叙事诗多涉及波澜壮阔的战争、国家的诞生、民族的兴起、天地宇宙、人类的原初等。拜伦叙事诗的题材来源既包括神话、历史、传说或前人文学作品之类的传统情节,也浸润着个人的主观体验。这并非是拜伦的独创,但丁的《神曲》就融入了诗人自己的生活经验及其宗教和爱国热情,弥尔顿的《失乐园》也融入了从清教时期向奥古斯都古典主义时期过渡时诗人自身坎坷的经历和遭遇。伊恩·P·瓦特在其《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中,谈到了小说与先前文学形式的一个重大差异:笛福和理查逊作品的情节来源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人,即取自神话、历史、传说或先前的文学作品之类传统的情节。在瓦特看来:“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的趋势也在日益增长。”[5](P7)拜伦正是在传统题材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个人的体验。他对传统题材的借用也打破常规、富有创意,所以其诗的题材和风格可谓变化无穷,令人叹为观止。
《唐璜》的故事情节发生在18世纪末,描绘的却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社会的现实生活。唐璜出生于西班牙的加地斯城,与丈夫分居的母亲独自抚养他。唐璜对传统的道德观不屑,16岁时便与母亲的朋友——一已婚贵族少妇发生感情纠葛,母亲为了避免家丑远扬,迫使他出海远航。唐璜在海上遭遇风暴,漂流到希腊一海岛,幸为海盗兰勃洛的女儿海黛所救。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唐璜和海黛如胶似漆、大摆宴席欢庆之时,海盗归来了。结果,唐璜被砍伤,并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售卖,后被买入土耳其苏丹的后宫为奴。王妃为唐璜的美貌所动,正在调情之时,苏丹驾到。唐璜与其他宫女被逐出王宫,因铺位不够,晚上他同一个宫女睡在一起。王妃知晓后,妒火中烧,下令将他和宫女抛到密道中的小船上,让他们流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去。拜伦不愧是讲故事的高手,故事发展至此,一个接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情节接踵而至,可谓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那就是:《唐璜》“包含了人类生活中各种奇异的矛盾的表现,每一种矛盾又作出了其最极端的发展”[6](P123)。从唐璜与朱丽亚恋情的发展到败露,从惊心动魄的海上历险记到海岛获救,从海岛生死恋的缠绵悱恻到兰勃洛的棒打鸳鸯,从奇异旖旎的东方风情到残酷的俄土战争……故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拜伦非凡想象力的牵引下,主人公的命运跌宕起伏,而读者在心理上仿佛乘上过山车一般,在巅峰和峡谷间穿梭。
从西班牙到土耳其再到俄国,又从俄国经波兰、德国、荷兰再到英国,随着唐璜的踪迹,欧洲广大地区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巨大画卷便展现在读者面前,难怪作家瓦尔特·司各特说:《唐璜》“象莎士比亚一样地包罗万象,他囊括了人生的每个题目,拨动了神圣的琴上的每一根弦,弹出最细小以至最强烈最震动心灵的调子”[7](P8)。王统照也曾高度评价拜伦诗歌作品的活力:“他能使已死去的人物、风景、事实,重复跃然再生于其笔尖之下,随其丰富的情绪而哀、而乐。”[8](P221)《唐璜》题材之广博、叙事能力之高超、感染力之深厚使这部作品经久不衰,赢得了世代的普遍赞誉。
传统史诗往往由英雄入诗,尤其是民间史诗,其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具有非凡能力的英雄,这也是此类作品被称作“英雄史诗”的缘故。英雄史诗中的主人公是“人类力量的集中代表”[9](P80);作品的结局一般是英雄的死,但那死是“悲壮的,不是悲观的”[9](P80)。“英雄的精神其实就是民族的精神”[9](P80),在这样的英雄人物面前,读者不禁感怀自身形象的渺小。可以说,传统史诗中的英雄是人为拔高了的英雄,他是集体的代言、民族的象征。
文学史上以唐璜为主人公的作品有不少,从中也演绎出了一系列面貌各异的唐璜形象。唐璜的原型是传说中一个生活在14世纪的西班牙贵族,一个风流不羁的浪荡子。拜伦笔下的唐璜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唐璜,拜伦以自身为原型,将自身的学识、见闻、体验和想象统统倾注到唐璜这一形象的塑造中,赋予该形象以崭新的意义。尽管不具备通常谓之英雄的种种特质,但唐璜就是拜伦眼中的英雄。在《唐璜》的开篇章节中,拜伦谈到了以唐璜为英雄入诗的由来。在这里,诗人追古溯今,讽刺了英、法历史上追名逐利、甚至臭名昭著的假英雄;而真英雄又因不能在诗篇里留辉,有如过眼烟云。因此,在诗人看来,唐璜就成了合适的英雄人选而被写入诗中。拜伦笔下的唐璜不同于以往史诗中的英雄,他不是受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驱使而又不失个性的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也不是肩负国家和民族重任一往无前的埃涅阿斯,他并非基督教人文主义滋养下追求完美人格和人性的诗人,也并非像撒旦一般貌似英雄实则魔鬼的假英雄。勃兰兑斯曾这样描述唐璜:“璜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主人公;他的精神与他的性格都不太高过普通的人;但他是运命的宠儿,一个特别优美、骄傲、勇敢而幸福的人,他较诸为打算或计划而更是为运命所领导者,他是那拥抱了全部人类生活的一篇诗之适当的主人公。”[6](P122)唐璜可以解读为在卢梭自然人性观影响下的拜伦,按照人性自然发展的规律而塑造出来的一个去伪存真的英雄。
诗人雪莱说,《唐璜》“每个字都有不朽的印记……它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久已倡言要写的——一种完全新颖的、有关当代的东西,而且又是极其美的”[7](P9)。雪莱的评价还不够确切,《唐璜》不仅折射出拜伦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他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在分析拜伦诗歌的伟大影响时,李嘉娜认为拜伦超越了诗人现象,而成为一个文化现象:“拜伦再现和预示了他的时代和他以后时代的文学、历史、文化和生活的精髓。他的生活模拟他的诗,而他的诗反映了时代和历史的要求。”[10](P118)诚然,拜伦的叙事诗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而且当今世界的很多热门或敏感话题在拜伦的叙事诗中都有所体现,如东方主义、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同性恋现象等。拜伦诗歌的前瞻性和当下意义已引发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唐璜》所达到的高度绝非偶然,诗人在诗歌艺术上有借鉴、有创新;在讽刺艺术上,诗人借鉴了古典主义者德莱顿、蒲伯的手法。诗中,拜伦对备受统治阶级赞美的惠灵顿极尽讽刺之能事。“毁灵吞”、“杰出的刽子手”之类的反语以及“‘各族的救星’呀,——其实远未得救,‘欧洲的解放者’呀,——使她更不自由”[3](P543)等倒笔的运用,极具讽刺效果。再看诗人对骚塞等湖畔派诗人狂妄自大、固步自封,甚至甘作御用文人的奴性嘴脸的大肆鞭挞:“你原想在那道菜里唯我独尊,/把其他啾啼的众生一一排挤;/岂不知你用力过猛,鸿图未展,/倒使自己跌一跤,像一条飞鱼/落在甲板上喘气。因你飞得太高,/又缺水分,鲍伯呀,你可就死于干燥!”[3](P2)这一段绘声绘色的叙述对鲍伯的急功近利、反而弄巧成拙之丑态极尽揶揄之能事。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拜伦也以古典主义为典范,他的诗和会话毫无二致,干净机智、自由流畅,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其思想。尽管拜伦声称自己“蔑视各种尺度,但斯宾塞的诗体与屈莱顿的两行诗体除外”[4](P126-127),可他并没有采用蒲柏最拿手的英雄双韵体,而是调和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原则,采用了一种新的讽刺模拟诗体。拜伦先是从英国诗人弗里尔的《僧侣和巨人》里得到了格律上的启示,更主要的灵感,则来自意大利诗人普尔其(Pulci)、伯尔尼(Berni)和卡斯提(Casti)的作品。通过对意大利八行诗体进行改造,拜伦把原来每行八个音节改为更适合英语诗的十个音节,每行都是五音步抑扬格,交替押韵,最后两行改换韵脚押韵。改造后的诗体语言明白晓畅、口语气息浓厚,颇具音韵上的特色。不仅如此,新的诗体“毫无拘束,充满幻想,惯用高潮突降法和怪诞不协调的事物,这些都在八行体中得到充分包容”[1](P15-16)。拜伦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古今兼收、英意并蓄,他总是善于发掘他人作品中可以为自己所用的元素,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以实现最佳的艺术效果。
三、《唐璜》中的叙述声音、叙事时序与时间观
(一)叙述声音
在传统的叙事诗中,作者多是局外人身份,并没有参与到故事情节中去,他们是故事外的叙述者。但这并不排除诗人进入角色,以人物的身份说话。亚里士多德曾对史诗诗人可用的两种叙述方式进行了区分:一种是诗人以自己的身份进行叙述,另一种是进入角色的扮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后一种方式更胜一筹,因为诗人进入角色叙事,有助于突出作品的摹仿性,有助于刻画生动、鲜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故事中人物的叙事之所以可能,陈中梅认为是因为他们具备讲故事或叙事所必需的知识。就所知的可信度而言,他们虽然不能同比缪斯,却有可能胜过诗人。[11]
但诗人以故事中角色的身份叙述,并不意味着诗人就融入了自身的体验和情感。但丁的《神曲》在这一点上有了突破,而拜伦则以更大胆的尺度把自己的思想、言行暴露在公众面前。因而在叙述声音上,《唐璜》较之前人的作品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拜伦将自身置于其作品的中心,搭建其浪漫主义自我表达与真实的布莱希特大剧场,……如果说在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作品中,诗歌的真实性问题还是个理论问题,而在拜伦的作品中,它就成了创作中重要而明确的题材。”[12](P97)《唐璜》中的许多章节在拜伦看来,都是“以写实和很在行的风格写成”[4](P261)。在拜伦的诗作中,诗人时而借叙述者的声音传达自己的心声;时而进入角色,以故事内叙述者的身份展开叙述。就后一种方式而言,故事内的叙述者有的只依情节的发展而演绎自己的角色,有的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拜伦自己的化身。伴随着叙述者的切换,叙述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化,有时是读者,有时是叙述进程中所涉及的各类人物。多角度的视点和多层次的叙述,有益于贴近人物的心理,更好地刻画人物性格,从而增强了《唐璜》的可读性。
《唐璜》第一章(第213—220节)中有一段叙述者“我”的自讽是诗人拜伦在透支青春之后百无聊赖、看空一切的人生经历的写照。不仅在诗行中展示自我,现实生活中的拜伦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即使把自己心中快要熄灭的余烬都收聚拢来,也不能再燃成一堆火焰来温暖我冷却的感情了。”[13](P171)诗人凄凉的内心世界从中不难体味,这段自讽恰是其思想、情感自然而真实的流露。在叙事诗作品中,对自己的人生和感悟作如此直白的描述,拜伦堪称先锋。
在《唐璜》中,拜伦主要借助唐璜这一形象来透视自己的人生阅历,传递自己的思想感情。拜伦不少作品都有浓郁的自传色彩,其笔下的人物形象与其自身有众多的契合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把诗人与其笔下的多个人物形象等同起来。拜伦自己也认为《唐璜》中的许多章节都是写实的风格。海黛与唐璜的那段唯美的海岛恋情的描写,就让人联想到拜伦与拉文纳的特瑞萨·归齐奥利伯爵夫人的情事。
在整个诗作中,视点在诗歌主人公唐璜和叙述者“我”之间的切换屡见不鲜。叙事视点自由灵活的交叉与转换,有效地弥补了单一视点的乏味和局限性。唐璜和诗人“一个天真,一个世故,一个行动,一个旁观而冷言冷语”[3](前言),在性格和处世方式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这两个对立的视角和形象,实现了拜伦自身虚构形象的完整性。
此外,除了“我”的叙述声音之外,《唐璜》中还存有来自其他视角的多个叙述声音。如该诗第四章意大利歌手罗珂甘蒂对唐璜所发的一通精彩的议论和出色的描述:该段口语体特征非常明显,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戏团众生相,戏班班主的阴险毒辣、女主角的人老色衰、男高音老婆的横刀夺爱……罗珂甘蒂的描摹能力,更确切地说,拜伦出色的叙事能力由此可见一斑,仅凭几笔,人物的形象便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叙事时序与时间观
史诗作家多偏爱倒叙。在《唐璜》中,叙述者“我”自称诗作“有严格的章法”,认为“胡乱穿插”会破了规矩[3](P14),但在该诗中,“我”却时常终止唐璜故事的讲述以进行描写、议论、说明、回忆、展望、抒情、感慨等,这些都有效地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并拓展了全诗的叙事空间。颇为有趣的是,除去与故事情节息息相关的叙述与议论,“我”的行文安排、诗学观等也不时地出现在诗行中,其叙事手法的灵活多样及应用自如,无不显示出诗人的才情和创新能力。
在传统的叙事诗作品中,时间的概念是微不足道的,“运用无时间的故事反映不变的道德真理”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它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瞬变的时间上,而是集中在绝对无时间可言的死亡的事实上;它们的作用是吞没我们日常生活的意识,以使我们做好面对永恒的准备。”[5](P17)然而,在《唐璜》中,我们通过种种迹象看到了拜伦有别于传统的时间观。在《唐璜》下篇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直接的时间标识,作者通过空间的切换来反映时间的流逝,从而形成诗歌的叙事线索。在上、中篇尤其是上篇有不少时间标识,这些部分呈现出故事性更强、更生动,也更富有感染力的特点。其中的时间表述涉及一年中时间的变换、一天中时间的变换等,但究竟为何年何月何日并不是很确切。例如,“那是夏季的一天,在六月六日——/我愿意在日期上力求说得准,/不但说某世纪,某年,甚至某月,/因为日期像是驿站,命运之神/在那儿换马,教历史换调子,/然后再沿着帝国兴亡之途驰奔;/它所终于留下的,不过是编年历,/还有神学答应死后兑现的债据。”[3](P58)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拜伦的时间观:时间稍纵即逝,时间一去不复返,但日期有如驿站,空间化了的日期可以见证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兴衰。这并非说拜伦不看重时间在叙事中的功能,恰恰相反,诗人笔下的故事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时间的纪元为拜伦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否则其诗才“就会因缺乏素材而无所施展”[3](P66)。除了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时间标识之外,在《唐璜》中,拜伦还时常终止叙述进程而进行回忆、展望等,这一点也足见拜伦对时间的重视、对叙事时序恰到好处的把握。此外,《唐璜》中瞬息万变、扣人心弦的情节发展也从侧面反映了拜伦对时间变迁的敏感和掌控能力,这一点正好切合了叙事的本质,因为“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的、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14]。而“小说与日常生活结构的密切关系直接依靠的是它对一种具有细致差别的时间尺度的运用”[5](P17),这一点拜伦的叙事诗也是以往的叙事文学所无法比拟的。《唐璜》被一些学者视作诗体小说,这部作品也为后世众多的小说家所推崇和借鉴,这当然与作者在时间进程中塑造出了那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不无关系,但更与诗人在透彻把握时间基础上的巧妙的情节安排有关。
如果说《荷马史诗》是西方民间史诗的巅峰之作,《埃涅阿斯纪》开创了西方文学史上文人史诗的传统,实现了民间史诗向文人史诗的过渡,《神曲》中饱含诗人自己的个人体验与思想感情,改变了以往史诗中以英雄入诗的传统,《失乐园》“更为广泛、精细地运用了文学样式的综合性、多样性”,赋予史诗这种文学样式以“更大的包容性、更大的活力”[15],那么,《唐璜》以其丰富的思想、高超的叙事技巧、鲜明的前瞻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把西方的叙事诗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研究拜伦的叙事诗,无论是对于文学史研究,对于提高叙事诗的技巧,还是对于相关的批评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标签:唐璜论文; 诗歌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文学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读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神曲论文; 失乐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