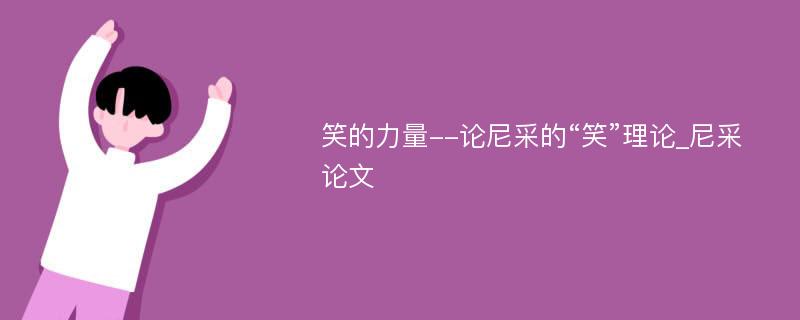
笑的力量——论尼采“笑”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力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5)10—0047—06
一、笑的研究:一种被边缘化了的声音
作为人类一种最基本的感情表达形式,笑恒久地陪伴着一个人生命的始终。它和“哭(悲)”、平静一起,构成了人类抒情3种最基本、最核心的方式。 人之为情感主体,他对自己整个存在情况的深度体验必然地要借助这3 种方式自然地流露出来,它们构成了人对存在理解的最明证也最无讳饰的直白。在很早以前,轴心时代的文化巨人们就洞察到了感情表达与存在体验之间的深刻关系。像彼时东方的中国、印度诸位贤哲对于“平静”体验的叙述,希伯莱、希腊诸位先哲对于人的“苦痛”状态的深度描述等,至今仍烛照着人们的精神探索之路。但相比较来说,人们历来对笑的力量却始终抱着犹疑的态度。除了伊壁鸠鲁,少有思想家把笑/快乐当作人的最高的存在体验。诚然,在一些宗教性的著作,比如《圣经》中,也有一些涉及得救的狂喜状态的描述,但这种狂喜,究源来说仍是从苦痛体验中派生出来的,而且,在《圣经》中,有关狂喜、欢乐状态的描写,其深刻程度也远不能与对人类生存的本质痛苦的揭示相比。这一点只要参读《传道书》、《约伯记》等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然,以上所说只是大略而论,如要细密地讨论这个问题,这就要涉及庞大的比较文化学的问题,这自然不是我们这篇小文章所敢略窥一二的。因此,在这里笔者只是根据现有的一些资料,对笑之研究的被边缘化的状态略略表述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主要则还是试图以此为根据,对尼采的有关理论作出自己的评价。
从研究的角度说,柏拉图已注意到了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自然的功能作用①,但较早深刻触及了哭、笑这两种情感与人根本的生存体验之间关系问题的思想家则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生来就有以文艺作品表述自己这两种不同情感的深度体验的强烈需要:“荷马不仅是严肃作品的最杰出的大师……而且还是第一位为喜剧勾勒出轮廓的诗人……当悲剧和喜剧出现以后,人们又在天性的驱使下做出了顺乎自然的选择:一些人成了喜剧、而不是讽刺诗人,另一些人则成了悲剧、而不是史诗诗人。”他认为,对于人类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喜剧和悲剧是在形式上比讽刺诗和史诗更高和更受珍视的艺术。”[1](页48) 但他旋即又指出,喜剧与悲剧相比较,在艺术的价值上先天地就是要略逊一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喜剧模仿低劣的人; 这些人不是无恶不作的歹徒——滑稽只是丑陋的一种表现。滑稽的失误,或包含谬误,或其貌不扬,但不会给人造成痛苦或带来伤害。”[1](页58) 像这样的效果比较起悲剧艺术对人灵魂的净化或陶冶,无论如何是大有不如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未在《诗学》中明言喜剧与悲剧的高下之别,但他在讨论情节、性格、命运的支配作用等文艺创作的基本问题时,则都是以悲剧创作作为文本的标准形态的,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亚里士多德这种对人类感情表达扬悲而抑喜的观点,对思想界特别是文艺思想的影响极其深刻。包括到后来康德、黑格尔的这方面的观念,也都深深地打上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印记。但康德、黑格尔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处则在于: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喜剧不管怎么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涵上都是完全独立于悲剧的,他也肯定滑稽的无害性即其存在的自然合理性②,而康德基本不谈喜剧,黑格尔则有以悲剧作为范本统一喜剧之审美内涵的倾向。黑格尔明确指出,要将笑与人的欢乐情绪分开理解,就是说,有一些笑是不值一提的,与人的崇高理念相关的、事实上属于非自然形成的那种“笑”才是关乎本质的:
人们往往把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混淆起来了……人们笑最枯燥无聊的事物,往往也笑最重要最有深刻意义的事物,如果其中露出与人们的习惯和常识相矛盾的那种毫无意义的方面,笑就是一种自矜聪明的表现……此外也还有一种笑是表现讥嘲,鄙夷,绝望等等的。喜剧性则不然,主体一般非常愉快和自信,超然于自己的矛盾之上,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幸和不幸;他自己有把握,凭他的幸福和愉快的心情,就可以使他的目的得到解决和实现[2](页291)。
黑格尔发现,根据经典的戏剧理论,喜剧中的笑与作为人们正常感情中的笑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于是他按照自己思想观念,以喜剧性为价值标的规范了各种笑的类型。黑格尔的确是高明的。他的划分法,容易解释许多涉及笑的戏剧现象,并使得喜剧与经典的悲剧观念一起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性的戏剧观。只是,按照他的理论,像“笑”的情感中常常包含的对权威的否定、对正常秩序的颠覆、无尽的对性禁忌的调侃、空洞的形式游戏、表面的刺激等,很大程度上就被逐出了情感研究的话语系统了。在这种思维系统之下,连人类的情感也终于显得那么整饬而有秩序了,笑已自觉地成了悲壮、肃穆感情的配角。
启蒙时代以来,重视笑、喜剧独立价值的思想家也不乏其人。狄德罗、歌德等都可以算是杰出的代表。狄德罗甚至这样说:“喜剧诗人是最道地的诗人。他有权创造。他在他的领域中的地位就跟全能的上帝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样。从事创造的是他,他可以无中生有。”[3](页155) 但遗憾的是, 他们对笑的讨论大体都是点到为止,比起他们的悲剧理论在深度和说服力上相距甚远。比如狄德罗《论戏剧诗》中《悲剧的布局和喜剧的布局》一节,看上去论喜剧与悲剧并重,但实质讨论的却基本仍是“悲剧的布局”问题。
真正摆脱了悲剧理论的束缚,完全独立地从笑的本身机理来研究笑,并进而阐发笑与人的存在本质之形上意义的思潮也许兴起于19世纪的后半叶。波德莱尔1855年的名文《论笑的本质并泛论造型艺术中的滑稽》则可谓是开这思潮的前驱之作。在文中,波德莱尔一变既往以道德诉求评论情感表现方式高下的思维定式(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悲剧论始终隐含有一个道德的立场),转而从泛人性论的角度考察笑与人性的必然关系。他尤其对于笑和人性之恶的关系津津乐道。在他看来,艺术中笑的力量实际上得益于人性之恶:“笑是邪恶的,因而是深具人性的。”[4](页311) 在波德莱尔之后,从人性的自然而非道德的评判研究笑的作用,并对笑的自然作用给予充分估价,就开始成为学术思想界一股显见的潮流了,如斯宾塞、尼采、费希尔、李普斯、弗洛伊德、柏格森等人的研究都可归入此类。在这些研究、论说中,尼采的观点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事实上,他的有关见解在那时期却可能是最为深刻的,他综合考察了笑在文学艺术、政治、社会、心理等人类不同领域的活动情况,并从艺术形而上学的高度指出,笑和人类存在须臾不可分离。
二、笑的力量和痛苦的含义
在尼采所有对于《新约》的酷评中,有一句指责是这么说的:“一部《新约全书》连一个笑话都不曾有过。不过,凭这一点也就等于批臭了这本书!”[5](页116) 在尼采后期的思想观念里,笑俨然成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
应当说,尼采并不是完全出于修辞上的考虑才把笑的作用提高到这样的高度的。事实上,大笑、极度的欢乐,本来就是古希腊狄奥尼索斯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所谓狄奥尼索斯精神迸发的应有状态。当然,尼采也还根据自己的艺术形而上学的观念,赋予了欢笑以更丰富的内涵。就是说,在他的笔下,笑和自然、沉醉一样,既标示了人的艺术化存在之至境,同时也是一条大道,可让现实生存进行艺术化实践的大道。不过,在正式介绍尼采笑之理论前,我们首先应对其笑和快乐的概念略作辨析。一般地说,在尼采学说中,笑和快乐是一个等价的概念,大体上可以相互替代。但如果究其细微处,则笑表示了一种更为本原的肉体力量,它直接象征着一种闪烁着生命光华的征服意志,而快乐和痛苦则“起源于智慧的中部;它们的前提乃是无限加速的知觉、规划、协调、补充、推论。快乐和痛苦始终是推论现象,而非‘原因’”。“一切快乐感和痛苦感就已经把总功利性、总有害性当作前提了。”[5](页284—258) 因此,大凡在涉及走向超人、体味超越之至境时,尼采就会强调笑的本原力量的救拔作用,而很少提到快乐感。这一层分际,在他中期写作《快乐的科学》、《曙光》之时,还未表现得十分清晰,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后期笔记中,则是陈述得相当清楚的。
关于笑,尼采说,笑对于人来说,首先是一种肯定性的力量。它包含着一种巨大的勇气,肯定个体创造的无可取代,肯定人类所有的创造性的一切,可以把“‘快乐’的本质恰如其分地描述为权力的充盈感”[5](页313)。当然,人的这一切创造也许只不过是梦幻,但这已足够显示人的某种存在本质了,笑的勇气、宽容就在根荄处呵护了人的这种本质。尼采说,文艺复兴改造中世纪最可夸耀的一点,就是以笑取代了精神上无尽的悲伤感:
笑、理性、自然已经战胜那些进行存在意义说教的伟大导师,存在悲剧终于转为存在喜剧,“无穷的笑的浪潮”——借用埃席洛斯的话说——最终将淹没这些伟大的悲剧角色。在“矫正性”的笑声里,人性就总体而言随着那些阐释存在之意义的导师一再亮相而改变。人性现在又多了一种需要,即需要这类导师和存在“意义”的理论竞相出笼。久而久之,人变成一种富于想象的动物,比其他动物多一种生存条件:必须时刻坚信,自己能够弄明白为何存在。如果没有周期性的对生活的信赖……则人类不可能又如此的茂盛[6](页43)。
不过,有关于笑,尼采在某些场合又说,它不是简单的肯定,不只是权力意志的简单呈现而已。笑时常包含着否定的意味,“笑意味着幸灾乐祸”[6](页184)。但这种否定不同于悲观主义的生命虚无论,也不同于基督教学说出于永生的企盼而扼杀现世的生命存在,它是一种生命的大智慧。它是参透了生命与存在的底色之后,以无畏来对抗绝望的一种潇洒。在尼采看来,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即像查拉图斯特拉那样能够成为超人预言者的人们,他们的生命中总带着这样的笑声:
他们全都留下了一个启示:获得最美的人正是那些并不尊重生活的人。当普通人一本正经地对待这片刻的生存时,那些走向不朽的人却知道如何报之以奥林匹亚式的大笑,或者至少使用一种高贵的轻蔑打发它。他们带着讥讽的微笑走向坟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身上没什么可埋葬的[7](页2)。
因此,在尼采看来,笑在最根本处,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圆融的境界。它是肉体快乐最直接、最本真的反映。它几乎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各种既有的形而上学学说可能对生命状态的压抑,因此它又自觉地反对着这种压抑。在笑声中,肉体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丝纤维都得到了自然的调动,这本身就是生命在舞蹈,“只有跳舞能使我说出最高贵之物的象征”[8](页133)一言以蔽之,笑的一切都是值得人们用其生命整体去体味的。下引一段话虽然是一段诗性的表述,但如果我们把握了尼采笑论的内在逻辑,其大意还是不难领悟的:
你们应当学会尘世慰藉的艺术——你们应当学会欢笑,我的年轻的朋友们,除非你们想永远做悲观主义者;所以,作为欢笑者,你们有朝一日也许把一切形而上学慰藉——首先是形而上学——扔给魔鬼!或者,用酒神精灵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来说:
“振作你们的精神,我的兄弟们,向上,更向上!也别忘了双腿!也振作你们的双腿,你们好舞蹈家,而倘若你们能竖蜻蜓就更妙了。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自己给自己带上了这顶王冠,我自己宣布我的大笑是神圣的。今天我没有发现别人在这方面足够强大。
“查拉图斯特拉这舞蹈家,查拉图斯特拉这振翅欲飞的轻捷者,一个示意百鸟各就各位的预备飞翔的人,一个幸福的粗心大意者——
“查拉图斯特拉这预言家,查拉图斯特拉这真正的欢笑者,一个并不急躁的人,一个并不固执的人,一个爱蹦爱跳的人,我自己给自己带上了这顶王冠!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的兄弟们,我把这顶王冠掷给你们!我宣布欢笑是神圣的:你们更高贵的人,向我学习——欢笑!”[9](页279—280)
当然,这也还存在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这就是笑的理论不能够仅仅关注笑与快乐的问题。显然,如果不能回答“笑”与它的孪生感情“哭(悲)”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问题,那这种笑的理论就是简单地为笑而笑,实践上是并不可行的。因为它已经无视于“哭(悲)”这另一种自然的感情了。尼采说,伊壁鸠鲁的学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学说,虽然它看上去立意至善,不欲令人遭受一点痛苦,但这却正是它的问题所在:“最雅致的伪装形式之一,伊壁鸠鲁主义……它会对痛苦草率从事,并且防范一切悲哀和深沉。”[10](页221) 正是基于这一点,尼采也发展出了一套颇成系统的关于享受痛苦的学说来作为其笑之理论的必要补充。虽然他其中的一些观点颇有些荒谬(由此亦可见他的笑的理念、他的整个艺术形而上学思想作为人生的指向不免太过单薄),但他设计的痛苦观倒也确实避开了传统涉及此问题时难免的苦行僧主义,对今人来说并非没有借鉴的意义。
虽然尼采认为究根地说来,“快乐比痛苦更原始”[5](页295),但如果在强调一切痛苦的经验最终都服从于“快乐的科学”前提下,那么,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承认,痛苦亦是“保持人之本性的头等力量”之一。对于伟人来说,“是痛苦给他们带来了最伟大的时刻!……对于痛苦,这些罕见之士必有自己的辩白……痛苦是保持和促进人之本性的头等力量,纵然它们是通过抑制安乐舒适、毫不隐讳地厌恶欢乐才具备这力量的”[6](页242)。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敢正视痛苦,正表示了一种软弱,一种“仇恨实在的本能”[11](页3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尼采指出,痛苦和欢乐、笑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适度的痛苦有利于快乐感觉的培养。至少它可以培养我们对快乐感觉的敏感程度。套用一句俗话:哪里没有痛苦,哪里就没有快乐。尼采这么说:“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忍受许许多多的痛苦,我们的胃已进化得相当完美,足以吞下如许坚硬的食物。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痛苦,我们也许就会觉得生活的宴席淡而无味;倘若我们不是如此敏于受苦,我们生活中的无数欢乐也就会不复存在了。”[12](页235) 另外,痛苦对于快乐感培养的重要性还在于,微小的痛苦的积累也许正是高度快乐享受到来的必要前奏,“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快乐是由有节奏、有顺序地微小痛苦刺激决定的。这样会造成权力感、快乐感的急剧上升”。尼采甚至借用人类的性行为的过程来说明这个问题:“男女交媾出现性快感就是如此……看来,微小的阻碍不断产生,又被不断地克服——这种以反抗和制胜为形式的游戏极大地激励了构成快乐本质的、充盈的、激荡的总权力感。”[5]页313—314) 虽然这样的论证逻辑有些荒唐——这明显是附会之说,但他的个人观点倒是由此而表述得十分清楚了:必要的痛苦培训是朝向那快乐目标的肉体保证之一(就是说不是长期精神上自我折磨所造成的痛苦),它并非是“权力感的下降”的标志。
某些时候,痛苦的必要性则在于它是生命意志冲动状态的附带产品。生命的冲动本身就带有一种危险性。也可以这么说,在某些状态中,尤其是在一些极端的状态中,痛苦或者欢乐其实已经无法命名人的彼种行动的价值内涵了。在这时候,如果斤斤计较于趋利避害,人就失去了生命中最纯真的力量,失去了超越的可能。尼采说:
卑贱者的特点,是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益,一心想着实惠和好处……和卑贱者相比,高尚者更不冷静,因为高尚、大度、自我牺牲的人屈从于本能,他们在最佳时刻便失去冷静。一只动物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幼仔,在发情季节追随母兽会不计死之将至,毫不顾忌艰危。它的理性暂时失落了,因为它的愉悦全部贯注在幼仔和母兽身上,而且担心这愉悦会被剥夺。愉悦和担心完全控驭着它,它会比平时愚蠢。高尚和大度者的情形与此动物相类[6](页45)。
根据上述的这些见解,尼采在心中始终为痛苦的控制技术保留了重要的位置。容易理解,不懂得痛苦的控制技术,也就意味着不懂得享受真正的快乐。这痛苦的控制技术是什么呢?尼采指出,其最重要者莫过于训练个人的自制能力。这种自制力当然不是服从于道德说教的自制,而是对自己的各种感官训练有素,能够以强力意志自如地调配它们去享受最值得享受之物。比如,当年的苏格拉底不到极渴时不饮水或其他饮料,这样,能使得他在饮水时最大程度地享受到甘霖滋润的快乐。“古代人的日常生活要有节制和审慎得多。它们知道如何弃绝和不去享受许多东西,以免失去自制。”[7](页132) 但令尼采遗憾的是,在现代社会里,古希腊人这种健康的自制能力却几乎完全失传了。现代人不但不敢直面一点点痛苦,简直可称为患上了“痛苦过敏”症[6](页82),而且, 还常常要借用“酒精和麻醉剂来消除神经紧张”。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堕落之处:“我们希望空气、阳光、居住地、旅行甚至还有药物刺激和毒品等能使现代人健康,但却没有想到需要任何对人来说是困难的东西。以一种公认的方式舒舒服服地健康和患病,这似乎就是我们的准则。”[7](页132)
简而言之,人越懂得自制,就越懂得欢乐;人越拘泥于琐碎的小满足,他离真正充盈的欢乐也就越远。——这就是尼采对痛苦感受强调的真正含义所在。
三、狂欢节的丰饶
尼采是近代最早注意到节日、喜庆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家之一。只是和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杜尔凯姆等人偏重于实证、 偏重于功能研究的方法不同,他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将节庆的意义提高到了关乎人类生存本质的高度。他认为,人的节庆活动首先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它为审美意义上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我们以前那些较高级的艺术——节日庆典艺术,会对我们的艺术产生什么影响呢?从前,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树立在人类节庆的长廊里,作为纪念崇高而欢乐时刻的丰碑。”[6](页116) 另外,节庆功能意义的重要方面还体现在,它昭示了一种可实践的人类艺术化生存的方式。在节庆这种全面肯定人性的社会组织形式里,人对其艺术本质的理解终于得以突破个人感觉臆想的局限,使得权力意志与肉体实践得到全方位的融合,使得生活本身就真正成为了艺术。“雅典人的节日庆典,他们制造了每天都看得见的令人振奋的华美而贵重的家具……由于把生活变得容易,我们失去了对于艺术的真正需要……在雅典人这里,生活每时每刻充满了责任、挑战、事业,这时人们就会知道如何尊重和追求艺术、节庆以及广而言之的教育,人们为了从它们那里获得欢乐而追求它们。”③ 当然,在尼采这里,古希腊祭祀狄奥尼索斯的狂欢节乃是一切喜庆节日的最高代表,酒神狂欢已包含着一切节日祭祀的奥秘这一点也是自不待言的。
在从事思想工作的一开始,在写作《悲剧的诞生》之时,尼采已充分注意到了节庆近乎神秘的保卫人类生命涵量的作用。在以后的20年中,他一直保持了对这个问题的相应关注。虽然有些具体问题的提法略有变化,但其中贯穿的思路却还是基本一致的。大略地说来,尼采主要是从全民性、仪式化、痛苦训练三个方面来关注狂欢节庆中那丰饶的生命秘密。
关于狂欢节与人的存在关系,尼采强调最多的,是其全民性的特点。狂欢节是全民参与的、抛弃一切束缚的节日。尼采认为,在这种全民介入的气氛中,人类内心中有一种普遍的神秘感情被唤醒,它推动着人直接去印证酒神力量的奥秘。此种感情的微妙丰富远远走在了人的理性的前头,甚至连柏拉图这样的大哲也察勘不透其中的奥妙,乃至以为是自己的理性出了问题,试图想要逃避那狂欢之力的烧灼:
面对欢乐的人群,我们如何能不感同身受和热泪盈眶?过去,他们的欢乐的对象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如果我们现在亲身体验到它们的话,它们对于我们仍然将是不存在的!天知道这些体验会把我们带到什么陌生的地方!在这些体验前面,我们的那些意见都化为了稀薄的云雾!要想不迷失自我,要想不迷失自己的理性,我们必须远离体验!柏拉图就是这样逃离了现实,投向了事物的暗淡的精神影像的王国:他知道自己充满了感性,知道这种感性的波涛如何轻而易举地就能吞没他的理性[12](页271)。
这令柏拉图都感到无法自我控制的“感性”是些什么呢?尼采说,它们主要便是“性欲,醉意和残暴”,这“人的最古老的喜庆之乐”。在这“古老的喜庆之乐”中,人的最强的生命力量得到了呵护和表现,人于是就成为了“美”的人:“兽性和渴求的细腻神韵相混合,就是美学的状态。”[5](页125)
但为什么全民性的氛围会注定具有这么大的魔力呢?尼采早年曾对此给出过一个解释。他说,根据酒神是宇宙最终的创生秘密这一点,日神式的“个体化原理”必然面临“崩溃”的命运[13](页5)。而“着了魔似的全民歌唱”就是推动着每个伟大的个体突破“摩耶”的幻象的最后一着和最强一着。因为在全民性中,人类的“整个生存及其全部美和适度”仿佛都得到了验证,“酒神冲动向他揭露了这种根基”。这样,在普天同庆的欢乐中,“在这里,个人带着它的全部界限和适度,进入酒神的陶然忘我之境,过度显现为真理,矛盾、生于痛苦的欢乐从大自然的心灵中现身说法”[13](页15—16)。
当然,关于上述的这些说法,很明显的,需要人们预先同意其“梵我不二”论的观念才是能够成立的。在后期尼采虽已基本放弃了对日神个体化性质的界说,但由于他始终将“梵我不二”论当作其哲学的一个不证自明的假设,因此我们在这里似乎不妨说,他早期的那些观念也构成了他后期对于全民性问题的界说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底色。
仪式问题是尼采另一个较多强调的狂欢节的内容。他的这种强调首先是与全民性问题有关的。所有的仪式活动都有一种强调全民(至少是集体)参与的性质,尼采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悲剧的秘仪学说,即:认识到万物根本上浑然一体,个体化是灾祸的始因。”[13](页42) 当然,仪式的意义决非仅限于此。尼采说,仪式之重要,还在于它总是伴随着相应的活动。仪式之为仪式就是它的一些场合性的活动总是和人们的日常活动有所分别的。尼采认为这种行动的意识就是至关重要的,已提撕了艺术形而上学的拯救秘密,按照他的肉体理论,行动所包含的意义自然要大于所有精神性的思考。因是之故,尼采说:“一种特定的估价和信念的产生乃是为着特定的‘仪式’和习惯,这与‘仪式’产生自单纯的估价这件事一样自然。人们应该锻炼自己,不是通过价值感的增长,而是通过行为;人们首先要能够有所作为。”他于是还对路德的宗教改革大为不满。因为路德的宗教改革取消了天主教对仪式的种种强调,主张“因信称义”。他评论说,这其实包含着一种权力意志的倒退。尼采说,如果单纯就“信仰”而言,“生命只表现在绝对避开自身,表现在向对立面的沉降,一味忍受幻觉”[5](页217—218)。
按照尼采的逻辑,仪式,尤其是宗教之秘仪值得推重之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秘仪总是特别强调等级秩序的。人们如果不是对地位的差别表现出相当的认可及服从的意识,没有任何一种仪式是可能的。据此,尼采盛赞信奉秘仪的人“从上向下看事物”,有灵魂的高度[14](页170)。
尼采认为,对人类来说,狂欢节的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牵涉到了痛苦训练的问题。但痛苦的练习乃是尼采笑的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关于节庆的功能作用的论述中,尼采明确指出,肉体的痛苦训练,直面生命之恶的巨大压力,亦正是狂欢节的题中应有之义。尼采指出:
“神所乐于见到的任何恶,都是被证明为有理由的”,史前的感情逻辑如是说的……把诸神想象为残酷游戏的朋友……希腊人那时知道的只是把残酷的快乐敬奉给他们的诸神,而不是裨益于他们的福祉的其他的愉悦的供品,这点无论如何是肯定的。那么,你们如何相信荷马让他的诸神蔑视人的命运呢?特洛伊战争和类似悲剧式的恐怖究竟有什么终极意义呢?毫无疑问,它们都被看作是诸神的节日欢乐了,而这位诗人在这方面比其他人更像“神”,想必他也认为,这些都是节日欢乐了……[14](页47)
和尼采有关笑的研究一样,他关于狂欢节的理论,长期以来,也是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的。虽然,他的理论绝不是没有可议之处,比如借仪式来发挥其等级制理论就很荒唐。另外,像以有些神秘主义色彩的“梵我不二”论来解释狂欢的全民性的魅力似乎也没说中问题之关键④,但无论如何,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看,他的观点确如空谷足音,在许多问题上都发前人所未发。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将尼采有关的散论条理化、系统化了,当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较尼采则更周密、更深刻。虽然政治环境险恶(只要读一读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和奥杜也夫的《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就可以知道在苏联官方话语中,尼采是一个怎样“反动的颓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巴赫金却不讳言他的哲学与尼采之间的联系。在1943年所作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评价问题……》中他坦然承认,他受到过尼采之节日文化研究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了他的理论基于尼采却超越尼采的一个关键点。他说,尼采尽管也注意到了狂欢节的全民性的特点,但尼采考虑相关问题时的出发点与总结点却是一个企图走向封闭的个人经验,尼采没注意到节日实际是一个蕴藏着“人类千年经验”的“非官方象征体系”。巴赫金说,相对于有限的个体经验,全民参与的狂欢节就是一个大经验,在这个大经验中,个体由对话走向了一个永未完成、又永远在完成中的自我肯定。这是狂欢节的全民性力量的真正拯救秘密所在:
[民间节日]⑤ 这里有着开放性和未完成性,记忆不等同于自身。只有实际意义、旨在应用的小经验,力求把一切都结束生命并加以物化,而大经验却力图使其复活(在一切都看到未完成性和自由,奇迹和启示)。在小经验里,只有一个认知者(其余都是认知的对象);只有一个自由的主体(其余都是死物),只有一个是活的未被封闭的(其余都是死的和被封闭的),只有一个声音在讲话(其余的都沉默不语)。在大经验里,一切都是活的,都在讲话;这种经验具有深刻的本质的对话性。世界关于我这个思索者的思考,更恰当地说,我是在主体世界中具有了客体性[15]页94—95)。
如果说在尼采的设计中,狂欢还不脱个人自我游戏的性质,与人的社会化存在特质有着一条深深的鸿沟,在巴赫金的设想中,这个问题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他借用对话理论,在狂欢观念中本质性地引入了“实践”这个环节。他透彻地阐明了,就人的存在实际言,“活的”“大经验”本来就是个人经验一个有机的本质性的构成部分,因此个人必须在与大经验的充分对话中才可能走向自我的完成。
如果单纯地依凭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人们不免担心,他的理论如何可能实践呢?在人们的想象图景中,他的所谓“艺术化”生存常常与一个绝望个人声嘶力竭的、命定孤独的、在旷野中呼告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侈谈“快乐的科学”,但“艺术化”生存却不能提供一点真正的快乐,除非他先用“醉”麻痹自己的神经。一个命定孤独的人当然不可能找得到真正的快乐。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在最基本的理论根基上弥补了尼采学说的这一缺陷,使得狂欢活动具有了某种真实的救度性的力量。不过,巴赫金这种对尼采思想的改造是否足以成为定论,仍是值得继续探讨的。比如说,巴赫金虽然引入了实践的概念,但他的实践理论却似乎缺少一个价值上的标向。他倾向于认为,依靠人的狂欢活动,人就可以自然地建立起合乎人性的活动方式以及其他精神活动的指归。但是,他是否对狂欢活动的自组织性质寄予了过分的希望呢?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价值标的的确仅仅依靠自组织的狂欢活动就能够完成吗?……当然,这些已经属于另一个研究领域的问题了。将话题转回到尼采与巴赫金在狂欢理论的学缘关系上,可以肯定,巴赫金至少点破了这样一个问题:以节日文化为轴心思考各种人类存在问题,或许本来就是尼采哲学的一个自然内涵。
尼采曾经设想,假如没有希波战争,希腊文化也许会孕育产生一种“最高的生活类型”。在这期间,“节庆和祭仪的结合是这时期的大事,改革本来可能由此开始。有了全希腊的悲剧思想,一种无比丰富的力量就会发展起来”。尼采说,狂欢节的这种“无比丰富的力量”是一种命运的力量。虽然,古希腊曾经把握住了这种力量的“高贵”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无非是对于命运命令的期待,“仅仅是为了看上去希望和努力才希望和努力”[7](页70)。 但这种命运之力毕竟是值得让人期待的,超人之力本来就是一种命运之力——也许,这才是狂欢节之丰饶的真正意蕴所在?
收稿日期:2005—08—11
注释:
① 参见陈中梅译亚里士多德《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59页注2。
②这一点是亚里士多德根本不同于乃师柏拉图之处。柏拉图所以赞成理想国中的公民要知道滑稽是以此可以避免滑稽,但真正的滑稽则是任何公民“都不得被发现在学习”的。参见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240页。
③ 译文据田立年译《哲学与真理》第130—131页,略有改运。
④ 笔者认为,如果从比较实证的角度看问题,那么,节日的全民性质的秘密也许是在于它通过纪念仪式和参与者的身体实践释放了丰富的社会记忆。请参阅康纳顿著《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⑤“[民间节日]”为引者通顺引文所加。
标签:尼采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中国节日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喜剧片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快乐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