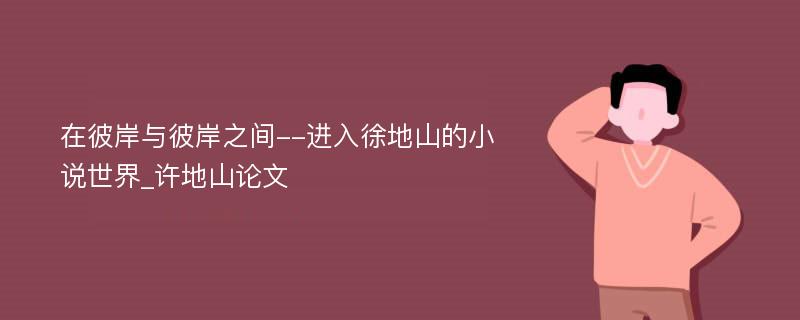
彼岸与此岸之间——走进许地山的小说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彼岸论文,此岸论文,世界论文,小说论文,许地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许地山(1893—1941,落华生),是五四以来的老一代的著名作家之一。他开始创作,正是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新的历史时期。如果说,鲁迅以它的《狂人日记》开拓了文学历史的新纪元;那么这时期优秀的作品尚且不多。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地山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的创始工作。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后,他便连续地发表了《命命鸟》、《商人妇》、 《换巢鸾凤》等小说。 不久, 小说集《缀网劳蛛》(1925)和散文集《空山灵雨》(1925)问世。他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影响。沈雁冰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落华生和叶绍钧、王统照同是在“民国十年到十二年的文坛上尽了很大的贡献的”。郑振铎认为,“在1920年到1941年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创作无疑地是中国现代文学上耀目的光辉”(注:郑振铎:《许地山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是的,在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叶绍钧是以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灰色、卑琐的人生而引起人们关注的;而王统照则以爱与美的强调唤起解读者的共鸣;许地山的作品却独树一帜,以“耀目的光辉”令人耳目一新。他既不像叶绍钧、王统照那样憧憬着理想的天国;也不像庐隐那样的苦闷与焦灼,而是大多在恋爱的外衣下,放进了他的人生观。这种人生的哲学具有着多元的文化意蕴,浓染着佛道乃至基督教的宗教精神。这种宗教的意蕴构成作品中的整体的文化氛围,也常常是他的人物的心灵依托。在《命命鸟》中他的人物就手里拿着《八大人觉经》,壁上挂的都是释迦应化的事迹,整日里生活在佛教的法轮学校里。更为重要的是,作家从生活的原点中汲取了艺术养料,而渗透着自己的人生哲学。有人说在他的作品中是把“儒家的义、佛学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爱混合在一起的(注:《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他对宗教的文化意蕴有所吸取,有所扬弃,转化为人生观、伦理观与心理情态。佛教的经义认为人世间充满了生与死的苦难,它属于此岸世界;因此要超越生死的境界,达到彼岸世界。许地山初期的作品《命命鸟》中不无这种因素。敏明与加陵便是如此。他们为了厌弃世间的苦恼,双双携手“走入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在月光水影之中,还听见加陵说:‘咱们是生命的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们快乐得很。’”这无疑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玄想。如果说,这在当时对于封建的教义也不失为一种反拨的话;这种所谓的抗争显然也是消极的。不过,就是在这一年,他所发表的《商人妇》则另具新意。作品中的惜官是被丈夫遗弃,并且被骗卖给印度商人,印度商人死后,他不堪家族间的种种欺压,离家出逃。罹尽种种磨难,却并无丧失对生活的信念。别人说他的命运实在苦,她反而说:“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来话说:眼前所遇到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总之,在她的人生哲学中,“要把眼前的事情看开”。因此,她排除了彼岸世界的空灵的梦,而执著于此岸人生的拚搏。《命命鸟》与《商人妇》以不同的生活信念,潜隐在许地山早期的作品中。
在我看来,许地山对于人生更为豁达、执著的态度,更为深沉地反映在他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作品中。这些作品粗粗的数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现实揭露与针贬的内蕴。这自然是一种负面的人生,但作家认为这种“不道德的事实”却可以使鉴赏者“见不肖而自内省”。有人说,这可能是作家所不擅长的,但却是作家所不能不为的。这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的趋动的结果。如《危巢坠简》中的《在费总理底客厅里》、《三博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本人是一个留学生,但他对一些留学生现象,却是并不认同的。这从那挖空心思写出来的学位论文《麻雀牌与中国文化》、《油炸脍与烧饼底成分》等命题中便可见一斑了。至于那位“前清监生,民国特科俊士,美国乌约克柯兰卑阿大学特赠博士,前北京政府特派调查欧美实业专使随员,甄辅仁”的名片,便使人感到特别的新鲜。倒是吴先生说得透底:“这人我知道,却没见过。他哪里是博士,那年他当随员到了美国,在纽约住了些日子,学校自然没进,他本来不是念书的。但是回来以后,满处告诉人说凭着他在前清捐过功名,美国特赠他一名博士。我知道他这身博士衣服也是跟人借的。你看他连帽子都不会戴,把穗子放在中间,这是哪一国的礼帽呢?”
与上述情态相悖,另一类作品则是正面的道德的宣示。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作家的伦理观,也可以看到作家泛化了的宗教意识。显然,这里是把佛教的慈善、基督教的博爱人间化了。同时也注入了五四文学中的平民意识。这里倾泄的是一种真情的“此岸”精神。久经传扬的《春桃》便大抵如此。自然,在这篇小说中,人们也许最初意识到的是它对传统的伦理习俗的反叛意识,然而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她那种兼容的爱与亲和慈善的博大胸怀,或者是二者的复调。像春桃这样的事迹,在中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的(据我所知,在北方的山区中这样的婚姻形式也是存在的);然而,它的精神却是许地山独特的发现。明乎此,就会了解到许地山艺术性格的独特了。春桃的生活情境是独特的,她一方面和苦难与共的刘向高结成特殊的因缘;一方面又迎来了失散后残废的丈夫,对于一个下层的劳动妇女,这时候她所选择的不是理念上的道德规范,而是生活。“爱只是感觉,而生活是实质的,整天躺在锦帐里或坐在幽林里讲爱经,也是从皇后船或总统船运来的知识。春桃既不是弄潮儿底姊妹,也不是碧眼胡底的学生”。她的生活中自然有情,更加有义。她像小院里的晚香玉一样,以自己为纽带构建成这个一女两男的别样的家庭。这也许正是许地山式的宗教人间化的艺术结晶。
二
作为一个小说家,许地山在现代小说史上另一个“耀目的光辉”,是他的异国风情。他虽然也写过北方地域色调的作品,但异国的氛围是浓郁而引人的。沈从文说:“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花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作者用南方国度,如缅甸等处作为背景,所写成的各样文章把僧侣家庭、民族风物,介绍得那么亲切。在作品中咖啡与孔雀,佛法与爱情,仿佛无关系的一切联系在一处,使我们感到一种异国情调”(注:沈从文:《论落华生》,《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104页。)。有人说这给他的作品以传奇的色彩。在我看来这似乎当从他的生活原点中加以解读。如所周知,许地山是祖籍台湾省的作家。爱国的信念使他的父亲在他童年时代便落籍于福建省的龙溪(即今漳州)。1912年任教于福建省立第二师范;次年便赴缅甸仰光中华学校任教师,1915年回国。此后,他还曾到过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学习。也到过印度这个佛教的古国进行访问。仰光的瑞大光宝塔,风光旖旎的绿漪湖,金碧辉煌,灿烂悦目。仰光的夜是迷人的。月华如水,洒满人间大地。各种热带的花木在银色的光波中超逸妖娆。许地山是一个内向性格的人。在异国他乡,他不仅领悟着自然风情;更为重要的是用心体察着人生的奥秘。他把自然的律动与生之苦闷,结构起来。这现实是实验的,更是一种生命精神的体验。这种生命体验使得他在作品中生成一种深沉的力量。由是,我们不妨说,异域情怀,在他的作品中,构建成互补的两重特征。一是那种异域风光,给予他的作品的是自然的底色,也是社会的底色。这种底色与人物的生活天地浓烈地炽成一种“神活”的世界,化成互为表里似的氛围。它是传奇的,又是本真的。是异域的,更是人物的。试看《醍醐天女》中的这段叙述:
我的家在旁遮普和迦湿弥罗交界的地方。那里有很畅茂的森林。我母亲自十三岁就嫁了。那时我父亲不过十四岁。她每天要同我父亲跑到森林里去,因为她喜欢那参天的树木,和不羁的野鸟和昆虫的歌舞。他们实在是那森林底心。他们常进去玩,所以树林里的禽兽都有和他们很熟悉。鹦鹉衔着果子要吃,一见他们来,立刻放下,发出和悦的问声他们好。孔雀也是如此,常在林中展开它们的尾扇,欢迎他们。小鹿和大象有时嚼着食品走近跟前让他们抚摩。
这里的森林、小溪、棕榈、鹦鹉、孔雀、小鹿和大象所构成的传奇式的王国,实际上都是作为人物的活动天地而出现的,是自然景观,也是社会景观。它们以异域的风情构成作品的底色。这是自然天性的涂抹,它以深厚而又凝重的氛围,给予解读者以浓厚的光泽。
然而这种底色还只是它的表象世界。就它的深层意蕴来说,无疑地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因此这种自然的律吕,佛国的天香与作家的心理奥秘会构成浑然一体之势。如所周知,生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是作家艺术创造的一个原点。生活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泛指,而是进入艺术家感知领域里的那一部分现实。正如庞德所说:“记忆犹如一个沿着海滨行走的孩子,你不知道他会捡起那个小石头珍藏起来”。艺术家的构思,包蕴着内部经验、外部经验、个人经验、群体经验乃至民族经验等等,是在这一基础上向艺术世界的一次远行。许地山的异域体验,正是如此。事实上,他在缅甸期间,就在寻求着宇宙和人生的秘密。他对朋友说:我“弄不透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在不断地思索着生、死、爱、恋之迷。也许正是这样,使他在燕京大学学习时,被同学视为怪人。据说其怪有三:一是天天在写梵文;二是不修边幅。每天总是穿着下缘毛边的灰布大挂,头发留得很长;三是吃窝窝头不吃菜而蘸糖。这使得他独来独往,落落寡合,被称为“许真人”(注:见宋益乔:《追求终极的灵魂——许地山传》,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这种怪,似乎和传统的名士风度并不相同;却从中可窥见几分道家的风骨和我佛态势,是苦苦的内心体验与人生奥秘探求的一种折射。循此,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毕业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较学,后来转到英国牛津大学仍然研究宗教史和印度梵文及佛学。这期间,曾以《道教思想与道教》的论文在伦敦举行的帝国宗教大会上做了报告,后来收入《帝国的宗教》一书出版。此后,关于宗教的著作有《道教史》(上)、《道藏子目通检》、《大乘佛教之发展》等等。可以说,宗教的神思构成他的人生体验的奥秘。由是不妨说,许地山作品中的异域情调,是与异国风情、宗教习俗以及宗教信念,浑然一体的。“他谨言慎行,若彬彬儒者;他奉佛唯谨,于佛大有缘法;他深通道家三昧,是道家良弟子;他注籍于基督教,是标准的基督教徒,亦儒、亦佛、亦道、亦基督(注:见宋益乔:《追求终极的灵魂——许地山传》,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他的《春桃》是在赴印度的途程完成的。这篇作品表层脱去了宗教的外衣,然而那神思依然为仁慈与博爱的观念左右着。因此,当我们解读许地山作品的异国风情时,是不能只就他的异国风光的表征为终结的。可以说,这种异域情趣是自然的律吕,佛国的天香,儒道交融,生命体验的统一。
三
应该说,许地山的艺术活力,与他的故事的叙述情景是分不开的。记得沈从文在《〈月下小景〉题记》中曾不无感慨的说:“中国人会写‘小说’的仿佛已经有了很多人,但是很少有人会写‘故事’”(注:《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在我看来,许地山便是擅长写故事的作家之一。这可能是文如其人的缘故吧!老舍在一篇五千多字的悼念许地山的文章中,曾七次提到许地山讲故事的特长。比方说,他有学问而没有架子,在朋友面前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出许多有趣的故事,从村夫走卒的俗野,高飞到学者的深刻高明,村的雅的都有,有时是脱口而出的笑话和戏谑,谈起来一整天并无倦容,听的人也整天不感疲倦。”(注:参见《敬悼许地山先生》,收《文人画像》,三联书店版。)在他的作品中,故事性也随处可以感受到。由于贪恋于故事情节的完整,有时可能感受到他的小说有些拖沓,有些“湾湾绕”,但他的小说确实是不温不火,有着徐徐道来的功夫。有人说,在五四以来的小说中,曾经出现过情结简化,思想深化的态势,那么许地山的小说恰恰补正了这种趋势。他的故事中曲折而多波澜。有着“峰回路转,有亭翼然”的景观。如果和现代小说比照,不完全的叙述,似乎已构成一种艺术魅力,那么许地山的小说显然在以完全的叙述见长。以《枯杨生花》为例。这里开头讲的是云姑婆媳寻找久不归来的儿子金成仁的事。出外以后,波澜叠起,儿子不仅不见,儿媳妇又在风浪中遇难。到这里一个悲剧已成定局。然而,云姑却被救助在一位朱老先生的家里。于是峰回路转,在这里她得以遇到年轻时的恋人思敬,从中引出一桩云姑年轻时跌宕起伏的恋爱故事。这可以说是故事中的故事,或者说是A、B故事的重叠与延伸,正是如此,故事由悲剧而转化为喜剧的结局,构成了大团圆的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故事曲折演讲中,精巧的细节,都是不容放过的。例如,由于寡居的云姑的儿子很像思敬因此引起许多闲话;而后来思敬的儿子砺生又很像云姑的儿子金成仁,这就构成了故事前后的结构的纽带,于是整个的故事才得以贯穿起来。从中可见,许地山在细微中结构故事的本事与审美特征。
许地山是以小说展开他的创作生活的,与此同时也不断地以小品文、散文诗的样式进行创作。后来结集为《空山灵雨》便是它的结晶。而这又是和作家的多种艺术智慧融会在一起的。作为一个作家,许地山不仅是智慧的,同时也通晓音律,会弹琵琶,正是如此,在小说创作中,他也不断地把散文的叙述与诗乃至音乐结合起来,造成一种互补的艺术表现智慧。我们从《命命鸟》、《换巢鸾凤》、《缀网劳珠》和《黄昏后》中都有可以看到这种印迹。这些诗曲或歌谣,有些是和作品的内蕴贴得很能紧的,或者具有现代影视中的主题歌的特征。例如,《缀网劳珠》中开端就是“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底网。/我把网结好,/还住在中央。”等多节的诗章便是如此。有些作品,显然又是与音乐俚曲结合起来的。借助音乐语言和诗的艺术张力,把小说的叙述与音乐的抒情交糅起来。造成独特的艺术效应。《换巢鸾凤》中一曲抑扬的“奥讴”,则把主人公祖凤与和鸾的情丝紧紧地糅和起来。
总之,当我们走向许地山的艺术世界时,宗教文化的氛围会扑面而来。它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景观,是作家的外部体验也是一种内部体验。它时时在变动着,从一个玄虚的彼岸世界,走向坚实的此岸的人生。这人生由于充满了荆棘,因而也显得更为丰富。希望对于他的人物来说,母宁是一种艰苦的考验,然而,她(他)们却像《缀网劳蛛》中的尚洁所说:“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它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底网便成了”。这种切实运作的精神构成他的作品的生命或动力。而异域的情怀,则赋予他的作品以光、色和审美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