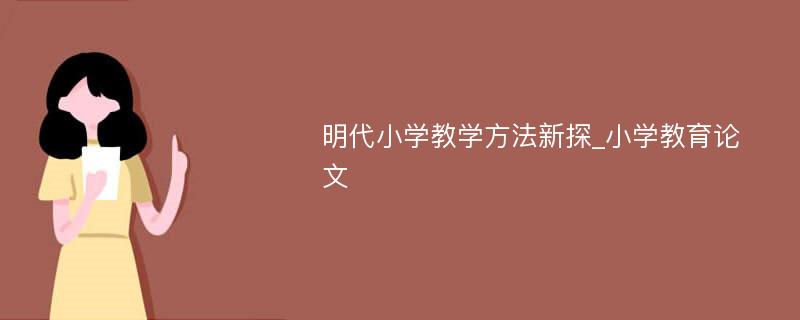
明代小学教学方式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教学方式论文,小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学方式是为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实现教育目标而在教学活动中实施的具体手段。明代小学,是包括社学、义学、义塾、武塾、乡校、家塾、蒙学性质的书院、小学等凡在程度上归属于初等教育形式的教育组织。明代小学一度兴盛于洪武、正统、成化、嘉靖、万历五朝,数量跃至19479所。其官办私立性质不一。明代小学在办学目标、 管理方式、教学形式、师生来源诸方面形成了一套系统,框范了明代小学在明代学校体系中的位置。明代小学在课程编制、教材选用上具备较大的灵活性,其教学方式尤具特色。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发现,分堂教学和社学大馆与小馆的复合教学在明代的小学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类复式教学与日课程安排也是其组织教学的方式。以下具体述之,以求方家指正。
一、分堂教学
在明代小学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种设堂分科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在中国古代小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1、分堂教学溯源
分堂教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胡瑗在苏湖设经义、治事斋进行教学的分斋教学法。这种教学方式在宋代究竟是否影响到小学,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在宋代的小学教育实践中,设斋教学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宋邓文原《东阳义塾记》载东阳义塾“为斋四:曰志道、进学、观善、时习。延礼训导二人以佐塾师,又设长是斋者二人,分小大学以阐教事。”[1] 则是宋代小学中设斋教学之明证。这种教学方式在元代似乎仍被运用。元牟《义学记》谓至元丁丑吴县范氏义学“会讲之堂匾曰‘清白’,东斋曰‘知本’,西斋曰‘敬身’,”[2]可资证明。
到了明代,设斋教学依然是小学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正德大同府志》李贤《新建大同义学记》谓天顺六年大同义学,“中为堂曰由义,左为斋曰时敏,右为斋曰日进”[3] 《嘉靖吴邑志》载正统十三年松江知府朱胜设立社学,“爰构大堂,及傍各两斋,斋聚百童而教焉。”[4]其余笼统提及社学设斋的材料亦颇常见。
应该注意的是,设斋并不意味着分科,设斋也完全可能仅仅是一种名目上区分,而不是实际教学内容上的区分。因此,尽管自宋以来设斋教学的方式为小学所大量使用,它是否具有分科教学的性质,我们并不能予以确证。
但是,不管这种分斋究竟是否具有分科性质,这种教学组织形式的存在,表明要求对小学教学实行分斋的思想一直是存在着的。因此,由形式上的分斋(比如为了教学的方便)而到实质上的分斋(分科),实际只要将分科的教学内容充实到具体的“斋”中去就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桂萼的“四堂分习法”是接受了过去的分斋教学法的影响的。[5]
2、桂萼的“四堂分习法”
从我们所见的材料来看,明确地主张分堂教学的是桂萼。[6] 桂氏字子实,号见山,江西安仁人。有关分堂教学的详细主张见于他的《社学图说》一文。
《社学图说》现存于《康熙安仁县志》卷七。考文中云“今辟存义仓之右废寺隙地”为社学,“以笃实长老二人”毕社学门左右,“以序出入”。而桂氏《成安政事记》云:嘉靖元年“冬十月,辟小学基于存义仓右”而设“四堂”,“前为门,令乡老长坐之,如坐里塾者法”,[7] 《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引《古今治平略》桂萼疏文中谓“余治县时;癖义仓之右废寺隙地……建为学舍,左右相向,中为四堂”云云。则《社学图说》当作于嘉靖元年桂氏任河北成安县知县时。《社学图说》的基本内容是将小学教学活动以“习礼堂”、“句读堂”、“书算堂”、“听乐堂”[8]教以不同内容。其中:
“习礼堂,以《经传通解》及陈详道、杨复考定者为图,曰胎教图,曰父子接礼图,曰童子图,曰冠礼图、曰士相见礼图,曰昏礼图,曰子事父母图,曰妇事舅姑图,曰祀先图,曰乡射图。皆金壁辉煌,令可娱目。以一师掌之。诸童子进学,即率见先生,习升降拜揖坐立之后,即授一图,指示点画,令其通晓。即此可以见礼器,即此可以辨杂服矣。”
“句读堂,内容榜管子《弟子职》,用朱子所定者,亦列四图,日讲一图;次及《孝经刊语》,教以句读,令其粗熟即止,必令无苦乃善;仍讲朱氏《小学》一二条。”
“书算堂,榜六书法,日止教一二[9],即以上下四方、 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教授之,亦不宜多,令其意易通而已。”
“听乐堂,内置鼓、鼙、笙、罄、投壶,师章射礼乐,或教以鼓节,或教诗歌,或击鲁薛之半以与投壶,或击薛鼓之全以习射仪。日讲一事,则所以养其德性、养其血脉、养其耳目心志者无所不有,而非僻之技亦无自而至矣。”
不难看出,四堂的划分,乃是以分科的方式将教学相对集中于某一场所。这种方式使教学活动在一单位时间内内容相对集中,从而在加强教学效果上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首先是将不同的学习内容(学科)置于不同的堂室中讲习,根据桂氏的设计,四堂的分科教学并不是将学生区分为四类而分别教育之。其次,每天每科学习一遍则为即日之课程。对以四堂教学的小学来说,其学生每日均须进入各堂学习。桂氏云:“以上四堂一遍,则日蜅矣。复自书算堂一名,略复归旧,以次至句读堂、习礼堂,而一日之事华,复于门塾左右序出。”第三、分堂教学的日课程设计有具体的实操演练,有适合儿童身心特征的形象的图示,有醒目的标语。由此可见,“四堂”分习实际也是桂氏安排小学日课程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桂氏所设计的分堂教学法,实乃导源于他对小学教育课程设置的主张上。
分堂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与范围上被应用?据《嘉靖宁波府志》卷七载“奉化县东社学,嘉靖六年增厅及乐、书、算等堂各三间。”《嘉靖九江府志》卷十张楠《九江府小学记》:“爰度小学基址,鸠工庀材,遵行图制,前创习礼堂三间,次句读,次书算堂,间如之;又次听乐堂,五间。”《万历汶上县志》卷二:“邑之社学,……各置挂桂公萼之学范焉。”“学范”即四堂法,汶上志载之。[10]由此可见,桂萼的四堂法对明代教育的影响也相当广泛。
不仅如此,桂氏的四堂法似乎被衍化成另外的分堂教学方式。《嘉靖宁州志》卷七载嘉靖十二年,知州蒋芝奉制立小学,“有明经、论治、习礼、听乐四堂”。内容上异于桂氏之书算、句读、习礼、听乐堂,蒋芝的小学课程涉及了明经治事。而同书卷十八蒋芝《小学成序》云:“宰臣建白,明诏郡县,遍置小学。书算、句读,达世学古;习礼、听乐,淑渐中和。”则所谓明经、论治、习礼、听乐四堂教学法受桂氏四堂法之启示。
分堂教学以桂氏的四堂法为典型,它为分科教学奠定了基础。
二、在城大馆与在乡社学的复合教学
在明代,还有一种在乡社学学生轮流进入在城社学大馆学习的教学组织形式。这种形式首为魏校所实行。他在檄令广东地方兴建社学的命令中,对这种形式作了详细的规定。
根据魏氏的说法,社学大馆的设置,实因“各里社学馆舍浅狭,读诵虽存,礼学尽废,故特建各隅社学大馆,以为诸生学习礼乐之所”。[11]但事实上,社学大馆内的教学并不限于礼乐,其实也包括了诵读。[12]
社学大馆所承担的任务之一,便是轮流教习本隅各里的学生。其法:
每前一日,学师(社学大馆老师)隅内生徒各里点一二名或三四名,共辏六七十名或百名,同一日会斋肄业。每日晚,命名里生徒一人用一小纸贴写其本里次日当坐斋生徒姓名,归往其家报之,明日本业赴学,即带自己名贴送回学中交纳。其余班未至者,各回本里教读学舍读书或归本家读书。[13]
可以看出,各里生徒轮流往本隅社学大馆坐斋学习,意味着社学大馆的教学实际是为了督促、检查、扩大、强化在乡小学的教学,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在乡小学的教学内容,同时无疑会扩充在乡小学的教学内容。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显然有着它的长处,一方面,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乡村小学,因而各小学的教学状况很快反馈到社学大馆,从而对社学大馆调整教学方案具有直接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社学大馆的教学本身是乡村小学教学的强化或系统化,因而社学大馆在执行其教学方案,从而贯彻社学大馆所服务的教育方针、扩大它对社会的影响范围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其突出的缺点是,一教学内容有些重复;二大馆对乡村小学控制过强,影响各乡村小学教师自身能动性的发挥。
魏校所设计的这种组织方式,除了他本人在广东的实践外,在明代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黄佐在设计小学教学组织方式时采纳了魏氏以社学大馆统各乡小学的主张。[14]叶春及则对它稍微作了一点变动。其主要变动有两方面:一是社学大馆不是固定的立于城内各隅,而是“于各都标一大者为大馆”,即以其规模实力强者来确定。这种变化,使社学大馆便于在乡学生上学。二是社学大馆不再是用于轮流教习在乡学生,而是“帅子弟之试有司者而祗教之”,即专门用于教习乡村社学学生之考选儒学的场所。[15]社学大馆这时比之在乡社学,职能扩大。质量提高、层次上升。
三、类复式教学
依照现代的教学理论,复式教学是指把两个年级以上的不同程度的学生编在一个课堂里,由一个教师在同一教学时间单位内使用不同教材交替实施教学的方式。在明代的小学教育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种与复式教学颇为类似的教学组织形式。它是按学生年龄大小及认知水平的高低,教师在同一教学场所对他们实施区别对待的教学活动。由于它在部分课程的教学上具有复式教学的特征,我们称之为“类复式教学”。
根据我们所见资料,明确规定要在小学中实施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是魏校。在给广东各地官民的告谕中,魏氏不止一次地提出了他对小学教学的具体组织形式的设计。由于小学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学生认知操作水平的差异。因此,对学生的教育就应该予以区分。正根据这一点,魏氏要求在小学教学中,对年龄大小不同的学生应区别对待。
在主课教学上,魏校主张“量其少长,或以《童蒙训》或以大学之道白直教之”,“教毕,仍命复位坐看记所教《蒙训》之类。年小未能看者,教之诵记。”在歌诗课教学上,“年小未能歌者,但令诵记听歌而已。”[16]
很显然,魏校主张对学生“量其少长”而教以不同的内容,这一点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复式教学而不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指教师针对学生的特长而施行教育,以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展,魏校的“量其少长”而施教,则把儿童按一定年龄阶段予以划分而对之实行不同的教育。
既然要“量其少长”而施教,则必定在课堂上要对学生予以分组或分班。尽管魏校没有明确地按学习年限和学习水平来划分年级,但在他的小学教育方案中,对学生实际是有着分组的。按照他的主张,小学在开学前一日,教师“列生徒长少之序挂于门内东西两壁”。次日早学时,学生依序分班。这种分班固然不一定就构成为年级,但至少在区分儿童年龄上有着直接的效用,在将儿童分为不同的年龄组而实施区别教育上也是非常有效的。可以推断,魏校所主张的“量其少长”而教学,是利用了这种序分的,而且必定有着两个以上的年龄组儿童在同一课堂内接受不同的教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六书九数五御之法”的教学上,“年小未能讲习者,在位诵记《蒙训》或教以嘉言善行。”[17]则完全是以全然无关的内容来施行教学的,在这一点上,这种课堂教学方式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复式教学”并无多大差异。
魏校的主张后被黄佐、叶春及用于他们对小学教学组织形式的设计中。其中在算数教学上,黄、叶均言“年稍长者教以《九章算法》。年小者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教授之,”[18]其教学内容便因学生年龄大小而有所不同。
导致小学中实行这种类复式教学的基本原因,除因学生数多、教师数少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外,学生接受教育的年限当亦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因素。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民间子弟入社学读书,“纵使穷忙,也须十月以后在学,三月以后回家。如此三年,果其材无可望,省令归业。”又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照此推断,则在三年学当中,必有不同年龄的学生在同一课堂中受不同内容的教育。
就明代社学而言,类复式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完成其社会教化的任务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采取类复式教学的小学在接收教育对象上范围较广,因此,它对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具有直接意义。另一方面,采取此种教学方式,使一个教师可以承担多重教学任务,从而在扩充小学教育影响上也具有重要作用。
四、明代小学的日课程安排
日课程安排是将每日的教学区分为几个时间单位,并规定在特定教学单位内以相对固定的教材进行教学。在明代,小学日课程安排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主张大体是由一些重视小学教育的思想家提出的。
魏校、叶春及、黄佐、沈鲤、刘宗周诸人的课程设计已经包含了他们对小学日课程安排的基本主张。归纳起来,他们在日课程安排上的主张大体有二
其一,基本上以每日按早、中、晚顺序排课。其中魏、黄、叶是以早学、午学、晚学而将小学每日教学活动区分为三个时间单位。刘宗周的划分较为繁琐,有晨起、早膳后、辰刻、午膳后、申刻、夜里诸时间单位。
此外,吕坤亦将小学每日教学活动区分为早晨、早饭后、午饭后和日落后几个时间单位。
据此,我们可以推知:明代小学对教学时间单位的划分基本上是以一日三餐吃饭时间为区分原则的。
其二,各教学时间单位内课程内容的安排亦有规定。我们将所见及的日课内容安排罗列如下:
王阳明: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他的小学课程包括直接的道德教育课程、歌诗、习礼、读书四大部分。其中歌诗、习礼、读书又是从属于直接的道德教育课程的。
桂萼:授课(习礼、句读、书算、听乐)、复习(听乐、书算、句读、习礼)
魏校:早学包括课前行为仪态监察、教师讲课《童蒙训》或大学之道,学生看或记诵新讲内容;午学包括课前行为仪态监察、抄写诗章、歌咏记诵听歌诗章;晚学包括课前行为仪态监察、习礼、教琴、讲习六书九数五御之法、记诵(童蒙训)或教以古人嘉言善行、有余力者听其习乐歌咏。各课皆包括课堂行为监察。特课包括谒圣(每月朔望)、习射(每月初五、十二、二十七日)。课外包括温习新学。课外行为仪态监察、行为自我检束。每月朔望放假。根据魏校的观点,小学教育课程之所以要不专于念书对对而要强化道德品格培养方面的内容,其根据即是小学教育乃大学教育之根本。在他看来,“民生有欲,非教不善”,故“欲一道德,同风俗,必当后刑罚,先教化”。
崔铣:晨起到酉时考德、释疑、授书、讲书、习字、习对、诵书。日中歌诗。三日一习礼。
黄佐、叶春及:早学以诵书、正句读包括《小学古训》、《孝经》、《三字经》、《四书》为主要内容;午学中以歌诗、习书数包括抄录吟诵《诗经》部分篇章和古体律待绝句、习六书法、学《九章算术》为主要内容;晚学以温书、习礼仪包括习礼仪、温习早学及教习《小学》、《日记故事》为内容。
同魏校所设定的课程结构相比,黄、叶作了如下变动:
第一、把魏校早学中的由教师讲解《童蒙训》或大学之道改成讲解《小学古训》、《孝经》、《三字经》、《四书》乃至治经。
第二、把魏校午学当中抄咏诵《诗经》具体化为诗经当中的《鹿鸣》、《菁莪》、《关睢》、《四牡》、《伐木》、《棠棣》、《蓼莪》、《采繁》、《采苹》、《南山有台》《缁衣》、《淇奥》诸篇。而把魏校晚学当中的书数移入午学。
第三、把魏校晚学当中以习礼仪为主要活动改为温习早学所读书、习礼。
吕坤:“平明到学,背书完,读新书,吃饭后略会出门松散一二刻,然后看书、作文、写仿华,仍读书。午饭后,再会出门松散一二刻,仍读书,日落后,分班对立,出对一个,破题一个,即与讲考。然后放学。”“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
沈鲤:
课程设置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小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不以科举为目的
第二、课程设置的核心应为修身养性
第三、义学课程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
这三个基本原则中,第三个原则与义学具体课程的设置直接相关。
沈鲤的义学课程结构以早学、晚学而分,早学包括授书、正字、讲解《小学》、诵书;晚学包括习仿、对句或作文、讲书、背书、讲贤孝勤学故事一条,吟诗一首;另外每日写疑难字或文藻字。早晚学行为仪态监察、讲书与故事、吟诗皆含道德教育。朔望考试、每岁腊月望日总考。
刘宗周:单纯就小学的具体教育实践而言,“六艺”教育被刘宗周当作了小学教育课程的全部内容。所谓“六艺,示所习也”所指即是。
家塾课程设置:《家塾规》是从“考德之要”和“修业之要”两方面来规定家塾教育课程的。“修业”是指学业课程的学习。其课程安排大体如下:
a、晨起书《纪过格》
b、早饭后温书旨、候讲
c、辰刻讲书
d、讲毕后,各自演绎所讲书的内容
e、午饭后读有关讲书的优秀时艺
f、申刻治古书一册:本经之外另治一经、 读性理著作或秦汉韩柳欧苏文字
g、晚上看《通鉴》五页
h、三六九会课
i、朔望考一月课程勤惰,考毕歌诗,歌毕闲评古今道理
我们将上述内容再予抽象,即可得到刘宗周对“修业”课程的基本规定:
A、道德行为的自我检束
B、学科学习
C、学业评估
可以看出,刘宗周对家塾课程的设计比较突出地体现他小学、大学之教一贯性的思想。
在上列诸人中,除刘宗周将“歌诗”设于朔望日外,其余人的日课安排中均有“歌诗”,但在时间安排上有一定差异。在其他内容的安排上,有所不同。
考察以上诸人的日课安排,我们发现他们对教学的主导内容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王阳明将歌诗习礼作为目的在于“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的辅助课程,则背书诵书或课仿便构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桂萼的日课安排首习礼,则习礼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便跃居首位。魏校、黄佐、叶春及皆将诵书、正句读安排在一日的黄金时间,则其构成为教学的主导内容是不言自明的。他如崔铣、沈鲤、吕坤皆以背书、授书兼及习字作为教学的主导内容,而副之以歌诗习礼。独刘宗周的安排较为特殊。辰刻开讲,诸生质疑问难。午后阅书,申刻治经史等,则一日之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学生自学。而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放在申刻之后。此种安排,显然不适宜于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学日课安排上,明代已有人触及了日课安排要注意儿童的身体卫生问题。吕坤在小学日课安排上主张饭后让儿童出门松散一二刻,理由便是“少年脾弱,饭后不可遽用心力,恐食不消化也。”
明代小学的教学方式中,在城大馆与在乡社学的复合教学形式除外,其余三种方式在明代以后的教育活动中被发展并予以肯定下来。日课安排被科学化,并形成为每日的教学常规运行方式,复式教学在当代农村教育中曾广泛运用,分堂教学后发展为学科教学。中国教育的源在哪里?我们不曾去凭吊自己的祖先,但我们却应时时记住历史所给予我们的积淀与回音。
注释:
[1][2]《吴都文粹续编》卷七、卷十三
[3]《正德大同府志》卷十三
[4]《嘉靖吴邑志》卷十三
[5]桂萼之接受了分斋教学法的影响应该说是肯定的。 考桂氏正德十三年曾任武康县令,武康属湖州府,而湖州正是胡瑗实行分斋教学的地方。桂氏在武康的经历,无疑会对他的思想有影响。
[6]魏校在广东建社学大馆,其中即置有“习礼堂”。 但大馆目的仅在于“教诸生学习礼乐”,故谈不上分科教学。
[7]《嘉靖广平府志》卷四
[8]桂氏任武康县知县时亦曾令该县各村兴办社学。 然考《嘉靖武康县志》和《嘉靖浙江通志》,武康无有社学建于存义仓之右者,故《社学图说》一文不可能作于武康。
[9] 《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汇考十·明三》引《古今治平略》桂氏疏文作“一二字”。
[10]《古今治平略》谓明世宗时,大学士桂萼上疏,以小学四堂法为言。则小学四堂法实被大力推行过。
[11][12]《庄渠遗书》卷九《谕民文》
[13]《庄渠遗书》卷十《河南学政》:“今拟与提调官经画其事,原设社学,各因其旧,以为小馆,各延教读,聚附近子弟读分其中,……别设一社学大馆,延请明师,专以礼乐为教。小馆生徒各量地远近为节班轮入大馆,弦歌揖让其中。大馆师与讲德书中大义,令其退而服行。”可资佐证。
[14]《泰泉乡礼》卷三《乡校》
[15]《石洞集》卷七《惠安政书·社学篇》
[16][17]《庄渠遗书》卷九《谕民文》
[18]《嘉靖香山县志》卷四、《石洞集》卷七《惠安政书·社学篇》
标签:小学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