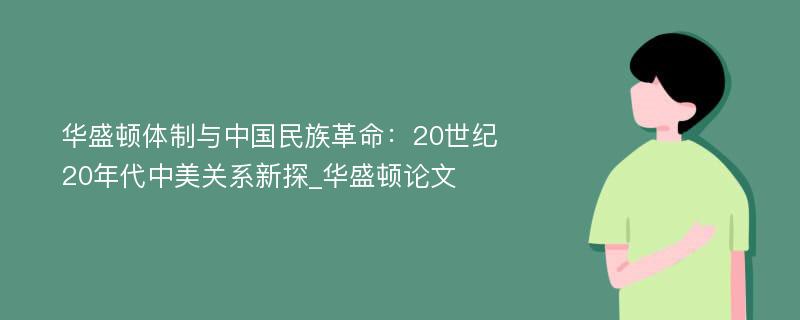
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盛顿论文,中美关系论文,中国论文,国民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在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中,20年代仍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学者对华盛顿会议的考察大多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关注大国,特别是美日在远东的争夺以及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条款的是非评价;对大革命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则受革命史学的影响侧重于揭露美国如何分化中国革命(注:参见陶文钊《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夕中美关系研究述评》,资中筠、陶文钊主编《驾起理解的新桥梁》,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66-71页。)。近年来虽有学者扩大视野,对大革命时期美国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别是美国决策内部的分歧和争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对华盛顿会议也进行了新的评价(注: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3章,重庆出版社,1993年;罗志田《北伐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和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但研究的视角仍没有超越经典意义上的中美双边外交关系,同时也没有把20年代的中美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本文试图变换角度,关注当时国际关系格局与中国国内政治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一视角至少可以发现:其一,华盛顿会议不仅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外国在华特权问题的决议案,实际上还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思想,有学者称之为“华盛顿方案”(Washington Foermula),学界对此还缺乏充分的研究;其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中国国民革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正是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的不满和反抗成为大革命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三,中国国民革命不仅宣布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所谓华盛顿方案的破产,实际上也动摇了作为华盛顿体系重要构架的大国一致原则,为后来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国民革命对华盛顿体系的影响是中国通过自身的变化影响国际关系的显例。本文即试图从以上三个方面对20年代的中美关系进行新的梳理。
一 解决中国问题的“华盛顿方案”
众所周知,中国问题是华盛顿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看来,中国问题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是如何避免由于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导致在华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二是如何应对五四以来中国日益高涨的要求改变不平等地位的民族主义浪潮。自一战结束以后,这两个问题就日益突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设想,可以通过在远东建立一种国际新秩序代替19世纪欧洲列强建立的旧秩序解决这些问题。在威尔逊看来,旧秩序是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为手段,以谋求独占利益或势力范围为目的,以双边协定特别是秘密外交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形式,国际和平的维持有赖于各国力量的均势或曰平衡。这种旧秩序下的均势实际上极不稳定,极易酿成一战那样的世界战争。因此列强应放弃老一套外交手段,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保证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不是以各国势力的不稳定平衡为基础,而是建立在贸易自由、公开外交和集体安全基础上。就远东而言,这一秩序应是建立在各国共同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扩张,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共同分享中国的原料和市场,以及同时保证中国得到必不可少的资金和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其核心是在美国领导下,通过与日本及其他大国的合作,并且使这种合作国际化和制度化来维持远东的和平。威尔逊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新秩序“将防止大战的爆发,并将有利于贫弱国家(中国)的逐步发展”(注:〔美〕欧内斯特·梅和小詹姆斯·汤姆逊合编《美中关系史论》,齐文颍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77页。)。美国学者迈克尔·谢勒曾这样概括威尔逊新秩序的内容:“所有工业化国家以开放性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来代替战争和殖民掠夺,作为使‘门户开放’政策国际化的工具,国际联盟将保证工业化国家获得欠发达国家的原料和市场的权利。从理论上说,国际联盟成员国也要尊重各贫弱国家的有限的政治独立。”(注:〔美〕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徐泽荣译,三联书店,1985年,45页。)
美国希望中国稳定和获得发展是基于这样一种利益考虑的,即:同一战前的土耳其曾引起欧洲列强的垂涎一样,中国的贫弱和动荡对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具有诱惑性,为日本出兵中国攫取独占利益提供机会,是引起列强摩擦和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因此保证中国的稳定和有限度的繁荣是必要的。美国设想,中国在西方列强共同监护下,按照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并在西方共同援助下获得稳步的发展,最终加入国际社会。
因此在美国看来,这一秩序既不同于19世纪欧洲列强建立在赤裸裸殖民掠夺基础上的旧秩序,也不同于列宁宣布的通过革命手段彻底打破和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的激进道路,美国倡导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是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的比较温和的国标自由主义秩序。这样一种建立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温和的新秩序不仅可以避免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冒险,而且还可以使中国获得适度发展,满足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并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沿着自由主义的和非革命的方向发展,从而最终解决中国问题。
美国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大体始于一战结束前夕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和国际联盟计划,经过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列强签订《四强协定》和《九国公约》最后完成。华盛顿会议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完成了这一新秩序的构建:其一,各国承诺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在对华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其二,实现门户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各国承诺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其三,中国政府承认华会制定的原则,即中外关系的改变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成,并认同美国为中国设计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这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框架,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方案”(注: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Octagon Books,Inc.,1968),pp.12,151-152.)。
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九国公约》中。在该约中,各缔约国承诺不在中国谋求独占利益和特殊地位,并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同时《九国公约》初步拟定了大国协商的机制,规定,‘无论何时,遇有某种情形发生,缔约国中任何一国认为牵涉本条约规定之适用问题,而该项适用宜付诸讨论者,有关系之缔约各国应完全坦白,互相通知”(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3),三联书店,1959年,220页。)。除这种协商机制外,美国贯彻其合作政策的主要工具是新国际银行团。银行团在1924年5月的一份对华贷款政策通告中宣布其政策为,“在中国的经济和财政事务中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并称其是“实施”华盛顿会议“尊重中国主权,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给予中国自由无碍之计划开发其经济资源及维持一有利巩固之政府”政策的“特定工具”(注:H.G.W.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1924(The Tientsin Press,Limited,1924),pp.809-811.)。
各国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以及给中国自由发展机会的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九国公约》中。该约第一条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第六条规定,“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3),217-219页。)。这些规定并非完全是空头支票。美国深刻意识到,华盛顿体制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衰弱、分裂的中国通过解决内部冲突实现稳定的能力。只有中国实现稳定和统一,新银行团协定所体现的通过经济合作防止日本对中国进行政治干涉和军事掠夺的政策才能真正实行,并可为《九国公约》制定的原则提供物质保证。因此应使中国从列强进一步蚕食的威胁中解脱出来,给予发展机会,使其在列强的监护下,实行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司法改革,然后逐步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并最终放弃治外法权。而这一切将使美国拥有中国的4亿顾客,从而极大促进美国商业的繁荣。
但是,中国获得这一机会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前文提及的华盛顿方案的第三方面,即:条约关系的改变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并俟中国“在自己家里建立秩序”(put her own house in order)后方能进行,而且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必须走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道路。这一思想隐含在《九国公约》以及华会通过的一系列有关在华特权问题的决议中。所谓“在自己家里建立秩序”包括: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代议制政府,形成一套完备的英美模式的法律体系,按照自由贸易原则改变税收制度,即废除厘金。用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话说,美国希望中国建立的“秩序”意味着和平变革或“循序渐进的进程”,同时“它意味着门户开放.对美国财产和侨民的保护,以及根据条约进行贸易和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同时这一秩序还应允许美国“在中国土地上驻扎着军队,在中国的江河上航行着炮舰”(注:Thomas A.Paterson,et al.,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Lexington,Mass.:D.C.Heath,Co.,1985),p.342.)。显然美国这种为中国的废约设定前提条件的政策可以有双重作用:一是尽量拖延恢复中国完全主权,以维护现状和既得利益,这体现在会议最后作出的解决治外法权、关税控制等有关外国在华特权的一系列决议案上;二是迫使中国走上美国式的自由主义道路。如前文所述,《九国公约》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缔约各国协定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美国学者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认为,“尽管该款没有明确阐明中国承担着在自己家里建立秩序的义务,但这一义务是隐含着的。如果再考虑到列强拒绝对条约体系进行任何实质性修改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华盛顿方案回到了美国的一贯思想,即在中国具有按照西方的效率标准管理自己的能力以前,列强不会放弃他们的条约权利。华盛顿方案的新特征不过是在中国从事改革工作时,列强愿意让中国保持和平。”(注: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p.12.)
尽管美国试图通过所谓的华盛顿方案避免美日冲突和应付一战后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并且从表面上看,这一方案比过去通过战争赤裸裸地宰制中国的旧秩序多少文明些,但这一方案无疑仍是极不合理的:它不承认中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造成的,它承认并继续维持不平等条约的合理性,容忍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侵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废约要求充耳不闻。换言之,列强不过是一些“洗手不干的有教养的盗贼”,他们并不打算放弃已经到手的赃物,而只是承诺今后不再趁火打劫(注:Pollar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New York,1933),p.236.)。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是列强交出从中国掠夺的赃物,即废除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享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而且,华会通过的少得可怜的一些有利于中国的协定和决议,有关国家也未打算认真履行,由于后来中法之间的金法郎案的争执,法国以不批准华会各项条约为手段要挟中国,实际上直至1925年8月华会有关中国各项条约和决议才正式生效,因此“一切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9页。)。由此而言,美国一手策划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华盛顿方案并不能抚慰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主义者断然“拒绝接受华盛顿会议签订的条约作为战后对外关系的框架”(注:Akira Iriye,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Asian Relations(New York,1967),p.145.)。
二 中国对华盛顿方案的反应与国民革命的兴起
美国深信华会是一个成功的会议,一举解决了远东问题。因此会议结束时,美国认为,华盛顿方案“足以满足中国人”在修约方面的“愿望”(注:Kellogg to the American Delegation,Sept.9,1925,U.S.State Department,ed.,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as FRUS),1925(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Vol.Ⅰ,pp.842-847.),“列强处置中国问题,不能再有进步,前途须中国自为之”(注:《美人对鲁案结果之得意》,《民国日报》(上海,下同)1922年2月10日。)。言外之意,华盛顿会议已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要求改变中外关系的愿望已经初步得到满足,以后就看中国自己如何作为了。但与美国的初衷相反,中国多数舆论对华盛顿会议表现出深深的失望。
在中国舆论看来,华会不仅没有取消列强在华既得特权,相反它使这些特权进一步合法化,因而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峻。时人的这一认识虽然有夸大的成分(注:不少学者认为,自1839年中国与列强打交道以来,华盛顿会议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而且争回了某些东西”,因此认为自华盛顿会议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比华会之前更加危险似有夸大之嫌。参见陶文钊《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夕中美关系研究述评》,66-68页。),但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外关系的一个侧面。罗家伦即认为,华会“最可恶”之事就是:“各国在中国所侵略之赃物,在此次会议以前为非法的,在会议以后为合法的,不但各国互相承认,而且中国也承认”(注: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东方杂志》19卷2号,42-43页。)。而《四国协定》和《九国公约》提出的大国合作被认为是共同宰制中国的大国同盟,是把中国视为列强的共同保护国,两约一出台,就遭到中国舆论几乎一致的谴责。孙洪伊于1921年12月27日发表《存亡大问题之警告书》,指出两条约的实质是把中国“夷为”“四国协定下之共同保护国”,国民应该“绝对否认”(注:《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7日。)。国民外交大会在华会闭幕后也发表通电.指出《九国公约》的目的在于“在政治上认中国为各国共同保护之地,在经济上认中国为各国共同侵略之场”,是中国“最大之危险”。通电请求美国参议院否决《九国公约》(注:《电请美参院否决九国公约》,《民国日报》1922年2月20日。),并对《九国公约》逐条进行驳斥:
“华府会议,业已闭幕,我国以北廷派遣代表参与其间,鲁案不得正当解决,二十一条不能宣告废除,以及撤退外军,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借地,自定关税,种种希望毫无结果。此故意计中事,而新予我最大之危险者,为《九国公约》……合而言之,在政治上认中国为各国共同保护之地,在经济上认中国为各国共同侵略之场。分而言之,中国的主权独立,并领土的、行政的完全,固属当然之事,不待他国特别订约以尊重之。若特别订约,则名为尊重,实即保护……设中国与他国订约,以担保英法美等国之主权独立,并领土的行政的之完全,其愤怒惊骇,亦无异于日人也。树立及维持有力而巩固之政府,中国人民应有充分之机会,何劳他国与之。况他国为扩张其国势起见,固常愿我国有一腐败如北廷之政府,假定各国以军械供给北廷,或新银行团以借款供给北廷,皆可谓已与以最完全且无障害之机会矣。由吾国人视之,为完全乎,抑为不完全乎?为障害乎,抑为无障害乎?国际间只有相互之义务,无片面之义务,我国在各国工商业之机会既不均等,而各国在我国工商业之机会,独求均等,已失平衡之地位。益之以租借地为收回,领事裁判权未取消,外军未撤退,关税未自定。而开放门户,更不啻喧宾夺主矣……是第四项所规定者,实此后利益均沾之代名词……第二条系一方使各国中之一国或数国,不得单独保护,或单独侵略他方,使中国永远不得脱离此数国之共同保护,或共同侵略。第三第四第五条系第一条第三项之具体规定。第六条……不过抄袭国际公法之陈文,而其恶果,则我国于国际上反失活泼灵敏之作用……第七八九条,系辗转规定前次各条之适用与效力。姑不赘论。总之该约显为共管中国之初步。”(注:《外交会解释九国公约之危险》,《民国日报》1922年2月22日。)
对《九国公约》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激进的共产党人。蔡和森称《九国公约》是“美帝国主义协同英、日、法各国帝国主义用门户开放、国际共管的网络宰制中国”的“吸血同盟”(注:《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161页。)。
华会有关其他问题的处理也遭到中国舆论的严厉抨击:“数年来全国所呻吟憔悴之山东问题,已在日本掌握,二十一条除曾为他国(指美国)利用一次外,即奔而不顾;关税问题则以前的议案全推翻,现在连增加至百分之七点五尚无希望,追问百分之十二点五与独立”,更危险的是,“路德四条,将来为处分中国之公式;四国协商为共同侵略中国之同盟;新银行团为开辟中国之工具”。因此中国在华会上是“天天上他国的当,天天候他国摆布”,已经“在罗网之中日深一日”(注: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42-43页。)。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舆论看来,华盛顿会议的“效力’”就在于“给中国立了一种共同宰制共同管理的根本大法,使他们以后的侵略皆有所根据而成为法律化”(注:和森:《由华盛顿会议到何东的和平会议》,《前锋》2号,1923年12月1日。),它“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而“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托拉斯的奴隶”(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因此与美国舆论认为“中国之地位远胜”华会之前相反,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认识是中国的危险形势更甚于华会之前:“不特国民多年来之痛苦与日本及各国在中国之侵略,不能救止,且因此使其加一重保障更为巩固”(注:《绝望之华盛顿会议》,《民国日报》1922年1月11日。),“我国既有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为亡国根蒂,今又扩充为各国共同保护条约,由共同保护而共同管理,再进而共同处分,吾恐不出十年,即将索我于枯鱼之肆矣”(注:《存亡大问题之警告书》,《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7日。)。对这样一个会议,中国除反抗外别无选择。
不仅华会的有关决议遭到中国舆论的同声谴责,美国孜孜以求的推行其合作政策的重要工具——新四国银行团在中国人民眼里不过是“各国共同侵略与开辟中国之武器”(注: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42页。)。新银行团虽然一再声明,“干涉中国内政并不在银行团计划之内”,“银行团作用仅仅是在中国当局请求的情况下帮助其重建经济和金融的平衡”(注:H.G.W.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1924,p.811.),但正如法国学者白吉尔( M.C.Bergere)指出的,银行团实际上“仍然遵循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并且只能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注:白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中国的政治生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辑,65-66页。),因此新银行团很快遭到中国舆论的反对。1921年底,《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文章,揭露各国企图利用银行团对华贷款在经济上瓜分中国的阴谋,指出,新银行团“所耽耽注视着,纯在于今后吾国万劫仅余之经济利权耳。其所孜孜计虑者,纯在于联络列强,以包办方法瓜分吾国此等万劫仅余之经济利权耳;纯在于用资本家宰制劳动家之手段,宰制吾人耳”,因此“美人提倡新银行团之目的,可一言以蔽之曰:均沾中国之经济利益耳”,不过是“群俄虎而分一脔,吾族无噍类矣。”(注:茹玄:《新银行团与经济瓜分》,《上海总商会月报》1卷6号,1921年12月。)
在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眼里,列强在华盛顿会议后对待中国的政策也证明,华会提出的所谓“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不过是一个骗局,而渐进废约则是列强维护在华特权永久性的幌子。在临城事件交涉中,美国等列强采取强硬政策,威胁要严惩中国,竟提出了包括停止增加关税、扣留关余和盐余、续索庚子赔款、建立有外交使团监督的护路军等惩罚性措施,意大利甚至主张援引庚子例派联军入华等,完全把华盛顿会议上的承诺抛诸脑后。这不过证明了华会所标榜的“人道正义”原则、“保障弱小民族的公道政策”都是骗人的鬼话,一旦找到机会,就“露出真面目”,并“借口匪乱”,“进一步做公开野蛮的侵略政策”(注:巨缘:《文明的列强,野蛮的中国?》,《向导》26期,1923年5月21日。)。
在关税和治外法权问题上,列强也“自食其言”,召开关税会议和组织法权调查遥遥无期。虽然后来关税会议于1925年10月终于召开,法权委员会也于1926年1月开始法权调查,但在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看来已为时太迟,况且“在这两个会议期间,中国所目睹的仅仅是一队黑得发亮的汽车,插着各国的国旗,在中国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疾驶而过,去参加无数个宴会和观光旅行”,中国要求立即实现关税自主和取消治外法权的愿望无一实现(注:F.Gilbert Chan and Thomas H.Etzold,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New York,1976),p.8.)。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从1922年到1925年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标榜给中国带来福音的华盛顿方案实际带来的根本不是稳定与和平,而是内乱和衰败。
综上言之,华盛顿体系在其建立伊始就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这种反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等列强否认中国的贫弱和动乱是西方侵略的结果,但中国民族主义者鲜明地提出中国苦难的根源即在于外来势力的压迫,“国际帝国主义既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因此“中国国民运动的真意义在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注:和森:《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向导》16期,1923年1月18日。)。第二,拒绝接受华会确立的列强间处理中国问题的政策和原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看来,“什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什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富源;什么机会均等就是均分中国的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他们的帐房和监工者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利益。”(注:《短言》,《共产党》6号,1921年7月7日,转引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86页。)而所谓的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不过是“各帝国主义互竞的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三,否定美国提出的华会使“中国地位远胜于三月之前”的说法,指出,正是华会“更陷中国于最危险之境域”(注:《国民外交大会对外宣言》,《民国日报》1922年2月25日。)。这样,打破华会建立的国际秩序,挽救民族于危亡即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应有之义。第四,拒绝美国提出的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道路以及在中国实现稳定和统一后才能考虑逐渐撤废在华特权的原则,提出对不平等条约必须采取“革命性的”手段,进行“根本的解决”(注:陈友仁语,参见FRUS,1926,Vol.Ⅰ,pp.851-852.)。中国民族主义者从华会得出的一个重要“觉悟”是“现在世界任何国家,无容许弱小民族及国家申述不平之余地,中国国民欲希望解除种种束缚,惟有杀出一条血路,死中求生”(注:元冲:《华会中各国真目的及中国问题被牺牲原因》(二续),《民国日报》1922年2月6日。);而对于国内政治,也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注: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47页。)。所谓“根本改造”就是打倒军阀,所谓“死中求生”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概言之,就是“人民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外而反抗列强内而解除军阀之政权及武装”,而“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废力气”(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的宣言》,《向导》82期,1924年9月。)。
中国民族主义者反对华盛顿方案的实质是反对华会对中外关系原则的安排,井“主张建立一种将美国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者排除在外的新‘秩序’”(注:Paterson,et al.,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p.342.)。与美国的初衷相反,华盛顿方案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美国为它设计的道路,相反,在列宁理论和苏俄革命模式传人后“成为中国抛弃西方列强”,转向国民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注:Werner Levi,Modern China's Foreign Polic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3),p.167.)。
三 美国政策的调整与华盛顿体系的危机
从华盛顿会议到五卅运动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华盛顿方案确定的基本原则。1935年11月,曾在20年代后期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马慕瑞(J.V.A.MacMurray)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若干新变化)的备忘录,对1925年前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思想做了回顾。马慕瑞称: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同意在对华关系上采取联合行动,其最终目的是取消所谓不平等条约加诸中国的种种限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列强将恪守“从中国放手的政策”(hands-off-China policy),这体现在《九国公约》中,其目的是赋予中国机会以承担长期延滞的改善国内条件的任务。此外列强达成谅解,可以通过国际银行团向中国联合提供贷款以援助中国,或提供其他具体的援助。如果中国在改善国内条件方面获得进步,列强将通过让步作出反应,直至条约加诸中国的限制完全取消。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自行其事,破坏或企图撕毁条约,列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它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事。美国的政策是,在中国“在自己家里建立秩序”,以及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司法体系和其他制度保证美国侨民的安全和权利以前,不要指望条约的条款有任何实质性改变(注: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introduction.)。正是从这一政策出发,美国一再拖延履行华会有关关税和治外法权问题的决议,对中国民族主义者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充耳不闻。
但是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的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风暴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政府,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美国学者多萝茜·博格曾这样评价五卅运动对中外关系的影响:“在条约体系形成的数十年间,列强坚信,他们不是从中国获得更多的特权,就是可以维持对他们有利的现状。但是在192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人民带着出人意料的力量和决心坚持外国列强必须放弃他们在中国一直拥有的特殊地位。外国政府任意欺辱中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有条约关系的列强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处于防守而不是进攻的地位。问题不再是西方国家和日本向中国要求什么,而是激昂的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中国向他们提出要求。”(注: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p,1.)
美国认识到,由于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华盛顿会议设想的自由主义模式和渐进修改中外条约体系的前提——中国的稳定已不复存在。中国的形势与1922年相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原有的以中国建立一个统一而稳定的政府并实施自由主义改革为修约前提的政策已无法维持。在五卅事件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Kellogg)“越来越相信,除非中国获得一些让步,否则它将单方面解除条约限制”(注:L.Ethan Ellis,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1921-1933(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8),p.299.)。面对中国提出的远远超出华盛顿会议限定框架的民族主义要求,面对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条约体系的努力,美国“面临的选择只有有限的几种可能”:其一,它可以通过使用武力维持其特权,但这需要派遣大批军事力量远征中国,而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不允许的;其二是放弃美国在华利益,而这又是美国所不情愿的;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寻找第三条道路,改变传统的对华政策,即通过对中国民族主义要求作出一定的让步,来缓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消减激进派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压力,同时引导中国民族主义走上温和的自由主义道路,以维护美国在华的根本利益。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关税和治外法权问题上。1925年6月25日,北京政府照会参加华会各国,提出修约要求。凯洛格在给驻京代办迈耶(Mayor)的电报中说,中国政府的照会“提供了一个证明美国愿意以同情和善意的态度考虑修改现存条约的机会”(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Mayer,July 1,1925,FRUS,1925,Vol.Ⅰ,p.767.)。6月30月,凯洛格在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修约要求持积极态度,并将敦促其他列强尽快召开关税会议和开始法权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提出,在关税和治外法权问题上,列强要做的不应局限于华会有关决议和条约的条文,而应超出条文范围,即将召开的关税会议除讨论增加附加税、裁撤厘金和修订中国关税税则问题,还应制定一个给予中国完全关税自主的计划和方案,而法权调查委员会也应提出一个逐渐取消治外法权的计划。美国的这一主张是6月30日凯洛格等人与施肇基会晤时由远东司司长詹森(Nelson T.John)提出的(注: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FRUS,1925,Vol.Ⅰ,p.769.)。 1925年7月1日,凯洛格在给迈耶的训令中指示,在与其他国家代表讨论如何答复中国政府6月25日照会时应表示上述的愿望(注:Kellogg to Mayer,July 1,1925,FRUS,1925,Vol.Ⅰ,p.767.)。凯洛格还声称,未来关税会议达成的协定应该比华盛顿关税条约中设想的“走的更远,并更具广泛性”,而且“关税会议不过是全面修改条约的第一步”(注:Kellogg to MacMurray,July 28,1925,FRUS,1925,Vol.Ⅰ,p.802.)。
凯洛格在给总统的报告中还称,他已要求驻华使馆把列强达成的复照文本寄回国务院,“如果它不符合我们的愿望,我宁愿单独对中国复照”。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尽管我渴望与其他列强尽可能地保持一致,但我感觉到中国的危急形势需要采取某种行动来消解公众的激烈情绪。”(注:Thomas B.George,The Open Door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American Policy and China,1917-1928,Ph.D.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1977,p.244.)不仅如此,他后来还训示马慕瑞向与会各国代表表明,如果会议无果而终,各国不愿接受美国的方案,美国将单独与中国谈判(注:Kellogg to MacMurray,October 5,1925,FRUS,1925,Vol.Ⅰ,pp.854-856.)。美国这样做实际上也等于率先背离华会确定的大国合作精神。
凯洛格在给美国参加关税会议代表团的指令中谈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直到几个月前,本政府以及其他列强政府都一直以为,(华会)关税条约的条款足以满足中国人在修改关税方面的愿望,但是最近几个月的事件表明,这些条款作为渐进实现关税自主的一个步骤并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期望,中国人民要求摆脱列强强加给他们的种种强迫性限制以获得自由的愿望并不限于关税问题,而是包括其他很多方面,在这些方面他们同样要求做出彻底的改变。我对中国人民的目标表示同情,并希望对我们与中国的条约进行修正,直至其公正可行……在我看来,就关税问题而言,特别会议的行动应超越关税条约所严格限定的范围,讨论整个协定关税问题,甚至包括旨在最终实现关税自主的建议。我还认为,美中条约中的其他问题也应该尽早重新考虑,而特别会议可以作为将来考虑这些问题的第一步。”(注:Kellogg to the American Delegation,Sept.9,1925,FRUS,1925,Vol.Ⅰ,pp.842-847.)
1925年1O月21日,关税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基本贯彻了凯洛格的思想,于1925年11月19日通过决议:各国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解除中外条约中的关税束缚,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生效。各国不再将裁厘作为中国实现关税自主的先决条件,但同时中国政府声明在关税自主的同时将厘金“切实裁峻”(注:外交部编《外交公报》54期,专件,1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应该说,这一决议超出了华会规定的讨论范围,它是在中国高昂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通过的,但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也不无关系。这一决议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后来南京政府与各国谈判新的关税条约提供了依据。
长期以来,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维护条约体系和保护在华利益是美国的一贯政策。正是在这种政策思想下,美国在1923年底和1924年初粤海关危机中与其他列强一道出动军舰,以武力阻止广州政府分享关余和收回海关,而且美国出动兵舰最多,态度也最强硬。但是五卅运动后,面对中国大革命的浩大声势和美国国内舆论的掣肘,美国认识到,用陆海军力量强行维护美国条约权利是不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炮舰外交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只能以外交手段维护在华利益。这一政策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武装力量的任务只限于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在不可能或实际上无法给美国人适当保护的地方促其撤离,在形势紧迫时“海军部队将用武力救援美国侨民,但不应用武力来保护他们的财产”(注:〔美〕伯纳德·科尔:《炮舰与海军陆战队》,高志凯译,重庆出版社,1986年,28页。);第二,美军应避免干涉中国的军事行动,除非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而不得不这样做;第三,避免在维护条约权利方面对其他列强承担义务。美国的这些政策思想体现在1925年以后一系列事件的处理上。
1925年6月沙基惨案后,广州各界发表通电,强烈要求英法撤退沙面水域的外国军舰,交还沙面租界。英法当局紧急商议,建议列强联合以武力保护租界。8月初,马慕瑞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提出,美国应同英法一道参加保卫沙面的工作,但国务院拒绝了马慕瑞的建议,指出“美国军队不应参加保护广州沙面的工作”,美国海军的任务只是“把美国侨民撤到安全地点”,其财产则指望中国政府来保护(注:MacMurray to Kellogg,August 14,1925;Kellogg to MacMurray,August 15,1925,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The National Archives,1960,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Microcopy,No.329.893.00/6507.)。这是美国放弃武力护约政策的开端。在1926年3月的大沽口事件中,凯洛格致电马慕瑞,明确指出美国“总的政策是不用武力来实施条约权利,只有在保护美国人生命时才有必要使用武力。”(注:Waldo H.Heinricks,Jr.,American Ambassador:Joseph C.Grew and the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Tradition(Boston,1966),pp.112-114.)
1926年9月底,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宣布,在北京关税特别会议尚未签订任何关税条约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单方面征收华盛顿会议所允诺的附加税,这无疑是对不平等条约提出挑战,引起了列强的极大恐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极力主张各国应以强硬立场阻止国民政府的这一行动。他认为广州政府不经列强同意以及无视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关税条约规定的条件是对华盛顿关税条约的公然践踏,是民族主义者对海关关政完整和整个条约体系的挑战,“其目的是间接地、一点一滴废除条约体系”。他建议国务院立即采取“坚决的”(resolute)行动,必要时与英日一道出动海军保护广州海关,或采取其他适当的强有力的防卫措施,“以阻止广州当局征收此税”(注:May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3,1926,FRUS,1926,Vol.Ⅰ,p.866;Thomas Buckley,"J.V.A.MacMuray:the Diplomacy of An American Mandarin,"Richard Burns,et al.,ed.,Diplomats in Crisis:U.S.-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1919-1941(Santa Barbara,1974),p.37.)。但马慕瑞的这一强硬立场不为国务卿凯洛格所赞同。凯洛格在10月5日回电中指出“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与英日讨论海军示威或采取其他强有力措施”,他指示马慕瑞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广州政府实际征收此税,只提出抗议即可。凯洛格告诫马慕瑞无论如何都不要发起或参与保护广州海关的“强硬政策”,如果其他国家不同意美国只提抗议的立场,可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单独行动(注:Kellogg to Mayer,October 5,1926;Kellogg to Mayer,October 22,1926;FRUS,1926,Vol.Ⅰ,pp.871,885-886.)。由于内部分歧严重,列强始终无法采取一致行动,海军护关只好作罢。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并开始向西方在华利益的中心——长江下游推进。上海公共租界一片恐慌,担心中国将以武力收回租界,英国建议各国以武力保护租界。马慕瑞对此甚表赞同,主张美国军队应承担“既保护租界完整又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任务”。但凯洛格反对马慕瑞的建议,国务院在回电中说:“如果目前上海的紧张局势需要美国海军出动登陆部队的话,就必须明确不误地认识到,这支部队的任务只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本政府不准备为了保护租界的完整而在上海动用海军部队”(注:MacMurray to Kellogg,Dec.19,1926;Kellogg to MacMurray,Dec.23,1926,FRUS,1926,Vol.Ⅰ,pp.662-663.)。
当时英国驻美大使表示,不管是否得到美国的支持,保护其公民的责任都将使英国“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公共租界中英国利益聚集的那部分地区(注: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p.275.)。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Chamberlain)在致国际联盟秘书长的信中也称,英国决心“不让汉口和九江的旧事在上海重演”(注:科尔:《炮舰与海军陆战队》,95页。)。但是国务院坚持美军不能参与保护租界。凯洛格告诉马慕瑞:“你必须理解美国人在感情上坚决反对本政府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除非为了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国内没有舆论支持我国政府为了维护公共租界的现状和完整而采取军事行动。”(注:Kellogg to MacMurray,Jan.31,1927,FRUS,1927,Vol.Ⅱ,p.65.)詹森在致驻沪总领事高思的信中重申,“美国没有人赞成用海军或陆军部队来维护条约在中国所导致的现状”(注:科尔:《炮舰与海军陆战队》,97页。)。
美国放弃以武力维护条约权利的政策,多次拒绝英国提出的对华强硬路线,实际上也就开始背离华盛顿会议上确立的在涉及对华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列强协调一致的合作原则。英国对美国背离合作精神的行为深为不满,并多次照会美国政府,但美国不为所动。在英国看来,美国的这种不合作行为“根本不替别人着想”(注:科尔:《炮舰与海军陆战队》,30页。),意在乱中图利。由于不同利益的分野,美国与其他列强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重大分歧。
实际上背离合作精神的不仅仅是美国。随着北伐军的不断推进,列强之间早已是竞争多于合作。从1926年下半年,英国和日本均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越来越背离华会规定的政策框架。1926年12月18日,英国政府向出席华会的各国驻华使节递送了一份被称为“圣诞礼物”的备忘录,宣布了英国对华新政策。备忘录主张各国“无条件应允”中国征收华会所建议的附加税,并建议各国发表一共同声明,废弃“中国经济政治非有外人监督不能发达”之意,一俟中国建成统一政府,即与之谈判修改条约问题,“以尽可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合法愿望”,并“情愿于中国自定国税新则一经规定宣布时,即行承认其应有得享关税自主之权”(注:《东方杂志》24卷3号,105-106页;Pollar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p.296。)。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给华盛顿条约签字国的一份声明中,阐明英国的政策是不再“坚持把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为同中国“谈判讨论修改条约和其他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先决条件。这是英国政策的重大转变(注:G.E.Hubbard,British Far Eastern Policy (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3),p.87.)。
英国的新政策使美国大吃一惊,也使凯洛格极为恼怒。为了走在英国的前面,凯洛格决定公开、全面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其结果就是著名的1927年1月27日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凯洛格声明所体现的政策变化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愿意尽快与中国讨论修约问题,而没有像华盛顿会议那样把中国的稳定、统一与和平作为先决条件;第二,美国准备“单独”与中国谈判,这意味着放弃了与其他列强协调一致与合作的传统政策;第三,宣称美国在华军队只是用于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等于声明美国在中国革命中保持中立,不以武力维护条约关系现状和干涉中国革命;第四,声明表示与“中国任何政府或任何能代表中国或代中国发言的代表谈判”,表明美国已不再认为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政府,开始改变只承认北京政府的政策,无异于公开表示愿意与南方政府发展关系。显然,美国在背离华会原则方面走得更远。凯洛格声明中表示“愿意以最开明(most liberal)的精神同中国办交涉”,并别有用心地表白“本政府在中国没有租界,并且绝不会对中国表现任何帝国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把美英竞争的态势表露无遗(注:声明全文见于Kellogg to Mayer,January 25,1927,FRUS,1927,Vol.Ⅱ,pp.350-353。)。
凯洛格以政策声明的方式把此前局限在国务院与驻华使领馆之间外交函电中的政策调整公开化。在随后的宁案处理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改变更是暴露无遗。
南京事件不同于中国人民收复主权的行为,它涉及列强在华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因此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震惊,也对美国政策构成严重挑战。一度率先调整对华政策的英国转趋强硬。英国外交部声称,“接受对在华外国人条约地位的攻击是一回事,而听任对外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进行直接攻击是另一回事”。言外之意,英国不能容忍对其侨民的攻击。“如果不对制造南京事件的中国人进行惩罚,类似的事件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发生,中国人就可能成功地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注: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p.422.)因此英国拟做出强硬反应,包括提出最后通牒和实行制裁。马慕瑞和美国驻南京领事戴伟士(John Ker Davis)也主张采取强硬政策。马慕瑞建议国务院将美国侨民撤出国民党占领区,然后“封锁上海以南所有中国港口,给中国施加压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有效措施”。马慕瑞警告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这一局势,那就意味着西方在东方的影响将立即崩溃。”3月28日,英、美、日三国公使经过讨论,拟向国民政府提出包括惩凶、道歉和赔偿等要求的照会,并要求限时回答,“如不服从,各国将保留采取他们认为的适当措施的权利”。这样的照会无疑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后来英国公使还提出各国应同意“在国民政府拒绝满足要求时实行制裁”(注:MacMurray to Kellogg,March 29,1927;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secretary of State,April 5,1927;FRUS,1927,Vol.Ⅱ,pp.166,180.)。
但这一方案立即遭到美国国务院的反对。凯洛格反对任何制裁及军事威胁手段,再一次表明美国在重大利益问题上决心放弃与英国的合作。 3月19日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宁案时说:“在中国不存在对我国人民的有组织的军事进攻。我们认为这些士兵这样做并非执行任何一个行使政府职能的当局的命令,而是乌合之众的骚乱。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凯洛格谈到美国对华增兵原因时解释说:“我们的部队不是远征军,他们不打算向任何人宣战”,“他们在性质上不过是一只警察部队,其使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我国侨民加以保护”(注:Kellogg to Gauss,March 31,1927,FRUS,1927,Vol.Ⅱ,p.97.)。4月25日,柯立芝又对报界说:“在(中国)目前的混乱和冲突中,我们充分意识到军队可能会暂时失去控制,也可能会伤害美国公民。驻扎在中国水域的我国军队只是为了防备这种结果的发生,做中国自己在和平来临时将做的事,我们不想实行侵犯中国人民的路线,我们在那里是为了防止中国人中无法无天之徒对我国人民的侵犯。动乱最终将会平息下来,某种形式的政府将会出现,这一政府无疑会准备对我们遭受的损害给予适当的解决。我们当然要维护我国政府的尊严,坚持对我国政府的威望给予适当的尊重,但我们的行为无论何时都是一个朋友的行为,我们无时不在关心中国人民的幸福。”(注:Bro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pp.320-321.)
柯立芝的这番说明是耐人寻味的。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谴责中国人对外国人生命和财产的“攻击”,相反把这种“攻击”看做中国革命中不可避免的事情,并认为美国应以耐心和理解的态度静观中国革命的结果,而不是以武力加以干涉。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凯洛格坚决反对采取通牒的方式和进行制裁,他在给马慕瑞的指示中称:“本政府不愿让照会载有任何含有规定时限的最后通牒性质的内容”,“美国政府对采取什么制裁的问题持保留意见”(注:Kellogg to MacMurray,April 2,1927,FRUS,1927,Vol.Ⅱ,p.177.)。
在美国的反对下,英、美、日、法、意5国于4月11日分别向陈友仁递交了内容相同,但没有回答时限及制裁威胁的照会,只提出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各国政府将至不得不采取认为适当之手段”(注: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398页。)。
尽管对美国政策的这种转变可以找出许多原因,如美国国内舆论、美国政策制定者如凯洛格和詹森的个性以及列强之间的竞争等等,但最重要的是20年代中叶开始的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压力。这种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浪潮使美国意识到,旧的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维护条约体系和在华特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政策的调整本质上不过是在面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强有力挑战时为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做出的明智的、现实的选择。正如孔华润所言,“国民党和共产党动员群众的能力意味着保留帝国特权将需要在华列强不断地使用武力,意味着美国公民的生命损失,而这不是美国人民或其领导人愿意付出的代价。因此他们开始退却,寻求与国民党中国的重新和解”(注:Warren Cohen,Empire Without Tears: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21-1933(New York,1987),p.83.)。
与在华其他列强相较而言,无疑美国的政策受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最大。其原因则在于美国对华外交一贯具有的温和色彩和较超脱的地位,美国在华利益的特点以及一战结束以后美国倡导的以尊重民族自决权为核心的国际自由主义思想。正是这些因素使美国能较迅速地对国民革命作出反应。这个问题需另撰文讨论,此不赘述。
美国政策的调整产生双重后果:其一,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适时地抛弃了遭到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反对的华盛顿方案,通过对华让步渡过了中国国民革命带来的双边关系危机,实现了新形势下与中国关系的调整;其二,就整个远东国际关系而言,美国率先迎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放弃华会达成的大国合作及一致原则,成为美日在中国问题上分道扬镳的起点,日本正是在既压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又可满足日本利益要求的大国合作模式名存实亡后走上了单独武力侵华的道路。华盛顿体系的最终破产固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但实际上在大革命后期主要列强背离大国合作原则,在对华政策上纷纷采取独立的路线就已表明这一体系出现了重大裂痕,九一八事变不过是这一裂痕扩大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就此而言,是中国的国民革命最早对华盛顿体系构成不可逾越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