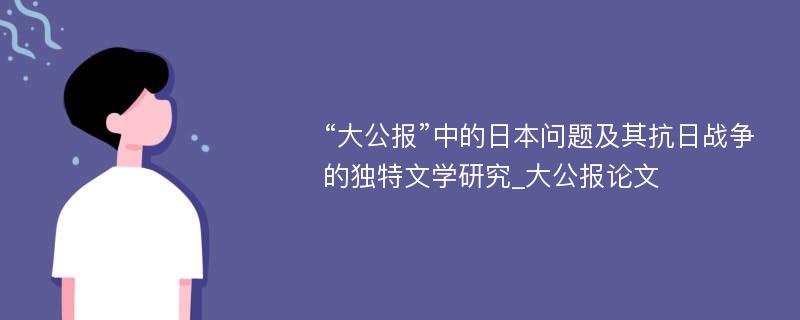
《大公报》的日本问题研究及其独树一帜的抗战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公报论文,日本论文,独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不但在新闻领域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它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与它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密切相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
《大公报》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九一八”事变前。早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刚创立之时,日本军阀侵华野心就已经日益膨胀。《大公报》的三位总编吴鼎昌、张寄鸾和胡政之都曾留学日本,对日本问题深有研究。他们撰写的社评和论文对中日关系的分析之深刻在当时就曾引起公众的瞩目,并且也被日本朝野所注意。1928年5月,日本军队制造的济南惨案后,《大公报》就已经预感到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略野心,并深感东北前途的危机,发表社评《东北对外关系之前途》,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发表言论呼吁中国政府和民众注意对日本军阀保持警惕。尤其是1931年的特大水灾发生之后,全国上下集中精力于救灾之中,《大公报》于9月4日发表社评《空前水灾中之外交危机》,提醒国人“外交危机之急迫,殆与水灾不相上下。此吾人所愿于万众惨痛中大声疾呼,唤起国人之郑重注意者也”。当时报馆设在天津的日租界内。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嗣后的中日关系,必然有长期间的纠纷。”(注:曹谷冰、金诚夫:“大公报八年来的社难”,《大公报》1946年7月7日。)为了更为公正真实地对中日问题发言,报馆毅然迁出日租界。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大公报》又在社评中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且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在日本问题上的惰殆:“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责亦无法谢国民,一笔误国殃民帐,实已不堪算,不能算!而今日外患频临,兆民水火,国家人格被污尽,民族名器被毁尽!”(注:《大公报》社评:“望军政各方大觉悟”,《大公报》1931年10月6日。)事变发生3天之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召开前所未有的编辑部会议,商讨对策,并提出此后的编辑方针,确立了《大公报》的此后的言论立场:“国家已到紧要关头,报纸应负起郑重责任。”(注:曹世瑛:“记爱国报人王芸生”,《新闻春秋》1996年第1~2期。)后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更成为《大公报》的主要内容。报馆曾经派出特派员陈纪滢秘密入关,到已沦陷的东北报道日本铁蹄下的实况,陈纪滢为《大公报》写出特稿《东北勘察记》,引起轰动(注:陈纪滢的东北采访有两次,一次是“九一八”事变不久,他在哈尔滨邮局工作,利用他的职务之便秘密为《大公报》提供消息和通讯;第二次是他已经随邮局从东北撤到上海,受《大公报》的总编张季鸾和胡政之之邀再去东北做秘密采访,途中曾遭日本军队的拘查,几经周折完成采访,1933年9月16日赶回天津,两天后《大公报》的“九一八”两周年特刊登出了他的《东北勘察记》(资料来源见:1.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2.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版;3.陈纪滢:《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4.《大公报》)。)。为了让国民从近代史上了解外侮的由来,报馆还派专门人员研究自甲午以来的中日关系。于是王芸生(注:王芸生于1929年进入《大公报》编辑部,1941年张季鸾逝世后继任《大公报》总编辑。)广泛搜集有关的史料和文献,并多次往返于平、津,查阅了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撰写中日关系史和日本侵华史。这部史书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写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回溯了60年的历史,逐日刊登于报上(自1931年9月起登到1934年5月,持续两年多从未间断)。而后由报馆汇印成七卷巨著,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在书中指出:19世纪之初,中日两国的情况本来很相似,因两国的统治者所走的道路不同,兴衰迥异,演变而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对这段历史的发掘,作者以“往者不可谏,来者大可追”的历史观来警醒世人,要看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历史根源,不能采取“历史糊涂主义”态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刊出后,影响深远,抗日战争时期还成为解放区研究日本问题的惟一史料(注: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于1931年10月~1934年5月在《大公报》连载,预计包括从1871年到“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关系史,但是只写到1919年就因事停止了。1934年8月张季鸾亲自安排王芸生进行了一趟“赣行采访”,到庐山采访了蒋介石等人,并专为蒋介石讲解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历史背景。王芸生在江西停留33天,回津后写出《赣行杂记》发表于《大公报》。也许是这一次的采访使连载中断了。所以直到王芸生的晚年,受周总理的嘱托,才又抱病整理修订此书,因经历体力不支,王芸生接受了张大年的提议,用“大事记”的方式补上从1919到“九一八”事变这一段中日关系史的写作,但最终也没能亲自完成,而是托原《大公报》记者张蓬舟代笔完成了“大事记”,收为第八卷。所以再版后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共有八卷本,王芸生于去世前两个月修订完成。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去世后,张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王芸生与<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张文中记载,范文澜说在解放区研究中日关系,王芸生此书几乎就是惟一的参考书。此书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材料,如故宫所藏档案(资料来源于《大公报》《大公报史》及笔者对王芸生之子王之琛先生的采访)。)。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发表社评“不投降论”,表达了坚定的抗战信念。《大公报》对日本问题的研究更为全面,也更有现实性。《大公报》不但社评和新闻栏目有专论发表,文学副刊也跳出了纯文学范畴参与其中。其间最集中、最独特、也最有意义的是香港版《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辟的日本问题专刊。
1938年,为了鼓舞抗战军民的士气,认清敌我力量的对比,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文艺副刊主编萧乾利用《文艺》综合版的篇幅,推出了几个日本问题专刊,包括:“日本这一年”“侵略者的老家”“穷兵!黩武!……”等几个专题,对1938年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大范围的分析和评价,文章作者都对日本问题素有研究,文中举用大量的数据和详尽的事例剖析了日本本土的种种黑暗现实和外强中干的衰败迹象。1939年3月,萧乾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加上新闻版的有关篇章和布德等人的几篇文学作品,结集成《清算日本》一书,以“大公报文艺编辑部”的名义,由《大公报》馆出版发行,名为“综合文艺丛刊”第一辑。《清算日本》由《大公报》香港版总经理金诚夫作序,指出“清算日本”的意义在于文化界对抗战中“知彼”应尽的责任:
我们对日抗战,已历一年有半,冲锋陷阵和英勇为国的任务,虽然已由武装同志负担了去,我们在后方的人,尤其文化界中人,对于日本的情况,应该不断研究,尽一个“知彼”的责任,拿来贡献给国人,使大家一方面抗战,一方面知道日本的实在情形。要知道今后中日间局势,不论推演到如何地步,关系只有一天复杂一天,我们要继续注意考察洞悉她的国情,我们才能对症下药,拿出对策,方能适应艰危的时局……这一次中日战争,是中国立国以来,向所没有的大规模对外作战,在此过程中的一切,都值得令人检讨,令人回忆。这种大时代的历史记述,虽然是现在或将来史家的责任,但是我们应该尽力所及,努力收集足以为史料的记载,以供时人检阅……(注:大公报《文艺》编辑部:《清算日本》,大公报馆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初版。)
《清算日本》共包括43篇文章。在国难当头的特殊时刻,萧乾把文学扩大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关怀,副刊作者把笔深入到“侵略者的老家”,展览出了他们“圣战”后的内幕。
与香港版《文艺》“清算日本”专刊相呼应的是张十方等人对日本从军作家“笔部队”的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配合军事上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也加紧了在文化上的宣传活动,日本国内文坛也深受战争影响,侵华文学充斥文坛,并且陆续向中国战场派出“从军”作家为侵略战争呐喊助威。“‘笔部队’的组成以及开往中国的过程,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开始已经通过国家权力,把日本文学拖入了侵华战争的轨道。是日本文学及日本作家自觉地全面协力侵略战争的象征性事件”(注: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文学——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第91~92、182、165、31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因而林焕平、张十方等人在《文艺》和《大公报》的另一个副刊《战线》上连续撰文,揭露发动侵略战争导致日本文坛的衰退情形及日本侵华“笔部队”中“作家”的真实面目。
火野苇平是日本侵华文学“笔部队”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他自1938年8月起在日本的《改造》和《文艺春秋》上连载《麦与兵队》和《士与兵队》(注:也译为《麦与士兵》和《士与士兵》。)。《麦与兵队》甚至在三四个月中重版至一百次,而且搬上了剧场,被日本文坛称为“笔部队报道文章之大成”;火野苇平本人也被称为“战争文学第一人”“文坛的幸运儿”。实际上,火野苇平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工具,他“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美化歌颂侵华日军,污蔑丑化中国军民,向数以百万计的日本读者传达了侵华战场上片面的、乃至错误的信息,煽动了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注: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文学——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第91~92、182、165、31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他在日本文坛的轰动效应也完全是军国主义的包装所致。1939年2月15日,张十方在《战线》上发表《火野苇平与日本文坛的倾颓》,全面分析了日本文坛的真实内幕和火野苇平走红的政治背景,及时透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文学的真面目。作者认为:正因为军阀“超强度”的高压,使得日本文化走向没落,忠实地表现社会和忠实地描写战争的作品极其匮乏,日本作家被迫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趋于绝对的沉默,甚至被投进监狱,一部分成为“文坛从军部队”的兵员及国内粉饰太平的歌手,还有一些作家只好写一点历史题材小说、恋爱小说、侠义小说、纯情小说、诙谐小说、探侦怪奇小说等等,赖以糊口。因而,日本文坛已经变得空无所有。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军国主义对火野苇平大加包装,使他“在空无所有的空间显出了独存的庞大”。“笔部队”的策划者菊池宽甚至宣称“火野苇平时代到来了”(注:详见张十方:“火野苇平与日本文坛的倾颓”,《大公报·战线》1939年2月15日第278号。)。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公报》对日本“从军作家”中的特异——石川达三的关注。石川达三作为日本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1938年1月到达南京,此时,南京大屠杀的血迹未干,目睹惨状,石川达三以个人的良知写出了反映战争真实状况的《活着的兵队》(注:也译为《活着的士兵》。)。但是,却被日本军部当局查禁,作者也被指控判刑,酿出有名的“笔祸”事件(注: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文学——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第91~92、182、165、31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这之后,石川达三“戴罪立功”,重返中国战场参加武汉攻克战,又写出了《武汉作战》,发表在日本《中央公论》上。在这篇小说中,石川达三一反《活着的兵队》中对中国战场的真实描写,变为竭力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歌功颂德,把战争的责任无理地推给中国政府和百姓。为了揭露这些侵华文学的虚假性,让读者了解到一些日本作家对战争的真正感受,《战线》刊登了石川达三写在《武汉作战》后的队记:“去春由于《活着的兵队》所引起的‘笔祸’,使读者不禁迷惑模糊。此次再度从军归来,匆忙间写成此稿……上次以研究置身战场中的个人而招来‘笔祸’,故此次力避‘个人’,仅概观战场的全般,人们读时,能够一面摊开一张详细的地图,该可以更为有味吧。”(注:详见张十方:“火野苇平与日本文坛的倾颓”,《大公报·战线》1939年2月15日第278号。)从这个附记可以看到石川达三的畏惧心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的“国策文学”绝不允许以个人体验为依据、具有真情实感的文学存在。
由此可见,《大公报》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与它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密切相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在文学创作上还出现了以布德为代表的专门描写日本士兵反战情绪的作品,揭露了他们“大东亚主义”的本质及其侵略行径的非人性。
布德的日本士兵反战小说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帮助陈纪滢编辑《大公报》的《战线》副刊,作品几乎都发表在《文艺》和《战线》上。他的小说多以日本士兵为主角,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灵魂的厮杀和搏斗、人性与兽性的交战,揭示了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也从侧面刻画了战争给日本妇女带来的深切痛苦。
布德的小说以《第三百零三个》最为著名,这篇小说取自一个真实事件:在扬州的妇女慰劳所里,一个日本军官发现了他的妻子,悲愤之中俩人一同自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吉田和慧子演绎了这个悲惨的故事。他们本是一对相爱的夫妻,战争使吉田兽性大发,在中国战场上肆意糟蹋、残酷杀害了三百多个中国姑娘,他的内心深处只有在对远在家乡的妻子慧子的想念中还残留着一点人性的温情。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使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慧子也被征来中国做了慰安妇。他不能承受这样惨重的打击,最终和慧子一同死去了。作者在这篇小说的题记中说:“能够勇敢地死,也许便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可是,死,并不能阻止日本军阀的狂暴。无数的吉田呵,无数的慧子呵,起来!举起你们自己的臂膀,把日本军阀打倒吧!”(注:布德:《第三百零三个》,《大公报·战线》1938年8月23日第174期。)从中可以看出小说中蕴涵的宣传意义和鼓动性。作品发表后,《大公报》新闻版还为此发表了社评《读<第三百零三个>》。为一篇小说而专写社评,这在《大公报》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方面可以看出这篇小说抓取题材和表现视角的敏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极其注重文化意义上的反侵略,因而再一次表现出新闻与文学、副刊与正版的密切结合。社评由王芸生执笔,他从吉田和慧子的凄惨故事中剖析了日本民族性中“悲剧的元素”,王芸生以他对日本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深刻洞察力,从四个层面揭示出这个悲剧产生的根源:
这故事太悲惨了,但在日本民族性里,的确含有构成这种悲剧的原素。这故事里包含这几个问题:(一)人性的残忍,这是整个的日本民族性。(二)军阀的万恶,这是日本统治阶级的本面。(三)武士的奴性,这是‘大和魂’的真髓。(四)妇女的卑贱,这是世界劣种的根性。日本形成国家之后,一直是军阀专制。日本社会的中心人物是武士,而武士便是一种奴性十足的阶级,武士的道德也是一种奴性的道德。日本古代的藩士,实是受藩主豢养的鹰犬。他们只知有豢主,而不知有国家。他们只知对豢主服从效忠,而对于平民则只有欺凌强暴。日本武士对于藩主的卑屈服从,藩主死时可以切腹殉葬,完全是一种妾妇式的奴性道德;对于女子的贱视,男子的尊严发挥到无以复加,则是奴性道德的另一面,他们入藩邸恐惶听命,回家来则令妻女膝席进酒,这种人得了势,自然是专制暴君……日本军阀是安心驱策它的同胞来中国送死的,这群被残忍牺牲的可怜虫,到中国也便发挥他们烧杀淫掠的残忍性。日本军阀征发壮男到海外送死,同时更征发少女来中国“慰劳”,这对于战士,对于出征军人家属不太残酷了吗?但在奴性日本之贱视妇女,是做得出来的!……日本这民族在加速度地还原,还原到它吃人的岛族;日本这国家,在起劲地演悲剧,将演到整个国家的切腹!(注:《大公报》社评:《读<第三百零三个>》,《大公报》1938年8月24日。)
最后这一段话还复沓般地出现于社评每一段的开头和结尾。这篇社评由于对日本民族性的深入分析和深刻了解,提升了小说的表现功能和认识价值,对吉田和慧子的悲剧没有单纯地停留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而是从国家和民族立场来解析悲剧生成的内在因素,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本质揭露得更为彻底。由于《读<第三百零三个>》写于南京大屠杀之后,整个中国沉浸在对日本侵略者深切的仇恨中,所以它表现出来的情绪异常激烈,有些言语也不够客观,但是却真实地表达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民族情绪。
《大公报》还刊登了布德的《海水的厌恶》《四层包围圈内的黑点》《寂寞的哨兵》《手的故事》等系列日本军人反战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复杂心态,有时还用象征手法烘托他们对自己命运的不可把握和对前途的茫然无措,其中以《海水的厌恶》最为典型。它也是取材于真实事件,作者在小说的后记中说明这个故事的来历:“最近在同一张报纸的两面,我发现了两个悲惨的事实,一千个中国工人被日人毒害抛在江底。而另一面,十五个日本海军陆战士兵投江自杀。”(注:布德:《海水的厌恶·附记》,《大公报·文艺》港版1938年12月7日第462期。)小说以日本士兵田武和大海之间的对话展开,田武和他的十四个伙伴对这场战争的意义发生了怀疑,因而对战争产生极度的厌倦,他们相约一起投身大海,用“尸谏”抗议战争,为更多的人换来自由。十四个伙伴已经跳进了海里,但是田武好像听到了海的灵魂与自己的对话,这加深了他对生命和亲人的留恋,迟迟不能行动。当他终于抛开这一切,投身到了海底去寻找他的伙伴们,却又听到了一千个中国工人的冤魂在海底愤怒的控诉……所以“海水的厌恶”这一题目本身就是象征,蔚蓝色的茫茫大海代表着正义和纯洁,却包藏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血腥。布德的这些小说非常注重对人物的心灵剖析及人性挖掘,尤其善于表现日本普通士兵被军国主义摧残、压抑、扼杀了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兽性对人性的亵渎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大公报》中另有一些作品与布德的小说取材相同,但是更侧重表现日本士兵面对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残暴行径产生的罪恶感,其中以雨田的小说《罪》(注:雨田:《罪》,《大公报·文艺》港版1939年8月2日~8月23日第675~687期。)表现得最为充分。《罪》主要是围绕着在中国战场上的两个日本士兵梅吉和柃木的故事展开,描写了梅吉强暴中国妇女后引起心灵上的罪孽和痛悔,而后切腹自杀。梅吉日夜怀念家乡的妻子定子,正是这种圣洁的爱情,使他绝不允许自己像好朋友柃木那样强奸中国妇女。但是由于对枯燥的战争生活的厌倦,他禁不住柃木的鼓动,在一天夜里强奸了一个“秀美娇小如同小鸟一样的”美丽少妇,这个中国妇女在逃跑的途中淹死在了冰冷的河水里,丢下了亲爱的丈夫和哭泣的婴儿。面对这幕惨剧,梅吉的眼前出现了定子黑亮的眼睛,他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人间的罪人,第二天,柃木在雪地中发现了他已切腹的尸体。作家对日本士兵这种自我忏悔的描写,都是围绕着他们对妻子的怀念中展开的。在这些作者笔下,战争的受害者不止是中国人民,同样还有日本人民,因而日本士兵的妻子都以美丽、善良的形象出现,寄托了作者无限的同情和怜悯。有时,作者的这种同情和怜悯甚至还反映在表现日本俘虏的作品中,如碧野的小说《花子的哀怨》。花子本来是无辜、善良、美丽的高丽姑娘,被人贩子卖到日本后,不堪忍受残暴的丈夫的虐待而逃出家庭,落入妓院。战争开始后又被征为日本军队中营妓,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俘。花子刚刚在战俘营中看到了生命的曙光,却惨死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作品表现了“我”对花子深切的同情和对她命运的关注。
以布德为代表的这一系列日本士兵反战题材的小说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复表现人类爱情、亲情的圣洁及其被践踏,它们或取材于新闻报道,或来自作家对人性的基本把握,具有高度的文学真实性。作者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把侵略者和日本普通百姓区别开来,把战争的责任归结为军国主义的扩张行为,所以在这些作品中,一个共同的事实是:作家的怜悯多于憎恨、同情多于批判。《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萧乾在伦敦演讲《战时中国文艺运动》时就明确指出:“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感情反映在文学上的,则是怜悯而非憎恨,许多关于日本俘虏的小说……他们都是自由的俘虏。一篇又一篇小说描写一个日本兵和一队日本军在一起他怎样要‘鸡子和姑娘’,但当他独自一人时,或者如一篇小说所写,在著名的西湖岸上追赶一个无助的姑娘时,他便唉声叹气,还会呜咽,厌恶他自己的污秽的手了。”(注:萧乾:《战时中国文艺》,《大公报·战线》,1940年6月15日~16日第575、576号。)中国作家的这些作品与日本“笔部队”中的侵华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正像一位研究者(注: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文学——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第91~92、182、165、31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所分析的,这种状况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这是善良的中国作家试图将日本士兵“人化”所做的努力,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人性、美好的心灵和博大的同情,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及侵华文学的兽性、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狂热。
标签:大公报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论文; 日本侵华战争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