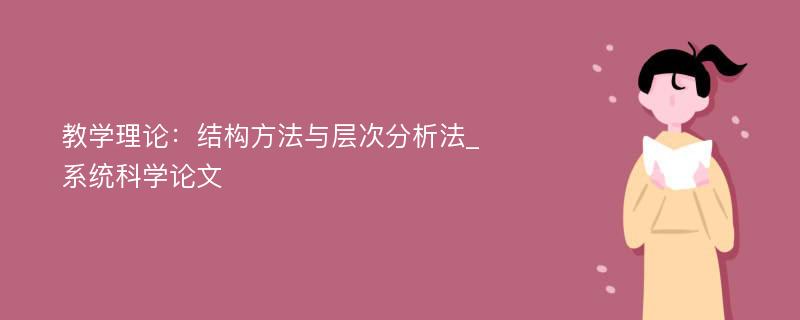
教学论:结构方法与层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层次论文,结构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2)03-0011-06
笔者曾指出,“《教育研究》倡导了一种良好的学风”,“它不时刊登一些观点彼此不同的文章,不时刊登‘正方’与‘反方’完全不同的论说,这种做法是学术繁荣绝对必需的,十分珍贵的”。[1]《教学要素层次论》[2](以下简称《层次论》)《教学系统要素与教学系统结构探析》[3](以下简称《探析》)也是《教育研究》近期内刊登的观点彼此不同的文章,毫无疑问,这对推动有关问题的深入讨论亦必是有益的。鉴于《探析》一文涉及到了教学论的某些基本问题而明显地存在一些不确切之处,有必要再作一番分析。
一、几个基本概念
系统科学所说的系统,包含三个基本点:一是它包含若干要素,单一的要素不构成系统;二是要素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彼此毫无关联的要素也不构成系统;三是这种关联还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关联的稳定性使系统具有确定性,关联在性质上的变化可使系统变成另一系统。
显然,要素概念是更基本的概念,系统的概念是建立在要素概念基础上的。什么是要素?回答的方式可以有三种:一是给出定义;二是作出某种解释而并非以定义的形式出现;三是作为一个十分基本的概念而不再加以说明。《探析》一文误以为《层次论》是给要素加以界定,给了一个“失之简单”的界定,其实,问题并不在简单不简单。《探析》特别强调,“在我国绝大多数《教育学》和《教学论》教科书中,一般都没有对要素及教学系统要素作出界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于是《探析》对要素及教学系统要素都给出了定义,以弥补这一缺憾。这表明,《探析》认为,对每个概念都只能以给出定义这样一种方式来描述。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最严密的科学也不可能没有仅予说明而不予定义的概念,而且这是严密逻辑的特征之一。
既然《探析》一文给出了定义,那么,我们再看看这种定义本身。首先是它对要素给出了定义,要素“有两种涵义,即:一是构成事物本质的必要成分;二是决定事物成败的必要原因或条件”。这里,不是在说系统的要素,而是在说事物的要素。然而,系统与事物这是两个不同的用语,事物可有条件地视为系统,但事物不等同于系统,需要在不同场合慎用。此外,逻辑定义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在定义的陈述中,不能再出现未加定义或未予明确的词语,《探析》的上述界定出现了“事物成败”一词,那么,事物何为成又何为败?如果是指系统,系统又何为成亦何为败?对此如何明确?显然,《探析》是将某词典的两处解释拼凑在一块而形成了自己的“界定”,在方法上,这种拼凑是很危险的;在论证方式上,以词典为据而不是以其为鉴也是不妥的,词典的作者之本意就不在对每个词语给出定义,而我们还进而以其为据来再作定义,实在更为不当了。
《探析》随后给出了教学系统要素的定义,“构成教学系统的必不可少的单元或部分”。这种定义与不少的定义有一个共同毛病,即,同义语反复或近义语反复,定义者似乎在告诉人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告诉。《探析》的这个定义在告诉人们,要素就是单元或部分,你只要知道了什么是单元、什么是部分,你就知道要素是什么了。这种定义的意义有多大,可想而知。更严重的是这一定义的逻辑缺陷,在这一定义中,系统是作为已知概念出现的,然而,系统概念是以要素概念为基础的,这种定义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它把一个概念作为已知的,却反而利用这一概念而把另一个较之更为基本的概念作为未知概念加以定义。
我们说一下结构概念。《探析》一文本身并未给结构再下什么定义,它只是运用另一作者的论述而将结构理解为“各组成要素在空间或时间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和顺序”。且不说这种叙述有什么毛病,至少,这不是对结构的惟一解释。
自然科学领域里,广泛运用结构方法,数学结构(如代数结构、拓扑结构、序结构),物理结构(如分子结构、原子结构),化学结构(形成结构化学),生物结构(如蛋白质结构、核酸结构);在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管理学)乃至人文科学(如语言学、逻辑学)中也使用结构方法。由于这种方法、观念的普遍意义,于是哲学也予以关注,出现了结构主义,包括教育哲学中的结构主义。20世纪之初出现了一个数学哲学流派,即法国的布尔巴基结构主义流派;1968年,皮亚杰出版了一部专门著作,书名即《结构主义》,广泛叙述了各种结构形式并提出了结构主义的本质。结构并不单指关联。
据笔者所知,对结构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指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二是指系统的要素及其关联;三是指与“初始符号对应的,满足一定条件的对象的集合”。[4](P1654)第一种理解仅把结构理解为要素的关联,第二、三种理解都把要素本身也视为结构之中,在第二、三种理解下,结构与系统相近。《探析》仅作了一种(第一种)理解,因而当有不同的理解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就认为是“把要素同结构相混淆”,并“导致人们(实则是《探析》本身)认识上的混乱”。
布鲁纳是教育学领域结构原则、结构方法的创始人,他认为:“学科的基本结构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间的关系。”[5](P805)我们看到,布鲁纳这里对结构所作的是我们前述的第二种理解,即被《探析》认为是混淆了要素与结构的一种理解。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具体的结构,即学科结构,此结构中的要素即为基本概念,另一方面,原理也被视为要素,此外结构还包括有概念、原理之间的关系。
看来《探析》在要素、结构、系统这些概念上都缺乏具体分析,既片面,又不确切,这自然影响到《探析》对其他一些问题的讨论。
二、要素的分析与确立
《探析》提出了确定要素的两条标准,一是“必不可少”,二是“相对独立”,奇怪的是,《探析》自己在给出要素定义时却丢掉了“相对独立”这一条。标准应是在定义中反映或可推断出来的,但从其定义中,看不出这一点。而在实际讨论一些要素时,《探析》对这两条又都作了主观随意的解释,这种随意性的事例不只一、二。
《层次论》所强调的并非“必不可少”这一条件,更非《探析》所曲解的那样是作为“惟一标准”的。《层次论》所强调的是,如果仅以必不可少为标准的话,便不宜把握基本教学要素,因而要区分基本要素与非基本要素。《探析》用一种绝对的观点来否定这种相对的区分,在《探析》看来,没有基本要素与非基本要素之分,而只有要素与非要素之分,或者是“教学系统的要素”,或是“系统之外的环境因素”。这里引出了两个问题:哪些因素属于环境?教学环境是不是教学要素?按照《探析》的说法,教务部门、教学管理人员是属于环境的,教师、学生才是属于教学系统的;《探析》也十分明确地认为教学环境不是教学要素。因而教学管理人员不是教学要素。事实上,《探析》并未遵循自己所提出的定义和“必不可少”的标准,而是先入为主地(因而具有随意性地)进行划分,不是先明确要素与环境的关系,而是认为,要素者则要素也,不是要素者环境也。
把教务部门(主要由教学管理人员组成)划归教学系统之外,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将教务部门说成是环境因素,更是不伦不类。恰好是承认基本与非基本之分,才可以避免这种尴尬。
教学环境是不是教学要素呢?李秉德先生认为是!而且是“一个常被人忽略甚至无视的教学要素”。[6](P13)那么,李先生说的是否真有道理呢?有道理!隐性课程概念及其意义进一步支撑了这种说法。
进一步需要探讨的是,环境是否还有结构(即它是否又包含有要素及其关联)?层次分析方法还是可以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得以深入的。
《探析》提出一条“相对独立”的标准,那么,什么是独立呢?又什么是相对呢?如果相对指的是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非相互分割,那么,系统本身所要求的基本点之一便是要素之间存在关联,彼此互不关联的要素不构成系统,因而,对相对再去说什么就多余了。这表明,非常强调以系统科学来“指导”教育科学的《探析》并未充分理解系统,且不说“应以系统科学为我们提供的认识方法论为指导”这种提法有多么的不恰当。
在没有说明“相对独立”的正面含义的情况下,《探析》以一具体例子去说明“非‘相对独立’”。《探析》说“教学规律作为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总是包含着某些教学系统要素。如有一条教学规律是:学生的发展以认知教材为基础的规律,就包含了学生与教材两个教学系统要素”。简言之,这段话的意思是教学规律包含了教学要素(或某些要素),例如,包含了学生与教材这两个要素。这段话所要论证的命题是:教学规律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不是教学要素。然而,这个论证中有几个几乎是常识性的错误。
教学规律与学生、教材是性质不同的范畴,怎么能说谁包含谁呢?怎么能说规律包含了学生、包含了教材呢?如果说是用语上的不当,可它明明白白写着“教学规律”“就包含了学生与教材这两个教学系统要素”。确切地说应是教学规律涉及这两个要素,但涉及与包含的区别太大。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包含关系,重叠关系,互容关系,互斥关系,互动关系……应作实际的分析。
如果教学规律真的包含了学生、教材这样的要素,那么包含这些要素的东西本身怎么就不是要素了呢?然而,我们不能以“教学规律包含了学生、教材等要素”为前提来论证“教学规律是要素”的命题。以错误的前提论证正确的命题是无效论证,但是,同样的,错误的前提对其他命题的论证也是无效的。逻辑上,这叫做“不A则B”。前提不对,结论随你去说了。因而,《探析》由此而论证教学规律不具有相对独立性是无效的,论证教学规律不是要素也是无效的。
还需要指出,《探析》把“教学规律作为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的说法至少是片面的,这是一种传统的但不很准确的说法。《探析》一文有好几处引语,这些引语表明了《探析》一文知识的陈旧性。另一方面,规律既然被认为是指要素间的相互联系,那么,按《探析》的观点,教学规律应是教学系统结构?但《探析》对此也缄默不语。
三、关联可否是要素
《探析》囿于自己单一的理解而把结构仅说成是关联,并认为关联不是要素,“把要素间的关联方式当作要素,必然会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混乱”。
前面提到过,布鲁纳认为学科的基本结构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间的关系。布鲁纳的这种理解显然与《探析》不同,不同在两点:布鲁纳事实上把概念、原理视为了要素,认为结构还有要素,结构不只是关联;既然原理也是要素,而原理中相当一部分是讲关联的,因而关联也被视为要素之一。可以说,布鲁纳的这种理解与常人的理解有更高的一致性,因为,我们通常在说某某事物还有结构(你不要把它看成“铁板一块”了)时,那指的是它还包含有若干要素,它们相互联系着。
再看列宁如何看待要素。他提到了辩证法的要素,显然,这里需要把辩证法也看成是一个系统或视为系统的事物(是可以且需要这样看的)。列宁开始把辩证法的要素叙述为三条:“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规定”;“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分析和综合的结合”。[7](P261)“结合”被视为了要素。随后列宁又“详细地把这些要素表述”为16个方面,其中大多数是讲联系、关系、结合、转化等可称之为关联性内容的。列宁不仅讨论关联,而且还讨论关联的关联。
列宁的、布鲁纳的这种把关联也视为系统的要素的做法是否妥当呢?其实,结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已加以运用。列宁对辩证法要素的分析方法无疑是精当的。
结构方法在教学论中不仅是用来对教学作整体分析的,也可作局部分析,这一方法亦具普遍意义。例如,我们可以把师生关系视作一个“事物”或系统,这个“事物”也是有结构的,事实上,它包含有“工作关系”、“认知关系”、“情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关系。师生间的“工作关系”、“认知关系”等就成了“师生关系”这一系统的要素,关联被视为要素。
对同一事物还可以从多种不同角度进行结构分析,角度不同,结构含义也就不同,并非对同一事物就只能有一种结构分析。例如,对于一所学校的教师群体,亦可视之为一种(广义的)“事物”,那么,这一“事物”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亲缘结构等便是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分析。在这些不同的结构中,各自所涉及的要素是不同的,在职称结构中涉及的是教授子集合、副教授子集合、讲师子集合、助教子集合等;在学历结构中涉及的就是博士、硕士、学士了。如果仅把结构等同于关联,对这种分析便是无法理解的,因而又会像《探析》那样感到“混乱”。
既然关联可以成为要素,那么,否定教学规律、教学原则等为要素的论据就不能成立了。既然可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要素,那么给要素分类就是自然的了,硬要素、软要素的分类也是自然的。
在《探析》中所列出的五个要素之中,教师、学生这两要素与教学内容这一要素就是不同类的;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与教学目的、教学手段也是不同类的,只是《探析》回避了对它们的分析。其实,这里,我们还可以问:既然可以把教学目的列为要素,为什么不可以把教学原理、原则也列为要素?如果说教学原理、原则是受教学目的影响的,那么,学生不是也受教师、教学内容的影响吗,为什么学生仍然要单列为一个要素呢?
四、要素有没有层次
《探析》一文时而认为《层次论》会使教学要素“难以穷尽”,时而又说《层次论》采用相对比较方法分析要素的不同性质“相对到最后”“最基本的要素(就)只能有一个了”。《探析》的这种作法显然是牵强附会的,应当说,亦非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为无论如何从《层次论》的论述中也推不出这些结论来,姑且不说这种结论是否肯定不恰当。
《探析》说“层次划分方法至少有三方面的缺陷”,其一是《层次论》给出的那个“没有穷尽的庞大的教学要素层次系统,不仅使人们对教学系统要素难以把握;而且更看不到教学系统的结构”。“没有穷尽”(而不是“难以穷尽”了)是《探析》推理出来的,“庞大”却是肯定存在的事实。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庞大就会使人难以把握呢?看到了要素,看到了关联,为什么就“更看不到”结构了呢?从《探析》的全文看,实用《探析》力求把要素简单化和静止地看待结构,这两点才导致了《探析》所认为的第一缺陷。列宁在分析辩证法要素时,首先简要地将其归结为三个,可是,随后,他又说详细地分划为16个,大概也是更“庞大”了。人类基因组那么庞大,数万个之多,一个国家的科学家还没法弄清,还要组织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六国人员合作研究,害怕庞大和复杂就只能在科学研究面前止步。再说,如果真的想简洁明了,那也必须建立在对复杂事物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否则,那才真的是混乱。不明白这一道理,致使《探析》具有明显的简单化倾向。那么,它静止看问题的毛病又十分突出地表现在哪里呢?除了它把结构作了单一的理解并认为凡不按此单一的理解去看问题便都是造成混乱的观点外,实际上,《探析》尤其不明白结构方法可以运用于对“软件”事物的分析。列宁对辩证法这一“软件”的分析方法是一范例;布鲁纳对学科的分析是教育领域里的一个范例,布鲁纳以概念、原理为要素对学科所作的分析,是取了一个特定(并非惟一)角度所作的“软分析”,不明白这种分析工作的重要性,就像不明白计算机“软件”的重要性一样。
《探析》所说的层次分析方法的第二个缺陷是“没有区分教学系统要素与教学系统的结构”,并说是“颠倒了要素与系统的关系”。我们已多次指出《探析》关于对结构的片面理解,正是这种片面导致了它所持的惟一区分方式。除了实在看不出《探析》所说的什么有关“颠倒”的事实和理由外,《探析》在否定教学方法是一个要素的同时,自己把教学手段列为了要素。可见,《探析》确实处在混乱的感觉之中,且没从中走出来。按照《探析》的逻辑,它把教学目的列入要素也是要受到它自身逻辑的质疑的。
《探析》所说的要素层次方法的第三个缺陷是“有悖于系统科学原理”。且不说《探析》处处以系统科学为指导,并以为自己是系统科学的权威解释者有多么不合适,但至少可以肯定《探析》是文不对题、无的放矢。《探析》引用他人之言:“下一层次的系统转化为上一层次时便成了要素”,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要素没有层次吗?《探析》频繁地使用却又是平凡地使用转化(实则是把转化简单化了)一词而并没有说明要素是不能分层次的。《探析》只是说“同一层次,不可再划分为不同层次”,但这是一句废话,它是在说“‘同一层次’不是‘不同层次’”,这就是在说“同是父辈的人不再分父子辈”。拿这句话来进行论证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说教育是有结构的,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它们的关联。
进而,我们说普通教育还有其结构,普通高等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普通初等教育,以及它们的关联。
普通高等教育仍有其结构,高等工科教育,高等理科教育,高等文科教育,高等医科教育……以及它们的关联。
文科教育还有其结构,社会科学类的,人文科学类的……
人文教育依然还有丰富的结构,语言学教育,艺术学教育,伦理学教育……以及它们的关联。
往下,还可以继续作结构分析,也是层次分析。
《探析》是不赞成这样深入分析的,认为这将“使人们对系统要素认识更加混乱”。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这种分析是使人的认识更加清晰了,还是“更加混乱”了呢?
在教育这个大系统下,有许多不同层次的(子)系统;这些不同层次的系统所包含的要素就是这个大系统的不同层次的要素。这有什么疑问呢?所谓“系统有层次、要素无层次”的结论从何而来?时刻都在说要辩证看问题的《探析》是不是太缺乏点辩证思维了呢?
转化的条件是重要的。《探析》承认系统与要素可转化,然而,转化的条件之一,便是它们皆有层次性。其一有层次,另一无层次,转化就不会发生。
在《层次论》一文中分明写着“不宜将不同层次的要素加以并列”、“避免把诸多要素摆在同一层面”,而《探析》所说的“同一层次,不可再划分不同层次”是在评论什么呢?是在针对什么呢?在进行评论之前,应当弄清楚被评论者说了些什么,否则评论本身的价值何在?
即使是《探析》承认系统是有层次的,可是,《探析》在实际上进行要素分析(包括它在列出自己的五要素)时,并未理睬这一点。可见它并未意识到结构方法和层次分析的强有力。
但是层次分析法,包括系统的层次、要素的层次(后者与前者必然相联系),具有普遍的意义。承认(应当说“实际上承认”)系统的层次,就必然承认要素的层次。对要素的层次分析,是结构方法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要素的层次分析法(加上要素的类别区分法)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在教学要素研究中的许多问题。
五、几个方法论问题
说到这里,笔者还希望再次肯定《探析》的批判精神,笔者本人也在努力养成这一精神。希望《探析》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因为它有利于学术发展,也有利于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但由《探析》一文可以看出几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注意到这些问题将使得批判精神朝着更有利于学术健康发展的方向发扬。笔者亦愿以此与《探析》作者共勉。
第一,《探析》一文使用了不少不应有的模糊语言,例如“绝大多数……教科书……都没有……”“似乎是难以穷尽的”“相对到最后,最基本的要素只能有一个”。说“绝大多数教科书”“都没有……作出界定”,语病就很严重,究竟是“绝大多数没有”还是“都没有”呢?“绝大多数”与“都”这是不可混淆的。如果只是“绝大多数没有”,那就不能说“都没有”。如果有,那就算有了,哪怕是一部分教科书有了界定,当然算有了。那么,既然有了,《探析》作者的“缺憾”感又从何而来?如果是自己没有充分占有资料,就应当坦言,而不应含糊其词。如果是充分占有了资料,并发觉确实有人有过界定,那就不要空发“缺憾”的感叹;若发觉没有任何教科书界定过,那就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界定的第一人。这是学术讨论中应有的态度。
第二,对于一个概念的定义(有时亦非逻辑意义下的定义而只是一种描述),在许多人文学科中常常是多样的。例如,在教学论中,对于教学、课程,这样一些十分重要的概念,其定义种类之多,是大家所熟知的。对于这些多种界说一般宜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或加以比较,或指出在不同时间、条件、地点下有各自不同的合理性或不当之处。在有多种不同界说的情况下,尤其不要误以为只有一种,并误以为这是惟一或绝对正确的。《探析》对结构就只作了一种理解,并误以为它是惟一正确的,殊不知,对结构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对于一些词语的使用,其含义并非总是去界定,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约定。更不能以为约定只有一种方式。一般说来,在某种明确的约定甚或是假定下,就可以展开正常的讨论,只要这种约定或假定本身不包含悖论。
第三,对命题进行论证的方式很多,基本的有两种:一是逻辑论证,二是实证式论证。有些作者(包括《探析》作者)采用引证式论证,即靠引用他人的言论来进行论证。这种论证,有几点是必须加以注意的:引证式论证必须纳入逻辑论证范围,亦即,其引证的命题本身必须是已被证明为正确的,至少,引用者本人对所引用的命题的正确性有过独立的判断。《探析》一文的引证性论证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只是它靠某一部词典来进行定义,而且它对系统科学的引用也有这种盲目性,只要问问《探析》是否考虑过以下问题就够了:为什么系统科学与教学论科学(教育科学分支之一)之间就成了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了呢?谁确定的这种关系?《探析》所引用的系统科学的有关言论是“系统科学”的,还是某位“系统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为什么那个研究工作者之言肯定就一言九鼎?不弄清这些问题,何以为科学的态度?例证式论证应纳入实证式论证的范畴,此时,应特别注意论证的充分性。《探析》也使用了例证式论证,但它显然没有顾及于此。
第四,《探析》很明显地没有准确地分析《层次论》所持的观点,如果是没有理解,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不仔细分辨一下对方的叙述,那就不能算郑重的态度;如果使用一些不当的手法,就更是学术批判中的忌讳。《探析》起先是说层次要素“似乎难以穷尽”,在后面正式加以评论的时候就变成“没有穷尽”了,这可能叫做一步步进逼的手法,但这显然是不宜采用的手法。“难以穷尽”意味着可穷尽但困难,“没有穷尽”意味着不能穷尽,那么《探析》究竟认为它所评论的是哪一种情形呢?而且,《探析》应当表明,它认为是可穷尽对,还是不可穷尽对呢?
第五,在《探析》一文的最后,它几乎把前面评论中的观点(包括《探析》自己的观点)撇开,不说任何道理地拿出了一个“五要素”。如果《探析》将自己的观点坚持贯穿下去,用自己所说的道理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么“五要素”而不能是“六要素”、“七要素”……那么也许对讨论更为有益。可惜它没有这样做。
当我们看到《探析》一文最后绘出两个图式时,便可明白,《探析》在概念上没有做好“自我把握”,它所绘的图应当是个系统模式图,可它将其称之为系统结构模式图。称之为结构模式图未尝不可,但这需要《探析》修改自己对结构的片面理解。
此外,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两个图式实在是没有多大价值。我们看看这两个图似乎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一个是使用单箭头,一个是使用双箭头,仅此而已;当然,简单并不一定不说明问题,但是,单箭头就是注入式,双箭头就是启发式,恐怕没有《探析》告诉我们这一点,单从那个图式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的。《探析》的结尾提出了“进行教学理论研究和进行教学改革”的“两个维度”。这种说法包含了许多的不确切之处,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将另文评述。在此,我们简单地指出这样五点:(1)“维度”是借用了一个几何概念,《探析》说“两个维度”,这意味着此二维决定了“几何”空间,这里,《探析》说了“教学理论研究”的空间和“教学改革”的空间,事实上,仅此二维,是绝无可能布满这两个空间的,尤其是前一空间。(2)提高要素质量,调整系统结构,“提高”、“调整”,这与维的概念不相干。(3)要“提高各个要素的质量”,《探析》是同意把教学目的作为要素的,那么,“提高教学目的的质量”是什么意思呢?这需要加以解释。如果对要素作详尽的分析,那么就可发现,有些要素有提高质量的问题,有些就并没有提高质量的问题,有些客观性软要素只是人们如何对其加深认识的问题。(4)至于结构调整,如果不承认结构的层次,要素的层次,那么,对调整的内容十分丰富便不一定能把握住。(5)如果不承认结构的层次,包括要素的层次,关联的层次,即使对于提高质量也没法深入理解。例如,教师作为一个教学要素,如果不对其作进一层的结构分析(包括要素分析、关联分析),那就不可能把提高师资质量的工作切实抓下去;而且,仅进一层还是不够的。对于学生,对于教材,又何尝不是如此,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没有一个笼统的学生质量、教材质量,只要一具体化,就必然要进一步作层次分析,就必然要深入到各类教材、各类学生上去,甚至作更深层的分析。否定层次分析方法,就把结构分析方法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否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