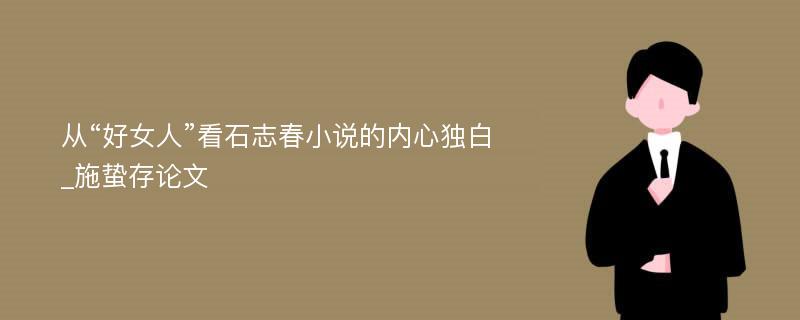
从《善女人行品》看施蛰存小说的内心独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白论文,人行论文,内心论文,小说论文,看施蛰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善女人行品》收有施蛰存1930年1月至1933年11月的十一篇小说,施蛰存在《善女人行品》序中说这是“一组女体习作绘”。这一组小说主要受奥地利作家亚瑟·显尼志勒的影响,描写女性心理,并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描写。但施蛰存又是有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作家,这便使他区别于显尼志勒,有着自己的独特性。
一
施蛰存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较早使用内心独白的作家,在施蛰存翻译的众多外国作家中,施蛰存最推崇的是显尼志勒,他说:“有一个时候,我曾经热爱过显尼志勒的作品。我不解德文,但显氏作品的英、法文译本却一本没有逃过我的注意。”[1](P.1212)并“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2]显尼志勒的突出特点就是内心独白,施蛰存说:“尤其是乔也斯的名著小说《攸里栖斯》所应用的内心独白式(Interior Monalogue)的文体,早已由施氏在《爱尔赛小姐》和《戈斯特尔副官》这两个中篇小说中应用过了。”[1](P.1204)施蛰存翻译了显尼志勒的多部作品,并从中受益。
显尼志勒最擅长的是性心理独白,施蛰存说:“施尼茨勒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是以性爱为主题的。因为性爱对于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关于他在这方面的成功,我们可以说他可以与他的同乡弗洛伊德媲美。或者有人会说他是有意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的,但弗洛伊德的理论之被实证在文艺上,使欧洲现代文艺因此而特辟一个新的蹊径,以致后来甚至在英国会产生了劳伦斯和乔也斯这样的分析心理的大家,却是应该归功于他的。”[1](P.1204)施蛰存的性心理分析特长早在《善女人行品》之前出版的小说《石秀》中已鲜明地显现出来。“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3]《水浒传》中的石秀,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但他怂恿杨雄杀妻子的行为有些不尽人情,金圣叹说石秀是“假公济私”,施蛰存的《石秀》抓住这一点因由进行探索、挖掘,分析石秀的杀人动机,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展示了石秀的性心理。石秀是爱潘巧云而不能,施蛰存便用内心独白暴露石秀的内心冲突:“在第一天结义的哥哥家里,初见了嫂子一面,就生着这样不经的妄念呢?这又岂不是很可卑的吗?……看见了一个美妇人而生了痴恋,这是不是可卑的呢?当然不算得什么可卑的。但看见了义兄的美妇人而生痴恋,这却是可卑的事了。这是因为这个妇人是已经属于了义兄的,而凡是义兄的东西,做义弟的是不能有据为己有的希望的。这样说来,当初索性没有和杨雄结义,则如果偶然见着了这样的美妇人,倒不妨设法结一重因缘的。于是,石秀又后悔着早该跟戴宗、杨林两人上梁山去。但是,一上梁山,恐怕又未必会看见这样美艳的妇人了。”石秀在爱与道义二重人格中矛盾着,并以兄弟之情压抑了爱恋之情。之后因得知和尚与潘巧云私通而导致性变态,由从前的“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到现在“因为爱她,所以想杀她”,石秀从桃红色的鲜血中得到一种性满足。弗洛伊德在分析这种性变态的情形时说:“他们当中有许多种变态的人们,他们的性活动和一般人所感兴趣的相距很远。这些人的种类既多,情形又很怪诞”(《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说这种性变态者,都是“不近人情的虐待狂者,专门想给对方以苦痛和惩罚,轻一点的,只是想对手屈服,重一点的,直至要使对方身体受重伤”。(《精神分析引论》)石秀从残害性对象中得到的性满足,很快就消失了,面对杨雄,他感到内疚和茫然。弗洛伊德说:“实际上,性倒错的患者很像一个可怜虫,他不得不付出痛苦的代价,以换取不易求得的满足。”(《精神分析引论》)如果说石秀欺骗杨雄上当,不如说他欺骗了自己,落得个如此“荒凉”。如果不用内心独白的方法去叙述,就没法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石秀的突兀行为。有人说,施蛰存的描写是不真实的,认为“生活中即使有施蛰存所描写的这种人物,那也决不是石秀,只能是另一种人。对于石秀这样一个古代的急公好义的起义英雄来说,究竟是《水浒》的写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还是新感觉派作家的写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呢?尽管《水浒》是一个浪漫主义气息很重的作品,但我宁可相信《水浒》所描写的石秀,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4](P.159)施蛰存则认为,他的《石秀》同《水浒》同样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只是“因为《水浒》中写的是石秀的‘表’,我写的是其‘里’。”[5]施蛰存是通过显尼志勒才了解弗洛伊德及其理论的,并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显尼志勒所擅长的内心独白,将人物的性心理描写到极至。他的《鸠摩罗什》、《将军底头》也都是用内心独白描写性心理的佳篇。
二
在《善女人行品》里,施蛰存以内心独白写女性性心理,是“完全研究女性心理及行为的小说”。[6]显尼志勒的作品也是多写女性性心理,施蛰存翻译的显尼志勒的作品,大都是描写女性的,如《妇心三部曲》中的《蓓尔达·迦兰夫人》、《爱尔赛小姐》、《毗亚特丽思》三篇分别写三位女性的二重人格的苦闷,《薄命的戴丽莎》也是写女主角戴丽莎一生的遭遇和繁杂的心理过程。但显尼志勒更多的是写女性变态的性心理,并且其变态情形是异常极端和不可思议的。显尼志勒的《毗亚特丽思》中的主人公毗亚特丽思,她在丈夫死后便变态地将性爱转移到儿子身上,而她的内心仍然朦胧着爱与道德规范的冲突,当儿子另有情人,母亲又将爱移向儿子的朋友,他们又相互嫉妒和仇恨,他们都在这种畸形的爱与恨的二重人格冲突中痛苦煎熬,最后,“毗亚特丽思把她底爱人,她底儿子,她底死伴抱在怀里。了解、宽恕、解放,她闭上了眼睛。”他们最后以死作为矛盾的解决。施蛰存则要保守得多,施蛰存在《善女人行品》里,突出了这个“善”字。施蛰存早期作品《周夫人》中的周夫人有恋童症,但与显尼志勒《毗亚特丽思》中的女主人公毗亚特丽思是不同的,第一,周夫人爱恋十二岁的微官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第二,周夫人只是有点爱恋的意识,绝不会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春阳》可算是施蛰存内心独白的代表作,在对异性的企盼方面,婵阿姨远不及毗亚特丽思执着、极端、变态,婵阿姨的性欲望是适可而止的。十三年前,婵阿姨的拥有一千亩良田的未婚夫在婚前突然死去,婵阿姨经过了二日二夜的考虑之后,抱牌位成亲而成为一千亩良田的继承人。十三年后的一天,“昆山的婵阿姨,独自走到了春阳和煦的上海的南京路上。”她感到这上海的春阳,“倒是有一些魅力呢……今天,扑上脸的乃是一股热气,一片晃眼的光,这使她平空添出许多兴致。”“真的,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她决定在上海玩一玩,于是在一个小餐馆里吃中餐饭,在这里,她羡慕旁座的三口之家,她留意了一个文雅的男子,幻想着他在她身边坐下,微笑着攀谈,婵阿姨做着罗曼谛克的白日梦,并由这个男子联想到银行的职员,“她的确觉得,当她在他身边挨过的时候,他的下颔曾经碰着了她的头发。”“婵阿姨的自己约束不住的遐想,使她憧憬于那上海银行的保管库了。”她回到银行,银行职员的一声“太太”,使她彻底地失望了,“愤怒和被侮辱了的感情奔涌在她眼睛里,她要哭了。”她在银行职员的眼里已不是年轻的小姐,而是中年的太太,她不得不回到现实。内心独白正是这种白日梦得天独厚的表达方式。梦醒之后的婵阿姨,又还原了吝啬的土财主的本性。
婵阿姨与毗亚特丽思的不同,便是婵阿姨仍回到原来的位置,不像毗亚特丽思那样不计得失、不顾后果,一意孤行地往前冲,当然也就没有显尼志勒作品所具有的悲剧性。施蛰存说:“以性爱为主题的施尼茨勒的小说和剧本中间所表现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一种怀疑论。他对于人类的命运有一种怀疑,他相信爱是支配人生的一个主力,但这个主力的唯一的强敌却是死及其邻人,例如衰老,贫贱,鳏寡之类。每一个人的最终运命都得取决于这个主力与它的强敌搏斗之结果,而这个结果往往成为人生的悲剧。施尼茨勒的作品就是以最熟悉的维也纳城作为背景而描写的这种人生的悲剧。”[1](P.1205)如毗亚特丽思就不得不以死作为结局。《爱尔赛小姐》中的爱尔赛小姐也是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痛苦。施蛰存的小说没有这样沉重的描述,他不仅消解了国师的神圣,消解了英雄的高大,也淡化了普通人生的苦痛,特别是那些无足轻重的女人,她们没有痛不欲生的体验,没有惊天动地的结局,她们多是小忧伤,小烦恼,即使有痛不欲生的忧伤她们也不痛不欲生,即使该有惊天动地的结局她们也决不弄得惊天动地。她们的人生态度是世俗的,平庸的,善变的,她们顺应环境,不与环境作对,她们会因环境而改变,却不会因改变不了环境而毁灭自己。所以,《周夫人》中的周夫人的爱恋,便因微官不再来而不了了之;《春阳》中婵阿姨的骚动,便因没有爱恋对象而消失,《雾》中素贞小姐对异性的憧憬,便因对“戏子”的偏见而终止。她们的情感欲望转瞬即逝,也许,“转瞬即逝”这个词用得有些极端,她们的情感欲望并没有立即消失,但她们的生活处境和人生态度使她们不得不放弃过多的奢望,过一种虽寂寞但平静、稳妥的日子。《狮子座流星》、《港内小景》《残秋的下弦月》、《莼羹》、《妻之生辰》也都是小悲小伤,她们的欲念是适可而止的,即使有点过分的企盼,也是碰到南墙就回头。不走极端,给自己台阶下。这不仅是施蛰存小说女性形象的人生观,并且是中国大多数老百性的人生观,也是施蛰存的人生观:不张扬,不锋芒,飘逸,中庸。
施蛰存笔下女性的人生观不仅与显尼志勒的人物不同,而且与中国五四时期的女性也有一定的距离。她们不是解放了的娜拉,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号角并没有唤醒她们,她们是被五四运动遗忘的人。这便使施蛰存作品的女性形象与五四时期的冯沅君、黄庐隐等女性作家作品的女性形象区别开来。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为了追求自由和解放不惜牺牲生命,在《隔绝之后》中,主人公自杀前有一封给母亲的信,信中说:“亲爱的阿母:我去了!我和你永别了!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最景慕的人。……但是我爱你,我也爱我的爱人,我更爱我的意志自由,在不违背我后二者的范围内,无论你的条件是怎样苛刻,我都可以服从。现在,因为你的爱情教我牺牲了意志自由和我所最不爱的人发生最亲密的关系,我不死怎样?”这样的女性是把意志自由和爱情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更别说安定的生活。而黄庐隐的作品中,“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7]施蛰存作品中的女性为什么不去求自由求解放呢?她们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吗?不是,她们没有一个没有企盼和欲望,她们没有一个不在寂寞和痛苦中煎熬。但她们委曲求全的生活,究其原因有二:第一,她们是一些五四精神没有影响到的人群,她们自身的封建思想、传统文化使她们不仅不能像冯沅君笔下的人物那样努力摆脱家庭、社会的束缚,她们甚至不能摆脱自己对自己的束缚,《雾》中的老处女素贞小姐虽然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很可亲的男子,柔和的容颜,整洁的服饰,和温文的举动……于是,她给自己私拟着的理想丈夫的标准发现了一个完全吻合的实体。”但她的封建思想使她将电影明星与戏子划等号,并对戏子极端的鄙视,她只能以老处女终其生了。《狮子座流星》中的卓佩珊夫人厌恶她那“身体一胖连礼貌也没有了”像“猪猡”的丈夫,喜欢汽车上的很整洁、很有礼貌的年青人,但她不可能往前迈出一步,封建思想使她只想生个孩子来排遣寂寞。她们是一群紧紧依附家庭、丈夫、土地的节妇,传统思想束缚着她们的过去,束缚着她们的现在,也束缚着她们的将来,她们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束缚她们的环境。第二,是她们不想失去既有的经济地位,经济权是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和《伤逝》里所阐明的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春阳》中的婵阿姨便是她们的代表,她的“自由解放”就意味着将失去已有的财产——族中人虎视眈眈盯着的三千亩土地,婵阿姨在短暂冲动之后毅然决然地打道回府,一方面是她不敢放荡,一方面是她不愿放荡,她不愿失去既定的生活,她宁可孤寂而安定,不愿快乐而动荡。所以,她欲望的不能满足,主要原因是她自己的局限,她有很多不愿也不舍丢掉的东西。吴福辉说:“她的冲不破是由她的一次希图冲破来表现的。”[9](P.144)其实,她的冲不破,同样也是她不敢冲破不愿冲破的必然结局。当然,这并不等于她们一点想法也没有,一点欲望也没有,她们跟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也包括世界上的男人,他们都有对爱、对性、对异性的企盼。只是因为她们是“善女人”,她们必须将欲望埋在心里。施蛰存选择了显尼志勒的内心独白方式,揭示她们被“善”字掩盖着的欲望潜流,善女人的“善”只是表面的贞节,内心仍有许多“不善”“不贞”的想法。这是施蛰存对善女人、对节妇的解构。小说以《善女人行品》为名,着实有着深刻的意味。
施蛰存也不是完全不写性变态,但他着重写男人的性变态,而且变态的情形也与显尼志勒不同。在与《善女人行品》同一年出版的《梅雨之夕》中,大多数作品是内心独白的精品,《在巴黎大戏院》写一个已婚中年男子的性欲望和性变态,在施蛰存笔下,写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欲望是不一样的,写男人直露,写女人含蓄。在《在巴黎大戏院》中,一个男子与一个年轻女子同看电影,在大戏院看电影只是给主人公提供一个谈情说爱的环境,如作品的主人公所说的:“在我们的这种情形里,如果大家真的规规矩矩地呆看着银幕,那还有什么意味!干脆的,到这里来总不过是利用一些黑暗罢了。有许多动作和说话的确是需要黑暗的。”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这内心独白将男子的性欲望和变态心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不停地揣摩那女子的心理:“她会不会像影片中的多情女子那样地趁此让我接吻?”这是一个委琐的男子,不停地猜测揣摩,却不敢行动。当女子将自己的手绢借给他时,他的性高潮就以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哦,好香,这的确是她的香味。这里一定是混合着香水和她的汗的香味。我很想舐舐看,这香气的滋味是怎样的,想必是很有意思的吧?我可以把这手帕从左嘴唇角擦到右嘴唇角,在这手帕经过的时候,我可以把舌头伸出来舐着了。甚至就是吮吸一下也不会被人家发现的。这岂不是很妙?好,电灯一齐熄了,影戏继续了。这时机倒很不错,让我尽量地吮吸一下吧。……这里很咸,这是她的汗的味道吧?但这里是什么呢,这样地腥辣?……恐怕是痰和鼻涕吧?是的,确是痰和鼻涕,怪黏腻的。这真是新发明的美味啊!我舌尖上好像起了一种微妙的麻颤。奇怪,我好像有了抱着她的裸体的感觉了……”这样的变态心理,这样的淫秽心理,是施蛰存笔下男性的专利。施蛰存从不这样赤裸裸地写女人,一反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人的鄙视。中国古典小说都认为女人是祸水,施蛰存认为男人才是一切罪孽的渊源,他说:“都市的人,现代的人,你知道,一个青年一定是好色的。”[8]女人多是“善”女人,善女人不可能像男人那样变态淫秽,她们的欲望是谨慎的,有分寸的,当然也是暧昧的。她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像男人那样的性要求她们不仅仅是不敢做,连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像男人那样歇斯底里地癫狂,传统文化对她们的束缚深入骨髓,她们只是做做谨慎小心的梦而已。
三
施蛰存推崇显尼志勒的内心独白,是因为他认为写人物重在写心理,少写行动。他说,显尼志勒“描写性爱并不是描写这一种事实或说行动,他大概都是注重在性心理的分析。”[1](P.1204)所以施蛰存写的女性都是欲望的畅想者,而不是欲望的实践者。这就与他的朋友刘呐鸥、穆时英区别开来,刘呐鸥、穆时英都是擅长写女性的,但刘和穆将女性的欲望都写在脸上,写在行动上,特别是刘呐鸥,他笔下的女性多是没有思想的躯壳,都是性侵犯者,小说情节都是肉的游戏,所以,刘呐鸥的小说很少写内心独白。刘呐鸥的全部小说只有一篇《残留》写了女性的内心独白,这篇小说不像他的其他小说那样只写故事框架,或者说只写男性心理,不写女性心理,《残留》全篇没有情节故事,只有一个女性霞玲在丈夫死后紊乱的、非理性的、痛苦的内心独白。刘呐鸥的内心独白与施蛰存的内心独白不同,刘呐鸥不像施蛰存那样写女性内心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刘呐鸥的女性没有这个冲突,她们只有欲望以及欲望不能达到的痛苦,刘呐鸥写了她们沉沦的心理过程。《残留》中的霞玲在失去丈夫的同时便失去理性,失控的性欲望像泛滥的汪洋,无拘无束,最后只剩肉欲的享受与体验。《残留》是刘呐鸥小说的一个典型意象,是他的其他小说的一个缩影,是他那些没有思想只有性游戏小说中女性行为的注释。刘呐鸥将女性写得如此放纵、失衡的原因有二:第一,刘呐鸥自幼在日本东京上学,没有接受多少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没有见到多少具有传统品格的女人。写不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女性,他写出的女人多具有异域风采,多是玩弄男性的风流女人。而施蛰存生活在松江、杭州一带,是都市边缘的小镇人,施蛰存早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见到的传统女人先入为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他笔下的女人是守旧的,拘谨的,内向的,她们不可能像刘呐鸥小说的女性那样放荡和肉感欲望泛滥。第二,刘呐鸥对女人有成见,成见源于他对包办婚姻妻子的不满,他把对妻子的厌恶扩展到对女人的厌恶,他在1927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女人,无论那种的,都可以说是性欲的权化。她们的生活或者存在,完全是为性欲的满足。……所以她们除‘性’以外完全没有智识。”[10]刘呐鸥的偏见,妨碍他对女人深入了解,所以他不可能真正的理解女人,不可能写出女人内心因灵与肉、传统与现代冲突的痛苦。施蛰存对女人是同情的,他深知女人的性苦闷和不能越雷池一步的艰难处境。周夫人的年轻守寡、婵阿姨的未婚先寡、素贞小姐的无性无爱,孤寂与性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她们所处的乡镇环境和她们所接受的传统教育,都使她不能像刘呐鸥作品中的女性那样走出封闭的环境,走进都市的舞厅、竞马场、特别快车,把自己当作商品来换取一时的快乐。穆时英小说的内心独白与刘呐鸥、施蛰存都有区别,从内容上讲,穆时英写女性的早期作品更接近刘呐鸥,写女人放荡的性心理,玩弄男人,把男人当作消遣品,如《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五月》等。但当他渐渐地了解了女人以后,穆时英就远离了刘呐鸥对女人的偏见,他知道她们是在快乐的面具下掩盖着寂寞和痛苦,所以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便着重揭示女人的苦闷,但这苦闷不是施蛰存小说中女性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苦闷,而是对都市生活、社交生活厌倦的苦闷,《黑牡丹》中的女主人公便是她们的代表:“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天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那么深深地浸在奢侈里,抓紧着生活,就在这奢侈里,在生活里我是疲倦了。”疲倦了的黑牡丹们并不能走出她们厌倦了的生活,她们只能苟延残喘地在生命线上挣扎着,“卷在生活的激流里,你知道的,喘过气来的时候,已经沉到水底,再也浮不起来了。”(《黑牡丹》)从形式上讲,穆时英不像刘呐鸥的《残留》那样,没有故事的艺术构思,全篇只是一些杂乱无序的内心独白;他也不像施蛰存那样,很巧妙地由“他述”转为“自述”,又由“自述”回到“他述”,用第三人称抒写人物内心独白。穆时英是将内心独白穿插在情节故事中,有时是用日记穿插,有时是将内心独白与外部交流语言双线交叉并进,如《五月》中写女主人公蔡佩佩,这是一个会玩弄男子的女人,在五月多情的季节,蔡佩佩同时与四个男人恋爱,但她表面却是一个纯洁的少女,她在与男人交往时,表现得矜持、圣洁,而内心里却狡猾、放纵,用内外双线并进的写法将内心独白和人物对话同时写出,将这复杂人物的复杂表现描写出来。
都是写女性的女性独白,施蛰存是站在女人的角度写女人,刘呐鸥是站在男人的角度写女人,穆时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将女人当自己来写。站在女人角度写女人的施蛰存,能设身处地地替女人着想,是真正从内心理解女人、同情女人,将女性的欲望企盼真实地表现出来。站在男人的角度写女人的刘呐鸥,仍是男权话语,对刘呐鸥来说,他既需要女人,又瞧不起女人,他需要女人的肉体,却鄙视作为“人”的女人,他对女人的心理描写是以偏概全,是将个别现象当普遍现象来写。穆时英写女人就是写自己,他是借写女人将自己的寂寞痛苦宣泄出来。如他在《黑牡丹》里写的:“我要爱上了那疲倦的眼光了”,“因为自个儿也是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着的人。”“她没问我的姓名,我也没问她的。可是我却觉得,压在脊梁上的生活在的重量减了许多,因为我发觉了一个和我同样地叫生活给压扁了的人。”穆时英生活的变故使他渐渐的由以前的抗争而颓废了,他认为:“人生是急行列车,而人并不是舒适地坐在车上眺望风景的假期旅客,却是被强迫着去跟在车后,拼命地追赶列车的职业旅行者。以一个有机的人和一座无机的蒸汽机关车竞走,总有一天会跑得筋疲力尽而颓然倒毙在路上的吧!”[11]穆时英的颓废使他过早的断送了他的才华。施蛰存没有刘呐鸥的玩世,也没有穆时英的虚无,施蛰存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实践着女性内心的写实。
施蛰存推崇幻想与写实地融合,没有幻想,就没法写出主人公内心的秘密,没有写实,就没法写出主人公真实的内心。施蛰存的内心独白正是幻想与写实地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