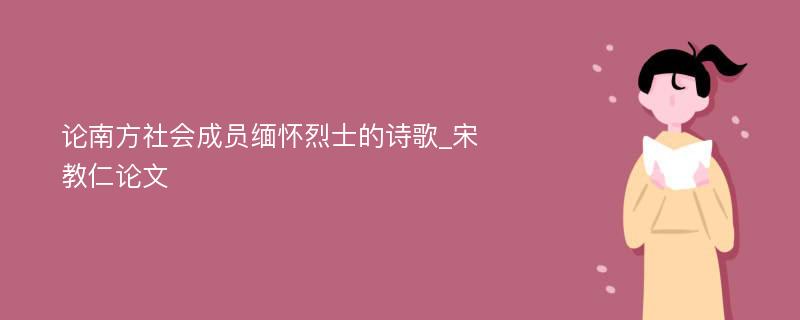
论南社成员悼念先烈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烈论文,诗歌论文,成员论文,南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2-0119-06
烈士本指的是坚贞不屈的刚强之士,如《庄子·秋水》中所言:“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后也指有志建功立业之人,如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南社诗人的“先烈”、“烈士”却有着与古义不同、相对固定又较为宽泛的含义,它是指20世纪初为了实现共和民主的社会制度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这其中既有为了共和事业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终离人世者,也包括为唤醒国民斗志,激励民众精神不惜以死警世者,还有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奔走呼喊,终为政敌所害者,当然,占篇幅最大的还是那些以武力推翻两千年帝制,却不幸殉国者,最后这类烈士还有一个特定称谓:辛亥烈士。
自清末始,中国的有志之士便从未停止过追寻共和救国的道路,然前路漫漫,中国的共和之路几经波折,形势大起大落,无数革命斗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这些先烈,南社诗人在悼念的诗中或长歌当哭,或拔剑长舞,用不同的形式怀念着这些英雄、社友、朋友甚至亲人。由于这一类型作品数量可观,与时代背景结合紧密,因此值得重视。
一、“七二黄花战骨霜,遥挥涕泪瞻高冈”:对革命先驱的哀悼
早在20世纪初,中国的革命事业便初见端倪,陆续有先行者投入到共和事业之中,只是由于当时形势不够明朗,参与人数不多,再加上农民起义和联军侵华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部分削弱了革命的影响力,所以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后期革命事业愈演愈盛的情况下,南社的诗人们开始回顾这些早期的革命先行者,蒋同超所作《挽革命先烈同学黎科(作者自注:庚子死事于汉口)》中,根据作者注释可得知黎科于1900年去世,由于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同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林圭、唐才常等烈士,因此作者非常详尽地勾画出这位革命先驱的形象:“弱冠游析津,公门厕桃李。新学斠欧化,微言析名理。日斜又庚子,大陆龙蛇起。红巾扰北清,白帜标南纪。黎子航海来,乃似忧天杞。故事踵胜广,义旗发江涘。指日捣黄龙,谋略智足使。如何天不佑,谋泄嗟何似。系作阶下囚,天道宁至此。…黎子好头颅,遽为同胞死。”[1]
从中不难看出,黎科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很可能有留学背景,在庚子年间想要发革命之举直捣黄龙,无奈因事泄被捕,后被处决,而作者也在记人的同时记录下了庚子年间的社会图景:农民起义和处于初期的革命活动并生,清廷的统治已经开始受到了严重威胁,数百年苦心经营的庞大帝国已经在风雨中摇摇欲坠,辛亥革命不过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诚如作者所言:“武昌一发难,共和不旋趾。溯此发轫者,实自庚子始。”也正是借助于这种追忆性质的哭悼,我们才得以一睹二十世纪早期的革命全貌。
在爆发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爆发于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同盟会策划、黄兴领导的一次具有较全面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地点是广州,最终以失败告终,当地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敛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其改名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场革命也是因此得名。这场并不成功的革命在一部分南社诗人心中留下了阴影,高旭在《哭赵伯先先烈》其三中这样描述:
吞胡壮志讵能平,弹压胸中十万兵。愤逐黄花新鬼去,中原从此坏长城。
哭悼的对象赵伯先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还是黄花岗起义的主要组织策划者和领导人,起义失败后他因壮志未酬,悲愤成疾,1911年5月18日病逝于香港。在这则作品中更多看到的是起义失败之后带给诗人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对于起义领导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惋惜之余,对于国家命运前途的忧心充斥字里行间。
尽管这场类似于预演的起义失败了,却并没有影响大多数南社诗人的革命热情,狭义的民族主义以及建立共和制的国家仍然成为当时悼念诗的主旋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呼声不仅是革命先驱们所遵从的,也是悼念先烈的南社诗人们所达成的共识,在作品中不乏言辞激烈者,如雷铁厓《哭广州殉义诸烈士》其一:
誓抵黄龙聚义兵,复仇匪羡帝王名。却怜涿鹿干戈起,辜负昆阳雷雨生。
子弟八千殉项羽,英雄五百死田横。胡儿漫喜根株尽,得遇春风草又生。
尾联坚信清廷的打压不会对顽强的革命势力造成毁灭性打击,志士仁人的力量必如春风吹又生的野草般席卷中国,作者毫不动摇地相信清廷必将自取灭亡,对于烈士们的哀婉化为一腔悲愤喷薄而出,在其四中不惜大骂:“白山黑水妖犹在,红粉青年我尚哀”。满洲女真兴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在此代指清廷,作者不加掩饰地称之为“妖”,既能看出因革命青年的早逝而流露出的不加节制的愤怒,也能从侧面折射出气息奄奄的清廷对于舆论的压制早已无能为力,的确是一派苟延残喘之态。
二、“荆楚一振臂,天下皆同仇”:对辛亥烈士的崇敬
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高扬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更是点燃了南社诗人们的革命热情,使得悼念先烈诗这一题材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诗人们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谱写成胜利的凯歌,其后又整体趋向于表达对辛亥烈士们的崇敬与怀念。
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时,这种不可遏止的喜悦和对于未来发展前途的乐观即使在悼念诗中也表露无遗。陈去病在题为《偕梦遽醉厂游岳麓,有悼陈天华烈士,还饮赋示同座诸子》的五言长诗中这样描述:
濡忍三百载,决绝终无由。人心忽思汉,天运复来周。荆楚一振臂,天下皆同仇。
遽翻往古局,一洗群伦愁。因缘得来止,豁焉开心眸。青天亦何问,金尊且暂休。
芳兰况满前,春意岂清秋。浩歌一采撷,安用哀高邱。
陈天华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出色的宣传家,生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为表抗议以死报国。在陈去病的作品中却看不到消极的怀念,虽然在标题中言明为哭悼诗,然而这首创作于辛亥革命之后的诗歌却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喜悦和豪迈之情,荆楚之士振臂一呼,天下仁人志士同仇敌忾,朝思暮想的胜利虽然姗姗来迟,却丝毫不能减弱诗人们的激情,以后辈的觉醒和努力来悼念这样一位革命的先驱,也许是告慰前人最好的方式。
王葆桢则用组诗的方式创作了《杨哲商烈士悼歌七章》,将杨哲商的传奇一生作成了几幅精彩的剪影,而背景便是近代中国革命如火如荼的形势。杨哲商是一位用行动支持辛亥革命的实干者,由于革命初起,武器奇缺,杨日夜赶制炸弹,不幸于1911年11月6日误触炸弹而亡。作者在其六中艺术性地处理了杨牺牲时的一幕:
风云莽荡武昌城,大陆龙蛰雷一声。豪杰蜂起天下走,江山半壁东南倾。
侨沪覆壁学张俭,裹铁手弄一丸轻。金汤臲卼颠仆破,石头铁甕徒虚名。
喜闻直捣黄龙府,拍案惊落灯花明,飞电流丹触导线,大化真火还无生。
呜呼六歌兮火纵横,海上夜夜怒涛鸣。
这章同时也是全篇的高潮,武昌起义的成功对于一个屡遭挫折的革命党人而言是多么的令人欣慰,同时这一章也是杨哲商生命乐章的最高音,他在欣闻武昌起义胜利之后,不由拍案称快,却惊落了灯花引燃了炸弹,在轰轰烈烈中终其一生,这样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悲剧意味,反而使全篇呈现出一种壮美的风格。
与壮美风格有所不同的是,有些悼念诗歌描写情感细腻,基调沉重,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对于先烈无尽的思念,如周伟《实丹烈士死三年矣,魂梦不见,容止全忘,旅夜凄清,三更枕上泪下如渖,得诗三章以代一哭》(其一):
有生必有死,死亦何悲伤。泰山与鸿毛,死更当较量。君死诚为国,君死更为乡。
卓哉应不朽,风雨哭国殇。君死三年矣,墓草趁斜阳。孤儿哑哑语,老父鬓全霜。
孤灯泣嫠妇,君妻已痴狂。一室太凄清,哭声尤凄惶。转倏寒食节,斗酒葡萄香。
塔儿月影高,魂兮其来尝。
这篇诗歌的哭悼对象周实(1885-1911),山阳(江苏省淮安县)人,1909年加入南社,1911年听闻武昌起义,从南京回家与阮式共谋响应于淮安,后被山阳县令姚荣泽所诱杀。而作者周伟是周实的堂弟,与周实同时参加南社,武昌起义之后,与周实一起返淮组织光复淮安的活动,周实殉难后,他为平反冤案奔走呼号,姚荣泽在上海受审时他出庭作证。
二人的亲戚关系使得作者在抒写哭悼之感的时候将记叙的笔触探向了烈士的家人,忠实地呈现周实去世的三年间家庭的变化与家人的伤痛,这种描述让诗篇有了更强大的感动人心的力量。
三、“专制不死共和死,人天消息果离奇”:对反袁斗士的惋惜
辛亥革命之后,许多人沉浸于短暂的胜利带来的满足以及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人们预料中的那么乐观,在经过几次谈判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作出让步,袁世凯就任总统,就任伊始便倒行逆施,甚而要恢复帝制,沐猴而冠。同时袁也开始大肆讨伐异己,杀害革命进步人士,南社成员中有不少思想进步、为信仰身体力行者也倒在了袁的枪口之下。如柳亚子所言:“新邦初建,期望太平……其后贼凯窃国,诛锄异己。逆谋未露,先陨遁初,虐焰将销,犹残英士,而……诸君子,并断头沥血,白首同归,几乎举吾社之良而尽歼之。”[2]
南社在这一时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柳亚子谓之“摧残期”,而对先烈的哭悼诗创作也进入了第二个高潮时期。与辛亥革命时的创作高潮不同,这一时期的悼念诗歌矛头直指袁世凯,对于这个破坏共和的窃国大盗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但同时也大多基调沉痛,甚至对于未来有着极端消极的想法。
而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哭悼对象当属宋教仁与宁调元。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湖南桃源人,南社成员。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1913年2月4日,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并“反复宣传和论述内阁制和政党内阁的必要性”,[3]3月20日,袁世凯指示刺杀宋教仁,两日后宋不治身亡。
宋教仁的入社对于南社有着重要的多重意义,宋的政治身份和政坛地位提高了南社的知名度,增强了南社的影响力,同时也使得南社在政治方面进步意味更浓,对于持革命新思想的有识之士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从这个角度上讲,宋的离世对于南社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对于南社成员也有着更加沉痛的打击。
宋去世之后,南社诗人写了大量的哭悼诗,作品从各个角度展现宋教仁生前的政治抱负、被害的前因后果以及死后社友们的感慨悼念。在其中也不难发现南社诗人们重新开始审视和反思所谓的革命,其中不乏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也有自身感到的恐惧与不安,革命不再是有着瑰丽色彩的梦想,而是就在身边时刻威胁生命的残酷选择。可以说由宋教仁案引发的这次哭悼诗高潮使诗人们更趋于理性,有些南社成员因在作品中表现出了这种理性的反思而显示出了另外的深意:
衮衮时贤竞厌贫,本来面目独斯人。争传渔父终兴汉,忍说桃源可避秦。
养虎而今贻祸患,伤麟千古共酸辛。碑前泪迹红如血,遗爱从知在国民。
——张昭汉《悼遯初先生》
在对于宋教仁终遭人暗算的不幸遭遇表达哀婉之余,颈联则隐隐地带出对于孙中山一味忍让、纵容袁世凯终酿祸患的微词。实际上宋教仁的去世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也正是由于这位共和功臣的离世使得革命党人彻底认清了袁世凯的面目,在宋遭遇不测短短四个月之后,孙中山再次聚集革命力量冒险起兵。
这场以江西、江苏为主战场的武装斗争于1913年9月1日再度失败,这次反袁革命是为了保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宋教仁案则是二次革命的导火索。面对袁世凯的狼子野心,革命党人已经耗尽心力,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南社的诗人们经历了革命后短暂的喜悦,面对的是更加黑暗的现实,心灵承受了从未有过的惶惑与悲愤。”[4]
如果说宋教仁的死尚且是权力争斗的暗涌使然,宁调元的牺牲却赤裸裸地揭示了袁世凯集团的独裁阴谋。宁调元(1873-1913)字仙霞,南社成员。早年间组织、参加革命起义活动,清末曾入狱,终被保释,1913年6月在汉口再次被捕,9月25日,宁调元以“内乱罪”被杀害于武昌抱冰堂。让诗人们痛心不已的是宁调元并没有倒在与帝制交手的战争中,而是死在了伪共和的阴谋里:
专制不死共和死,人天消息果离奇。塚中枯骨嗤公路,泽畔骚魂伴屈累。
晞发西台挥古泪,断肠南国写新词。鸡鸣风雨堪惆怅,回首当年恨不支。
——高旭《收辑亡友宁太一遗墨装订成册,因题四诗以弁其首》(其一)
贾傅长沙赋鹏余,南幽回忆为停车。前言戏耳偏成谶,狱到共和不可居。
——刘约真《哭太一诗后十首》(其三)
民国已经建立,为了实现共和事业而呕心沥血的元老级人物在清末尚能最终获释,此时却终遭不测,诗人们对于如此的“共和”怎能不痛心疾首,字里行间传达出的无奈催人泪下。在如此混乱的时代中,有进步思想的仁人志士不仅是要面对新政权冲突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险局面,还要提防打着维护帝制幌子的旧武装力量的迫害,新权的飘摇不定和死灰复燃的旧派势力让形势更加复杂,也把这些进步人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面对着这样一个虽言共和,然奸佞当道,小人掌权的社会,有些南社诗人在哭悼诗中开始表现出消极的情绪:
自君之死矣,国事愈蜩螗。酬庸烹功狗,浩劫酿红羊。杀人已盈野,党碑姓字香。
民穷脂髓尽,苛政方高张。饥者填沟壑,壮者散四方。走险聚为盗,四野全跳梁。
高官方酣醉,那恤民苦伤。丁茲多难日,存反不如亡。魂兮倘归来,故国已全荒。
——周伟《实丹烈士死三年矣,魂梦不见,容止全忘,旅夜凄清,三更枕上泪下如渖,得诗三章以代一哭》(其三)
作品应该是创作于1914年,曾经想要建功立业以告慰英灵的豪情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呈现眼前的俨然是一幅人间炼狱图,有功之臣不得善终,当权之人为所欲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饿殍遍地,盗贼横行,一派民不聊生的场景。作者竟发出了“存反不如亡”的声音,故国全荒,看不到任何希望,诗人们的情绪已然滑落到了谷底。
四、时代鲜明,含义深远的意象运用
南社诗人的悼念先烈诗歌虽非一人、一时之作,然而因为题材相似、表达意图相近,在意象运用上出现了趋同的现象,更有一部分意象因具有特殊意义而被重复使用。
首先,“头颅”意象。“头颅”是在近代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广泛地用在富有献身精神,表达豪情壮志的作品中,从侧面反映出时人的人生观,对于追求信仰的执着和甘愿杀身成仁的勇气:
苍茫惹起无涯感,狂荡东风未许删。大好头颅争价值,几多血泪认澜斑。
须知秦帝鲁连耻,肯信周兴管叔顽。剩有精卫常不死,巍巍万古太行山。
——高旭《悼吴绶卿先生》
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有过留日经历,回国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1月7日,在车站被暗杀。
此处的“头颅”指代生命,更象征着一种大无畏的气魄,这类意义在哭悼诗中广泛出现,如“淮南此义士,相惜好头颅”(胡蕴《周实丹烈士挽诗二首》其二),“恨未从军轻一掷,头颅无价哭无声”(宋教仁《哭铸三尽节黄冈》其二),“头颅付黄祖,此意问谁怜”(柳亚子《三哀诗》其一),作者或对于先烈勇于献身表达敬仰之情,或用以激励自身实现人生价值,“头颅”也因此成为最集中出现的意象。
其次,“屈原”意象。之所以“屈原”作为大量使用的意象出现在这类诗歌中,原因有二,其一是由于屈原本身的经历及他忠心爱国的情怀,在小人林立、谗言横飞的环境中洁身自好,坚守高洁的品质,与先烈所处的环境及所谱写的人生有相似之处,“屈原”已经升华成了一种精神,作为意象出现自然很平常;其二是地域性的原因,屈原是楚人,而近代革命首发难者便是荆楚志士,两湖籍的先烈人数尤多,以这一时期出现在南社诗人哭悼诗中的先烈为例,吴绶卿是湖北人,杨笃生、宋教仁、宁调元、林圭、陈天华等均为湖南人,这种地域的相合再加上特有的经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屈原,而“屈原”意象也成为了爱国之精魂、高洁之人格的代名词出现在了哭悼诗中。
如“屈平已没久,招魂复有谁。……哀哉楚大夫,生死关安危。自从葬汨罗,豺虎满廷闱。长城谁而坏,蛾眉相谗讥。……”(胡韫玉《吊钝初先生》),“抉目至今悲伍相,招魂何处哭三闾。”(庞树柏《三月二十二日为遯初周年,晚过沪宁车站遯初被害处》),“泽畔行吟吊屈原,西风无语近黄昏。”(周人菊《倬夫过沪,竟夕未寐,谈实丹烈士往事,遂成一首》),“屈宋流风远,千秋得嗣音。”(王鼎《辛亥六月读白门悲秋集怀周君实丹》其一)。“屈原”意象已经在这一部分哭悼诗中化身成了爱国精神甚而用来指代有能力挽大厦于将倾的英雄人物,比屈原本身所象征的含义又进了一步。
再次,杜宇啼血、苌弘化碧意象。这二者经常同时出现,杜宇啼血原指为事业日夜操劳,至死不渝,而苌弘化碧则是周朝大夫苌弘因得罪朝中权贵,蒙冤被杀,有人私藏其血,三年后化为碧玉,用以指代刚直忠正、为正义事业蒙冤抱恨之人。而这两个意象恰对应了诗人笔下忠诚正直,却含冤被害的先烈:“碧血冤沉淮水滨,同声昭雪誓春申。”(周斌《哭同社死友》其一),“大好河山归浩劫,苌弘化碧杜鹃啼。”(邢启周《追哭太一先生》),“斜日数声啼杜宇,烽烟遍地泣哀鸿。”(刘筠《再哭遯初先生》),“已悲金烬暗,况值杜鹃号。”(黄忏华《亡友周仲穆哀辞》其一),“土中埋玉树,海底瘦香桃。化作三年碧,荣于一字褒。”(黄忏华《亡友周仲穆哀辞》其二)。
辛亥革命之后许多志士没有逃脱鸟尽弓藏的命运,“新邦初建,刑赏不明,激起了南社同人的极大愤慨”,[5]而苌弘化碧、杜鹃啼便是南社诗人给予这些先烈献身事业的肯定和由衷的赞扬。
最后,英雄意象。这里的“英雄”包含两类,一类是群像型英雄,如项羽八千子弟,田横五百士,另一类则是民族英雄,尤以岳飞和文天祥为代表。群像型英雄也通常出现在对群体烈士的悼念作品中,如“子弟八千殉项羽,英雄五百死田横。”(雷铁厓《哭广州殉义诸烈士》),“田横犹有家,项羽岂无坟。”(柳亚子《湘中烈士墓将被狡,发诗以悲之》)。
而民族英雄的意象在近代诗歌中同样大有深意,面对异族统治,尤其是清末社会的千疮百孔,民生凋敝,时人渴望民族英雄恢复汉家山河,但在南社诗人的先烈哭悼诗中,这种意味并不浓,民族英雄意象也被泛化成了忠肝义胆、名垂青史的含义:“天生妙手堪屠龙,岳飞报国真精忠。”(高旭《吊亡友宁太一用夏存古细林野哭原韵》),“文山集杜同千古,司马下蚕不足贤。”(蒋信《题太一遗书》)。以英雄写英雄,英雄意象也成为了悼念先烈诗中很有特色的部分。
总之,南社诗人悼念先烈的诗歌鲜活地刻画出十数位先烈的形象,为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补上了浓重的一笔,同时以哭悼为切入点,完整地描摹了上个世纪初直至袁世凯去世这十几年时间中的社会形态、时人思想,勾勒出一幅交织着先驱热血和英雄壮志的社会长卷。
标签:宋教仁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历史论文; 诗歌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屈原论文; 袁世凯论文; 离骚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