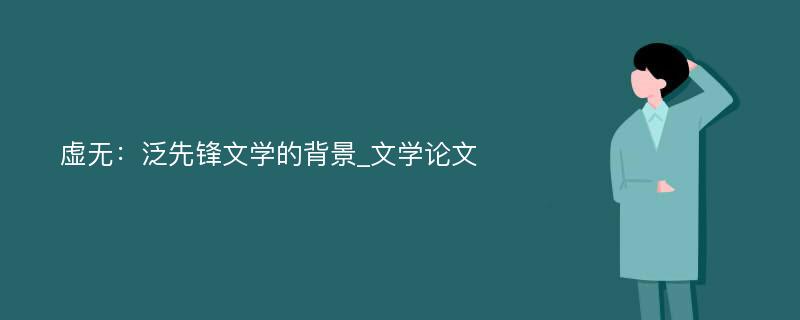
虚无:泛先锋文学的底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底色论文,虚无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到虚无,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一个否定性概念,意指一种极端的怀疑主义立场或者对人类一切价值的否定,甚至还指一种颓废厌世的悲观思想。其实,这是误解。就虚无一词的原初意义看,本无所谓褒贬,它不过就是一个哲学范畴而已,正如道家的“无”佛家的“空”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空无、虚无实际上强调的是宇宙万物虚实相生、阴阳互动、变化不居、生生不息的一面。西方存在主义也讲虚无,那主要是指对自由的无化。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但事实上人又无时无处不在限制之中,自由既然在现实中无法安顿,便只能安顿在自我的意识之中,这即叫作自由的无化,或者虚无。我以为,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它更多地是对世界无规律、无秩序、不确定的一面的体认,这种世界观正好与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形成互补,共同代表了人类的智慧。我之所以认为泛先锋文学普遍带有虚无的底色,正在于它在创作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虚无主义的精神旨趣。
从结构走向解构。传统写作可以统称之为深度写作或结构写作,追寻社会、历史、人生等等的深层意义是这类写作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比如现实主义追求历史深度,浪漫主义追求情感深度,现代主义追求生命深度,如此等等。而近年的先锋写作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下,普遍采用了反深度写作的姿态,以消解意义颠覆价值为能事,进行着一场反文化的狂欢。你以为英雄崇高吗,先锋文学中恰恰在进行着反英雄的写作。洪峰《湮没》中的“我”由于活得实在无聊,一心想做个水中救人的英雄,于是便一次次想把女友推入水中然后去救,结果不是被女友打了耳光,就是把女友置于死地。毫无疑问,这样的情节编排实际上是对英雄的嘲弄与亵渎,这样的写作实际上成了典型的非英雄或反英雄写作。你说爱情神圣吗,泛先锋文学却普遍将爱情当作了解构的对象。如果说《不谈爱情》(池莉)、《爱又如何》(张欣)等新写实小说中还只是剥掉了爱情的神圣光环,使其向生活还原,并表现出一种爱的无奈的话,所谓晚生代、新市民、新女性文学中则普遍将爱情写成了性游戏、性交易与性暴力,只有性,而没有爱;只有欲,而没有情,爱情被还原为赤裸裸的欲望本能。九十年代末的所谓美女作家在“私人空间”、“躯体写作”的旗号下,将性展览、性挑逗、性刺激当作招睐读者的主要手段,并把性活动与吸毒、泡吧等情节搭配在一起向读者出售。2000年,一位被炒得相当火爆的美女作家在一次签名售书时就曾脱掉上衣袒胸露乳向观众示意:“你们不是要看吗?”从而引起媒体和观众的极大反感。不过,这倒是非常形象地阐释了“另类”们躯体写作的实质。至于法律、道德、亲情等等则更不在话下,一律在欲望的旗帜下被打得落花流水。(注:格非一部小说的题目就叫作《欲望的旗帜》。)语言呀,艺术呀,历史呀,这些过去被涂上灵光的东西也统统泼上了脏水,被当成了狗屎和垃圾。(注:叶曙明小说《环食·空城》就多次说语言是狗屎、垃圾、灰尘。)
从抗世走向随俗。传统写作总要坚守着某种价值立场或理想追求,不管这种立场或信念是政治的道德的还是文化的生命的,抑或是宗教的艺术的,总之坚守住了某种东西才会认定自己的创作有了一种灵魂。对那些被认定为是否定价值的东西,或与理想相违背的东西,则采取一种批判抗拒的姿态。尽管常常是“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创作者们还是把匡世或抗世当作自己的光荣。先锋写作就不同了,既然它以颠覆价值为能事,它就没有什么东西要坚守,当然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抗拒。有些“晚生代”作家就公开声称他们是没有历史、没有理想当然也没有社会责任的一代,“历史到我这儿就断代了”,“我只能看见我自己”,“我们都是可怜的试管婴儿,也不知道精卵是他妈谁的”。(注:转引自李洁非《新生代小说》。)与坚守和抗拒相比,他们无宁更喜欢违禁与随俗。比如何顿的小说《太阳很好》就写了一个违禁与随俗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宁洁丽原是一家精神病院的会计,丈夫随一个富婆出走后,她也禁不住物欲、情欲的诱惑做了一个小老板的外室。当她遇到男性目光的骚扰时,便做好了违禁的准备:“我在屋里闷得太久了,我已经没有必要为刘平(宁的丈夫)守节,相反我内心确实有背叛他的强烈愿望。”当她决定辞去医院职务投入小老板的怀抱时,也没有丝毫犹豫:“我想最坏的结果顶多是吃父母的饭罢了,实在不行还可以当别人的姘头。”宁洁丽周围的朋友们则为她的违禁行为导航引路、呐喊助威,她们教导宁洁丽“大家都在玩……我们是把这个世界看成了乱玩一世的世界。”王朔干脆创造了一个顽主和痞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违禁和随俗更是家常便饭。当然,如果仅是小说中的人物乱玩一世那还没有什么,只要创作者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进行审美化的观照,读者是不会把作者也当作顽主的;问题是小说的叙述者和作者都对违禁与随俗的价值观表现出积极的认同,他们宣称自己进行的就是经验化写作,言说的就是自己,“我是流氓,我怕谁?”人家倒有点大丈夫做事敢作敢当的气势,他人也就不必为之遮遮掩掩了。
从创作走向游戏。传统文学总是把创作看作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当然,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未免自视太高,但视为一种有益世道人心或助人怡情养性的工作者却是大有人在。正因如此,有人提出创作就要深入生活,就要拷问自我,就要“放血”(当然是放自己的血)。文学当然需要虚构,但虚构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要遵循生活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情感的逻辑、心理的逻辑等等。在泛先锋文学家们看来,上述创作观念真是太陈旧太迂腐了,他们既以颠覆价值、随俗而变为能事,就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要遵守。当把爱情最终还原为性的时候,他们也最终把文学还原为商品。是商品,就要寻找买点,就要满足大众窥秘、猎奇、追求感官刺激等游戏娱乐的需要。因此没有什么创作,只有写作;作家也不是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不过是商品制造者,是码字的,(注:这是王朔的高论。)写作只不过是为了“换盐吃”(注:在一次莫言与某高校学生的对话中,有一位女生问莫言,你妻子是否也看你写的《丰乳肥臀》之类小说,莫言答我妻子从来就不看文艺作品;又问你为何写作,答“换盐吃”。)。于是写作也就变成了一种与大众阅读同歌共舞的游戏。虚构更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沉重,他们不少人公开声明,写作就是造假、撒谎,“艺术达到最了不起的境界是要具有异常的复杂性和迷惑性”——纳博科夫的这句话成了他们最常引用的理论根据;因此,他们讲究的是局部逻辑、细节逻辑但整体可以不逻辑、大势可以不逻辑。所谓局部逻辑,就是在经验化写作现在化写作的旗号下,把个人的生活经验或一些社会资讯不经审美转化而直接涌入作品。
游戏化写作的基本内容就是游戏人生、展览欲望。韩东的小说《三人行》就是典型的游戏之作,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游戏:三个诗人在1993年春节前买了几把玩具手枪,于是就在大街上、客厅里对熟悉的朋友乱放一通,朋友们当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除夕之夜,他们在阳台上大放鞭炮并拔枪齐射,结果吓死了一匹孤独的猫。诗人们有时也颇有君子风度,不过那是在准备嫖妓的时候。“‘是鸡?那就搞一把呀。’他说,于是小夏和东平在厕所里第一轮的谦让开始了。‘你来你来,你老大,孔融还知道让梨呢。’‘你来你来,你年轻,比起老头来更需要。’”他们当然也谈诗,但又“总是用女人的乳房或臀部或大腿结束一场有关文学的谈话。”也有人说韩东等人的小说充满“伤皮肉的精神洪流”,但在《三人行》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孩子撒娇式的恶作剧,一种“迷失在开心馆里”的狂欢,实在没有“伤皮肉”的痛苦或精神洪流。
游戏化写作的主要手法是复制与拚贴。所谓复制主要是指把个人生活经验或一些社会资讯不经审美转化而直接涌入作品,不少新女性作家提出的“私人空间”、“躯体写作”,不少晚生代作家提出的“现在化写作”,实际上都意味着对复制的不同阐释。个人的生活经验总是有限的,而写作却要不断地进行,所以泛先锋小说家的作品都已普遍存在着重复的现象,经验重复,情节重复,感觉重复,语言重复,长篇小说成了以前短篇小说的集合或连缀。所谓拚贴,是指将各种感觉的碎片、经验的碎片很随意地组装在作品之中,并不注意加以剪裁。这样做并非都是由于幼稚,很大程度上倒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因为在虚无哲学中本来就更多地看到的是世界的平面化和主体的零散化的一面。
最后,我还要指出,泛先锋写作中的虚无主义的精神旨趣并非仅有消极意义,它的积极意义起码有二:一是对理性主义、乐观主义世界观起到一种互补与消毒作用。二是它以否定的方式对人性的肯定,它的玩世不恭中也蕴含着对戮害人性的东西的抗议。但总体看来,它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对社会及人类精神的腐蚀作用恐怕也是不能轻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