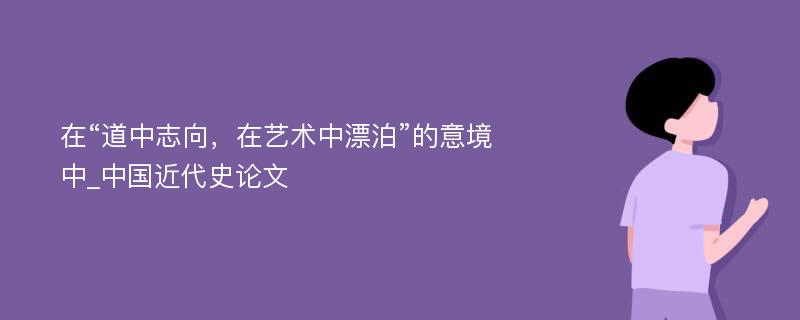
在“志於道,游於艺”的意境中品史入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境论文,志於道论文,游於艺论文,中品史入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5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克罗托关于C[,60]分子结构模型的论文——一个完美、对称的球碳学说诞生了。原来,打开克罗托灵感大门的竟是一个意外的玄想——蒙特利尔万国博览会的美国馆——外形犹如大球的穹隆建筑。奇异的玄想和严谨的实验,成就了伟大的科学发现,克罗托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其实,早在15年前日本科学家大泽映二就提出了相似的预言,但却由于缺乏克罗托般的玄想,因而也就不无遗憾地品尝了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味道!科学史上,玄想启迪重大科学成果的例子屡见不鲜。奇怪的是,在历史教育界,却有一种迂腐的声音:历史是严谨的科学,不能有任何想象的成分。在此我想借用钱钟书先生这位“圈外人”的话,以引起大家的深思:“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事局中,潜心腔内。”[1]
历史:充满玄想的人类往事
言及玄想,人们往往与浪漫、虚构、空想相联系。实际上,玄想既可以是艺术家、诗人、作家的思维特征,也可以是历史教师在传授历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思维活动。
表面上看,验证历史事实是否真实,只需要严谨的推理和缜密的考据就可以了。其实不然,这里需要诗人般的灵感,因为了解人生惟有用人生的体验,而人生的体验得之于灵感。历史学家从原始人一齿一骨的发现,便要据此推出早期人类、时代和社会,这样的历史考据,虽然研索于小处,却需要着眼于大处。着眼于大处,就是抬头玄想,若没有了玄想力,历史就止于浮浅的传说了。历史不是“白痴的呆像”“石膏的美人”。例如李鸿章的一生,就是一首悲怆苍凉的诗歌,一出曲折抑扬的人生剧。让学生写关于李鸿章的评论文章,如果不把自己放入李鸿章的境遇中去体验他——“玄想”,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也许可以改头换面,放到张之洞或者蔡元培身上。我很欣赏一位学生的以“黑夜里的黯淡星光——我眼中的李鸿章”为题的小论文,下面呈现的就是其中的几则精彩片段:
19世纪末的清廷就似最浓的黑夜,李鸿章这位集功过荣辱于一身的老人,给黑夜带来一缕星光,无奈黑夜的浓重终究“黯淡”了这缕星光。正如李鸿章的“政敌”维新派梁启超所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从当年踌躇满志地登场到在辱骂声中黯然退场,是时势造就了李鸿章的“功”与“过”。
……
李鸿章,毕竟不是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他终究只是被清廷支配的一颗棋子,在不可挽回的颓势中,用单薄的脊梁撑起祖国最后一点尊严,不得不承受世人的鄙薄的目光,郁郁而终。然而我们也无法忽略他的卓识与才干,在他的阶级立场上,他以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处于被动中的祖国创造了一线主动的生机,尽管失败,也是一次可贵的尝试。
如果李鸿章的一生是一道试题,那它必定也拥有精彩,也不乏创造力的解答过程,遗憾的是,在解答之初,就定下了错误的命题……这一切的“是”或“非”,终离不开“时代”,这位造就英雄抑或败者的创造之主。李鸿章,他是划过黑暗的一道星光,无奈的是,有些“黯淡”。
历史的玄想立足于历史的真实;真实的历史需要玄想使之丰满。玄想常常使人在冥思苦想后产生奇异的灵动;而玄想的灵动又需要严密的理性证实。实验主义还给了胡适“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的方法。正如胡适所说:“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2]关于历史的玄想,在史学家怀特的论述中称之为“想象”。史学家在为了表现历史而预构历史领域时,预构是一种想象的行为;史学家在运用比喻描绘一幅由存在着辩证张力的不同要素构成的一致性图画时,比喻中包括了想象的色彩;史学家在为读者展示过去时,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那种他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因此,历史与想象须臾不可分离,它总是想象的创造,如果我们仍然主张历史必须以真实为其根本特征,那么真实决不是与实在的吻合,而是指想象恰当地构造了一种心理上的历史性存在,使人们认为它是真实的。[3]无疑,对于历史教育来说,最幽玄、最抽象、最难以把握,乃至最不可捉摸的是历史的“灵境”。而这种“灵境”的破译,是需要带有意向性的玄想的,因为“灵境”本身并不能自我说明或自我展示,故此,没有玄想,“灵境”会变得索然无味。
历史:道艺交融的心灵感悟
历史丰富多彩,问题是我们如何体现这种多彩的历史意蕴,让那并不如烟的历史背影更加清晰、感人,并行云流水地呈现给我们的学生;如何运用理论之光照射历史幽暗的殿堂,在今天的角度和高度“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并把它游刃有余地表达出来,让我们的学生体悟历史的神韵。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历史教师,除了要有科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而外,还需要有一点文学艺术的素养。
第一是要有一点个性。从中外史学史来看,标志着伟大史学家独特成就的是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泯灭了个性,也就丧失了作为史学家的自我。有了个性,不等于有了深度,但欲求深度,必须先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古代的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以及近代以来的梁启超、王国维等,其显明的个性自不待言。翻阅西方古典时代的那些有成就的史学家的著作,便可见其个性化的语言功力。古希腊历史大师希罗多德行文严谨,又时有诗人的情怀,因而他的作品对读者有着强烈的召唤力;古希腊另一位史学大师修昔底德的文笔虽然缺少了希罗多德史著的优雅,但却从容自然,人们很容易跟着他娓娓道来的故事,进入逆行的时空隧道。古代罗马史学家李维的文笔秀丽奇绚、细腻滋润,塔西佗叙事的含蓄凝练、言简意赅,都让人难以忘怀。历史教育何尝不是如此?北京已故特级教师时宗本、上海著名特级教师孔繁刚等大师的课,为什么有如此的穿透性和感染力呢?依我看,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课堂个性风格和富于深刻性、情感性和启示性的表达功力。
第二是要有一点激情。历史教师不应拒斥诗人对历史的感受,而应向诗人伸出感应之手。真正有分量、有力度的激情,乃是深刻久久积蓄后的爆发,而不是情绪肆无忌惮地溢出。事实上,古往今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已无数次表现过自己的激情,他们的激情往往不似诗人那样炽热如火,但却用深沉的目光表达了内心剧烈的起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艰苦的日子里,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的结尾,充满激情地呼唤道:“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底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底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赫一些,也许有的暗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底祖先,曾经为民族自由而奋斗,为民族发展而能力,乃至为民族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国民族的儿女!”[4]看到这类语言,还会怀疑历史的实在可以唱出最厚重的激情吗?对于历史教师而言,思想与激情同样重要。只因有了思想,有了激情,便有了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产生的痛苦体验和茫然感受,也产生了创造的锐力,并诞生出深刻。没有思想或者缺乏激情的历史教师,其课堂必然会缺少感染力。
第三是要有一点体悟。历史消失的是时间,永不消失的是后人对千秋功业的缅怀。在这种缅怀中,有运筹帷幄的大智大勇,辚轹百代的玉想琼思,解颐醒世的妙喻珠联。我经常喜欢说,能不能准确地表达历史,往往不在于你的概念是否科学,也不在于你的解释是否到位,甚至不在于你的思考是否周详,有时候恰恰在于你是否心领神会地理解了古人的心境,破解了古人的忧伤。历史中有许多具体的细节,细节需要体悟,否则就没有历史的血肉,也会窒息思想的释放。孔繁刚老师近年来与我一起帮助几位年轻教师设计公开课时,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历史课不能没有细节!但是,细节的描述需要点诗人的情怀。诗人眼中的历史似乎不同于历史教师眼中的历史。但是,诗人比教师更为看重对人生的体悟,更加注重形象化的表达,也更加强调自我情绪的投入。诗人看待历史的眼光似乎是稚嫩的。纵使“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的咏诗名句,仿佛也远不如教师从历史“趋势”、国家“兴亡”等分析来得深刻。然而,这不正是诗人的独到之处吗?通过二乔被锁在铜雀宫中的联想,还有谁能怀疑历史上战争的毁灭性力量呢?有谁能否认“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对人生、历史的深深叹息?有谁能否认“百年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来,今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火”“秦宫汉阙,都作了衰草牛羊野。不凭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晋耶?”中浸透的那种融个人感受、历史纵阔于一体的惆怅与悲凉?
第四是要有一点文采。历史是故去的老人。假如我们在课堂上再现历史的时候,抓不住这个“历史老人”的那些独有的和内在的个性特征和明显的外在形态,则必然陷入公式化、呆板化和单一化的境地。实际上,在我们的历史教学中这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几乎麻木了学生的中枢神经,也使历史教师的创作欲望、创作习惯和创作水准在不经意之间慢性弱化,以至于历史教学缺乏应有的语言的美感和深厚的史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历史课的地位与其说是诸多客观因素所致,毋宁说是被我们自己过于教条化、随意化和冷漠化的教学所葬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课堂教学中历史教师对于讲授语言、板书语言、问题语言的雕琢是何等的重要!值得注意并强调的是,历史表达的色彩,决不单单是一个语言问题,它反映着一个人的史学见解、教育理念、教学智慧和综合素养。它是教师思想的实现形式、逻辑的展现方式和创作的呈现范式。它是培养学生学习、认识历史的借鉴工具和思维蓝本;是引导学生表达、阐述历史的案例典范和选择方案;是激发学生钟情、热爱历史的灵动纽带和情感桥梁。在约而不疏、赡而不芜、纵横捭阖、沉缄深邃的讲授中,学生所获得的绝不仅仅是历史知识本身,还有对历史学习的热情、思维质量的跃升,以及爱屋及乌所带来的对于我们这些劳动者的钦佩与爱戴。
历史:情入琴丝的理性滋养
陈寅恪先生的严谨、博学、理智和见解自不待言,有意思的是,在谈及认识历史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了解之同情”。史家“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塑之眼光及精神……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表一种之同情”。[5]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必须运用经典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没有理论指导的历史学习,必然没有石破天惊的思想火花;同样,没有科学方法引领的历史学习,也必然是漏洞百出和难以服人的堆砌。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经典理论却无能为力,科学方法也寸步难行。因为历史是一门关于“人”“人类”“人类社会”的学问。所以简单的理论套用和机械的方法推演,并不一定能获得历史内性、内在、内藏的智识,相反却往往使历史公式化、教条化。我们经常在课堂上听到一些似有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的“醒世恒言”。例如,讲到婚姻变化根源,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讲到文字产生的原因,得出的结论亦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讲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文化、民族国家……产生、变化和发展的原因,无一不冠之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鲜活的历史,就这样被这些通性、通则、通发、通识糟蹋得苍白无味,哪里还有些许历史的意蕴!
有学者曾经提出,对待历史,只能透视而不能分析。分析是科学家的技巧,透视则是艺术家的手艺。历史学家需要借助于艺术的方法,通过“感情移入”,才能获得一个真正的历史。因为,“历史所能给予人们的不是报告录而是一种‘唤起作用’。它显示于人们的是人生含蕴的一种放射性,错综复杂,纯然成为一种超机的发展,只能体味,只能感觉,只能‘感情移入’的将自己活在对象之中,在对象中发现自己,或者是将对象融合在自己的体中,再由自己的体内去认识对象。”[6]历史的意韵则是在求真求实的前提下,史家和历史教师通过心灵的体验、对于历史回声感悟之后的心灵释放,历史的意韵体现于他们灵魂跃动的轨迹。
谈到历史学的艺术性,很多人会以为是史书或者讲授者仅仅在文字或语言的修饰,要讲求艺术效果,但是,张荫麟先生指出:“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7]而姜蕴刚则更是在《历史艺术论》中指出,古来“有价值的历史作品”,其内容及形式都是彻底地艺术化了的,至于“生动感人、叙述明亮”的文笔,只是彻底贯彻史学艺术论后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远不是最终目的。[8]对此,英国史学理论大家柯林武德也有同样的精辟论述,他认为,历史学的艺术性不仅是“修饰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9]
在我看来,在历史教育中,由于大胆想象而出现问题,远比没有主体意识而产生的、缺乏内心感受的历史说教更有价值。乌托邦把幻想和空想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又把其最终的实现规定为静止和永恒,这是对世界复杂性的一种总体性的简化,是对可能显现与实在显现的完全等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如此,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得里亚的“基督城”也是如此。我要说,乌托邦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以后也还会出现的最美丽的错误。意向的漏洞百出,或许比那些人云亦云的麻木和从众噪音珍贵得多!意向的汹涌,不是妄语肆意和形神离散,而是理性的升腾,常常孕育着最不平凡的机理!意向的沉默,不是思维迟滞和精神淡漠,而是激情的冷冻,往往包含着最不平静的感怀!
在历史教育的园地,没有什么被奉为永恒圭臬的法度,只有在一望无垠的荒漠上永恒驰骋的活力!中国古人讥笑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我们只有追求真理,才不会遭受类似的讥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