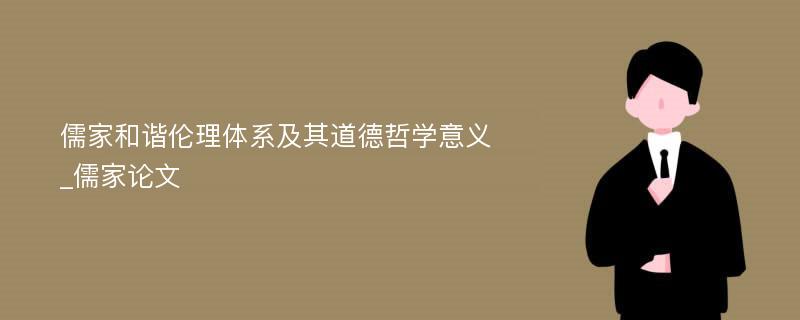
儒家和谐伦理体系及其道德哲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伦理论文,道德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7)06—0004—07
儒家在历史上进行的最成功的努力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和谐道德哲学体系与和谐伦理精神体系。它在体系上所建构的道德哲学与伦理精神的“和谐”,用现代哲学的话语表述就是:同一性或辩证同一性。这种体系性的和谐或同一性具体表现为一个有机的结构系统:道德哲学体系、伦理精神体系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伦理世界的和谐;道德世界的和谐;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和谐。
一、特殊的文明路径与中国社会的基本课题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文化选择中,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主流和正宗,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出色地探讨和解决了中国社会、中国文明的基本课题。
如果说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四次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转型①,那么,最具决定意义、对各民族发展产生最深刻影响的社会转型,便是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即奴隶社会的转型。在这个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社会转型中,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如何对待在迄今为止最为漫长的历史发展即整个原始社会中所形成的氏族社会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它的社会体制。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民族和西方文明的选择是:通过一次又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如梭伦改革等,彻底挣断原有的氏族纽带,建立起以家国相分、以国为本的城邦制度。而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特殊路径,则是通过“西周维新”,探索了一条“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道路。这两条不同社会文明道路的选择,对日后中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基因意义的决定性影响。这里无意也无须对这两种历史选择和这两条文明道路进行评价,最为直白的事实是:“西周维新”所开辟的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路径,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开发了人类在最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积淀的文化资源和文明财富,中华文明日后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辉煌,已经对祖先所进行的这一创造性选择的历史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作了具有解释力的回答。当然这种凸显和偏重历史连续性的选择也内含着某种保守性。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应当特别加以关注的是:“西周维新”只是从体制上进行了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路径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决策,文化上、理论上的努力并没有完成甚至没有进行,但是,这一任务必须要完成。于是,到春秋时期,与特定的社会背景相结合,便出现了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事实上存在着两条线。明线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文化表现和文化争鸣;暗线是继续完成“西周维新”所没有完成的文化任务。所以,百家争鸣的基本主题之一,就是对家国一体文明、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的论争。其中,伦理是最为核心的理论问题之一。因为,家国一体的文明形态,本质上是伦理—政治一体的形态,由家及国,就是由伦理到政治,理由很简单,家庭是自然的和直接的伦理实体,家庭伦理精神是自然伦理精神。家国一体的社会体制和文明形态要解决的基本难题就是如何由伦理过渡到政治,如何实现伦理政治的一体,伦理政治一体就是文化与理论上的家国一体。这就可以解释,春秋虽然百家,儒、道、墨、法四家却是基本的结构。理由很简单也很清楚,这四家的文化理路分别诠释了家国一体社会体制所内蕴的几种可能的逻辑路向。其中,儒家代表的是由家及国的路向,提出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思路;法家则反其道,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由国及家的路向,即由政治到伦理的思路,故强调法治;墨家则着眼于家国之间的社会,提出“兼爱”、“尚同”的主张;而道家的独特贡献之一是为社会转型和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的安身立命提供人生的大智慧。儒、道、墨、法提供了家国一体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下三种可能的文化方案与理论主张,同时也提供了在动荡社会中安身立命的哲学智慧。
在百家争鸣和历史选择中,儒家之所以成为主流,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提出的文化主张和理论体系与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路径和社会结构相一致,从文化上和理论上出色地解决了中国社会的基本课题。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儒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薪火相传,不断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在先秦,孟子对儒家的贡献,不只是继承和阐发了孔子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在继承中发展创新,由此才形成孔孟儒家学派。到秦汉之际的《礼记》,日后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便正式形成,由此儒家学说便形成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四书”之中,《论语》提出儒家学说的某些奠基性和原创性的思想;《孟子》对这些思想加以发挥和发展,尤其形成“五伦”、“四德”的伦理道德体系;《大学》则将复杂的、并不系统的孔孟学说凝练为“三纲八目”的经典理论;《中庸》将儒家学说提升到一个“极高明”的形而上学境界。由此之后,儒家“孔孟之道”也是在不断的创新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活力。
总之,儒家伦理以和谐或调和为取向(即所谓“维新”)而不是以冲突或紧张为取向,出色地解决了人类走向文明进程中“家”与“国”这个最基本的难题和课题,建构了道德哲学体系、伦理精神体系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体系之间的和谐。儒家提出和建立了一个与中国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和文明路径相适应、相一致的高度完备并富有创造性活力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是它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伦理的主流与正宗的根本原因。
二、“伦理世界”的和谐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伦理世界由三个要素构成:伦理实体——家庭与民族;伦理规律——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伦理原素——男人与女人。而儒家所设计的伦理世界,不仅在要素方面与黑格尔的发现完全吻合,而且它的创造性贡献,就是依循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原理,出色地解决了这三对要素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伦理世界“预定的和谐”。
1.儒家的伦理世界:“五伦”世界
儒家伦理世界的民族特质,如果用一个概念概括,就是“五伦世界”。在《论语》中,孔子经验地指出了包括五伦在内的诸多伦理关系,也试图发现并揭示这些关系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最终没有在哲学的层面完成它。孟子最具重大意义的伦理发现和对孔子理论最重要的创新发展在于,将所有的伦理关系及其内在原理范型化为五种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五伦之中,家与国,或家庭与国家,是两个基本的伦理实体。天伦或天道是神的规律,即家庭伦理关系或人作为家庭成员而行动的规律;人伦或人道是人的规律,即人作为国家公民而行动的规律;伦理世界的两大规律的中国式话语,就是天伦与人伦。而夫妇作为男女关系的范型,则相对于黑格尔伦理世界中的“男人和女人”。
五伦世界对家国一体、由家及国文明形态的创造性体现,突出表现为“人伦本于天伦”的伦理世界的建构原理。五伦之中,父子、兄弟是天伦;君臣、朋友是人伦;夫妇则介于天人之间。君臣比父子,朋友比兄弟,一切男女关系则比于夫妇。“由家及国”的伦理原理是:一切人伦关系都以天伦关系即家庭伦理关系为理想模型,由此最终便可达到“天下一家”。父子—君臣是伦理世界的纵轴;兄弟—朋友是伦理世界的横轴;夫妇—男女则是伦理世界的第三维。由此,一个立体性的伦理世界,准确地说,伦理世界的立体性原型,或自在而自然的伦理世界便屹立于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之中。“人伦本于天伦而立”,就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的伦理世界原理与道德形而上学表达,是五伦世界,即中华民族的伦理世界的最根本的原理与法则。
2.人与伦的关系:伦理世界的基本问题
伦理的真义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伦理中的基本关系是“人”与“伦”的关系。在这里,“普遍物”虽然包括整体或集体,但并不止于此,而且整体或集体之所以是实体,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是普遍物。“伦”,就是伦理世界中的普遍物,甚至可以说,就是道德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物。在这个意义上,“伦”既指伦理实体,它的基本形态是家庭与民族或家庭与国家;更指这些伦理实体作为普遍物的本质以及它们在时间之流中所形成的整个的生命。所以,在家庭伦理实体中,伦理关系或所谓天伦关系,并不只是乃至并不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不是他们之间爱的关系,而是单个的人作为家庭这个实体的成员与他所处的整个的“伦”的关系——这个“伦”在时间上表现为一个生命之流,一个世代更迭、延绵不断的生命之流;在空间上表现为一个由神的规律而构成的血缘共同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伦理关系,实际上是人与整个伦理秩序、人与份位的关系。而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具有伦理性,乃是因为集体是作为个体公共本质的普遍物,如果集体不具有或者说不实质性地具有这个本性,那么,个体与集体之间就不是伦理关系,而只是经济关系或政治关系。同理,整体与整体、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具有伦理性,乃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单一物与普遍物的关系,一个实体是另一个实体的普遍物。在伦理世界中,家庭是它的成员的普遍物,但民族又是家庭的普遍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说,如果一个人只属于家庭,而不属于民族,那么,他只是一个非现实的阴影。
3.伦理世界中的两种伦理原素及其伦理性质
正如韦伯所说,儒家伦理的特点,是一种“乐观的紧张”。在伦理世界的基本关系中,以君臣关系为代表的上下之间的关系可能依父子关系的原型而“乐观”地发展,朋友关系也可以向着兄弟关系尽情地延伸,唯独对男女关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与紧张。因为,依据“人伦本于天伦”的原理,男女关系以夫妇关系为原型和归宿,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乱伦。而在伦理世界的设计中,男女、夫妇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天伦,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人伦,它既具有生物性自然关系的性质,又具有化育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的重任,因而才需要既警惕又极其严肃地对待它。夫妇关系在性质上介于天伦和人伦之间,连接着天伦和人伦,使天伦与人伦、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在运作中造就有机的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又是伦理实体、伦理世界生生不息的源泉。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将男人和女人当作伦理世界的两个“原素”。
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原素”意义在于他们分别代表伦理世界的两种不同的伦理性格或伦理性质。与其说他们是伦理世界的两个原素,不如说他们是伦理世界所需要的两种伦理性格的人格化。这两种伦理性格是:女人是“家庭的守护神”;男人则是一种消解家庭的自我实体性,连接家庭与社会,推动家庭成员成为社会公民的力量。正因为这两种伦理性格及其人格化力量的存在,作为伦理世界的基本伦理实体——家庭才得以巩固而不至为国家所颠覆;同时伦理世界也才不至于囿于家庭这个自然伦理实体,而是不断为更大的伦理实体即民族国家提供生生不息的活力源泉。我们每每批评儒家伦理在男女关系上的保守性,尤其是让妇女局限于甚至困于家庭之内,殊不知,在两千多年后,另一位哲学家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却做出了同样的伦理发现和伦理设计。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必须同时进行一种反思:我们是否缺少哲学的素养?用黑格尔批评康德的话说,我们是否缺乏辩证法?因为,在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和道德形而上学视野中,男女所代表的是伦理世界具有原素意义的两种基本的“伦理性格”。这两种伦理性格也许是思辨的结果,但对伦理世界和现实的伦理生活来说,却具有真理性的意义。
总之,儒家所设计的伦理世界,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五伦”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两个基本伦理实体之间的关系是以家族为本位,由家族(或家庭)走向民族;两大伦理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人伦本于天伦”,人的规律源于神的规律;两大伦理性格之间的关系是“乐观的紧张”。由此,造就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伦理世界的“无限整体”与辩证和谐。
三、“道德世界”的和谐
儒家的道德世界观的特质是基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确切地说,是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的道德自我意识或道德自觉;儒家所努力建构的道德世界是一个使“道德规律成为自然规律”的世界。
1.儒家的道德自我意识
儒家将全部道德自我意识乃至主体的道德世界建立在“人之异于禽兽者”的道德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基础上。孟子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他将人之异于或贵于禽兽的方面认作人性,是大体;而人之同于禽兽的自然本能,则是小体。大体与小体都与生俱来,因而人既有成圣成贤的可能,也有沦为禽兽的危险。“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个体要上升为实体并成为道德的主体,关键在于“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这种立足于性善认同的人性论,与西方以性恶论为基础建立形而上学的道德世界和道德自我意识正相反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道德自我意识以善作为人性的本质,因而道德的全部任务,就是如何向人的这种公共本质和处于彼岸世界的实体回归。道德本质上就是向人的善之本性回归的现实运动。“人皆可为尧舜”,之所以不能为尧舜,主要原因是为“人欲所蔽”或“气禀所拘”,“大体”为“小体”所遮蔽,人便不能向自己的普遍物即善的公共本性或公共本质回归。“大人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可以为大人,而不肯为大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对人的公共本质的这种自我意识,一方面使道德的完成成为人内在的良知良能,“我欲仁斯仁至矣”;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人迷失自己的公共本质的可能性与危险性。不过,儒家伦理对这种危险性的警惕和紧张同样采取“乐观”的态度,它相信既然人性的迷失只是“物欲所蔽”,或者如佛家所说是“客尘所蔽”而不是“客尘所染”,因而只需要“去蔽”,便可以达到道德的自觉与他觉,而不需要经过那种艰苦的赎罪得救的过程。这种原理与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所以需要道德,是因为人不是神;人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人不是禽兽。
2.道德世界的自在:“四心”
性与心的关系是什么?虽然儒家伦理对心性关系有着复杂的诠释系统,但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话语表述,“性”是人的实体的自在形态;“心”是人的实体的自为形态。人性的内涵是什么?孟子概括为“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
无须借助哲学思辨,直觉便可发现,儒家“四心”结构中,四分之三是情感,只有四分之一是理性或与理性相关。它是一种“情感+理性”,以情感为主体和统摄的、情理一体的人性结构。这种人性结构与西方由亚里士多德开辟的“理性+意志”,以理性为主体和统摄的道德传统正相比照。“由家及国”的内在原理是以家为国的本位,即所谓家族本位。而家的绝对逻辑是情感逻辑。家族本位在人性结构中必然要求情感本位。但家庭伦理关系,既是一种实体性关系,又是一种要求以严格的伦理区分为内在规定的关系,于是,在人性结构中就需要有一种对人伦关系进行辨识的理性要求和理性能力;而由家庭长幼之序扩展为国家生活中的上下等级,更需要严格而发达的宗法理性。所以情虽然是由家及国文明路向下人性的主导结构,但理性结构也是一种必然要求和必要结构。不过,这种“情感+理性”的结构,与西方“理性+意志”的结构,在道德功能上则是相通的。正如黑格尔所揭示的那样,人性和德性中必须具备两种能力或品质:一是思维能力,一是冲动能力。前者是意识的品质,后者是意志的品质。“情感+理性”的结构同样具有这两种能力和品质。因为情感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意志,即主观形态的意志,具有行为的品质。与意志的行为品质不同的是,它更加诉诸人性的直接性,所谓“情不自禁”,在这种结构中,道德行为往往是一种“身不由己”的人性反射与人性反应。“四心”结构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背景下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性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所谓“良知”、“良能”的结构。它超越了理性的中介,诉诸人性的直接性,具有更为浓郁的“自然”特征和人性价值。
3.道德世界的自为:“四德”
如果说“四心”是儒家道德世界的自在,那么,“四德”便是它的道德世界的自为。“四德”根源于“四心”并且是其直接表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不过,仁义礼智的“四德”,只是内在于“四心”之中,在“四心”之中,只是有“四德”的萌芽,“四德”的真正形成,还有待于人们“扩而充之”。仁义礼智,就是儒家所设计的德性之实体。“四德”之中,仁既是起点,是根源,也是统摄,所谓“仁包五常”。仁何以成为道德世界之基?因为仁的本质是爱人。而爱则体现了伦理的本性,是伦理实体形成的必要条件。伦理要成为一个实体,就必须扬弃个体抽象的独立性,使个体上升为实体。扬弃个体抽象独立的自然形式就是爱,但是仁爱与博爱又存在根本的区别。仁爱最大的中国特色之处,就是差爱与泛爱的结合,所谓“爱有差等”,“亲亲仁民”。仁爱有爱的一般本质,此即“泛爱”,但它的具体性又表现为“差爱”。差爱在家庭内部表现为“亲亲有术”,在社会中表现为“爱人有等”,更重要的是,仁爱的顺序是由亲亲到仁民,由家族血缘之爱推扩到社会之爱。亲亲是仁民之基本之本。这就是“由家及国”的爱的逻辑。正因为如此,仁必然提出义的要求。“仁”是爱人,“义”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爱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礼”既是具体的道德准则,便是如何知仁行义的规定。“礼者,经天地,理人伦。”(《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识,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仁是爱人,义是如何爱人,而礼则对爱作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唯有如此,爱人才符合伦理。“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也。”(《孟子·离娄上》)礼的功能,是对仁义进行节文,使之无过无不及。焦循注曰:“太过则失其节,故节之;太质则无礼敬之容,故文之。”(焦循:《孟子正义》)有了“礼”,人们在道德上便可以登堂入室了。“智”是“四德”中的特殊结构。“智之实,知其二者弗去是也。”智的本务,是知仁行义,后来宋明理学又将它解释为“仁与义殊”,即知晓仁与义的区别,“必仁且智”,以防止“爱而不别”。这里的智,不是一般的理智,而是“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良知,是基于是非之心的道德直觉,而且是一种具有直接的行为能力,即良知与良能一体的道德直觉。这样,“居仁由义”,“礼门义路”,“必仁且智”,儒家伦理便建立起了一个从家庭伦常之序出发的道德精神体系。仁义礼智,就是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体现由家及国文明路向的“中国四德”。
性善—“四心”—“四德”,便构成儒家伦理所设计的道德世界,它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文明形态下中国民族的道德世界观或道德自我意识,它所达致的是“道德规律成为自然规律”的道德世界的辩证和谐。
四、伦理精神的同一性
伦理世界、道德世界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伦理精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建构。伦理精神成为真正的自我,还必须完成另一个任务:建构自身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既包括伦理世界的同一性、道德世界的同一性,更包括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同一性。这三个同一性,就是伦理精神的同一性,或伦理精神“预定的和谐”。
伦理精神同一性的建构,在形而上学的层面面临的最大难题有三个:(1)伦理实体如何成为“整个的个体”;(2)个体如何上升为实体,并成为道德的主体;(3)伦理实体如何成为道德的主体。儒家伦理比较卓越地解决了前两个问题,对第三个问题的探索却陷入了困境。
1.伦理世界的同一性
伦理世界的同一性首先表现为两大伦理实体之间的同一性。这两大伦理实体在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中表述为家庭与民族,在中国道德哲学体系尤其是儒家道德体系中表述为家与国。实际上,儒家哲学中“国”的概念,并不是后来或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民族概念。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民族作为位居于家庭之上、在人的反思中存在并体现为精神的最为重要的伦理实体,但是,他又认为,民族作为伦理实体只是自在的形态,它的自为形态,或者说它作为“整个的个体”的形态就是政府。政府就是民族伦理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的自为形态,它是能动的,其本质是它的普遍性与公共性。他这里显然有美化政府的倾向,因为政府作为民族的“整个个体”,只是它的理想形态,并不是现实形态。政府“应是”民族的“整个的个体”,但在现实中并不“就是”。将政府当作民族的“整个的个体”,具有“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保守的以及政治乌托邦的色彩。儒家对伦理实体的设计具有不同于西方道德哲学的原理。对伦理实体的同一性及其同一体,儒家用一个特殊的概念表述:天下。在儒家的伦理世界中,家是阴极,国是阳极,天下则是处于二者之上的太极。儒家道德哲学中的“国”,与政府相关但并没有将政府当作民族的“整个的个体”,“国”毋宁说是民族的共同体,而只有道德的政府才是这个共同体的“整个的个体”,或者说才是民族的自为和能动的体现。儒家维护君主制,但是在孔孟那里,也认为只有好的君主即仁君,才能作为国的象征和代表。儒家特别强调家与国之间的共通性与贯通性,其最高理想就是“天下一家”。在儒家道德哲学中,“天下”与“国”之间的区分比较精微。“天下”既可以理解为文化意义上的“国”,以与西方政治意义上的“国”相区分,又是“家”与“国”的贯通统一,因而包含了“国”。但无论如何,“天下”是“家”与“国”两大伦理实体的统一,是伦理世界的这两个最基本的伦理实体的同一体。
伦理世界内在的否定性,并不是家庭与民族这两个伦理实体的分殊,而是由此形成的两大规律或两大势力,即所谓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或天伦与人伦、天道与人道的分殊。两大势力矛盾的根源在于人的行动。家庭与民族是伦理世界的自在状态,由于构成伦理世界的原素是以男人与女人为不同伦理性格的个体,于是,个体在伦理世界中就具有两种不同的角色:家庭成员或民族公民。如果个体只属于家庭而不属于民族,那么个体只是“非现实的阴影”;但如果个体只属于民族而不属于家庭,那么个体就完全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家庭是伦理世界中最现实的存在。这种矛盾在自在状态下还只是潜在着,然而,只要一开始行动,人们势必遵循两大规律中的任何一种规律,或者作为家庭成员依循神的规律而行动;或者作为民族公民依循人的规律而行动,由此便产生两大势力之间的冲突。在儒家设计的伦理世界中,这两大势力或两大规律之间的矛盾,就是忠与孝之间的矛盾。孝是个体作为家庭成员依神的规律而行动;忠是个体作为民族公民依人的规律而行动,故忠孝难以两全,所以儒家伦理经典就将《忠经》与《孝经》分立。但是,对伦理世界来说,忠孝难以两全,又必须两全,两大伦理势力必须统一,否则伦理世界就会因陷入永劫不复的分裂而难以成为一个“无限的整体”。于是,儒家提出了“移孝作忠”和“以忠保孝”两种思路。事实上,在伦理实践中,儒家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是将两种思路互补,共同缔造伦理世界两大规律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其中,“移孝作忠”是基本的思路,这个思路是“由家及国”的要求,其中蕴涵着逻辑上的一致性与必然性。对此,孔子的推论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以忠保孝”的思路和措施是:“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移孝作忠”、“以忠保孝”,伦理世界中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就在理论上被扬弃,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行为与伦理精神“由家及国”,由家庭成员过渡到社会公民。但是,在现实中,这两大规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还是存在,在遭遇二者激烈冲突的时候,儒家伦理乃至整个中国传统伦理占主流地位的主张是:“精忠报国”。以维护国的伦理实体为最高取向。这一点与黑格尔的道德哲学思想也是相通的。黑格尔的观点是:“两种规律的任何一种,单独地都不是自在自为的,都不自足;人的规律,当其进行活动时,是从神的规律出发的。”[1]
2.道德世界的同一性
道德世界的同一性要完成的形而上学任务,是如何在道德自我意识中扬弃义务与现实、道德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义务同一现实,以道德同一自然,使个体上升为实体。
在道德世界中,个体提升为实体,首先必须扬弃自身抽象的独立性,使自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关于扬弃个体的抽象独立性的基本概念,在中西方道德哲学中是相通的,这就是“爱”。所以,伦理、道德,伦理学、道德哲学,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或者说,必须以爱为逻辑和历史出发点。但由于中西方文明形态特别是中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特质,爱作为伦理和道德的出发点,又具有迥然不同的内涵和性质。西方是以上帝为终极实体的博爱,中国是以家庭为策源地的仁爱。中国道德哲学的仁爱要解决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这种爱人之情到底如何发生?个体如何以爱扬弃自己抽象的独立性?第二个难题是:在扬弃个体抽象的独立性而走向实体的过程中,如何体现“由家及国”的要求?儒家道德哲学对道德世界的设计,用一个字解决这两个难题,这就是“推”。“推”的儒家道德哲学概念就是:“忠恕”。“忠者诚以待人,恕者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扬弃个体的抽象独立性而符合“与他人统一”的原理和要求,从积极的方面说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消极的方面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由家及国”,由家庭走向社会的路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忠恕的爱的“推己及人”中,个人既找到了“与他人统一的感觉”,个体由家庭成员过渡到社会公民,建立起了个体道德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又在道德自我意识中建立起道德世界的同一性。
道德世界与道德世界观中“由家及国”的建立道德同一性的原理,被《大学》用二十四个字高度概括,此即所谓“三纲八目”。“三纲领”中,“明明德”是个体通过“自明”向作为人的公共本质的普遍物即“明德”(光明的德性)或善性的复归。道德同一性建构的基础,首先是个体向道德实体回归的运动,“明明德”即复明光明的德性,复明光明的德性即回归人性本体或人性这个人的实体。在这里,“明”的真义是“自明”,“明明德”即个体至善,或个体向人性实体的运动。这个过程完成以后,“亲民”即是社会善。“亲民”有两种解释:“新民”、“仁民”。两种解释实为一体,仍然统一于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新民”即使人民去其旧染,日新又新,而这个新民的过程及其本性,是要求从天下一定的情怀出发,视中国如一家,天下如一人,由家族之爱,推扩到天下。人身上具有仁义礼智四德之端,关键在于扩而充之。“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敬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在家国一体的文明中,亲民新民本为一体。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就是“至善”的境界。至善的境界,就是道德世界与伦理世界统一的境界,这个境界用儒家道德哲学的话语表述,就是“安伦尽份”。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子止于孝”,是五伦与十德的统一,或者说,是伦理与道德的统一。“八条目”是道德实现个体向实体运动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个系统由两个部分组成:修身之前是内圣的功夫;修身之后,是外王的功效。内圣与外王一体贯通,其中枢就是修身,故道德之完成“壹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家国一体背景下伦理与政治贯通在道德世界中的体现,是家国一体的道德贯通。第二,在“外王”的环节,身、家、国、天下贯通。在这里,不仅家国一体,而且身、家、国、天下四位一体,是家国一体的伦理贯通。修身方能齐家,齐家方能治国,治国方能平天下,在道德贯通的背后,是伦理的贯通,“外王”就是道德贯通与伦理贯通的统一。“大学之道”即“大人之道”,即以家国一体、由家及国为文化原理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贯通之道。
3.伦理世界—道德世界同一的智慧:中庸
家与国、道德与自然,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两个基本关系或基本矛盾,而个体与实体的关系则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体的基本矛盾。儒家道德哲学体系最杰出的努力之一,在于在依“由家及国”思路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最高的境界,这就是:中庸。
中庸在儒家道德哲学中是一种至高境界,它是最为恰当地处理伦理世界、道德世界矛盾的大智慧和大德性。一般人都将中庸当作一种方法,甚至当作折衷调和的方法。实际上,在儒家道德哲学中,中庸是伦理与道德尤其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根据除了上文所引孔子的感叹外,“四书”的体系本身也是说明。“四书”将中庸列于四本书之最后,并不意味着它相比之下最为次要,相反,而是因为它最难达到。在“四书”体系中,因为孔子是儒家至圣先师,《论语》当居首位,其次是亚圣之《孟子》。但《大学》、《中庸》之选择与排列,当有其另一番用意。《大学》将儒家学说概括为“三纲八目”,《中庸》则提出一个最高境界,并为之提供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庸》放在最后,乃是因为它最形而上,也因为它的境界最难达到。中西方伦理都强调中庸,亚里士多德就对中庸作过许多论述,但唯独在中国,中庸不仅是一种道德理性,而且是一种伦理精神;不仅是一种伦理精神,而且是一种伦理性格;不仅是一种伦理性格,而且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大智慧。它对儒家伦理如此重要,乃至四本经典或原典中,专有一本以中庸命名并专题讨论中庸问题。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体系中,处理伦理世界、道德世界的矛盾委实需要更大和更高的智慧。“中庸”的真谛是什么?就是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朱熹《中庸章句》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在儒家道德哲学中,“中”既是宇宙万物之本体,又是道德之本体。“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在本体的意义上,“中”就是率性,就是对自己的本性和宇宙本性的无过无不极。庸即是对中的固守。“中者天下之定理,庸者天下之达道。”中庸被推崇备至如此。因为,在家国一体的伦理世界中,过分执著于家,或者过分执著于国的伦理实体,都会导致伦理世界的非合理性,甚至它的分裂。既要以家为本,由家及国,又要使伦理精神发展到国的普遍性,以使个体不至沦落为“非现实的阴影”。在伦理世界的两大伦理实体中,儒家伦理并非要求在家与国之间寻求某种折衷,而是寻找无过无不及的黄金分割点,以家族为本位,是儒家伦理精神,也是儒家伦理世界毫不动摇的法则,这是由家及国的基本要求。在这个要求下,任何折衷调和都根本不可取,可取的只是因时因地而制宜的“义”。与此相连,作为“伦理造诣”的德,也就必定要提出中庸的要求和境界。中庸是在处理家与国、孝与忠的各种关系和矛盾时恰到好处,否则便会导致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体系的崩坏。这就是为什么儒家在道德世界的德性要求中要特别强调义与礼的缘由。
中庸,就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下,建立伦理世界的同一性、道德世界的同一性,以及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同一性,或者说建立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辩证和谐的大智慧和至高境界。
基金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05&ZD040)、东南大学“985”项目
注释:
① 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历史形态及其四次历史转型。
标签:儒家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道德论文; 文化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国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