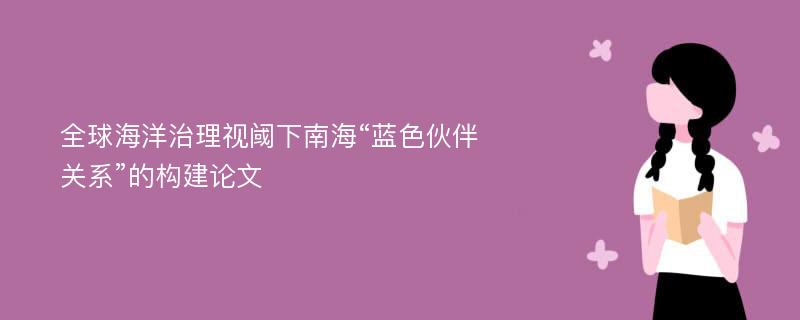
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
侯丽维,张丽娜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摘 要: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在理论上推动了新一轮国际发展合作、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上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强劲的新动力并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向度与范式。然而,在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面临着治理主体乏力、客体局限以及机制薄弱等问题。为此,必须从鼓励多领域共同推动的“蓝色”合作、培育多元化紧密互动的“伙伴”主体、保障多层级合作联动的“关系”结构等3个方面入手进行优化。
关键词: 全球海洋治理;南海;蓝色伙伴关系
2017年6月5日联合国海洋大会首日,国家海洋局(1) 2018年3月,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海洋局的职责整合,组建自然资源部,不再保留国家海洋局。 倡议的主题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促进全球海洋治理”边会在联合国总部召开,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林山青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倡议。与会各方一致认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又称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该目标共含17项,目标14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及其各项子目标,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应高度重视国际合作、缔结新型的伙伴关系——蓝色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和均衡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1]同年11月3日,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在厦门国际海洋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愿立足自身发展经验,积极与各国和国际组织在海洋领域构建开放包容、具体务实、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2]显然,蓝色伙伴关系不仅是全球海洋治理理论的热门议题,更是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是中国政府对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以新的姿态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海洋秩序变革的重要契机。本文致力于在全球海洋治理的视阈下考察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从蓝色伙伴关系的主要内涵出发,探讨其对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价值,着重分析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的建议。
一、“蓝色伙伴关系”的内涵及其对全球海洋治理的价值意蕴
从“蓝色伙伴关系”理念所包含的内容和秉持的功能来看,其在理论上推动了新一轮国际发展合作、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上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强劲的新动力并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向度与范式。
(一)“蓝色伙伴关系”的多维内涵
“蓝色伙伴关系”(blue partnership)的概念来源于“伙伴关系”,所谓“伙伴关系”,是指包括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企业在内的多元行为主体承诺一起提供资源和专业知识并承担风险,以实现共同的治理目标的一种国际合作形式。[3]当前,国内聚焦“蓝色伙伴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有学者认为蓝色伙伴关系是中国政府在全球海洋治理供给不足的现状下所提出的一种积极举措,通过联合相关国家、国际组织来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海洋治理问题。[4]还有学者指出蓝色伙伴关系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途径,应拓展与其他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合作并强化这种共识,从而推动建立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系。[5]
“蓝色伙伴关系”作为“伙伴关系”理念在海洋领域的扩展与引申,是一个含义丰富、层次分明的集合性概念,具有“开放包容、具体务实、互利共赢”的特点。首先,从来源上看,蓝色伙伴关系作为我国在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中最现实可行的海洋外交战略,其理论基础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确立的“不结盟”原则。中国愿本着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思路,与各国建立平等、开放、合作的伙伴关系,这也是对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思想理念上的继承与创新,打造更加紧密的全球伙伴关系网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其次,从性质上看,蓝色伙伴关系是我国健全海洋治理体系与加强海洋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在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坚持陆海统筹”“海洋强国”战略部署之下,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有助于全面推进“五位一体”(3) 具体指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安全、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海洋生态发展。 的海洋治理体系,也是进一步满足我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需要更高水平海洋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再次,从本质上看,蓝色伙伴关系是我国开展多层次、多主体、多领域综合互动的一种海洋合作机制。2017年9月,中国-小岛屿国家海洋部长圆桌会议在福建平潭召开,作为其会议成果的《平潭宣言》指出,中国及岛屿国家“推动宽领域、多层次的海洋合作,并致力于提升合作水平,巩固合作关系,构建基于海洋合作的‘蓝色伙伴关系’”。最后,从作用上看,蓝色伙伴关系是在全球海洋治理的感召之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海洋治理模式。作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抓手和践行路径,构建最广泛的蓝色伙伴关系旨在充分实现各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妥善处理和协调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各国之间的博弈与政策分歧,从而最大程度上增进全球海洋治理的平等互信。
(二)“蓝色伙伴关系”对全球海洋治理的价值意蕴
考察蓝色伙伴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对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物流设施设备作为物流行业的基础,必须要重视实践教学,积极的结合新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完善和创新实践教学课程,才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更好的适应未来工作岗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水平,更好的为物流行业培养优秀的人才,促进我国物流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1.探索全球海洋治理的全新范式
蓝色伙伴关系的建立旨在打造一个包容、开放的合作平台,创造一种新型的国际海洋合作模式,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增强海洋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满足中国“经略海洋”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意愿和要求,同时也满足伙伴方的发展需要,堪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紧密衔接的创新之举。一直以来,中国极力寻求应对全球性海洋问题的治理模式,[6]而蓝色伙伴关系作为对全球海洋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也是中国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客观需求和必然选择。蓝色伙伴关系倡议自2017年6月提出以来成果颇丰。同年9月,中国与来自四大洲12个岛屿国家的代表就共同构建蓝色伙伴关系达成共识。紧接着在一年时间内,中国先后与葡萄牙、欧盟和塞舌尔分别就建立蓝色伙伴关系相关事宜签署了政府间文件。这些合作硕果表明蓝色伙伴关系正从理念和愿景逐步转化为现实与行动。健全并加强蓝色伙伴机制和能力建设,不仅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全新范式和经典样板,而且为世界各国开辟了国际海洋合作的新道路,更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贡献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2.拓展全球海洋治理的蓝色空间
“蓝色伙伴关系”作为全球海洋治理深入推进的桥梁和纽带,不仅在地理空间上拓宽了我国海上国际合作的地域和范围,还进一步在合作空间上扩大了我国在不同海洋领域的纵深发展。在2017年6月19日发布的《“一带一路”海上合作设想》中,我国政府明确表示了对于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路,并强调“愿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一道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海上合作,建立积极务实的蓝色伙伴关系”。按照《“一带一路”海上合作设想》的具体内容可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建设3条连接亚洲与非洲、大洋洲、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海上“蓝色经济通道”。由此,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将延伸和遍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并通过这些经济通道的建设带动与相关国家的海洋领域合作,从而在横向上扩展了海洋合作的地域空间。同样地,在《平潭宣言》中提出“鼓励共同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各方在推动海洋治理进程中平等地表达关切,共同建立合作机制”,并强调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发展蓝色经济、保护生态环境、海洋防灾减灾、海洋技术应用等,进而在纵向上积极推动不同领域海洋治理的深入发展。
3.贡献全球海洋治理的伙伴理念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7]蓝色伙伴关系作为伙伴关系理念在海洋领域的细化与延伸,是全球海洋治理框架下的海洋特色外交战略,也是中国积极响应《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提出的“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有力举措。从加强伙伴关系的顶层设计来看,十八大报告指出“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十九大报告也强调“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这些党中央会议的整体精神为蓝色伙伴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石,更将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进入新时代,中国的伙伴关系数量进一步增加,并继续深化升级原有伙伴关系,构建起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伙伴关系网络。截止2018年底,中国已经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实现对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的全覆盖。蓝色伙伴关系网络的持续推进,既拓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对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还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注入了全新的蓝色活力、贡献了中国智慧,更为开创全球海洋治理新局面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现状及问题审视
探讨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需要充分回归南海在全球海洋治理语境下的现实面貌,通过考察南海地区海洋治理的实际状况及其现有成果,以此来深入探究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所面临的问题。
(一)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现状分析
全球海洋治理从本质来看就是一种合作——由于治理海洋问题需要采取系统的共同行动,故催生各治理主体展开相关合作。[8]南海地区海洋治理的合作硕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盟在海洋治理上已有的合作经验,二是中国与东盟或东南亚部分国家在海洋治理上已有的合作实践。
作为南海地区海洋治理的主导力量,东盟的海洋治理观与中国所倡导的蓝色伙伴关系在海洋发展的核心理念上是一致的,强调多层级的海洋合作与伙伴关系,旨在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这一点从东盟出台的各类官方文件可以看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2025》指出“养护、开发和可持续管理海洋,并推动在此方面的海洋合作,不断努力实现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加强全球和区域伙伴关系,支持相关国际协定和框架的执行”。[9]《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2025》提出“扩大东盟海上合作,全面解决海洋问题”,“促进国家、区域和国际海上合作机制之间的联系”。[10]正因如此,东盟近年来通过构建内外多层次合作框架和平台,借助对话伙伴的力量,积极致力于南海海洋治理机制建设,进而在区域合作中确立、维持其中心性(ASEAN’s Centrality),[11]其中对南海海洋治理最主要的贡献便是创设了东盟海事论坛及其扩大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依据《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于2010年成立了东盟海事论坛,其为东盟国家、中国等开展海洋安全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提供了全新平台。东盟海事论坛及其扩大会议的议题涵盖范围较广,包括渔业合作、科学考察、打击海盗、海事安全等涉及海洋合作的领域,不仅有助于维护南海海洋安全,还提升了东盟在区域中的海洋治理能力。东盟地区论坛是东盟开展南海海洋治理的又一重要平台。作为目前亚太地区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平台,东盟地区论坛自1994年成立以来已举行了25届外长会议。2018年8月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5届东盟地区论坛上,各国外长一致同意加强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以及其他地区机制的合作,从而有效应对跨国犯罪、海洋安全、自然灾害等挑战。该机制的创设无疑为推进和规范南海海洋治理提供有力保障,为各方在落实海洋治理方面加强共识并深入开展海洋合作平添助力。
中国与东盟或东南亚部分国家就南海海洋治理展开务实合作并取得积极成果,合作逐渐呈现出双多边同时推进、多领域同时开展的新局面。在双边层面,中国与马来西亚于2009年签署了政府间海洋科技合作协议;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2012年修改和续签了《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中印海上合作基金,并联合建立了“比通联合海洋生态站”;中国与越南于2013年签署了《关于开展北部湾海洋及岛屿环境综合管理合作研究的协议》,并于同年成立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积极推进中越海上共同开发;中国与泰国分别于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签署了《关于海洋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建立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的安排》以及《海洋领域合作五年规划(2014-2018)》。
在多边层面,2011年,中国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用于南海环境保护、科学考察、航行安全和搜救等;2012年,中国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上发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并于同年发布《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2016年发布《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6-2020)》;2016年9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审议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两份成果文件;2017年11月,东盟各国与中国通过了《未来十年南海海岸和海洋环保宣言(2017-2027)》。截止2018年底,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共识,并形成了“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在2019年5月召开的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7次高官会议上还审议更新了《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16-2021年工作计划》,确定了一批新的海上务实合作项目。
(二)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问题审视
尽管当前南海地区海洋治理已取得一定成绩,但相较于全球海洋治理的整体水平而言,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建设的深度或广度都有所不及,亦无法满足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现实需要,具体问题可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
1.治理主体乏力、作用有限
[23] 张丽娜、侯丽维:《南海区域合作的法律困境及对策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01-102页。
首先,南海沿岸各国由于地理位置差异和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对南海海洋治理存在诸多分歧,进而导致南海海洋治理主要行为体日益乏力。一方面是南海沿岸各国与海洋关联度不同从而引发的海洋利益享有不均与海洋治理责任均等分配之间的矛盾。从南海海域周边国家来看,拥有狭长海岸线以及实际控制较多南海岛礁的越南、群岛国菲律宾、中国以及马来西亚在开发和利用海洋上存有优势。就地理位置来说,这些国家相较于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与南海海域的关联度和紧密度方面更胜一筹,致使上述两类国家在海洋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各不相同,进而导致南海沿岸九国事实上享有海洋权利的不平等,因此很难通过治理责任均等分配来步调一致地推进南海治理合作。另一方面,南海沿岸各国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资金上的匮乏导致海洋治理能力不足。除新加坡以外,其他南海沿岸国均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涉及海洋经济的传统工艺技术依旧落后、海洋基础设施还很薄弱、海洋经济的配套产业尚不完善。以印尼为例,虽然印尼作为东盟经济的“领头羊”,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140个国家中,印尼各项基础设施指标排名均较为靠后,其中,基础设施总指标位列第81位,港口建设第82位,电力供应第86位。[12]可见,南海多数国家往往“自顾不暇”,出于自身发展需求对于海洋的破坏力明显高于其保护能力,海洋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较弱。
其次,东盟作为南海海洋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在海洋治理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有一定局限性。坚持协商和包容性原则的东盟多主张宽泛的文本和非正式协议,在东盟内部达成的协议和共识往往不具有强有力的约束性。东盟前任秘书长鲁道夫·塞韦里诺(Rodolfo C. Severino)认为,在推进其事业的进程中,东盟更倾向于非正式的、松散的安排,而不是条约和正式的协议,它主要依靠领导人、高官们的个人关系以及同行之间的影响,而不是依靠制度。同时,它依靠协调一致和共同利益而不是具有约束性的承诺。[13]这种安排固然有一定利处,但在面对其所制定的南海治理议案和框架时,东盟国家在形式上愿意接受和在事实上遵守并服从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盟在南海海洋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政治外交形势的风云变化,南海海洋权益如今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美、日等域外大国凭借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优势执意介入南海问题,东盟成为域外大国争相拉拢的对象,[14]使得东盟主导南海海洋治理效用的有限性开始凸显,这也不利于南海周边国家积累政治互信从而开展更深入的南海区域治理合作。
图3结果表明,随着pH值的增大,两种捕收剂对石英及绿泥石的浮选回收率逐渐增大,而对赤铁矿的浮选回收率降低,说明两种药剂在高pH值条件下都可作为铁矿反浮选捕收剂使用。由图可以看出,在所研究的宽pH值范围内,两种捕收剂对石英、赤铁矿的捕收性能相似。当pH值大于7.0时,CM-5对绿泥石的选择性浮选回收效果明显好于油酸钠。
再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海事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虽然在南海海洋治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对于南海开展的计划项目治理领域和作用影响毕竟有限。例如,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的“扭转南中国海和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项目(2000-2009年)、“执行南中国海战略行动计划”项目(2014-2019年)[15]旨在对南海海洋环境保护(主要涉及3个领域:海岸栖息地的退化、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以及陆地污染)展开合作治理。而其他由上述全球性国际组织制定与执行的区域海洋计划,例如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东亚海区域海洋计划等由于所涉地域范围较广,对于南海区域的海洋治理针对性不强、作用甚微。
2.治理客体局限、领域较窄
全球海洋治理客体即全球海洋治理所指向的对象,是指已经深刻影响或将要影响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海洋问题,其不仅覆盖面广、内容繁杂,而且兼具低政治性、高政治性的基本特性——前者是指直接关系到人类共同利益的低政治敏感性领域,包括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等;后者是指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海洋安全、海洋争端等领域。
一方面,南海海洋治理面临着治理客体局限性的制约,治理对象多集中于少数低敏感领域。就区域性合作治理而言,依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倡导的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可探讨或开展以下五大领域的海上合作: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而在这些敏感性较低的涉海领域里,南海海洋环保领域的合作治理实践往往较为集中,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扭转南海和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项目、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东亚海区域海洋计划等,其他涉海领域的区域治理实践则十分零散。从国家间合作治理来看,目前中国已与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海洋部门签署了双边合作备忘录,所涉及的内容也属低政治性领域居多,且合作的水平和层次尚浅。
另一方面,南海海洋治理的实践范围尚未涵盖日益兴起并引起特别关注的新兴海洋问题,比如生物多样性减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海洋微塑料污染等。首先,南海作为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对于生物资源养护与管理方面的海洋治理较为欠缺。南海是典型的半闭海,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3条对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应开展的合作领域第1款首推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以海洋生物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类——渔业资源为例,南海渔业合作较成熟的区域除了有政府协定《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及其补充议定书》作为强有力支撑的中越北部湾地区以外,南海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尚未建立起系统的渔业合作治理机制。其次,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正遭受严重破坏,亟待展开有效治理。由于受南沙群岛岛礁归属争议和海洋划界争端的影响,加之受水下考古专业技术要求和资金人力限制,任何国家欲凭一己之力无法胜任该项保护工作。[16]而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采用公司合作方式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打捞且允许商业打捞,如此一来更加剧了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肆意破坏与掠夺。[17]最后,面对海洋乃至全球环境的新兴污染源——微塑料的不断扩散与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急需将此纳入南海海洋治理范围。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开阔大洋漂浮大块塑料和微塑料总重量约26.9万吨,[18]时间一久这些塑料垃圾将会严重威胁海洋生态系统。由于海水的流动性较强,南海沿岸国家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从而在该领域切实展开双边或多边合作治理。
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在保证混凝土抗压、抗渗、抗冻指标的前提下,可适当掺入一定量的优质粉煤灰,不仅可以明显改善混凝土拌和物的工作性能,还可以起到抑制混凝土碱-集料反应的作用。优质粉煤灰掺入混凝土后,第一,可稀释水泥中的碱含量;第二,在掺入粉煤灰后,可优先生成碱-钙-硅胶凝体,可达到延缓碱-集料反应的速度,从而减小混凝土内部的膨胀应力。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掺入优质粉煤灰,其活性SiO2含量必须达到能够足以抑制或减缓碱-集料反应的要求。
[26] 杜兰、曹群:《关于南海合作机制化建设的探讨》,《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84页。
当物料为横观各向同性材料(秸秆类与木质类生物质原料)时,可以认为模孔内物料在同一截面内任意方向上具有相同力学特性,因此 Ey=Ez,νxy=νxz,νyx=νzx,由于弹性模量与泊松比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3.治理机制薄弱、效果不彰
[3] Robert G. Ridley, “Putting the ‘partnership’ int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HO Drug Information , Vol. 15, No. 2 (2001), p. 57.
海洋治理机制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指依靠什么治理或如何治理,主要包括治理目标、治理制度和治理效果3个方面。
第一,南海是全球海洋治理目标缺失的缩影,[19]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南海沿岸国家缺乏开展海洋治理的意愿,其治理主体并未就海洋治理达成高度的共识从而形成统一的治理目标。进一步分析可知,南海沿岸国多为发展中国家(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以海洋油气、渔业海产、涉海旅游、海港及运输等产业为主要构成的海洋经济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越南为例,根据越共中央所通过的《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中明确指出,“海洋经济必须要占到国家GDP的半壁江山(一半以上)”,它具体包括“努力争取在2020年使海洋经济占国家GDP的53%-55%,并使海洋经济占国家总出口金额的55%-60%”。[20]正是由于海洋经济带来的丰厚收益成为南海沿岸这些本身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无法摆脱的依赖,因而在面对南海海洋资源的无序、过度开发以及生态环境退化等一系列亟待开展区域海洋治理的问题日益严重时,南海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显示出强烈的治理意愿。[21]这一点从南海沿岸国对于协定选择性加入的态度中也能得到印证:《迁徙物种公约》除了唯一的缔约方菲律宾以外,南海其他沿岸国对待该公约并未有积极反应;对于《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和《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及管理措施的协定》,南海沿岸国更是无一例外地都未批准通过。[22]这些做法从侧面折射出南海沿岸国对于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消极意愿和心态,更加剧了南海地区海洋治理目标的分散化,使得南海陷入各自为治的局面。
从上表可看出,在1-1不退位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六年级,他们之间存在差异性.其中五、六年级处于同一级别,且为最高级V级.在2-1不退位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他们之间存在差异性.其中五、六年级处于同一级别,且为最高级IV级.在2-1退位中,6个年级所处的等级较其他两种减法大致有所降低,一年级,二、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之间存在差异性.其中五、六年级处于同一级别,且等级最高为III级.在减法的3种口算速度测评中,一年级均为最低等级,为I级.
第二,南海海洋治理的法律基础较为薄弱、硬法制度供给不足。通过梳理南海海洋治理的各种法律文件可以发现,无论是普遍国际法层面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是区域国际法层面最为重要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或是双边条约层面中国与越南签署的《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署的《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与马来西亚签署的《海上科学技术合作协议》等,[23]目前南海海洋治理仍以没有法律拘束力的“软法”为主,“软法的集束化”(cluster in soft law)表现尤为明显,换言之,软法在南海海洋治理中呈现出一种“集中”的“制度丛”(system plexus)现象。[24]“硬法”的严重缺位使得南海海洋治理缺少强制性条约的约束,导致南海不论是在全球性合作治理层面,还是区域性合作治理或国家间合作治理层面,都缺少坚实的法律基础作为其海洋治理的重要保障。
第三,南海海洋治理的效果差强人意。评估海洋治理的效果重点关注机制的绩效,即机制的有效性。从一般层面上看,有效性是用以衡量社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25]反观南海海洋治理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如下。早在1990年印度尼西亚发起的非官方地区对话平台“处理南海潜在冲突研讨会”,其主要成员为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旨在南海问题上寻求协商对话和促进南海地区信任措施建设,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该机制影响式微,甚至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26]又如,自2005年中、菲、越三国签署的旨在南海进行联合地震勘探的工作协议,由于菲律宾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2008年之后便被搁置。同样地,为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内的合作措施与项目,中国成立了海洋科研和环保、航行安全与搜救、打击海上跨国犯罪等3个专门技术委员会,并得到了东盟各成员国的积极响应,但是相关领域的海上合作至今未得到有效落实。由上述看出,南海海洋治理更多停留于形式上的安排,实际治理效果却不明显,仍面临着“共识多、落实少”的治理困境。[27]再如,由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于2004年11月签订了《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作为亚洲首个政府间促进合作旨在打击海盗和武装劫掠的区域协定,《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对于加强南海地区海上犯罪的治理意义重大。然而根据亚洲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区域合作协定信息共享中心(ReCAAP ISC)在2019年1月发布的海盗事件2018年度报告显示,南海地区在2007-2018年发生的海盗和武装抢劫事件总数量为161起,其中实际事件131起,未遂事件30起。也就是说,2007-2018年南海地区平均每年发生约13.4起海盗和武装抢劫事件,虽然近几年数量有所降低,但总体而言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在2014年甚至还达到42起,[28]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南海地区海盗和武装抢劫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得到有效抑制,南海地区海上犯罪的治理效率有待加强。
研究发现,低浓度硝酸盐(10 mmol/L)能够促进小麦根系伸长生长,而高浓度硝酸盐(60 mmol/L)反而会抑制小麦根系生长,再次证明了硝酸盐对根系生长发育的双重作用[3,4]。低浓度硝酸盐能够诱导根部O2-·浓度升高,而一定浓度ROS能够促进细胞壁松弛,有利于细胞伸长生长[14]。高浓度硝酸盐诱导小麦产生大量O2-·,使得细胞内氧化还原动态平衡改变,同时也会引起细胞内物质与结构损伤,最终表现为抑制小麦幼苗生长。
三、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优化路径
[11] Amitav Acharya, “The Myth of ASEAN Central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 Vol. 39, No. 2 (2017), pp. 273-274.
(一)由易渐难:鼓励多领域共同推动的“蓝色”合作
基于全球海洋治理客体的多样化与跨国性,海洋治理任务和形势变得更为严峻,亟待解决的海洋公共问题数量日益增多且涉及的层次和领域也异常广泛。当前,南海需要大力拓展海洋治理的范围,深入开展多领域辐射的蓝色合作以此来助力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
第一,从南海低敏感领域逐步转向次敏感、敏感领域海洋合作治理。在具体议题上,可以从深化海洋科学合作、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等相对低敏感的领域率先入手,低敏感领域合作产生的“外溢效应”或将带动其他领域合作,[29]然后逐渐走向海上安全合作、海洋技术开发合作、海洋数据信息交流共享等次敏感领域,最终要触及海底资源开发共享、海洋政策协调开发等涉及主权的敏感领域。[30]由于南海各沿岸国之间围绕岛礁主权、海域划界、资源争夺和通道安全等海权争端所涉利益重大、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在南海较为敏感领域开展海洋合作治理并非易事。因此,可借鉴南海部分国家在海上安全合作、海底资源共同开发方面的海洋合作经验,为南海各沿岸国在次敏感、敏感领域海洋合作治理提供有益参考。譬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作为苏禄海的沿岸国,存在划界争端。苏禄海地区充斥着海盗、绑架、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而2017年的马拉维危机更是暴露了海上安全合作的缺乏。三国由此开展了海上联合巡逻执法,虽然这种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为南海沿岸各国开展次敏感领域的海上安全合作从概念发展到实操阶段提供了借鉴。再如,马来西亚和泰国采用“超国家管理模式”共同开发泰国湾争议海域,马泰两国总理共同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4) 谅解备忘录全称为《关于为开发泰国湾两国大陆架划定区域海床资源而建立联合管理局的谅解备忘录》。 其决定将泰国湾争议海域的划界问题搁置50年,在双方海域主张重叠区域建立共同开发区。(5) 具体做法是由两国建立一个由两国代表组成的联合管理局,从备忘录生效之日起50年内负责争议区海床和底土非生物自然资源的探测和开发,该管理局在共同开发中产生的任何费用和获得收益均由双方平摊和平分。 继上述备忘录达成之后,两国在该争议地区共同开发进展顺利并取得显著成效。(6) 据马来西亚-泰国共同开发管理局统计,自1994年以来,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争议海域一共开发了63个探井和114个开发钻井。参见邵建平:《东南亚国家处理海域争端的方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02-106页。 同样地,马来西亚和越南采用“联合经营模式”共同开发泰国湾争议海域,(7) 具体做法是由两国共同签署的《马来西亚和越南在两国大陆架重叠海域特定区域内实施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的谅解备忘录》中规定马越两国同意分别指定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PETROVIETNAM在指定海域实施“共同开发”。参见邵建平:《东南亚国家处理海域争端的方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06-108页。 其共同开发的实践效果比较成功,不仅给越南和马来西亚带来了经济收益,还有助于两国关系互信的建构。简言之,可参考上述南海部分国家之间共同开发的案例和相关管理经营模式,为南海沿岸九国在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提供实质性方案和具体思路,进而为南海各沿岸国在敏感领域进行海洋合作治理开展积极探索。
一个人的健康成长,是离不开静的。邹韬奋1928年12月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静》的文章,他说道:“有担任大事业魄力的人,和富有经验的人,富有修养的人,总有一个共同的德性,便是静。我们试细心体会,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问,魄力,经验,修养等的程度,往往和他们所有的静的程度成正比例。”
第二,开拓新兴海洋领域南海海洋治理实践与合作。以上文所提及的生物多样性减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海洋微塑料污染这几个新兴海洋领域为例,分别施以相应有效机制来推动这些新兴海洋领域的深入治理。首先,尽快建立南沙海洋保护区。南沙群岛位于珊瑚三角区内,其不仅是南海最大的一组岛屿,还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而建立南沙海洋保护区不仅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11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4.5中的规定,而且还有助于恢复衰退的南海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其次,倡导南海沿岸各国签订《南海水下文化遗产合作保护协定》以建立南海水遗合作保护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建设南海统一的水下文化遗产数字化平台,实现有关数据信息交流共享,将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海洋治理轨道。最后,在微塑料污染领域,由南海沿岸各国合作商讨制定南海海域科学统一的微塑料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控制标准,以控制陆源塑料垃圾为抓手在南海各沿岸国推行具有可操作性的“限塑令”,逐渐探索可以完全降解的植物塑料、天然塑料等材质成为有机塑料的替代品,切实开展微塑料污染的海洋治理。事实上,在南海涌现的新兴海洋问题远不止上述3类,而共建合作保护机制则是南海各领域海洋治理“善治”的核心所在,更是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稳定锚和压舱石。
计算上述四个结果的关键点在于如何推算出泵效水平、理想沉没率和安全下泵深度三个基准值,就很容易计算出上述结果。
(二)和谐共存:培育多元化紧密互动的“伙伴”主体
全球海洋治理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过程,其真正实现需要依靠各种行为体的通力合作。因此,形成主权国家、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元行为体协调互动、合作共治的海洋治理格局是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前提保证。
[4] 朱璇、贾宇:《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期,第50-59页。
另外,可借助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和崛起中的海洋强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影响力,为南海展开合作治理添砖加瓦,进而为实现蓝色伙伴关系凝聚共识和增强互信。当前,中国不仅是国际海事组织A类理事国,还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A组成员,多年来中国一直以高票数当选联合国政府间海委会执行理事会成员国,凭借着中国在涉海国际组织地位和话语权的逐步上升,可为南海地区在海洋治理领域相关议程设置、规则制定以及机制创新方面贡献经验、智慧和力量。与此同时,中国还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向东盟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设立总额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等,为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海洋合作与南海地区海洋治理提供助力与保障。可见,中国在促进南海地区开展合作治理以及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方面扮演着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关键角色。
其二,在东盟的基础作用之上,努力将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治理主体作为一种补充力量纳入到南海海洋治理的网络之中,通过其深度参与和广泛合作推动多元治理主体紧密互动从而形成南海海洋治理的合力。譬如,积极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南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涉海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保障。亚投行作为中国政府主导建立的政府间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其重点是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于印尼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强调“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32]再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分委会(WESTPAC)(9) 该组织的主要职能是执行海委会全球性海洋科学、海洋观测服务项目在西太地区的开展,并根据本地区成员国的共同兴趣,发起、推动和协调适合本地区的海洋科学、观测服务及能力培训项目。 近年来发起了一系列地区合作项目,包括“西太平洋海域海洋灾害对气候变化的响应项目”“东南亚海域海洋预报系统”等,应充分发挥该组织在南海海洋治理上述具体领域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深化蓝色伙伴关系的互信与合作发展。诸如此类的区域组织还有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依据《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管理和养护公约》的规定而建立的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委员会等,这些组织为南海海洋治理在完善合作机制与搭建合作平台方面提供了有益助力。此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东南亚国家智库共同发起建立的“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作为地区国家涉海研究合作的新范式,通过经常性召开国际研讨会、学者访问交流等形式深化国内外涉南海研究机构的联系,其不仅为南海海洋治理提供智力支撑,还为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创造良好、和谐的国际环境。
(三)协同共治:保障多层级合作联动的“关系”结构
多元多层合作治理被认为是全球海洋治理在运作中最为现实且最具普遍意义的治理模式,从全球海洋治理所涵盖的全球性合作治理、区域性合作治理和国家间合作治理3个层面上来看,[33]南海海洋治理若要形成国际、区域和国家多层级合作联动的协同共治结构,需要在法制建设的基础之上提升海洋治理的实效性,以此来保障南海海洋治理的“善治”以及蓝色伙伴关系的深化与发展。
一方面,推动南海海洋治理在现有“软法主导”的框架之下,逐渐向“软硬平衡兼施”的模式转变。放眼望去,无论是南海区域性合作治理还是国家间合作治理,其绝大多数以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合作协议、海洋计划等形式的软法协议达成。一旦法律制度的安排在义务(obligation)、精确性(precision)和授权(delegation)3个维度中的一向或几向维度上受到弱化时,“软法”王国便出现了。[34]诚然,软法较为灵活、富有弹性,与硬法相比更容易达成,[35]但软法最多还是全球治理的补充,而非主体。普罗斯佩尔·威尔(Prosper Weil)就指出软法使用程度增加“可能会动摇整个国际规范体系,将其变为一个不再服务于自身目的的工具”。[36]从长远来说,软法最主要的价值在于推动硬法形成的过程,作为硬法的先导,[37]甚至是刺激硬法形成的因素。从南海海洋治理的现实状况来看,采取“软硬平衡兼施”的模式会是最优选择:在海洋安全、海洋争端等高政治性领域有拘束力的协议难以达成,以软法先行较为适合;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等低政治敏感性领域则从软法逐渐过渡为硬法,以先制定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和行动计划为起点,在其获得广泛认同后,继续寻求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和议定书。这个软法过渡为硬法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操作和执行:第一阶段是从寻求科学认识的一致性到共同制定战略行动计划的过程,它是一个将科学结论与政策措施相结合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固化政策和措施,并将其转化为法律的过程,它为签订公约打下政治基础。[38]由此一来,充分发挥软法和硬法各自的优点,最大程度上实现南海地区在不同海洋领域的有效治理,为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平添砝码。
另一方面,借鉴闭海或半闭海区域海洋治理公约的立法模式,导入南海海洋治理的有效机制来巩固南海海洋治理的法治成果。闭海或半闭海区域海洋治理公约主要遵循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以《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为典型的“地中海模式”,一种是以《保护波罗的海海洋环境的赫尔辛基公约》为典型的“波罗的海模式”。[39]由于采用“波罗的海模式”要求签署公约的沿岸国将承担同样的保护区域海洋环境的义务,采取相同的保护措施并执行统一的污染防治标准,往往对成员国有较高要求,而根据前文所述,南海各沿岸国因所处地理位置差异和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对南海海洋治理存有诸多分歧,通过治理责任均等分配、采取相同措施和执行统一标准来推进南海合作治理存有较大困难且极不现实,故针对南海沿岸各国的实际情况在海洋治理领域应借鉴“地中海模式”。(10) 所谓“地中海模式”是指区域海环境治理法的法律框架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框架公约,另一部分是附加议定书的立法模式。框架公约、议定书以及附件都是整个文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框架公约规定了沿海国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国家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就必须签署框架公约;议定书规定的是针对具体污染形式的技术条款或是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特殊规则。缔约国签署框架公约时,必须至少同时签署一个议定书,并有义务在条件允许时参加其他议定书。地中海沿岸国于1976年2月16日缔结了《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并于1995年修订该公约。时至今日,沿岸国共签署了7个议定书。 参照该立法模式,可允许南海沿岸各国在签署海洋治理框架公约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发展水平自由选择签署一项或几项议定书,在使各国接受南海海洋治理基本原则和基本义务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团结各国力量在南海合作治理中步调更加一致、磋商更有效率,从而避免“搭便车”的现象出现。[40]同时,环境规划署、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还可为南海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及深入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提供资助,使其逐渐达到议定书要求的保护水平,最终加入符合其自身需求不同海洋领域的议定书。这种“框架公约+议定书”地中海模式的制度安排使二者交汇融合、互为补充。美国学者基欧汉(Keohane)等人就提出了“制度复合体”(regime complex)治理模型,以避免制度全面性(comprehensive)中的困难,这也有助于在不同问题的处理上更加灵活,更能适应客观情势的变化。[41]由此一来,不仅增强了南海不同海洋领域治理机制的契合度和善治程度,还为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凝聚意愿和增强互信奠定坚实基础。
注释:
[1] 《国家海洋局倡议的边会在联合国海洋大会首日召开》,国家海洋局网站,2017年6月12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06/12/content_5201829.htm。
[2] 高悦:《2017厦门国际海洋周开幕》,《中国海洋报》2017年11月6日,第1版。
式中,W1为国有水管单位计量点水量,m3;P1为国有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执行价),元/m3;P2为末级渠系水价,元/m3;其他变量同上。
对ZK1号孔进行了取样测试,按孔深每100 m取一组岩样,测试项目:密度、导热率、放射性元素铀钍钾含量,其中密度与导热率测试工作在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测试中心完成,导热率采用瞬态平面热源法、DRE-2C导热仪进行测试的;放射性元素铀钍钾含量测试工作在广州澳实分析检测公司完成,其中放射性元素铀钍采用了ME-MS法测定;放射性元素钾采用了K-XRF法测定。
其一,南海沿岸国家应该在海洋治理领域坚持互利合作、充分利用各国的优势共同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推动各方就构建“蓝色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诚然,南海沿岸国家发展程度各异,但要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具体务实、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31]针对南海地区多数国家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困境,可以发挥南海地区唯一发达国家新加坡以及新兴大国中国在海洋治理实践中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强化南海各沿岸国家海洋治理的共同目标和意愿。众所周知,新加坡在很多领域拥有着其他大多数亚洲国家难以企及的竞争力,被誉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一直致力于发展环境友好型海洋经济,其政府成立的环境部将海洋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融为一体,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弱经济发展对海洋环境带来的消极影响。(8) 2011年新加坡海事及港口管理局(MPA)颁布了一份全面的环保倡议—新加坡海事绿色倡议,该倡议于2016年新增了两个项目,分别是绿色意识项目,关注对可持续运输方式的探索;以及绿色能源项目,旨在促进海洋清洁燃料的使用及节能操作措施的运用。 新加坡拥有的成熟资本市场与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可为南海沿岸发展中国家提供海洋治理的技术与资金援助,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劳动力供给数量庞大,它们可以向新加坡提供海洋治理领域的劳动力支持。由此双向互动、互利共赢,从而进一步加强南海沿岸各国积极开展海洋治理的意愿和能动性,促使南海九国共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蓝色命运共同体,为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5] 贺鉴、王雪:《全球海洋治理视野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2期,第71-82页。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1页。
[7]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8] 梁甲瑞、曲升:《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4期,第57页。
教育如何适应并推动新型城镇化?城乡教育如何打破二元结构实现一体化发展?要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首先要坚持科学的教育规划和专业性的指导,将保障制度和体制的深入改革作为动力,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线,对以城市促进农村发展的加强辐射能力,逐渐提高城市教育在城乡一体化进行中的承载能力,抓好城乡建设双向沟通,体制机制的动态平衡这两个关键点。基于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教育一体化才能够应对各种挑战。
[9]ASEAN SOCIO -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 , March 2016, https://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2/05/8.-March-2016-ASCC-Blueprint-2025.pdf.
[10]ASEAN POLITICAL -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 , March 2016, http://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2/05/ASEAN-APSC-Blueprint-2025.pdf.
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面对南海地区海洋治理的严峻形势与挑战,必须从鼓励多领域共同推动的“蓝色”合作、培育多元化紧密互动的“伙伴”主体、保障多层级合作联动的“关系”结构等3个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从而为推动南海构建“蓝色伙伴关系”贡献有益方案。
[12] 曲凤杰等:《走向印度洋:“丝绸之路经济带”东南亚-南亚-印度洋方向重点国别研究》,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
[13] [菲]鲁道夫·C. 塞韦里诺著:《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来自东盟前任秘书长的洞见》,王玉主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14] 韦红、颜欣:《中国-东盟合作与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构建》,《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5页。
思维方法的暗示指展示教师的思考和分析。例如,针对温室无土栽培所需控制的因素,教师提醒先分析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矿质代谢、水分代谢的影响因素的思考方法。这样暗示学生养成一定的分析方法,使其能力得以提高。又如,针对生物学中的元素→物质→结构→功能,通过高考习题的分析加以总结。
[15] 于铭、徐祥民:《世界区域海治理立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9-100页。
[16] 石春雷:《论南海争议海域水下文化遗产“合作保护”机制的构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2页。
[17] 刘丽娜:《中国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
[18] 兰圣伟:《急需加强海洋微塑料监测调查》,《中国海洋报》2018年8月2日,第1版。
[19] 袁沙:《全球海洋治理:从凝聚共识到目标设置》,《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3页。
[20] 成汉平:《越南海洋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21][27] 吴士存、陈相秒:《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4期,第32、31页。
[22] 陈嘉、杨翠柏:《南海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反思与前瞻》,《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35页。
全球海洋治理主体是指在解决全球性海洋问题过程中具有权威性并具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体,通俗地说就是由谁来治理。具体而言,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纵观南海海洋治理主体可知,其主要存在以下3个问题。
[24] 朱立群、[意]富里奥·塞鲁蒂、卢静主编:《全球治理:挑战与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25] Oran R.You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 :Causal Connections and Behavioral Mechanisms ,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p. 3.
总体而言,在有限的低政治性海洋领域展开的治理实践并不能满足南海日趋严峻的海洋治理的现实需要,亟待拓展南海海洋合作与治理的广度与深度,尤其加强对除海洋环保以外的海上搜救、防灾减灾、海洋科研等其他低政治领域以及其他新兴海洋领域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的建设完善。
[28] ReCAAP Information Sharing Center, Annual Report for 2018 , http://www.recaap.org.
铜仁春旱不多,一般不影响花生适期播种、正常出苗和幼苗生长。但夏季伏旱多有发生,大面积种植花生区应加强基础设施,做到能排能灌,同时,加强空中水资源开发利用,政府主导做好人工干预天气工作。
[29] [英]安特耶·维纳、[德]托马斯·迪兹主编:《欧洲一体化理论》,朱立群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64页。
[30] 傅梦孜:《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中国海洋报》2018年12月27日,第2版。
[31]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第2版。
[32]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
[33] 崔野、王琪:《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12页。
[34] Kenneth W.Abbott and Duncan Snidal,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54, No. 3 (2000), p. 422.
[35] Shih-Ming Kao,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alysis of Existing Practices and Prospects”,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 Vol. 43, Iss. 3 (2012), p. 285.
[36] Prosper Weil, “Towards Relative Normativ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 77 (1983), pp. 413-442.
[37] Ulrika Mörth, Soft Law in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4, p. 191.
[38][39] 于铭、徐祥民等:《世界区域海治理立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1-92、93-96页。
[40] 李聆群:《南海渔业合作:来自地中海渔业合作治理的启示》,《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130页。
[41] Robert O.Keohane & David G.Victor, “The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 Vol. 9, Iss. 1 (2011), pp. 18-19.
The Construction of“ Blue Partnershi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HOU Li-wei ZHANG Li-na
( Law School,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Hainan)
Abstract: The proposal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Building Blue Partnership” initiative has theoretically promoted a new roun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implemented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strategy of ocean power, and in practice has injected a strong new impetus to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and provided a new dimension and paradigm for China’ 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lue partnershi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is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weak governance subjects, object limitations and the weakness of mechanis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it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encouraging the“ blue” cooperation promoted by multi-field, cultivating the multiple and closely interactive“ partner” subjects, and guaranteeing the“ relationship” structure of multi-level cooperation linkage.
Key words: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South China Sea, “ blue partnership”
中图分类号: D8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9856( 2019) 03- 0061- 12
收稿日期: 2019-02-12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南海岛礁所涉重大现实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6ZDA073);2019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陆海统筹视阈下海南省海岸带综合管理法治保障研究”(Hyb2019-20)
作者简介: 侯丽维,女,四川营山人,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海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张丽娜,女,辽宁新民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晨 曦]
